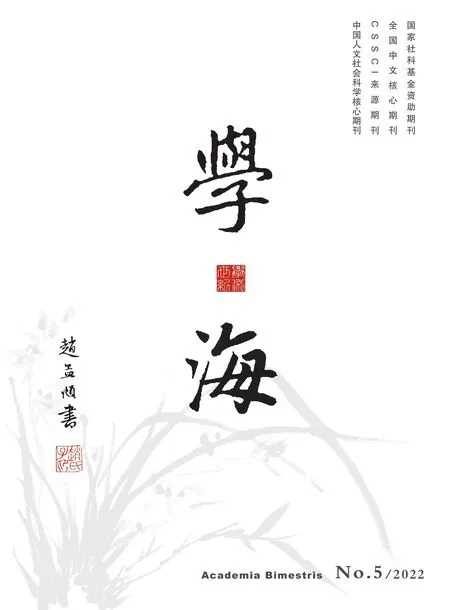高空抛物刑事责任的类型化界定
陆俊杰
内容提要 面对屡禁不止的高空抛物现象,刑法应当及时跟进。相关司法意见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高空抛物罪的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的需求,但在认定高空抛物案件的刑事责任时仍须进行类型化判断。通常而言,日常生活中高空抛物侵害的法益并非完全相同,未必都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司法实践应当慎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基于类型化的分析,应当拓展有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犯罪的适用,并善于用竞合论妥当评价高空抛物行为的刑事责任。明确纵容者、房屋出租者、物业怠于履行防范义务等相关主体的刑事责任边界,形成系统的认定高空抛物的归责体系。
问题的提出
在高楼林立的现代社会,高空抛物的现象屡禁不止。长期以来,高空抛物的行为主要被视为民事法律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并且在无法确定抛物者时,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来实现风险的分散承担。然而,在风险叠加的现代社会,现代化的副作用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促成对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①通过刑法来回应现代社会风险的声音不绝于耳。②尽管在刑法领域,对于诸如“风险刑法”的称谓与学术意义仍存在不同的争议,③但对于刑法回应现代风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已然成为共识,预防性刑法观的学术命题开始成为刑法理论转向的一个重要航标。④高空抛物行为通过私法的方式处理,在现实中已显得捉襟见肘,高空抛物致人伤亡的案件屡见报端,这就倒逼人们不得不转换视野,寻求以公法的方式规制高空抛物行为。
早在2019年8月23日,中国法学会组织召开高空抛物法治工作座谈会,就有与会专家主张在今后修正刑法时,有必要将高空抛物行为纳入其中。此后不久,最高司法机关也制定了相关司法解释,2019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较为明确、系统地规定了高空抛物行为的刑事责任。高空抛物作为犯罪处理首次具有了较为明确的司法适用依据。2020年12月26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高空抛物罪,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关于高空抛物犯罪的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意见》出台之前,高空抛物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犯罪的情况即已存在。通过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早在2012年,地方法院就有相关的刑事判决。⑤此后,高空抛物的有罪判决不断增加。可以说,《意见》只是对实践中高空抛物有罪处理的进一步总结和归纳,为裁判实践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导依据,并非开高空抛物犯罪化之先河。从《意见》的内容看,对高空抛物行为的认定采取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立场,即在综合考虑高空抛物行为的动机、抛掷物的具体情况、危害结果等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刑法分则的具体罪名定罪处罚。
从形式上看,《意见》在对司法经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明确了高空抛物的具体裁判规则。但《意见》中的部分内容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例如,故意从高空抛掷物品是否一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尽管《意见》罗列了6大罪名,但除了上述罪名之外,高空抛物是否还涉及其他罪名?若构成其他罪名,是按照数罪并罚还是竞合处理?没有及时阻止他人高空抛物的行为是否也可能构成犯罪?物业服务者怠于履行监管责任的,有无构成犯罪的可能?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高空抛物罪后,上述问题的争论并未因此平息。例如,关于高空抛物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具体区分,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鉴于实践中高空抛物案件表现出不同的类型,如何厘清高空抛物罪与关联罪名之间的关系,仍需在理论上予以廓清。
高空抛物行为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反思
无论是根据《意见》还是《刑法》第291条第2款的规定,高空抛物行为均可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⑥换言之,高空抛物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存在竞合的空间。然而,在本文看来,竞合论的立场值得反思。
从客观危险来判断,高空抛物和高空坠物造成的客观危险其实并无二致,倘若肯定高空抛物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高空坠物在造成相同结果的情况下,同样应当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二者的区别只是犯罪的主观方面:故意与过失。然而,《意见》并未做出如此规定,根本原因是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高空抛物,其思路存在问题。
本文认为,就高空抛物而言,抛掷的物品通常而言并非具有爆炸性的物品,不可能存在危及公共安全的危险。即便抛掷如煤气罐等可能产生爆炸的物品,完全可以按照爆炸罪论处,而不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理由是,爆炸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同时被规定在《刑法》第114条中,二者的法定刑完全相同。倘若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则不仅可能会架空爆炸罪的规定,而且会扩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范围。基于刑法明确性的要求,在有明确罪名可以适用的前提下,应当排斥口袋性罪名的适用。据此,不应将高空抛物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了更清晰展示此种处理方式的弊病,下文结合裁判实践中的具体素材,予以论证。
(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件特点归纳
按照《意见》第5条第2款的规定,“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114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处罚。”司法实践中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判例颇不少见,通过案件检索可以发现,此类案件的发生地均在闹市区或者居民区内,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多数判决采取的是结果主义立场,造成损害结果的,认定为本罪。常见类型为,造成楼下车辆被砸坏、其他住户的外墙热水器排烟管、抽油烟机排气管受到损害,以及致人死亡(尚未查询到致人重伤)。但是,没有造成损害结果的高空抛物行为也有被认定为本罪的情况,只是此类案例数量极少。如在“杜荣高空抛物案”中,被告人杜荣在闹市区持续高空掷物和破坏正在运行的电梯控制设备,且在已经告知造成他人被困电梯的情况下,仍继续实施上述行为。法院认为,被告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⑦
第二,所抛物品的类型较为复杂,通常具有一定的破坏力。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判决中所显示的高空抛掷的物品有:煤气罐、铁锤、曲线锯、戒纸刀、建筑垃圾、钢筋、酒瓶、花盆、玻璃罐、灭火器、砖头、轮胎、铁锹、木板等。既有单纯抛掷其中一种物品,⑧也有抛掷多种物品的。⑨
第三,部分裁判文书明确表明行为的持续性或者反复性,考虑高空抛物的次数,以此说明行为的危害性。例如,有的裁判文书在裁判理由中表述,被告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高空抛物,或者持续高空抛物,据此认定行为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⑩
第四,有判决认为,未造成人身伤亡但造成财产损失的高空抛物行为同样可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例如,在“赵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中,被告人赵某某因琐事纠纷,为发泄怨气,将加重行李箱、雨伞等物品,数次抛出窗外,砸坏他人轿车。法院认为,被告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综合上述裁判,其基本逻辑是,抛物行为发生在人员密集的场所,因场所的独特性,抛物行为会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安全构成侵害,从而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安全,故根据《刑法》第114条的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之弊端
对于高空抛物行为,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值得认真反思。
第一,从罪责刑相适应的角度看,高空抛物行为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罪质上并不匹配。众所周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刑法中三大口袋性罪名之一,刑法对于何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并无明确的界定,因此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形成的共识是,在解释本罪时应当采取同类解释的方法,从行为的质和量上控制本罪名的滥用。结合相关的司法解释和裁判实践,常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种情形:(1)殴打正在驾驶中的公交车司机,争夺公交车操控权,妨害车辆正常行驶,并危及乘客及车辆安全;(2)在城市主干道采用故意驾驶机动车撞击他人车辆制造交通事故的手段勒索钱财;(3)故意传播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4)驾驶重型货车在高速公路上长距离逆行;(5)私设电网造成他人生命和财产损失等。
从上述情形看,这些行为共同具有的明显特征是行为危害具有辐射性、弥散性,难以把控,一旦行为实施完毕,则可能造成难以估计的结果,受损的人数和受损权益的范围均可能呈现出不特定的状况。这也是为何刑法理论通常将公共安全理解为集体法益的理由。
但是,高空抛物的情况,除了诸如高空放火、高空抛掷手榴弹等罕见情形外,很难将裁判实践中常见的诸如高空抛掷玻璃、杂物等行为与前述行为的危险性相提并论。
第二,高空抛掷煤气罐导致煤气罐爆炸,危害公共安全的,可以直接按照爆炸罪处理。爆炸罪的对象不限于炸药,具有爆破性的物质均可认定为爆炸罪中的“爆炸物”。高空抛掷铁锤、酒瓶、花盆、玻璃罐、地砖、木板等行为,即便造成了具体个体财产损失或者生命健康权损害,但由于上述物品的自身特性不具有危害瞬时扩大化、危害弥散性和危害范围难以把控的特点,即使造成多人法益损害的,也是特定的法益,而非公共安全。换言之,高空抛掷上述物品不可能产生诸如放火、爆炸一样危害“不特定”生命财产安全的法益内容。既然如此,从实质解释的角度,就不应将高空抛物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第三,将高空抛物的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会造成处罚结果上的不均衡。按照《刑法》第114条、115条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包括危险犯和实害犯两种类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高空抛物行为,则意味着没有造成损害的,也要构成本罪。从逻辑上看,“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包括造成后果但不严重,以及没有造成任何后果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应当认定具有现实的危险,按照《刑法》第114条的规定处理。从裁判实践来看,除了少数案件在没有造成后果的情况下按照《刑法》第114条的规定处理外,绝大多数案件均是在造成后果后才以本罪处理。按此逻辑,应当认定为犯罪的行为在裁判中反而没有被认定为犯罪,有关人员是否应当认定为渎职犯罪?但目前并未看到一起这样的案件。实际上,在实践中,即便高空抛物造成财产损失,也有不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的判例。例如,在“陈小明妨害公务案”中,被告人陈小明酒后滋事,砸中楼下车辆。警察赶至现场后制止其高空抛物行为,被告人陈小明不听民警劝阻,用楼道间的瓷砖等物抛砸公安民警,致民警陈某脸部受伤。经鉴定,陈某的身体损伤程度为轻微伤。法院认为被告人构成妨害公务罪,而没有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
此外,如果将不同裁判结论的案件进行比较,即可发现《意见》中所说,在被害人是特定的情况下,按照故意伤害罪处理;在不特定的情况下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在实践中并不容易把握。例如,在“朱某云故意伤害案”中,被告人朱某云站在自家墙头往下扔砖头,将他人砸成轻伤。法院认为,被告人朱某云构成故意伤害罪。但是,在“丁美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中,被告人丁美刚在楼顶向楼下抛掷砖头,导致路人死亡。法院认为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上述两个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均是将砖头从高处抛掷下去,结果也均是造成他人生命健康权利受到损害。但是前案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后案却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什么行为方式相同,作案工具同样是“砖头”,裁判结论却有如此大的不同?可见,裁判实践的定性依据并不充分。
或许反对的观点认为,在“朱某云故意伤害案”中,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伤害特定的人,而在“丁美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中,行为人的目标不特定,即“砸死谁算谁倒霉”。但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首先,认定犯罪的逻辑应当是先客观后主观,而不是相反。只有在危害程度特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进一步认定行为人主观的罪过及其内容。例如,同样是危险方法且造成结果时,才可以进一步追问行为人的罪过心理,据此判断其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基于体系解释的立场,如果两个行为的危害程度相同,就不能对之做出两个异质罪名的评价。同样是投掷砖头,一个被认定为危险方法,一个认定为故意伤害,倘若根据行为的目的是否具有确定性来判断行为的定性,显然与犯罪评价的原理背道而驰。
退一步言之,即便是将高空抛物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无法解决针对具体个人实施的高空抛物行为如何定性处理的问题。按照《意见》的规定,针对特定对象的高空抛物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但是,只要承认高空抛物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特点,就不能否认针对具体个人的高空抛物同样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例如,甲基于伤害的故意对在居民区楼下散步的乙抛掷砖头,如果认为此时甲只是构成故意伤害罪,则完全是根据甲的故意内容判断的,而非根据甲所实施的行为的性质来判断的。如前所述,不能认为楼下人多时,该行为就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楼下只有乙一人时该行为便只具有故意伤害的性质。公共危险不从结果逆推行为是否具有危险,即不能认为砸伤二人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砸伤一人就是故意伤害,而应当在肯定行为本身是否具有危险的情况下才判断结果的性质。换言之,采取结果逆推的方式会导致危害程度相当的行为却因行为人的运气而被认定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罪名,这种犯罪评价的逻辑并不可取。
这也是为何在裁判实践中会出现同样是高空抛物的行为,且所抛物品并无差异,但结论却千差万别的原因。如果肯定高空抛物对公共安全具有危险性,则无法解释实践中甚至还有将高空抛物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案例。例如“郑某某过失致人死亡案”,2015年8月以来,被告人郑某某受雇做杂工,负责清扫垃圾,经常从楼上往楼下平地丢弃砖块、木板凳等杂物。在已被提醒楼下有人的情况下,被告人仍然将杂物抛至楼下,造成他人死亡。
同样地,如果肯定高空抛物可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在行为人明知楼下有人仍然高空抛物,导致他人死亡的,即应当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故意杀人罪的竞合。由于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较重,应当按照故意杀人罪处理,而不是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采取这种竞合的立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高空抛物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逻辑上是存在问题的。
综上所述,承认高空抛物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竞合的处理方案,系在逻辑上错乱地将高空抛物行为与公众感性认知上的危害公共安全对接,因而造成刑法的错位评价以及罪名认定上的混乱。
拓展刑法中非公共危险犯罪名的适用范围
尽管立法承认高空抛物是独立罪名,但从实践来看,高空抛物还会涉及其他罪名,根据行为的具体样态和法益危害的类型,应当做具体判断,拓展高空抛物罪名的适用范围。
(一)高空抛物可能涉及的其他罪名
如果行为人抛掷的物品具有具体特殊性时,应当根据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在判断侵害法益的具体类型基础上,适用相关罪名。
1.高空抛物罪。高空抛物首先涉及的罪名是高空抛物罪。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罪属于轻罪,最高法定刑也仅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就意味着在理解本罪适用时,应当注意刑法体系的整体立场,在罪责刑相适应的基础上,准确适用本罪。本文的基本立场是,由于刑法规定了高空抛物罪的竞合条款,这意味着成立高空抛物罪只能是在行为不构成其他重罪的前提下才可能适用。倘若行为同时触及其他重罪,则应根据竞合的原理排除高空抛物罪的适用。进一步而言,在认定高空抛物罪的“情节严重”时,应当将造成他人伤亡(含轻伤)、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等情况纳入考量,并结合案件中行为事实的客观性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综合评价。如根据行为人多次抛物、行为人单次抛掷的物品较多、抛掷的物品重量体积较大等具体情形进行判断。
2.侮辱罪。如果行为人针对特定的人从高空抛洒粪便、垃圾等情况,应当按照侮辱罪处理。理由是,首先,高空抛物的行为具有公然性,在判断公然性时应当从时空条件来判断,只要采取能够让他人知晓的方式,均不否认公然性的存在,即便高空抛掷污秽物时没有其他人在现场,但是行为人抛物的地点是在居民区、人员密集场所,即便是晚上,也应当认定为公然性。其次,抛物行为本身具有撞击性,符合侮辱罪中“暴力”的特征。最后,根据刑法的规定,侮辱罪只有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例如,行为人基于愤怒向跳广场舞的多人实施高空抛洒粪便的,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由于侮辱的对象人数众多,可按照侮辱罪处理。
3.寻衅滋事罪。如果行为人基于显示自己在小区中的蛮横与淫威而高空抛物,导致二人轻微伤的,因没有达到故意伤害罪的轻伤标准,无法按照故意伤害罪处理,而按照本文前述分析,也不宜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此,本文认为,可以按照寻衅滋事罪处理。理由如下:在客观上符合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8年6月25日《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37条的规定,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导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可构成寻衅滋事罪。高空抛砸物品的行为可以被认定为随意殴打他人,殴打他人的行为未必一定是使用身体对他人进行殴打或者近距离的打击行为才可以认定。远距离利用他物对人进行打击的行为同样可以认定为殴打。这也符合刑法中行为的定性。在刑法理论上,通常认为利用工具实施危害社会的身体举动也是刑法中的行为。所谓随意,通常是指没有理由或者理由不正当。有观点认为,寻衅滋事行为都具有无因性。在被害人对案件有原因时,应当否定行为人构成寻衅滋事罪。本文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尽管寻衅滋事罪的行为多数都具有无因性,但是,不宜否定有因性的行为同样可以构成本罪。例如,基于对他人的怨恨而在数年后殴打他人的,裁判实践中也可以认定该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当然,承认有因性并不意味着只要殴打他人就构成本罪,倘若纠纷的发生有合理或正当理由的,尽管在行为方式上为刑法所禁止,也不宜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此外,有观点主张寻衅滋事罪不要求具有流氓动机,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正如有学者所说,寻衅滋事的定罪有文化传统,对于邻里纠纷、民事纠纷引发的打架行为,处理时“枪口”就要抬高一点。寻衅滋事的本质特征是,用厚颜无耻、卑鄙下流、蛮不讲理、逞强耍横、寻求刺激、发泄情绪、无事生非、小题大做、借故生非等流氓一样的思想去破坏社会秩序。倘若不强调行为人的动机,则日常生活中基于琐碎事由的殴斗行为也可能按照本罪处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例如,甲因不满乙在宅基地建房过程中私下扩大建筑面积而殴打乙的行为,既不能认为甲具有流氓动机,也不可以将甲的行为认定为随意殴打。对于此种情况,构成其他犯罪的,应当按照相应犯罪论处。因此,在实践中,倘若行为人基于戏谑他人或者逞能等动机而高空抛物的,根据结果可评价为随意殴打他人或者任意毁损财物的行为,应按照寻衅滋事罪处理。
(二)善于利用竞合论实现刑事责任的恰当评价
随着刑法立法越来越精细化,罪名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需要改变传统理论关于罪名之间界限分明、非此即彼的观念。当行为或者法益之间出现交叉或者重合时,应当适度地承认竞合论。从历次刑法修正中可以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按照处罚较重的定罪处罚”的规定在刑法中越来越多,以至于有学者说立法其实无意再去区分罪名之间的关系,甚至无意区分想象竞合与法规竞合。从理论上看,该观点当然存在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因为,如按照竞合论处理的话,构成要件的类型化是否会被冲淡,进而构成要件的意义是否会因此缺损,都是有待进一步斟酌的问题。
但毋庸置疑的是,从刑法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实然规定看,竞合论的市场显然是在不断扩大的。所以,对于高空抛物同时造成多个法益侵害时,应当运用竞合的原理,实现罪刑均衡。例如,基于流氓动机的高空抛物,造成一人以上轻伤,同时构成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因寻衅滋事罪的最高法定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伤害罪的最高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故应按照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倘若只是造成他人轻微伤,因实践中不处罚故意伤害未遂,所以只能按照寻衅滋事罪处理。倘若行为人明知楼下既有人又有汽车等财物,基于流氓动机高空抛物,仅仅导致财产损失的,则应当根据财产数额的标准来判断,如果造成公私财产损失5000元以上尚未达到数额巨大(高于寻衅滋事罪中“任意毁坏财物2000元以上的标准”)时,则同时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和寻衅滋事罪。此时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最高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低于寻衅滋事罪最高法定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故宜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是,若毁损财产达到数额巨大的标准,此时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最高法定刑为7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此情况下,则应当按照故意毁坏财物罪处理。如果纠集多人基于流氓动机而高空抛物,造成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此时寻衅滋事罪的最高法定刑为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重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最高法定刑,故应按寻衅滋事处理。在造成他人重伤的情况下,此时应按照故意伤害罪处理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按照寻衅滋事罪则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宜按照寻衅滋事罪处理。但是在造成他人死亡的情况下,因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明显高于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应按故意伤害罪处理。在过失高空抛物致人重伤后,行为人明知不救助可能导致他人死亡的,由于犯罪行为可以成为不作为的义务来源,倘若因行为人不救助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则应当认定为过失致人重伤罪和不作为的故意伤害致死(甚至杀人)罪。对此,处理方案可能有两种,一是按照数罪并罚处理,二是按照竞合犯处理。本文认为,可认定为后行为吸收前行为,且后行为重于前行为,直接按照后行为处理即可。
(三)纵容他人高空抛物的行为
在造成法益侵害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难认定,值得讨论的是,与抛物者有关联的人是否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对此,《意见》和刑法均没有规定。本文结合生活中常见的与抛物者有关联的主体予以讨论。常见的类型包括如下三种类型。
甲明知与其生活的乙高空抛物但没有阻止,倘若造成损害结果,乙的刑事责任较为容易确定,但甲是否也要承担刑事责任?本文认为,甲构成不作为的帮助犯。
纵容行为违反了甲对于其支配领域中的危险排除义务,按照不作为的原理,甲的义务属于基于对法益的危险发生领域的支配产生的救助义务。在刑法理论上,对于上述救助义务通常限定于危险发生在行为人可支配的空间。例如,甲邀请他人到家做客,他人突发心脏病,倘若甲不救助,可以构成不作为犯。但是,对于支配空间之外的风险,刑法理论并未过多关注。在高空抛物的情况下,危险不是发生在甲可以支配的建筑物内,但是危险是由此建筑物内的人所制造的,此时尽管结果危险在外,但行为危险发生在建筑物内,故不能否认甲对于危险的发生具有实际的控制能力。
纵容的类型包括口头的允许以及行为上的默认。例如,乙对甲说:“是否可以将垃圾直接扔到楼下?”甲说:“你随便。”此时不能认定甲是教唆行为,而是口头允许型的纵容。当甲对乙的要求置之不理时,甲成为行为上的默认。无论哪一种情形,都构成纵容。
值得讨论的是,如果按照犯罪共同说处理的话,由于纵容不是直接故意,只有在甲和乙罪过内容相同的场合下,才可以成立共同犯罪,故纵容的行为无法按照共犯处理。对于纵容行为,按照犯罪共同说处理难免会形成处罚漏洞,而按照行为共同说则可以解决上述问题。根据行为共同说,在共同犯罪认定中,应当先判断违法的共同性,然后分别判断行为人的责任。其基本立场为:通过共同实行的行为实施各自的犯罪,共犯者相互之间的罪名未必一致,这在刑法理论上被称为罪名从属说的否定说。共犯的处罚依据并非共同的意思联络,更不是借用他人的可罚性,而是利用他人扩张了自己行为的因果辐射范围。照此逻辑,由于甲对于从其支配领域中发生的危险具有排除义务,因此,甲构成不作为;乙实施高空抛物的行为是积极作为,二人构成共同犯罪,然后在责任论中需要进一步去判断甲的心理罪过,据此再认定各自的罪名。例如,在上述案例中,如果甲对乙说:“等下,我看看楼下是否有人”或者大喊一声“扔垃圾了,赶紧避让”,则甲的罪过不可能是故意,在责任论上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但是甲仍然需要对乙所实施的行为承担责任。当然,如果甲没有采取防止结果发生的行为,则甲在罪过上应当认定为间接故意,基于行为共同说的立场,在过失的情况下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在甲是间接故意的情况下,更应成立共同犯罪。
当抛物者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按照行为共同说,此时建筑物中危险支配者与抛物者同样构成共同犯罪。例如,丙纵容10岁的儿子丁高空抛物,导致他人重伤。倘若坚持犯罪共同说,则丁因缺乏责任能力,无法认定二人为共同犯罪。由于纵容行为不是“利用他人”的行为,所以丙也不构成间接正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人对重伤的后果承担刑事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对此,或许有人认为,可以根据丙的纵容行为直接将其认定为间接正犯,但这与间接正犯的原理相冲突。因为丙并没有利用丁缺乏责任能力的事实,而是默认,很难将默认解释为利用。所以,不能按照间接正犯来处理丙的刑事责任。
无法处理丙的责任,根源在于犯罪共同说存在的问题。倘若按照行为共同说,则首先不考虑二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只要能够确定丁是正犯行为,肯定丙的纵容与丁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就可以得出二人构成共犯的结论。在责任认定中,由于丁缺乏责任能力,所以不构成犯罪,而丙则需要对自己的纵容行为承担责任。但由于丙的行为不是实行行为,所以只能成立帮助犯罪名。
(四)高空抛物中物业怠于履行监管义务的责任
《物业管理条例》第46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发生安全事故后,物业服务企业在采取应急措施的同时,应当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协助做好救助工作。”根据上述规定,物业公司在其所辖的小区范围内具有安全防范的义务。实践中,在高空抛物致人伤亡后,对于物业怠于履行监管义务通常按照民事责任处理。但本文认为,仍然可能存在刑法适用的空间。
在物业发现有人高空抛物时,怠于履行职责以致发生危害结果的,可按如下方案处理:(1)如果有证据证明物业管理人员具有纵容心理,例如,对他人多次实施的高空抛物行为既不阻止也不过问,则可认定为纵容他人高空抛物的行为,根据行为共同说按照共同犯罪处理,然后根据物业的心理态度,在责任内容上进行具体判断。纵容通常为间接故意,因此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失的,在肯定共犯成立的前提下,按照具体的故意内容定罪处罚。(2)在物业采取措施的情况下,应当根据该措施对于防止危害结果出现的妥当性进行具体判断。例如,物业管理人员仅仅张贴了禁止高空抛物的宣传单,但没有对特定的高空抛物者采取进一步的防范措施,则可认定措施不当,在承认与抛物者构成共同犯罪的前提下,判定其罪过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然后再根据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处理。如果抛物者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物业管理人员应在过失范围内对危害结果承担责任。倘若只是造成财产损失的,因刑法不处罚过失损坏财物的行为,故因缺乏有责性不能认定为犯罪。(3)在高空抛物致人轻伤,抛物者及时向物业报告后,物业怠于履行职责致使伤情恶化,应当认定其不作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性。例如,甲高空抛物导致乙轻微伤,甲报告物业后,物业管理人员不予理睬,或者到达现场后不对乙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导致乙因得不到及时救助出现伤情恶化的结果,物业管理人员同样可以构成不作为犯罪。理由为,物业管理人员相较普通业主而言,对于安全防范和救助的能力更高,但比起警察等职业群体而言,其能力又弱一些。因此,可认定其为刑法上的保证人,鉴于保证义务较弱,故不能认为抛物者与危害结果的出现属于“因果关系的断绝”,即抛物者和物业管理人员均应对危害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
结 论
面对频频出现而又屡禁不止的高空抛物现象,刑法应当及时予以回应。应当改变裁判实践中仅将高空抛物行为按照民事责任处理的方式,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阻却刑事责任,责任竞合不仅具有法律依据,而且也符合司法对责任的分类、分层评价原理。同一行为引发的责任类型可能是多样的,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便涉及责任的竞合问题。对于高空抛物,不能因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而一概阻却刑事责任。对于高空抛物构成犯罪的,应当对该行为与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构成要件之间的关联性做出判断,不宜盲目否定刑事责任。从这一点上看,《意见》的出台回应了社会的关注,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唯民事责任而忽略刑事责任的裁判路径予以矫正。但是,在认定高空抛物时,仍然存在思路上的瑕疵,尤其是,不能以结果倒推行为的危险性,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更不能为了回应舆论的要求,不惜牺牲罪质判断的规范逻辑,进一步扩大这一口袋型罪名的适用范围。总之,高空抛物的刑法评价应当局限在侵犯个体法益的犯罪域内,不能以公众抽象安全感的降低而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同时,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适度扩大刑法中关于侵犯个体法益的罪名适用范围。在责任认定时,应当摆脱犯罪共同说的窠臼,大胆采取行为共同说,妥善界定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范围,形成关于高空抛物刑事责任的体系性规则。
①参见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
②参见陈晓明《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
③参见陈兴良《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
④参见高铭暄、孙道萃《预防性刑法观及其教义学思考》,《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
⑤参见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2)深罗法刑一初字第204号刑事判决书。
⑥《刑法》第291条第2款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⑦参见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5刑终155号刑事裁定书。
⑧参见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3刑初136号刑事判决书。
⑨参见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高新刑初字第169号刑事判决书。
⑩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刑终441号刑事裁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