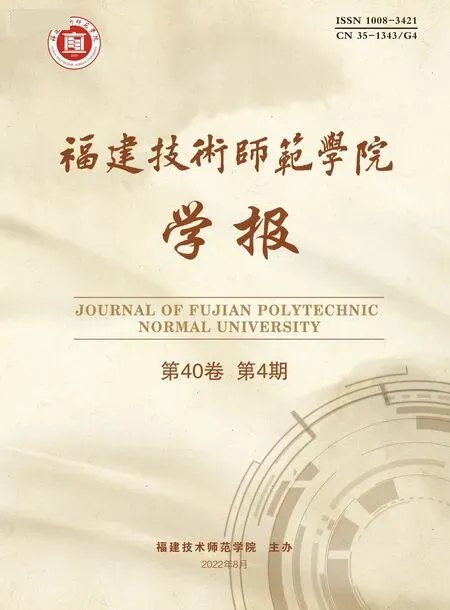《中国丛报》与林则徐的媒介形象塑造
常昌盛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1830年初,28岁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接受美部会(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差遣来到广州宣道。为了传播基督教福音、了解中国,裨治文认真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并按时向美国本部汇报其对中国的观察。1832年5月,裨治文在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建议和支持下在广州创办了《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这是由在华传教士创办的、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第一份英文月刊,共20卷,232期。在《中国丛报》续存的20年时间里,裨治文长期担任该报主编,直至1847年迁居上海为止。
《中国丛报》的创办几乎与美国的报纸现代化处于同一时期。19世纪30年代,得益于印刷技术的革新和工商业的迅猛发展,经济新闻越来越受到关注,这进一步刺激了美国报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广州口岸的英文报刊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机遇。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终结,港脚商人开始步入自由贸易时代。随后,鸦片走私泛滥导致中英贸易摩擦频仍,成为《中国丛报》重要的新闻议题。《中国丛报》创办原旨为拓展在华传教事业,在反对鸦片的同时也竭力呼吁打开中国市场,带有明显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烙印。回顾美国报业的发展,大众化报刊确立了新闻客观性的宗旨。1839年,《中国丛报》把鸦片贸易危机设置为重要议程,“有闻必录”成为这一议程的重要特征。
政治人物报道是报刊建构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目的性、针对性较强的报道方式和传播策略。鸦片战争前,作为皇帝任命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南下赴粤查办海口事件(珠江一带的鸦片走私活动)成为《中国丛报》的重点报道对象。作为备受关注的“媒体人物”,《中国丛报》是如何报道林则徐的,为其建构了什么样的媒介形象,赋予这一形象怎样的内涵是本论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未见其人”的报道方式
鸦片战争之前,广州口岸的行商体制横亘在中西方之间。一般情况下,政府官员不得接触外国人,即使引发国际贸易争端,双方消息的互通也只能由行商以“禀”和“谕”的形式代为传递。1839年3月,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这位钦差大臣的出现牵动着在华外商群体的神经,其处理问题的举措又会影响中西关系的走向,自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可在中西没有直接交往渠道的情况下,《中国丛报》是如何报道林则徐的呢?
(一)“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首先,《中国丛报》采用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报道方式。1839年1月《中国丛报》的“时事报道”(Journal of Occurrences)栏目刊登一则预告性消息,林则徐作为其报道视野中的媒体人物正式登场。这则消息称:“林则徐,福建人,受皇帝委派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就鸦片贸易展开调查并提出新的举措,预计将在几天后抵粤。他打算‘切断毒源’,并准备在必要时‘沉舟破釜’,因为现在看来,大皇帝对这些交易和使用鸦片的恶行已经相当愤怒,而且他内心深处时刻都在想着要永远消除它们”[1]504。这则消息重在传达林则徐即将到任的信息,《中国丛报》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不过单凭这则消息就可以看出,《中国丛报》密切关注事态的动向,有着较强的新闻敏锐度。总的来说,虎门销烟之前,《中国丛报》对林则徐的报道大多采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报道方式,把林则徐发布的禁烟谕令译为英文并全部刊载出来。
作为月刊杂志,《中国丛报》不仅要报道时事新闻,还需兼顾其他栏目。如何在有限的版面中选择最有价值的新闻,并最大限度宣传“声势”成为《中国丛报》的又一指导方针。在新闻稿件的选取上,《中国丛报》先后刊登了林则徐签署的各类公文英译稿。在《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中,林则徐直言“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责令“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2]22-23。在《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中,林则徐对行商们疾声厉色道:“乃十余年来无不写会单之银铺,无不通窑口之马占,无不串合快艇之行丁工役。并有写书之字馆,持单之揽头,朝夕上下夷楼,无人过问。银洋大抬小负,画则公然入馆,夜则护送下船,该商岂能诿于不闻不见?乃相约匿不举发,谓非暗立股分,其谁信之?”[2]19-20此外,《中国丛报》还刊登了行商与外商、义律与英国臣民,各国领事与林则徐之间的通函原文。这些函件都围鸦片主题展开以回应林则徐的禁烟举措,无不体现着“至上而下”和“中心—边缘”的权力结构及其关系。
《中国丛报》没有对这些稿件发表任何评论,其用意是为让外商知道中国政府反对鸦片贸易的坚定立场。不过林则徐的措辞并非一以贯之地强硬专断,有时候也不乏循循善诱的教导。在《中国丛报》刊登的《示谕夷人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中,林则徐从天理、国法、人情和事势阐述鸦片贸易的危害,并劝诫鸦片商贩上缴烟土,“本大臣与督抚两院,皆有不忍人之心,故不惮如此苦口劝谕。祸福荣辱,皆由自取,毋谓言之不早也”[3]128。由此看出,在虎门销烟前期《中国丛报》是通过向读者“转述”林则徐的话语来报道林则徐的。这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报道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此时的《中国丛报》还没有机会接触到林则徐本人,只能透过谕令中的文字和语气来判定他的态度。通过《中国丛报》的这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报道方式,“以声夺人”的林则徐给西方读者留下了疾声厉色但又劝善规过的媒介形象,彰显林则徐不辱使命的初衷和根绝鸦片的决心。
《中国丛报》缘何如此关注鸦片与林则徐呢?这除了新闻价值以外还与《中国丛报》主编裨治文的个人立场密不可分。作为基督教传教士,裨治文对鸦片深恶痛绝,在考察中国的传教环境时,鸦片泛滥的问题更是让他触目惊心。1836—1837年,裨治文曾在《中国丛报》上设置罪恶与道德议程,邀请西方各界人士公开批判鸦片贸易。此外,从事鸦片走私的几乎全为英国商人,只有采取行动与英国作出区隔,才能防止中国的禁烟运动累及中美贸易,保护美国的利益。在禁烟方面,林则徐的行动与裨治文的设想在某种程度上高度契合,因此裨治文不吝版面对鸦片贸易的相关议题进行了大量报道。
(二)“未见其人,先闻其事”
除了替林则徐“发声”之外,“未见其人,先闻其事”是《中国丛报》采用的另一种报道方式。不同于简单“转述”林则徐的公告,这种报道方式可以通过报道事件来反映事件人物的性格特征。同时,通过观察双方的集体行为,探究行为背后的动因,即使在新闻中心人物“缺席”的情况下,也能窥探其行事作风。1839年3月24日在广州突发的军事行动涉及到中英双方的切身利益、关乎在华外侨的生命安全、影响着中外政治的发展动向,具有极高的话题度和新闻价值。3月24日,林则徐下令捉拿鸦片走私的幕后策划者兼英国商会会长颠地(Dent),义律闻讯从澳门赶来,乘坐炮舰“拉恩”号抵达广州,亲自进入商馆护送颠地离开。林则徐见其“是夜欲将颠地带逃”,于是下令派兵围困商馆,《中国丛报》完整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形。
“义律上校刚一上岸,警报就迅速地传布出去,巡捕官中便层层传令把商馆四周的所有通道封锁起来。几分钟后,商馆广场上的中国人都被驱走。广场入口都已关闭由兵卒看守着,商馆门口在两夜前早就被一些苦力们所监视,现在则挤满了大队人马,他们手执长矛,提着灯笼。整个商馆前的沿江两岸由船艇排成三条警戒线,载满了武装人员,临近屋宇的房顶上也驻满了兵勇。为了封锁场地,钦差大臣下令要求买办和仆役撤离商馆。大概到了晚上九点钟,商馆中没有一个中国人留下,唯一的同伴就是剩下的两三百个外国人。广州城,或者至少毗邻商馆的那个地区实际上是处于戒严之下。巡逻队、哨兵和军官们一面鸣锣吹号,一面加紧巡查,为那夜的黑暗和忧伤增添了一层混乱。如果再多一点群情激愤的话,这些商馆可能会变成另一个“黑洞”,或是变成一个杀戮的场景”[1]627。
《中国丛报》的这篇通讯没有正面报道林则徐本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定立场和思想倾向,而是用客观事实向西方读者呈现“围困商馆”事件的全貌。通过对真实场景的记录和细节的捕捉,《中国丛报》把当时的情景、气氛、叙事者的情绪和感受一起构成强烈的现场感,向西方国家表明中国政府禁烟并非虚谈,也让读者感受到林则徐雷厉风行的政治作风和动如雷霆、其疾如风的威严气势。
义律的军事先发行动导致商馆遭到围困,广州内的所有外商均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作为一份英文报刊,《中国丛报》自然担心在华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其后续的报道是否会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此次围困商馆事件中,义律利用中国人不懂外交、不懂西方法律的弱势,把中国的禁毒问题上升到国际外交冲突的层面,以期博得其他西方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从有利于扩大传教事业的角度出发,主编裨治文可以借此声援义律要求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抗中国,从个人对鸦片的立场来看,裨治文希望根除鸦片这种罪恶商品,所以裨治文选择不偏不倚的立场,保持报道的平衡。除了刊登义律对英国臣民的公告以外,《中国丛报》还刊登了《各国夷商禀遵谕以后不敢夹带鸦片等由》《米利坚国夷商京禀该商向不贩鸦片由》以及义律与林则徐关于收缴鸦片的通函。从书信内容看出义律已经摒弃了以往坚决的语调和态度,转而较为恭顺地遵从林则徐的缴烟谕令。
1839年5月23日,在20 291箱鸦片缴完之后(其中的8箱是额外从因义士处缴获),广东当局下令驱逐义律及十六位鸦片商。《中国丛报》如此记录道:“由于两位老行商浩官和茂官迟迟未到英国商馆确认离粤人员,直到下午五点义律才得以离开,同行的还有16名驱逐人员名单里所有当时在广州的英国人。义律上校一行离开后,商馆前和靖远街街口由苦力充当的警卫立即被撤走,商馆附近的街道被准许通行。民众们也很好奇,想看看发生的变化,于是广场上很快就挤满了注视的人群”[4]31。
此次报道中,林则徐并未现身,但“未见其人,先闻其事”的报道方式赋予了林则徐强烈的“存在感”。围困商馆持续了两个月,《中国丛报》的报道在事件发生和结束时均对义律施以重墨,使得前后形成极大反差。两个月前,义律调兵遣将、兵临城下,大有长驱直入的气势,不料自己身陷囹圄,最后悻悻而归。表面上是报道义律的遭遇,实则是在暗暗夸赞林则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政治才干。在《中国丛报》搭建的新闻框架内,没有出场的林则徐被塑造为雷厉风行,不怒自威的禁烟大臣。
二、见人见事的现场报道
百闻不如一见,无论是“闻其声”还是“见其事”,如果见不到其人,那么会让新闻读者留下不少缺憾。一则新闻报道如果缺乏现场感,不能近距离感受,就无法直观把握新闻人物的精神内涵,这样写出的报道自然避免不了猜测、臆想和过度阐释。
(一)旅行者视角下的见闻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将20 291箱鸦片于虎门镇口就地销毁。《中国丛报》主编裨治文受美国商人京(King)之邀,一同前往虎门镇口观看销烟现场。裨治文藉由这次拜访,进行一切可行的调研和观察,以了解林则徐直接领导下的销烟工作是否忠实。根据虎门销烟的现场见闻,裨治文撰写《镇口销烟记》,以第一视角描述这个存放和销毁鸦片的镇口镇。
“镇口是一座位于狭长地带上的村庄,位于小溪的东侧,分布呈南北走向,大概有三分之一英里长。存放和销毁鸦片的地方就选定在这条溪的岸边上,位于一处山坡,距村庄北端不远的地方,占地约400或500平方英尺的区域,用竹子安插着。在我们一行人经过村庄时,成群结队的看客涌到船里,房屋上,以及山的两边”[4]72。
与其他“转述”的报道不同,裨治文置身于真实的场景中,从点到面、由表及里,从多层次多角度观察虎门镇口、派驻军队的精神状态和中国勇士的风貌。透过“旅行者”的视角,裨治文以亲身者的观察和叙述使得报道更加客观真实。“当我们缓缓靠近海岸时,战船和帆船鸣炮致敬。两个师的军队分一南一北,身穿制服,按照各自的军姿站立围成一圈”[4]72。裨治文在描述林则徐派来接待的侍从时,这样记载:“他穿着厚重的长袍,穿着靴子,系着腰带,如同一位战士。他是个本土的穆斯林,来自北方某个省份。身材高大魁梧,肤色黝黑,留着浓密的黑色长胡须。他显然是在营地里长大的,并且习惯了军旅生活”[4]72。
临时搭建的销烟场地是什么样的?人员规模如何?那里的防卫是否严密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中国丛报》为西方读者进一步解读。《镇口销烟记》属于“旅行者见闻”,《中国丛报》主编裨治文以旅行者的视角,采用“移步换形”的叙事结构,由远及近、从外到内,逐步向西方读者揭开销烟现场的神秘面纱。
“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四周围上坚固的栅栏,像马来西亚营地。除东边以外,每边都安置门道,这些门前都有哨兵把守着,没有令牌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当从这个地方出去时,每个人都要被搜查。据说,销烟工人的数量约为500人,文武官员的人数不可能少于60或80人。我几乎没有见过一群比这更为英姿飒爽的男人,许多差役和扈从也都很年轻、仪表堂堂。所有这些官员都被委派为检查员和监督员,其中的一些官员坐在垫棚下的高椅上,观察着围墙内每个角落的一举一动,以他们位置的视角,没有什么能逃得过他们的眼睛。一些文武官弁则轮流站哨,日夜蹲守,另一拨人负责监督烟箱里倒出的鸦片,这些烟箱被存放在围墙内的高棚之中。他们特别注意查看每个箱子和袋子是否与从趸船上搬下时做的标记相符”[4]73。
如此精心安排的会见场景,环环相扣、有条不紊的程序可以看出林则徐邀请西方人观看销烟的动机。林则徐想借西方人的所见所闻向各国传递中国的声音——“必将鸦片流毒尽绝根株”。通过裨治文的现场报道和“移形换位”的叙述结构,可以看出林则徐的治军严明和严谨周详的工作作风。
(二)身临其境,走入震撼的销烟现场
除了要有现场感,“出镜”记者还需要通过仔细的观察、深入采访和情景融合才能翔实地向读者进行现场报道,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受。中国人用于销烟的化烟池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是如何销烟的?带着满心的好奇,裨治文在林则徐侍从的陪同下来到了化烟池旁,其目光所及之处皆被记录到《中国丛报》之中。
“位于围墙西侧的栅栏内,有三个大水池或凹地,自东向西分布,大约150英尺长,75英尺宽,7英尺深,底部铺设石板,沿着池边钉上笨重的木桩。这三个水沟都有自己的围栏,且只有一边设有入口。我们在那查看时,一个没有鸦片,第二个正被填满,另一个几乎已准备清空”[4]73。
裨治文一行人重复检查销烟的每一道工序,被中国人谨慎和忠实的态度所折服,裨治文详细地描述了中国人销毁鸦片的整个流程,足以见证中国人对销烟工作的监视比在广州拘留外国人时要严格得多,他继续写道:
“处理鸦片的工序大致是这样的。首先,用山顶上引来的淡水灌满一片约两英尺深的凹地。第一块凹地处于这种状态中,它刚刚被灌满了淡水。在第二块凹地上面搭建台架,人们在台架中干着活,台架上面按几英尺的间隔摆放着木板。装进篮子里的鸦片传递到苦力的手中,苦力们踩着木板把鸦片运到凹地的每个角落。然后把鸦片球一个一个地拿出来,扔在木板上,用脚后跟踩碎然后再踢进水里。与此同时,其他苦力也在化烟池内忙碌着,他们拿着锄头和宽大的铲子,忙碌地敲打和翻起水池底部的鸦片。另一些苦力则被雇来搬运盐粒和石灰,并将它们大量地撒在整个化烟池的水面。第三块水池大约填了一半,就像个蒸馏的大水池一样,水池中的鸦片并不是在旺盛地发酵,而是在缓慢地分解,几乎已经准备好排出去了。需要通过一个狭窄的涵洞排放,这个涵洞开在化烟池和小溪之间。涵洞有两英尺宽,比化烟池的底部要深一些。涵洞设有一个过滤网,像筛子一样细,以防止任何较大的鸦片碎块冲进小溪里”[4]73-74。
裨治文以现场报道的方式,把所看到的事实如实写出来,也让西方读者看到林则徐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的中国官员。通过《中国丛报》的描述,不但让读者看到了林则徐在处理鸦片问题上刚正不阿的态度。透过这篇新闻报道,不禁让人感叹林则徐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于细微之处见真章的威严气势。更重要的是,《中国丛报》粉碎了外界盛传中国政府假意销毁鸦片的谣言。在镇口的销烟现场,林则徐严厉执行公务,不留任何投机取巧的余地,任何趁机偷运鸦片的人,一经发现直接当场处死。《中国丛报》的这一篇现场报道使得虎门销烟真正地达到“共见共闻,咸知震慑”的效果,也把林则徐塑造为一名刚正不阿、正义凛然的禁烟英雄。
三、人物“专访”与林则徐媒介形象的完成
人物专访是现代报刊上常见的一种新闻形式,但在华夷之别甚严的清朝中后期,林则徐折节接见外国人并接受“专访”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看,“专访”林则徐是西人第一次与中国官员面对面接触,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和历史意义。虎门销烟之前,《中国丛报》已多次报道有关林则徐的新闻,刊发其签署的谕令和公告,对这个“访问对象”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此次专访为了突出重点,主编裨治文除了勾画访问对象的举止、神态和性格特点以外,还发掘了林则徐一些独特的兴趣爱好,从多方面展现了林则徐丰富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
(一)《中国丛报》主编眼中的伟大政治家
参观完化烟池之后,裨治文和京被安排前往谒见钦差大臣。关于林则徐的形象,裨治文这样描述,“他看起来不过四十五岁,身材矮小,体格结实,有一张光滑饱满的圆脸,细长的黑胡须,和一双敏锐的黑眼睛。他的声音很清晰,音调分明。他的面容显示出一种一贯谨慎而又深思熟虑的睿智”[4]77。在向中国官员们脱帽鞠躬致意后,裨治文和京开始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访问,不过不是直接访问林则徐,而是通过身边的侍从传话来交流。
林则徐愿意折节接见这个美国访问团,一来是因为当时广州城内只剩下美国人,而京在美商中颇具声望,接见美商代表可能对禁烟有所帮助。其次,裨治文陪同前往虎门既可充当京的翻译,又可以把这次虎门销烟的亲身经历写进《中国丛报》当中,更彰显中国政府销毁鸦片的决心。不过这次会晤的主题是贸易与禁烟,裨治文创办的《中国丛报》并未成为讨论的话题。在京与林则徐会晤的过程当中,主要谈论了三个议题:如何恢复中美贸易;关于英国人撤离广州港的意图以及向英国女王和其他欧洲君主传递国书的最佳方式;询问地图、地理和其他外国书籍的情况,希望获得一部马礼逊编撰的《华英字典》。与林则徐会谈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平静而友好的气氛中开展的,“当美国商人京不时对那些行商发表评论时,他忍不住笑了,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微笑。钦差大臣还问我们:那些行商之中谁最好?京先生没有回答。应他的要求,我们对英国海军力量进行了介绍,这似乎让他很不愉快,有一两次他竟然皱起了眉头”[5]339。
会晤结束后,林则徐把致英女王的禁烟信《移英吉利国王文为会禁鸦片烟事》交给裨治文,但他并不知道该如何将此信交给英国王室,最后决定发表于1839年5月份的《中国丛报》上。以《中国丛报》当时的订阅和发行情况来看,每个月都有大量《中国丛报》送达英格兰海岸,因此这封信的发表即使不能通过正常渠道传递给英国王室,也能保证很多英国人仍有机会在《中国丛报》上读到它;“照得天道无私,不容害人以利己,人情不远,孰非恶杀而好生。贵国在重洋两万里外,而同此天道,同此人情,未有不明于生死厉害者也”[4]9。现在不是欧洲使臣急于与中国官员直接通信,反而是林则徐“急欲了解如何将此信递交英国王室”,并同欧洲各君主商谈争取其对中国禁烟运动的支持。实际上,林则徐后来安排英国商船“担麻士葛”号(Thomas Coutts)商船的船长湾喇(Warner)将此信带到英国,但英国外交部事先知道其内容,因此拒绝接受。
(二)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通过这次会晤,《中国丛报》展现了林则徐不同于以往的一面,在封建闭塞的东方帝国中,这位钦差大臣的国际视野让主编裨治文感到非常意外。
自林则徐赴粤以后便开始密切关注英国的反应,招揽翻译人才,极力探求西方知识。根据裨治文的记载,林则徐幕下的翻译人才有4人,其中较为出色的译员正是裨治文的得意门生,华人基督徒梁发之子梁进德。相较于其他3位译员,梁进德对中英文字的掌握程度虽然是最熟练的,但裨治文也只是称其“能较为轻松,正确和流畅地阅读和翻译常见题材的文件”[4]77。可见,林则徐询问外国书籍的情况,除了“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外,更需要提高译员的能力,壮大自己的翻译队伍,这是林则徐进行大量译报的内在逻辑。魏源在《圣武记》里写道:“林则徐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林则徐对当时收集到的西方报刊书籍进行了摘译和编辑,包括《四洲志》《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华事夷言录要》《滑达尔各国律例》和《洋事杂录》。可以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他这种国际视野是同时代的其他中国政治家所缺乏的。
总的来说,裨治文对与钦差大臣会谈的结果是比较满意的,他记叙道,“从会谈的整个过程和询问的内容来看,钦差大臣的唯一目标似乎一直非常明确,就是要消除鸦片走私,保护和维护合法和正当的贸易。在谈话的方式和内容上,他都表现得很好。他的确不时地透露出对自己国家和君主或多或少的偏爱,以及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漠视,这正是伟大政治家的特点”[4]76-77。
裨治文撰写的《镇口销烟记》详细记载了虎门销烟的所有细节,是《中国丛报》发表的较有代表性的纪实性报道。从报道姿态来看,裨治文以“融入”的姿态来观察虎门销烟中的人和事,获得了真实影像,捕捉到有价值的材料。从文本建构看,“融入”的报道姿态往往“靠事实说话”,裨治文深入考察,切身体会销烟现场,避免了主观色彩和倾向性。从船上到岸上、从远到近、由外到内,裨治文报道的场景涵盖乡村、营地、军队、士兵、官员、销烟工人等。这些叙事元素构成了完整的文本,并呈现出鲜活的叙事图景,触发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
虎门销烟对西方国家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力,达到了“共见共闻,咸知震慑”的传播效果。此次虎门见闻,主编裨治文近距离接触林则徐,气氛轻松友好。林则徐文雅的举止、谈吐得体、思维缜密的特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裨治文眼中,林则徐对西方知识怀有极大兴趣,他密切关注国际事务,拥有伟大政治家具备的所有品质,这些都是裨治文在“第一现场”里获得的深切感受。就此种意义而言,《镇口销烟记》这篇报道更加丰富了林则徐媒介形象的内涵。
四、结语
《中国丛报》刊登林则徐的谕令往往采用“实录”的方式,不做任何评论,在会见林则徐时从多个层面对其进行考察,呈现了一个立体、鲜活的人物,甚至不乏溢美之词,可见《中国丛报》对林则徐的报道是正面且褒扬的。其原因有三:一是裨治文与林则徐都对鸦片持反对态度;二是英国对华贸易常年占据中外贸易总量的最大份额,挤压了美国对华贸易的空间,不利于自身商贸的发展;三是响应美国政府要求制定温和的对华政策号召。通过报道虎门销烟和塑造林则徐的光辉形象,《中国丛报》或许可以在西方舆论界占领主阵地。
作为查禁鸦片的主要人物,林则徐南下赴粤之初就开始受到《中国丛报》的关注。在无法直接接触林则徐的情况下,《中国丛报》只能通过“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和“未见其人,先闻其事”的方式报道林则徐,塑造了林则徐雷厉风行、不怒自威的媒介形象。在随后的虎门销烟现场,裨治文采用“见人见事”的报道方式,考察销烟场地并会见了林则徐本人。裨治文以“第一现场”见闻展现了林则徐丰富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向西方读者呈现出一个信念坚定、执法如山的禁烟英雄,同时又是一位举止文雅、思维缜密又具有时代先锋精神的伟大政治家,完成了对林则徐媒介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