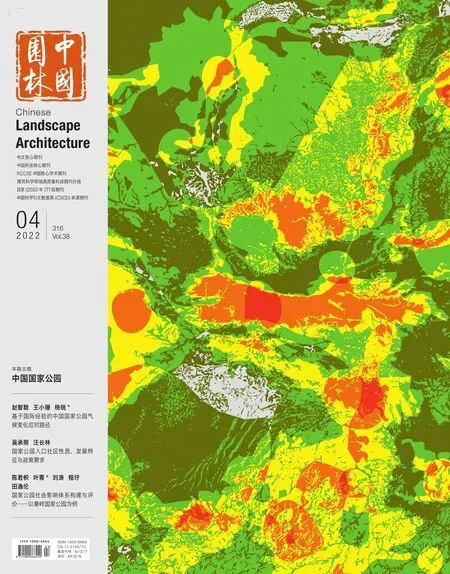基于国际经验的中国国家公园气候变化应对路径
赵智聪
王小珊
杨 锐*
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纵观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成了气候变化应对的先行者。在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双碳”目标等国家战略下,国家公园如何全面、系统地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亟须研究的课题。
1 概述
1.1 研究背景
气候变化正对所有自然和人类生态系统产生影响[1],是全球共同的挑战。联合国将“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目前已有近200个国家签署《巴黎协定》,力争“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能力”。我国也正积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2013年发布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2020年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在我国全面、系统构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的背景下,气候变化成为各行各业积极响应的议题。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丰富[3],兼具极高的碳汇价值[4],是受气候变化影响大同时又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区域,更是风景园林学科和行业为气候变化应对贡献力量的重要载体。
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成为气候变化应对的先行者与探索者。1992年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等国际组织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对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的影响[5];21世纪初,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开始关注国家公园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开展了“气候友好公园项目”(Climate Friendly Parks Program)等[6];2010年前后,美国、英国、欧盟、新西兰等地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制定了系统的气候变化应对战略与行动计划[7-10],这些举措甚至早于其国家层面的气候变化应对政策。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气候变化已对我国海岸及近海资源、冰冻圈、森林及其他自然生态系统产生显著影响。近年来,我国学者已初步开展保护地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11-12],对适应气候变化的管理方法进行了探讨[13-14],但对国家公园如何在规划管理中主动应对气候变化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实践层面,多数国家公园试点的总体规划中提及了气候变化,但仅在科研、科普和监测等部分略有涉及,尚缺乏系统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在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为我国全面、系统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抓手,探寻国家公园气候变化应对路径成为亟须研究的重要议题。
1.2 气候变化应对的概念与主要内容
气候变化应对(Climate Change Response)可泛指一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所做出的反应与行动,也称气候变化行动(Climate Change Action)、气候变化解决方案(Climate Change Solutions)等。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提出“各缔约方应当采取预防措施,预测、防止或尽量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并缓解其不利影响”,指出了减缓与适应2个气候变化应对的主要途径。减缓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增加碳汇,以限制未来的气候变化;适应是指对自然或人类系统进行调整以响应实际或预期的气候刺激或其影响,从而减轻危害或利用有益机会[15]。此外,《公约》第五、六条分别强调了加强气候变化研究与宣传教育两方面内容。
国家公园在我国气候变化应对中可发挥重要作用。响应减缓目标,国家公园的自然生态系统拥有巨大碳储量,具有重要的固碳功能,其保护与修复对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减少生物碳释放具有重要作用;响应适应目标,国家公园内的自然与文化资源具有气候脆弱性,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或风险纳入保护管理范畴,可增强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响应研究目标,国家公园因其具有的原真性与完整性,是观测、了解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载体,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响应教育目标,国家公园内的自然资源变化是气候变化影响的最直观展示,国家公园是公众认识、了解气候变化的重要媒介。美国将其国家公园定位成全国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16],英国也强调国家公园的“气候领导力”,每个国家公园均是区域气候变化应对的领导者[17]。我国国家公园具有国家代表性,当前国际环境下,国家公园的气候变化应对行动对增强我国气候领导力、展现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我国国家公园的气候变化应对包括如下四方面内容:1)依托国家公园的广阔地域与多样生态系统,研究气候变化的影响与响应机制,为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提供科学基础;2)研究气候变化对国家公园的保护管理目标可能造成的威胁,积极适应以减少负面影响;3)响应双碳目标,增加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碳汇,减少碳排放;4)发挥国家公园的“国家代表性”作用与宣传效应,促进气候变化应对主流化。
1.3 研究方法
为探索国家公园气候变化应对的中国路径,本研究选取开展较早、体系完善或具有特色的美国、英国、欧盟、新西兰、澳大利亚与哥斯达黎加6个国家与地区,梳理其国家公园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脉络、战略、政策、规划、技术方法和实践项目等,总结出科研、适应、减缓和教育4个方面的应对途径,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家公园具体情况,提出中国国家公园气候变化应对的4条路径。
2 部分国家或地区国家公园气候变化应对途径梳理
2.1 科研层面:依托多方力量,清晰体系架构,开展监测评估
依托国家与当地的各类研究机构,构建国家公园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一是充分依托国家层面气候变化科研项目,保证相关政策的科学性。如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依托“美国全球变化研究项目”(Climate Change Science Program)进行总体气候战略布局。该计划提供了从气候变化预测到各类保护地适应气候变化方法的各种科学依据与工具[18]。此外,欧盟的联合研究中心(Joint Research Centre)、澳大利亚的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机构(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Research Facility)均为其国家公园的气候变化应对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二是与国家公园所在地的科研机构与高校开展广泛合作,将国家公园建设为研究气候变化的最大天然实验室。如美国阿拉斯加地区国家公园与当地的费尔班克斯大学合作,开展“气候变化情景规划”,构建科研数据、工具、方法和成果的信息共享平台,提供了气候情景预测、未来植物生长条件预测、历史海冰图集等各类数据与成果[19]。
构建系统的气候变化研究框架,为国家公园气候变化政策措施提供科学保障。在国家层面气候变化研究体系基础上,根据管理需要,制定国家公园气候变化研究框架。如新西兰保护部的《气候变化适应科学计划》提出了提高对气候影响认识、完善已有信息与监测体系、保护修复与适应性管理三大板块、14个子课题的研究框架。美国《气候变化应对战略》也提出科研的行动框架,包括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合作开发国家公园的预测模型、建立监测体系、评估与管理碳源汇四大目标,并进一步细化为10项具体行动[7]。
构建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估框架。气候变化脆弱性(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是指系统容易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程度,包括整体性的气候变化和极端情况[20]。《巴黎协定》敦促缔约方“评估气候变化影响和脆弱性,以拟订国家的优先行动”。各国均对国家公园内的自然、文化资源与基础设施开展了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估,了解不同气候情境下,资源与设施会受到何种类型与程度的影响。为使评估结果直接指导决策,多国研发了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如美国《沿海气候变化脆弱性综合评估方法》[21]、欧盟《评估物种和栖息地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补充指南》[22]、新西兰《国家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框架》[23]等,各国评估框架虽有不同,但均从脆弱性核心概念出发,涵盖了气候变化暴露度、敏感性和韧性三方面内容。英国峰区国家公园[24]、美国恶土国家公园[25]等已完成了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估,哥斯达黎加更是完成了其所有陆地保护地的气候变化脆弱性分析[26]。
开展气候变化监测。气候变化监测包括对气候本身的监测与气候变化对资源影响的监测。美国阿拉斯加地区国家公园管理局开展了阿拉斯加资产清查与监测项目,在现有的气候监测网络中增加了20个气象站,并建立了程序清晰、标准化的数据收集与管理系统,每个监测站配备专门管理员,负责上传数据并评估气候变化对公园资源的影响,监测结果会生成定期报告,通过研讨会、工作坊等形式向公众公布[27]。
2.2 适应层面:进行适应性管理,制定多情景响应预案,提升气候韧性
运用适应性管理框架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大挑战在于其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不确定性体现在气候变化的程度不确定及气候变化的影响不确定;不可控性体现在气候变化程度取决于全球的减排努力,而不受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控制。因此,多国国家公园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与规划都采用了适应性管理框架,如英国南唐斯国家公园制定了《气候适应规划》,包括目标制定、风险与机会评估、适应措施及实践反馈等内容[28];欧盟也提出了《Natura2000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管理框架与决策框架》[8]。部分国家公园制定了气候变化适应规划,如匈牙利的《克勒什-穆列什国家公园适应气候变化管理计划》[29]、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国家公园适应性管理与压力响应框架》[30]等。为应对海平面上升、冻土融化、极端天气等气候变化影响可能对国家公园内的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国家公园内的基础设施设计也考虑了气候适应性。如英国国家公园通过增加人行道的透水效率来减少洪水对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害,并设置防洪桥等设施确保洪水中仍有安全通道[9];新西兰国家公园在设施与游憩规划中,提出考虑自然灾害与气候变化的影响,已有设施若无法补救,则要拆除或搬迁[31]。
制定不同情景下的响应预案以面对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不确定性。美国10余个国家公园开展了气候变化情景规划(Climate Change Scenario Planning),基于可能的不同气候变化情景,开展气候变化影响预测与脆弱性评估,给出对应的资源管理方法与保护目标调整方案[32]。新西兰国家公园运用动态适应性路径规划(Dynamic Adaptive Pathway Plan),也给出了多个未来路径下的方案[33]。
提升国家公园气候韧性。气候韧性包括单一国家公园的气候韧性与保护地网络的气候韧性。对单一国家公园而言,完整、功能齐全、健康的生态系统的韧性更强[34],为此美国、英国、欧盟、新西兰等地国家公园均采取相关措施减轻火灾、物种入侵等已有威胁。如新西兰库克山国家公园提出景观尺度害虫控制计划,通过协调多个流域及国家公园周边的土地管理,防止物种入侵,控制已入侵物种的扩散,并加强对主要入侵物种的清除;英国湖区国家公园则将清除入侵植被纳入其志愿活动,让公众共同参与气候变化的应对。当气候变化程度较大时,其影响会超过单一国家公园能够承受的范围,如导致物种迁移出保护地,因此需提高保护地网络的气候韧性。欧盟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方法中,针对生物多样性提出“保护-扩大-连接-整合”的保护战略[35],增加连通性并保护气候避难所[18,36];哥斯达黎加绘制了全球首个基本生命支持区域地图[37],在国土尺度构建生态网络以提高气候韧性。
2.3 减缓层面:摸清家底,低碳运营,保护修复
摸清国家公园当前的碳源汇及碳储量情况,以此为基础制定减排与保护修复计划。多国国家公园气候变化应对的第一步便是“算清碳账”。2002年,美国国家公园最早的气候变化应对行动——“气候友好公园项目”主要内容就是计算国家公园碳排放,在此基础上制定减排计划;2014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计算了所有国家公园的陆地生态系统碳汇贡献[38];欧盟制定《气候变化与自然2000导则》前,开展了Natura 2000网络的碳储量评估[39],并提出对泥炭地与森林等重要碳库开展保护与修复工作;哥斯达黎加则在碳汇、碳储量评估的基础上,结合水安全、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等价值分布,绘制了基本生命支持区域地图,识别了全国的保护、修复与重点管理区域[37]。
促进国家公园及国家公园社区的低碳、可持续运营。首先是降低国家公园自身保护管理、访客接待等工作中的碳排放及环境影响。美国国家公园发起了“绿色公园计划”(Green Parks Plan),提出减碳、节水、绿色采购、回收利用、绿色交通和绿色景观等10个可持续目标[40],部分大型访客中心及偏远的维护站已开始采用分布式光伏供电。对于原住民较多的国家公园,开展了社区减排工作。英国国家公园内有大量农场、牧场与居民,英国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研究发现其碳排放源头主要为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因此提倡采取可持续的土地管理方式,如控制放牧强度、实验探索厌氧消化技术、轮作等,在气候变化敏感区鼓励退耕还林、还草等;此外,还开展了传统建筑可持续改造的培训,以提高原住民对传统建筑性能和能源效率的认识。美国国家公园为调动自下而上的减排积极性,设立了减排激励制度。自2002年起,每年颁发“环境成就奖”,表彰在支持国家公园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和管理目标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国家公园基层团队与合作伙伴。
将碳储存与碳吸收功能提升纳入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对于识别出的碳汇、碳储量高的区域加强保护,对具有较高碳汇提升潜力的区域优先开展生态修复。英国国家公园发起“与自然净零”(Net Zero with Nature)项目,对国家公园及周边地区的森林、湿地、草地和泥炭地开展保护与修复[41]。苏格兰自然遗产(Scottish Natural Heritage)则发起了泥炭地行动,以保护修复具有重要碳储存功能的泥炭地。
2.4 教育层面:解说气候变化,提升气候素养,构建交流网络
将气候变化内容纳入国家公园解说教育体系。国家公园是气候变化影响的最直观展示舞台,从冰川退化到动植物变化等现象,能够让公众直观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从而提升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与行动。因此,美国、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国家公园均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公园解说教育体系,根据各国家公园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实际情况,研发自然教育内容。以美国国家公园为例,国家公园管理局为解说员开发了4个解说气候变化的自学模块课程;各国家公园均制作了气候变化相关的小册子,展示气候变化的影响;还为教师提供国家公园相关的气候变化课程内容与工具;并在多个社交媒体建立了国家公园气候变化账号,展现国家公园受到的气候影响与气候应对行动[16]。
提升员工的气候素养(Climate Change Literacy)。气候素养是指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与解决方案的知识和能力。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影响国家公园各个方面的工作,因此需要让所有员工对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对国家公园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都有基本的了解。2016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发布了《员工气候变化素养:需求评估和战略》,将气候素养细化为17种气候能力,提出各类员工的气候能力要求及对应的培训与激励机制[42]。
构建气候变化交流网络。国家公园不但自身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也带动了国家公园的合作方及周边社区共同参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提出要与当地社区、非政府机构、特许经营商、教育合作伙伴等广泛合作,建立气候变化交流社群,并开发了“气候变化交流工具包”,通过开展气候教育、建立社群、提供相关培训等方式,介绍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提升气候意识与气候素养,推广气候行动[16]。原住民在气候变化应对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澳大利亚大堡礁国家公园约有70个原住民团体,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原住民团体保持良好的沟通,关注气候变化对原住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将原住民可持续利用资源的传统生态知识运用到气候变化应对中[30]。
3 中国路径的思考
自1992年加入《公约》以来,我国积极参与《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国际气候行动。2015年,我国发布《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提出了15条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政策和措施;2020年我国提出的“双碳”目标,为国家公园气候变化应对带来了新的机遇。本研究结合我国国家公园具体情况与各国国家公园气候变化应对经验,提出中国国家公园气候变化应对的4条路径,供国家公园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参考。
3.1 充分凝结共识,鼓励多方参与
气候变化应对涉及国家公园运营工作的方方面面,需要大量利益相关方与各级各类管理部门的参与,也涉及政策、资金、人员等有限保护资源的分配。因此,国家公园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步是凝结共识。各方需就国家公园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国家公园在全国气候变化应对中的定位、国家公园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先事项等问题达成共识。
本研究抛砖引玉,提出如下4个认识供各方讨论。其一,认识到国家公园气候变化应对的代表性,国家公园在全国气候变化应对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不但可以发挥国家公园作为“窗口”的宣传作用以推动气候变化应对主流化,还具有为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提供中国案例、中国方案的潜力。其二,国家公园需采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相比负面影响产生后的被动响应,主动、积极的应对有利于减少国家公园价值损失,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主动积极适应气候变化。其三,气候变化应对要服从于国家公园核心目标,遵循生态保护第一原则,不能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原真性。固碳只是生态系统服务中的一种,部分生态系统虽然固碳功能不强,甚至是碳源,但具有调节、净化等重要的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要警惕唯“碳”论,不能为减排增汇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原真性。其四,减缓与适应并重,“双碳”政策背景下,各行业已就以“减排”为主要行为的气候变化减缓达成初步共识,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也应跻身其中作出贡献;不仅如此,鉴于气候变化正在对国家公园的保护目标产生直接影响,对于国家公园而言,气候变化适应也尤为重要,应做好两手准备,防患于未然。
气候变化影响范围大,应对行动涉及领域广、持续时间长,并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因此气候变化应对不能局限于某个单位或某个部门的行动,要构建多层级、多部门政府协作机制,并充分调动社区、特许经营商、研究机构、志愿公益组织、访客、公众等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
应尽早建立相关机制以促进多方参与。其一,在国家层面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中成立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全国各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的气候变化应对行动;在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中成立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公园内各部门间的气候变化应对行动,与当地政府的农业、交通、能源等部门开展合作,推动国家公园社区及周边地区的低碳可持续发展,如完善公共交通网络、加强清洁能源利用、发展绿色农业等。其二,建立多方参与机制,与高校、各类科研机构开展合作,构建开放的科研数据与成果共享平台;设立节能减排激励制度,对积极减排的特许经营商给予荣誉、资金或政策奖励;与公益组织合作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志愿活动项目;设立低碳游憩激励制度,对访客的低碳行为给予荣誉奖励。其三,建立国家公园与周边社区合作交流平台,发挥国家公园品牌效应,与周边社区合作发起国家公园低碳社区活动,共享气候灾害预警系统,合作共建生态廊道,预留气候缓冲区,提升区域气候韧性。
3.2 夯实科研基础,形成前沿基地
气候变化应对的措施与政策要以科学为依据。相比已有各类威胁,气候变化的威胁在感知与衡量上更为复杂,且气候变化所要应对的主要是未来的威胁,当下应对行动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反馈。因此,气候变化适应政策要建立在对气候变化影响机制、影响预测与科学评估的基础上,气候变化减缓政策要建立在对碳源汇、碳储量现状与潜力的科学评估基础上,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应对政策与行动也需定期调整更新。
为了给国家公园气候变化应对政策与行动提供充足的科学依据,本研究提出以下3个方面的建议。其一,针对国家公园气候变化影响与响应机制开展系统性的科学研究。研究重点包括国家公园和其他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的碳源汇现状与固碳潜力、历史气候变化影响与机制、未来气候变化影响预测、资源与设施的气候脆弱性评估、生态系统气候韧性评估与提升等。其二,加强对国家公园重点生态系统与物种的研究。加强对生态系统内生态过程与重点保护物种习性的研究,为气候变化下的保护优先事项提供依据,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生态系统的关键过程与重点物种的主要生存要素的保护中。其三,加强气候敏感要素的监测并建立数据共享平台。气候变化的研究依赖长期监测数据,成本很高,但相同生态系统的气候影响却具有一定共性,数据与结论都可相互借鉴。因此,应整合形成气候变化研究共同体,加强气候变化影响的监测并建立数据共享平台,以最大程度利用全球的科研力量,为国家公园气候政策与行动提供科学依据。
3.3 战略规划指导,分级分区落实
我国正在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2],且正在更新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应在此基础上,制定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气候变化应对战略。国际比较发现,美国、新西兰等自上而下进行管理的国家公园系统都至少在国家层面管理机构提出了总体应对战略,其气候变化应对体系更加科学和系统。我国应制定“中国国家公园气候变化应对战略与行动方案”与“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气候变化应对战略与行动方案”,为国家公园和各类自然保护地明确气候变化应对目标,制定系统性应对气候变化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全面提升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的治理能力。
气候变化应对行动的落实需要各级政策与规划的支持,建议如下。其一,国家层面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应牵头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与技术指南,包括国家公园低碳运营政策与考核制度、国家公园碳源汇核算指南、国家公园碳汇交易制度、国家公园低碳社区建设指南、国家公园气候变化适应指南、国家公园气候教育与访客低碳行为引导指南,以及加强国家公园气候变化科研指南等。其二,各国家公园以上述制度与指南为依据,开展气候变化应对专项规划。专项规划以科学研究为基础,运用适应性管理框架,制定国家公园气候变化的科研、减缓、适应、教育行动计划与监测评估迭代框架。其三,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公园各类规划、许可和管理决策的评估标准,如将温室气体排放、气候脆弱性评估纳入国家公园设施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促进低碳、适应性基础设施建设;颁发特许经营许可时,优先选取低碳经营的特许经营商;在国家公园生态体验规划与管理中,优先采用低碳的访问方式等。
3.4 适应减缓并重,提升气候能力
基于国际经验,研究提出下列三方面的行动优先事项。其一,开展国家公园“双碳”目标响应行动,计算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当前的碳源汇与碳储量,将生态系统碳汇提升与碳库保护纳入国家公园保护修复工程;同时,制定“国家公园低碳运营计划”和“国家公园社区减碳计划”。其二,开展国家公园气候适应行动,制定气候适应性管理框架,对国家公园重要资源进行气候脆弱性评估,制定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响应预案,识别并保护气候避难所、气候廊道,提升生态系统气候韧性。其三,开展国家公园气候能力建设,评估国家公园员工的气候能力,识别当下气候能力与达成所需气候行动的差距,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培训,设立激励机制,激发员工自主学习动力。
4 结语
本研究系统性梳理了6个国家或地区国家公园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脉络、战略、政策、规划、技术方法与实践项目等内容,总结出4个方面的应对途径。科研层面,各国依托多方力量,构建了清晰的研究架构,强调科学监测评估;适应层面,各国纷纷进行了适应性管理,制定了多情景响应预案,提升气候韧性;减缓层面,各国均采用适当测算方法摸清家底,鼓励低碳运营,开展保护修复;教育层面,多国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公园解说教育体系,开展培训以提升员工气候素养,构建了气候变化交流网络。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中国国家公园气候变化应对的4条路径:充分凝结共识,鼓励多方参与;夯实科研基础,形成前沿基地;战略规划指导,分级分区落实;适应减缓并重,提升气候能力。
在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双重背景下,国家公园的气候变化应对有望成为两大战略的共同抓手与代表,国际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国家公园应立足区域、放眼世界,成为区域气候变化应对的领导者、国家气候变化应对的代表,提供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中国方案。
致谢:感谢“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管理分局课题合作研究采购项目”对本研究的支持;感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研究生陈路遥、陈雪纯、李可心、王方邑、彭家园为资料收集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