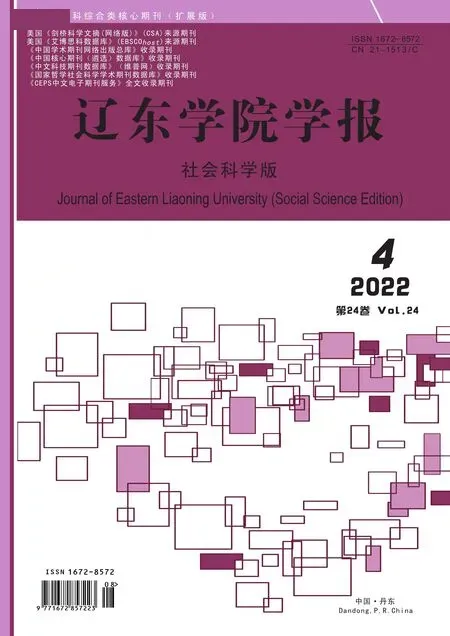时代话语环境与陈子昂的“汉魏风骨”指向
朱其欢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30)
一、陈子昂所处时代的言论环境
陈子昂生活的武则天时代,社会政治相对清明,武则天一直是积极鼓励朝臣进谏。早在公元674年,武则天称天后之际陈子昂就上“建言十二事”[1]3477,第六条就是要“广言路”[1]3477,不得不说是先见之举。据《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三月,初置匦于朝堂,有进书言事者听投之。”[2]118为能及时阅读和处理这些意见,武则天特地设置了一个专门机构——匦使院,隶属中书省,并以谏议大夫补缺拾遗一人任知匦史。凡臣民有冤滞和匡正补过、进献赋颂者,皆可写成书面材料,分别投入不同的匦中。《资治通鉴·唐纪》具体记述了匦的使用方法:
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申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3]6438
可见,朝南丹匦名曰“招谏”,就是为了鼓励谏诤、广开言路。除此,《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还记载:“丙申夜,明堂灾,至明而并从煨烬。庚子,以明堂灾告庙,手诏责躬,令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极言正谏”[2]125,“以天下大旱,命文武官九品以上极言时政得失”[2]125,可见武则天并非一味专权,时常就灾事询问百官意见。以上例子证明武则天能开谏诤之门,鼓励大臣批评朝政。又据《新唐书·朱敬则传》“初,武后称制,天下颇流言,遂开告密罗织之路,兴大狱,诛将相大臣”[1]4219,可见朱敬则曾于武后时上书进谏。其谏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宽简,润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1]4219朱敬则直接以秦朝灭亡的后果劝告武则天。对于朱敬则的直言武则天并没有降罪,而是“善其言,迁正谏大夫,兼修国史”[1]4220。可见武则天鼓励朝臣谏诤不是流于形式,而是真正付诸行动。再者,武则天重用贤相狄仁杰也说明她能虚心纳谏。武则天多次听取狄仁杰的谏言,对狄仁杰一些逆耳的言论也没有降罪,甚至对狄仁杰敢于直触逆鳞、反对她意欲立“武姓”为王储之事也能接受。《资治通鉴·唐纪》:“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数使人说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太后意未决。”[3]6526针对这种将要颠覆李唐江山的企图, 狄仁杰从容言于太后曰:“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姑于庙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预知。”仁杰曰:“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最终“太后意稍寤”“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3]6526。以上诸例从多方面说明武则天执政期间言论是相对自由的。陈子昂身处这样的环境,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他要适时利用这个良好的环境去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文学理想。
二、陈子昂主张“汉魏风骨”的原因
“风骨”传统中断已久,陈子昂再次主张,“汉魏风骨”客观原因是当时宽松的言论环境,主观是因为其个人的政治和文学理想。与其说《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是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主张,不如说是构建其政治报负的重要宣言。陈子昂在《答制问事八条》之一的“重任贤科”中说贤人为“政要之至极”[4]1229,在“招谏科”中说“然朝廷尚未见敢谏之臣,骨鲠之士,天下直道,未得公行”[4]1231。陈子昂认为国家政治蓝图的构建,需要文人的积极参与,如果文人缺乏风骨,不敢言不敢做,那么世风将愈加衰颓,朝廷的政策就将会难以执行和缺乏监督,他的政治理想大概率不会实现。所以陈子昂对文人提出的强烈批评是其构建其政治理想的一部分。
(一)政治理想
关于陈子昂,《唐才子传·陈子昂传》记载:“初,年十八时,未知书,以富家子,任侠尚气弋博。后入乡校感悔,即于州东南金华山观读书”[5]105。书中亦载其父陈元敬“以豪侠闻。属乡人阻饥,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5]102。在这样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陈子昂很容易养成一种激进直率的性格,所以入朝为官的陈子昂成为了坚定的改革派,这从他多次针对武则天的朝政措施直言进谏就可以看出。陈子昂的政治思想,概括之就是实现儒家之所谓“大同”社会。《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6]582,这是中国古代儒家所信奉的最高政治理想。陈子昂也不例外,其政治理想的构建主要包括“攘外”和“安内”两个部分。
据《资治通鉴》记载,在武则天当政的半个世纪中,突厥、吐蕃、契丹的侵扰多达50余次,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的安全。陈子昂于垂拱二年(686年)随乔知之北征,亲眼目睹了那里的政治、军事形势,归来后即向武则天呈上了 《为乔补阙论突厥表》 和 《上西蕃边州安危事》等书表,揭露边塞“主将不选,士卒不练”“故临阵对寇,未尝不先自溃散,遂使夷狄乘利”[4]759等实情。他在《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匈奴为中国之患,自上代所苦久矣”[4]755,并发出“匈奴不灭,中国未可安卧亦明矣”的感慨,指出应趁匈奴内忧之际“行远图,大定北戎”。在《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中,陈子昂始就武则天不许十姓君长入朝之事进行劝谏,并精准地指出外敌的野心,“夫蕃戎之性,人面兽心,亲之则顺,疑之则乱,盖易动难安,古所莫制也”[4]1302,又为巩固边防提出数条建议。史书记载陈子昂于垂拱二年(686年)和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先后两次随军出征,到过边塞。边患问题一直是陈子昂所忧虑的,他的一些主张并不是捕风捉影,而是其深入边境腹地亲自考察形势的结果,是有建设性的。可惜的是,武后“虽数召见问政事,论亦详切,故奏闻辄罢”[1]4077,可见陈子昂的“攘外”主张并没有被采纳。
除却对边患问题的忧虑,“安内”亦是其政治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为本”是陈子昂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在《谏政理书》中陈子昂说“王政之贵,莫大乎安人”[4]1376,在《为陈御史上奉和秋景观竞渡诗表》中提出的“近而安人”[4]627,都是其鲜明的政治主张。陈子昂在诗文中反复对武则天不善待百姓的行为进行尖锐的批评。比如《感遇·其十九》中,就武则天为修佛像大肆劳民伤财的行为表示不满,发出“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4]87的感叹;其在《上军国利害事》中道“夫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轻其死则无所不至也”,并直谏武后要“垂衣裳,修文德,去刑罚,劝农桑,以息天下之人,务与之共安”[4]1289,为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可见在陈子昂政治思想中,百姓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陈子昂也深刻认识到作为一个不得施展抱负的失志之人,凭借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现实。在《感遇·其二十》的“一绳将何系,忧醉不能持”[4]90中,陈子昂流露出一种沧桑的孤独之感,希望文人能够自拾“风骨”,关注时事,以百姓国家为念,共同构建“大同”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其中有陈子昂自述在解三处无意中见到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东方虬在武则天执政时任左史,《汉书·艺文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7]1715。左史的前称为“起居郎”,唐贞观初于门下省置起居郎,掌记皇帝日常行动与国家大事,龙朔二年(662年)改起居郎为左史。该官职本质是对皇权施以制约。陈子昂在武则天执政时曾担任右拾遗。唐朝设左、右拾遗,是谏官的一种,主要是向皇帝奏论政事,称述得失。从这个角度来说,陈子昂和东方虬之间的对话不是两个普通诗友之间的对话,而是唐朝左史和右拾遗两个官员之间的对话。陈子昂笔下的“修竹”与他赞叹的东方虬笔下的“孤桐”除了是对当时文人不言朝政缺乏风骨的一种批判,也寄予了对官员应具备坚贞孤傲、骨气端翔品质的一种期待。所以说《修竹篇序》实则也是陈子昂构建其政治理想的重要宣言。
(二)文学理想
陈子昂关于文学的见解在不少诗序中有涉及,如《薛大夫山亭宴序》中的 “诗言志也,可得闻乎”[4]1158,《饯陈少府从军序》的“盍各言志,以叙离歌”[4]1171,《偶遇巴西姜主薄序》的“挥手何赠?诗以永言云尔”[4]1205,《金门饯东平序》中的“请各陈志,以序离襟”[4]1150等序,均直接展现了“诗言志,歌永言”的传统。而陈子昂完整的诗论主张,则主要反映在《修竹篇序》一文中:
东方公足下: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赌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4]163
从此序文可以看出,陈子昂主张要创作出有“风雅”和“兴寄”的作品,即诗歌要有讽谏意味同时也要有情感寄托,要彻底革除陈陈相因的宫廷文学与辞藻艳丽内容空泛的形式主义诗风,最终将诗歌拉回写实主义一途,这是陈子昂的文学理想。
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在继承“汉魏风骨”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是陈子昂提出的诗美理想,这里涉及诗歌的声律问题。“汉魏风骨”即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诗歌创作更多的还是关注诗歌的内容与诗歌风格的古朴,对于“声律美”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其二,陈子昂在诗歌中显露出的对宇宙人生的认识是具有超前性的。例如《感遇·其一》中的“太极生天地,三元更废兴”[4]25,《感遇·其六》中的“玄感非象识,谁能测沦冥”[4]41,《感遇·其十三》中的“闲卧观物化,悠悠念无生”[4]66,以及《登幽州台歌》中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4]269。这种以宏观的态度自觉去探索宇宙奥秘的意识是建安诗人所不能比拟的。总的来说,陈子昂所作的《感遇》38篇是其诗文革新的标志性作品,实现了壮大昂扬的情思与声律和词的采美相结合,是其为唐代诗歌健康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三、陈子昂“汉魏风骨”论的指向
(一)“汉魏风骨”论的文学传统
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都曾涉及“风骨”概念。《文心雕龙·风骨》篇中的“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8]513,主要从作品“情志”和“言辞”两个方面进行阐释。钟嵘也提倡风骨,不过他使用的词语是“风力”或“骨气”。《诗品》称曹植“骨气奇高”[9]39。《诗品序》中钟嵘又指出:“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9]6,“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9]9。这里所说的“建安风力”实即“建安风骨”。刘勰、钟嵘两人都极力推崇“建安风骨”,把它作为对六朝形式主义文风进行批判的武器。到了唐代,陈子昂基于改革文风的需要,高倡“汉魏风骨”,用“风骨”作武器,横扫六朝绮靡文风之余习。从文学传统而言,对当时诗歌创作形式主义的批判是陈子昂高倡“汉魏风骨”的一个方面。
(二)“汉魏风骨”论的社会环境
就社会环境而言,陈子昂主要是对当时文人创作风气表示不满,用“风骨”来对文人施以批评。文人争相创作应制诗来歌咏盛世,希图博得龙颜一悦获得高位;或是为了保住官位一味附和,不敢对朝廷政策提出任何质疑。陈子昂认为这群文人已经丢失了风骨。
初唐贞观时以太宗为中心的宫廷诗人创作群体,继承了南朝宫体诗的许多体制和风格,热衷于创作流连光景的闲适诗,咏物赠答题材占了很大一部分。如太宗《元日》:“高轩暧春色,邃阁媚朝光。彤庭飞彩旆,翠幌曜明珰。恭己临四极,垂衣驭八荒。霜戟列丹陛,丝竹韵长廊。穆矣熏风茂,康哉帝道昌。继文遵后轨,循古鉴前王。草秀故春色,梅艳昔年妆。巨川思欲济,终以寄舟航。”[10]8诗作艳丽而秀美,完全与齐梁体诗风一脉相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太宗影响之下,整个宫廷弥漫着庸俗浅薄的诗歌创作风气。到武则天执政时,诗歌创作风气并没有得到大的转变。武则天本人酷爱文学,多次主持诗歌唱和活动。《旧唐书·礼仪二》记载:“其年,铸铜为九州岛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鼎成,自玄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则天自为曳鼎歌,令相唱和……”[2]868由此可以看出武则天主持的诗歌唱和活动不仅声势浩大,而且往往亲自参与。除此,《尧山堂外纪》中也有记载:“武后游龙门,命群臣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夺锦袍赐之”[11]395。东方虬与宋之问当时所作的诗句一直留存。东方虬:“春雪满空来,触处似花开。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10]1075宋之问:“宿雨霁氛埃,流云度城阙。河堤柳新翠,苑树花先发。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映几重。群公拂雾朝翔凤,天子乘春幸凿龙……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11]395这种纯粹意义上的应制诗,群臣皆认为其“文理兼美”,可以想见当时社会繁缛浮华的诗风占据主流地位。武则天执政时,文坛上主要活动的文学群体是珠英学士集团,文章四友等。据《旧唐书·张行成传》附传:“以昌宗丑声闻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诏昌宗撰《三教珠英》于内。乃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谟等二十六人,分门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2]2707珠英学士皆为诗人兼学者,在修书其间,日夕谈论,赋诗聚会,是初唐后期规模最大的一个宫廷诗人聚会。聚会时所制诗文大多是“黼帐帷宫,缛文房之绣彩;祥云瑞景,霏翰苑之荣光”[4]628。例如沈佺期的《昆明池侍宴应制》,完全与齐梁形式主义诗风一脉相承,其中除了对山水景物刻板的描绘,没有一丝一毫涉及时事。“文章四友”中的李峤、苏味道、崔融都做过高官,但是他们“在其位不谋其政”,而是将自己的才华禁锢于宫廷御苑、楼阁台榭。
反观汉魏文人,即使是身陷囹圄,也不忘对朝政百姓的忧虑。汉末政治腐败,士路艰窘,反而激起了士人们普遍的关心政治和从政的热情,出现了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名士。如陈仲举就是“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12]1。东汉文人五言诗中的许多篇章,如《今日良宴会》中“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13]56,以及赵壹、郦炎等人的诗中反映出来的当时文士清谈的行为,都不仅仅是在饮酒作乐那么简单。这些古诗中写诗人慷慨激昂地谈议,正说明聚会的清谈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涉及政治,其中当然不乏对时人时事的褒贬和对世相的批评。故《后汉书·党锢列传》曰:“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14]2185其中的“处士横议”就是指当时议论朝政的一种风气。到了魏时,从三曹到建安七子,无不怀抱“救民涂炭”之志,曹操以天下为己任自不必说,王粲、徐干、应玚等诗人也有关心天下百姓之怀。比如王粲的《七哀诗》真切地描绘出了战争中百姓所承受的悲苦,可谓句句泣血。这些诗人无疑是具备风骨的。
陈子昂之所以主张“汉魏风骨”,本质上就是针对晋宋以来文人自抛“风骨”的行为,他希望通过呐喊唤醒文人重拾丢弃已久的风骨。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云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又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8]67,由此可见,晋宋时期文坛盛行只知谈玄说理,醉心山水的不良风气。文人已丢失风骨,不再怀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诗人已被山水浸渍得毫无风骨可言了。晋宋时很多身处魏阙的文人,像谢灵运、谢朓等,享受着比下层百姓优厚的待遇,却只知道吟咏风月,局限在自己的世界里,对朝政、对社会却不甚关心。这与初唐时期的很多诗人沉湎舒适圈,只写无实际意义的应制诗与流连光景的闲适诗的情况很像。陈子昂认为这群文人丧失风骨,沦为只会追求权位的“傀儡”。陈子昂希望能够激励诗人重拾“风骨”,故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后附《修竹诗》一篇来阐释文人“风骨”的具体内涵。“龙种生南岳,孤翠郁亭亭”“岁寒霜雪苦,含彩独青青”“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4]163……这些诗句,表面是在赞扬竹子的坚贞与挺拔,实则句句在说做人。做人就是要和竹子一样,无论是在严寒还是酷暑,都应该保持挺拔的姿态,坚贞不移,展现凛凛风骨。
陈子昂“风骨”论除了是对当时文人创作风气的不满,还包括对文人为避祸不涉朝政的批判。《资治通鉴·卷二百三》云:
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3]6439
为了巩固统治,武则天采取了极其黑暗与恐怖的政策。为了剪除李唐宗枝,她任用酷吏,放纵滥刑,朝廷人人自危,噤若寒蝉,针对武后这种有违天道的行为,只有陈子昂先后多次上书进谏,并把矛头直指酷吏,其在《谏刑书》中说:“臣闻自古圣王谓之大圣者,皆云尚德崇礼,贵仁贱刑,刑措不用,谓之圣德,不称严刑猛制、用狱为理者也”[4]1361,之后他又呈上《谏用刑书》再次极谏滥刑。除此,《旧唐书·张行成传》亦记载:“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荐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宗晋卿候其门庭,争执鞭辔,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引辞人阎朝隐、薛稷、员半千并为奉宸供奉……辞人皆赋诗以美之,崔融为其绝唱……”[2]2706可见,当时文人已完全沦为名利的工具,他们不书写人情冷暖,而是为权贵歌唱。在《两唐书》所记载的谄附文人中,宋之问、阎朝隐表现尤甚。陈子昂在其作品中多次批判这种阿谀奉承致世风衰颓的行为,如:《感遇·其十》中的“谗说相啖食,利害纷口疑口疑。便便夸毗子,荣耀更相持”[4]55;《十六》中的“蚩蚩夸毗子,尧禹以为谩。骄荣贵工巧,势利迭相干”[4]75;《二十》中的“玄天幽且默,群议曷嗤嗤。圣人教犹在,世运久陵夷”[4]90等。可见,对文人自身德行有亏、不保坚贞行为的批评,也是陈子昂“风骨”论批判的一个方面。
四、结论
对陈子昂文学成就的评价,后人认为其高倡“汉魏风骨”,一扫六代纤弱文风,是唐代诗界走上革命道路的檄文。如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云:“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15]2402;再如韩愈《荐士》评价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10]3780; 白居易《初授拾遗》亦云:“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10]4658。王夫之则说: “陈子昂以诗名于唐,非但文士之选也,使得明君以尽其才,驾马周而颉颃姚崇,以为大臣可矣。”[16]634这是对其政治才能的高度评价。 陈子昂高倡“汉魏风骨”,除了是对晋宋以来形式主义文风的批评,更重要的是对文人自失风骨行为的批评,而初心都是其“忧国忧民”的情怀。陈子昂用自己短暂的一生深刻阐释了文人的凛凛风骨,正如其《修竹诗》中所言的“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