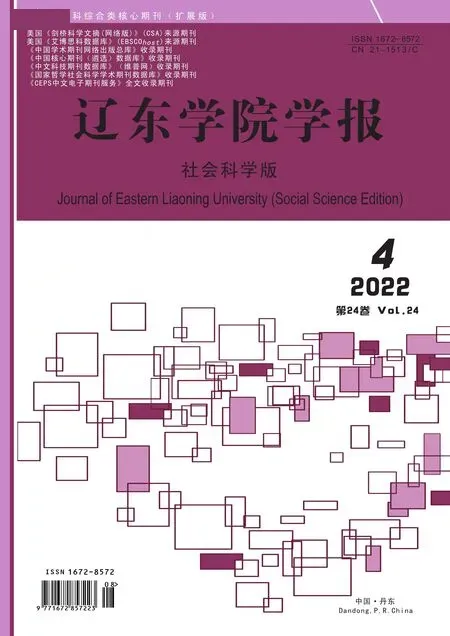蒙古族灵幻小说中的自然意象及其叙事功能
朝鲁孟其木格,乌吉斯古楞
(内蒙古师范大学 蒙古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引 言
灵幻(蒙古语为Zθng Shidilig)小说是内蒙古文学发展史上首支自觉成立的文学流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乌力吉布林、阿赫林、金宝等作家的小说被认为是该流派的创作初期作品。学者莎日娜根据这些作品怪诞、梦幻等特点,将其统称为“灵幻小说”。从创作动机与创作观念来看,灵幻小说家们并非只为创作而创作,而是对宇宙、世界、人、生命等进行深度探究。他们探索世界的复杂性、多元性、无限性以及可能性,将眼光从狭隘的民族视野拓宽到世界和人类。这一点与流派宣言中“与世界文学进行交流、对话”[1]的愿望相符合。灵幻小说家们作品中的怪诞、神秘、夸张、变形,一方面是古代英雄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习俗中的进一步演化,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观念与表现形式启发的结果。灵幻小说中的自然意象是作家们上述追求的体现,作家们不再满足于讲述完整的故事,而是重视各种意象在叙事中起到的作用,通过广泛运用意象使灵幻小说作品具有更加深刻的蕴含。
一、灵幻小说自然意象的选择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提道:“一旦把物象的来源,以及它赋予意象的外观作为标准,去衡量意象的类型,那就可将意象的类型区分为以下几类:自然意象,社会意象,民俗意象,文化意象,神话意象。也就是说,它可以来自世界的各个领域,以极大的兼容性,兼容着各种物象和各种情趣,使意象叙事本身变得丰富多彩。”[2]290因此,文学作品中的意象丰富多元,在作家精心选择后成为一种审美载体,进而蕴含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
当代蒙古族灵幻小说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洞穴、沙漠、山丘、密林、草原、石头”等自然意象,从古至今在蒙古族文学里十分常见。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自然意象来自游牧民的日常生存空间,也是游牧文化的组成部分。游牧民依据自然事物来判断空间方位、空间距离、空间特征以及时间,所以这些自然意象所承担的功能涉及游牧民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存地带、经济、生态、心理、审美、社会等等,构成一个体系。在文学艺术中,自然意象不仅仅作为故事的背景空间而存在,有时能够承担独立的意义,决定空间中人和事物的存在方式,甚至被赋予了不同意义。“文学作品不仅描述了地理,而且作品自身的结构对社会结构的形成也做了阐释。”[3]56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被作家或多或少赋予社会意义,然而文学中的空间处于新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文化话语时它们所被赋予的意义不是单一的,这往往取决于小说家对它们的重塑。
从生命崇拜的视角来看,大自然是“有生命的地方”,是“活的场所”[4]16。蒙古族人类学观念中,大自然是游牧生态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蕴含着对大自然、生命宇宙的深刻认识和细腻阐释。由此而言,自然具有神圣性,表现在游牧民对自然持有的敬畏心理,包括日常生活最普遍的自然事物,如天空、大地(包括山、坡地、岩石、沙漠、崖、土地等)、水流(包括河、溪、湖等)、路、树木以及动物等。在文学艺术中,对自然的敬畏心理会无意识地渗透进作家们的创作中,表现为意象的反复出现、反复重塑,产生不同意义。就灵幻小说而言,作家笔下描绘的洞穴、沙漠、山丘、密林、草原、石头等无不充满神圣性和神秘性,令人既崇敬又畏惧,甚至被赋予异质性,被不断重构。
灵幻小说中,一些自然意象并非孤立的自然存在,而是一种象征或隐喻。如“洞穴”,在乌力吉布林的《暗天无日的20天》[5]中,主人公刚巴跟随神秘女子找到的“洞穴”是一座古墓,他觉得自己一夜暴富的愿望马上就会实现,眼前的“洞穴”神秘而充满诱惑,在巨大的诱惑与非理性的本能冲动下,刚巴拉着同伴进入“洞穴”内部进行探索。洞穴内漆黑、潮湿、泥泞,脚底下除了金银财宝还有人畜的尸骨,可洞口突然被巨大的岩石堵住变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怀着一夜暴富愿望的两个人在封闭的“洞穴”中经历了从兴奋、挣扎到最后绝望的过程,两个人的生命也逐渐耗尽,刚巴的伙伴在求生的痛苦挣扎后绝望自杀。刚巴眼睁睁地看着伙伴死去,求生的欲望胜过了最初的对金钱的欲望,他真正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如何度过有限的生命?不愁吃穿,过安安稳稳日子的时候,应该想到些什么?世上最珍贵的是什么?常言说,只要活着就能从银碗里喝到水。这说明了什么道理?”[5]238结尾中,刚巴从“洞穴”中获救,从漆黑中走出来的刚巴就像获得生命的再生与自由,外面的阳光、微风让他感到惬意舒适,让他感到此刻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小说中的“洞穴”不仅是埋葬生命的空间(其内部遍地尸骨,刚巴的同伴也在洞穴里死去),同时也是重塑生命的空间,刚巴重新认识了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获得再生。
在昂格图的《挂在云间的口袋》[6]中,主人公“我”好几天夜里听到一个陌生人的声音,约“我”在日出时分去苏力德沙坡相见,而陌生人与他约定的“苏力德沙坡”在现实中却是个“禁地”。对于生活在大漠中的人来说,它是“荒野的、神圣的、有灵的”沙坡,从来没人爬上去过,更不知道爬上去是好是坏,是活是死。等到第三天,“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于是在日出的一刻爬上了“苏力德沙坡”,正当徘徊时只见头顶响过雷划过闪电,“我”刹那间掉进一个“圆形洞穴”,里面封闭得连个插针的缝隙都没有。“圆形洞穴”内部结构十分复杂,不断分叉、层叠不穷,“我”穿过层层机关越走越深,走到最后眼前出现了一座无比巨大的庙,庙里堆满了各种金银珠宝,后来发现这些财宝是一个伟大人物的随葬品。正当“我”好奇时,梦里出现的陌生人说,是时候回去了,但今天的所见所闻要在一百年后才能说出来。听到这话“我”有些生气,因为百年后早就不存在了,觉得等到那时,这些埋在地下的财宝会白白浪费。经过一番思考后“我”理解了伟大人物为子孙后代能够在将来更好地生存而做的先见之明,他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远比眼前这些金银财宝多得多。最后“我”带着沉重的思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圆形洞穴”[6]213。小说中,“我”进入“圆形洞穴”选择了“地狱”字样的“洞穴”进去游历了一番,最后在神秘人物的引导下战胜欲望开始觉悟,精神得到重生。游历“地狱”的“洞穴”后精神重生的内容不得不让人联想到《神曲》中但丁在理性象征维吉尔的引导下通过地狱、炼狱获得新生的过程。虽然远不及《神曲》所体现的思想蕴含,但这部作品中“我”游历“圆形洞穴”的过程却象征了人战胜自身的各种贪欲或者欲望,最终内心反省,精神获得再生。洞穴里看不见的神秘伟人虽然代表过去,但比起他的肉体,其精神却依然在延续、发展,甚至影响后世子孙。
因此,与之前《暗天无日的20天》中的“洞穴”让人生命获得再生的意义不同,《挂在云间的口袋》中的“洞穴”象征人的精神再生。这种“洞穴”与再生的故事原型可以追溯到蒙古族古代英雄史诗中的“石洞”意象与复活的情节结构。例如,在史诗《江格尔》中,在江格尔两岁时,家乡遭遇劫难,他被父母藏进白色的山洞中并用石头堵住洞口,父母被杀害,而江格尔活了下来;还有一次,英雄们生活的“宝木巴”被莽古斯洗劫,英雄们被莽古斯俘虏捆绑并昏死过去扔进了石洞里,后来英雄萨布尔与莽古斯交战取得胜利后去石洞祈求天神降下甘霖,众英雄得到了复活。 在孟克的《鹿斑狼》[7]中,同样出现了“洞穴”意象,是主人公若布华老汉生存的白头山“山洞”。若布华因为与挖掘开采山岩的人发生争执失踪后独自一人来到“山洞”里生活,由于通往“山洞”的道路崎岖艰险,人们很难找到上山的路,况且有人曾经试图越过通往“山洞”的路,在悬崖峭壁断送性命,之后那里就成了“禁地”[7]29。“山洞”生活让若布华处于一种最原始自然的生存状态,无论从肉体还是精神上都与外面的世俗世界隔绝起来,而与之对立的则是身为生态学家的儿子所处的现代文明世界。偶然的一天,老人的儿子奥力吉拜领着一群陌生“专家”闯入父亲生存的“洞穴禁地”,扰乱了只属于那里的秩序。小说中的“山洞”象征人类回归自然,另一方面则象征某种归属感或者回归到“根”。小说中若布华老汉梦中经常被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呼唤,让他“回到家”“回到自然”,这便是一种暗示。当“山洞”空间作为自然的象征时具有原始性、神圣性,是令人敬畏的地方。而小说中外界的不断闯入者导致生态遭到破坏,若布华老汉成了那片地带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守候者。“山洞”意象作为归属地或者“根”的象征体现在作者以“苍狼白鹿”始祖神话为原型,让若布华老汉与他年轻时的爱人在梦幻与现实交替中分别以狼和鹿的形象出现。
与上述“洞穴”意象的“再生”“回归”“归属”及“根”所表现的“有生命的地方”不同,小说《不毛之地》[8]中,“草原”意象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地方”,极具讽刺。小说里的“草原”黄沙漫漫,看不到一丁点绿色,与“我”童年时的草原有天壤之别,“我”回到家一片黯淡,毫无生机。无论是在以往的蒙古族文学作品中,还是在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对“草原”的描绘与塑造往往充满生机,令人神往。但《不毛之地》中的“草原”却显得不安、未知和不确定,人的精神与身体处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状态。文学作品中,“草原”往往与“家乡”“家园”等同,是人最基本的生存空间。巴什拉认为:“家是人在世界中的一角,是人类最初的宇宙。”[9]146对生长于“草原”的人来说,这是他们最基本且最原始的居所,也是他们身体与精神的庇护所,它具有一种强大的融合力,承载并聚集了人们的回忆、梦想等,失去了它就等于失去了安稳的存在。
另外,吉日木图的《千只黑眼》[10]中讲述了一位大使为给失明的儿子陶力恢复视力,闯入一片“森林”寻找乌鸦并挖出一千只乌鸦的眼睛,结果遭到乌鸦群报复,最后以失败告终的故事。小说中的“森林”显然是自然的隐喻,“乌鸦”则是生命的象征,同样作为生态体系中的生命个体,人类因自身利益去牺牲更多生命的事情违背了生态伦理,破坏了生命的规律。所以在这篇小说中,“森林”成为了让人类发现自我、反思自我的空间。
上述作品中出现的自然意象是灵幻小说作家们自身生存经验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精心选择设置的意象,在叙事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蕴含着深刻的意蕴。
二、灵幻小说自然意象在叙事中的作用
巴·布林贝赫先生曾在《蒙古英雄史诗诗学》[11]50-58中提出的“史诗地理学”的概念,认为在蒙古族英雄史诗中不仅有反映实实在在存在的地理空间,还有大量通过想象创造的空间,但这不仅仅局限于英雄史诗,在民间故事里也非常普遍。“史诗地理学”这一概念,把蒙古族英雄史诗中出现的地理空间划分成四类,分别为:具体的地名(如阿尔泰、额尔齐斯江、阿米尔河、塔尔巴哈台、普陀山等);艺术创作和抒情感的地名(如花的原野、毁坏的山梁等);表现游牧生活的集体记忆中的通用的地理名称(如辉腾河,意为冰冷的河;呼和锡礼,意为蓝色山丘);从宗教、神话与民俗有关或者源自印藏的地理名称(如阿纳巴德海,蒙古语作欢乐海;乳海,意为纯洁的奶;宝木巴故乡;相约的小山丘等)。史诗中,这些地理空间发挥着各种不同的功能,成为故事情节发生发展的重要场所。巴·布林贝赫先生以“相约的小山丘”[11]63为例子,这个地理空间在不同史诗中多次出现,而每次发挥的功能都有所不同,如:双方交战的“场地”,传达消息的“站”,望远、观察地势的“岗”,传达信息鼓舞众人的“台面”,休闲休息的“场所”,套马的“场所”,迎接凯旋英雄们的“圣门”,交战双方的领地“分界线”或自然的“屏障”,敬拜腾格里以及众神灵的“朝拜敖包”,等等。“史诗地理学”中的地理空间是古代先民原始思维与想象的产物,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在当代叙事文学中,这些地理空间作为意象参与叙事并建构叙事,作家们借助意象达到叙事的各种目的。
灵幻小说中的自然意象同样在叙事中具有多重功能,为把握文本发挥关键作用。
灵幻小说中,作家通常会安排一个自然意象作为叙事线索来推动故事情节,如《扎巴萨尔山谷》[12]中的“扎巴萨尔山谷”(“扎巴萨尔”意为中间,小说中指双峰山中间的峡谷)、《鹿斑狼》中白头山的“山洞”、《史诗中的希拉塔拉》[13]中的“希拉塔拉”草原、《阿拉木斯山》中的“阿拉木斯山”等等。《扎巴萨尔山谷》中,“扎巴萨尔山谷”贯穿主人公丹达尔老汉的一生,年轻时他在这里与萨日莱相遇、约会、结婚,而这些都已变成回忆。老年丹达尔每次来到“扎巴萨尔山谷”,昔日美好的记忆就会不断涌现,亦幻亦真中他遇见自己未曾谋面的女儿,最后也是在这里他的生命走到尽头。“扎巴萨尔山谷”将主人公的过去与现在来回切换,并把一个个情节片段展现出来,最后拼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与此相似的是孟克的《鹿斑狼》,“白头山”是叙事的开头,“自古以来都说白头山有神灵。能看得见尖峰上飘拂的风马旗。到底是何时、何人扎下风马旗,而又为什么、如何祭拜白头山,对此人们难以做出判断”[7]1,“白头山”神秘而令人敬畏。若布华老汉的失踪以及后来上山都与“白头山”密切相连。“白头山”的岩石不断被挖掘开采,山上的植物与动物变得稀少,若布华无法容忍这种情况便对开采者开了几枪警告后,为躲避人们的追踪逃到山上的山洞,从此与外界断了一切联系。老汉在“白头山”过着最自然、最原始的生活,在梦幻与真实中与变成鹿的爱人相见、交谈,展开主人公过去的种种生活经历。与“扎巴萨尔山谷”相似,这里亦真亦幻,时空来回切换,贯穿人物一生的活动。不难看出,“白头山”这个意象不仅从头到尾参与叙事,而且逐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与此相似的还有金宝的小说《阿拉木斯山》[14],小说中的“阿拉木斯山”连接历史和现在,连接现实世界与超验世界,时间在此倒流,又在此往前流,这一意象作为一个空间完全成了一个时间的标识物。
在另一篇小说《史诗中的希拉塔拉》中,“希拉塔拉”既是具体的地理空间又是人们意识中建构的空间,历史上这个地方是英雄战败和牺牲的地方,是贯穿整篇小说的重要线索。 “我”为了写一部以“希拉塔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而踏上取材的旅途,途中“我”听着车载CD中响起的关于“希拉塔拉”的歌曲(蒙古族民歌《希拉塔拉之上》),不知不觉睡着并做了个梦,梦中见到的正是那场在“希拉塔拉”失利的战争以及战败牺牲的英雄阿拉坦沙嘎。无数次寻找“希拉塔拉”的旅途让“我”突然感悟到:“为了写一部关于希拉塔拉的长篇小说历经数年采集素材,但凡叫希拉塔拉的地方几乎都采访过,这次的旅程也将化为泡影,我们离开希拉塔拉正在返回的途中。说实在的,希拉塔拉是受伤的士兵留下遗嘱牺牲的地方。我突然觉悟到原来它只是留下的后人在歌中唱的传说之地。”[13]356“希拉塔拉”是“我”写的小说里的地方,是民歌里的地方,是梦里出现的地方,被称作“希拉塔拉”的草原有无数个,但最重要的是它早已变成一种精神象征存留于人们心中。因此,这一意象在叙事中作为线索最终解答了“我”的困惑,同时也推动整个叙事的进程。
灵幻小说作家选择的自然意象能够丰富叙事的意义内涵,因而在小说中自然意象发挥着深化主题意蕴的重要作用。《石头的自由》[15]中,“石头”这一意向是理解整个小说的关键。这篇小说是民间传说故事中的猎人海日布(1)海日布是蒙古族民间故事《猎人海日布》中的人物形象。故事讲述了猎人海日布救了一条小白蛇,原来这条小白蛇是龙王的女儿,为了报答猎人的救命之恩,小白蛇告诉猎人可以从他父亲那里挑一件宝贝,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父亲嘴里的宝石,这块宝石能让人听懂动物的语言,重要的是千万不能把动物的话讲给别人听,否则他将会变为石头。海日布拿走了龙王的那颗宝石,有一天,他照常去打猎,途中听到鸟儿们正在说不久将会有一场暴风雨引发洪水灾难,海日布担心父老乡亲的安全,把他从鸟儿嘴里听到的话告诉了乡亲们,同时又把自己如何得到宝石的事也讲了,谁知海日布刚说完就变成了一块石头。因为海日布的及时告知,乡亲们躲过了那场灾难。变成石头之后的虚构故事。小说中雕刻家“我”(名叫uul,译音为乌拉,是山的意思)、传说里的英雄海日布与石头建构了两层关系,并且三者之间形成一种环形轨迹,具有“圆型”时空结构特征。第一层关系表现了小说结构形式,即三者的相互循环关系。民间故事中的猎人海日布从人变成石头已有几百年时间,在小说中,名叫乌拉的“我”身上重演了几百年前海日布的故事,也从人变成了石头,被雕成石雕后几百年间被到处展览,身体已经永远束缚在石头中。历史上的海日布是今天的石雕,今天的“我”乌拉在未来是石雕;故事中的海日布能听懂鸟儿的话语,小说中的“我”可以与大山和石头对话;故事中的海日布违背了龙王的指令,把灾难的消息告诉人们,受到惩罚,最终变成石头,而小说中的“我”违背老师的意愿,放走了海日布的雕塑,自己最后僵化成石头。第二层关系是人与石头的关系,其实隐喻了人类与自然(生命)的关系。小说中,“石头的自由”这条线贯穿始终,“我”一直认为把石头恢复成其原来的人的模样,石头就能得到自由,所以试图把几百年前化成石头的海日布刻出人样恢复其肉身。相反,化为石头的海日布以及大自然的山石都认为:“这宇宙世界是石头的天地。……脚下的大地母亲属于石头,你死后骨头也属于石头”[15]101。仔细想想其实就是关于人类生与死的问题,生命来自大自然终究会回到大自然,这是生命的循环规律,人是自然生命的一种存在。当小说中“我”变成石头最终回归儿时的山里,大山对“我”说:“孩子你自由了。自由是属于石头的。自古以来都是如此”[15]106。这里“石头的自由”暗示对待生命死亡的一种坦然态度。海日布和“我”变成石头象征人的死亡,变成石头的“我”回到生长的山里象征生命回归自然,回归最原始的生命存在形态。
在另一篇小说《驼背老人》[16]中,“敖包山”这一意象贯穿整篇小说。虽然小说中最后没能真正堆起敖包,但驼背老人心中的“敖包”是最后的精神寄托。小说中老人没日没夜地寻找石头去山顶堆敖包,可途中总是遇到荒唐的事情阻碍他,即便如此,老人心中永远牵挂着“敖包”。老人坚定地追寻“敖包”的故事不禁让人想起卡夫卡《城堡》的主人公K一意追寻“城堡”的故事。K竭尽全力想要进入“城堡”,但越想到达就越遥不可及,有目标但却是无路之路;灵幻小说《驼背老人》中老人无论如何都要把“敖包”堆建起来,可是“驼背老人每天都背来石头。由于石头越来越难找,因此只能一天捡一两块拿去堆到敖包上。敖包不见高,说起来也怪,堆了几个月也没能堆成”[16]8,通往山顶虽有路可走,但抵达不了目标。小说中,抵达目的地的路途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阻碍、威胁使主人公受挫、徘徊。《城堡》[17]中,主人公K夜里走到被白雪覆盖的村庄,站在“从大路通向村子里的木桥上”凝视着“一片虚无空洞的幻景”。这里的“木桥”是K进入村庄追寻“城堡”的起点,但是眼前的道路被黑夜、雾霭、白雪覆盖变得模糊,隐喻了通往目的地的艰难与阻隔。在灵幻小说《驼背老人》中,老人“在草场上来回张望徘徊”,寻找堆到敖包上的石头。“草场”是老人寻找石头走上敖包的起点,但总是被神秘的影子妨碍、威胁,甚至有一次踏着背着石头还没走到一半就跌倒受伤,更可悲的是最后连“草场”也失去了,这样一来就阻断了老人抵达目的地的道路。K的无路可走与驼背老人被阻断的路隐喻了人类试图摆脱精神困境的状态。
灵幻小说中,自然意象也会起到烘托人物形象的作用。长篇小说《沙漠深处》[18]里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形象为莫德格玛和塔嘎拉拉图。与这两个人物形象关系密切的自然意象是“chonotiin balar”(意为有狼的森林,以下简称“森林”),这片森林如同古代英雄史诗中的“相约的小山丘”,不属于具体的实指,而是个复杂、具有延伸意义的意象。小说中,“森林”好比一个整体空间,包括普通人、动物植物、死人的灵魂、半人半鬼半兽的异化者都在这里,因而具有多重性质。比如它是人安定的家园、是动物植物的生长地、是扭曲异化者的地盘、是灵魂短暂休息的地点,所以拥有自然和社会两种维度。自然维度主要体现为一种和谐、友善,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依赖生存,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友善相处,这表现主人公莫德格玛身上与生俱来的充满爱与善的性格特征。“森林”的社会维度以权力、贪欲、复杂的矛盾关系为表现塑造的。塔嘎拉拉图一出现在“森林”,周遭的一切事物都会变得躁动不安,一种阴森、恐怖、异常的气息充斥整个空间。哪怕是白天,当他出现时“背后的柳枝发黑,乌黑的乌鸦呱呱叫着飞来飞去”“恶臭味在空气中如同毒蛇般溜走”“乌黑色的驴”等等阴森恐怖的事物都会随之而来。“黑色”“黑乌鸦”“毒蛇”“黑驴”是塔嘎拉拉图这个人物内心扭曲、阴暗的一种外化,其形象既恐怖又荒诞滑稽,是一个怪诞的人物。总之,灵幻小说作家笔下的自然意象往往有着其重要的叙事功能,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起到重要作用。
结 语
小说中的空间元素指文学中的场所与地理空间,也是小说情节发生的场景和人物行动的舞台。灵幻小说中,作家们将自身的不同生存空间体验和经历,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转化为作品里的空间元素,其中包括自然空间意象。然而这些空间元素并非简单的外部环境或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而是以参与叙事、对叙事产生影响来达到探索和思考生命、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多元性、无限性以及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