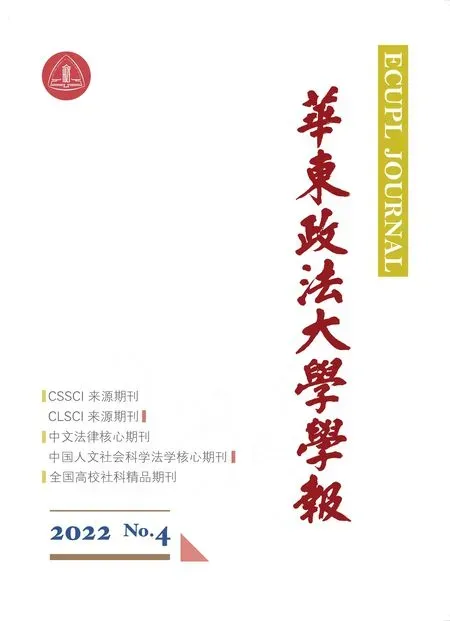行政复议重作决定的理论基础、适用要件与效力
李 策
目 次
一、重作决定典型案例的考察
二、重作决定理论基础的剖析
三、重作决定适用要件的“三层次构造”
四、重作决定法律效力的强化措施
五、结语
修改行政复议法,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1〕参见马怀德:《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政府理论》,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6期,第18-19页;马怀德:《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政府理论的核心命题》,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22页。2020年2月5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要求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2〕参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人民日报》2020年2月6日,第1版。行政复议决定是行政复议制度的关键环节。附随于撤销决定的重作决定,对于实现撤销决定的效力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行政复议法及其配套法规的规定较为原则,〔3〕参见《行政复议法》第28条。实践中重作决定的必要性被忽视、适用比例较低,适用要件不明确、适用随意混乱,法律效力不统一、法律效力有限。这种乱象既不利于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行政复议的公信力,亟需从学理和立法层面进行检讨与回应。
已有研究中,有学者指出了重作决定的性质及其两项适用条件,〔4〕参见蒋杰:《行政复议各类决定的适用条件辨析──兼议〈行政复议法〉第28条的缺陷》,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70页。也有学者肯定了重作决定存在的必要性并分析了重作决定的法律规范和典型案例。〔5〕参见沈福俊、崔梦豪:《行政复议责令重作决定的反思与完善》,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3期,第35-45页。同时,诉讼法上对于重作判决的理论基础、适用要件和法律效力等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可资借鉴。〔6〕参见刘欣琦:《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重作判决适用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5期,第140-148页;邓刚宏:《行政诉讼中重作判决的理论基础与完善》,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80-88页。既有研究深化了对重作决定的认识,为进一步完善重作决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但从总体上看,既有研究对重作决定的理论基础缺乏系统完整的反思,对适用要件的理解较混乱,缺乏统一标准,也忽视对于重作决定法律效力的检讨与完善。实践中行政复议典型案例对于重作决定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本文梳理司法部(原)行政复议司、国务院(原)法制办公布的238个典型案例,得到81个作出撤销决定的案例,其中24个案例作出了重作决定。〔7〕数据来源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司编:《行政复议典型案例选编》(第1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司编:《行政复议典型案例选编》(第2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司编:《行政复议典型案例选编》(第3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司编:《行政复议年度案例选评》(2014-2015),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司法部行政复议司编:《行政复议典型案例选编》(2016-2017),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重作决定在复议实践中的困境,论证其存在的理论基础,结合我国行政复议法立法目的的嬗变,重新审视重作决定的适用要件和法律效力。希望借此推动《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基本法典”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编相关条款的完善,〔8〕参见马怀德:《行政基本法典模式、内容与框架》,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第55、57页。从立法层面破解重作决定的现实困境,并为复议实践提供学理支撑。
一、重作决定典型案例的考察
相比于其他复议决定,重作决定具有鲜明的特色,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其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适用要件和效力如何,究竟存在何种问题,均需要通过实践来检视。
(一)典型案例中的重作决定
通过对案例的考察可以发现,在每个案件中复议机关基本都对重作决定的适用要件、法律效力等作出了分析和归纳。总体上说,这24个作出重作决定的案例具有以下五个特征。
第一,被申请人具有重作职责是作出重作决定的必要条件。重作行为本质上是在履行法定职责,如果没有重作职责则属违法重作。第二,被复议行为的性质有(拒绝)授益行为、侵益行为、中立裁决三种。被复议行为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裁决、征税、信息公开、工伤认定等多种行政行为类型。第三,在撤销理由方面,除了明显不当和滥用职权没有相关案例外,行政行为因为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超越职权、未向复议机关提供证据而被撤销的,均可以责令重作。第四,在重作期限方面,只有少数案例对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限定了期限或做了笼统限制。第五,在重作内容方面,有笼统责令重作行政行为、责令重作某类行为(如行政处罚)、责令作出内容明确的特定行政行为,以及仅责令重新作出、依照法定程序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回应申请人请求、回应请求并作出行政行为、回应请求并作出某类行政行为的情形。
(二)重作决定的实践困境
1.适用必要性被忽视,适用比例低
《行政复议法》第28条的规定是“可以”责令重作。从法规范性质上讲,该规定属于授权规范而非命令规范,意指复议机关拥有裁量权,可责令也可不责令。因此,复议机关不存在必须责令重作的义务,再加上重作决定适用要件模糊等原因,实践中复议机关作出重作决定的比例较低。
重作决定适用比例低的具体表现有两个。一是可以责令重作而仅撤销不责令重作。如在王某不服某区劳动局工伤认定案中,复议机关查清事实后撤销了被申请人的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但没有责令重作。而事实上,复议决定作出后,被申请人主动对王某的工伤重新作出认定。〔9〕参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司编:《行政复议典型案例选编》(第1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180页。二是以履行决定、变更决定等其他决定代替重作决定。〔10〕要解决该问题,还需要厘清重作决定与履行决定、变更决定的适用边界。参见马怀德、李策:《关照时代命题的行政法学》,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64-174页。如在丁某不服保监会信访投诉处理案中,被申请人保监会明确拒绝履行查处职责,复议机关依据《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1款第3项撤销告知书,但没有作出重作决定,而是依据第2项作出决定责令履行职责。〔11〕参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司编:《行政复议典型案例选编》(第2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7-41页。重作较低的适用率,导致其难以有效发挥督促行政、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作用。
2.适用要件不明确,适用随意混乱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1款第3项,重作决定的适用前提为“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这种规定非常抽象和原则,实践中复议机关对于重作决定适用要件的认定比较混乱。
重作决定适用的随意和混乱具体表现有三个。一是选择适用,即不存在确认违法附加重作决定的案例。根据行政复议法,重作决定可以附随于撤销决定和确认违法决定。但是在笔者梳理的24个作出重作决定的案例中,重作决定都是附随于撤销决定。二是随意适用,即在相似案件中,有的撤销并责令重作,有的则仅决定撤销。例如,同样是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不予工伤认定决定,在凌某等不服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予认定工伤案中,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作工伤认定。〔12〕参见司法部行政复议司编:《行政复议典型案例选编》(2016-2017),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33-134页。但在徐某不服某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中,复议机关没有责令重作。〔13〕参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司编:《行政复议典型案例选编》(第2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三是混淆适用,即与履行决定混淆。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身就是履行法定职责,因此重作决定和履行决定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在某有限责任公司不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核准公司变更登记案中,复议机关撤销了被申请人作出的《不通过通知书》,并责令其依法核准申请人的变更登记申请。〔14〕参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司编:《行政复议典型案例选编》(第3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68-69页。本案中,责令核准变更登记申请既可以理解为撤销后的重作决定,也可以理解为履行决定。重作决定适用的随意和混乱,导致行政复议同案不同判等弊端,不仅严重损害了复议的公信力,也不利于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法律效力不统一,法律效力有限
关于重作决定的法律效力,《行政复议法》 第28条的规定是“一定期限+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且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这种规定比较抽象。《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49条也没有明确重作内容,而仅对重作期限作了限定。实践中,重作决定的期限和内容不统一、不规范,法律效力十分有限。
具体而言,一是不限定期限,或者随意限定期限。在24个典型案例中有17个案例没有限定期限,其中2个案例笼统要求“一定”“及时”,15个案例没有限定任何期限,这与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实施条例的规定不符。二是重作的内容具有模糊性。在24个典型案例中有19个案例仅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而没有明确被申请人应当如何作出、作出什么样的行为。由于重作期限的缺失和内容的模糊性,被申请人可能以基本相同的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行为基本一致的行为,申请人可能因为不满而再次复议或者起诉,导致复议程序空转,无法实质化解行政争议。
二、重作决定理论基础的剖析
剖析理论基础问题,能够明确重作决定适用的必要性,还能够为要件重构和效力增强提供理论支撑,从而间接促进适用比例的提升。这对于弥补撤销决定的不足,优化行政复议决定体系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重作决定的逻辑证成
从逻辑上证成重作决定存在的必要性,是改革重作决定的首要问题。考虑到重作决定和行政诉讼重作判决的相似性,因此可以首先对重作判决进行考察。相关研究者否定重作判决必要性的理由有六个。一是撤销判决本身蕴含了责令重作的效力,不必再责令重作。撤销判决的形成力要求行政机关继续履行本就负有的法定职责即重作行政行为。〔15〕参见张宏、高辰年:《反思行政诉讼之重作判决》,载《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25-26页。二是重作判决违背了诉判一致的诉讼法理,属于“无诉而判”。〔16〕参见刘欣琦:《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重作判决适用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5期,第140页。三是撤销及重作判决只能适用于负担行为,授益行为应当适用履行判决。四是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重作判决督促行政的目的与之不符合。〔17〕参见张旭勇:《行政判决的分析与重构》,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5页。五是重作判决是司法权与检察权的错位,应当由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积极行政。六是司法权的职责是判断是非曲直,行政权的职责是执行法律,应当严守二者的界限,重作判决是法院对行政权的干预。〔18〕参见邓刚宏:《行政诉讼中重作判决的理论基础与完善》,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81页。
上述观点,除了第五、六项明显不适用于行政复议外,前四点对于行政复议重作决定大体也是适用的。结合我国行政复议的现状和上述意见,笔者认为,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实有坚持重作决定的必要,其逻辑基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基于行政隶属和领导关系,复议机关有权主动作出重作决定。《行政复议法》第1条强调行政复议的内部监督定位。立法者的论述指出,“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19〕杨景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草案)〉的说明》,1998年10月27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因此,在复议程序中,复议决定不必以当事人的请求为前提。同理,复议机关有权超越诉判一致的束缚,主动作出重作决定,不必以当事人的请求为前提。其主要目的在于督促行政机关积极行政、维护客观法律秩序。〔20〕参见[日]美浓部达吉:《行政裁判法》,邓定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李策:《行政法治的新发展与行政法法典化——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21年年会综述》,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3期,第34-35页。
其次,重作决定能够弥补撤销决定的不足。诚然,撤销决定的形成力使法律关系恢复到行政行为作出前的状态,〔21〕参见江利红:《日本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466页。撤销决定的拘束力能防止行政机关在事实和法律状况无变化时重作相同的行为。〔22〕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页。但是,一方面,由于这种效力是蕴含在撤销决定中的,缺乏明确性,而重作决定直接将撤销决定的效力明确化,更加有利于撤销决定的执行和落实。另一方面,撤销决定作出后法律关系即回到最初的状态,〔23〕参见王名扬:《外国行政诉讼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此时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是概括的、抽象的,行政机关对是否行使、如何行使拥有裁量权。而重作决定使得行政机关必须行使该职权,且对如何行使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因此,重作决定能够发挥督促行政、规范行政的独立价值,这是撤销决定所不具备的。
最后,重作决定符合行政复议监督行政、保护权益、化解争议的立法目的。《行政复议法》第1条规定行政复议具有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的立法目的,司法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第1条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增加为立法目的。〔24〕参见马怀德、李策:《行政复议委员会的检讨与改革》,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4期,第17-19页;马怀德、李淮:《聚焦行政权力规范运行的行政法学——2019年行政法学研究述评》,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22-123页。无论是适用于授益行为还是负担行为,重作决定明确被申请人必须履行法定职责,都有利于实现行政复议监督行政的立法目的。当适用于负担行为时,尤其是适用于行政处罚等制裁行为时,重作决定还能够通过督促行政进而保护被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侵犯的第三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25〕参见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释解》,中国言实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当适用于有争议的授益行为时,重作决定可以通过督促行政直接给相对人授益,同样有利于实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
(二)重作决定的性质与定位
“每一个法条,都紧密交织在法体系中,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关系。”〔26〕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44页。《行政复议法》第28条规定了行政复议决定的类型。《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43条至第48条对之进行细化,并增加了驳回复议申请决定。在此基础上,厘清重作决定的性质与定位,对于促进重作决定的实践适用、明晰复议决定体系的逻辑性大有裨益。
第一,重作决定是附属于撤销决定的非必要性决定。重作决定乃是为实现撤销决定的效力而设置,并且课予被申请人重作义务,被申请人对是否重作无裁量权。《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1款第3项规定,撤销或者确认违法的,〔27〕重作决定不能附属于确认违法决定,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详述。可以责令重作行政行为。可见,与变更、履行等决定不同的是,重作决定不能单独作出,必须附随于撤销或者确认违法决定,具有附属性,可称之为“从决定”。〔28〕参见郜风涛主编:《行政复议法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页。而且撤销、履行等决定都是“必须”作出,只有重作决定是“可以”作出,也即“可作可不作”,因此重作决定属于非必要的决定。
第二,重作决定在行政复议决定体系中的定位是给付类决定。在民事诉讼法上,民事判决一般有三种类型:形成类判决、给付类判决、确认类判决。行政诉讼上亦有类似的分类。〔29〕参见黄锴:《行政诉讼给付判决的构造与功能》,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73页。如果用这种分类来审视行政复议决定的话,那么撤销决定和变更决定属于形成类决定,确认违法决定属于确认类决定,履行决定属于给付类决定。虽然重作决定附属于撤销决定,但重作决定不能产生、变更或消灭法律关系,因此不属于形成类决定。也不是确认法律关系或法律效力,因此不属于确认类决定。重作决定是法院要求被申请人履行义务,因此属于给付类决定。
第三,重作决定在本质上是履行决定。重作决定不仅和履行决定同属给付类决定,而且两者在适用要件上,都要求行政机关尚未履行职责;在法律效力上,都要求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职责。但履行决定一般需要当事人申请,重作决定则无须当事人申请;履行决定中法定职责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还可以包括调查行为等。〔30〕参见李策:《行政投诉案件中原告资格的本土逻辑与实践反思》,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146-157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91条规定,在适用履行判决时,尚需被告调查或裁量的,应判决“重新作出处理”。这种“表述”也表明履行决定和重作决定的适用和效力极为相近。因此,除了不需要当事人申请外,重作决定完全可以被视为履行决定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在本质上应当是履行决定。
(三)重作决定规范对象的性质
重作行为是重作决定的结果和规范对象。重作行为的性质关系到被申请人能够重作的行为的范围,进而关系到复议机关能否责令重作、如何责令重作。对于重作行为的性质,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重作的行为是一个新的行政行为,如果原行为因证据不足被撤销的,行政机关有权重新收集证据,复议机关可以作出重作决定;另一种观点认为,重作的行为是原行为的延续,实质上是复议程序的延续,根据“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行政机关无权重新收集证据,也不能依据新的证据重新作出行政行为。〔31〕参见刘欣琦:《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重作判决适用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5期,第145页。上述观点争议的焦点是原行为因证据不足被撤销能否责令重作的问题。但第一种观点忽视了重作的行为与重作决定关系,第二种观点忽视了行政机关在重作行为中的裁量权。
其实,无论从法理还是从立法角度讲,重作行为都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重作行为是根据重作决定而为之,重作行为要受到重作决定的限制。《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62条也规定,被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按照复议决定重作或违反规定重作的,依照《行政复议法》第37条〔32〕《行政复议法》第37条规定:“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经责令履行仍拒不履行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有关不履行复议决定的法律责任的规定追究责任。因此可以认为重作行为是在履行复议决定、是复议程序的延续。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在重作行为中对于重作的内容、时间、方式等有一定的裁量权,并不完全受复议决定的束缚,重新作出的行为在主体、职权、程序、效力等方面也符合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49条第2款规定,对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这是将重作行为当作新行为对待。因此也可以将重作行为视为新的行政行为。
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实质化解争议的角度观察,对于授益行为,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允许复议机关责令重作;对于中立裁决行为,为了尽快确定法律关系,实质化解争议,也应允许重作;对于负担行为,由于涉及相对人、其他利害关系人和公共秩序,需要作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考察。行政复议重作决定的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也需要结合重作决定的性质和行政复议的目的进行建构。〔33〕参见王万华:《行政复议法的修改与完善——以“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为视角》,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99-117页。
三、重作决定适用要件的“三层次构造”
重作决定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但立法的抽象和学界的争议使适用者在实践中对重作决定的适用要件存在不同理解,这是重作决定适用混乱随意的根源所在。重作决定本质上是履行决定,据此可以将其适用要件重构为呈现递进关系的“三层次构造”:行政行为被撤销—重作职责的存在—具有重作可能性。
(一)重作决定适用要件的重构
如有学者认为,重作决定的适用条件包括以下两项:一是行政行为被撤销或确认违法;二是撤销或确认违法的理由是且只是违反法定程序。〔34〕参见蒋杰:《行政复议各类决定的适用条件辨析──兼议〈行政复议法〉第28条的缺陷》,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70页。诉讼法上的观点或许更加值得参考。相关研究结论有重作判决的适用要考虑行政行为被撤销、撤销理由和被诉行为的性质;〔35〕参见沈福俊、崔梦豪:《行政复议责令重作决定的反思与完善》,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3期,第41-44页。重作决定的要件有行政行为被撤销、重作可能性以及维护公益或者公民权益;〔36〕参见张旭勇:《行政判决的分析与重构》,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9-152页。重作决定的要件有行政行为被撤销、维护公益或者公民权益、具有重作职权;〔37〕参见邓刚宏:《行政诉讼中重作判决的理论基础与完善》,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4期,第86-87页。重作决定的要件要考虑行政行为被撤销、维护公益或者公民权益、行政程序。〔38〕参见刘欣琦:《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重作判决适用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5期,第144-145页。
既有研究深化了对重作决定适用要件的认识,为进一步完善其适用要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但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既有研究对于将行政行为被撤销作为要件形成共识,但对确认违法是否可责令重作有争议。其次,“维护公益或公民权益”也可以作为不得责令重作的条件,如公民没有违法行为不能责令重新处罚,其目的也在于保护该公民的权益。因此该要件缺乏一致性和确定性。最后,行政行为因为某种理由被撤销的,往往存在可责令重作以及不可责令重作的相反情形,自相矛盾,因此将撤销理由作为适用要件也缺乏一致性和确定性。例如,被复议行为因事实不清被撤销的,如果复议机关查明申请人有违法事实,可以责令重作;如果查明没有违法事实,则不可责令重作。
依据《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1款第3项,“行政行为被撤销”是重作决定的前提。参考履行决定的要件,可将“重作职责的存在”作为重作决定的第二个要件,由于履行重作职责本身就是在维护公益或公民权益,且履职的外化表现即为行政行为,因此该要件可以涵盖所谓的“行政程序”“维护公益或公民权益”“被诉行为性质”“撤销理由”等要件。重作行为还必须具有可能性,否则属于重作不能,故“具有重作可能性”应作为第三个要件。虽然行政复议法及配套法规并没有规定该要件,但考虑到具有履行可能性是履行决定的要件,而重作决定本质上是履行决定,故可将重作可能性作为重作决定的适用要件。〔39〕参见曹康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综上,可以将重作决定的适用要件归纳为呈现递进关系的“三层次构造”:行政行为被撤销—重作职责的存在—具有重作可能性。
(二)要件一:行政行为被撤销
《行政复议法》 第28条第1款第3项规定,撤销或确认违法的,可责令重作。对于撤销可责令重作,没有争议,本文的24个典型案例都是撤销并责令重作的案例。行政行为被撤销,意味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回到最初状态。〔40〕参见王名扬:《外国行政诉讼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这是责令重作的前提,类似于履行决定要件中的“不履行”,无论是重作决定还是履行决定都是在要求履行职责调整法律关系。
关于确认违法是否可以责令重作,目前尚有争议。《征求意见稿》第76条规定重作决定只附随于撤销决定而不附随于确认违法决定。有学者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认为,重作决定也可以附属于确认违法决定。〔41〕参见蒋杰:《行政复议各类决定的适用条件辨析──兼议〈行政复议法〉第28条的缺陷》,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70页。其理由在于,确认违法决定使得行政行为客观上没有意义,只有责令重作才能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职责作出合法有意义的行为。〔42〕参见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释解》,中国言实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但也有学者认为,重作决定只能附随于撤销决定,不能附随于确认违法决定。〔43〕参见沈福俊、崔梦豪:《行政复议责令重作决定的反思与完善》,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3期,第41页。诉讼法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70条规定,重作判决也只能附随于撤销判决而不包括确认违法判决,学界也基本持同样观点。〔44〕如刘显鹏:《行政诉讼重作判决探析》,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127页。
确认违法决定一般适用于以下的两种情况:一是虽确认违法,但行政行为仍然存在并具有效力;二是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此时不存在行政行为,但决定履行无意义的。〔45〕参见郜风涛主编:《行政复议法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259页。对于第一种情况,由于存在有效的行政行为,责令重作属于重复处理,故不能责令重作。对于第二种情况,由于重作决定本质上是履行决定,履行没有意义也就是责令重作没有意义,故也不能责令重作。据此,在俞霞金、徐存镖等6人诉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复议案〔46〕参见中国指导案例编委会:《人民法院指导案例裁判要旨汇览(行政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126页。中,法院确认行政行为部分违法意味着违法部分仍存在并有效,此时责令重作会出现针对同一法律关系的两个矛盾的行为,因此不应责令重作,而应先撤销违法部分然后再责令针对该部分重作。
(三)要件二:重作职责的存在
所谓重作职责,是指被申请人依据行政法律规范有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职责。该要件类似于履行决定中的“法定职责”要件,如果没有法定职责,则不能责令履行。根据本文对24个典型案例的分析,重作职责(行为)可以分为三种:授益性职责、中立裁决职责、侵益性职责。其中,前两种是有主观公权利对应的职责。〔47〕“没有无法律义务的主观权利,但没有相应主观权利的义务却是大有可能的。”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李策:《行政投诉案件中原告资格的本土逻辑与实践反思》,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147-150页。
对于授益性职责,应当责令重作以保护相对人权益,但从实质化解争议角度讲,适用履行决定更为妥当。如果行政机关对申请没有任何答复,则应适用履行决定,此点无甚争议。当行政机关明示拒绝申请人时,便涉及撤销加重作决定和履行决定的界分。有学者指出,区分二者的标准是行政机关是否已经作出处分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48〕参见章剑生:《判决重作具体行政行为》,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29页。如果已经作出的,通常是拒绝授益申请行为,只能撤销并责令重作,反之则应当作出履行决定。因为如果有一个行政行为存在,必须通过撤销来消灭其效力,然后才可以再作出新行为。但是,重作决定只是抽象要求重新作出行为,而不能为被申请人设定具体义务,被申请人重作后当事人可能因不服而再次复议起诉,不利于实质化解行政争议。
在德国法上,对申请的否定性决定涉及否定决定之诉,其仍是要求履行义务,不包含对否定决定的撤销,因此应适用义务之诉。〔49〕不过,在义务之诉的判决中通常都会宣布对否定决定或者复议决定的撤销。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将对于拒绝申请决定的撤销诉讼与课予义务诉讼合并提起。〔50〕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对于行政机关拒绝申请的行政行为,得提起履行之诉,法院可以直接作出履行判决。其背后的逻辑是,以是否按照申请人的申请履行授益性职责为标准判断,拒绝履行也属于“不履行”,应适用履行决定而非撤销和重作决定。这样也更加有利于保护相对人权益,实质化解行政争议。
对于侵益性职责,为督促行政应责令重作,但从保护相对人权益的角度讲,应提升责令重作的规范性。对此,诉讼法上有观点认为,由于侵益性职责并非在保护申请人权益,故原则上没必要责令重作,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撤销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权益造成损失的,可例外责令重作。〔51〕参见张旭勇:《行政判决的分析与重构》,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51页。但是,责令重作本身就是在要求被申请人行使侵益性职权,而行使职权总是在维护私益或公益。因此上述主张可例外责令重作的观点其实自相矛盾。
侵益性职责(如行政处罚)针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而该违法行为往往又侵犯第三人权益和公益。因此,侵益性职责涉及申请人、第三人或公益、被申请人三方法律关系,其间利害比较复杂。考虑到行政复议监督行政的立法目的,以及当下违法行为滋生、行政不作为的严峻形势,应当允许复议机关作出重作决定以督促行政、惩罚违法行为。〔52〕参见杨小君:《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不过,由于此时重作决定可能侵害相对人的权益,所以应提高责令重作的规范性,严格要求合法合理重作。
对于中立裁决职责,为实质化解争议,应当责令重作以尽快确定法律关系。此类案件中,相对人具有要求行政机关中立裁决的主观公权利,撤销决定使得裁决行为效力消灭,但相对人的申请仍然存在。作为对申请的回应,复议机关应当责令重作以实现其主观公权利。
(四)要件三:具有重作可能性
具有重作可能性意指被申请人在事实上能够重作行政行为。这种可能性是一种现实的、实际的可行性。如在某村民小组不服某市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确权决定案中,某村民小组不服某市政府的土地确权决定而申请复议,复议机关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确权决定,在被申请人具有重作职责情况下,确认被申请人能够重新调查事实、适用法律,于是作出重作决定。〔53〕参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司编:《行政复议典型案例选编》(第3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161页。如果重作不可能,则不应作出重作决定。重作不可能一般是指由于客观事实而导致无法重作,主要是指由于时空条件变化导致被申请人无法重新履行程序或者搜集证据等。
四、重作决定法律效力的强化措施
重作决定的价值最终是以法律效力的形式体现的,面对当前重作决定效力疲软的现状,有必要从重作内容、重作期限、对重作行为的监督三方面强化重作决定的效力。
(一)重作内容的明确
在行政诉讼理论上,根据内容的明晰度,可以将司法判决分为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仅笼统判决被告履行义务,不明确义务的具体内容;实体性裁判则要求被告履行内容明确的义务。〔54〕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下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878-880页。同理,在复议决定体系中也存在实体性决定和程序性决定的区分。除了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外,《行政复议法》并没有对重作决定内容作出限制,因此重作决定是典型的程序性决定。
1.以实体性重作决定为原则
程序性重作决定的内容具有模糊性,导致其法律效力不足。原因在于,片面地将重作决定仅仅理解为撤销决定的补充,忽视了其独立价值,即重作决定要求被申请人必须履行义务,并对义务内容提出具体的要求。从实质性化解争议、保障合法权益的角度讲,重作决定原则上应当是实体性重作决定,这意味着复议机关应当明确被申请人重作的具体内容,即被申请人应当作出特定的行政行为。被申请人直接执行即可,无须再次启动行政程序,也无须裁量,如此才能防止程序空转。
在符合重作决定的适用要件的前提下,只要事实清楚,复议机关就应当作出实体性重作决定。如果案件事实已经查明,被申请人没有裁量余地的,复议机关应当作出实体性重作决定,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特定行政行为。〔55〕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00条第3款规定,“三、原告之诉有理由,且案件事证明确者,应判命行政机关作成原告所申请内容之行政处分”。如果案件事实查明,但被申请人有裁量余地,那么可否作出实体性决定呢?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存在隶属和领导关系,〔56〕Cf. Peter Leyland & Terry Woodseds., Administrative Law Facing the Future: Old Constraints & New Horizons, Blackstone Press Limited, 1997, pp.246-247.复议机关对被申请人具有层级监督权,〔57〕参见杨伟东:《关于创新行政层级监督新机制的思考》,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41页。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其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和指示。因此,复议机关可以全面审查被申请人的行为,既审查事实问题也审查法律问题,既审查合法性也审查合理性,审查广度和深度都远超行政诉讼。〔58〕参见耿宝建:《行政复议法修改展望》,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在对相关行政管理领域事实问题的判断上,复议机关也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因此,复议机关具备相当的机构能力,〔59〕See Jeffrey Jowell, “Judicial Deference and Human Rights: A Question of Competence”, in Paul Craig & Richard Rawlings ed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in Europe: Essays in Honour of Carol Harlo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73.与被申请人之间也不存在首次判断权的问题。〔60〕参见黄先雄:《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及其适用》,载《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114页。即使被申请人有裁量空间,复议机关也有权依据全面审查原则尤其是合理性审查原则行使该裁量权,进而作出实体性决定,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特定行政行为。
2.以程序性重作决定为例外
如果复议机关客观上无法作出实体性重作决定,应当作出程序性重作决定。复议机关作出程序性重作决定的条件是尚需被申请人调查事实,也即虽然被申请人应当重作的事实已经查清,但具体如何重作的事实尚未查清。复议机关主要是案件审理机关,虽然有权调查事实,但受限于复议机关的人员经费、专业性等,许多事实仍需被申请人调查。〔61〕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鉴于复议机关是被申请人的上级机关,故复议机关查明事实的能力要强于法院。因此,复议法中“尚需被申请人调查事实的案件”的范围应当小于诉讼法中“尚需被告调查事实的案件”的范围。《征求意见稿》第76条第1款第1项规定,被复议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适用撤销决定;第75条规定,复议机关查明事实的,适用变更决定,而变更决定是典型的实体性决定。同理可知,复议机关能查清案件事实的,作出实体性重作决定,否则,作出程序性重作决定。
程序性重作决定的法律效力较差,对被申请人行为约束有限,因此需作若干限制,以防止被申请人偏离复议机关意志,再次作出违法、不当的行为。一方面,违法行为被撤销后,行政机关重作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往往比较明确,因此,复议机关应当明确被申请人重作的法律依据。既要明确重作依据的法律文件,如某一部法律,还要明确该法律中的具体条款,又要对这些条款进行法律解释。如此,被申请人才能按照复议机关的“法律观”正确重作。〔62〕参见梁凤云编著:《新行政诉讼法逐条注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577-578页。另一方面,明确被申请人重作的行为的类型和特征,也即责令重作某个具体的行为,以限缩被申请人的裁量权。此外,如果被申请人是否应当重作的事实未查清,复议机关也应当责令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决定是否重作,而不能仅撤销不责令重作。
(二)重作期限的厘定
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复议实践中很多案例根本不限定重作期限,或者对重作期限的限定较为随意,严重影响了重作决定的法律效力。因此必须重新厘定重作期限。
重作决定必须限定期限。从保障申请人合法权益角度讲,即使案件十分复杂,也必须限定重作期限,这也有利于监督复议决定的执行。《广东省行政复议工作规定》第17条第1款规定,重作期限为60日,复杂案件为180日。《公安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第67条规定,重作期限最长不超过60日。上述观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没有区分重作决定的具体情况,有“一刀切”的嫌疑,无法回应纷繁复杂的复议实践。
考虑到实体性重作决定和程序性重作决定在重作难易程度上的不同,应当为二者分别设定不同的期限。第一,对于实体性重作决定,重作期限应当远远小于法定期限和60日期限。在紧急情况下,应当责令立即重作。理由在于,一方面,重作内容非常明确,被申请人只需要直接执行,程序简便。另一方面,经过复议后,耽误的期限已经较长,应当尽快重作。第二,对于程序性重作决定,由于需要被申请人再次启动执法程序,调查事实、适用法律等,因此可以适用《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49条的规定,即依照法定期限,没有法定期限的为60日。〔63〕《行政复议法(专家建议稿)》(2020年5月15日整合版)也持同样观点,其第65条第4款规定:“被申请人应当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法律、法规、规章未规定期限的,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期限为60日。”由于经过复议耽误不少时间,故实践中具体期限可以略短。即使案件复杂、专业性强,原则上也不可以延长期限,以督促被申请人尽快重作。
(三)重作行为的监督
为了防止被申请人违背复议机关的意志,再次作出违法或不当的行为,有必要对重作行为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以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如上文所述,重作行为具有双重性质,既是执行重作决定的行为,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新行政行为。因此,对重作行为的监督,应当综合运用对复议决定的监督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两种监督方式,实现对重作行为的全方位监督,强化重作决定的法律效力。
首先,被申请人应当主动就重作行为向复议机关备案。不同于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领导关系,由此产生了层级监督权,〔64〕参见杨伟东:《关于创新行政层级监督新机制的思考》,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41页。因此复议机关有权监督重作的行政行为。而且重作行为是在履行重作决定,故为了确保复议决定得到执行,被申请人应当主动向复议机关备案,接受复议机关监督。《公安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提供了先例,其第67条第2款规定,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应当书面报公安行政复议机关备案。
其次,复议机关有权主动审查重作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一方面,重作行为是执行重作决定的行为,复议机关有权主动审查、监督、撤销,但这种监督仅限于依据行政复议法及复议决定的监督,也即限于被申请人“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行为”以及重作决定明确提出的其他要求。如《吉林省行政复议条例》第30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行政复议法,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行为,复议机关可直接撤销。此外,复议机关还可以给与相关人员行政处分。另一方面,除执行复议决定之外,依据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之间的隶属和领导关系,〔65〕参见马怀德:《论我国行政复议管辖体制的完善——〈行政复议法(征求意见稿)〉第30-34条评介》,载《法学》2021年第5期,第19-21页;王青斌:《行政复议制度的变革与重构——兼论〈行政复议法〉的修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128页。复议机关对被申请人具有层级监督权,可以主动审查重作的行为,有权改变或者撤销违法或不当的重作行为。
最后,当事人对重作行为不服的,可以再次申请行政复议。当事人对重作行为不服的,如果重作行为违反“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行为”以及重作决定明确提出的其他要求的,应当按照上述情况由复议机关按照复议决定执行程序主动审查。如果重作决定发生上述情况以外的违法或不当的,由于重作决定可以视为新行政行为,而且这些违法或不当情况不属于复议决定的规范内容,因此不应当按照重作决定的执行程序处理,而应当按照行政复议程序处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49条第2款也规定,对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五、结语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66〕《韩非子•心度》。本文尝试剖析了重作决定的理论基础,重构重作决定的适用要件,进而从重作内容、重作期限、对重作行为的监督三方面强化了重作决定的法律效力。随着法治中国建设迈向“规划”时代,〔67〕参见马怀德:《迈向“规划”时代的法治中国建设》,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第18-37页。重作决定需要进一步发展,既需要通过修改《行政复议法》对之进行调整,并在配套法规中细化和完善;又需要实践中复议机关充分行使层级监督权,强化重作决定的效力;还需要行政法学理论不断回应复议实践,为重作决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基础。重作决定的完善必将推动行政复议实现保障权益、化解争议、监督行政的立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