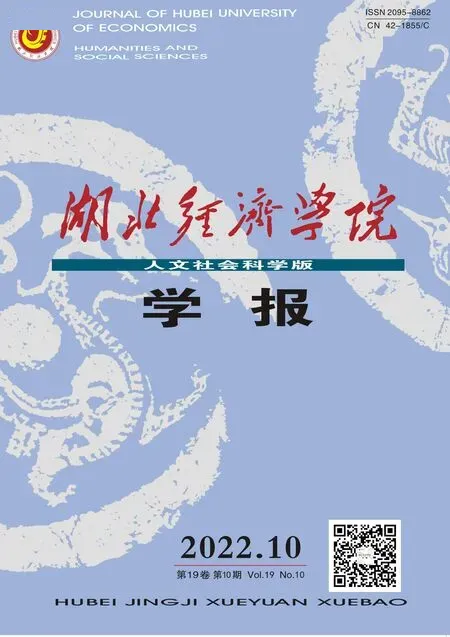博尔赫斯诗歌的时空体研究
张泽欣(天津外国语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所,天津 300204)
博尔赫斯对自己诗集《诗人》的题名El hacedor曾有过一番说明。他指出hacedor一词是对英文的maker的翻译,在对maker的词源追溯中,他选取了它在12世纪的苏格兰方言中的含义,即“诗人”:博尔赫斯正是以此认为自己是一个hacedor,即一个诗人和作家[1]。在原语言中,hacedor和maker主要指“制造者”或“创造者”,它们的引申义往往是“上帝”和“造物主”。如此宽广的词意范畴不可避免地会给理解和翻译带来含混(尽管有上述“澄清”),但读者的阐释空间却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了。虽然“博尔赫斯绝不是在用‘El hacedor’神化诗人与他自己”[2]141,但诗人和作家所从事的活动无疑都是创造性的,他们都是自己作品(世界)中时空的创造者。作为hacedor的博尔赫斯的创造意识是高度自觉的,这种创造意识的对象是“世界”,因此自然也就无法脱离时空关系。正是在各类文体的创作实践中,博尔赫斯寄托了他的时空观,创造了种种独特的时空书写形式,这也正是自命为诗人和作家的他选择的创造道路。在本文看来,在时空问题的探究路径上与之类似的是以文艺理论闻名的巴赫金,是他所提出的时空体理论。巴赫金认为,时空体是“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3]274,其中的关键是一种将时间和空间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视为一个兼顾形式与内容的文学范畴来观测的视野。在小说时空体之外,博尔赫斯凭借诗歌体裁特有的凝练和音韵,创造出了他的诗歌时空体。在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观照下,本文以博尔赫斯诗歌中的时空体为研究对象,试图在国内博尔赫斯诗歌时空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其诗歌的时空特色。
一、复杂众多的时空
博尔赫斯诗歌中所表现的时空体首先是复杂众多的,如果硬要对它们进行概括,那么最合适的词汇恐怕只有“无限”。这些时空体在不同时期、不同诗作(甚至在同一首诗)中都是都有所差别的,有的彼此之间还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但它们始终并立共存。在《时间之书——博尔赫斯研究》中,唐蓉对博尔赫斯诗歌中的时间进行了分类,并总结出了“绝对流逝的线性时间”(“赫拉克利特的时间”)“永恒循环的时间”“虚幻的时间”等各具特色的时间形式[4]37-43。这样的分类固然卓有成效,但却也不免片面。从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角度来看,对时间进行单独分类的行为忽视了空间,无论如何都会造成时间与空间之间的疏离和割裂,造成对部分时间形式的盲视。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整个复杂的文艺时空关系,有必要将这些时间形式与空间形式结合在一起,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时空体”加以考量。
虽然博尔赫斯诗歌中的时空体是复杂众多的,但这不意味着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捉摸的;相反,在本文看来,参考唐蓉对博尔赫斯诗歌中时间的分类,博尔赫斯诗歌中所有的时空体大体上都可以看成是两种主导时空体及其各类变形的并存,“绝对流逝的线性时空”“永恒循环的时空”以及在这两者持续的角力、交混和对话中产生的种种梦幻时空。“绝对流逝的线性时空”往往会从赫拉克利特的名言(谁都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中借用流水的意象,——如果没有空间的维度来构成比喻,人们甚至无法描述时间。在赫拉克利特的例子中,如果没有水这一流动性的空间作为载体并指出方向,“时间流逝”的概念就会变得不可思议。同样地,“永恒循环的时空”这样的时空体在去除了空间要素后将变得难以想象,其中像是首尾相接的圆形这样的空间意象总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无论如何都必须作为时间兼空间的时空体来进行考量。这两种矛盾冲突的主导时空体贯穿了诗人的创作始终。它们在早期诗作《一切墓碑上的铭文》[5]15和《城南守灵的一夜》[5]48中就有所体现。在前诗中:
专横的灵魂盲目地追求永生
这时他在别的生命中得到了保证,
这时候你自己就是那些不曾生活在
你的时代的人们具体的延续
而别人将是(现在也是)你在尘世的不死。
一种“永恒循环的时空”在此处已经隐约可见:永生的形式从单一个体的不死转变为了人类群体的永恒。逝去的个体,其精神和肉体仿佛在他人和下一代的记忆和生命中得以延续。然而,在后诗中:
那些细小的智慧令我感动
它们随每一个人的死亡而失去
——书籍的习惯,一把钥匙的习惯,一具肉体在别的肉体中间的习惯——
这样的诗行抛下了对时空永恒性的质疑,它否定了时间在空间中可能进行的无损耗的积累,认为时空的流逝必然会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带来损耗。就像诗中所述,一个人死去后,世界不仅失去了一种独特的整理、翻阅书籍的习惯,而且还会渐渐失去这种习惯通常会留下的物理痕迹,从而任何人事的逝去都意味着一种绝对的损耗,再也不可挽回。
“绝对流逝的线性时空”和“永恒循环的时空”在诗人的整个创作生涯中都还有着更加充分完整的表露,有时它们甚至会与其他类型的时空体同时出现在一首诗中:在这种情况下,博尔赫斯诗歌时空体的复杂众多特征是十足鲜明的。在《界线》[5]184中,“绝对流逝的线性时空”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我图书馆的藏书中(我正望着它们)/有几本我再也不会翻开。/今年夏天,我将有五十岁了:/死亡消磨着我,永不停息。”所有错过的街道、镜子、门扉、书籍都永远地成为了未知,不断衰老的、有死的人只能把进一步接触它们之后所能获得的更具体的时空形象视为是不可能的可能。在《循环的夜》[5]64-66中,“永恒循环的时空”几乎达到了它的顶峰。这首诗深受毕达哥拉斯灵魂轮回观的影响,它不仅借毕达哥拉斯的弟子指出“星辰与人都一遍遍往复循环”,而且全诗的用韵也呈现出回环反复的趋势(例如,首尾两节八行诗的结尾词分别为:Pitágoras/cíclicamente/urgente/ágoras/Anaxágo ras/constante/incesante/Pitágoras)[6]90-92,甚至连它的首尾行内容都是一致的(“毕达哥拉斯勤奋的弟子们知道”),不同之处只在于标点符号:首行的末尾用的是冒号;末行整句带上了双引号,末尾用了省略号。可见,这首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在模拟、暗示着夜(时空)的无限循环。将这两种主导时空体和其他类型的时空体同时囊括在内的范例当推《赫拉克利特的悔恨》[5]188。在这首仅有两行(外加两行出处信息)的小诗中,博尔赫斯诗中重要的时空体尽数出现:
我曾是那么多不同的人,但从来不是那个
怀抱着倒下的马蒂尔德·乌尔巴赫的人。
这些时空体充分表现了博尔赫斯诗歌中诸时空体复杂的并存状况,它们包括:第一,“绝对流逝的线性时空”。在“曾是”与“从来不是”对置中,在这种对置之后紧接着的第二行诗所透露出的景象中,时空的流逝是绝对的。诗中的“我”可能曾是任何一个阶段的博尔赫斯,甚至可能曾是赫拉克利特或者任何其他人,但却“从来不是”那个在第二行诗中“怀抱着倒下的马蒂尔德·乌尔巴赫”的人。“倒下”一词在原文中是desfallecía[6]262,它运用了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这一时态着重于描绘动作发生的情境和延续。由此,诗题中的“悔恨”不仅有了具体可感的来源,而且真正地成了逝去时空中无法弥补的悔恨。第二,“永恒循环的时空”。诗题中的赫拉克利特和第一行中的“我曾是那么多不同的人”总会让人联想到博尔赫斯其他表现“永恒循环的时空”的作品,例如在《回声》[7]163-164中,“国王的死无止无休,再现于莎士比亚的梦中”,而“人们还将继续梦见那死亡”,那死亡成了“时光的一个程序”,“是某些永恒的形和物”,——这种永恒循环的生死观与前例的《一切墓碑上的铭文》是高度契合的。不过,在此处,由于“从来不是”这一否定判断和第二行诗的出现,“永恒循环的时空”还未能继续展开便被打开了豁口,让位于“绝对流逝的线性时空”。第三,在“绝对流逝的线性时空”和“永恒循环的时空”并存的这首诗中,通常意义下的时空逻辑已然无法成立,正是在“永恒循环的时空”被打开的豁口中,各种神秘梦幻的时空体纷纷涌现,让读者陷进了无限迷宫式的错乱时空。问题首先在于第二行的“马蒂尔德·乌尔巴赫”,在据称是其灵感出处的小说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一人物[8]。于是在真实悔恨的语调和情境之下,事件和人物反倒走向了神秘与虚幻,其中真实性成分的多少恐怕只有诗人本人才知道。另一种梦幻般的时空体在诗后附加的出处书名和作者信息中更是彻底现形,因为它们相对于“马蒂尔德·乌尔巴赫”,无疑是一种更确切的虚构[9]。此外,从赫拉克利特到博尔赫斯,诗中的“我”在声明了自己“曾是”和“从来不是”什么人之后,并没有道出现在的身份,这暗示了一种对现在的否定和对未来的质疑,这是“布拉德利的时间观”[4]42的表现,它既出于“绝对流逝的线性时空”又能归属于“永恒循环的时空”,其中“目前是流向我们的未来在过去中分解的时刻,也就是不再存在的存在”[7]364。
二、并置质感的时空
巴赫金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一种“完整的时间”(或称“歌德的时间视觉”)的概念。他认为,歌德的小说世界是时空紧密贴合的典范,在其中“没有不参与行动和变化(在事件之中)的布景和环境。……这个时间及其所有重要的因素,都限定在具体的空间里,都打上了空间的印记”[3]258。当然,各个作品的时空体各有其特殊性,并非都能像歌德小说中的时空体那样完满,但“完整的时间存在于时空体的思维方式之中,因此,时间与空间在巴赫金看来必须共同被纳入思考进程之中”[10]94。同样地,研究博尔赫斯诗歌中的时空体,虽然难以获取到像“完整的时间”那样充满时间必然性和完整性的视角,但也不能放弃对与诗歌时间生成密切相关的空间的考察。博尔赫斯的诗歌时空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众多的有机整体,这一整体深受共时性思维的影响,并将历时性纳入其中,由此呈现出共时性占据主导,兼顾历时性的并置质感的时空特色。
一方面,正是这些时空体在博尔赫斯诗歌创作整体中的复杂众多和共存并立决定了不同时空在诗中的并置,这种并置的具体表现就是诗歌中的意象组群和它们的排列组合形式。在充分铺展开的“永恒循环的时空”和与之类似的时空体中,共时性的思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既然时空如环形往复,那么一个人就可以像是所有人,所有人也都可以是一个人。人不仅像普洛透斯那样千变万化,还超越了时间,由此:“你啊,既是自己又是别的许多人,/不必为埃及的普洛透斯感到吃惊”(《普洛透斯》[7]36)。在“绝对流逝的线性时空”主导的篇章中,时空虽然一去不返,但在一行行诗句中却又借由文字相继复现(虽然已经不再是原初的模样),个体记忆的时空与创造意识凝聚成诗,诗在读者的精神世界和不断地阐释中又获得了新生。由此,一切记忆中的历史都将成为现在和未来,都为永恒这一包罗万象的剖面所聚集。由此,在博尔赫斯许多诗歌中排布着的各不相同的,甚至大跨度地超越时空的夸张意象组合与其说是诗歌体裁和诗歌蒙太奇技法的要求,不如说更是诗人自身时空观和创造意识的自发凝聚,不如说更是其中复杂众多的时空体之间对话交流的复杂产物。在《另一首赠礼之诗》[5]155-159中,时空(意象)的并置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
为了蒙得维的亚的清晨,
为了友谊的艺术,
为了苏格拉底的最后一日,
为了入暮时在十字架与十字架之间传递的
那些个词语,
为了那个伊斯兰之梦,它拥抱了
一千零一夜,
从开头提及致谢对象开始(“我感谢那座/由无数的因与果织成的神圣迷宫”),该诗绝大多数的诗行都是由介词por(为了)起头的名词组合,于是这整首长诗都可以还原为同一个句子的不断反复:quiero dar gracias al divino laberinto de los efectos y de las causas por…(我为了……感谢那座由无数的因与果织成的神圣迷宫)[6]218-223。在此处的节选中,来自不同时空的事物和情境(以名词的形式出现)基本都被一到两行诗所摘取,并在结构相似的上下诗行的对照下呈现出极具博尔赫斯特色的纵聚合关系。“蒙得维的亚的清晨”“苏格拉底的最后一日”“一千零一夜”……这众多超越时空的意象的上下毗邻(并置)不仅给全诗带来了庞大的气魄,还灌注了诗人所钟爱的种种时空体形式:这使这首诗不仅是对惠特曼《草叶集》的一种模仿和致敬(惠特曼是博尔赫斯喜爱的诗人,该诗后面也提到了他),更是一种彰显自身诗风和诗歌时空观的尝试。与惠特曼诗歌中时空相对统一的意象组群不同,博尔赫斯这首诗中各种超越时空的意象并置更是复杂众多的时空体并置:“绝对流逝的线性时空”(“为了1955年的某些黑夜与白天”)“永恒循环的时空”(“为了一件事,就是这首诗无穷无尽/它与一切造物的总和合一/它永远不会到达最后一行”)“梦幻的时空”(“为了无数世纪前我在诺森布里亚所说的语言”)……
另一方面,在显露出时空并置特征的同时,在博尔赫斯一些历时性叙事色彩较为浓厚的诗作中,我们往往能看出其中的诗歌时空体有着趋近“完整的时间”的倾向,并呈现出更加丰富具体的时空质感。在这里,“质感”一词强调的是时间得以表达自身的具体空间,是空间中“一切事物——从最抽象的思想到河岸上的碎石子——自身都打上时间的烙印,充满时间,并且在时间中获得自己的形式和涵义”[3]258,是十足可见的时空。诗集《天数》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7]258-259就更强调时空的质感:
我记得那个原来鲜红、后来变成粉色的标记。
我记得背风向阳的角落和中午的小憩。
我记得有两把曾经在沙漠里扬威逞雄的宝剑交叉而悬。
在此处的节选中,时空质感的表现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博尔赫斯只是在诗中简略地提及“标记”“角落”“小憩”“两把宝剑”,那么凝聚这些意象的时空就会显得十分抽象,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与事件脱离,与人的观照脱离,从而失去了其具体性,模糊未知又不足以取信;然而,与之相反,在上述诗句中,诗人极其详尽地对这些意象加以描述和限定,把它们放入了自己个人的回忆和印象中,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的细节便是这里诗歌时空质感的来源:“标记”在时间的消磨下,从鲜红色褪成粉色;“角落”有了“背风向阳”的空间方位和时间限定,成了小憩这一事件的发生地(这很可能是一种习惯性的事件);“两把宝剑”出没于沙漠,时间是“曾经”,是“交叉而悬”的它们尚能“扬威逞雄”的那一时刻。不过,如果只是到此为止,如果只是充分地展现出了回忆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空质感,如果只是历时性地依序描绘这一切,那么博尔赫斯也就不是博尔赫斯了。在诗人细数着自身回忆中的人事时,不同时空的意象并置现象在“不经意间”又一次出现了(此处仅举一例):
我也记得阿莱姆在一辆锁着门的车里自戕的枪声。
这里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事实逻辑矛盾:阿莱姆是阿根廷政治家,他于1896年自杀身亡,而博尔赫斯生于1899年,因此博尔赫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亲耳听见阿莱姆自杀时的枪声。这行诗(类似的诗行还有不少)与这首诗和其他诗作中的诗行交错对应、相互联系,形成了诗歌时空体之间对话交流的关系,鲜明地表现出了博尔赫斯诗歌并置质感的时空特色。
三、对话交流的时空
在晚年为《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写就的“结束语”中,巴赫金指出了时空体之间相互关系共有的对话性,这种对话超越了作品,进入了读者的世界中,于是“作品及其中描绘出来的世界,进入到现实世界中并丰富这个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也进入作品及其描绘出的世界”[3]456,在“众多作品与众多读者彼此之间会形成复杂多变的时空关系,它们彼此之间又是可以相互沟通的”[10]93。相较于许多作家,博尔赫斯自觉的创造意识和充溢的时空探索精神使得他笔下的各种时空带有了更为自发的对话性,并在彼此之间建立起了深刻又复杂的对话交流关系。
这些对话交流关系首先体现在博尔赫斯创造出的众多的诗歌时空体之间,体现在这些诗歌时空体与作家的小说时空体和散文时空体之间:正是在这些作品时空体之间的对话交流关系中,博尔赫斯巴别图书馆式的文学宇宙昂然屹立。博尔赫斯诗歌时空体之间的对话交流的关系在前文中已有涉及,在这些诗歌时空体的复杂众多和并置质感的特征中已有体现,因而此处不再赘述,重点将放在这些时空体跨体裁的对话交流上。事实上,相较于诗歌写作,在进行散文体写作时,由于体裁对文字容量和音韵的宽容,博尔赫斯的时空书写是更加显著的。无论是在小说还是在散文中,种种时空体的表现不仅更加自明,而且更加具有逻辑性和体系性,甚至“在他的小说中涉及时间、塑造时间和表达时间的篇章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4]54。在小说《通天塔图书馆》对图书馆的描述中,无尽的时空有了图书馆的形象:“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图书馆就已存在”[11]71,“图书馆是无限的、周而复始的”[11]80;相反,图书馆员却是有死的,代代相继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在这里显然可以分别划归于“永恒循环的时空”和“绝对流逝的线性时空”,由此诗歌时空与小说时空之间实现了互通。Babel(巴别塔或通天塔)本身就预示着无限时空的可能,在理论上,它的层数不仅是无限的,其中的人们的文化归属和语言种类也是难以穷尽的,在以此为名的图书馆中,不仅可能藏有世界上所有的书籍,甚至还可能藏有一本能是所有书籍总和的“全书”,不同文学体裁时空体之间的对话交流在这里只会是一桩司空见惯的日常。在散文中,较为典型的例子有由八篇文章组成的随笔集《永恒史》(这一题名本身就暗含着不同时空体的并立),在这里博尔赫斯更是直接用专题研究的方式展开了他对时空问题(尤其是文学中的时空问题)的探讨。例如,在《双词技巧》中,博尔赫斯记录下了一连串冰岛诗歌中的双词描写技巧:“铁器是上帝,海盗的月亮是盾牌,蛇是长矛,剑的露水是血,游隼是乌鸦,红天鹅是所有鲜血淋淋的鸟类,红天鹅的肉是死鸟,狼牙的染色者是幸福的斗士。”[12]34-35在对令人费解的“海盗月亮”做进一步讨论时,博尔赫斯指出了如此技法对于诗歌的必要性:“将每个双词技巧归纳成一句话不是解出未知数,而是取消诗歌。”[12]35无论如何,“海盗月亮”的说法是不会被盾牌顶替的,虽然它最早出自现实世界,而且它对应于盾牌的原因可能确实和海盗与月亮直接相关,但如今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意象并置之下可能产生的文学(诗歌/散文)时空。文章搜罗、理解、阐释这些双词技巧的过程虽然是不断接近它们所产生的具体现实时空的过程,但更是不断接近乃至进入它们所凝聚的诗歌时空的过程,这个体现在文字上的过程本身构成了一种阐释古老诗歌技巧的散文时空,它反过来又在诗人涉及古代冰岛和日耳曼题材的诗歌中出现。
博尔赫斯的诗歌时空体不仅能够跨越作品的体裁,与他的小说时空体和散文时空体之间建立对话交流的关系,它们还作为沟通的桥梁将文本的世界与我们读者所处的现实世界相连。一方面,博尔赫斯的诗歌时空体在作品的传播、阅读、接受中影响了众多的读者和他们的生活创作,这些时空体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正是借由这众多读者具体的思考、言谈、书写、行动才得以产生。例如,在作家富恩特斯看来,博尔赫斯在西语美洲小说中的重要性与他所展现的全新时空体密切相关,“他备受赞誉的直白修辞价值并不在其自身,而在于它如此清晰明了地将时空体作为小说的主角展现出来,即使不可避免地牺牲掉小说的密度和广度”[13]36。他认为博尔赫斯创造出的时空体是十足现代的,这种现代时空体的出现使得西语美洲小说的时空观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富恩特斯在文章中为博尔赫斯小说时空体赋予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博尔赫斯的诗歌时空体:因为正像富恩特斯在论及文学中的“空间革命”时会提到诗人和诗歌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一样[13]40-41,如果博尔赫斯的小说时空体没有与诗歌时空体之间建立对话交流关系,如果作为小说家的博尔赫斯和作为诗人的博尔赫斯之间是割裂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能看见的博尔赫斯的小说乃至西语美洲其他作家的小说中的时空形式恐怕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另一方面,博尔赫斯的诗歌时空体在连通了现实世界,以其特有的形式丰富了现实世界人们的生活之后,还从现实世界持之以恒的应答中丰富了自身,由此完成又再度展开了两方之间的无尽谈话。前文中论述过的《赫拉克利特的悔恨》就是说明现实反过来进入诗歌时空的佳例:在本文为了阐释诗中混杂的时空体而先后引证的两篇文章中,第一篇题名为《马蒂尔德·乌尔巴赫的虚构》(La invención de Matilde Urbach),第二篇叫《卡默拉利马斯如何归还》(De cómo regresóCamerarius),它们分别就“马蒂尔德·乌尔巴赫”这一名字和诗后标注的书目和作者(“加斯帕尔·卡默拉利马斯”)进行了一番考据,并澄清了不少广为流传的误读。这样的诗歌考据和批评鉴赏,甚至包括其中所澄清的种种误读在内(曲解和误读也在可能性的考虑之中),无疑都是对博尔赫斯原诗时空的丰富和扩充,——就连本文也可以算作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四、结语
博尔赫斯诗歌中的时空体首先是复杂众多、并立共存的。这些时空体之间或许会相互转化并产生各种变体,但不同的时空体仍然具有特殊性和不可通约性。其次,博尔赫斯诗歌中的时空体还是并置质感的。正是在诗人共时性主导并兼具历时性的诗歌时空观下,这些各具特色的时空体既实现了在毗邻诗行和不同诗篇中超越时空的并置,又兼顾了质感的凝缩。最后,博尔赫斯诗歌中的时空体还在根本上呈现出对话交流的姿态,呈现出无限向外开放的未完成性:这些诗歌时空体置身于深刻复杂的多重对话关系中,它们不仅在彼此之间形成了对话关系,而且还能够跨越诗歌的体裁与作家的其他文体创作相连通,它们甚至超越了文本的时空,实现了与现实世界中各个时空的沟通。从而,正是通过博尔赫斯的诗歌时空,“通过‘众多的时空之门’,我们为历史打开了众多新的阅读之门”[1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