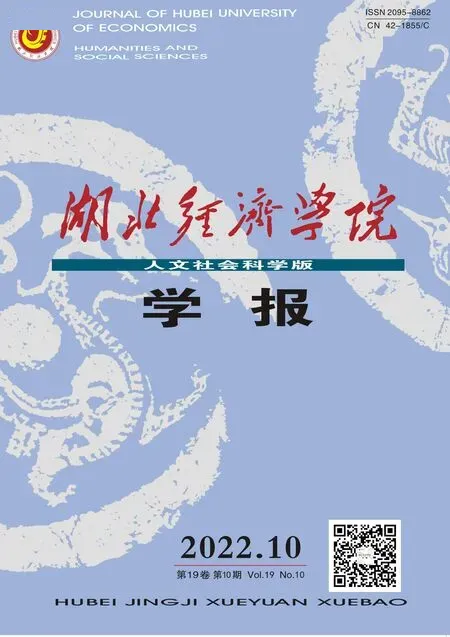“梦幻乃唯一的真实”
——论爱伦·坡的诗人宇宙观
李鲜红(河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一、引言
埃德加·爱伦·坡作品的编者帕蒂克·F·奎恩(Patrick F.Quinn)认为,坡是作为一名诗人开始其创作生涯的,其文学生命的第一阶段以三本诗集告终[1]。坡一生共出版了四本诗集,即《帖木儿及其它诗》(Tamerlane and Other Poems,1827)、《阿尔·阿拉夫、帖木儿及小诗》(Al Aaraaf,Tamerlane,and Minor Poems,1829)、《诗集》(Poems,1831)和《乌鸦及其它诗》(The Raven and Other Poems,1845),共六十三首,外加一出没写完的诗剧。实际上,其文学生涯亦终于诗歌,坡也首先视自己为一名诗人,尽管诗作不多,但他和惠特曼、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并列为美国十九世纪三位最富创造力的诗人。在其短篇小说《阿恩海姆乐园》(The Domain of Arnheim,1847)中,坡借主人公之口引出了幸福的四个条件:简单的、纯生理的户外自由运动;女人的爱;摆脱野心并视名利为粪土;通过不断追求,创造一种新的美。后一个条件在坡看来尤为重要,他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幸福的程度与它成正比。以此反观坡自己,他一生都没有过像样的简单的、纯生理的户外自由运动,而是终生在贪婪的都市的街道上奔波操劳。至于女人的爱,由于他母亲和妻子的过早去世,远谈不上满足,反而是给他沉重的打击。可在“不断追求创造一种美”方面,他可谓是做到极致了。一个自身遭际困顿、心灵极端敏感的诗人,在对时代潜伏的病痛和不幸的感知方面,是比常人更为敏锐的。当现实浇灭了他心头的最后一丝火苗时,他转而“相信梦幻乃唯一的真实”[2]1357,正如他的后继者波德莱尔所言,“美国的气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爱伦·坡“从一个贪婪的、渴望物质的世界内部冲杀出来,跳进了梦幻。”[3]183其实叔本华、克尔恺郭尔和马克思等,皆有自己的“梦幻世界”,只不过换了一种称呼而已,譬如称其为某种超越当下的、形而上的心灵“境界”、人生“眷顾”或曰社会的远大“理想”。很明显,坡的“梦幻”不是指向理论王国,而是钟情于纯美的文学世界。
二、时代潜伏的病痛
坡的诗歌“似梦一般深沉”“似水晶一般神秘”[3]185,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遥远奇特美妙的世界。此世界远离美国的现实生活,具有“人间之外的色彩”[4]121,它是虚无缥缈的、梦幻的;此世界崇尚语言的形式美,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没有像同时代美国浪漫主义诗人那样,钟情于对大自然山水花鸟或边疆野趣的沉思和遐想。他的诗歌想象多驰骋于古典的欧洲理趣、神秘的东方玄论以及难以捉摸的天外世界或荒诞不经的内心世界。”[5]261他追求的是一种“陌生化”的美、遥远的美、有奇域风情的美。在其诗歌里,人们见到的是形式美、音乐美,一点不像同时代浪漫主义诗歌那样充满教诲。在通过诗歌的纯粹“美的形式”和“无限的暗示”中,坡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浪漫主义灵感与其特殊的表达方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坡是一位独特的浪漫主义诗人。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曾说伟大的诗人产生于他伟大的灵魂对自身的反思,坡就是这样的一位诗人。他所处的时代,精神生活动荡不安,诗人敏感的心灵过早并过于强烈地感受到表面水流顺利的大河底处深藏着的暗涛——时代潜伏的病痛。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经济开始腾飞,但坡不以为然,在给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的一封信中,他尖锐地指出繁荣背后的实质,“与6000年前相比,现在人类只是更活跃——但没有更幸福——没有更聪明”[6]716。那个时代的美国,既是其政治与经济的过渡时期,也是其知识文化界经历着空前动荡的时期。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知识界从未经历这样剧烈的动荡;美国所建立的制度从未经受过这样严格的审查,或者说他们的哲学从未遇到过这样尖锐的挑战。启蒙时代那种纯净而有秩序的宇宙——人们能够发现那个宇宙运行的规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新物理学和新生物学地冲击下正趋于瓦解;哲学家无法找到普遍的规律,只能就局部和偶然现象的分析进行争论。然而和谐健全的美国性格正在逐渐消失,引起普遍的不满,由自信的时代转变为怀疑的时代在很多方面都有所表现。人们奇怪,正当一个民族的物质繁荣和科学昌盛达到巅峰的时候,他们思想的特点却不是坚定和自信,而是混乱和怀疑;更加奇怪的是,物质繁荣却很少使广大人民感兴趣,科学也很少能解决根本性问题。美国人对新时代的到来既无经验也无精神准备,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去适应新的经济和哲学秩序。这一转折关头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不是光辉的物质成就,而是惶惑和混乱[7]。
作为对这种动荡时期的应答,美国浪漫主义诗歌应运而生,它是对工业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一种反驳。浪漫主义诗人关注人的生存与精神、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人与上帝、人与机器、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理性成为囚禁于机械体中的“纯粹理性”,阻碍或隔断了人与上帝、人与自然情感那种应有的、充分的、顺畅的沟通,使人类走向了一条“抽象或量化”生存的人生。这种“阻碍”或“隔断”使诗人欲求人的完整性,他们高度颂扬想象力,而不是理性;强调直觉、精神,而不是物质。一部分诗人从自然中寻求艺术创作灵感,从上帝创造心灵的世界里寻求生活的永恒,比如爱默生。他在1836年发表的《论自然》(Nature)里,相信人通过直觉可以认识真理,每个人都有内在的神性,因而在一定范围内人就是上帝。《论自然》寄寓着爱默生对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最高理想,其基调是乐观的;而与此同时,也有诗人急切地关注新世界前途未卜的命运,他们崇尚旧世界古典的美感与和谐,对当时的现实世界充满了极端的困惑和绝望,坡就是属于其中的一位。他曾经对洛威尔这样说过:“我一直生活在未来的幻想中,怪异、冲动、激情、寻求孤独、蔑视现实、渴望未来,这就是我的生活。”[8]作为对爱默生《论自然》的一种答复,坡于1847年发表了被后世称为“美国天书”的《尤里卡》(Eureka,或译《我发现了》)。爱默生在《论自然》里,提出了一个关于宇宙的整体理论,包括它的起源、现状和终极;坡在《尤里卡》里,同样探讨了宇宙的本质、起源、创造、现状及其命运,但其基调却是悲观的。
三、坡的诗人宇宙观
坡的诗人宇宙观,集中体现在他的散文诗《尤里卡》里。关于物质的产生和消失,坡说:“来自单一,更来自虚无,这就是物质的产生。万物皆以返归单一的形式返归于虚无。”[9]宇宙的产生在坡看来,乃是一个从“无生有”至“有生无”的过程。他指出,宇宙产生于虚无,在类似“大爆炸”的原始推动力作用下,原始粒子产生,并形成了多样的物质与星系,但是,每一个粒子自产生起就都处于回归寂灭的状态,也就是于扩散运动中回归原始的“统一”。这其中的扩散与凝聚都是凭借上帝的意志,因此宇宙的发端和毁灭实质上就是上帝意志本身神性的扩散与回归,但这只是坡所构筑的物质宇宙。在坡的精神宇宙里,上帝的神性也分解为无数的粒子向外扩散,因此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神性,人的生命由生到死的运动即“上帝的复原”,所以,“死”是个人的灵魂与上帝相“统一”的过程。整个宇宙——物质的和精神的——就这样在上帝的心跳中被创造和被毁灭,循环不已。坡认为这种“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过程是一个既真实又壮美的过程,而这个真与美相融为一体的过程正是他所要追求的“超凡之美”(Supernatural beauty)。坡的物质宇宙之外还存在着精神宇宙,因而他对于宇宙的认识是基于人的想象力的。为了更好地理解他的这种诗人宇宙观,以下是对它的一番解析。
在坡眼里,天地万物是一种诗意或艺术的创造,是“上帝的技艺”。当上帝在宇宙原初的混沌状态下把其仁光辐射到广袤的天地时,便产生了世间万物。产生伊始,万物与宇宙还是一个未区分的整体,可以尽享“天人一体”之乐。随后,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到了坡的时代,称之为理性时代。理性时代在促进工业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遗留下了不少恶果。纯粹的理性障碍了人与上帝的真正沟通,使得人与上帝的仁光日渐分离,人类成为“关闭在机器中的天使”。换言之,人失去了原初的完整性,日渐异化。那么如何去恢复这种完整性呢?坡认为,既然上帝创造了万事万物,在万事万物中体现自身的存在,然而现今只有那些对自我不断进行反思的人身上才有上帝的影子,那么,就需要那些人借助于一种力量,来帮助人们恢复自身的完整性,即恢复自我。
但那种力量究竟是什么呢?既然“行成于思”,因而那种力必须是来自于心灵的。又既然万物的创造是“上帝的技艺”,那么这种可使万物重归自我、重归完整性的力又必须是充满想象的。简言之,作为上帝创造物的人类,他们的职责便是运用诗意的想象力,重新与上帝沟通,以求达到最初的完整性。
因而,对于上帝的创造,正确的做法便是要在其创造的美与和谐中获取一种富有想象的快乐。怎么获取?按照坡的看法,无疑是通过直觉和想象、通过与上帝直接进行心灵的沟通。不通过直觉和想象而采取其他方式来获取快乐,都是在否定上帝的存在,都是在日益背离上帝。据此我们可以猜测坡是想否定通过获取物质的方式获得快乐的做法。在他那个“工业万能”的时代,人们对“物质的、反常的、几乎是畸形的发展感到自豪,对于工业的万能怀着一种天真的信仰;……时间和金钱的价值是如此之大!物质的活动被夸张到举国为之风靡的程度,在思想中为非人间的东西只留下很小的底盘。”[4]122不幸的是,坡认为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人类就是在追逐物质主义。他们屈从于科学理性主义,宁愿要物质的现实而不愿要幻想的真实。结果人类的心灵日渐扭曲、黑暗,感觉日呈病态、迟钝。就连人类生存的外在世界也染上病态的色彩,失去了最初的神圣之美与和谐,也失去了秩序。更可悲的是,我们这个日益腐化堕落的世界也日益不利于诗人的栖身。尽管在诗人的心中,神圣的幻想力的火苗还在燃烧;尽管在他的灵魂中会微弱地闪现并渴望崇高的和谐与美,然而他周遭的事物都在图谋把他贬到不能再贬低的程度。科学家和功利主义者辱骂他,极力败坏他的名声,他们那些机械的、缺乏生命力与想象力的思想不断侵蚀他的意识。最后,连诗人进行思考时,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在这个对诗人来说“不过是一座巨大的监狱”[4]122的国度里,生活成了地狱。他唯一可逃离的方式便是小心翼翼地从世俗的、理性的、物质的世界撤离出来,退守到一个幻想的世界当中。在那里,在那些非物质的梦想地带,他可以洗尽尘世的铅华,享受天堂般的美景,与上帝的思想同一。
从这个物质的世界撤离之后,诗人便开始了对自我的完整性的追求。可是诗人却遇到了更大的不幸:他与他自己也是格格不入的。如果说在前存在阶段(即灵魂在与肉体相结合前即存在的阶段),诗人曾经有过完美的精神上的和谐,那时他的意识是纯想象力的。然而,当他在这个日趋腐化堕落的世界中渐渐长大时,他的自我也渐渐受到侵蚀,进而或者妥协,或者变形。他的生存阅历提醒他要对乏味的逻辑和枯燥的科学持尊重的态度,他的现实驱使他倾向于物质性。可他的心灵里,却还留有神圣的火苗;他的灵魂中,也还存有崇高的和谐与美。这样,欲望和良知在心底开始了疯狂地搏斗。结果,他的心灵难免要遭受扭曲,病态进而驻留其中。这样,诗人的心灵就失去了其原初的完整性。虽然可以暂且逃离物质的世界,沉湎于梦想的地带,却无法停止与自己的冲突。那么,诗人认为,除非是回归寂灭,要不难以重获自我的完整性。而在这“寂灭”之前,诗人的想象力不但要跟庸俗的物质世界相抗衡,还要跟他内心庸俗的一面相抗衡。这样,作为诗人的坡便注定了是孤独的、痛苦的,同时也是悲观的、倾向于死亡的。
坡的极端悲观体现在他承认上帝可以认识,但又宣布上帝神性的微粒在人身上表现为反常,因为“任何从正常的偏离都包含着一种向其(指上帝)回归的趋势”,即是说,对毁灭、本能、苦难、解体、堕落的屈从,反而成了对上帝的崇拜;坡的消极体现在,他更多地继承了南方天主教传统,认为原罪无可逃避,人必须要受诅咒,注定要忍受忧愁,并且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毁灭。但这种毁灭倾向或称虚无主义倾向,在坡看来也是不足为惧的。因为只要窥见了那种“超凡之美”的光芒,对死亡的恐惧便会停止。因“超凡之美”非凡胎肉眼所能及,坡因而欲通过其梦幻般的作品让世人“隐隐约约地对其瞥上一眼”[6]14。
四、宇宙观观照下的梦幻世界
从诗歌《阿尔·阿拉夫》到《尤里卡》,坡对于事物的看法都是宇宙式的。
不难看出,坡对想象力的推崇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对坡来说,这种诗意的想象力对于创造一个美妙的梦幻世界来讲是前提条件。早在出版第一部诗集《帖木儿及其它诗》时,坡就在序言中说:“构成这本小书的大部分诗都写于1821年至1822年间,当时作者还是个未满14岁的少年……这名少年对世界尚一无所知。诗只能出自他的心底。”[2]3这些“出自心底”的诗作无疑是诗人的想象力的结果,它们在内容上已表现出诗人对生命意义的关切和探求,在形式上已显露出了他那种具有梦幻般节奏的艺术特色。在其书名篇《帖木儿》里,诗人欲告诉世人,对世俗功名的追求到头来终将是虚幻。坡在《梦》中说道,“因为我一直耽溺于白昼的梦幻/并把我自己的心,不经意的/一直留在我想象中的地域——/除了我的家,除了我的思索——/我本来还能看见什么?”[2]33诗人对此的回应是他22年后在《梦中之梦》中的两行诗:“我们所见或似见的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梦中之梦。”[2]129诗人认为想象力是“各种才能的王后”,是“一种近乎神的能力”[4]124。而任何破坏这种诗意想象力的做法,他都是不赞成的。比如在《致科学》这所诗中,科学虽促进了社会发展,但不受诗人的欢迎。“你改变了一切,以你锐利的眼睛/你为何如此折磨诗人的心?”[10]135科学是求实的,扯破了美丽的神话传说的面纱,从而破坏了诗意。“难道不是你从车上拖下月亮女神?/不是你把树精逐出森林/到一个更快乐的星星避难安家?/难道不是你从湖中揪出水精/从碧绿的草丛驱走小精灵/并扯破我的夏梦,在罗望子树荫?”[10]135《致科学》是一首重要的诗歌,也是他第二部诗集《阿尔·阿拉夫》的引诗,描述了由于科学的步步进逼,诗歌已经无处藏身,表达了对于逝去了的诗歌的传统和美的哀叹。在这一点上,这部诗集与前部诗集《帖木尔》是一致的:都表达了诗人从客观的外在世界中退却,逃隐到主观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表明了诗人要在这个日益世俗化的世界中保留高度的想象力时所遭受的痛苦。科学与幻想的冲突、现实与梦境的冲突、真理与诗歌的冲突,成了主题诗歌《阿尔·阿拉夫》的一部分。《阿尔·阿拉夫》延续了诗集中前几首诗的梦境,它描述的是一个遥远的世界里,在一个脱离了尘世的现实的世界里,诗歌的神话仍虚无缥缈地存在着。“阿尔·阿拉夫”原是阿拉伯神话中的一个灵魂寓所,坡却把它想象成16世纪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曾观察到的一颗行星,成了上帝派来接获释灵魂的“天国大漠旷野中的一块绿洲”[2]45,诗人特别羡慕那儿,因为那里“没有我们世界的浮沫沉渣,有的全都是美人,全都是鲜花”[2]44。坡在他的《诗集》序言里也特别提到了想象与梦幻,“想想那虚无缥缈,如仙山奇境的一切”[2]12。
想象力是前提,但光有想象力还不够,还得用一种非凡的功能将这些想象出来的奇特怪诞的梦表现得有美感。这种非凡的功能在坡看来便是语言的魔力,“我如此信服语言的魅力,所以我相信要描写那转瞬即逝的美之梦并使之具体化也是可能的。”[11]1383坡又告诉我们语言给读者或听众带来的快感,“如百合花盛开在湖边,或以Amiryllis(代表美人和情人的普通名词,这里指罗马田园诗中的女牧羊人)的泪眼闪烁在镜中,这些词藻、声音、颜色、气味、感觉,不管是口头或笔头表达都是欢乐的双倍来源。”[11]77坡在其诗歌中通过语言的形式美、词语的音乐性,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听觉与视觉、节奏与音韵、想象与情感高度统一的世界。对于词语的“音乐性”的强调,我们从其《诗集》的序言中关于对诗的阐释便可看出。
“依我之见,诗与科学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诗的直接目的是获得快感,而不是求得真理;诗与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诗的目的是获得含混的快感,而不是明确的快感。只有达到了这个目的才算是诗。小说赋予可感知的意象以明确的情绪,而诗所赋予的是不明确的情绪。要使意象给人的感觉不确定,音乐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要素。因为我们对音乐的理解是一种不确定的概念。音乐与给人以快感的思想结合便是诗。没有思想的音乐仅仅是音乐,没有音乐的思想则是散文,因为它的情绪是明确的。”[2]13
在其名诗《致海伦》中,坡以古希腊史诗与神话开始,以“美”与“灵”的关系为主线,运用了一系列手法,如对比、通感、比喻、象征等。在诗前两节,坡以“轻轻划过香海的尼斯小船”赞扬古希腊艺术之美、自然之美、人之美,这种美能使“疲惫的绝望者”得到安慰。最后一节,“美”(海伦)与“灵”(Psyche,普绪客,希腊神话中以少女形象出现的人类灵魂的化身,与爱神厄洛斯相恋)的完美结合道出了诗人的艺术追求。《诗集》当中有首《睡美人》,通过运用一种舒缓的节奏,坡使梦幻曲的音律与超自然的气息水乳交融,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也感到香消玉殒的伊蕾娜是在沉睡。在《伊斯拉斐尔》中,语言流畅,音韵具有节奏感,给人以一种“此声只应天上有,人间何曾几回听”的感觉。在诗中,伊斯拉斐尔天使的歌声美若“笛声”,能使浩瀚之星辰羞涩,使寰宇之天籁无声,皎洁之明月为它动情,旋转之北斗也停步聆听。因为它心中点燃了激情的火焰,并配以相称的韵律。然而诗人自己周围的现实却难以触发激情,假如他能处在天使的境地,他也会唱出高亢豪放的曲调。“如果是这样,我能住在/伊斯拉斐尔住的地方/而他住在我住的地方/那他唱一支人间歌曲/就不会那么动听悠扬/而从我在天空的琴里/传出的曲调会更豪放。”[10]141诗人居住的世界里充斥着太多的理性主义,因而诗人通过主张诗歌要有激情这种方式来无声地反抗。同时,诗人追求一种纯粹的形式美。坡认为诗歌只应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不是给人以真理。“诗之所以为诗,即在于能使人情感激荡,使灵魂升华。诗歌的价值,同其造成使灵魂升华的激荡成比例。”[5]447他的后继者波德莱尔呼应道:“……诗不能等于科学和道德,否则诗就会衰退和死亡;它不以真实为对象……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这种本质表现在热情之中,表现在对灵魂的占据之中……是一种心灵的迷醉。”[4]126波德莱尔的这种表述,初看就如同坡的一样。
在坡通过语言的魔力创造的那个形式美的梦幻世界里,除了古典的美感、激情外,还有另一种畸形的美感——死亡。如前所述,诗人从一个贪婪的、渴望物质的世界的内部冲杀出来,跳进了梦幻之后,却还要面对心灵的无休止的冲突。诗人的悲观使他追求死亡,通过死亡来求得自身的完整性。对坡而言,死的吸引力无疑就是爱的吸引力。在爱与死的结合中,坡看到的不再是爱神独自绘出的微小画面,而是超出人世之框的巨幅图景。画卷铺天盖地,甚至超越天地,上至天国,下抵地狱,其中之底蕴、之诡秘,谁能知晓?坡在《创作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1846)中说,人世间“最忧郁的”莫过于“死亡”,“最忧郁且最富有诗意的”就是“一位美丽的女子”(自己钟情的恋人)的“死亡”,因为“这一时刻最接近美”。那么坡追求的是一种什么美呢?他在《诗歌原理》》(The Poetic Principle,1848)中说:“如果一个人仅仅是用诗来再现他和世人一样感知到的那些景象、声音、气味、色彩和情趣,不管他的感情有多炽热,不管他的描写有多生动,我都得说他还不能证明他配得上诗人这个神圣的称号。远方还有一种他尚未触及的东西,我们还有一种尚未解除的焦渴,而他却没能为我们指出解渴的那泓清泉。这种焦渴属于人类的不朽。它是人类不断繁衍生息的结果和标志。它是飞蛾对星星的向往。它不仅是我们对人间之美的一种感悟,而且是对天国之美的一种疯狂追求。”[6]683
这种“天国之美”就是上文所说的“超凡之美”,是一种“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既真实又壮美的过程,是一个真与美相融为一体的过程。在诗歌中,坡用非凡的才能将“死亡”表现得那样凄凉又那样美丽,如那长眠于海边孤坟的《安娜贝尔·李》;那样可怕又那样有魅力,如那死神建立的《海中怪城》;那样奇异又那样恐怖,如那永远不会睁开眼睛的《沉睡的人》。无论是窥见“在无名荒冢间摇曳落泪的百合花”(《不安的山谷》),还是望见“苍昊之下那汪忧郁凄清的海水”(《海中怪城》),读者都不由自主地进入对死亡和毁灭的冥想与体验当中。这些形象,很显然都是坡试图忘记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在坡的一生中,他见证了很多离别或死亡。一岁时父亲离家出走,三岁时母亲也去世,成为孤儿。虽被一富商收养,却跟养父的关系日渐不好,终至破裂。成年后与表妹结婚,十二年后妻子病故。从此他便一蹶不振,靠着酗酒度日。残酷的现实,非诗人那颗敏感脆弱的心所能承受。因而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他那被现实所扭曲的心态和被他的心灵所扭曲的现实。在另一首表现“死亡”的诗《黑鸦》中,诗人营造了一个极度形式美和音乐性的诗歌世界。他描写一只会讲“永不再会”的黑鸦,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落在一个还有微弱灯光闪动的窗户处,扑动双翅,要求入内。屋内一青年,正为死去的情人而哀伤,听到门外有声,先疑有人来访,继而启窗见鸟立室外,感到惊奇,问其姓名,鸟答“永不再会”,引起青年对故人的怀念,心中的忧郁犹如泉涌一般奔涌而出。殊知这只象征悲哀和痛苦的不祥之鸟,仿佛了解人心一般,不时以“永不再会”一语加以应和,使青年的心情愈益郁悒,对自己愈加肆意折磨,尽情地领略悲伤的意趣,全诗在缠绵的悲思中结束。全诗格律工整,音韵优美,诗行长短交错,并运用了头韵,行间韵,重复(迭句)等艺术手段。这些都为整首诗的气氛做了极好的渲染,使黑鸦象征无尽的哀思——对于逝去的美女的哀思。同时,一般用来暗示某种“不祥之兆”“不谐之音”的黑鸦在这里却成了傲立寒冬、不畏寂寞的美的形象,它在喧嚣的“风雪交加”的冬夜里反复呐喊的“永不再会”似乎在宣布旧世界逝去的悲怆以及新世界到来的恐惧,还有未来的虚无和缥缈。
五、结语
评论家丹尼尔·霍夫曼(Daniel Hoffman)认为,坡一直被他现实生活中的不幸所困扰,因而欲寻求一种想象与艺术上的控制与自由。霍夫曼评道:“对于这个任性而又穷困潦倒的年轻人来说,他所拥有的只是在他那些富有节奏性和音乐性的文字当中所构筑出来的梦幻和徒劳的想象。埃德加只能求助于成为他自身想象力的主角。”[12]通过想象力和语言的魔力,坡在他营造的那个梦幻般的诗歌世界里追求美感,崇尚精神,赞美和谐。他的创作深深地受其诗人宇宙观的影响。在一个崇尚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社会里,他反对诗歌的说教功能和现实认知价值,提倡“为艺术而艺术”,追求一种纯粹的形式美,那是因为决定他诗质的背后存在另一个世界及其“象征统治秩序”——非真实世界的意象。坡是在向新英格兰的哲人们(如爱默生等)提出挑战同时也在消耗着自己。“他选择的是在‘回归性’或‘追溯性’的艺术想象中自我逃避,在怪诞和梦幻中寻求片刻的安慰,直到生命的终结。”[5]265
坡在《尤里卡》的序中这样说:“对爱我并为我所爱的为数不多的人——对那些爱感觉而不是爱思索的人——对梦幻者以及那些相信梦幻乃唯一真实的人——我奉上这册真言之书并不是因为书中句句是真,而是由于其真中充溢着美;此乃真之本质。”[2]1357一语道破了他诗歌创作的精神实质。坡的不幸(要说不幸的话)在于他把自己所生活的现实与他想象中的世界一直搞混了,似乎长期处在与健康的人性相对立的道路上。但我们若像过去许多批评家那样,认为其诗歌不过是诗人青春期的梦呓而已,我们恐怕就是在误读他。狄尔泰在论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时所说,“一切沉思、严肃的探索和思维皆源于生活这个深不可测的东西。”[13]坡也是如此,他对人生和世界地探索与思考,主要源自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危机和其个人的生活困境;他对宇宙的本质、来源和归宿进行的探索,以及由此推及的上帝与人的关系地深究,其实都是为了弄清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地位和人的存在意义及价值。只要对其诗人宇宙观稍加了解,就不难认识到,坡对于生命的需求恐怕是深奥的。其颠沛流离、劳心伤神的一生是那么短暂,但他就像中世纪神秘的炼金术士,屈从于生命脆弱的幻觉所具有的魔力,并且未尝有过丝毫的懈怠。因为诗人知道,要是诗人自己失去了幻觉,失去了想象力,那么这个世界必定显得更加恐怖,就如其短篇小说《厄舍古屋的倒塌》中那座古宅,轰然倒地,化为尘土。坡的伟大,就在于他以一种探索尽善尽美之物的狂热精神,使美国文学充满独创性。而且他创造的那个梦幻的诗歌世界足以使一个诗魂摆脱掉世俗的、理性的物质世界,逃遁到一个无拘无束让想象自由驰骋的王国,哪怕逃一会儿也好。而至于那个梦幻世界里所描述的死亡,笔者赞同曹明伦先生所说的[6]7,即坡或许是想探究死亡的奥秘,从而能够更坦然地面对死亡,有他在《尤里卡》一文篇末“附记”为证:“当我们进一步想到上述过程不多不少正好是每一个体智能和其他所有智能(也就是整个宇宙的智能)被吸收回其自身的过程,我们因想到将失去自我本体而产生的痛苦便会马上平息。为了上帝是一切的一切,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上帝。”[2]1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