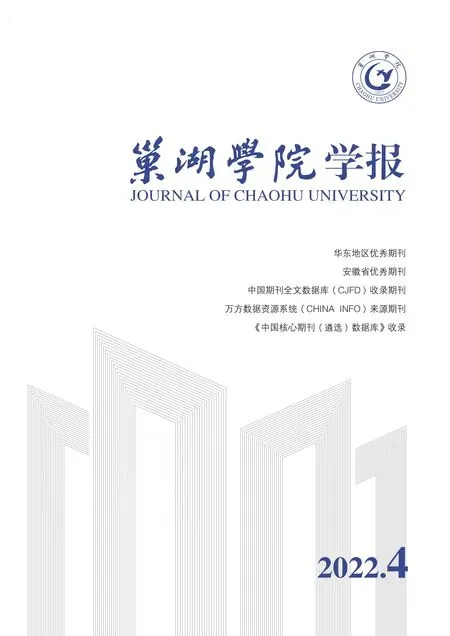清末民初北京开设通商场问题述论
刘 桂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引言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门在西方列强的炮火威胁之下逐渐打开,开放口岸陆续出现。其中,依照中外约章开辟的口岸称为约开口岸,中国自定章程主动开放的口岸是为自开口岸。北京通商场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既不是约开口岸,也不是自开口岸,而是列强违反条约开辟的特殊通商场域。刘彦在《被侵害之中国》中称其为“特别商埠”,因其“既非与何国约开之埠,又非中国自开之埠。而事实上外人居于斯、贸易于斯。与约开自开之埠,毫无区别,且有违超过于自开商埠之权利,而与约开商埠之权利相等者”[1]。这种“特别商埠”,并非北京所独有。其产生的原因,既有外国公使的纵容和包庇,也有中国政府管治不力的无奈。北京通商场的开设,更是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影响。民国时期,已有一些学者的著作中论及此事,如郑斌《中国国际商约论》、刁敏谦《中国国际条约义务论》、刘彦《被侵害之中国》等,这些著作虽有论及,但不够深入、系统。近年来,关于北京设立通商场问题的研究,为数不多。李育民[2]在分析具体的不平等条约特权时,曾以北京通商场为例进行论述,其认为北京通商场的开设,是列强滥用最惠国条款、违约侵权的结果;李永胜[3]叙述了中日《通商行船续约》签订前后双方的交涉细节;吕铁贞[4]从法理角度出发,认为晚清时期一直未实现外商在北京通商的合法化;曹英[5]指出北京是清季内地违约设栈最严重的地区,在丧失司法主权的情况下,洋商在北京居留、贸易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了直接威胁。以上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北京通商场这一特殊通商区域大有裨益,但仍然难以从宏观上把握北京通商场开设的始末。本研究主要依据相关著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等资料,力图对清末民初北京通商场开设始末做比较详尽的考察。
一、清末北京开设通商场问题缘起
北京通商一事,由来已久。自康熙三十二年(1693),俄国遣使至中国,要求派商队到北京贸易,康熙帝许三年至京贸易一次,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人,外人进入北京通商自此始。而后乾隆皇帝认为北京通商多有不便,遂停止俄人在北京贸易,令统归恰克图。此外,清政府还允许某些朝贡国与北京会同馆进行贸易,如朝鲜、越南等,但朝贡国需遵守严格的规定。以上所述皆与近代以来的开放通商问题性质不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渐开,但清政府始终坚持北京不在内地通商之列。其主要理由是“北京系辇毂之地,领事裁判权的存在,旅居京城的外国人‘不归敝国皇帝治辖,实不雅观’。再者如果使北京开埠通商,则京城外国人必定增加,争端之事不断‘宫禁成何体事’”[4]。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八款明确规定:“天津条约英国第九条所载英民持照前往内地通商一款,现议京都不在通商之列。”[6]这是中外约章中首次明确规定北京不实行开放通商。
庚子事变之后,情况发生了转变,《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人开始获得在北京驻军的权利。清政府仍然严厉禁止洋商在北京居留、贸易,但此时洋商在京城居住、贸易已日渐增多,其中尤以日商为甚。外商所设行号,多以使署员弁等之用的名义、或公然开设之。1901年10月,《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清政府就照会各国驻京公使:“现在和议已成,言归于好,京城地面不在通商之列,其洋商所设行栈自应按照条约一律移至通商口岸,如有已经修盖房屋者,亦应即行拆去,不得借口索价,以免轇轕。”[7]按照《辛丑条约》第十一款规定,中外各国通商行船条约应行商改。美、英、日趁机向清政府提出修约问题,清政府先后任命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吕海寰、盛宣怀、伍廷芳等为代表,进行谈判。英国最先提出北京开埠的要求,但外务部认为,京师为根本重地,不便通商,驳斥了英国的请求,“辇毂之下,岂可任各国商民任意聚集,而我毫无管束之权。”[8]美国也不甘落后,希望趁此机会能够迫使清政府将北京开放。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H·Conger)认为,外国人在北京开店设栈,其经营区域虽然在使馆区,但业务却遍及整个城市,事实上,北京已向特殊贸易开放。“如果各国商人已经获准在北京做生意这个信息是正确的,那么当然,美国公民也有同样的权利”①Mr.Conger to the President and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October 10,1901,U·S·State Department,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US),1903(U·S·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Washington,1904),P121.。1901年10月10日,康格向美国总统和外事委员会提出建议“现在是中国政府自愿将北京开放成条约口岸的最佳时期”,“北京应该是其后广袤人口和辽阔领地伟大而又方便的中转站”②Mr.Conger to the President and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October 10,1901,FRUS,1903,P122.。10月16日,康格再次致信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他表示自己和大多数同僚一样,“认为最好使北京保持开放,并且希望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将导致整个城市向对外贸易开放”③Mr.Conger to Mr.Hay,October 16,1901,FRUS,1903,P121.。日本接着也向清政府提出北京、奉天、长沙等地开埠通商的要求,之后双方进行谈判交涉。
清政府内部对于北京开埠通商一事持有不同意见。张之洞和吕海寰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出发,倾向于主张北京实行开埠通商。张之洞认为:“北京开埠一事,于我并无所损,如彼再提,我正可藉此催其撤兵。愚见窃谓若能量减护馆之兵,移紫禁城外,我国体固为极好,即仅撤护路兵,于大局亦甚有益,撤护路兵者即撤护馆兵之渐也。”[9]并且他认为“自开”相较于“他开”,“自开”法权在我,归我管辖;“他开”则我无治外法权,不能管辖约束洋人,以致产生华洋纠纷,胶葛繁多。吕海寰也赞同日本代表小田切万寿之助的意见,北京应开埠通商。1902年1月25日、26日,中英交涉时盛宣怀致袁世凯、军机处的电文中谈到,北京不能实行开埠通商。“其万难允者如运盐进口,运粮出口,洋商入内地制造,京城开通商口岸等款,已经痛驳。”[10]随着谈判的深入,清政府出于自身的考虑,亦转向比较认同北京由中国政府自行开辟通商场。其时在京城居住、贸易的洋商已渐多,政府虽然多次照会外国公使团,催洋商移居租界,以符约章,但阳奉阴违者居多,遵从者寥寥无几。北京虽然无商埠之名,但确有商埠之实。用“自开”来抵制“约开”,中国尚可收回某些利权。此外,纵观当时的国际形势,泰西发达之国家首都亦多开放而商业繁盛,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非常可观,这也是清政府主张北京自开通商场的一个诱导因素。
二、北京开设通商场交涉经过
北京开设通商场一事的交涉经过,以清朝覆灭为界,可以分为外人要求“设场”交涉和抵制外人“设场”活动两个阶段。1903年10月8日,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列强纷纷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获取同样权益,北京“设场”由此取得条约依据。条约规定,北京开设通商场的前提是撤退全部外国在华的护馆、护路兵,但这一前提条件未能履行。民国初年,列强同样未能履行条约规定的撤军前提,以洋商在北京居留、设栈之事实抵制条约,放任本国商民违约在京居留、设栈,北京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限制外商在北京的商业活动,但收效甚微。清末民初北京开设通商场一事,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成为近代列强侵华史上又一桩悬案。
(一)清末北京通商场的交涉与设立
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英、美、日三国分别派出代表与中方进行修约谈判。1902年5月,日本代表小田切万寿之助、日置益与中国代表进行商约谈判,并向中国提出商约草案,共计十三款。此时中英商约谈判尚未完竣,在沪负责谈判的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伍廷芳表示,难以同时与两个国家分别进行商约谈判,以“英约未订,不便深议”[11]为由,暂时停止了中日商约谈判,另一方面将日方约款草案送至张之洞、刘坤一处,并呈报外务部。英约完竣后,次年2月间,双方开始正式开始谈判。
小田切万寿之助拟定的草案十三款,约文中尚未提出北京开埠的要求。但双方就某些款项分歧很大,难以达成一致,尤其是英约所没有的条款。日方变计提出,已经拟定的各款可以签字画押,没有拟定的条款再继续讨论。吕海寰等认为这种办法各国从来都未曾有过,难以实行,拒绝了日方的要求。1903年3月,双方在沪交涉暂行停止。
适时张之洞应召入京,清廷下旨所有商约在京师开议,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赴外务部与张之洞谈议。内田康哉提出北京开埠、加税免厘、米谷出口三条在京议定,其余仍在沪订[11]。谈判的地点由北京转向上海,重点是讨论日方所提的三条议约。4月7日,吕海寰、伍廷芳将日本要求北京开设通商场的照会电达外务部,其文曰:“所有直隶省北京、盛京省城及大东沟、湖南省长沙府等处,订自本日起一年之内,添开通商场,准各国人居住、营业。所有章程,商与日本协定。”[3]外务部和张之洞拒绝了日本照会所提要求。6月3日,张之洞与内田康哉举行会议,两人为北京开埠一事激烈争论。内田康哉说:“京城地面,各国洋商业已纷纷设肆,中国并未过问。与其散漫无稽,于地方管辖之权有碍,不如划地开一商埠,尚有限制。”[3]张之洞则说:“各国如能将护馆兵撤退,当将开埠事商我政府,但必须仿照日本东京所开外国居留地例,巡捕由我自设,地面由我管辖,或可与我政府酌商。”内田康哉答复此事需向日本政府请示[3]。6月22日,内田康哉表示可以用撤军换取北京开埠,但是护馆兵不能立即撤退,可以撤退城外护路兵。8月14日,张之洞与内田康哉有关北京开埠问题交换照会,规定各国护路兵和使馆卫队全部撤出后,北京开设通商场,准各国通商居住。
1903年10月8日,日本代表小田切万寿之助、日置益与中方议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伍廷芳在上海正式签订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共十三款,并有《续议内港行轮修补章程》等七项附件,其中与北京开设通商场相关的是约文第十款及附件六、七。第十款云:现在两国议定:“如驻扎直隶省之各国兵队暨各国护馆兵一律撤退后,中国即当在北京自开通商场,其详细章程临时商酌订定。”[6]附件六、七规定了具体的办法:
所有北京开设通商场一事,按照通商行船条约第十款所订:如各国护馆、护路兵队一律全行撤退后,于北京内城之外,择彼此相宜并无窒碍之地划出界址,开作各国商人居住、贸易之所。界内地方,准各国商人租地、造屋、开设行栈店铺,惟民房民地必须业主情愿出租者,公平商议租价,不得抑勒强迫。所有道路桥梁,均由中国自行管辖经理。各国商民在北京通商场内居住者,须遵守该处工部局及巡捕章程,与居住该处之华民无异,非得华官允准,不能在界内自设工部局及巡捕,自定界开办以后,凡从前各国商民之散居城内外者,均须迁入界内,不得仍前散居各处,以致漫无稽考。所有外国商民房地,公同酌定,给予公平价值。其迁移入界限期,临时酌定,若逾限不迁,即不给价。[6]
照此办法,北京开设通商场的前提是各国护馆、护路兵队一律全行撤退。
条约签订之前,英、日、美、法、德态度坚决,强烈要求清政府宣布北京开放通商。“必须使中国外交部清楚地了解到,这些国家决心使北京成为通商口岸”[12]。然而,条约签订后,在未履行各国护馆、护路兵一律撤退的前提下,一些外国商民即在北京居住、设栈。清政府多次就此事照会外国公使团,但仍然无法禁止外商在北京违约居住、设栈。“外务部前曾照会各国公使,禁阻洋商在京城内开设行栈,惟各国公使谓此项利益应准仍旧。”[13]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外国公使团的纵容和包庇,另一方面是清政府的衰弱积弊,无法与列强抗衡。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性办法,如对开设的洋行店铺进行登记造册,并且“一面照会各国公使转告该国商人将所开行店即行停办,一面咨行巡警部通饬各属遇有违约开店之事立即予以实力拦阻”[5];或是实行营业执照制度,所有新开设的店铺,必须请照经营,否则不得开张,但收效甚微。
清廷迫于无奈只能承认既成事实,遂向各国声明“此后不得再行开设”[14]。英国公使朱尔典曾以领袖公使名义答复清政府:
北京通商一事,虽未经条约议决,然自拳匪乱后,京师内外城,外国商民居住贸易,已成公认之习惯。一千九百零三年中日商约大臣曾议决外人军队撤退后,中国即在北京划定商场,内外城外国商民须迁移于划定地界内。并无禁止现在外人通商之语,所谓禁止者,不过推测而得。谓两方既议定划界后,乃承认外人贸易居住;则未划界限之时,不准外人贸易居住也。然同年外务部曾宣言,已有外人商务屋所,可不封闭,惟此后不得再援例开设。外交团亦迄未承认此议,故公平议之,现在中国实被此宣言制止,不能不许已在北京外居住贸易,由此而知不许同样外人来此居住贸易之说,为无理矣。[15]
仔细分析英国公使的答复,错漏之处昭然若揭。按照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外国军队尽行撤退后,北京才能开放通商场。清政府多次照会外国公使团,在北京城内居住、设栈的洋商应移至租界。无论是约章还是中国政府的照会,都明确表达了禁止洋商在京师居住贸易的意思。“自定界开办以后,凡从前各国商民之散居城内外者,均须迁入界内”[6],按此语义,并没有明文规定定界未开以前仍准外商开设行栈。“惟此后不得再援例开设”[15],实为不得已而为之,退一步讲,此后外商也不得再进入北京开设店铺。朱尔典却认为中国被此宣言约束,无法禁止外商在京城贸易,前之来者既未禁止,后之来者更不可禁。各国纷纷援引最惠国条款,放任本国商人在京城居住、贸易。然而,只要外国在北京的护馆护路兵没有撤退,清廷就没有义务在北京划设通商场,所有洋商在北京的经营贸易活动即属非法性质,以“习惯”来抵制条约,其荒谬程度可想而知!美国对于清政府禁止外商在北京购地居留置产的声明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康格提议,“最好不要正式地同意他们的要求,也不要断然拒绝,以迫使他们做出直接而明确的规定”①Mr.Conger to Mr.Hay,August 21,1903,FRUS,1903,P121.。其后,国会同意了康格的建议,“这个问题可以留到以后必要时再讨论”②Mr.Hay to Mr.Conger,October 9,1903,FRUS,1903,P122.。
(二)民初中国社会对通商场的抵制与效果
迨至民初,北京划设通商场一事仍旧困扰着北京政府。同清政府一样,民国初期,政府也不同意西方国家违约在北京开设通商场。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中国尚未收回领事裁判权,外人在北京居留设店,多不遵守中国警章,以致管理困难;另一方面北京的护馆护路兵队一直没有撤退,如果划设通商场,这不符合条约规定,同时也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国家利益。1912年9月12日,民国政府外交部特为此事照会各国公使,议定:“凡民国元年九月以前外商已开各店铺仍准其照旧营业,惟须与华商一律遵守警章,同受保护。此外无论如何,不得再行开设店铺,如有违约私设者即行查封,以符条约。”[14]对于此照会,仅有瑞典和西班牙两国表示会转饬本国商人遵守条约(西班牙后又表示不能遵照),英、美、日、德、意、西等11国纷纷表示“未能将贵部所拟者循照饬行。”[14]英、美、日、德、西等11国给出的反对理由主要有:第一,外商在京城居住营业已成习惯,不便取缔;第二,1903年中日约章所订,其文并无禁止现在在京洋商居留贸易之意,所以直到择定地界之时,仍准洋商居住贸易;第三,从公平角度出发,既然允许此前在京师的洋商居留贸易,此后来京的外人,也应准其居留贸易。因此民初时期,在本国公使的庇护下,外商违约在京城开设店铺之事时有发生。
1915年3月7日,据京师警察厅厅长吴炳湘报告内务部称,日人拟在单东楼创设一种报纸,名曰北京卫生报,并以顺天时报印字局为印刷所,为此特到警厅备案[16],现向内务部请示该如何办理。内务部认为此与约章有碍,应行查照禁止。又1916年11月,日本侨商在崇文门开设北京实业银行一事,内务部令警察厅查明该银行开设日期等具体情况,并咨询财政部、外交部处置办法。财政部认为北京实业银行开设地点与条约不符,应该令其迁移。警察厅立刻查明了北京实业银行的营业时间、地点、存款办法、利息等情,按照“民国九月十六日以后外国商人不准在北京添设营业成案”[17]的规定,于12月8日饬令该银行将营业牌照撤去。北京实业银行没有严格遵令,而是“于干涉之时即将铜牌摘去,迨巡警去后,仍复悬挂如故。”[17]北京乃非通商口岸,外人在京师仍归中国政府管辖,且民国政府的照会中声明在京营业的华洋商铺,都必须遵守中国政府法律。日本外商之行为,显然违反了条约规定。
此类外商违约在京城居住、设栈的事情还有很多,警察厅是直接处理外商居留、设栈的第一机构,而处理此类事情,往往非常棘手,稍有不当即易酿成国际交涉。外交部咨议吴宗濂和京师警察厅长提出两种不同的处理办法。吴宗濂认为,现在不能禁止外商在京城内外任意开设商铺、建造宅邸、租赁民房的现象,京师虽无租界之名,但确有租界之实。“与其任听外人违约杂居,转成掩耳盗铃之状,何如明降申令,现以京师一方面实行开放,以示大同,俾之受我范围,藉得绳以法律。”[18]吴宗濂建议京师开放,外人以前在京师购地建屋、设店经商、赁居民房等事应与华人同等对待,并向警厅备案注册、纳税领契;此后租赁民房,只可居住,不可做买卖。他认为京师如果不开放,外商可以借口教会租地、或以华人之名继续做买卖,反而不受中国法律管辖。警察厅长吴炳湘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外人在京城居住,管理困难,一旦处理不当,或损国家主权,或生国际交涉。就管辖外人方面,他认为“就曰开放之后,可以要求其遵我警章,但现在领事裁判权尚未收回,警察权实无后盾。”[19]因此他不建议京师开放,而是建议北京如1903年中日约章所订实行开埠,谓“与其先准杂居,毋宁先自开埠。盖杂居仅外人称便,而开埠则可请其照约撤兵也。”[19]
内务部和外交部核议吴、王二人的文书后,对于开放和开埠的意见,均没有同意。就京师开放一事,内务部、外务部一致认为领事裁判权没有收回,北京开放“既属窒碍难行,应即毋庸置议”[18];就京师开埠一事,外交总长孙宝琦认为开埠不能在撤军之前,只有外国军队撤退后,北京方才可以开埠。对于补救办法,京师警察厅拟定了《外国人暂居规则》《外国人租赁房屋规则》和《受理房产卖与外国人规则》三项,对外商在京师居留、设栈进行严格约束,如《外国人租赁房屋规则》第五条中,租赁房屋“只供自己居住,不得开设行栈及其他一切营业之用。”[20]但此三项对于限制外商在京城居留贸易则无济于事。
三、北京“设场”问题评价
清末至民初时期,北京开设通商场一事未能妥善解决,外商在北京非法开设银行、店铺等,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损害。1903年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中规定,各国护馆护路兵一律全行撤退后,北京才能划出地界开做通商场,外国公使团不顾中国政府的屡次抗议,在未履行北京开设通商场的前提条件下,任本国商民在京城开店设栈,是为违反条约。再者,在京城设店的外国商民,往往以领事裁判权为庇护,不遵守我国律法,这是对我国司法主权的严重践踏。中日商约中本来规定,在北京通商场内居住的外国商民,必须遵守该处工部局及巡捕章程,与华人无异。但实际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弱者难以执行条约中对己有利的条款。在交涉过程中,中国政府注重维护国家权益,始终坚持撤军而后才能“设场”,负责交涉的中国官员也时刻维护国家主权,力图减少日本对我国主权的侵害。
中国政府屡次照会外国使团,请在京城居留贸易的洋商,或移至租界,或歇业停办;或禁止洋商开设新店。在国力不敌列强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只能默认洋商在京城居留贸易的定局。各国政府更是明确表示不能承认中国政府禁止洋商居留贸易的照会。首先,外商在京城居住设店已成为“习惯”,中国政府不能禁止该情形,迫于无奈,只能任洋商在京城继续营业。但是,仅仅凭借已成为“习惯”,进而声明不能取缔违约设栈的洋商,个中霸道无理,不析自明。其次,中国政府的照会无禁止现在在京城洋商居住贸易之意。1912年9月12日,民国政府致外国公使团的照会确实表示民国元年九月以前的店铺仍准继续经营,但这实际上是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奈之举。清政府的照会则没有表示择定地界以前准洋商居留贸易之意。“不得再行开设”,用清政府的话说,“本是通融办法,于遵守约章之中乃寓体恤外商之意。”[14]然而清政府的宣言一定程度上为列强找寻到了允许已开店铺继续存在的借口。1903年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已经明确规定开设北京通商场的前提和办法,且中国之宣言,正示不让外人在京城通商之意,本无须再特下禁令,外国公使团以此为借口,认定中国政府已准在京洋商居留贸易。该理由极不充分,且多诡辩。第三,中国政府既然没有禁止现在在京洋商居留贸易,那此后来京的洋商,也不能禁止其居留贸易。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均明确禁止此后来京的洋商在京城居留贸易,清政府也未认现在在京城居留贸易的洋商之行为为合法。依恃强权攫取更多的侵略特权,是西方列强的一贯做法。
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曾明确规定,“京都不在通商之列”,随后,法、美、德、丹、比、意、奥等多国与中国所订条约,均有此等规定[2]。之后,中国与法、美、德、丹、比、意、奥等国也没有签订有关北京开放通商的条约,也就是说,清政府与这些国家所订条约继续有效,北京仍然不在内地通商之列。1903年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仅中国与日本政府所订,只要中国与各国所订“京都不在通商之列”的条约继续有效,各国就无法援引片面最惠国条款在京师开辟通商场。直至1943年南京政府与各国签订新约,列强在华驻兵权得以取消,此时外人在北京居留贸易才算得上是符合条约依据。
四、结语
西方各国倚靠强权、无视条约规定,违约在北京开设的通商场,无论是清末时期还是民国初期,均未能取得合法地位。无疑,北京通商场是一个非法的特殊通商区域,因为“使馆军队和卫队既未撤退,自不产生中国方面在北京设置外人区的义务。”[21]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均未能取缔列强违约在京城开设的通商场,在国力孱弱的近代中国,中国政府无法与西方列强匹敌,加上西方列强无休止的侵略野心,或是明火执仗,用条约索取侵略特权;或是暗度陈仓,强暴地侵占更多条约外的权利。中国的国权在西方的炮火和强权之下一步步沦丧,列强违约在北京开设通商场即是近代中国遭受外国侵略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