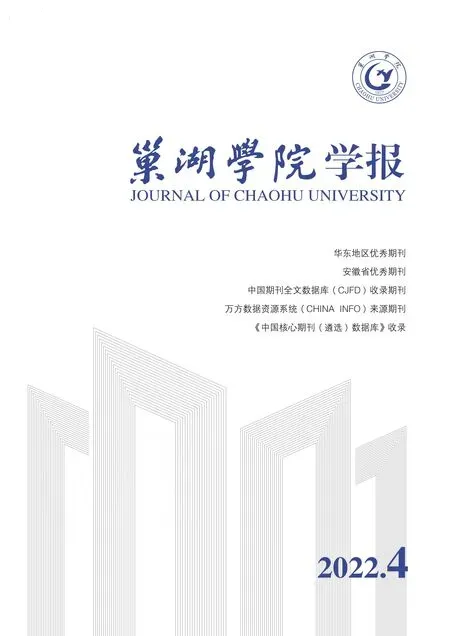从清末民初公园论看近代中国“公共”意识的建立(1870—1920)
胡 蝶
(武汉大学 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引言
自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近代中国大门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进入中国工作、生活,也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以来的生活方式带入近代中国社会。“公园”作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应运而生的产物,同样被在华西方人带入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也成为了构筑近代中国“公共”意识的成分之一。
在以往对近代公园的研究之中,历史学领域的研究者一方面聚焦于各地公园的建造、管理、变化发展沿革等依托于公园本身深入挖掘的角度,如朱钧珍[1]、储兆文[2]均从中国园林整体发展角度进行了研究,戴海斌[3]通过梳理二十世纪以来北京中央公园的历史变迁,论述公园在北京社会生活各方面起到的作用。王敏[4]运用详实的史料,讲述了在公园平等开放问题上,近代华人的抗争过程,揭露了西方人拒绝向华人开放公园是出于维护外侨特权及歧视华人的心理,借上海租界花园管理方对华人的态度探讨近代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殖民主义侵害。熊月之[5]则探究近代上海公园在当时社会起到的社交、集会功能,发现上海租界公园被西方各国作为表达其民族情感、弘扬民族主义的工具,表现了当时社会歧视华人、宣扬西方人至上等独特的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现象。他又以上海张园为例,详细叙述了上海私人建设花园向公众开放时的功能特点,着重论述了进入二十世纪后,张园所特有的政治集会场所的功能,勾勒出西方政治思想传入中国后,革命派以公园这样的公共开放场所为舞台,宣传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反对封建政府的政治活动[6]。上述论文史料翔实,论据充分,展示了近代公园建立以来所承担的多种功能作用,以及当时上海公园之中所发生的多种历史现象,但更多关注公园政治功能背后的社会历史进程,对公园展现的近代社会文化的探索停留于史实层面。
另一方面则转向对公园背后展现出的文化殖民、政府管理、城市发展等文化社会方面的研究。例如胡俊修和姚伟钧[7]以汉口中山公园在管理上遇见的问题为例探讨了近代时期公园管理之中存在的问题。吴昌和孙善根[8]则通过报刊史料探寻了宁波公园面临的管理困境。通过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到,近代时期的公园管理共同面临着民众素质低下损害公园环境以及公园方服务意识低、管理效果差、损害公众利益等弊病。除此之外,李德英[9]详细探寻了成都城市公园在近代社会中发挥的大众教育与社会活动职能。陈蕴茜[10]则聚焦于中国近代公园所独有的弘扬民族主义的建筑功能,追溯中国近代公园之中“民族空间”的建立与被殖民经历的关系。鞠熙[11]从民俗学角度出发,认为北京公园建设过程中蕴含的西方时间、空间、审美、道德观念与中国旧有民俗间的矛盾导致市民生活状态及思想观念与政府在建设公园时的期望不符的状态,揭露了近代北京公园建设历程中,由于进展过快,未能协调好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衔接问题而导致的社会割裂的矛盾。风景园林建设领域的研究者则致力于近代公园的建筑风格美学以及与西方园林的对比研究[12]。
此前相关研究大多着眼于公园本身,对公园这一新生事物所展现出的社会认知变化关注较少。公园作为一个能够为公众提供活动休憩场所的开放公共空间,是国人“公共”意识建立的途径之一。“公共”意识是伴随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体系发展而产生的新思想,与近代中国同样是西风吹拂的产物。通过研究清末民初之际报纸、杂志刊登的时人有关公园的论说,可以一探近代“公共”意识建立的过程。
一、“公园”的起源
现代社会中,“公园”一般是指政府修建并经营的自然观赏区和供公众休息游玩的公共区域。这种近代意义上的公园在中国此前漫长的社会历程之中并不存在,直至清朝末期,封闭已久的中国被西方强行打开大门,“公园”才被西方人带入中国民众的视野之中。
中国古代园林起于殷商,称“囿”“苑”“圃”“园”。这些园林归属于商王,主要的用途是进行捕猎、游乐、训练武技等活动,以满足商王休闲娱乐的需求。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奴隶社会,这种耗费巨大的休闲娱乐场所仅商王具备能力修建。两汉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家园林开始出现,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园林作为统治阶级休闲娱乐生活的最佳场所不断发展变化,直至明清时期,集中国审美意趣之大成的各种古典园林在全国各地建造起来,并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产生了不同的特点[13]。这些构建精巧、审美高雅的园林是只有统治阶级才有财力与能力获得的额外享受,家境贫寒的普通士人或商贩、农民等底层劳动者根本无缘得见,更没有机会进入园中享受休闲娱乐活动。
公园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农业社会之中,大多数人作为农民居住于乡村,自然之美随处可见,活动场所也十分广阔,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生活才是常态,并不需要特意修建花园等人工建造的绿化设施。资本主义兴起后,随之而来的城市化使越来越多的人群聚集于狭小的城镇,工业化造成的大气污染随时威胁着市民的健康,大量增加的工作岗位使父母忙于工作,孩童无人看管,产生了青少年犯罪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西方政府开始在城市中修建公园,建造绿化带。一方面起到净化空气、缓解城市居民健康危机的作用,另一方面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为结束工作的人们提供放松身心的去处,也让青少年有消磨时光的地点[2]。因此,公园的诞生从一开始就有着社会公益的性质。
鸦片战争后,随着大批西方人进入中国居住,公园也作为生活配套措施传入中国社会。据《北华捷报》记载,1850年前,外国人已经在上海修建了一个面积较小的公园,但由于这一公园人员嘈杂、环境简陋,上海外国人委员会决定成立专门的公园委员会负责在上海周边地区寻觅大块土地修建新公园的事宜。由于不熟悉中国官场的一些潜规则,在买地时受到了一些阻碍,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这一计划,而是更换了一个更加熟悉中国世情的副委员长处理此事。此人多方奔走,上下打点了5个衙门后,终于以5000美元的价格购得了用于兴建新公园的土地[14]。这一公园由在华外国人共同出资建造,所面向的自然也是外国人。
与中国古典园林不同,公园是西方工业发展后应运而生的产物,它的出现本就是为了满足广大市民休闲娱乐、放松身心的需求,因此具有显著的“公共”特性,社会大众均可自由出入。公园等为保障公共利益而修建的大型公共设施此前已经广泛进入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公共”的观念在西方已然深入人心,管理者应当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观念十分普遍。然而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初期的中国,“公园”这一舶来品尚未进入普通中国人的视野,国人对于“公园”的认知也需要一个过程,但既然切实的公园已经在洋风吹拂最前沿的上海建立起来,这一新兴事物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也不过是时间问题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海的文人已经频繁踏足公园,并对这一新的游乐之地颇为推崇[15]。随着“公园”逐渐进入国人的社会生活,人们对“公园”这一新事物所带来的新观念的认识也在与公园的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
二、“公家花园”:有限制的公平
公园在中国兴建的初期,国人对于“公”的认知主要来自对“公平”的诉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在华外国人提出在上海建立一座public garden时,国人便称之为“公家花园”,与中国传统私人园林相对应。
据《申报》记载,1872年,在华英国人提出在上海外滩筑堤并建造外滩公园,以便改善环境、游玩休闲,时人便将外滩公园释以“公家花园”四字,并提议向社会募捐筹修建之资,而非向西方借贷,以免花园落成后“将禁华人入内游玩,以示结清严密之关防”[16]。可见中国人此前已经遭遇了不少不公平的待遇。然而公园落成后,华人仍不免受到排斥。1885年,《申报》发表《论华商致工部局请准华人得共游公家花园事》一文,文中显示,上海外滩花园的建造经费由多方共同募集,西方人主持修建,修建资金大半来自华商,日本人稍有贡献,朝鲜人则全无参与。但公园建成后,不仅西方人得以在其中游玩赏乐,于公园建成贡献微小的日本人,乃至毫无贡献的朝鲜人均可来去自如,唯独中国人被拒之门外。作者在文中提出,“西人于造成之后名之曰公家花园,以见其大公无私之意”,认为西方人建造“公家花园”,其用意是宣扬公平公正,以示其毫无为己打算的私心。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无“public”的意识,于是套用更为熟悉的“公平”的含义,认为public garden既然向公众筹款,便应当公平地向所有民众开放,但事实上的“公家花园”却被西方人视为私有物。对于这种行为,作者首先站在西方人的立场,认为禁止素质不一的中国人进入公家花园这等高雅场所情有可原:
华人之居租界者实繁有徒。其中贫富贵贱各有等差,良莠贤愚亦不一品。若一听其入内游观,则富贵者可往,贫贱者安得阻之勿往?贤良者可往,愚昧者安能禁其勿往?倘竟概听其往,则不免有人品混杂之弊,与花草催折之虞。夫是以一律阻止,是其情尚可缘也。[17]
他认为,只有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明事理、有修养的人才有权进入公园;其他家境贫寒、愚昧无知的苟苟小民,不被允许进入环境优美、草木繁盛的花园之中也是理所应当的。作者心中“公家花园”的“公”字,是有条件及限制范围的,其应用范围只在有地位的中国人之中,其意味则更加注重于“公平”之义。但他眼中的“公平”,只分别作用于中国有教养的人与西方人内部,而非如今所说的人人平等。为争取华人入园权利,华商陈咏南、吴虹玉、颜永京等曾联名致函工部局,提出了华人凭证入园、每周向华人开放一两日入园、扩大公园面积、改造跑马场为花园以便各地华人也能进入外滩公园游玩的举措,作者却认为均不可取,更是直指扩大公园面积的建议“因欲使华人得有游目骋怀之地而特加葺治,恐亦必无此事也”,表现出当时社会西方人与华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并习以为常。但当作者论及华人内部关系时,却认为在有权进入花园的华人阶层内部,应当实现人人机会均等,不考虑名气、财富的差别,“若竟择有名大商巨贾,始获领据,则不免有向隅人,即斯举仍不得谓之公”。而作者认为愚钝无知、有碍观瞻的人,却并不在“公”所应当保障的范围之内,这与作者论及处理与西方人关系时所持的谄媚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认为,虽然作为公园的主要出资人,“华商此举理直气壮,无有能非之者”,但中国人在与西方人交涉时应当“先为筹度”,万事先为西方人着想,对于“公平”的要求似乎荡然无存,幻想希望能够通过自我筛选及自我规训,使“合规”华人获得进入公园的权利,而不愿直面西方人禁止华人入内的出发点正是出于对中国人的歧视[17]。
然而这样态度卑微的恳切请求并不能打动公园管理者,中国人仍旧无权进入自己出资建立的公园。1888年,《申报》又一篇公园论的作者赤花散人愤而指出禁止中国人入内的外滩花园分明是“外国花园”,“何为而以公家名也”[18],以“公家”所应当蕴含的“公平”之义反对公园管理方对华人的不平等对待。赤花散人认为,西方人以华人“品类不齐,性情各异,其知自爱者旅进旅退,静穆宜人。其不知自重者,往往酗酒滋事,指桑骂槐。又其甚者,以风雅之场,为角胜之地,斗口斗手,闹闹嘈嘈。一交三伏,汗气逼人,虽非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遇”为由拒绝华人入内论调是“今一言而推我数十万人尽入陷阱而不知”[18]。
从提升国民素质的角度来看,民众劳作整天后进入公园游玩休闲,正可以使他们徜徉于花草山水之中,而“不致胡行于酒楼妓馆,中日沉迷而莫返也”。公园是休闲娱乐、放松抒怀的绝佳地点,对于改善市民的精神面貌、身体素质均有极大帮助。因为部分素质较低的民众行为不当而禁止所有华人进入公园,不仅不公平,而且不利于中国国民素质的提升。不努力提升国人道德水平,只一味禁止举止不合规范的群众入园,使素质较低的民众享受不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一直处于不懂得公共道德的境地之中,国家自然也难以富强,这对于出钱又出力的中国而言是极为不公平的[18]。
可见赤花散人同样认为公园所担负的“公”应当重在公平公正。他在文中问道:“名之曰公家花园而独禁华人弗入,……然西人不公之处正不止此,西人至华,华人未敢阻止。华人至新金山旧金山等处则西人禁之、拒之甚,而至于驱之、杀之,此其事公乎?不公乎?”“名曰公家花园,中国又岂得过而问之?彼因公家捐资而成,而不尽没公家二字?”[18]将华人被禁止进入公园的遭遇与华人在海外的境遇相联系,论证在“公家花园”面前,国人并没有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所谓“公家”的“公”字,只作用于外国人,于中国人来说则名不副实。
从此阶段公园论可以看出,公园在国内建立的初期,国人对于“公园”之“公”的认识,多来源于对现实生活中所遭遇不公之事的反抗。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与英、法、美、俄等列强之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丧失了大部分主权,西方人可以在中国境内自由生活,进行游历、经营、传教等社会活动而不受中国法律的制约。而海外华人却饱受排挤,各地均有排华事件发生,与西方人的地位存在强烈的不对等,即使在中国国内,也存在中国人出资兴建“公家花园”却被禁止入内的不公遭遇,更是当时社会中西地位严重不平等的表现之一,这引起了时人的思考与发声。因而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公园论中,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国人是否拥有平等进入公园的权利的问题,提出有教养的中国人应当与西方人获得平等待遇的要求,但并无作为社会公众的一份子而争取应有公共权益的意识。
三、“公司花园”:少数阶层的公平
即使舆论对于公家花园禁止华人进入一事颇多抗议,由外国人管理的具有公共性质的外滩公园仍旧没有对中国人开放。但此次论战无疑反映出公家花园这样精心设计、环境优美的公共场所颇受文人雅士的欢迎,这令不少商人看到了新的商机。各式各样的由私人经营的具有营业性质的游乐园林出现,张园、徐园、愚园等私家园林的开放是这批以公司性质经营的游园的先声。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无锡富商张叔和将自家花园“张氏味莼园”改造成为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大型游园,李士棻曾在诗中描写过园中场景:
烟波小筑近黄滩,士女来游从异观。
五里恰当萧寺半,一园堪赋硕人宽。
水心山活三神似,屋角花稠万锦攅。
上下蜂房迷户牗,几疑深入大槐安。[19]
园中烟波浩渺,建筑钩心斗角,蔚为壮观,游玩者中颇多名伎骚客,往来应酬之间一片繁华景象。1892年,张园已免费向中外游人开放[20],除了集中西园林景观之大成,还伴有多种游乐设施。1893年,张园试放电光焰火,因所选用焰火效果不佳且燃放时间较短,使斥资观看的游客大为不满,园主于是登报表示将园方所得收入捐给善堂[21]。可见张园虽在后期免除了入园门票,但若要享受园中多样的游乐设施仍需额外支付费用,这笔开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不是可以随意消遣的小钱。
与主动免除门票面向普通游客的张园不同,由富商徐鸿逵创建的徐园则更受文人偏爱。徐园以中式园林景致见长,园中多次举办“赏菊会”“品兰会”等雅宴,时人赞叹其不愧为一处清幽胜境,与“沾俗子,负贩农夫,以及乡媪邮姬,重台贱隶,莫不插足,争先往复。甚至炀者、癞者、盲者、跛者、算命者、卖卦者”[22]来往出入的豫园大不相同。徐园虽然由家庭私有的花园变成了可购票进入的场所,园中却人烟稀少,往来其中的也多是文人雅士,追求“清雅脱俗”的游玩体验。被读书人津津乐道的“赏菊”“品兰”等风雅活动更是需要引荐,由园主发出邀请方能入内参与,众人挥毫泼墨、吟诗作赋以襄盛举,是一种扩大版的文人诗会。虽然对购票的参观者一视同仁,但实际进入徐园游玩的人群只局限在经受过教育、有钱有闲的上层中国人之中,是少数阶层方能享受的公园。
上海虽出现过私园开放的热潮,但私家园林终究有限,且受园主个人影响较大。有商人看到了市民对于大型花园的热情,开始兴办“公司花园”。1889年,由粤商共同出资建造的杨树浦大花园建成开放,园中装置完备,配套完整,购票便可入园游览。这种由商人出资建造,以营利为目的向所有人开放的园林可被概括为“公司花园”。园中不仅有花卉植物等自然风光,还引入了商业店铺等休闲娱乐场所,集戏院、马戏团、动物园等娱乐项目为一体,且不论身份国籍,只需花费一角钱购票便可入内游览,一时间游人如织,颇受民众欢迎[23]。
此类由商业公司开办的具有商业性质的公园只要有能力购买门票就能进入,因此有关上海杨树浦大花园的记载多以记录其中风景设施为内容的游玩见闻为主,而少有对此前类似公家花园运营中存在不公的不满。但由于进入需要门票,且所处位置较为偏远,虽然园方设置了接驳车船以便游客前往,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见识过花园之中的新鲜事物后,公司花园的吸引力便骤然下降,不会重复前往游览。杨树浦大花园经营不久客流量便不断下降,至于濒临破产的地步。1892年1月,即有包工头登报控诉建造者卓子和父子欠下一万三千两工程款未结清,并擅自抵押公园地产房屋[24],仅十余日后,大花园便由英国商人接手,改名半淞园,取消门票,并扩展出向外出租宴会场所、戏台、拍摄场地等业务[25]。短短几年时间,这座由中国人主持兴建的商业乐园便半途夭折。可见此时中国国内并无支撑民众寻求额外享受的物质条件,位置偏远、门票昂贵的公司花园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并不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生活场所。
1917年,上海著名游乐场地大世界兴工建造,“游场系由黄楚九君发起创办,据闻所集资本以某大帅之三十万为最大股东……场内多特别花园一处,将来竣工必大有可观”[26],是一座典型的公司制游乐花园。园中园景、水池、高台、商场、餐厅、动物园等设施应有尽有:
其中往来游客,男女衣着悉如富人。黄发垂髫,咸相顾色喜。见有人,乃大悦,问所从来,具答之。偕入餐室,呼酒点肴共食。室中更多熟人,便各问讯,并述南北战祸迷漫,使同胞国人,陷于苦境,不聊生焉,并为外人侵凌。问现已和未,乃不意仍战,无怪增兵。游客一一为具言所闻,皆痛恨。[27]
大世界中的游客虽无性别、年龄限制,但皆衣着富贵、关注时政,且彼此熟悉,进入其中的众人均能平等交往,分享资讯,共同娱乐,俨然已有西方中产阶级俱乐部的模样。不仅能够娱乐休闲,还能交换资讯、互通有无、结交朋友,比以往单纯观赏景观、游玩放松的公园更具备公共交往的特性。
这一类型的公园虽然能够做到不分身份对象地面向所有人开放,但其所有权归属于企业,而非政府部门等非盈利机构,其作用是供人娱乐,以盈利为目的,商业性远大于公共性,与其称之为“公园”,倒不如说是“游乐园”更为恰当。公司花园作为商业项目,自然不会将顾客拒之门外,而门票这一道关卡使得能够进入公园的人群只能是居住于城市且有一定收入的市民。对于尚处于农业国状态的中国社会来说,能够支付这笔费用的人群上至官员地主,下至工厂工人,绝对数量并不大。
“公司花园”虽然也是“公园”,其实质仍旧只是少数人消遣娱乐的场所,虽然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但只适用于少数群体,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农民以及底层城市居民仍旧无缘享受“公园”这一公共设施。这一独特的公园类型所指的“公”指向的是共同出资建立商业机构的集体,对于公司来说,其“公共”性质仅适用于该公司的成员,公司作为由数位出资人共同出资建立的营利组织由出资者共同所有,表现的是所有权在特定集体之中的共有,“公平”也仅适用于民众之中有能力支付门票的少数派,而非所有人。
四、“公众花园”:面向公众的场所
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将目光聚焦于公园正式向公众开放后的历史,认为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公园才不再是华人的禁地。但通过对当时报刊杂志中公园论的研读,可以发现,二十世纪初,许多知识分子已经要求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公园,公园被视为理应面向公众开放的场所。在此之前,国人对于公园的看法更注重于外国人对华人的不公平对待,进入二十世纪后,则开始注意到“公园”这一构造所具有的公共特性。
(一)提倡兴建公众花园的潮流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进一步向西方列强开放,全国各地外国商人开始提请建造“公众花园”[28]。清朝末年,清廷派出考察团对西方各国社会进行实地体验考察后,发现城市中均大量建有公园等公共设施,于是将公园等公共场所的建设视为西方列国强盛的原因之一。受此启发,各省督抚纷纷开始重视创办公园,并寄希望于公园的建设能够“开各人智识”[29]。社会舆论也将公园视为强盛国家必不可少的公共场所,1905年《大公报》上便有人发表议论,认为应当顺应世界潮流,在首都北京兴造公园。
各国京城地方皆有公园,且不第有一处之公园。今中国之北京,市肆之盛、民居之稠,与泰西各国等,而街衢之不洁、人畜之污秽,则尤非各国京城可以举。似于此而不设公园,其何以造福于臣民而媲美于各国哉?[30]
作者认为西方各国兴造公园是出于改善城市卫生、培养民众公德心的目的,而作为清廷首都的北京则十分脏乱,这显然不是一个大国所应有的风范。中国只有跟上此时世界兴建公园的浪潮,才能够追上西方国家前进的步伐。至于公园建造、管理的花费,则一改上世纪向民间筹款的风气,转而要求清政府出资建造。
造之经费不过二万金,长年需人照料之经费不过二千金。中国公家之帑项虽极支绌,然年来建一离宫,修一衙署,动辄靡费数十万以至数百万金,宁独于区区公园之经费而靳之哉?如谓此项经费当出于民间而不动用公款,则城内各处极大之道场佛寺,用以供奉木偶而无益于地方者,民间皆能合力以建设之,更不宜于此公益公利之公园而视为缓也。[30]
作者已经认识到公园的公益属性,要求将公园的建造管理花费纳入政府公共开支之中。文中指出,建造民众活动的公共场所是政府应当承担的管理职责,因而应当由政府出资修建管理,而非由民众自筹。并以西方各国在各殖民地建设公园的行为作为对照,显示建造公园对于当地文明发展的重要性。
要之公园之于社会,实有莫大之利益,泰西各国获一殖民之属地,除整理街道,推广市廛以外,必先构造公园。奈何中国以北京为首善之者已六七百年,而于此项工程羞无人议及耶。[30]
将兴建各种西方传来新鲜事物的举措与国家近代化程度相联系是近代舆论界的普遍论调。有人甚至将各行各业的兴盛均托于公园,称“农业有这公园,农业就不难发达;工业有这公园,工业就不难振兴;商业有这公园,商业就不难茂盛”[31]。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公园作为一个不属于事关“军国大事”的重要机构,而仅仅作为一个供民众平等游玩休闲的公共空间,被列入振奋国家的要地之中,无疑是近代国人持个人主体性与独立性参与到社会之中的公共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
(二)公园中的公共生活
局限于公园尚未普及的社会现状,国人在公园之中的经历较为贫乏,因而起初关于公园的认识一向着眼于观察体会园中花草、景色、建筑构造等较为具像化的方面,而缺少公园是一个由民众共同享有的社会交往空间的认知。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国人与西方各国的交流进一步加强,对公园的认识方得到进一步深化。1903年,《启蒙画报》刊载的《叙公园》一文提及了公园作为公共空间的特别之处。
无事到公园歇歇,可以听许多人说话,便能长各样的知识,如同读了各种书一班。也有一家团聚闲谈的,也有闲步歌唱的,也有领着小孩,坐在椅子上教书的,也有坐着小马车,穿林游逛的。个人自乐其乐,天机活泼,没有一份拘束。……法国巴黎的公园,比别处的更好。闲暇无事,到这公园里走一回,看见许多的字,如同进了图书馆。看见妇女们做活计,如同入了裁缝所。听见各人的谈论,又好像读了新闻纸……每逢到了礼拜放工的日子,陆军海军乐队都要到公园里游玩,一面奏着音乐、唱着军歌,无论上下贵贱人等,都可以随着唱和……就是我们别国人,随着他们进去逛逛,果然懂得他们的话,亦肯详详细细的讲给听。[32]
公园作为公共空间是开放的,不论年龄、性别、职业,都可以自由进入,不管是在公园之中进行休闲娱乐、教育运动活动还是在此地工作、聊天,都是人们的自由。在公园,众人得到的不仅是自身休闲娱乐方面的满足,也能够在公共空间中与他人产生交互,不论身份的高低贵贱、种族资产,都能自由地交换信息,满足自身与社会各界沟通交往的需要。这在近代中国社会中也能够起到消除阶级意识、开阔市民眼界的作用。
1909年,陈兰薰在《时报》上发表《创办南洋公园说》一文,指出公园的公共特性于国人认知的作用:
高斋雅士,市肆华商,以及征夫行人,村童里妪,得以岁时游览,呼吸新气。快心目而导郁滞,养天和以纾神虑。佛氏所谓一大悲木,绕益众生,使之离恶道而入天堂者,殆于是见之耶。虽然公园之利,要非徒供人游览而已也。道德者人之要素也,而法律者则驱人而入于道德。中国人不自治,游踪所致,放僻邪侈,恣所欲为。遇有美观,必毁而后己。其乖戾道德实甚。公园之中,严定规则。……保全公益,渐摩益熟,则人人皆知以法律自治。[33]
公园不仅打破平日里的阶级隔阂,使得不同阶级地位的人进入同一公共场所,还通过推行公园的管理条例使得国人逐渐适应有例可循的公共生活,明了社会生活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界限,使“公共”意识进入国人的社会意识层面。这是近代封建阶级观念逐渐被外来力量打破,应掌握新的经济资本的阶级崛起、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出现的需要而产生的公共交往空间所带来的独特作用。由此产生的公园、公共图书馆、学校等带有大众性、平等性的空间建造,在无形中让国人意识到了公共空间蕴含的近代政府职能、阶级关系等方面发生的改变。曾经,以官员为首的上层阶级可以理所当然地占据公共设施以供私用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公共设施因其共有性而不应被任何人随意占用,理当由大众共同使用的观念盛行。因此,当甯垣公园的洋房被某协统占据举办私人宴会,禁止园中游人进入后,便被披露于舆论,从而有了“所谓公园者,其性质固如是乎?”[34]的质问。
进入民国时代,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进一步学习西方社会管理制度,更加重视社会教育、环境卫生等公共领域,把提升国民的文化水平、建立公德观念等工作视为政府的职责,并将建立公园以及博物馆、美术馆、运动场、图书馆等“种种社会教育之设施”的公共场所视为改善国民“每逢休息时间,三五成群,酣嬉赌博,狭邪冶游”的陋习,以达到“改良习俗,增进智识教育”的社会教化目的的重要途径[35]。
公园的建设在一定意义上也确实达成了这一期待。1917年,《湖南警察杂志》刊载的《论公园与市民之关系》的作者发现,中央公园开放之后,一年四季,不仅“春秋佳日,士女如云”,即便“日暮天寒”,园中仍旧游人“往来如织”。公园如此受到市民的喜爱,可见此处“必有于心理上受无穷之感化,于身理上受无形之利益,而不自知者。”[36]作者将这一现象视为公园向民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公众生活的佐证。公园这一能够供人游目骋怀的公共场所的出现,使国人不再沉迷于小群体之间短时间内能够给予人强烈刺激的赌博、狎妓等无意义的活动,也不再因无处可去、无事可做而终日无所事事、沉沦颓丧,而是通过欣赏自然美景、与他人沟通交流发现了公共生活的美妙,也意识到身处的社会之广大,自己便是社会公众的一份子,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
二十世纪初,有关公园的论述中出现了从十九世纪末时针对已有公园的现状发表议论到主动对公园的建设展开丰富设想的转变,这也意味着公园被纳入作者的私人视野之中,成为时人眼中社会公众理当享有主动建设权、建议权、监督权的公共设施。随着君主专制统治的清王朝在不断地冲击下彻底灭亡,此前被压制于君权之下的民权浮上水面,新的思想解放浪潮提出政府应当成为为广大民众服务的社会管理机构的要求,社会公众成为此时段内毋庸置疑的主体,“公益”“公利”成为热点话题,而公园则是政府得以助力“公益”的最佳载体之一。要求政府兴修公园的声音与将民众视为公园主人的观念无疑昭示着“公共”意识在民众之间的广泛建立,公园中丰富多彩的社会公共生活也将这一意识落实到了具体的市民生活之中。
五、“公园”与“公共”
“公”的概念古已有之,起初指朝廷、国家,与统治者的统治息息相关,公园初次在中国出现时,国人称之为“公家花园”,即取此意。陈弱水在《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曾对中国历史上“公”的含义进行梳理,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即社会治理之中政府的统治,与“私”的概念相对。第二类指普遍、全体,即人类共同福祉、全体平等的心态。第三类指由程朱理学阐发的天地间的至理等理学概念。至近代则与“共”并用,指在政治、宗族、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集体事务与行动[37]。在此之前,“公”字多指政府事务而少有涉及公共领域,由此衍生的公共生活、公共事务、公共道德等概念同样不显于近代中国。公园作为公众共有的休闲娱乐场所,是“公共”意识的重要体现,公园在中国的建设过程以及时人撰写的公园论中论述主题的变化过程投射出了“公共”意识在近代中国的建立历程。
中国本没有公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专制统治者是国家的主人,自然的享有一切权利而无需对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履行义务,国人也并无官府应当提供公共生活场所的意识。长期以来,中国的园林建筑均由私人所有,明清时期江南地主的私家花园更是千年来中式古典建筑艺术登峰造极的产物,而能够供全体国人共同使用的休闲娱乐场所则未见踪影。这种情况直到西方人进入中国殖民居住,开始在中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公园方才改变。
公园初次在中国出现时,国人仅仅将其视为西方人兴建的新事物之一。由于历史上缺乏此类建筑,国人对于公园所代表的由社会公众所共同享有的公共空间并无概念,只是以修建时的出资额为依据,要求得到进入其中的权利,所寻求的并非“公共”而是“公平”。十九世纪晚期,“公共”意识尚未建立,公园论中相关论断对public的理解是基于当时所感受到的中外之间强烈不对等状况,认为既然名为“公家”则管理者理应大公无私,对想要入园者平等相待,不能因洋华之别而区别对待。公司花园的兴建使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市民有了进入大型游乐项目中游玩的机会,但这种基于商业目的而兴修的公园只是小部分人能够享受的游乐场所,此类“公园”与其他商业建筑并无区别。部分公司花园的修建虽无“公共”概念作用,但其向所有具备经济能力的民众开放的特点使得其中聚集了一大批能够相互交往、分享资讯的人群,具备了社会公共交往场所的雏形。二十世纪,更多华人得以进入西方国家学习生活,在西方公园中切实地参与公共社会交往生活,使作为“公众花园”存在的公园进入国内舆论界的视野,并在国内要求实行政治民主的呼声下,要求政府承担起为社会公众修建公共设施的责任。这一要求政府从广大民众的统治者转变为社会管理者的观念变化,正是“公共”意识建立的体现。
公园是西方近代政府为居住于拥挤的城市而无法拥有私人花园的市民、工人提供的休闲娱乐场所。为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圈地运动等强制城市化的历史事件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被迫进入城市。他们居住于狭窄的房屋内,生活单调枯燥,缺乏休闲娱乐场所。随着工厂的大量兴建,逐渐加重的大气污染以及大量缺少父母看顾的少年儿童造成的社会问题使政府开始在城市中兴修公园。公园由政府出资建造,平等的开放给所有居民。公园的出现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环境,减少了大气污染,保障了城市居民的健康;另一方面则使父母均全天工作而四处游荡的少年儿童获得了休闲娱乐的场所,其日常活动由偷窃、抢劫转变为运动、健身,城市面貌大为改善。公园的修建不仅满足了城市居民放松身心、改善环境的需求,也达到了改善城市治安的目的。可以说,公园的出现是近代西方政府履行管理与服务职能的典型产物。而这一行为也正是西方近代政府进行统治的基石,其社会建设多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而来,由政府建设的图书馆、博物馆、医院、学校等西方近代公共设施皆基于政府的管理与服务职能而得以建立。
这种为社会公益服务的性质正是近代民主政府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逐渐觉醒的社会公共意识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相辅相成,时人开始意识到政府不应是全然的支配者,而应是有义务为市容市貌、国民素质、社会风尚等相关社会发展问题负责的机构。公园的建设正与中国国内高涨的要求废除封建统治、建立民众政府的声音相互呼应。作为有利公益的公共场所,公园理应由政府出资兴建。在近代中国,公园的修建使越来越多的国人有机会走出胡同、弄堂等日常生活的固定区域,进入更加广阔开放的社会空间,不分阶级、财产的与社会各色人等产生交互,也使进入公园的人们更加认识到世界的广阔与真实,真正认识到“社会公众”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人际交往规则得以将虚无缥缈的社会公德落实到了市民日常生活中所应当遵循的共同守则,公共道德的意识便在这一过程中建立。
至此,中国近代“公共”意识建立的过程也得以显现。起初国人对于“公共”之意不甚明了,只是基于海内外华人所遭受的不公对待以及上海华商付出了参与建造公园的资金的立场,要求获得与外国人平等的入园权利。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的商业行为而出现了独特的“公司花园”,此间的“公”指由多人共同出资、共同所有,而非公众公有,但少数人在公司花园之中的社会交往活动已经具有近代社会民众公共生活的雏形。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促使更多人认识到公园应当是政府负责承建的公共福利设施,社会公众有权对公园等社会公共设施发表建议观点,将公园建设纳入到社会公众的权利领域之中。而且,逐渐在各地建立的公园中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也使得民众建立了对公共空间、公共道德的认知,使“公共”意识进入大众认知之中。
六、结语
报纸杂志等出版物中记载的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期时人对于公园的议论,是中国国内近代“公共”意识建立过程的一个侧影。由这一过程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新事物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一系列与之相呼应的新概念、新意识、新文化,而这一事物在中国传播、普及的过程,就是其后的思想文化逐渐被学习、理解、接纳,最终得以适应中国发展的过程。新事物与新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近代公园建设的过程同样如此。从十九世纪局限于西方殖民聚居地区,至二十世纪在全国全面铺开,公园在近代中国的建设历经了半个多世纪。它的发展历程之所以如此漫长,是因为公园作为大众公有的休闲娱乐场所,其建造需要拥有雄厚财力且无意攫取高额回报的近代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清廷自然无法做到。因此,在近代民主政治与先进思想作用下诞生的公园只有在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动摇,大众民主思想传入的基础上才能大量出现。而近代民众针对公园产生的议论,也同样是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从十九世纪晚期在公园论中表达中国人面临的中外之间不对等关系的抗议,至二十世纪主动要求政府建设公园,并对公园进行设想、监督的历程无疑展现出了“公共”意识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建立的过程。
公园论的变化发展佐证了近代“公共”意识是如何进入中国,并在日常生活之中逐渐被民众吸纳接受,成为普遍概念的历程。研究这些新事物及其背后承载的意识变迁,是我们探索中国近代化历程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