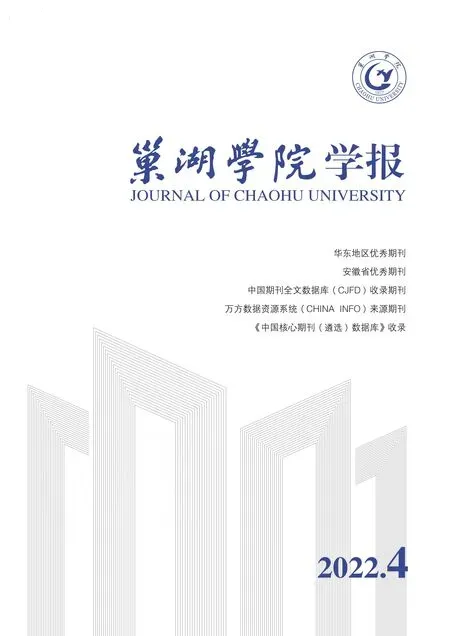造反与革命:双重视角下的清末云南会党
谢 军 罗安伟
(1.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500;2.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引言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清廷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甲午一创,庚子再仆”[1],随着民族、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非推翻满清无以救中国;孙中山组织、领导了一系列反清革命运动,但都以失败告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云南省作为西南地区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给了濒临倒台的清王朝沉重一击。云南辛亥革命的胜利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既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努力的结果,同时又受到秘密会党的推动和影响。
会党史研究是近现代史研究的热点议题,有关云南省的会党研究,不乏深刻之作,但有关云南会党的研究多集中于辛亥革命时期。欧阳恩良[2-3]探讨了同盟会与西南袍哥的联络与合作,在肯定了袍哥组织推动西南三省辛亥革命走向成功的同时,也从袍哥固有的缺陷出发,对其进行了批判,并对“如何正确评价辛亥光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关系的转变”这一论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涉及到云南袍哥(哥老会)活动的论著,内容集中于辛亥革命时期且着墨有限。文章即针对云南省会党的起源、晚清时期的发展,以及云南会党在清末起义与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进行探究,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会党在云南社会的早期传播与壮大
会党是以游民游勇为主体,以异姓结拜为形式,具有一定政治经济目的的封建秘密结社组织,“据文献记载,清末秘密结社的名目有200多种,会党名目约占半数以上。”[4]其在近代中国社会有很大势力。
(一)云南会党的起源与早期传播
会党自产生以来,虽然名目不同、形式各异,但其特征可归纳为四点:“一、组织的非公开性。二、具有秘密的宗旨(包括口号和誓词)、奇异的入会仪式(包括宗教仪式)和互相联络的隐语暗号等。三、进行“非法”的活动。四、在一定条件下,对统治者和政府当局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抗。”[5]云南的秘密会党活动较早,其来源则鲜有提及,从相关史实来看,云南的会党发轫于邻,最早出现于嘉庆年间,清朝中后期流行于云南的会党,主要是哥老会和天地会。
哥老会兴起于道咸年间,由四川的啯噜会演变而来。哥老会传入云南的准确时间尚未可知,光绪元年(1875),云南巡抚岑毓英在奉旨查办帮会的奏折中说:“查滇省地处极边,民情犷悍,当此大乱初定,穷黎生计维艰,遇有奸宄妄造妖言,往往听其煽惑”,时值回民起义平定不久,云南百废待兴,岑毓英在折中对云南人民易于听从“奸宄”“妖言”的煽惑感到担忧,但却认为当时“并无安清道友、哥老会名目。”[6]实际上,哥老会在咸丰年间已经活动于云南,只是岑毓英未曾查觉。普洱思茅的哥老会是“四川客籍居民所建立的民间组织。”[7]到咸丰年间,哥老会蔓延整个普洱地区,大肆活动,甚至出现联合反清起义。当时,吴端、孙太平等人,联合破产农民、行商、游民、散兵游勇,结盟拜会、密谋反清,咸丰七年(1857),孙太平、吴端率哥老会众千余人乘势起义,但起义军被清军击败,吴端被捕杀,此后孙太平又率众千余人攻打普洱城,但再次遭受失败。光绪九年(1883),省城昆明发现哥老会结盟拜会、势力滋蔓,还进行聚赌盗窃活动。
天地会产生于康乾年间的福建,到嘉庆年间,迅速向外扩散。“天地会由福建向外传播扩散的路线,大体有四条:第一条是由福建传入广东,再由广东传入广西、贵州、云南”[5],这一判断是符合史实的,云南的天地会来源于两广地区,尤以广西会党早期在境内活动较多。道光十一年(1831)九月,云贵总督阮元奏称:“遵查云南尚无‘三合会’匪。”①见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印《昆明市志长编》(卷六),392页。其实,“三合会”“三点会”“添弟会”等名称,都是“天地会”在传播过程中为避免清廷查拿的变称,并无实质不同,而天地会传入云南,至晚是在嘉庆十六年(1811)。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广西西隆人罗道士在云南项董寨卖药,投宿在民人吴文锦店内,告知来会的田万和“添弟会人多势众,伊亦系会内之人,只须出钱结会,到处有人扶助”[8],又有广西客民周大赍与黄奉朝联络十余人在广南结拜添弟会。嘉庆十七年(1812),广西人钟某等人潜入云南师宗县,诱惑寨民歃血订盟,广西西林人岑肇基、周上潮至云南宝宁县苟占林家内约人结会,“告以添弟会人多势众,遇事有人帮扶”,广西人林闰才、张效元等也在云南师宗县、宝宁县地方,“诱惑该处民人,兴立添弟会。”[8]
这一时期的资料显示,天地会传入云南的时间较早,且受广西天地会众宣传、传播的影响较大,其设会原因并非“反清复明”这一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作祟,而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的互帮互助考虑。到了道光十二年(1832),广南府宝宁县又出现平四等人聚众结拜添弟会之事,道光二十八年(1848),赵州弥渡会党“焚杀掳掠,且敢围署伤官”[9],经林则徐调兵剿捕共数百名。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云南境内不仅昆明地区会党蔓延,曲靖府属南宁、平彝、罗平等州县,以及大理、昭通、东川、宁州等地,亦会党众多。
(二)清末云南省会党势力壮大的原因分析
云南作为异于粤、闽的内陆省份,到清朝末期会党发展迅速,以腾冲的洪帮为例,光绪二十七年(1901),杜云山到腾冲创办“敬慎公”堂后,“几年间发展洪帮成员9000多人”[10],而云南境内会党的信从之多,竟“几如水之赴壑”[11],尤可见其势力之大。清末云南会党势力的急剧发展,主要源于下列因素。
1.自然地理方面
内部而言,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疆,高原地势海拔较高,又多山地丘陵,“论形势,有登高而呼之概焉。夫左绕金沙,右界澜潞,重光复岭,鸟道羊肠”[12],受制于地理地貌,近代云南经济落后,社会较为闭塞,遇到天灾人祸,民众往往难以继续生活,“当饥馑连年之后,正贫窘无聊之时”[11],为了图生存,就易于投身会党、聚众起义。
外部来看,云南的东川、昭通二府,界连川、黔;广西州、广南府境连粤西,尤广南三面与广西毗连。会党经邻省传入滇省,清末时期川、粤等省会党势力强大,常常入滇骚扰与结会,尤其在滇粤交界地区的会党游民,“其扰滇劲匪不下百数十起”[11],广西西隆州的天地会首领唐十二、陈有才等,就曾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联合李三花由八达分州渡清水河进入云南的广南境内,并进攻至丘北县;蛮河一带,更是聚集多股会党,其中广西会党领袖曾秀兰,先是在越南“设赌敛财,纠合党类”,后来到河口地区活动时,大肆扩张势力,导致“由河口至蛮耗沿河两岸,以及猛喇、王布田等寨,汉夷绅庶,率为诱胁,拜台结盟,纷纷入会。”[11]
2.社会经济方面
历史上,云南财政一般收不敷支,依赖中央补助和邻省指拨协饷。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主、官绅兼并土地加剧,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锐,大量农民破产,沦为流民,而会党以“只需出钱结会,到处有人扶助”[8]相号召,“又其团体异常团结,会章以手足相顾,患难相扶为要旨。凡属同志皆称手足,遇路人有相斗者,每遇暗号,莫不争先协助,惟恐不力”[13],出于互助需要,大量流民被引入会党。
3.军事斗争方面
会党本以游民、散勇为主体,同光年间,清政府为了镇压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和工人起义,也曾在云南大肆办团练、扩军队。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许多散兵游勇“往往暗中煽惑莠民开立山堂,结盟散片”[14],而随着地方军伍的遣撤,大量被裁士兵苦于生计,参加秘密会党。河口地区原来人烟较少,“自中法和议定后,裁撤营练、散勇之耐瘴者,僦居其间,久之遂成村聚,五方杂处,良莠不齐,奸民最易混迹。”[11]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已形成大股会党势力;周云祥领导的矿工起义被镇压后,许多被裁兵勇和失败工人亦因无家可归、无业可就而投入会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兴中会以及同盟会成立以后,曾联络会党在广西、广东等地多次发动起义,随着起义的失败,一些会众逃入滇境,这些残余会党力量为了恢复势力,大肆吸纳滇境流民、工人结义入会。
4.政府官员方面
在专制体制下,一些云南地方政府官员害怕会党闹事影响自己的官运,在会党尚未起事或者上级未知时,对会党活动往往不追究、不报告,甚至粉饰掩盖,这在客观上助长了结会活动。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思茅、威远一带的会党首领倪小斋、杨东湘等聚众起事时,思茅厅同知李同寿就畏于声势“不敢遽发”,署宁洱知县翟乐善在接到绅民呈送的函件后,“并不禀明道、府,认真访缉”,署威远厅同知杨巨臣“屡奉道札,因循不复”,导致“匪氛愈炽,匪胆愈张”[11];宣统二年(1910),大姚县会党首领陈可培与邓良臣等到观音寺结盟聚会,署知县郑兆年“派人诘散,并未根究查拿。”[11]在这种官员畏事的官场风气下,有利于地方会党势力的发展。
5.国际形势方面
与一些内陆或沿海省份不同,云南背靠英、法殖民地缅甸、越南,直接面临英法入侵威胁,“英伺其西,法瞰其南,巧取豪夺,互相生心”[15],国内矛盾、中外矛盾交织,动荡的局势有利于匪盗、会党滋生。一些会党分子还抓住边境地区政府管控无力的情况,游荡于边境两侧,发展力量,前述会首曾秀兰在中越边境的活动,即是一例。
孙中山曾指出:“云南有两个导致革命的因素,一是官吏贪污,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都把云南当作侵略的目标。云南人民在反动官僚的压榨和外侮欺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16]近代云南社会动荡不安,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云南各族人民历来对满清民族压迫政策极度不满;作为地处西南的边境地区,云南境连缅、越,又直接面临英法外患威胁。这些都为云南会党的壮大与活动提供了温床,于是会党到处“纠伙结合,歃血放片。”[5]
二、清末云南的会党活动
中国近代会党的发展与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密切相关。清末,云南地区民变不断,会党数次起事抗官,还参与到资产阶级革命之中,这些会党活动在云南近代化过程中,扮演了不同角色。
(一)抗官视野下的造反者
从起事的动因来看,清末云南的会党起义中,有许多可归为游民游勇式的造反活动,起义会众迫于生计,以反抗政府的形式谋求生存,虽然存在反封建压迫的色彩,但并没有清晰的斗争目标和纲领,当起义面临清军的镇压时,往往迅速失败。
光绪二十八年(1902),“天地会首领李二老板联合17股会党武装将近万人,突袭了云南边境城市剥隘。”[14]光绪二十九年(1903),个旧地区周云祥领导了矿工大起义,而在河口地区爆发了曾秀兰领导的会党起义。河口地区邻近越南,“烟瘴极重,居民无多”,中法战争结束后,许多被裁练勇在此地落脚扎根,并渐渐形成村落。会党首领曾秀兰曾在越南以非法手段聚敛财产,吸收民众加入会党,到河口地区活动后,利用该地“山菁丛杂,防布难周”的形势,在活动时“声息灵通,踪迹飘忽”[11],因此该地会党日形猖獗。曾秀兰的会党集团,其成员主要为散兵、游民以及被胁迫入会的平民,文化程度低,尚无民主革命思想,除了与清军作战,亦从事“抢掳烧杀”“勒索银米”“劫夺商船”等犯罪行为。后来,在清军捕剿下,曾秀兰集团遭受大败,余党或投河自尽,或易装潜逃。光绪三十一年(1905),路南州会党首领姜子云“纠党数百,将于铁路起事。”[11]光绪三十三年(1907),思茅、威远地区的三点会首领倪小斋、杨东湘、周朝纲等,纠集团伙,“潜立忠义堂名号,储器械,备糗粮,分头煽惑,图谋不轨,一月之间,拜会至六次,惑众逾千人,蔓延数厅县及各土司地面,约期起事。”[11]但在清廷的调兵镇压和卧底侦查之下,此次会党起义亦走向失败。到了宣统二年(1910),还有大姚县人陈可培与川人邓良臣结会聚党,在清兵、县衙的串通、配合下,进入县城“攻警局,劫监卡,抢衙署、典当,并伤帮审委员”[11],起义军还仿效旧式农民起义,奉陈可培为元帅、邓良臣为副元帅,多路出击。后来,在团练和清军的联合进攻下,起义失败,首领陈可培、邓良臣被捕杀。此次起义尽管发生于辛亥革命前一年,但与上述几次起义一样,仍圉于以杀官安民为号召,反抗官府统治,无法走向更高层次。
从社会影响层面来看,上述会党起义打击了清廷对云南的统治,作为低水平的游民抗官起义,虽带有一定的反封建压迫色彩,但都毫无意外地走向失败。这些起义的最终失败受多方面的影响,有三个原因非常关键:一是会党成员受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又未与革命党联系,起义没有先进的民主革命纲领作指导;二是会党成员多为破产农民、无赖和游民,财物匮乏,军械落后,无法解决缺粮少械的问题;三是会党成员没有广泛联络其他阶层、团体共同反清,孤军与远较自身强大的清政府作战。而云南辛亥革命的最终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革命党人解决了以上问题。
(二)民主共和观念下的革命者
“昔时哥老会皆排外。自近时革命党人入其中,教化而指导之,遂自称为革命军。”[17]除会党自发的起义和造反活动外,清末的革命党人也在两广、江西等地联络、指导会党起事;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部分起义军逃匿于滇越边境,积蓄革命力量,以图在滇起事。革命党人选择云南发动革命起义是有多方面考量的,一则由于云南与缅甸、越南交界,清政府统治相对薄弱;二则滇境内有通达越南河内的滇越铁路,方便革命党人从境外筹集物资支援革命;三则如果在滇越边境起义,进可攻退亦可守,如云贵总督锡良所说“出界一步,匪可逍遥,我难过问。匪之来,防不胜防;匪之过,剿无可剿”[18];四则此时云南会党势力很大,“哥老会盛行,在城市乡村里都公开组织活动。”[19]这一时期,云南会党在革命党人的联络和指导下,由自发的造反活动转而参与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会党之间在起事过程中也进行了有益的联合。
1.河口起义与永昌起义
广西的起义活动失败后,同盟会联合会党准备在云南发动起义,“规划攻取河口,以窥昆明。”[20]河口是红河扼要之地,与越南隔河相望,对面即为越南老街,“为铁路工人及游勇出没之区”[13],会党众多,可攻可退,而且还可以利用滇越铁路运输军械粮食。1908年,孙中山指示参加过镇南关起义的同盟会员、哥老会领袖黄明堂等人在河口发动会党起义,参与其事的还有黄兴、胡汉民等革命党人。三月二十九日,由会党组成的起义军队在清军防营的配合下,发动起义占据了河口城和新街等地;次月,在清军守备熊通及管带黄元贞的内应下,起义军击杀河口副督办王玉藩,占领了河口地区,并成立“云南省都督府”,哥老会领袖黄明堂任“中华国民军南都督”、关仁甫任云贵都督。此次起义中会党一改往日分散的山头主义而有了联合,在起义初步得手欲进攻蒙自地区的时候,周云祥起义后的残余游匪欲相助,“是为偏师”[18]。关仁甫在进军路上,也得到红河沿岸会党帮助。可惜河口起义虽然发动顺利,但形势恶化迅速。云南省都督府成立后,黄兴催促军队沿铁路而上进攻昆明,但会首黄明堂犹豫于粮食接济,在行军路上会党军又借口疲惫,不愿向前,后多数士兵竟相散而去,而王和顺一部也因军械不济延误了军机。一般会党群体的目光短浅、组织涣散,可见一斑。无奈之下的黄兴想率军进取蒙自,军队却不听号令,“乃知本身非有基本军队不能指挥他军。”[13]
清政府得知河口起义后,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应对,一是在云南境内调遣军队围剿起义力量;二是求助他省,还令广西提督龙济光率军赴滇协助;三是开展对法外交,包括管控滇越铁路、限制革命党人在越南活动、缉捕越南境内革命党会党成员等。而起义军则随着声势日益扩大,资金、粮食日渐匮乏不支。在清军的合击之下,起义军进攻蛮耗、思茅等地铩羽而归,退回到河口都无法安定,革命党领袖黄兴也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陷入困局的起义残军逃入越南境内后,大部分被法国政府缴械捕获,河口起义失败。此后,一些同盟会员如杨振鸿、马骧等依旧循着联合会党的旧路,继续策划、联络会党进行革命,永昌成为革命党谋划革命的下一个着力点。
1908年,马骧等人成立了同盟会下关小组,还策动、联络袍哥组织“玉龙公”准备在永昌起义;杨振鸿也在干崖策动袍哥与清军防营发动起义,亦图谋先占永昌,再由永昌光复全滇。当年十一月,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云南同盟会员决定利用此次时机联合会党发动起义。革命风声起后,杨振鸿面对云贵总督锡良“悬赏二万金严捕”[21],赴蛮允运动巡防军杨管带,但该管带一面赞成革命,一面派人截击杨振鸿;在永昌,会首杜文礼、白年等领导的起事被革命党人以准备不周叫停,但由于没有及时疏散起义群众,导致风声愈大,俟杨振鸿到永昌,杜文礼等人因“政府已下密令捕拿彼等,早已潜逃。仅东边三百余人可以集合”[22]。杨振鸿冒险起事后,乡民先是误记时间,“时未到而即至”[21],后遇清军严备就溃散而去,起义归于失败,杨振鸿也在逃避清军追捕中病逝。此次起义失败固然与消息走漏、计划不周、清军严备等原因有关,但会党的怯懦逃跑、巡防军的阴奉阳违也难脱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腾越起义时,此会首杜文礼还在永昌纠集党群,“希图劫掠。”[23]河口起义、永昌起义的相继失败,证明了由游民散勇组成的会党群体,在缺乏革命意识和组织纪律的情况下,无法完成云南的反清事业。
2.腾越起义与重九起义
自从事革命活动以来,革命党人没能建立起一支完全听从指挥、忠于自己的军队,虽屡屡联合会党发动起义,但无法获得完全胜利;河口起义中,革命党人以会党为主体还联络清军反正,虽曾取得小胜利,但由于会党军缺乏组织纪律,加上当时河口地区广大人民革命意识未觉醒,起义无法取得成功。河口起义后,一些同盟会领袖认为“以后举事,民军简直不中用,非运动新军不可。民军太无战斗力,太无训练,新军比较来得好,而且投身新军的人往往有真正想救国家的人。连秀才举人也有投到新军里面当兵的,可见一斑”,孙中山也深以为然[13]。自此,革命党人认识到改变方法与策略的重要性,1911年爆发的腾越起义和重九起义中,在联络会党的同时,亦重视运动新军参与起义。
“辛亥云南光复之役,发难之地,一为省会,一为腾越,而腾越为先。”[13]腾越起义之前,杨振鸿曾在腾越广泛联络会党和军队力量,永昌起义失败后,云南革命活动渐入低潮。辛亥八月,武昌起义爆发,并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各省纷纷响应,九月初五,杨振鸿的学生张文光与彭蓂、钱泰丰、李学诗以及哥老会首领陈天星(陈云龙)等人秘密集会,决定以张文光为都督,于九月六日发动起义。张文光,字曜三(又绍三),腾阳旧家人,家素丰,从小豪侠成性,广交好友,他“目击满虏专制,民困阴霾,狠手无寸柄,輙慷概欷歔”[21],“在腾越哥老会中有很大影响。”[16]后来,张文光以经商为便,在缅甸交结会党和革命党人士,认识了革命党人杨振鸿、黄毓英、马骧等人,并经杨振鸿介绍加入同盟会。张文光还发起组织革命团体“革新会”,寓意“革故鼎新”,广泛联络反清力量,而具有反清传统的会党成为重要的联络对象。关于张文光、杨振鸿、马骧等人的身份问题,有学者认为,同盟会员杨振鸿、马骧、张文光等“都参加了哥老会。”[24]这一判断缺乏史料依据,还影响到了后来的研究者[2-3]。参阅相关史料,这一论断还可商榷,笔者认为张文光、马骧、杨振鸿等在进行革命活动时,虽与会党中人交往甚密,但并非会党成员,且经历过云南光复的周开勋将军就回忆说:“(张文光)本人不是青红帮分子,但却结识了不少哥老会人物。”[16]
早在1909年,张文光就和刀安仁等建立秘密团体“自治同志会”,大力联系清朝旧式防营、新军、工人、哥老会、屠户、小商贩、秀才等阶层、行业之人,“发展了农民、会党群众数千人入会。”[16]1911年,张文光逃匿清政府追捕到干崖与土司刀安仁约定举义有期。武昌起义爆发后,张文光感到革命形势面临机遇,联络会首陈天星、革命党人钱泰丰、彭蓂等“于卧牛岗歃血誓众”[21],商讨起义;陆防军部分官兵也以野操为借口,在腾越郊外开会,决定以“自治同志军”为中心,“发动会党、学校师生、少数民族、农民和清军士兵”举行起义[16]。作为起义前革命党与陆防军重要的联络力量,会党在腾越起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会首陈天星、周维美等率军与陆军、巡防营激战并杀死了腾越陆军管带张桐、巡防营管带曹福祥等人,促进了起义取得成功。在攻占腾越的过程中,张文光意识到在革命运动中不致外衅、争取帝国主义国家保持中立的重要性,下令率兵保护领事、税司、教堂、英人医院等,由哥老会首领周维美奉命“送举义信及对外宣言,致各洋员处交涉勿惊”,起义军将各署局攻下后,派人巡视街道巡查匪盗,而市民“安眠如恒,义军尤未敢扰及民分粒”,形势可见安定[21]。起义成功后,腾越成立滇西军都督府,张文光被推为滇西军都督,哥老会领袖陈云龙为都指挥,会首周维美、杜云山分别被委为都督府武巡捕、国民军第十一营管带,由此可见哥老会在腾越起义中之作用。腾越起义成功后,资产阶级政权滇西军都督府推动各地反正,而在省城昆明爆发了主要由讲武堂师生与十九镇部分新军发动的重九起义,结束了清王朝对于云南省府——昆明的统治,成立了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都督府。重九起义极大地促进了整个云南的反正,会党对起义的发动与成功有重要影响。
清末“新政”中,清廷以云南为边防重镇,在云南筹建陆军第十九镇,并兴办云南陆军讲武堂、陆军小学堂等,以培育军事人才;清政府还鼓励各省支持公费生和自费生留学海外,在此背景下,云南省“渡海求学者先后达千人。或习师范,或习政法,或习陆军,多以救国自任,而陆军生尤激烈。”[15]这些留学生接触到民主共和思想后,对满清封建政府痛恨日甚。在日留学过的滇籍新式知识分子回国后,有多人在各级军校中任教,或在军队中担当军官职务,借工作机会广泛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结果造成“革命的种子已播于全省军队中。”[16]1910年,法国向清政府要求云南七府矿厂的开采权,激起公愤,云南陆军小学堂学生杨樾在请愿演说中“拔刀断指,沥血大书”[25],讲武堂学生李伏龙“每星期放假外出,他都要到军械局视查一周,然后又到总督署大门前察看一过,以便将来进攻,其热心革命,可见一斑。”[19]正因如此,重九起义有“省中举义,以统兵之将,节制之师,义声所倡,人心先附,其事易”之说[13]。新军在重九起义中的主导作用,是起义成功的关键,而会党对于发动新军起义又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自武昌起义,天下响应,于是云南九月初九日亦有光复军之起,克复省垣,檄定全省,以军界之力居多焉。”[23]新军是重九起义的主导力量,但将云南辛亥革命中的会党与新军分开论述、各自一体,是不恰当的,云南辛亥革命中新军与会党是相互联系的,且不少新军本身就是会党分子。重九起义前,云南的哥老会盛行,陆军第十九镇成立后,军队中“当兵吃粮的人没有不参加哥老会的。”[19]早前同盟会员黄毓英等人,为了联络会党以发动新军,结识了包括云南省哥老会总会首何高升在内的许多会党首领,借机发展革命力量;到1910年,唐继尧担任七十三标三营管带后,革命党人更是利用与会党的关系,在军中大力宣传革命工作,造成军中革命思想的盛行,会党是革命党人联络、发动新军的重要桥梁。到蔡锷领导的重九起义爆发时,驻昆新军第七十三标、七十四标、炮标、马标等队伍能够积极起义,会党的响应和联系功不可没。重九起义后,革命党人组建起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随着滇西、滇中、滇南反正成功,全省基本光复。就像时人所说,云南的光复不仅得益于革命党的领导,“而哥老会帮助的力量也是不小的。”[19]
三、清末云南会党的内在缺陷及其表现
在清末的云南革命运动中,会党扮演着重要角色。河口起义由革命党进行构思和筹划,而会党是起义的主体;腾越起义和重九起义中,借新旧军队的力量,会党与同盟会共同推动了革命反正,促成了云南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秘密会党对革命成功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其内在缺陷也很明显,并且给革命运动和民主政治造成了重大损失。
(一)主观意识上
1.缺乏坚定的革命信念,具有强烈的雇佣意识
会党成员多由破产农民、工人以及被裁撤而走投无路的旧式军人组成,除少数成员外,多数人并没有国家大义观念,往往将革命起义当作是一份临时工作,懒散懈怠,拿钱则办事,缺饷则散去,将自己的躯体视作谋生的根本,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往往在革命过程中没有拼尽全力,遇到困难便畏难而逃。河口起义中,会党领袖黄明堂与清军斗争之余仍旧照做开堂的把戏,因为开堂结会可以赚取钱款,依然是一套会党的色彩。进行革命活动不忘捞钱,会首如此,会众更甚。起义军占领河口后,蒙自清军防务空虚,还存有大量军械可补充起义军,“而且到了蒙自以后,我们事先和滇越铁路公司也接洽过,铁路线可以给我们应用,军用品也可以运送便利”,黄兴督促黄明堂率领军队开往蒙自,士兵竟然要求再发一个月军饷,否则拒绝听从指挥[13];在战斗中,遇到缺饷、缺粮,会党没有办法就哄然一散,逃到越南边境不能带枪入境,“有的人把枪丢了,有的人连人带枪逃到安南地方再给人缴下来,有的人竟把枪卖给了安南人”,连法国政府都无奈地警告:“照你们这样做法,简直不是搅你们的政府,是要搅我们安南了!”[13]
2.意识活动的封建性和迷信性
大多会党成员由于缺乏新式知识,对于革命以及革命后所要建立的新政权充满疑惑,缺乏概念;受封建迷信的影响,会党在革命起事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迷信活动,白白延误战机,贻笑大方。腾越起义和重九起义成功后,各地为维护治安,多有扩充兵力之举,一些会党分子也乘机参加军队,“市井无赖,溷厕军籍,呼朋引类,歃血联盟。甚至军队复为山堂,将领称为哥弟”[15],河口起义中,黄明堂被命令率军前进蒙自,不但进退反复无常,而且“开的时候烧许多的纸钱,不晓得又是犯了什么神,一定要开回来。”[13]
(二)组织形式上
1.封建家长式的组织结构
会党成员绝对服从首领,这导致进步的会首可以借此发动革命运动,但遇到顽固迂腐的的会首,或者会首发生动摇时,会党便会成为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阻碍。腾越反正后,永昌哥老会首领杜文理(杜文礼)“合群不逞之徒千余人,假号腾军,自永平,掠曹涧,据喇鸡呜井数日”[13],被迤西巡按赵藩派兵击败后,竟又投入永昌军队之中,最终于九月二十日被诱杀于腾越橄榄寨。云南光复后,哥老会首领陈香亭煽动会党叛乱,并“拐饷潜逃。”[23]
2.分散主义下的流动性和割据性
会党习惯于居无定所、流窜劫掠的生活,新政府成立后,会党成员对于现实稍有不满,或者遇到困难,就易于重操旧业,与政府为敌,威胁社会的稳定。腾越起义后,分别任驻腾越炮兵队长、驻南门升官庙营长的哥老会员班龙珠、张琦,竟打算抢劫腾越城,还派人联络张文光“说大家哥弟都愿照旧拥护你”[25],后经张文光急报李根源,才不致酿成大乱。大理光复后,军队中的哥老会分子“尤屡次联络党羽,思乘间抢劫饱扬,一夕数掠。”[23]
会党成员多来自于底层社会,除了恣意妄为,难以安于现状外,居功自傲和保守心理比较重,当起义活动取得成功时,企图制造割据以满足私欲。腾越起义成功后,张文光曾派遣哥老会首领、都指挥陈云龙领兵前往大理联络反正,但是陈云龙庸妄骄张,治军无纪,沿途将军队扩充到二十多营,还“糜饷扰民,阻兵肇乱”,信任哥老会杜文理(杜文礼)等人,造成“一时杂沓并进,兵即匪,匪即兵,各自号一军”的局面[13]。当时大理已经反正,陈云龙执意进军酿成兵端后,李根源由昆明到腾榆调解,才平息冲突。云南军政府成立后,蒙自又发生兵变,队官、哥老会员李振邦煽动士兵抢劫工厂、商店、洋行,叛军拥护李振邦为“迤南防军司令”。云南辛亥革命成功后,许多会党分子暴乱即因此而起。
四、清末云南会党评价
在造反与革命双重视角下,清末云南会党活动在不同情境下的性质与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作为民间秘密结社,会党提倡互帮互助与“兴汉反清”,这是会党壮大的原因之一,也是革命党联络会党起义的基础。为了谋求生存,清末云南会党自发地活动,往往既反抗官府,又劫掠平民。作为封建专制社会的产物,云南会党发展到清末时期,势力庞大,活动频频,河口起义前多次反抗官府、进行破坏活动,但此时各股会党势力既孤立又落后,起事也旋起旋灭。这些劫掠偷盗、反抗官府的造反活动,具有反封建压迫色彩和盲目破坏性,也导致了官府加大力度对会党结会与造反活动进行打击,当经济基础和社会性质没有根本改变时,云南会党活动有增无减,并出现了这样一幕:会党势力壮大,则政府打击加剧,壮大起来的会党为谋生存又揭竿而起反抗政府,形成晚清时期云南会党治理的死循环,云南会党在这样的情境下,扮演着造反者的角色。
到河口起义时,云南会党的角色发生了改变,领导河口起义的关仁甫、黄明堂等人既是会党领袖,又是同盟会员,其思想经过改造已不再局限于利用会党互帮互助、抗官造反,而具有了一定的民主革命思想。当具有一定民主革命思想的会首在封建家长制的组织形式下率领会众发动资产阶级革命起义时,这些会众就已经不自觉地参与到云南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之中了。河口起义后,革命党人注重在巡防军和新军中散播革命思想,使得军队中的会党开始具有了自觉的革命意识,由不自觉的革命者向自觉的革命者转变,这也是腾越起义和重九起义能迅速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正如陈旭麓所言,会党“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体现者,而且游离于生产之外,它破旧而不能立新”[26],即使在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中自觉的革命者也不占多数,除了军队中有会党分子倡乱闹事外,广布于民间且未参与辛亥革命的会党聚众开堂、谋为不轨之事不胜枚举,在资产阶级新政权下依旧扮演着造反者的角色。虽然云南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封建秘密结社组织固有的缺陷并没有在革命中轻易抹去。就如前文所述,这些缺陷在革命进程中造成了许多消极影响,更侵害到新政府治下社会的稳定,于是乎,云南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对会党进行治理势在必行。
游民具有反社会秩序的本性,这使得会党自产生以来就不容于统治阶级。从清末云南地方政府到辛亥革命时成立的云南军都督府,二者在施行各项政策、维护政权稳定的同时,都没有忽视对秘密会党进行打压和治理。从时间线上来看,有清一代对于秘密会党的治理是愈发严苛的。到了清朝末期,在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基础上,急于“新政”的清政府对于会党治理收效甚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使得诞生于封建专制社会的秘密会党反而蓬勃发展,宣统朝《大清现行刑律》颁布一年后,由会党参与其中的辛亥革命就葬送了清朝的统治。
云南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对于会党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是会党受前述内在缺陷的限制,愈发地威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是革命党人认为辛亥革命达到了“反清”“排满”的目的,会党已完成使命。于是,九月十三日云南军都督府在昆明成立后,就对会党采取了打压政策。军都督府治理会党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针对民间社会,制定内外结合之策。1912年初,军都督府相继发布《军都督府通谕开山设堂会党从速解散白话告示》《军都督府核定开公口山堂惩治律》,在肯定会党反抗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要求会党成员解散公口山堂,不再入会,并且“要努力为一个良民,不要蹈从前的覆辙”,从此以后“父戒其子,兄戒其弟,未入会时,勿再失足,已入会的,早早回头”,律令还规定对组织和参加会党者施以重惩,对图谋不轨的会首处以死刑,“参与谋议,居该党重要之职务者,永远监禁”或者徒刑[21],甚至连知情不告发者都要处一月以上一年以下之监禁或一百元以下之罚金,这两份布告说明详细,法条严苛,对于从会党内部瓦解其势力有积极意义;省咨议局也致电各地官吏、公所,要求各地弹压土匪、会党,并且考虑到地方巡警较少,建议适度增加巡警、团勇,防止匪党滋扰,从外部环境对会党进行治理。二是针对政府军队,安抚消弭其势力。在军队中会党的问题同样严重,由于当时军队新编的过多过快,导致会党分子浪迹其中,数量庞大。军都督府针对会党在军队中迅速蔓延的问题,除了裁撤部分军队外,也在军规中明确晓谕,但有“烧香结盟者”,宪兵可直接拘捕。会党作为民间秘密结社,大多数会众缺乏政治觉悟,而贪图私利。云南在反正的过程中,由于军队过多,财政掣肘,士兵亦有不满于军饷者,各地多有会党分子劫掠财物之事,蒙自兵变亦与此有关,因此,保障军饷成为军都督府压制会党的重要手段。例如在大理宣布反正之后,会党首领钟湘藻因不满曲同丰诱杀上级蒋辅丞,率领军中会党徒众公开活动,引发严重骚乱,当标统孙绍骞等人劝说钟,并许诺升其为管带时,钟湘藻还提出自己的要求,要求承认军中的会党组织、允许开山堂结拜,后来机关部召开会议,承诺向陆军提供军饷,兵乱才最终解决。
清政府倒台时,虽然社会性质未曾改变,但是云南省建立起了以蔡锷为首的革命性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应该说,军都督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在政府的强势镇压政策之下,一些哥老会员遭到惩治,云南会党陷入低潮期。
五、结语
秘密会党产生于封建专制社会,在近代畸形的社会土壤里迅速发展。清朝末期,云南外患于英、法的虎视眈眈,内忧于民变不断,而会党起义充当了民变的重要内容。云南的秘密会党最早从两广和四川传入,从无序的抗官起义到参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会党不仅组织暴乱,而且在云南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实现了创会传说中的“反清”目标。辛亥革命后的云南会党虽然遭到军都督府的镇压,但只要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和性质没有改变,会党一有机会便会抬头,暴露其落后于时代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