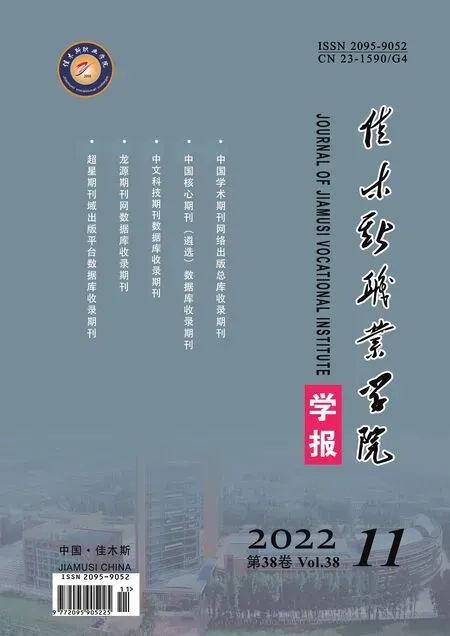民族自决和全民公决的共同渊源与现实困境
张奕睿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2)
全民公决在20世纪为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使用,而拥有浓厚民族自决色彩的全民公决在战后举行了百余次。但现今民族自决和全民公决已经走入极端化的困境。冷战后,迅速被分离主义势力所运用,成为分裂活动的合法化工具,严重冲击了国际社会的正常秩序和主权国家的基本底线,并为国际霸权主义的干涉扩张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当前民族自决和全民公决已然呈现出密不可分、互相影响、配合运作的状态。对此,本文采取一种二者的交互联系视角对其观察分析。
一、共同渊源:人民主权、自决原则与民主权利
(一)基于人民主权理论的同质性
人民主权理论,是指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拥有国家主权,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这是民主政治理论的最高要求。现代民族自决和全民公决制度都以人民主权理论作为思想渊源和基础,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这样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
民族自决权思想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深刻阐释了作为意大利君主的基本职责是团结意大利人形成统一自主的意大利国家。虽然马氏具有浓厚的君主主权思想,但他提到这种自决权的行使也是“给本国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1]。自决权的服务对象在于人民。而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重点规制了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主权独立[2]。这正是资产阶级及其附属劳动者、因封建土地继承关系而被外族封建领主奴役的农户的集体要求。大范围的民众通过战争的方式,以赋予君主政府强大的专制王权而形成的具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为载体,加以实现民族自决。
进入18世纪,资产阶级反对王权压迫建立民主政治的革命斗争兴起。在此时,民族自决权成为时兴的政治口号和政治目标。例如法国大革命中“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的口号。民族自决权在该阶段形成了严密的理论体系,直接来源便是以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让-雅克·卢梭为代表产生的人民主权理论。让-雅克·卢梭认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国家权力的源泉,这样的共同意志被称为。而人民将“公意”塑造成名为社会契约的现实载体,通过其进行自身权利的集体化转让,从而形成一种政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便称为国家。人民是整个国家的生命力源泉,国家主权掌握在广大人民手中,人民可以自主制定法律、参与政治活动。而政府,实际上只是一种代理人的角色。同理,只有人民作为主体,自决权才能作为一种公意的表现方具有合法性。民族自决在该理论充实下产生了颠覆性变革。正如王英津先生所言:“人民自决权思想是由人民主权学说直接导出的。换言之,人民自决权是人民主权的逻辑延伸。”[3]在其指引下,哲学家康德提出的“道德意识自由说”及对人所具备的社会参与能力的阐述,极大增强了人民对行使民族自决权能力的信心。革命导师列宁从社会主义的人民主权理论提出了反抗阶级压迫的革命式民族自决概念。至此,在人民主权理论基础上的民族自决权框架得到了充分建构。
全民公决制度则直接来源于人民主权理论。“全民”反映了该制度的主体是在任意政治实体下享有投票权的全体人员。而“公决”是一种民主表决的体现,同时这与常见的民主代议制方式不同,“公决”更加侧重于对民众直接表决的强调。同时公民作为国家的权力主体,在事关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事件上,多数情况会激发出主人翁心态,增进参与决策管理意愿。而该制度设计也正是迎合于此。纵观历史,全民公决同样形成于18世纪晚期席卷全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如雅各宾派在法国执政时期提出的公民投票权等。这使得“人民主权的理念获得最大程度实践,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公意。”[4]
(二)作为民族自决原则的共同体现
自决原则,实质上是一种国际政治和国际法原则。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广大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自主、科学社会主义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广泛联合行动的双重需求下,自决原则得到了由国内实践走向国际政治原则的深刻转变。列宁对自决原则作出了系统阐释,他说道:“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5]在国际法上,《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款都对自决原则作出了直接规定,而全民公决则更作为一种自决原则的实现方式体现。因此民族自决和全民公决无论从实质上、形式上还是行使主体上,都明显具有高度的自决原则特征。
(三)保障民主权利实现的相互补充
1966年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强调,“所有人民都具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条文中将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定义为“所有人民”,并且人民可以通过民族自决权获得自身本所拥有的政治、经济等相关人权。可以说,这样的自决权蕴含着高度的民主式人权观念,实际表现出人民主权理论的延伸。
民族自决权更作为一种民主权利的救济性权利而存在。最初便是用于反抗封建压迫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侵犯。根据联合国大会第2625号决议,在殖民统治下、被外国政府统治或被多民族主权国家所奴役歧视的少数群体人民可以使用这一权利。正常情形下,这些群体下的人民已然在现代民主社会获得了必要的基本权利,但决议条文很明显证明了在决议中的情形下,这一类人民是无法掌握主权权力的,且自身的基本权利是持续受到侵犯的状态。而他们的目标是从侵犯其基本权利的政治主体中脱离出来,以达到重新实现自身基本权利的目的。正因如此,亦可以解释为在实践当中的“再民主权利”。
全民公决则是民主权利的直接体现。全民公决本就作为基本权利中所规定的人民民主参与权的一部分,是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制度设计。而作为与自决权这一救济性权利配合运作的程序要件。实际上就是两者相互补充而确保民主权利实现的组合。而这种配合也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二、现实困境:主体界定、国际实践与主权侵犯
(一)民族自决的主体界定问题
在笔者看来,当前国际社会中对民族自决主体的界定模糊不清,且“就以与民族自决权有关的问题而言,必须提出其他标准用于确定‘自我’的范围。”[6]
第一,“民族”“国族”与“族群”。“民族”指民族自决中“民族”概念定义。“国族”对应的英文称呼为nation,指国家概念的主要构建群体的族群化称呼,例如中华民族、意大利民族等。而“族群”对应的英文称呼是ethnic group,指基于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在语言、文化、历史或者血缘上的稳态共同体,是一种实际意义上的国民群体划分[7]。“族群”和“民族”在中文中意义是一致的,都是在多民族国家中等级次于“国族”的群体,包括了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实际上,“民族”概念本身就是源于全体人民根据自身的意愿目的在不同历史力量的交流过程中逐渐淬炼出来的模式。新石器时代末期,传统人类部落在新生的国家结构下逐渐趋向和平式的交流融合,产生第一次身份认同,形成有自身特性的低级共同体,即族群。伴随着传统国家间交往,诸多族群找寻共性、互通有无,产生第二次身份认同,建立起具有多元同一性的高级共同体,即国族。在西方资产阶级兴起之后,国族认同产生出以国族共同体为基本形式的国家组织体,即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形成后,也会由多种因素出现既有国族和新族群的相容问题,形成建立于民族国家之内的第三次身份认同,形成以国家为核心的新国族。纵观上述阶段,国家概念一直是贯穿发展全局的助推器。这代表了“民族”概念的产生变迁与国家概念的密切联系。以至于学界对广义民族的分类标准也以国家作为参照物,分为“小于民族国家、等于民族国家、大于民族国家”等多类[8]。实际上充分说明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高度一致性。而能够代表这种一致性的则正是“国族”概念。正如明斯特所言:“民族概念的核心观念是,具有共同特性的人民应该效忠于本民族及其法律代表,即国家。”[9]
在民族自决权中,“民族”的实际含义也充分认定为“国族”。马志尼在论述意大利民族自决时,就反复强调了“意大利人民”“意大利国族”的概念,并强调了国族与人民的同质性,认为只要是主权国家之人民则为民族。列宁虽然提倡国内被压迫的“民族”具有民族自决权,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实际是为了达成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障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宣传和维护民族自决权,绝不是为了‘提倡’实行分离,相反地,是为了促进和加速各民族的民主的接近和融合……是因为我们想建立大国。”[10]可以发现,其最终的视角还是落在了“国家民族”之上。同时,人民主权理论也与国族天然结合。因为人民主权理论是一种与国家、与全体人民紧密结合的集体性概念。如若强调“族群”,则是强调了分异于全部集体的少数派为主体,使其具有特殊意义,与人民主权理论的本质是不符的。
第二,“人民”与“民族”。“人民”被混淆为“民族”,这样的定义颇有问题。首先,根据前文的论述,民族自决中应当使用“国族”概念,而“民族”的概念常常被民众认为是“少数民族”代表的“族群”概念。如果任由“民族”作为民族自决主体,且对“民族”概念的国族定义不进行系统普及,那么势必会导致民众无法做出正确认知,而被不法分裂势力曲解利用。其次,“民族”概念仅在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人民武装斗争下具有事实主体性,因为此时的“民族”都处在被西方殖民者压迫之下。但时至今日,这些“民族”基本上都取得了国家独立。此时对“民族”概念的使用便显得缺乏实际意义。再次,根据安东尼奥·卡塞斯先生的理论,民族自决权应分为对内自决权与对外自决权。而对内自决权指的是人民对于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自决权,实际强调了深化对国家事务的民主参与,符合人民主权理论和时代现实的要求。但在对内自决权中,很明显“民族”作为一种非政治亦非法律上的民主权利主体,是不能直接行使这种权利的,改为具有政治权利属性的“人民”则更为适宜。
(二)全民公决的国际实践问题
一是全民公决不为大多数国家承认。当前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在国内法中确认了全民公决制度。而诸如我国等大部分国家则将其排除在法律之外。对于独立公投则采取全面禁止态度,包括我国、西班牙等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当中将内部民族分离视为严重侵犯国家主权的分裂性行为①参考《西班牙宪法》第二条:“西班牙王国是所有西班牙人共同且不可分割的家园,西班牙王国不可分割的团结为西班牙王国之基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两者条文引申出严禁以民族问题进行分裂国家行为的目的表达。。在国际法中被认为的普遍人权在国内法不被承认,实际反映了国际法与国内法适用的矛盾,亦是民族自决原则异化后与国家主权原则产生冲突的表现,但怎样解决是很棘手的问题。无论是否符合国内法规定,独立问题也高度受制于政治力量配比和国际政治局势,例如北塞浦路斯公投案件,虽然严重违反塞浦路斯共和国国内法,但由于土耳其的幕后支持,实际上塞浦路斯处于无法行使管辖权的状态。二是独立公投的投票人群范围局限性问题。包括近三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已进行的多数独立公投,其投票人群范围往往局限在要求脱离的人群中。而这只是全体公民中的少数部分,仅有他们的意见不能够代表集体民意。针对剩余民众在公投中的民意体现则并没有制度设计和对应实践,这与民族自决和全民公决的制度精神是相违背的。三是全民公决的投票制度不符合真实多数民意问题。全民公决投票有使用简单多数原则和绝对多数原则之分。但从实践上来看,在对于独立公投等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采用简单多数的国家更多。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省公投案,在进行第二轮公投投票时出现了49.4%赞成、50.6%反对的情况。西方国家往往使用简单多数通过原则,不仅无法代表真实民意,也同样侵害了其他民众的基本权利。同样违背了民族自决和全民公决的制度精神。
(三)对于国家主权的侵犯问题
对国家主权的侵犯分为两点:一是对国家对内及对外最高权的侵犯,包括产生的分离主义势力膨胀、国内少数民族谋求独立、自治区的分离倾向和恐怖主义等。二是在人民主权原则上,人民主权理论在当今已经被大多数民主国家写入宪法,在宪法上明确了人民具有国家的最高权力。而早先论述的民族自决和全民公决在现实实践中对人民主权原则的侵犯,实际也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
三、结语
综上分析,两者的共同渊源与现实困境颇有理论上的脱节意味。但究其脉络,并非制度设计本源的短视与失误,应当归结于分裂势力曲解民族自决的基本含义并强加于国家主权原则之上,以及国际法的非强制性和国际政治的妥协性,也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违背国际法原则的行径不无关系。同时,应当认清其最终的根源,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卑劣的阶级区分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失衡,令人民主权原则形同虚设,各族群之间等级分明、障碍重重,甚至在歧视剥削中丧失国家民族的真正认同。之此,我们更应呼吁国际社会积极合理关切,在解决民族自决和全民公决的现实困境方案中能够达成国际一致。维护各国国家主权安全完整,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进步,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模式与效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