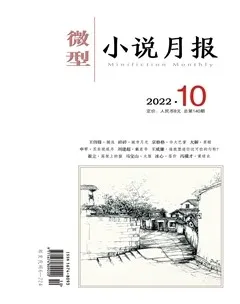谁敢塑造你这可怕的匀称?
老虎!老虎!
他的脑袋里在号叫。
他渴望变成老虎。
这种渴望不是精神的隐喻,而是一种真实的改造。对着镜头,他龇牙咧嘴地叫喊着。他的额头高耸,两颊隆起,上嘴唇中间被切开,嘴唇上穿过十几个金属钉,上边挂着长长的虎须。他的脸上文着虎脸一般的纹路,只不过是蓝色的。不止脸,露出的身体部分,也覆盖着同样的虎皮刺身。还有指甲,锋利而细长。他喜欢爬树,必须每天吃肉。他的宠物是一只猫,在他看来,猫就是缩小版的老虎。
这可不是偶尔心血来潮的角色扮演游戏,这是上千次血淋淋的手术,没有回头路。他无法再回到那个眉清目秀的样子,他曾经还戴着眼镜,斯文得像个知识分子。
他叫丹尼斯·阿夫纳,是美国退役海军。他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战争,心智没有受到过创伤,也就是说,他这样干,不是因为他受到了什么不堪忍受的刺激,而是主动选定的。他也因此获得了一些虚妄的名声,伦敦一家博物馆的开幕式还把他请了去,让他充分展示他的“风采”。
大多数时候,他还得做回人。在生活中,他踏踏实实地,在社区修理电脑赚钱糊口。除了博物馆,还有不少电视综艺节目也邀请他展示“风采”,可惜,他没有因此赚到钱。只因他对变成老虎的渴念是无止境的,一笔笔钱,都贡献给了整容医师。叫“整容医师”并不准确,依照相关法律,正规整形医生不能接受阿夫纳的整形要求,因此他的多数整形手术,是由人体改造艺术家史蒂夫·海沃德施行。“人体改造艺术家”,好吧,一个新的职业,不知道客户多不多。
在心理学家看来,他或许患上了一种“躯体变形障碍”。这是一种心理疾病,患者会对自己身体的某个部分非常反感,比如耳朵,比如眼睛,比如鼻子……患者会陷进这种思维旋涡深处,觉得自己非常丑陋,任何人的安慰都没有效果,因而不得不去整容。
的确,这个时代,人们通过屏幕上的“完美之人”来反观自己,差距变得永远难以填补。但是,他可不是要把自己变成完美之人。他想变成老虎。他没有精神病,到底为什么呢?追问的人太少,人们看见他,在心底惊讶和辱骂一番就完事了。可这对他来说,却是他的生命的核心所在。
他生于一九五八年,具有印第安人的血统。他的社区里,处处都住着印第安休伦族和拉科塔族人,但在二十二岁之前,他过的还是正常人的生活,甚至还参加了海军。二十二岁的某一天,他和部落酋长的一次谈话,彻底改变了他的思想,也改变了他的人生。
酋长看着这个眉清目秀又不乏健硕的年轻人,感到了深深的担忧。在酋长看来,这已经是一个美国人了,而不是一个印第安人。酋长决定跟这个年轻人好好深聊一次,他们聊了印第安人的历史和文化,聊了今天的生活方式,聊了如何继承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这应该是印第安年轻人的责任。
“世界是如何有了光的?是我们的神踏入篝火燃烧了自身。跟神一起燃烧自身的,还有山鹰和老虎,它们一个被烧黑了,一个被烧黄了。”酋长的鹰眼盯着他,“而你,阿夫纳,你有老虎的勇敢灵魂,遵循老虎的生活方式吧!”
那一刻,他感到自己的灵魂被洞穿了。
“酋长,那我该怎么做呢?”
“我们会用彩绘的衣物和铁环,把自己装扮成本部落的图腾。”酋长的脸上和身上还有着刺青的印痕,因为衰老,看起来像是一些老年斑。
他下定决心,要在虎与人之间完美转换,集虎与人两种生物于一身。就像他的祖先所做的那样。他找到了“人体改造艺术家”,后者为自己能够大展拳脚兴奋不已。
在此后的三十二年里,他便在通过老虎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他没有娶妻生子。很多人对他的私生活很好奇,他说:“我见过很多女人,她们清楚,对我来说,成为一只老虎比做人更重要,但是很多女人很难接受这个现实。”他没有说,他变成的老虎为什么还是只母老虎。
“那你变成虎人快乐吗?”
“不,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乐趣,”他沉吟了一下,“但我的灵魂感受到了野性的呼唤。”
大约二〇〇五年的时候,他搬到了一个岛上居住,这里的原始环境更适合与自然交流。一个网名叫“原子弹醉汉”的人看到新闻后,在论坛留言说:“你敢搬到我们这儿?我们这里到处是猎人,如果你想搬来的话,你最好待在森林里别出来,不要穿黄色的衣服。”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五日,在太久没看到他之后,人们在他的“虎穴”中发现了他,他已经死了。死因不明。有些人觉得他是自杀,更多人认为他是因为整容过度,而导致身体衰竭。但他的朋友说,可能因为他长期无法融入社会,而导致了抑郁症。他本意是想在人类和老虎中任意切换,但事情并不像他预想的那么顺利。这一年他五十四岁。
卡夫卡在《变形记》中让可怜的主人公一觉醒来就变成了甲虫,阿夫纳也想一觉醒来就变成老虎,可他找不到作者。我想起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一书,里边提到原始思维的核心特征之一,便是“互渗性”,即一切存在之物既是其自身,又是一种神秘力量,且神秘力量是其本质。阿夫纳就认为自己既是阿夫纳,又是强大的老虎,而老虎更加是自己的本质。值得一提的是,列维-布留尔读了司马迁的《史记》法文译本后,对太史公写的星象与人事的关联大感震惊,才萌发了研究“原始思维”的念头。
另一个人类学家名字中也有个“列维”,列维-斯特劳斯,他的《野性的思维》认为,过去人类的具体性思维与现代人类的抽象性思维,并非等级化的,不说前者低级而另一个高级,而是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的两种平行发展、各司其职、相互补充与渗透的思维。此书影响力非常大,直接拉开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大幕。而在谈论文化的学术话语当中,结构主义至今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存在。
阿夫纳不一定读过这两本书。当一种文化的土壤已经失去,还能否坚持住原来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其中的神秘?神秘为什么随着文化的逝去也失去了灵光?但他一定读过并喜欢布莱克的这首诗:
老虎!老虎!你金色辉煌
火似的照亮黑夜的林莽,
什么样超凡的手和眼睛
敢塑造你这可怕的匀称?
什么样超凡的手和眼睛,敢塑造你这可怕的匀称?那一定不是“人体改造艺术家”的手。
选自《青年作家》
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