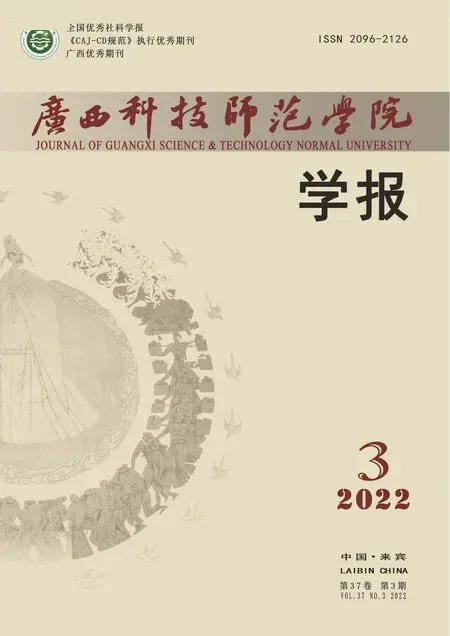论王阳明诗中的悲苦色彩
马 雯 彬 彬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在明代历史上,王阳明“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诚如王士祯所言:“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1]在各种身份之间,“心学大家”无疑是王阳明最为显著的一个身份,作为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之学说思想历来备受瞩目。蔡元培指出:“明之中叶,王阳明出,中兴陆学,而思想界之气象又一新焉。”[2]然而,同众多古代学者的遭遇一样,王阳明因其学术上之成就过于夺目、声名太过显耀,盛名之下往往掩盖了他其他方面的成就。如其文学成就、诗文造诣方面多被掩盖,所幸后人多有发掘而不至湮没。清人王世贞云:“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3]
王阳明对于辞章之爱一生不减,以其不世之才,又加以学力宏肆,发而为诗歌创作,置诸当时同辈亦足称翘楚。而王阳明一生经历之曲折、仕途之坎坷、心学之发扬,使其诗中具有浓厚的悲苦色彩。对王阳明诗中悲苦色彩的研究,我们不仅可见其诗歌创作的风貌,还可以窥见其人格形象与心灵世界。
一、伤别之苦与首丘之思
王阳明的众多身份与头衔里,他首先是以一个“天姿异敏”[4]的士人身份出现的。士人,在中国古代指士大夫、儒生等知识阶层人士。《晋书·刘颂传》载:“今世士人决不悉良能也,又决不悉疲软也。”[5]859颜之推《颜氏家训·归心》言:“俗僧之学经律,何异士人之学《诗》、《礼》?”[6]士人作为礼乐制度和礼乐传统的维护者、社会精英阶层且情趣高雅的士人具有特定的文化属性。故《孟子·尽心上》云:“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7]281中国士人有着多愁善感的特质和深厚的故土情结。王阳明一生辗转各地,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因而朋友、故土成为其心中的重要慰藉。自古文人多骚客,对朋友的感伤离别是中国文学自古以来的抒情母题,而落叶归根的乡土情结与首丘之思又是另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班彪《北征赋》指出:“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8]伤别之苦与首丘之思是中国传统士人进行文学创作表现的重要情思,这类诗作在王阳明诗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王阳明一生仕途乖蹇、聚散无常,临别感伤与离别怀念都发而为诗,其诗展现出诗人伤感别离的内心情感世界。在王阳明诗中,伤感离别、追忆旧友是王阳明诗歌的重要内容,此类诗作的表现对象主要可分为两类:亲人和朋友。《易经正义·兑》云:“君子以朋友讲习。”[9]276孔颖达疏:“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讲习道义。”[9]276在王阳明诗中,朋友包含所有志同道合的相识,亲人和朋友这两类群体构成了其诗伤别之苦的表现对象。以武宗正德元年(1506 年)王阳明三十五岁被贬龙场驿驿丞为分界,王阳明伤感别离类诗作的情感在被贬前后有所不同。在正德元年被贬之前,其诗对于离别的感伤更多是出于文人的多愁善感心理。这一时期的伤别诗作以弘治乙丑年(1505 年)王阳明改除兵部主事时所作《京师诗八首》为代表:
久别龙山云,时梦龙山雨。觉来枕箪凉,诸弟在何许?终年走风尘,何似山中住。百岁如转蓬,拂衣从此去。[10]672(《京师诗八首·忆诸弟》)
老舅近何如?心性老不改。世故恼情怀,光阴不相待。借问同辈中,乡邻几人在?从今且为乐,旧事无劳悔![10]672(《京师诗八首·寄舅》)
五泄佳山水,平生思一游。送子东归省,蒪鲈况复秋。幽探须及壮,世事苦悠悠。来岁春风里,长安忆故邱。[10]672-673(《京师诗八首·送人东归》)
予有西湖梦,西湖亦梦予。三年成阔别,近事竟何如?况有诸贤在,他时终卜庐。但恐吾归日,君还轩冕拘。[10]673(《京师诗八首·寄西湖友》)
以上选自《京师诗八首》其中四首,《京师诗八首·忆诸弟》《京师诗八首·寄舅》为思念亲人之作,《京师诗八首·送人东归》《京师诗八首·寄西湖友》则为伤别追忆朋友之作。《京师诗八首·忆诸弟》由别山梦雨而感慨诸弟离散,发出“终年走风尘,何似山中住。百岁如转蓬,拂衣从此去”的感慨;《京师诗八首·寄舅》咏叹“光阴不相待”“乡邻几人在”,只但愿“从今且为乐,旧事无劳悔”。此两诗虽亦多有感慨,然尚是哀于时不待人、白驹过隙而发拂衣归去、但求无悔的心思。而在伤别、寄赠朋友的诗中,无论是《京师诗八首·送人东归》里的“世事苦悠悠”“长安忆故邱”,还是《京师诗八首·寄西湖友》中的“三年成阔别”“他时终卜庐”,亦尚是一些伤别怀旧之牢骚。正德元年(1506 年)被贬之前的王阳明伤别之诗,其在内容、情感上尚是处于传统的慨叹咏怀,而自正德元年贬谪之后,其伤别诗作内容内涵愈加丰富充实、情感思想更加浓厚明显。以贬谪龙场这一时期的伤别诗作《赠陈宗鲁》为例:
学文须学古,脱俗去陈言。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又如昆仑派,一泻成大川。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子才良可进,望汝师圣贤。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10]1072
此诗作于正德四年(1509 年)十二月,时王阳明谪戍期满,复官庐陵,在黔诸门人送别,阳明以诗答之,此为答门人陈宗鲁之作。在贬谪龙场时期,王阳明在伤别怀友诗作中实现了对传统伤别诗作的情绪化愁思的超越,开启了其心学浸润之下的诗歌创作,较之正德元年之前的传统伤感情绪表达有所不同。
《九章·哀郢》言:“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11]这种落叶归根、思恋故土的首丘之思历来是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之一,亦成为王阳明在伤别之思主题外的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如《来仙洞》写道:“石门遥锁阳明鹤,应笑山人久不归。”[10]706《再试诸生用唐韵》言:“樽酒可怜人独远,封书空有雁飞来。……遥想阳明旧诗石,春来应自长莓苔。”[10]1069《元夕二首》曰:“故园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寂寥。”“炎荒万里频回首,羌笛三更谩自哀。”[10]705在王阳明诗中,伤离别、念旧友、思故土并不是分隔开的,在更多的时候是离别之伤、念人之情、故土之思交相融合、浑融一体,如写故土之思而旁及思人,写别离之伤而兼写怀旧。总之,伤别之苦与首丘之思情感的融入使王阳明诗中带有些许悲愁、忧伤的色调。
二、贬谪之痛与苦闷之情
王阳明一生正道直行、仕途乖蹇,且以显扬圣学、报君安民为己任,但在大道潜行、人心堕落的社会环境下,往往多遭贬谪、心为行役,内心饱受贬谪之痛与苦闷之情,这些贬谪的伤痛与内心的苦闷往往借诗歌得以抒发,这是王阳明诗中悲苦色彩的一个重要方面。
束景南认为在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构建中,弘治十八年(1505 年)的“心学之悟”、正德四年(1509 年)的“龙场之悟”、正德十四年(1519 年)的“良知之悟”、嘉靖六年(1527 年)的“天泉之悟”是王阳明心学思想发展的四个里程碑。而“心学四悟”中的“龙场之悟”又是最为人所道的。但抛开龙场驿在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上的重要意义来看,贬谪龙场这一经历对王阳明本身而言是一场磨难,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那种贬谪的内心痛苦与身处荒凉乡野的苦闷之情还是极其直观而浓烈的。
王阳明贬谪龙场的内心痛苦与苦闷,在其赴谪期间的诗歌中便多有体现。如在《答汪抑之三首》中,“去国心已恫,别子意弥恻”“回思菽水欢,羡子何由得”[10]676,已然流露出对于贬谪“蛮貊”的不安和远离故土的不舍;在答和挚友湛甘泉的诗中也有“君莫歌九章,歌以伤我心”“君莫歌五诗,歌之增离忧”[10]677之句;在《赴谪次北新关喜见诸弟》中,“已分天涯成死别,宁知意外得生还”“投荒自识君恩远,多病心便吏事闲”[10]683,诗人对被贬谪后可能会遭遇的生离死别忧心忡忡,赴谪的苦与悲意味更为浓厚。就一个贬谪仕子的身份来看,王阳明对于赴谪龙场其内心充满未知的担忧,故而在赴谪期间一系列的答和、抒怀诗作中,其遭受贬谪的悲痛与内心的苦闷情绪往往充溢于其诗句之间,使人得以一窥其忐忑心态。
王阳明至龙场是在正德三年(1508 年)春,而离黔在正德五年(1510 年)十二月。王阳明谪居龙场近三年,在这一时期的诗作中,贬谪之痛与苦闷之情亦常常流露于诗句之间。据《王阳明年谱》云:“(正德)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岁,在贵阳,春至龙场,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鴂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12]此处言龙场之地的偏僻环境,而言龙场之民“旧无居”、王阳明“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则多有不实之嫌。实际上,王阳明初至龙场无所居而结草庵、择岩洞居住,在正德三年(1508 年)初至龙场所作的诗中对这种场景多有描写。如《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
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辑。灵濑响朝湍,深林凝暮色。群獠还聚讯,语庞意颇质。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污樽映瓦豆,尽醉不知夕。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10]694
“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的草庵不仅低矮到“不及肩”,而且简陋飘摇“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辑”。居住环境的恶劣与王阳明作为贬谪臣子的心情是一致的,只有在和淳朴的乡民们“污樽映瓦豆,尽醉不知夕”的时候,其内心的苦闷方才有所缓解。最后一句“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除以黄帝、唐尧的教化情怀自励外,这也是诗人在无奈之下的自我排解。王阳明在谪居龙场期间,地方的偏僻与环境的简陋自是其内心苦闷的一部分,然而其内心更多的痛苦则是源于他作为贬谪臣子的郁闷心情。如《采蕨》与《山石》二首:
采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浮云塞长空,颓阳不可回。南归断舟楫,北望多风埃。已矣供子职,勿更贻亲哀。[10]696
山石犹有理,山木犹有枝;人生非木石,别久宁无思!愁来步前庭,仰视行云驰;行云随长风,飘飘去何之?行云有时定,游子无还期。高梁始归燕,题鴂已先悲。有生岂不苦,逝者长若斯!已矣复何事?商山行采芝。[10]698
此二诗中王阳明是以去国之臣的形象出现的,在《采蕨》中采蕨以充饥的形象似有比附采薇孤臣的意味,而《山石》以“商山行采芝”的“商山四皓”作为效法,两诗在流露出孤臣去国的苦闷情绪的同时,还包含着效法古贤、避世隐居的思想。而诗中“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行云有时定,游子无还期”是其作为“游子”思归而不得归的痛苦;“已矣供子职,勿更贻亲哀”“人生非木石,别久宁无思”是思人而不得见的悲伤;“南归断舟楫,北望多风埃”“行云随长风,飘飘去何之”是对前途未卜的迷茫与困苦。总之,在近三年谪居龙场的生活期间,王阳明虽然借“龙场之悟”以构建心学“大厦”,但同时作为士人与贬臣,其内心是痛苦和苦闷的。思亲、怀友之苦,念国、盼归之痛,身世飘摇之感,前途未卜之困,所有这些不安全感与失落感始终占据其内心的情感世界,形成其诗中的贬谪之痛与苦闷心境。
三、感世之伤与忧世之心
蔡仁厚《王阳明哲学》云:“王阳明从小就有志于做圣贤,他一生思想的发展,最能表征一个人的人格学问成长的过程。”[13]郝永认为:“阳明的贬谪、达观、事功一体健全心态,是对传统文人‘忧愁幽思’情绪化贬谪心绪的超越,亦是对道佛价值观指导下忘怀世事‘达观’心态的超越,是其作为一时代大儒所具有的更备正价值意义的心理样态。这种心理样态甚至本质着阳明的一生,成为他的个性心理,并具传统中国文人共性心理意义。”[14]中国文人历来有着“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情怀,在这种共性心理之下,王阳明“做圣贤”志向与“贬谪、达观、事功一体健全心态”使得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尤深。在王阳明所处的明代社会,统治集团相互倾轧,君王德业日隳、德政不修,朝中臣僚往往托慎重老成之名、为固禄希宠之计、挟交蟠蔽塞之资、肆招权纳贿之恶,更有天灾频发、内外兵祸,已然显衰世气象。在这样的局面下,人性的堕落越发严重,有志于“做圣贤”的王阳明便往往把正道直行、开导人心、纾救民困视为己任,这些内容寄托于其诗作中,显示出浓厚的感世、忧世情怀。
王阳明有匡扶大志,少习举业兵书,希冀建功立业、报君安民,然仕途乖蹇,多有才不救时之感,诚如其早期诗《登泰山五首·其五》所云:“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置我有无间,缓急非所赖。孤坐万峰颠,嗒然遗下块。已矣复何求?至精谅斯在。淡泊非虚杳,洒脱无蒂芥。世人闻予言,不笑即吁怪;吾亦不强语,惟复笑相待。鲁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10]670王阳明虽常有“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10]670的感慨,但毕竟只是一时牢骚抱怨,每当看到社会的苦难一面,其心中的感世忧民情怀便展露出来。如正德丙子年(1516 年)王阳明升南赣佥都御史以后所作《祈雨》二首及《回军九连山道中短述》:
旬初一雨遍汀漳,将谓汀虔是接疆。天意岂知分彼此?人情端合有炎凉。月行今已虚缠毕,斗杓何曾解挹桨!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10]746
见说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雾长阴阴。我来偏遇一春旱,谁解挽回三日霖?寇盗郴阳方出掠,干戈塞北还相寻。忧民无计泪空堕,谢病几时归海浔?[10]746
百里妖氛一战清,万峰雷雨洗回兵。未能千羽苗顽格,深愧壶浆父老迎。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功微不愿封侯赏,但乞蠲输绝横征。[10]750
王阳明巡抚南、赣、汀、漳诸地,在剿抚盗贼之余,对于民生政事亦多关心,《祈雨》二首便流露出对祈雨而得的喜悦之情。然而在“旬初一雨遍汀漳”的喜悦之余,又想到“寇盗郴阳方出掠,干戈塞北还相寻”,面对盗寇肆虐、干戈不断的局面,只能夜不成寐、忧心如焚,“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他虽早有归隐山林的志趣,却念及民生疾苦,“忧民无计泪空坠,谢病几时归海浔”,逸居山林的生活又不知何时何日才能实现了。这里不仅展现出王阳明对于民瘼之深的体察与同情,更显示出其隐逸山林的佛老思想与忧乐天下的儒家精神的矛盾冲突,但就王阳明一生的经历来看,面对政衰时弊、人心堕落、民困生哀的世道,其感世、忧世之心是伴随一生的。又如在《回军九连山道中短述》中,王阳明虽欣喜与“百里妖氛一战清”,但同时也意识到民众反抗的源头实际上是生计无望之下的绝望挣扎。王阳明认为“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整顿内治、纾救民困方才是治乱之道,故而“功微不愿封侯赏,但乞蠲输绝横征”,民生得利、民困得纾才是最大的心愿。对于世道的忧虑、对于民瘼的同情、对于治理的见解都见于诗中,足见其感世、忧世之情。
在王阳明诗中,一方面对于世道的衰乱、人心的堕落深感忧虑,显示出其作为仁人和臣子的忧心忡忡,而另一方面由于君主的猜忌与臣僚的攻诋,使得其行为多受掣肘牵制,内心多有不得志的郁闷与才能不得施展的无奈。这种伤时忧世的诗句在王阳明诗作中尤多,如“我心惟愿兵甲解,天意岂必斯民穷”[10]762“小臣谩有澄清志,安得扶摇万里风”[10]762“丹心倍觉年来苦,白发从教镜里新”[10]757“尚劳车驾臣多缺,无补疮痍术已疎”[10]756等。其实在心学体系构建的过程中,王阳明已经逐渐意识到了寄希望于君主或者靠政治上的作为极难改变世道的黑暗,而必须以引导人心来达成人性和世道的救赎。但作为有着强烈家国情怀与忧乐情志的士人,他对于现实的黑暗与痛苦不能作冷漠的旁观者,所以其诗充满纠结与矛盾、苦闷与失望,如《归兴》与《寄江西诸大夫》:
一丝无补圣明朝,两鬓徒看长二毛。自识淮阴非国士,由来康节是人豪。时方多难容安枕,事已无能欲善刀。越水东头寻旧隐,白云茅屋数峰高。[10]755
甲马驱驰已四年,秋风归路更茫然。全无国手医民病,空有官衔縻俸钱。湖海风尘虽暂息,江湘水旱尚相沿。题诗忽忆并州句,回首江西亦故园。[10]754
此二诗透露出王阳明对于朝局时事的灰心与绝望,“自识淮阴非国士,由来康节是人豪”“全无国手医民病,空有官衔縻俸钱”,这不仅仅是对于自我的无奈嘲解,也是对于朝廷局面的辛辣讽刺。面对“时方多难容安枕,事已无能欲善刀”“湖海风尘虽暂息,江湘水旱尚相沿”的社会现实,有志而不得展、有才而不能施,也只有归寻旧隐方可一缓内心的苦痛。而在感世忧世、感时伤时而终归灰心失望之后,王阳明也就把拯救世道的方法转向人心的救赎上了。
四、道穷之悲与穷途之感
王阳明门人黄绾言:“功高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此守仁之所以不容于世也。”[12]230结合王阳明一生的悲剧命运来看,这种“不容于世”的表现主要在“功高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所谓“功高而见忌”是指仕途上的乖蹇坎坷,而“学古而人不识”则是指王阳明心学学术体系构建在当时所遭受的冷遇。这种“不容于世”的遭遇,在王阳明晚年经历的由世宗所掀起的“学禁”和“礼禁”两方面的打击尤其明显。虽然王阳明在平定宸濠之乱和“思、田之乱”的过程中展示了其高超的军事才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自己安国保民的人生抱负,但也多受帝王心术的猜疑和臣僚的攻诋。在各种猜忌与攻诋下,王阳明的悲剧命运已然不可避免。在这一系列的政治运作中,王阳明不仅在仕途上多遭冷遇,而且连其学说也被定位为“异学”“伪学”。
在“党禁”“学禁”双重风波的冲击下,王阳明为拯救人心、拯救人性而构建的心学学术体系也被定性为“叛道不经之书”,受“异学”“伪学”之名。如果说在嘉靖登极之前王阳明的一切苦难出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7]276的磨炼,那么在嘉靖登极后其生命的最后七年,政治理想的破灭绝望与心学思想的备受冷遇显示着其一生的曲折命运终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悲剧结局。面对在“党禁”“学禁”恐怖压抑下的社会环境,和王阳明晚年病痛的折磨,其产生了深深的道穷之悲与穷途之感。这种“道穷”“穷途”的悲叹反映于其诗歌创作之中,使得诗句之间笼罩着深深的失望与落寞,例如,过钓台作诗“人生何碌碌?高尚当如此”[10]794,谒伏波庙有诗“尚喜远人知向望,却惭无术救疮痍”[10]797,书诗于于泉翁壁上“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道通著形迹,期无负初心”[10]799,等等。
虽然嘉靖时期的“党禁”“学禁”大大加深了王阳明晚年命运的悲剧色彩,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王阳明复心成圣的心学思想体系的建构过程实现了其由凡而圣的自我超越,故虽然在嘉靖间漫天的诬谤与攻诋之下王阳明走向了悲剧命运的终点,但在其诗文学说中却显示出其于嘉靖“学禁”“党禁”之下的铮铮铁骨。从王阳明一生坎坷曲折的命运来看,他人的诬谤与攻诋伴其一生,“道穷”“穷途”之感的生发也不仅限于嘉靖年间王阳明最后七年的生命,而且广泛体现在王阳明各时期的诗作中,如《即席次王文济少参韵二首》其二与《元日雾》:
此身未拟泣穷途,随处翻飞野鹤孤。霜冷几枝存晚菊,溪春两度见新蒲。荆西寇盗纡筹策,湘北流移入画图。莫怪当筵倍凄切,诛求满地促官逋。[10]711
元日昏昏雾塞空,出门咫尺误西东。人多失足投坑堑,我亦停车泣路穷。欲斩蚩尤开白日,还排阊阖拜重瞳。小臣漫有澄清志,安得扶摇万里风![10]762
《即席次王文济少参韵二首》作于正德四年(1509 年)九月,当时王阳明正谪居龙场,此为组诗二首。王阳明在诗中以“野鹤”“晚菊”“新蒲”自喻形单影只、年岁渐老,在对“荆西寇盗”“湘北流移”忧心的同时,又感于到处勒索催讨拖欠税赋的场景,既有对自己苦闷心态的剖析,又充满对于时事的担忧与批评。而诗首“此身未拟泣穷途,随处翻飞野鹤孤”则表明作为谪臣的“穷途”之苦。《晋书》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5]900王阳明身处人性堕落的世道之间,作为谪居去国的孤臣,自然易与阮籍一样产生“穷途”之感。《元日雾》作于正德十五年(1520 年)五月,当时王阳明在正德十四年(1519 年)十一月回到南昌不久,他写道:“《元日雾》一诗将武宗身边的佞臣比喻为浓雾,暗示佞臣们设计阻挠自己,表达了希望能够驱散云雾见青天的心境。”[15]无论是谪居龙场时作的《即席次王文济少参韵二首》,还是困于南昌之时作的《元日雾》,王阳明一再引用阮籍“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的典故,以表达其“此身未拟泣穷途,随处翻飞野鹤孤”“人多失足投坑堑,我亦停车泣路穷”的穷途之感。这种仕途上的“穷途之感”与后来嘉靖时期在“党禁”“学禁”下的“道穷之悲”是王阳明诗作悲苦色彩中最浓厚的一笔。
结 语
王阳明将自身的际遇感怀寄托于诗文创作之中,故其诗蕴含着浓厚的悲苦色彩。具体而言,其诗所蕴含的悲苦色彩可分为由远离故土和亲友所引发的伤别之苦、由青云路断所带来的贬谪之痛、由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所触发的忧世之心和由“党禁”与“学禁”所激起的穷途末路之悲等四种,这四种情感贯穿了王阳明整个生命历程。同时,我们研究王阳明诗中的悲苦色彩对理解其建立的心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王阳明与祖摩的故事》中的成长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