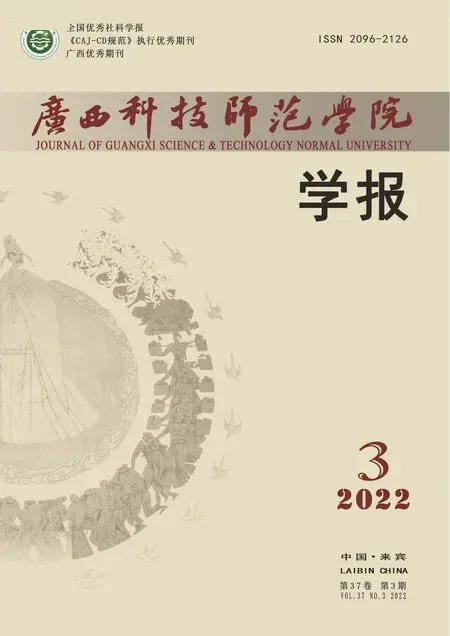蹇先艾小说中的贵州交通叙事
沈松钦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蹇先艾(1906—1994),他是贵州乡土文学第一代作家中的关键人物。1935 年,鲁迅将其小说《水葬》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接续鲁迅这一条文脉,蹇先艾将黔地文化和黔民生活带入文学视域,开创了贵州现代文学之路。对“老远的贵州”来说,喀斯特地貌面积达10.9 万余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61.9%,全省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蹇先艾早年常居北京,他的家人居住在贵州黔北,故他经常往返于黔北老家和北京。贵州复杂的地貌与交通奠定了蹇先艾小说的地理叙事基础。在蹇先艾的笔下,他将贵州交通叙事作为建构小说故事的技巧和手段,利用贵州交通叙事来串联故事场景、扩容叙事空间,形成多层次的、富有张力的叙事艺术。贵州的交通不仅建构了他小说的叙事结构,成为故事生发的缘起和原点,还作为其小说创作的叙事情境,兼具现实意义与精神指归。
一、串联故事场景与扩容叙事空间:交通作为叙事工具
蹇先艾是贵州遵义老城人,但他小说的叙事空间与场景并不局限于遵义城内。他常常通过河流船舶或是山间驿道将叙事空间扩展到其他城镇,并在这些空间之间切换自如。贵州遵义地处云贵高原向湖南丘陵和四川盆地等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形起伏大,地貌类型复杂。大娄山山脉自西南向东北横亘其间,将遵义全市河流分为乌江、赤水河和綦江三大水系。干流乌江、赤水河均有航行之利,可直通长江。在山水组成的环境中,水路和旱路串联起蹇先艾小说故事生发的场景,成为转换并扩容叙事空间的渠道。典型的文本有《到镇溪去》和《在贵州道上》。
小说《到镇溪去》主要围绕孙松轩的心理活动展开,从标题上看这一文本就明显涉及故事场景转换和叙事空间变化;也正是在空间转换和扩展中,巧妙地贯通了故事结构。从包谷场到镇溪,坐船比走旱路省“一栈路”,因而船运是人们日常出行和进行商业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此时,便引出船上唯一忧郁的人——主人公孙松轩。孙松轩的工作是给别人挑担子,他每年都要在坝县和K 省往返二三十次。往返的必经之路是一座小小的包谷场。他虽然不住在这里,但他更愿意将包谷场当作他的“故乡”,因为包谷场有他喜欢的女人——客栈老板娘。但是,身处包谷场的孙松轩通常是忧郁的,老板娘对他的冷落让他看不到爱情的未来。到了镇溪的孙松轩则充满了无限希望,他每次都盼着能早点回到包谷场。孙松轩在不同的空间场景有不同的心境,与连接包谷场和镇溪的这条水路密切有关。当孙松轩被夏胡子带着从包谷场坐船去镇溪给药材帮做事的时候,他是带着老板娘的冷落从包谷场出发的。船只刚刚驶入峡口时,“曲长的山峰并着”[1]152,孙松轩漠然地听着船上飘来的关于“老板娘的故事”;当故事讲到高潮之时,“两侧的山峰笔立着,水流得更紧迫”[1]154,老板娘悲惨的经历让孙松轩的心情变得兴奋又烦躁,他开始插话问老板娘的事,他似乎又燃起了希望;到了峡口,水势逐渐平稳,听完老板娘的故事之后,孙松轩对自己的爱情又充满了希望,他甚至渴望早点回到包谷场去,去见他最喜欢的那个人。从包谷场到镇溪,蹇先艾由线及面,通过水路行船的贯通和整合,将镇溪、包谷场以及行船途中的场景串联起来,完整立体地呈现出故事结构,形成了多层且富有张力的叙事空间。
如果说《到镇溪去》是通过水路交通来串联故事场景和转换叙事空间的话,那么《在贵州道上》则是围绕贵州的山路来达成一次交通与叙事的完美契合。蹇先艾写于1929 年的《在贵州道上》主要讲述了“我”和妻子一行人从遵义桐梓出发赶路的故事。“‘贵州全省,山国也;桐梓,又贵州岩邑也’。解放前的桐梓,群山阻隔,交通不畅,信息闭塞,处于极端落后的境地。”[2]故事中,“闷头井”“祖师观”“石牛栏”都是险峻危险的地方;乱石凹凸不平地嵌在土里,再加上路上汩汩流动的雨水,于是夫头就叫了两个“加班匠”,以此引出故事发生的主要人物赵洪顺。赵洪顺是“加班匠”中的一员,主要负责抬短程。“加班匠”是在贵州的高峰悬崖上衍生出来的一门职业。在贵州境内,触目常是奇异的高峰,往往数个山峰并峙,仿佛笔架。特别是黔路上被万重山包围的羊肠小道,很多地方只能容得一乘轿子通过,脚侧便是万丈深崖。顺着山谷的曲路蜿蜒而下,是连绵不绝的山岭,几千级石梯盘旋在山腰。贵州复杂的山地环境衍生出了“轿夫”“加班匠”“盐巴客”“挑水工”“赶驼马”等职业。
这类“加班匠”最大的特点就是嗜烟成瘾。为了换取买烟的钱,赵洪顺卖了老婆的衣服首饰,甚至把自己的老婆也卖给了别人,还欠了一位老太婆的家事钱。前行的路途遥远且险恶,行走的山路大都是崎岖鸟道,高峰与山沟相互交错。于是,作者就在险要地势的休息处分别引出赵洪顺的丑事。“石牛栏”“河洞”“三坡”成为连接桐梓和目的地的通道与纽带。在“石牛栏”,赵洪顺与他老婆的琐事勾连出场,但赵洪顺抵死不认。此时“我”对赵洪顺没有心生多大的反感之情,甚至还答应多给他一些小钱。随着“加班匠”的步伐向前迈进,情节也跟着坎坷的路途向前推进。翻过几座山之后,蹇先艾在“河洞”引出赵洪顺欠一位老太婆家事钱被追债一事,这时赵洪顺开始渐渐表露,他果断承认自己做的错事,但仍死性不改。到了“三坡”,“加班匠”的帮抬工作结束,赵洪顺做的所有丑事全部被揭穿,最后被官府抓获、枪毙。卖妻子的衣服首饰、典卖妻子、当街踢打妻子、欠老太婆的钱被追债等故事及其场景连点成线,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石牛栏”“河洞”“三坡”三个空间串联赵洪顺故事的完整场景,起到贯通和整合叙事空间的重要作用。“石牛栏”“河洞”“三坡”将故事场景中的线串成面,最后联结成网,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形成了多层次、富有张力的叙事场景。
二、建构与解构:交通作为叙事技巧和手段
贵州复杂的交通环境不仅是蹇先艾小说发生的叙事空间和重要场景,而且是蹇先艾重要的叙事技巧和手段。“黔之地,跬步皆山,上则层霄,下则九渊。”[3]万重山将贵州重重“封锁”,交通困难成为其时制约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因而,蹇先艾的小说中牵涉贵州交通的故事基本都反映了当时比较尖锐的现实问题。在叙事技巧上,蹇先艾并没有放弃传统小说常规的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是将这种曲折离奇的情节寄托在了贵州的交通上。
贵州省内山地崎岖,山脉绵延,崖谷深深。蹇先艾将故事情节投射至百丈深的悬崖上的小道上,道路蜿蜒曲折,故事情节也随之回环曲折。读者不清楚小说中的道路会在哪个方向转弯,也不知道故事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故而,蹇先艾的交通叙事为故事增添了几分神秘气息。他利用贵州交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先建构了故事文本的神秘性,后又解构了故事的神秘性。
典型的文本是蹇先艾写于1936 年的《谜》。《谜》主要讲述了团丁张德桂护送武区长从县城回南乡丁家堡,最后团丁被其杀害的故事。在工作岗位上,区长和团丁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但从私人感情上来说,区长和团丁在同一个村子长大,属于老乡。一路上,心直口快的团丁抛开了双方的身份地位和武区长肆意地谈天说地,他说区长是南乡的“老虎”,还认为区长能到现在这个位置一半是因为走运,等等。团丁以老朋友的身份和区长开玩笑,但这却让区长误会了团丁的心思。因此,当做了许多坏事的武区长看到团丁身上的毛瑟枪且恰在荒无人烟的羊肠小道,听到团丁口中肆无忌惮的话时,武区长立马将自己和“命案”两个字联系起来:“在这深山之中,离丁家堡还有十好几里路,根本用不着求助于他的武器,像团丁那样强有力的汉子,顺手轻轻一推,他马上就会掉到几百丈深的悬崖底下去,连尸首都要找不着的。”[4]48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走下又长又陡的山坡之后,地势逐渐平缓,武区长将傲慢收了起来,他试图利用“甜言蜜语”来稳住团丁。过了木桥,到了关键地点“鬼岩洞”,那个凹进去的深穴“像一个妖怪张大了血盆似的巨口等候在那里”[4]52。团丁向武区长求证这几年赚了好几万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此时的武区长仍吞吞吐吐地逃避着问题。“鬼岩洞”的环境和团丁的“不怀好意”让区长乱了脚步,又长又陡的山坡映衬着武区长忐忑的内心,他的心突突地跳着。过了“鬼岩洞”之后,区长和团丁又经过一片葱郁的松林。区长觉得团丁一定是对他存杀害之心,葱郁的松林这一封闭环境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消灭一个人。区长的心虚被这片松林激发,他将自己当年通过非正当手段获得的工作、利用职位之便收受的非法资金、强占别人妻子的秘密都说了出来。如果说在“鬼岩洞”和“松林”处区长还对钱财的事遮遮掩掩的话,那么在山崖之上的软脚石梯处区长立马一股脑儿地将秘密倾吐出来。到了斜坡处,此时距离丁家堡已经很近了,团丁又“恢复到卑微的下人的地位”[4]58,区长的手脚则大摇大摆地晃动起来。
“长坡”“鬼岩洞”“荒凉的松林”“软脚石梯”“斜坡”见证了武区长“傲慢—谦虚—傲慢”心境的变化。“鬼岩洞”的传说和葱郁的松林等建构了小说的神秘性,推进故事向前发展。在武区长给团丁安排好工作并打发他上路的几天后,团丁突然死于“鬼岩洞”。团丁的死是故事的暗线,也就是题目中的“谜”。但这是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谜”,“谜”的神秘性也不再“神秘”。此时,“鬼岩洞”解构了故事的神秘性。蹇先艾小说中交通上的关键节点,作者并非简单地将其嵌入小说情节中,而是将它们自然地融入故事情节中,共同构成了故事的环节。概言之,作者将“鬼岩洞”设置为关键情节点,并作为叙事的重点,以此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三、生发故事的缘起和原点:交通作为叙事场景
蹇先艾在写作小说文本的时候,一般就地取材,将贵州旱路和水路作为生发故事的缘起与原点。故蹇先艾的小说比较热衷讲述“山路故事”和“交通痼疾”,叙事多以艰险山路为空间背景,人物频繁活动在山路或者水路场景之中。蜿蜒的山路和行船的水路作为非常重要的故事场景,由此生发故事。但蹇先艾对两者运用的笔墨来说,以蜿蜒的山路作为叙事场景占据的篇幅比较多。受到地质构造的影响,贵州地貌类型以高原山地和丘陵为主。“山多河少”的特点让蹇先艾将大多数故事生发的原点和背景集中于高峰之中险峻的山路。《盐灾》和《盐巴客》就是典型的故事。
蹇先艾写于1936 年的《盐灾》以红沙沟自治村为故事发生背景,主要讲述了红沙沟公所文书臧岚初面对村民盐荒的故事。该村的环境具有典型的贵州特征:山脉高耸入云,山脉切割强烈,村自治所在半山崖,十余户住户则统一住在山脚。正是因为这深度切割的山形地貌,将灾难和现实割裂,成为臧岚初和村民之间沟通的一道“屏障”。臧岚初是红沙沟公所的文书,他从省城师范学堂毕业后自愿来到这里。红沙沟面临着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没有盐;因为当时“贵州的食盐基本从外省(以四川为主)输入”[5]。当家家户户严重缺盐的时候,盐荒问题不仅仅是臧岚初精神上的问题,也是极现实的问题——他既不愿下山去面对,也无从知晓盐荒对村民的实际危害程度。但当臧岚初走出村自治所,下山看到山脚的村民之后,“盐灾”给村民带来的伤害这一幕真实的景象呈现在他的面前。“今天我下坡去在村子里走走,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的面貌都非常黝黑,没有一点笑容,像丧亡了什么人一样;不说话,低着头,拖着鞋,不扣衣服,无目的地乱走。”[4]3村民走路提脚都费力、全身酥软,好几个已经自杀了。目睹盐荒给村民带来的实际灾难后,臧岚初不再逃避问题,他厚着脸皮去找他的叔叔臧洪发;虽然最终并没有解决红沙沟的盐荒问题,但他始终作出了行动。地势地貌似乎分割、遮蔽了老百姓遭受的苦难,成为臧岚初和老百姓之间的一道“屏障”,也成为灾难和现实之间的一道鸿沟。当臧岚初真正深入到山脚下的群众中去的时候,才真正了解这次盐灾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当时,贵州的盐是和“灾难”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盐灾》聚焦的空间是一个村子,《盐巴客》则聚焦一类人——盐巴客。“我”意外和一名受伤的“盐巴客”同住一间客栈,在“盐巴客”所讲的故事中,“我”解除了对“盐巴客”的误会。“我”起初认为“盐巴客”都是蛮横无理的粗人汉子,经常霸占着并不宽敞的一条路;亲闻了“盐巴客”的悲惨遭遇后,“我”了解到“盐巴客”是专门为有钱人“下力”的人,他们行旱路的时候经常会遭遇不测,一是天灾,二是人祸。天灾无法避免,水路途中遭受泥石流、洪灾等自然灾害时,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人祸则是由他们的身份地位决定的,负重上百斤的“盐巴客”经常会在险要的山崖丧命。“盐巴客”干的是“下力”活,“黑而发光的脸上布满了辛苦的皱纹,红肿着压断了骨架的双肩,脚杆上随时都带着斑斑的伤痕”[4]4。为了赚钱,“盐巴客”经常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而从山间开辟出来的小路非常狭窄,如果双方在同一条道路上相向而行的话,必须要一方停下让另外一方先行,才能安全错开前行。“盐巴客”故事的缘起和原点便围绕山间小路铺开。在蹇先艾的笔下,如蛇形般蜿蜒在山间的小路不仅是小说叙事的场景标记与地理标志,还是蹇先艾用来生发故事的缘起与原点,由此展开故事情节。作者将这些空间和场景作为缘起和原点,引出主要情节或者借此来整合故事情节。
四、现实意义与精神指归:交通作为叙事策略
从文化视角来看,蹇先艾“描写乡土生活,审视故土文化构成其乡土小说的基本内容”[6]。他将自己对故乡的情感寄托在贵州的交通情境上,在交通叙事中表达自己对贵州黔北的感怀之情。蹇先艾以交通情境作喻,将多次往返于北京与贵州两地的见闻在贵州复杂的山路和水路交通中完整呈现。值得注意的是,蹇先艾以贵州水路和贵州山路作为小说情境的交代是别有深意的。茫茫水域的水路常常给人以动荡不安、漂泊无依之感,曲折蜿蜒的山路则给人一种恐惧和敬畏感。蹇先艾小说中的贵州交通叙事不仅是他本人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表达,也完整地凸显了他独特的精神世界。
1919 年,蹇先艾离黔赴京求学。在此之前,其小说对贵州的描写主要以田园牧歌式的故土记忆为主。直到1927 年,蹇先艾因家事返家住了3 个月,并在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朝雾》的自序中称:“那时我的父母刚去世不久,一个人孤独地流落在北京,生活里充满了寂寞,思想便陷到悲观的泥淖中去了。每当烦闷的时候,我就梦想到故乡,憧憬着苗岭。”[7]此时蹇先艾对故乡的感怀已经慢慢显露,父母的突然离世和身处异乡的孤愁逐渐在作品中展现,动荡不安和漂泊无依之感逐渐进入蹇先艾的精神世界。于是,他根据自己返黔途中的见闻写作《水葬》。“1929 年后期代表作《贵州道上》发表,标志他的乡土小说进入了一个新境界。”[8]蹇先生之后的作品便一改以往对贵州的美好想象和乡间记忆,“崎岖鸟道”和“悬崖绝壁”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1919—1937 年间,蹇先艾因结婚、家庭变故、躲避战乱等原因多次返家。蹇先艾没有因为其时恶劣的交通而将人们的艰难一写到底,而是将自己的思念和乡情融于其中,同时赋予拯救和解放的作用,将交通对贵州发展的作用和价值全面凸显。
贵州“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布局衍生出了小说中“加班匠”“挑煤炭”“赶驼马”“编草鞋”等特有的职业与工作,其代表角色如《在贵州道上》的赵洪顺、《水葬》中的骆毛、《蒙渡》中的搭船女人、《赶驼马的老人》中的黄老头等。在蹇先艾的笔下,即使眼前的生活不尽如人意,但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例如,《蒙渡》中的“我”本来是想通过旱路开始长途旅行,但因前方正在拉夫,最后选择了水路。行路伊始,就遇张姓女人搭船去水牛镇,她进而讲起可怜的身世和遭遇:丈夫被川军拉走、婆婆身患重病、家里三个孩子没人照顾,走了四天三夜的草鞋上已沾满了泥浆,黑暗的生活似乎一眼看不到尽头,但仍然想为一份可能存在的美好生活而到处奔波。蹇先艾最终要点明的是,当时的交通不便虽然是贵州发展的“痼疾”,但通过交通等去认识外界也是那时的人们能够选择的一道窗口。这是蹇先艾在小说中选择交通作为他叙事策略的现实意义。
结 语
蹇先艾的小说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贵州黔北的现实烛照,他将这时期贵州的现实状况真实全面地融入笔墨,在交通叙事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黔民复杂的人性和生存境况。贵州交通在蹇先艾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书写,且这种书写是带有一定批判性的。其时,交通不便本身就是制约贵州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以其作为背景的黔民的生活中则充满了一定的悲苦意味。蹇先艾将贵州交通叙事作为他建构小说故事的技巧和手段,用其来串联故事场景、扩容叙事空间,完整立体地展现故事结构。同时,蹇先艾还将交通作为故事生发的缘起和原点,用来建构并解构故事文本,营造出具有现实主义的情境,最后形成多层次的、富有张力的叙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