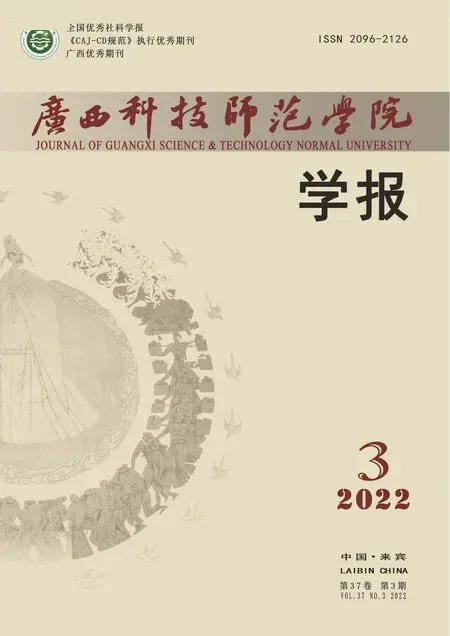老舍现实主义的边缘:规劝、讽喻与“为人生”
赵雅炅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北京 102488)
对于当下的文学史研究来说,学界对现代作家,尤其是经典作家的派别、主义及道路的划分工作早已尘埃落定,必要的细化、补遗等后续工作也逐渐走向尾声,在“类”的划分下进行“个”的讨论已成为我们当今文学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增长点与着力点,那些已被规划范围的作家笔下仍有许多隐性与“秋毫”尚未得到充分讨论,老舍正是其中之一。以往学界往往从单一角度出发,分别查探各个美学向度与老舍作品的吻合程度。如樊骏对《骆驼祥子》[1]、吴小美对《四世同堂》的现实主义评判[2],谢昭新对老舍作品中无意识痕迹的心理分析[3],刘勇从北京文化出发探讨地方文艺对老舍文学世界的构建意义[4],等等。在此之上,老舍作品的浑融特征也得到了学界重视并得到了两个向度上的共同关怀,为下一步在更复杂的关系中考量老舍作品奠定了理论与角度基础。如谢昭新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徘徊——论老舍小说的理想爱情叙事》、严革的《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老舍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以及石兴泽的《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矛盾冲突——老舍性格心理的纵向分析》等文章。然而,两个向度本身缺乏一定的关系探讨与脉络爬梳,从而难以看清老舍究竟受到何种风向影响,并呈现出怎样的细微变化与张力。
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中的特殊位置成为共识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他夹于鲁迅传统和赵树理传统中间的民间视角与民间意识,其次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前无组织的自由状态。此外,老舍身上还有很多难以归类的特质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解读。例如,老舍虽难以被归入某个派别,但被划在现实主义这个更大范围的单元“集合”下由来已久,在此基础上,老舍这一“元素”在“集合”中处于什么位置,是否受到其他“集合”的影响而产生位移,与其他“元素”的细微差别以及他对整个“集合”主题的复杂展现和过滤,都是可以填补的缝隙与空白点。
不像有些五四时期作家一样对待传统始终秉持着决绝姿态,老舍身上本就一直留存着旧式文人的精神特质与传统道德的价值观念,这一特质与观念在文学革命风头最盛时未曾湮灭,与民间通俗文艺形式相结合更是成为老舍20 世纪40 年代创作的主旋律。老舍与传统小说的关系是一条起起伏伏未曾断绝的潜流。
老舍小说中对规劝与讽喻的运用,恰可看到古典传统小说与五四时期“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两种“集合”特征的闪现。这令人不禁沉思,规劝和讽喻这两种带有训诫色彩的手法本就是“为人生”的一个侧面,还是“为人生”这一时代要求被包裹在老舍“规劝与讽喻”的形式中无法抽离出来的体现?亦或是上述两个“集合”在老舍身上产生了特殊时代所特有的交叉现象?这需要我们在新旧文学的双重关照下,以老舍的创作为基点,对两种“集合”在此之上呈现的复杂关系与模糊外沿进行仔细摸索。
一、“为人生”的新旧之别
为了进一步掂清老舍现实主义的复杂成分,首先需要厘析“为人生”这一文学思潮的时代特质与传统源流,如若“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古已有之,并在思想内涵与创作技法上与现存的并无分别,那么只能称其为“经世致用”的文学传统在特殊时代条件下的同质性复苏及重新概念化,由此老舍身上也就并不存在现实主义维度上的两种力量的角力或绞结。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为人生”既位于连续性历史传统的延长线上,又具有新的精神内涵。
学界对此已有一定探讨。温儒敏在《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一书中称,“作为一般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或方法,在传统文学中就已经存在;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则完全是现代的产物”[5]2,并声明在书中仅讨论作为一种自觉文学思潮的现实主义,归属于现实主义的“为人生”也遵循上述设定。这也是学界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
笔者认为以往学者对作品与思潮进行区分是很有必要的,但在梳理各自的发展历程过后,将二者进行对照思考与综合讨论也是有意义的。如若现实主义在创作上仍延用老一套,在理论观念上却吸收改造了西方文学而完成了新的自我建构,并在20 世纪20 年代初打上了“为人生”的旗帜,那么其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之间就应该存在一定的脱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存在缝隙的基础上,现代性思潮的获得是否为文学实践催生出了新的精神内涵与书写走向?为了试图回答这一疑问,我们需要对同样意在干预社会人生的新旧文学进行大致的甄别与区分。
(一)是否“自觉”与最终导向
1921 年1 月24 日,文学研究会于北京成立,标志着“为人生而艺术”一派的形成。“‘人生派’对文学基本问题的看法,是顺着《新青年》同仁所主张的文学服膺于‘思想革命’以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这条线索下来的”[5]22,将“人生派”作家们的理论精髓精而简之便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来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并在俄国现实主义的影响下发起对求真写实精神的文学倡导。
首先,“人生派”的作家创作的作品在经历理论上的觉醒与论争后,率先踏入试验场的便是“问题小说”与“问题剧”,叙事文学的主阵地也固定了下来。因而顺着叙事文学这一线索并结合上述几点来对古典文学进行回溯是本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一方面,《史记》作为我国叙事文学的早期代表,与班固“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评价共同熔铸了“实录精神”这一举足轻重的写实品格与原则。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思想主张并不是针对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而提出的,而是对著书立说的史家的勉励之语。东晋的干宝仍处处拿自己的《搜神记》与史书典籍作比,在作家的主观世界里《搜神记》依旧是对其所见所闻的忠实记录而非文学创造。另一方面,古代文人还没有形成“教化民众”[6]与思想启蒙的自觉。从唐传奇到明代四大奇书到晚清谴责小说,总体来看都是以“奇”作为小说谋篇立意的构思基础与美学追求,妖神鬼怪是常见题材,即使面向现实也多展现阴差阳错、起死回生、绝处逢生等非常态的人生境遇,与五四时期如实反映生活的主张相差甚远。即使是将喻世、警世、醒世写在书名里的“三言二拍”也不例外,这些作品虽有道德劝诫的理性冀求但仍未摆脱炫鬻、奇巧的美学形态与传奇的叙事模式。
其次,到叙事文学以外去寻求,虽隔一层抛开艺术形式与创作技法来单看其“为人生”的精神承续,但仍可觅得一些蛛丝马迹,即来源于儒家经学、对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并成为重要价值取向的“经世致用”思想。这确是一条济世为民的持久传统,但与新文学的“为人生”相较,仍是相异的,异在“人”这一精神内核。旧文学的“人”被包裹在“道”之下无法独立出来,实际上是“道”高于人,而新文学则是对人的重新发现,若也有其“道”,则是取道以为人。
再次,对“为人生”的最终导向进行追问也是对上述问题的有益补充。“人生”是个十分宽泛的范畴,“为人生”也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中心语的缺失导致产生“为了人生的什么”的疑问,从而其最终导向不明。虽然“人生派”的口号表意欠明但其在文学作品上的指向却清晰可辨。从易卜生《娜拉》的译介到胡适的《终身大事》、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许地山的《命命鸟》等众多“问题小说”中,热烈讨论着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与问题,综括之后都统摄于对人生自由与独立的强调,最终通往对个体的人的关爱。而旧文学对知“仁”守“礼”的强调,对“杀身成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经世致用”等的倡导,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个体的要求甚至苛求,从而使之有益于群体、国家。因而,二者之间还存在着终极目的的不同走向。
综上,“为人生”是具有新旧之分、古今之别的,实践技法上相似而精神内涵相异,文学主张趋同而美学风貌迥然。二者间的差异与不同是笃定的,却并不意味新文学范畴下的“为人生”于旧文化中觅不到一丝相承接的源头,只是旧文学难以找到将求实的原则融入形象呈现与虚构框架,并同时倡导改善个体人生的叙事模式。
(二)新旧文人精神品质的共通性
两种事物间的差异是矛盾的前提,而共通则为交叉或绞结提供可能性与合理性。所以在廓清新文学“为人生”的文学事实与传统文学的质性分野后,抉发现象背后的某种精神联系是必要的,并可借机对老舍现实主义复杂面相的生成因素做出一点阐明。
自古以来,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大都对一己之外的现实社会具有超越性的关注与担忧。汉有司马迁“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唐有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宋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明有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都是对感时忧国的代表性诠释,并逐渐化为知识分子的一抹心灵底色以及其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这种具有穿透时空力量的忧患意识在世道太平时尚不明显,社会矛盾越激化关于拯救苦难的呼号也就越加炽烈。迈入近代,亡国灭种的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重,因而具有历史性的感时忧国与具有时代性的救亡精神在现代作家身上结合了,这也是文人的精神品格与时代责任的合体,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充当着文坛的主流与基调,这种旋律正与出身贫寒,对下层社会、民间百态拥有深刻体认的老舍自身的精神气质十分切合。
因此,在现代新文学的文坛上才会闪烁着“为人生”这样与旧文学相似但却具有实质差异的文学火花。
二、叙述手法的张力与裂隙
老舍小说叙述手法上的隐约性与内敛性已被学界所知,但学界还忽略了老舍叙述手法中的规劝与讽喻、张力与裂隙。实际上,老舍叙述手法的含混特征与内在指向可能是探讨作家两种思想传统共存形态的一个切入口。
从部分作品的表层叙述来看,老舍的确惯用“藏”的艺术。老舍个人的主张、道理、情感等在多数小说的字里行间基本上可以做到不露痕迹,甚至在结束一场剧烈的矛盾冲突后也吝啬于向读者提供一个包含价值判断的立场。如《老张的哲学》就是一场界限鲜明的善恶搏斗,可从头至尾老舍并没有替好人扼腕、向坏人瞪眼,相反仍以平淡却不失明快的语气交代了老张最终坐上厅长高位的结局,仿佛这场悲剧已是意料之中的平常事,甚至是否可称其为悲剧也要打上一个问号了。在《开市大吉》中,连“我”也成了挣黑心钱的杂牌大夫,“我”对此引以为豪并由衷地佩服同事老王的手段更加高超,故事也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氛围中结束。从故事层面来看,老舍不仅丝毫没有给读者以“正向”的引导,还更有携读者一同看笑话之势,那么是否真的符合“他的小说泄漏出比鲁迅还多的虚无主义因子”“他的笔锋尽处,竟然空无一物”[7]的说法呢?应该是不尽然的。像老张这样被作家浓墨重彩的人物,老舍通过对其相似言行的叠加,凝结出老张鲜明的媚官倾向与个人道德缺陷。而《开市大吉》虽然全篇基调轻松愉快,但读者不会对文字“言听计从”,真正站在“我”的立场去视物,更不会为这场“笑话”叫好。在因与果、表与里、言与意的反差所产生的震惊和刺痛以外,另有一种不得不对现实进行逼视的力量。由此可见,老舍的小说看似凑趣与残酷,但瘠土之下仍是炽热如火的劝世之意在涌动。
从作家自身而言,老舍并非是真正超然物外的自然主义者,不论是生活还是创作,感情都在其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曹禺形容老舍,“他是一位有很深的正义感的人,嫉恶如仇”[8]188。老舍自己也不止一次提到,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就曾明言:“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我能是个热心的朋友,而不能给人以高明的建议。”[9]165这便足以显示《老张的哲学》一类作品的本质并非虚无或冷漠,在主观意愿上仍是“为人生”的,只是对现实或人生的干预程度因力有不逮而停在了提出具体对策之前。
老舍难以抑制的道德激情与对人民觉醒的期待在一些篇什中不难发现,并演化为一种规劝性叙述。在《哀启》一文里,老舍借老冯之口向正在受压迫受欺凌的平民大众发出“挺起胸膛、不畏强暴”的忠告。在《鼓书艺人》中,孟良既是秀莲的人生导师,也是整个小说中超越众人、又面向众人讲话的理想人物,他劝告秀莲要做新中国、新时代的新妇女,要既能独立,又能自主。“你不自轻自贱,人家就不能看轻你”,这两句被反复强调的劝诫虽说都是说给秀莲听的,但其实分别面向秀莲的两种身份并超越纸面的限制触及现实世界:一方面面向当时处于懵懂与迷茫的广大女性,应和着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呼声;另一方面则面向众多靠鼓书、京戏、杂耍等技艺讨生活的民间艺人,甚至辐射到更远。与之题材类似的还有《兔》。文中,小陈是个会唱戏的年轻票友,但有日益堕落下去的危险,俞先生时常劝解小陈不要因为玩意而耽误了正事,而正事便是艺人的品行。“我”虽然是个旁观者,却也在小陈被包养“下海”后还力劝其还掉欠债,脱离泥沼,重新找个事做。此处老舍的规劝除了以个体的独立自强这一“五四”式的倡扬为指归,更带有传统伦理文化中对洁身自好、人格节操与自我尊严的道德要求。《二马》是更为清晰的例证,小说中多次提及知识、人才救国的重要性,甚至不惜将叙述声音独立,试图以激切直白的呐喊叫醒麻木的国人,如“真本事是——拿真知识挣公道钱”[10]等。从上述饱含温情与力量的规劝中可以见得,老舍写作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目的性及指导倾向,他虽然说不准未来中国的出路与救国良策究竟怎样,但其中大抵离不了独立、自强、实干这些最基础也是最本质的因素。这些因素虽是由传统小说的手法来表达的,并夹杂着浓厚的旧文学色彩,但其对人物人格理想的最终塑造却与“为人生”的时代诉求相汇合。
相对于规劝来说,讽喻是老舍着力更多也更加得心应手的表达手法。老舍笔下如大蝎、文博士、丁约翰、冠晓荷等人物身上集合了典型洋奴的所有基本品质:肤浅、媚俗、圆滑、自私,以及对待洋人与国人的截然两副面孔,捧高踩低俨然如常事。而老张(《老张的哲学》)、穆太太(《善人》)、病鸭(《铁牛与病鸭》)等整日追名逐利不做实事的伪善官员身上,也背负着作者较多的讥讽态度与暗含的针砭力量。其中,《善人》与《华威先生》在叙事手法上具有同构性,细究起来,前者可被追为20 世纪40 年代“暴露与讽刺”的渊薮,且前者更富有寓言与喻世色彩,讽刺的分量也更足。此外,《善人》与《儒林外史》的讽喻手法相较也不可说不相似,语言谐谑锐利,人物与场景极尽精简,以速写的方式围绕中心人物记录下一连串事件与细节,以此构成一种颇为简洁却意味深长的反讽语境。其中,《善人》在对穆太太沽名钓誉、自私自利的伪善形象进行雕画的基础上,讽刺的笔锋更是波及了穆太太背后那个扭曲颠倒、装腔作势的官僚体系和上层社会。《猫城记》是一部典型的讽喻体小说,文中囊括了大量的隐喻关系与意义符码,最典型的如猫人与庸众,迷叶与鸦片,货币与国魂。此外还有娶妾玩妓的男性猫人,追求节烈的公使太太,虚伪孱弱的教育机构,懒散而贪婪的一众猫人……无不是对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中国社会与国民性格的绝妙戏拟,作者言在此而意在彼,暗含辛辣的社会批判,具有揭破现实的力量。老舍在文中虽然只交代了各个人物的现实身份,并未直笔点出其承载的社会意义与道德归趋,但显然作者已为我们提供了领略故事背后深意的钥匙,即贯彻小说始终并与之浑然合一的讽喻手法。这一手法在寓言结构之下埋藏了讥刺效果与批判意图,延续了古典讽喻传统中含蓄温和的表意方式,不仅连接着言与意,更互通着虚与实,换句话讲,老舍笔下的这些人物与情节虽都是虚构的,但其来源与最终指向却并非虚空。
以上论述即使不能看出老舍创作中系统、详细的社会分析与对策提案,但总归能一窥其所不满的社会现象与国民性痼疾,并从中察觉出一种关切、一种推崇的倾向,亦或是一种通向解决的可能性期待,在小说中虽看不到出路但已然展开了一个世界。老舍对于自己只能提供方向而无法指出道路的事实也曾表示过失望,但文学创作毕竟不等同于社会学科,温情而形象性的关切虽不能为革命方案增添新质,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文艺与人心的长足进步。
然而也正是这样并不具体与清晰的趋向才能够容纳包含传统与现代两种因子的微妙张力。这也表明,在老舍的作品里,规劝与讽喻的技法所留下的并不是一种色彩,而是传统道德规训、表达手法与现实主义的复合物。两种色彩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相处得颇为和谐,20 世纪40 年代开始出现抵牾。《舞台姐妹》曾遭批判,老舍公开出言反对:“有人说:电影宣扬了‘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要不得!要批!试问:清白做人,认真演戏有什么不好?又有什么不对?”[8]468我们可以从这一激烈冲突的“后事”来反顾老舍暗含裂隙、龃龉与挣扎的“前史”。
三、现实主义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冲突
在构建新文学的里程中,如何处理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现代作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西方文学浇灌下而萌芽的现代意识天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某种拒斥,然而这种拒斥并不是永恒有效的,时代需求才是拨动作家内心那根天秤指针的永续动力。显然,与其他多数作家相比,老舍内心的指针被拨动时所受的阻力更为强大,其位移与颤动也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动态。
老舍在正式踏入文坛之前,在少年时期就大量阅读了《小五义》《施公案》《红楼梦》《水浒传》《儿女英雄传》等古典通俗小说,其日后小说创作对男性侠义、女性温良气质的反复书写也可看出上述传统经典读本的影响。此外,老舍后来就读的北京师范学校也是一所偏重古文教育的院校。作家在《我的创作经验》中也曾表明,在其他课上“别人演题或记单字的时节,我总是读古文。我也读诗,而且学着作诗,甚至于作赋。我记了不少的典故”[9]489。老舍在《老舍选集》自序中也进一步表明了其文学成就的原生基础:“在五四运动以前,我虽然很年轻,可是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11]200老舍对传统文学的吸收与接纳使其文学体系的“根基”更加稳固,也预示了其下一阶段的文学转向与蜕变过程更加复杂与曲折。
1926 年,老舍经许地山介绍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正式成为“人生派”的一员,然而不论是当时“人生派”参与的思潮论争还是后世的研究论述,典型与中心从来都与老舍无涉。谢昭新认为,“他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的情势下登上文坛的。这就决定他在登上文坛的同时,就带上20 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特有的历史使命,以冷静、务实精神,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3]绪论。意在说明因为时间的落差老舍成了五四运动的反思者,然而老舍的自述却表明他仍是五四运动的追随者。老舍曾反复提及“五四”带给自己新变化,如,“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学兴起,我不由得狂喜”[11]200,以及“‘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12]。结合《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我们基本可以还原作家早期的创作路径,即其写作是运用传统的技法并在西方文学的启发下开始的,而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捩点,从此老舍在时代思潮与意识形态的规约下,创作向现实主义靠拢。同时,时间的落差与距离的隔膜使这种规约与洗礼不是彻底的,也并不十分深入,“问题小说”浓厚的感伤情绪因而也没有攻破老舍幽默的盾牌。所以,较晚“归队”的老舍还保有些许“懵懂”与“传统遗迹”,这些被遮蔽、被忽略的“懵懂”和“遗迹”不断在潜层悸动,并逐渐向显性的缝隙与张力转化。
这种缝隙首先显现在老舍20 世纪30 年代的文学观念上。老舍写于20 世纪30 年代初的《文学概论讲义》提到,“文学必须会干点什么,不拘是载道,还是说理,反正它得有用”,就鲜明凸显了老舍与其他“人生派”同人在文学直感上的区别。新文学向旧文学宣战的主要攻击点便是“载道”与“消闲”文学,而老舍却表示不拘是什么只要它有用。在这里,他并非是有意唱反调或是具有反思精神,而是倾向于一种对主义的疏离,以及对理论界限的模糊认识。错过了文学思想风急浪高的五四运动使老舍还未习惯完全以一种标准体系去衡量文学,而是更多依靠自己已有的文学经验与素养去综合看待。在《我怎样写〈二马〉》中,老舍曾表示文言的加入只是为了使人发笑与增添趣味,可见老舍没有对文言或古典文学有强烈的敌对情绪。《施公案》《三侠五义》等古典小说的影子还在其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因而在写作上也没有被“赶尽杀绝”,并尚能使传统与现代并行不悖。由此与文坛主潮之间这一点细微的区别或许是作者本人都未真正察觉到的。同在1936 年,老舍便曾有过分属两个文学脉络的表述:“一本讽刺的戏剧或小说,必有个道德的目的,以笑来矫正或诛伐”[13]与“文学不只是告诉人去改造人生,而且告诉我们如何去创造人生”[9]495。但总而言之,新文学所包含的进化论思想还是给了老舍较大施力的理性约束,牵引着他总还是在“为人生”的边缘徘徊,如“写家的企图必是想打破旧的方法与拘束,而杰作永远是打破纪录之作”[9]529。这样的意识仍强势植入了老舍的文学认知当中。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到来,时代需求与文坛风向产生了大幅度的偏移。1938 年前后,文坛掀起了关于“民族形式”的大讨论,此时不论是文艺论争还是实践创作,老舍都终于跻身风暴的中心。这一次旧文学得到了时代话语的青睐,从而旗鼓相当的两股力量在老舍的思维中首次直面相撞,随即在理知上产生了对于这一问题的反复、矛盾甚至撕裂。在宣传抗日的功用外,老舍还从构建文学体系的内在角度觉察到了传统文艺形式的不可或缺性:“不能像五四时一样永远模仿西洋的语言和技巧,也须用自己的语言和技巧完成自己的东西,明日之文艺必须走这条路。”[11]29然而破旧立新的使命与责任感仍在老舍的文学视景中拥有一定的作用力,老舍在《血点》一文中就曾表示以前的旧把戏在新时代是行不通的。在随后几年里,老舍在情与理、认知与实践中都产生了难以自我消化的矛盾,他一边深感旧诗有趣,一边又觉其陈腐想要躲避,在创作中对于旧形式也一再放弃,还指出,“不论我怎样躲避旧的一切,她都会使我步步堕陷,不知不觉地陷入旧圈套中。说到这里,我就根本怀疑了民族形式这一口号”[9]701。可见时代风潮之急已使得始终追赶不及的老舍产生了精神深处的茫然与巨大裂隙。
结 语
贯穿老舍文艺思想始终的是,文学要发挥惩恶扬善、改善人生的社会功能,而规劝和讽喻的手法正是可以承载这一功能并使新文学与旧文学相联的桥梁。时移世易,随着时代需求与文坛风向的变化,针对从启蒙到救亡的不同宣传要求,老舍也逐步从桥的一头走向另一头,但期间不乏犹疑与折返。从老舍在20 世纪40 年代复杂而艰难的文学转向与思想蜕变上可以看出,在大的时代主题下,新旧文学之间既有引力也有斥力,由此给具有特殊时代身份特征的文人带来了严峻考验。老舍在这种新旧力量的互动下产生了思想上的激荡与挣扎,在创作上呈现出了旁逸斜出的文学魅力与新旧交叉的综合性审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