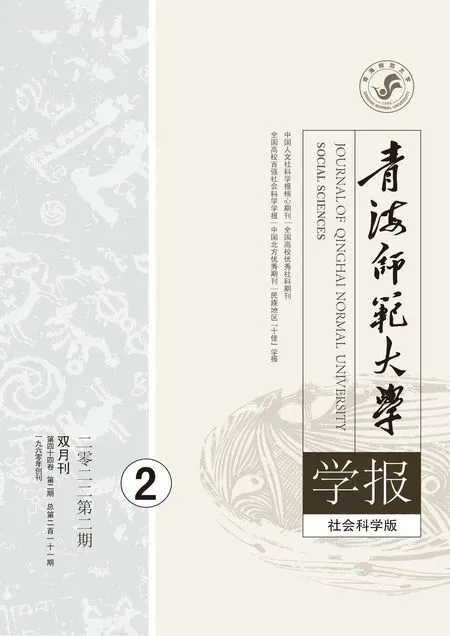青海方言使用与传承探微
赵 君
(青海师范大学 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16)
引言
方言是民族共同语的地方变体和地域分支。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语言生活参差多样,方言是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地域文化的显著标志,也是语言研究的活化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补充说明中谈到“方言是客观存在的,有其自身的使用价值”。
一、青海方言的特点
青海位于我国的西北,幅员辽阔,是我国多民族省份之一。全省现有人口562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46.98%。境内的通用语言包括汉语、藏语、蒙古语、撒拉语,土语,其中操汉语的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74.3%,讲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5.7%。[1]青海汉族以河湟地区为主,由历史上多地移民形成。青海汉语方言的形成是社会、地理、历史、语言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青海汉语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中原官话的秦陇片,其下包括西宁话(包括西宁、平安、湟中、湟源、大通、互助、门源、化隆、贵德)、乐都话(包括乐都、民和)、循化话(包括循化、同仁、贵德)三个次方言。青海方言具有地域性、存古性、杂糅性的特点。
(一)地域性。青海方言的地域性首先表现在它忠实地记录了一方之言独特的语言系统。以语音系统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代表青海方言的西宁话包括23声母,零声母在内,30个韵母,阴平44、阳平24、上声53、去声213四个声调,乐都话包括27个辅音声母和零声母,32个韵母,平声23、上声55、去声214三个声调。循化话包括23个辅音声母和零声母,31个韵母,平声13、上声42、去声55三个声调。
从词汇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构词音节数与普通话有所不同。“抠”(普通话中是双音节的“吝啬”)、“消停”(普通话中是四音节的“不慌不忙”)、“鼻疙瘩”(普通话中是双音节的“鼻子”)、“恨吼”(普通话中是三音节的“猫头鹰”)。二,构词语素不同。包括构词语素与普通话构词语素完全不同的词语如:“丁丁马勺(蝌蚪)”、“巷道(胡同)”、“胰子(肥皂)”;构词语素部分相同的词语如:“冰水(凉水)”、“黑饭(晚饭)”、“糨子(糨糊)”。三,构词语素语序不同。如:“知不道(不知道)”、“胡博整(甭胡整)”。四,词义与普通话不同。包括完全不同的词语如:“娘娘(青海话中指姑姑)”、“先后(青海话中指妯娌)”、“后楼(青海话中指厕所)”;部分相同的词语如:“洋芋蛋(除了指土豆青海话中还指爱吃洋芋的人以及皮肤黑黄皲裂的人)”。
从语法来看:一,可以看到语序的不同。如宾语前置句:“你茶喝、馍馍吃。”(喝茶、吃馍馍)、“你帽子哈带上。”(你把帽子带上)、“你桃儿几个有俩?”二,可以看到语气词的丰富。如青海话中常常使用“呗”(相当于“啊”表感叹:那好呗!)、“撒”(相当于“吗”、“呀”或“啊”表反问、祈使、感叹:妈妈好着撒?、你吃撒!、这个事情撒!)、“否”(相当于“呀”表肯定:他不知道否!)、“俩”(相当于“吗”表疑问:你知道俩?表陈述:这个事愁死俩!)“好”(表疑问:他走不走好?)、“喂”(表陈述:妈妈说着喂)、“靠”(表强调和感叹:你放心啊靠!)。
其次青海方言的地域性还表现在它反映了青海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包括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语言不仅是交际和思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和组成部分。“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同时方言作为语言在不同地域中的变体形式集中体现了当地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特性、历史发展以及生活习惯等内容,是各地区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特色内容”。[2]所以从青海方言的“熬茶”、“弩害(性格懦弱的人)”、“骀害(不成器的人)”、“尿床骀(经常尿床的人)”等词中可以看到青海地区特有的物质文化。青海地处高原,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气候寒冷,缺少新鲜蔬菜,且民众喜食牛羊肉。熬茶一般用湖南益阳的砖茶,用小茶壶、文火熬制而成,可以补充维生素,去油腻,另外加入盐、姜、花椒既可增味又可消炎、发汗解表、帮助消化,故为民众喜爱。青海是五大牧区之一,畜牧业是青海重要的传统生产方式,马牛羊是畜牧生活常见的生物,“驽马”是跑不快的马,“骀”是劣马,青海方言以此为基础创造出含贬义的“弩害”“骀害”“尿床骀”。再者从“娘娘、姨娘(青海话中分别指“姑”和“姨”)我们可以看到久远的婚姻制度文化。我们知道姑是父的姐妹、姨是母的姊妹,他们与娘不同,娘娘、姨娘的称谓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中曾今出现的血族内婚制中的姐妹夫婚、兄弟妇婚及媵妾制。另外,我们从“撒十二精药”一词中可以看到青海独特的行为文化。它反映青海独特的丧俗。青海人逝者出殡埋葬后,为家宅的安宁,家中、各处要撒由巴戟、芍药、人参、获神、鬼箭、桔梗、远志、狼毒、茯苓、杜仲等十二种中药熬成的汤药镇煞、驱邪。由于上述中药对应的分别是天精、地精、人精、神精、鬼精、山精、道精、兽精、松精、吞精等,故名十二精药。除此而外我们可以从青海熟语“野狐加狼”“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所反映的人们对奸恶、贪婪的厌弃,从而管窥人们的心态文化。
青海方言除了反映地域文化外,也反映了地域历史。比如汉代以前,青藏高原是羌人的主要聚居地,自汉始青海多移民进入,西汉霍去病收复河湟地区,东汉汉族移民,隋兵卒,明军户、流官、难民、商客、兵卒,解放后支援青海建设大量移民涌入。这样的历史我们同样可以从青海方言词汇中找到记录。比如“米柜”,众所周知青海不产米,但青海方言中却有“米柜”一词,这是移民的过程中,江南百姓把家中放米的柜子带到了青海,“米柜”一词由此得以流传。另外,青海历史上曾经是屯兵、驻防的地方,青海方言中“营干(工作,如:你做撒营干着?)、操练(引申为欺负、折磨,如:操练坏了!)、箭杆(引申为急、快,如:稀屎冒箭杆!)”这些词汇忠实地记录了与屯军有关的事物、行为,并真实地反映了青海屯军的历史。
第三,青海方言反映了地域独特的情感。语言情感是语言集团对各种语言怀有的不同情感和主观评价,它包括语言的尊卑感、优劣感和亲疏感等。语言是民族的标志,也是某一公民从属于某个社会群体或某一地域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们相互认同的一种最直接、最重要的标志。林华东教授曾指出:“人们一般都是首先认同自己生存的空间,学会父母教给的语言,认同父辈绵延下来的文化历史习俗,从自己的宗族文化到族群的区域文化进而认同民族主流文化,汉民族内部的各民系族群,无论它们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涯,其内部认同首先都是以母语为依据。”“少小离家老大归,乡音无改鬓毛衰”,表达的是游子通过乡音认祖寻根的感慨;“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体现的是通过乡音、乡情获得的认同感。一个民族的语言总是和这个民族的社会心理之间存在着深厚、牢固的联系。方言作为某一地区人们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常常会给同一地域、族群带来语言情感的深厚系联。乡音的亲切感,实际反映的是人们内心的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地域的认同。青海方言发音轻柔,有类关语,表达委婉,再加上多拟声词和重叠词的使用,形成了细腻、委婉、幽默、轻快的风格。[3]如,青海话中把一种雀儿叫“加拉啦”,把操难懂方言的人叫“哇达拉”,把“乌鸦”叫“老哇”,“青蛙”叫“癞呱呱”,“蝌蚪”叫“丁丁马勺(丁丁重叠是小的意思,马勺是形状的描述),“桌子”叫“桌桌”,“勺子”叫“勺勺”,小孩的棉背心叫“钻钻”。这些词汇表达不但生动、形象,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也透射出一分细腻。而“你胡不要闹(“不要”合音读为[pau])”将表否定的副词“不要”放在表方式副词“胡”之后,使普通话“不许!这般如此!”的表达改变为“这般如此,不许”![4]使祈使性表达委婉了许多。近在咫尺、远在天涯的青海人正是通过这深刻印在心灵深处的风格烙印、情感表达、寻找着乡音乡情,完成着族群、地域、身份的认同。
(二)存古性。方言是语言研究的活化石,方言记录了语言的历时和共时的变化,方言既能存古又能征古,折射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青海方言记录的语音、词汇、语法材料对研究方音、方言词汇和语法的历史演变以及与古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继承关系具有非常宝贵的参考价值。
青海方言“街”“杏”声母的读音很好得保留了古音声母g、h的读法,并反映了古今语音演变的规律:宋代始与g、k、h相拼的齐齿呼、撮口呼签的声母都变成了j、q、x。
青海方言古朴典雅,因其使用了一些古语词,如上古语词“绌”(缝制,《史记·赵世家》“黑齿雕题,却冠秫绌”)、“抟”(环绕、盘旋,《庄子·逍遥游》“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滑”(滑稽,《史记·樗里子传》“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还有中古语词如“央及”(请求,《救风尘》“我央及你救他一救”)、“阿门”(怎么,古书中叶作“阿莽”。《敦煌杂录·劝善文》“思量阿莽有慈悲”)、“得济”(得到好处、救济。《宋史·向宗回传》“岁饥,发廪兴力役,饥者得济”)。除此而外,还有13世纪后的中原官话词语。如:动弹(离开、行动,《水浒传》第27回“家无片瓦,动弹不得”),胡三(挥霍财务又做胡散,《儒林外史》第9回“凭者伙计胡三”)。[5]
(三)杂糅性。青海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元明时期逐步形成了以汉、回、藏、蒙古、土、撒拉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格局。民族的融合必然带来语言的接触、影响、融合,反映在语言上就是青海方言呈现出的杂糅性的特点。具体来说就是青海方言词汇中不仅有着各民族的词语的身影而且融合使用。如:青海方言中的“乌拉子(奴仆)”、“阿拉巴啦(凑合)”就是藏语词,“阿訇(伊斯兰教师)”、“赛俩姆(吉祥如意)”就是回族阿拉伯词语,“胡都”、“一挂”是土语词,“西纳哈”是蒙古语词。“倒多罗”,是汉藏语词的合用。“倒”是汉语词,“多罗”是藏语词头,倒多罗就是反过来的意思。“巴颜喀拉山”(富饶的青色的山)是蒙汉词语的合用。“孟达天池”则是撒拉与汉语的合用,“铜布、勺子、西纳哈(勺子)”则包含了藏语词、汉语词、蒙古语词。和”还有青海方言“你茶喝、馍馍吃!”s-o-v宾动式语法结构明显不是古汉语疑问句、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的影响,而是受藏语、土语常见的s-o-v宾动式语法结构的影响产生的。
二、青海方言使用现状及其成因
(一)青海方言使用现状
1.使用范围缩小。青海方言适用范围的缩小一方面表现在方言使用区域的缩小,另一方面表现在方言功能范围的缩小。前者表现为跨区域流动使人际交流无法用青海方言来实现而只能选择普通话。即使在原来青海方言使用频繁的农村,使用范围也出现了缩小的趋势。后者表现为在教学、宣传、工作、公众场合交际场合人们选择普通话。青海方言被限制在家庭生活和小聚居环境中。并且在家庭语言的使用中,为了构建孩子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许多父母也主动放弃了青海方言的使用。
2.使用人数减少。青海方言使用人数的减少表现在城市和农村使用青海方言的人在减少,能准确、完整使用地道青海方言的人更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能正常使用地道青海方言的是老人,能基本使用青海方言交流的是85前,90后勉强使用青海方言,00后则很少使用青海方言交流,10后则大多不会说青海方言。
3.代际传承断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评估语言活力最常用的指标是该语言能代代相传,语言的代际传承是评测语言活力的重要标准。青海方言代际传承的断裂表现为青海方言使用的老龄化和年轻一代不愿意使用青海方言,不能熟练使用或不能使用青海方言。
4.方言系统弱化。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方言系统各要素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方言系统的弱化是指青海方言与普通话和其他方言共存的过程中,受其他方言和普通话的影响,语音、词汇、语法呈现出向普通话靠拢,方言区别性特征削减[6]。“反映在语音上表现为发音的转变和声调的改变。反映在词汇上就是方言中过于土俗的或与普通话表述不一致的方言词语逐渐被普通话词语代替的现象。反映在语法上表现为方言表述方式向普通话表述方式靠近。”如青海话中“我”的读音为[n44]。方言使用者在交际中受交际对象普通话表述的影响,尽管方言声调不变,但改变读音学普通话读作[u214]。再如:在老青海人说“生、牲、栈、沾”和“声、升、占、战”时,有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之分,而年轻一代则无此分别,均读为舌尖后音。还有青海方言中过于土俗的词汇“记手(定情物)、顶缸(顶替)、落怜(可怜)”,以及语义表述与普通话不一致的“后楼(后楼在青海方言中有厕所的意思)、米汤”(米汤在青海话中有虚情假意面子上的话的意思,如灌米汤)被普通话词语代替。除此而外在语法方面的普通话倾向表现为青海方言句式与普通话句式的混合使用,呈现出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如下列一段对话:“王老师,你阿扎里去呢?(阿扎里去,青海方言o—v句式)我刚从大通来。(普通话句式)。[7]
(二)青海方言使用现状成因
1.社会的发展和需求
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人口迁移加剧,跨区域流动的加大,人际交往频繁。存在着很大差异的青海方言明显阻碍着人们的沟通和交流,为了满足人们日常交流,实现城镇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协调统一发展,人们必然选择一种超越青海方言障碍、便利交际的工具,于是对普通话的学习和使用便成为人们一种必然的选择,这使得青海方言的使用范围变小、人数变少。
2.普通话的推广
我国方言众多,不同方言之间日常交流的语言障碍不利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人际交往。我国在1955年就提出了推广普通话的政策。2000年颁布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言,规定党政机关公务用语、教育教学用语、宣传用语、汉语文出版物用语应当使用普通话。这使得普通话在正式、官方、公众场合的使用范围和频率加大和提高,而青海方言的使用范围和频率大大缩小和降低。
3.思想观念的影响
存在于同一社会的不同的语言,由于语言本身及外在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因素的作用,使得语言的功能不相一致,并最终导致语言使用中的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青海地处偏远地区,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经济、文化发展落后,这使得青海方言在与其他方言和民族共同语接触时缺少融合力,处于弱势,即使解放后新中国开发边疆,青海涌入大量外来方言,其弱势的状况也没有改变。这种经济、文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投射在语言心理上便形成了弱势语言心理,即认为青海方言土俗,劣与其他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使用青海方言无疑会标明自己在区域经济、文化上不发达的状况,于是在语言的使用上表现出对青海方言的一种有意识的疏离与鄙弃。
三、青海方言传承策略
(一)地方教育部门发挥主导作用、多措并举
方言的传承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普通话的推广有我国的《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强力支持,方言是一方之言,所以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使方言传承更具效力。同时可以多措并举促进传承。比如可以借助2008年国家语委和教育部开展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工作,2015年国家财政部支持、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实施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开展方言保护的工作,也可以设立方言传承部门、建立方言博物馆,保护以方言为载体的文艺形式。像青海花儿这种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独特艺术价值,但却受大众文化的冲击,陷入发展的一定瓶颈,面临被人忽视囧境的方言艺术,我们需要通过努力培养接班人,鼓励创新发展,引导大众的关注和喜爱,促其传承与发展,以此来促进青海方言的传承。
(二)学校提供方言学习平台和专业支持
现行的教育体制使人们从小到大都是普通话的教育,只有到大学,到大学中文专业,人们才能接受青海方言知识,故而青海方言教育严重缺失,方言意识淡漠。因此,学校要在各级教育中借助课程或校园文化活动融入青海方言的教育,提升青海方言的意识。学校方言教育离不开四个方面:一是对青海方言知识的传授。二是对青海方言价值与功能的阐明。青海方言是青海文化的载体,是青海语言研究的活化石,是普通话的源泉,是人们情感的系联。三是正确认识普通话与青海方言的辩证关系,改变错误认知。四合理依托语文教学,比如在大学依托专业教育或社团活动,在中学依托单元文化活动,比较青海方言与普通话的异同、体味语言与文化多样的发展。
青海方言的研究与传承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培养,也离不开专业的支持。所以我们要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同时通过经验丰富的专家和训练有素的学者对青海方言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要利用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等方法对青海方言进行多元化的研究,要对不同等级的青海方言进行相应的挖掘、整理并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还要注重技术的研发,收集方言影像资料、建立方言数据库,助力青海方言的传承。
(三)媒体助力方言传承
青海方言缺少书面语的传播,媒体的发展与完善因此成为青海方言传承的重要平台。电视、广播和互联网作为老少皆宜的大众媒体,对青海方言的宣传与辐射不容忽视。因此,作为广播电视媒体在把握传播力度和传播范围的基础上,要注重青海方言节目的丰富多样性。比如可通过讲述青海风土人情、青海方言老话,播放青海方言戏曲、方言影视剧、方言歌曲以及融入了青海方言因素的小品、相声,开设青海方言专栏邀请专业人士普及青海方言知识等,以此突破青海方言的地域限制,扩大人们与青海方言的接触,潜移默化青海方言的影响。新媒体技术则可以鼓励大众利用社交媒体软件和短视频平台制作高质量的科普推文和青海方言音频作品,助力青海方言的传承。当然,无论何种媒体的助力都离不开青海方言文化内涵的挖掘和高质量的追求。
(四)营造方言氛围和传承意识
青海方言的传承还少不了社会的支持,社会要努力营造青海方言氛围。比如可以集中社区青海方言优势,开展社区青海方言建设;可以建立青海方言主题公园,方便群众青海方言习得、交流;可以打造青海方言文创产品,设计新颖时尚的书签、文化衫、帆布袋、微信表情包等文创产品,体现青海方言特色和方言文化,激发民众青海方言兴趣;还可以组织有关青海方言传承的公众活动,拓宽民众接触青海方言的途径,发挥民众使用青海方言的主观能动性,增强民众传承青海方言的责任感。
青海方言使用的最小单位是个人,最基本社会单位是家庭。青海方言代际传承的断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人、家庭青海方言传承意识的缺失。要构建家庭和个人的青海方言传承意识,个人和家庭首先要建立正确的语言观,摒弃方言劣势和劣势方言心理,重视青海方言的价值,改变对青海方言的鄙视、冷漠、无感。其次要注重青海方言的代际传承,父母要有意识的使用青海方言,影响和培养子女青海方言的习得和能力,子女要有青海方言学习意识,要向父母及家中的长辈学习使用青海方言。
总之,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言是汉语的有机整体,方言具有不容忽视的语言价值、文化价值、情感价值。坚持社会语言生活多样性,构建和谐社会语言生活都离不开对方言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