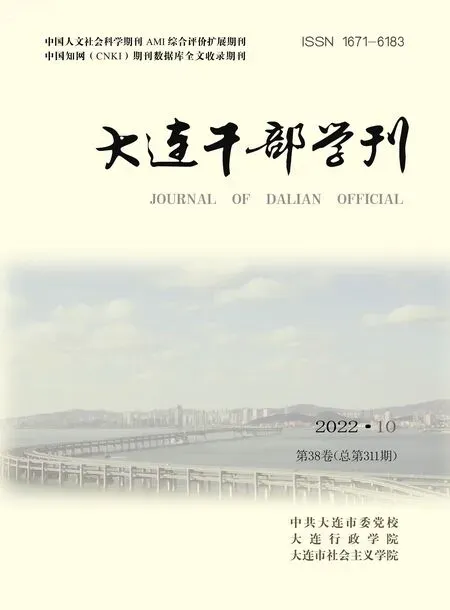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再探
——回应西方学者对 《国家与革命》的质疑
冯婉玲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列宁的 《国家与革命》集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革命理论,这一经典著作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对 《国家与革命》提出了各种质疑,本文拟就国家职能理论方面的主要质疑进行分析与回应。
列宁在 《国家与革命》中,根据马克思的 《法兰西内战》和 《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以下简称 《起源》)和《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中的相关论述,阐述了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镇压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专政职能;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过渡型国家(“半国家”),发挥 “镇压剥削者反抗”,以及 “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 ‘调整’社会主义经济”[1]24的职能作用;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经济高度发达,个人全面发展,人民自主参与社会管理,不需要任何暴力、强制和服从,阶级消灭,国家消亡。对于这些论述,西方学者提出了诸多质疑。泰克西埃质疑列宁背离了恩格斯的思想,忽视了国家的治理职能;诺曼·莱文质疑列宁背离了马克思关于 “市民社会才是社会立法和管理源泉”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职能理论,对列宁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都存在不少曲解或误读,但他们的质疑当中也有不少值得反思之处。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对于正确认识当代国家的职能作用,以及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西方学者对 《国家与革命》中国家职能理论的质疑
法国哲学家雅克·泰克西埃 (Jacques Texier)在 《马克思恩格斯论革命与民主》一书中,详细解读和评析了 《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他批评列宁没能正确理解恩格斯关于国家职能作用的论述,忽视了国家的治理职能。泰克西埃指出,恩格斯认为国家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以及同社会异化之前,具有负责维护氏族公社和公共利益的治理职能。统治阶级在刚刚获得统治地位之后,为了巩固政权都会注意维护社会秩序,建立法制;在政权巩固时期,为了抑制冲突,避免无谓斗争,也会注重建立一种共同的生活秩序。例如,在 《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强调,“只有当国家能有效地确保社会职能,国家的暴力才具有合法性。……在印度帝国,国家的合法性基本上来自灌溉工程承包者的职能。”[2]203统治阶级虽然倾向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但为了确保阶级统治的稳固,会注意平衡社会各方利益,以巩固国家权力。由此可见,恩格斯重视国家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治理职能。
泰克西埃批评列宁对于 “秩序”的理解,以及对于国家职能的理解过于狭隘,偏离了恩格斯的原意。他认为恩格斯所说的 “秩序”是社会公共生活的秩序,而列宁把它狭隘地理解为使统治阶级的压迫合法化固定化的秩序;恩格斯认为国家不仅具有专政职能,而且还有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的治理职能,但列宁只强调国家的专政职能,忽视了国家的治理职能。
主张 “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美国历史学教授诺曼·莱文 (Norman Levine),在 《列宁国家思想来源的探询》一文中,批评列宁继承了恩格斯的 “阶级——国家”理论,而背离了马克思的 “社会——国家”理论。他认为, “马克思想要一种民主的和大众控制的政治、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区别于建立在生产方式和分配上的少数所有者阶级和国家。”[3]马克思认为,即使阶级和国家消亡了,政治需要仍然存在。而恩格斯在 《起源》中,却以为只要消灭阶级就不仅可以消灭国家,而且可以废除一切政治需要。诺曼·莱文认为,列宁由于没有接触到马克思阐述 “社会——国家”理论的重要文本,包括 《巴黎手稿》《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等,所以没能理解马克思把国家视为社会反思物的 “社会——国家”理论。恩格斯的 《起源》及其论述的 “阶级——国家”理论却深刻地影响了列宁。恩格斯的 《反杜林论》使列宁把共产主义等同于无政府主义,以为共产主义社会不再需要政治。诺曼·莱文认为,由于列宁的思想中缺乏马克思的政治观念,所以他在俄国建构的帝国主义国家显示出 “极权本质”。
在随后发表的 《列宁 〈国家与革命〉再讨论》一文中,诺曼·莱文继续阐发上述文章的观点。诺曼·莱文认为,马克思在1843年至1845年的7篇著作中阐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别,以及社会治理理论,但列宁只阅读了其中3篇①,因此没能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同时,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系的观点。马克思主张铲除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但保留并改造市民社会,以之作为社会立法和管理的源泉。市民社会才是实现完全民主的唯一可能的地方, “市民社会包含着各种结构和社会团体,它们能够建立社会规则并消除矛盾和摩擦”[4]。诺曼·莱文认为,列宁没能阅读马克思早期关于社会治理方面的著作,因此他与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存在重大差异, “马克思重视市民社会对自身的治理,而列宁则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处于所有治理阶段以后的状态,看作是一个消除了市民社会立法以后的、只剩下核算和管理规则的社会状态”[4]。
二、对西方学者质疑的回应
泰克西埃和诺曼·莱文等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都把国家视为管理社会事务的主体,是否都重视国家的治理职能,以及对列宁是否继承或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存在争议。其实,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存在不少曲解或误读,他们过于夸大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职能论述的区别,但却忽视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别,忽视了资产阶级国家与无产阶级国家职能作用的区别。
(一)列宁深刻把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准确阐明了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核心职能是阶级专政职能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著作中论述国家职能作用的侧重点有些不同,但并没有如诺曼·莱文所说的那样存在 “重大分歧”。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国家,侧重揭露资产阶级国家宣称维护全体市民共同利益的虚伪性,强调市民社会对自身的治理;恩格斯为了完整揭示国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论述了国家在产生之初,作为社会管理的公共机构,具有治理职能。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职能的某些论述的侧重点有些不同,但在 《共产党宣言》《起源》《反杜林论》等公开发表和广泛传播的代表性著作中,他们都主要强调了阶级社会中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的工具,强调国家的专政职能。 《起源》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所写的关于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 《古代社会》一书之摘要写成的。可以说,《起源》不完全是恩格斯的独创,而是两人 “共同合作”的一个代表性著作。在 《起源》中,恩格斯指出,国家是 “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 ‘秩序’以内。”[5]189正如列宁在 《国家与革命》中解释道,统治阶级要维护的 “秩序”是阶级统治的 “秩序”。为此,统治阶级可能会利用国家机关来软硬兼施地达到维护秩序的目的,既发挥国家镇压被剥削阶级的专政职能,也发挥其维护社会稳定的治理职能。正如泰克西埃也指出,在 《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强调 “只有当国家能有效地确保社会职能,国家的暴力才具有合法性。”[2]203可见,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首先是为了确保阶级统治的稳固。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提到路易·波拿巴统治下的行政机构掌控国家权力,维持社会公共秩序。在敌对阶级的力量相对平衡的时期,国家似乎独立于各阶级之上,发挥治理职能,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 “调停者”。然而,正如列宁指出,这其实是因为资产阶级要维持政治和经济特权,必须以恢复社会秩序为前提,因此才在特殊时期放弃对国家机器的直接控制。
综上所述,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著作中对国家职能作用的论述之侧重点有些不同,但总体上看,他们都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的国家一般都具有专政职能和治理职能。他们都把专政职能作为国家的根本职能,即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最主要的职能和作用是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同时,他们把治理职能作为从属职能或次要职能,即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维护阶级统治而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因此,列宁在分析阶级社会中的国家,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本质及国家职能时,着重分析其阶级统治的本质及阶级专政职能,强调资产阶级国家是剥削和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不仅没有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而且准确把握并忠实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
(二)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需要无产阶级国家,列宁阐明了无产阶级国家作为“半国家”,具有镇压剥削者与 “调整”社会主义经济的职能
诺曼·莱文质疑列宁没有阅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然而, “列宁实际上知道四本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是诺曼·莱文所说的三本”②。诺曼·莱文批评《国家与革命》的写作准备材料 《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又称 “蓝皮笔记”)没有囊括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然而,列宁在这本笔记中所选取的文献主要是围绕反驳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澄清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理论这个主题展开的。虽然这本笔记没有囊括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国家问题的所有著作,但已经把相关的最主要的代表性著作都摘录了。
诺曼·莱文认为,马克思主张 “无产阶级革命会消除国家和阶级,市民社会则保存下来”[5],市民社会的社会团体和机构自行立法,自主管理。然而,马克思没有笼统地谈论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国家。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需要过渡型国家 (无产阶级国家或 “半国家”),直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无产阶级国家自行消亡。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本蓝皮笔记中,对 《哥达纲领批判》作了详细的摘录和批注,尤其重点批注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需要“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前是 “长久阵痛”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第一阶段)还没完全超出 “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权利眼界”,分配的不平等仍然严重,还存在强制;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阶段,“劳动成了需要,没有任何强制”[1]159-164等论述。列宁根据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把国家的发展与消亡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 “长久阵痛”时期,需要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剥削阶级的国家。第二个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需要过渡型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这不同于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不同于剥削阶级的国家。第三个时期,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不需要国家,国家消亡[1]161-162。
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社会主义社会) “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6]434。正是因为这些资本主义残余 (包括盈利至上的经济原则,见利忘义的道德风气等)还存在,所以资本主义很容易 “死灰复燃”,源源不断产生新的 “剥削者”。马克思还提到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存在 “资产阶级权利”,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 “资产阶级权利”是指交换价值基础上的平等权利。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 “按劳分配”,体现了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 “平等的权利”,但这种 “平等的权利”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事实上存在自然差别和社会差别的各不相同的人身上,因而事实上还存在着不平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个人普遍实现了全面发展,自然差别和社会差别缩小,劳动成了生活第一需要,这时才能 “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视野”。因此,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需要无产阶级国家,以之消除 “资本主义残余”,缩小 “事实上的不平等”。列宁结合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在 《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 ‘调整’社会主义经济”[1]24。列宁在此深刻领悟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需要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阐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具有 “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 “调整”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职能。事实上,的确只有坚持 “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 “调整”社会主义经济,才能不断消除 “资本主义的残余”,缩小 “事实上的不平等”,从而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综上所述,诺曼·莱文提到的马克思主张铲除资产阶级国家后,就不再需要任何性质的国家,就可以完全实现市民社会的社会自治之说法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实际上,诺曼·莱文忽视了共产主义发展的阶段性,而且把国家治理与社会自治视为简单对立。他先验性地预测社会是天然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调节潜力的有机体,以为推翻了国家的管制,社会就能实现良好的自治,然而,国家治理与社会自治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依存的、辩证的关系。列宁不仅没有背离马克思的思想,而且准确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无产阶级国家的重要职能。
(三)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职能理论,阐明了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职能的区别,以及无产阶级国家专政职能与治理职能的辩证关系
泰克西埃质疑列宁只是重视国家的专政职能,忽视了国家的治理职能,这个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泰克西埃首先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他只是评析了 《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并未注意到在后面几章列宁对无产阶级国家职能作用的论述。在 《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列宁为了批判机会主义者所宣扬的国家独立于各阶级,调和各阶级利益的 “阶级调和论”,强调阶级社会中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阶级专政的职能。这里提到的国家是指剥削阶级的国家,尤其是指资产阶级国家。在 《国家与革命》后面的第二至第五章,谈到无产阶级国家时,列宁论述了无产阶级国家作为过渡型的国家,不仅具有镇压剥削者的专政职能,而且具有“调整”社会主义经济的治理职能。
泰克西埃不仅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而且忽视了国家的阶级性,忽视了无产阶级国家职能与资产阶级国家职能的区别。列宁结合恩格斯 《起源》中的论述,论证了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剥削和镇压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职能。由于资产阶级只占人口的少数,资产阶级的镇压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所以这种镇压是血腥和残酷的。无产阶级国家作为过渡型的国家或 “半国家”,不同于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不同于剥削阶级的国家),尤其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的镇压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镇压,因此这是“一件很容易、很简单和很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流的少得多”[1]86,只需要有简单的国家 “机器”,简单的武装群众组织。列宁还指出,对于 “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极端行动”是需要镇压的,但这种极端行动产生的 “根本原因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极端行动就必然开始 ‘消亡’……这种行动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消亡”[1]87。可见,列宁认为镇压剥削者和极端行动是必要的,但镇压只是必要手段,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消除产生剥削者和极端行动的社会原因,即 “调整”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才能消除剥削消灭贫困。列宁的这些论述不仅阐明了无产阶级国家职能与资产阶级国家职能的区别,而且阐明了无产阶级国家的专政职能和治理职能具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内在关系。一方面,无产阶级国家只有坚持发挥镇压剥削者和敌对势力的专政职能,才能保卫无产阶级政权,保障治理职能之正常发挥;另一方面,只有充分发挥国家的治理职能,不断 “调整”经济始终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真正消除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最终废除一切暴力和强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运动刚刚兴起,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为了指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着重论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专政职能。列宁在帝国主义战争激化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历史时期,为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国家建设,论证了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职能作用的区别,并论证了无产阶级国家专政职能与治理职能的辩证关系,论述了 “调整”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重要职能,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的重大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的当代思考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对于正确认识当代社会的国家职能,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不能脱离国家的阶级性质来认识国家的职能作用
泰克西埃忽视了国家的阶级性,忽视了资产阶级国家职能与无产阶级国家职能的区别,因而曲解和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职能理论。马克思主义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国家的根本职能和主要作用。资产阶级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其最主要的职能和作用是维护资产阶级富人群体的利益;无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维护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正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政府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长期以来,我国坚持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脱贫致富,成绩有目共睹。据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有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我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实行免费医疗,设立专门医院,应查尽查,应收尽收,有效控制了疫情。这与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极少数利益群体的利益或为了眼前的政治利益,强行复工复产,举办大型活动,导致疫情迅速蔓延,病亡人数不断攀升,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现代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国家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能形式与以往相比有所不同,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阶级本质和主要职能的论述并没有过时。国家的阶级性质依然是我们观察分析当代社会不同国家的本质及其职能作用的重要依据。
(二)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来认识无产阶级国家的职能作用
诺曼·莱文忽视了共产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因而曲解和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职能理论,忽视了无产阶级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职能作用。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分析方法,具体分析无产阶级国家的发展与消亡的历史过程,具体分析无产阶级国家的职能作用。列宁在 《国家与革命》中阐明了在社会主义阶段,镇压剥削者和 “调整”社会主义经济都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重要职能,两者相辅相成。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把 “剥夺剥夺者和镇压他们的反抗”作为首要任务。1918年4月,当苏维埃政权初步巩固后,列宁在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提出,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他指出, “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7]168。然而,随后三年,苏维埃俄国遭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武装干涉,因而不得不继续把保卫苏维埃政权作为工作重心。1920年11月,在反对武装干涉的战争结束时,列宁在 《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讲话》中指出, “应当做到把全部热情和纪律都转而用于和平经济建设的工作”[8]7。列宁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都证明了镇压剥削者和敌对势力,以及 “调整”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都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重要职能和任务,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工作侧重点不同。
总体来看,在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经济始终保持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主要职能和核心任务,但阶级专政的职能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基本职能和必要任务。在全球化时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还存在不可消除的对抗与斗争。因此,我国在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与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
(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职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虽然泰克西埃、诺曼·莱文等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职能理论存在不少曲解或误读,对列宁的质疑和批评有失偏颇,但他们的质疑当中也有一些观点值得深入反思与借鉴。泰克西埃关于重视并合理发挥国家在维护公共秩序方面的治理职能;诺曼·莱文关于发挥社会团体和公益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协调作用,建立社会规则,消除社会矛盾和摩擦等观点,对于我国在新时期改革完善政府的治理职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实际上,马克思正是从 “社会——阶级——国家”三者的互动关系中来分析国家的产生、发展与消亡,来具体分析国家的性质和职能及其发展变化。在以往的剥削阶级社会中,国家与社会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立关系,这实质上是占人口少数的统治阶级与占人口多数的被统治阶级的对立。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代表人民利益,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国家与社会的真正和谐统一、良性互动、协同共治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改变,人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各类社会组织日益增加,各类市场主体不断发展成熟,因此迫切需要理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完善政府的治理职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和基础,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职能,逐步推进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建共治共享,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注释:
①诺曼·莱文认为列宁只是阅读了马克思的 《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和 《神圣家族》这三本著作,剩下四本著作,包括 《评一个普鲁士人的 〈普鲁士王国和社会改革〉》 《詹姆斯·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 《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因为列宁生前未出版,所以列宁并未阅读。
②胡兵经过考证,在 《列宁 〈国家与革命〉研究读本》一书中指出,列宁知道马克思的 《评一个普鲁士人的 〈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