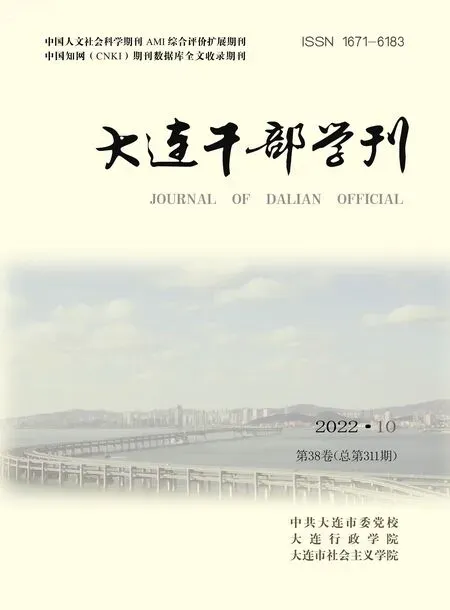大革命时期广州国民政府对广东南路乡村社会冲突的干预
梁小娟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湛江 524037)
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国民政府,前身是1923 年建立的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 (大元帅府),是中国国民党于1925年7月在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的基础上改组后建立的政权。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国民党扶持农运的系列新措出台,建立起了国共两党与农民的合作关系,农民加盟了有工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阵营,这对后来广州国民政府统一东江南路,统一广东,稳固国共合作基础,推动国民革命发展无疑是有巨大积极作用的。但农运新措的出台及推进同时也触动了乡村传统政治权力利益结构,触发了乡村政治权益的重新分配,引发了频繁的乡村社会冲突。据广东省农民协会统计:1926年1月至3月,广东乡村可统计发生案件共164 起,其中政治方面案件有88 起,占案件比例的53%;经济方面案件有37起,占案件比例的22%;教育方面案件有12起,占案件比例的7%;会务方面案件有18 起,占案件比例的13%;其他方面案件9 起,占案件比例的5%[1]。随着北伐的进行,乡村社会权益的重新分配引起的冲突愈加频繁,广州国民政府对此缺乏充分的应对,最终导致革命统一战线阵营的分裂和国共合作的结束。考察大革命时期广东南路乡村社会冲突及国民政府的干预,可进一步探讨国共两党与农民的合作关系,总结历史经验和智慧,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借鉴。
一、扶农新措在广东南路乡村社会的局部尝试
国民党在农运问题上经历过两次大转变。第一次转变 (1919 年五四运动至1924 年1 月国民党“一大”),历时4年8个月,国民党由不搞农运转为扶助农运,并由此得到农民的热烈支持和拥护,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第二次转变 (1924年1月至1927年4月),历时3年4个月,国民党由扶助农运转为镇压农运,终因丢弃农民而埋下了国民党日后失败的祸根。
1924年1月国民党 “一大”后至1925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南征前,国民党中央作出了系列扶农决策。国民党 “一大”确定扶农政策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1月31日决定设立专理农民事宜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2 月20 日明确中央农民部职责;3月19日国民党中央审议通过了农民部所提的“农民运动计划案”,派员至各地支持组织自耕农、佃农、雇农等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团;1924年7月至1926年9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共举办了六期农民运动讲习班,毕业学员772人[2]140,分派到广东各地开展乡村动员。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领导人热情投入宣传组织农民工作中并两次发表政府对农民运动宣言,坚决执行国民党 “一大”决定的扶助农运的政策,坚决打击压制农运的恶势力,坚决维护农会和农民的利益,国民党与农民关系进入最好时期。国民党的系列扶农举措虽未直接公开触动土地问题,但国民党领导人扶农态度,国民党赋予农会的特许农民建立农会组织,组建农民自卫军,以及有警告、控告和解决地税问题等权利,给予弱势农民群体的权益诉求权和阶级认知唤醒的同时,也是对地主豪绅和民团等强势权势阶层原有的垄断性权益的否定,从而激起农村权势阶层的强烈反对。因此,国民党对农村土地问题的刻意回避,使原拥有垄断性权益群体与农民之间所激起的社会冲突无法避免。
1924年1月国民党 “一大”后至1925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南征前,在国民党扶农政策影响下,南路乡村的地方军阀、县长、地主、土豪劣绅民团、土匪等权势阶层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为公开的局部冲突。据黄学增1926 年初调查:南路地区农村社会阶层有田主 (地主)、农民,农民人数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六以上,有自耕农 (占总数的2/10),有半自耕农 (占总数的2.5/10),有佃农(占总数的4/10),有雇农 (占总数的1.5/10)[3]。南路各属县城乡村设有民团局。民团是乡村土豪劣绅的保镖,土豪劣绅既借民团之助以维持他们的地位与权力,又进而利用民团抽剥农民。乡村的传统统治者有大地主、官僚、失势军阀,民团是他们在乡村统治的机关。民团分子不外乎土豪、劣绅、土匪三者,他们的权力之大可以支配全县行政,甚至县长亦须依赖他们,不良的驻防军队也与他们勾结为恶。此种状况不独佃农受其害,自耕农、小地主亦难免涂炭[4]272。在南路,民团县称为民团总局,区称为某区民团局,乡称为某乡乡团局,局内设有数量不等的团兵,拥护局长局董 (皆绅士)坐局苛抽农民,以保护地主之利益。地方军阀、县长、地主与团局、土匪等构成的农村权势阶层垄断压榨农民利益,农民敢怒不敢言,乡村社会中暗藏的冲突一触即发。
1924年11月,广州农讲所第二届海康籍学员黄杰、遂溪籍学员陈钧达受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遣返回雷州秘密开展动员农民工作。当时,南路军阀邓本殷党羽邓承荪与土豪劣绅胁迫雷州农民弃水稻种植鸦片,雷州一、四、六区各乡受害最深,引起当地农民的强烈不满。黄杰下到乡村基层,秘密动员一、四、六区等41个乡的农民建立起了南路最早的农会。县长陈炳焱发觉此事后,声言要扣押黄杰、陈钧达等 “运动农民者”,农会活动因此受阻。1925年6 月至秋天,韩盈 (中共党员)、黄广渊、薛文藻 (中共党员)、苏天春 (中共党员)等先后返回遂溪、雷州,组织了 “雷州青年同志社”乐民分社和纪家分社,在遂溪乐民组织了五个农会,组织了农民自卫军70余人[2]18。10月中旬,国民党员黄河沣由广州回到本乡海山村,即投靠广州湾法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邓本殷,勾结该乡劣绅黄树滋、陈光烈、乐民区长黄仲龄,破坏农会活动,强行解散 “雷州青年同志社乐民分社”和第一、二、三乡农民协会与农民自卫军,派人殴伤会员10 多人,军阀邓本殷同时呼应,派某团驻扎乐民监视农民。黄河沣、黄树滋又将黄广渊等人密告于邓本殷,在海康、遂溪从事农运的韩盈等9人受到通缉。由此可见,1925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南征前,由于南路地区尚处于地方军阀统治之下,国民党的扶农举措在南路的局部尝试没有得到更多的支持,农民权益诉求和阶级认知的活动遭到了地方军阀、土豪劣绅民团勾结的强势势力的打压,而国民党人解决乡村社会冲突的方式是通过投靠帝国主义,联合地方军阀和劣绅打压农会,这说明了扶农举措在国民党内部并未完全达成共识。
二、南征与广东南路农运的快速发展
1925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南征至1926年7月北伐前,国民党中央继续执行扶农政策,在共产党人有效动员组织下,广东各地农民协会纷纷成立,农运呈现出强劲发展的势头,农民协会组织的建立以及系列活动达到鼎盛时期。但1926年3 月广东统一后,国民党内部和乡村反农势力日益增长,指责农运 “幼稚”和攻击农会是 “土匪”的声浪开始出现,国民党对乡村冲突表现软弱,国民党与农民关系出现严重裂痕。特别是1926年3月和5月连续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广东各地乡村到处弥漫着排共反农信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被迫退出中央农民部。北伐前夕,刚掌握党政军大权不久的蒋介石公开宣布禁止农会自由,在国民党的公开抑制下,乡村地主劣绅民团等强势权势打压破坏农会的恶性事件不断增加,农运形势开始变得严峻。
1925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南征讨伐邓本殷至1926年3月南征取得胜利期间,南路军阀邓本殷及其八属联军被打败,南路各地土匪被逐渐肃清,南路乡村传统权益的强势势力被削弱。同时,在南征军、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对扶农政策的传播,南路军的支持和共产党人的深入动员下,南路农运快速发展,特别是1926 年3 月,广东省农协南路办事处 (地址在梅菉市)成立后,与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合署办公,指导南路农民运动,使南路农民运动获得公开合法的发展机会,而各地农会的兴起为农民开辟了一条权益保护的渠道,共产党人组织农民开展铲除贪官污吏和劣绅土豪,废除苛捐杂税等系列权益诉求活动。1926年2月5日,遂溪县界炮群众冲进界炮团局,将为恶乡里的保卫局长、土豪杨文川拉出痛打。同月,共产党员韩盈等人发动组织2000多人到遂溪县城游行示威,逼使县长伍横贯承诺减免煤油和猪牛捐税。遂溪县农协筹备会配合县政府除暴安良,枪毙土豪黄景星,逮捕并严处四区北降村民团长、恶霸谢拨韦。3月底,南路办事处把利用宗族关系钻进农会的海康县大地主卓子藩逐出农会。同月,黄学增带领吴川农民向县长苏鹗元要求取消蒜头捐、蒜串捐、壳灰 (肥料)捐,取得胜利。3至4月间,遂溪县各区解散民团,收缴了民团枪支,建立起农民自卫军,遂溪县一、二、四、六区都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拥有枪支700多杆。遂溪县农协联合各界,向省政府上控贪劣失职的遂溪县县长伍横贯,伍横贯被革职。6月,遂溪县第七区农民协会呈文县政府,查办了横行不法的警察署长李成林。同月,遂溪县农民协会联合各会联名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央组织部揭露控告了贪污无耻的官僚政客徐闻县县长谭鸿任。
国民党的扶农新措对南路农村社会的地主土豪劣绅和民团等权势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被剥夺感和群体心理恐慌的双重压力下,他们一方面通过内部诉求,在国共两党的权力中间寻求国民党内部反共势力的支持以应对权益危机;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寻求新的组织渠道和政治庇护,如利用农民中的宗族观念,戴上假面具,混入农民协会,充当会员,甚至窃取领导职务,把持农会。化县一些区、乡民团团董,为了保持其统治地位和剥削手段,甚至请求将其民团改名为 “农民自卫军”,还要求主持兴办 “农民协会”。这种现象其他各县亦有发生。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此阶段对南路乡村社会冲突处理态度总体来说是积极的,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议确定: “中国国民党无论何时何地皆当以农民运动为基础,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亦当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的政策首须着眼于农民利益之本身,政府之行动亦须根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5]27。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也存在着排斥共产党和农会的信息,如南征军收复南路时,南路县长的安排主要由国民党广东省民政厅、南路行政委员会 (主任甘乃光)从广州委派这些新的南路之县长到任,许多人原来就是当地的豪绅,他们到任后,继续维持邓本殷统治时期的反动统治,对农民运动采取消极态度,有的甚至和当地土豪劣绅勾结起来,反对或压制农民。驻扎在南路各县的南征军第十一师师长陈铭枢,甚至有意包庇旧势力与农会对抗;海康县的洪钟鎏,利用其国民党员的身份,组织 “雷州革命同志社”,对抗共产党人组织的 “雷州青年同志社”,唆使无知学生到县署和驻军师部诬告农民暴动和殴打学生。在海康县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巡行大会上,又率领无知学生高呼 “打倒工会、农会”的口号;到处造谣诬蔑农会和工会是土匪。对于这些行径,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及时处理,报省党部将 “雷州革命同志社”解散。
农民运动是国民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冲突事件中,国民党理应支持农会抗击 “土豪劣绅”。但是,1926 年3 月、5 月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有些地方开始出布告限制农民开会游行,出现了 “农民协会不日由政府明令解散” “国民党已取消农工政策”的谣传,并且国民党内有人提议农运应受限制,国民党中央在公开的决议和宣言中,总体上也是倾向于支持农民和农会的,但与军政官员的利益追求并不一致,难以避免受到他们的反对。
三、北伐后打压农运抑或扶持农运的矛盾
1926年7月北伐后至1927年 “四一二”政变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陷入打压农运抑或扶持农运的矛盾。此时,国民党仍表示继续扶农,并发表了扶农的第三次宣言,但只是口头宣言,没有具体有力的执行措施。北伐开始后,革命重心转移出广东,党政军中敌视农运的势力趁机拼命打压农会、农民自卫军,国民党反农势力各县县长、各地驻防军更是借口 “维持后方治安”来限制农运,剥夺农民集会巡行自由,农民开会是 “聚众滋事”,与土豪劣绅争斗说是 “扰乱北伐后方”,农运陷于困难境地。土豪劣绅民团也趁机发起猛烈进攻,冲突事件愈发增多,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处置力度明显减弱,共产党人被迫退出省农民部,农运日渐消沉。
广东南路的国民党组织,曾经在南路以农运为中心的国民革命中,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国民党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革命组织,一些失势官吏、政客、地主土豪劣绅混入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升官发财、把持党务,他们害怕和仇视农运,当乡村社会的冲突触及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同地方反农反共势力、驻防军军官勾结起来,破坏和反对农运。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南路办事处和各县农运利用合法的地位,更加深入进行动员组织农会,扩大农会,争取权益。国民政府对农村权势阶层与农会之间的冲突危机不能形成统一的干预行动时,就有可能宣泄成流血冲突。
北伐开始前后,乡村权势阶层仇视农运的势力更加嚣张,对农会发动了猛烈攻击。1926年6月至8月间,电白县连续发生地主民团包围农会,抢掠农民,火烧民屋,捕禁吊打农会积极分子的事件多起,甚至暗遣凶手,谋杀农会职员和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县长杨锡录支持土豪劣绅重建 “联团”对抗农会。地主土豪秘密从香港偷运回武器, “企图扑灭农民协会,使农民协会永不发生于电白境内”[2]140。对此,黄学增写了 《为电白农民求救》一文,愤怒地揭露了电白县地主土豪和民团破坏农运的罪行:“国民党的政纲不是扶助农民的吗? 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一次、第二次宣言与夫迭次通令,不是给予农民以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并保护农民之利益的吗? 奈何两个月来电白的地方长官绝不惩戒或制止土豪劣绅地主们此种不法行为?”最后向国民政府提出了 “惩办土豪劣绅地主、解散不法民团、取消团局一切苛捐杂税、解散八堡会、赔偿农民损失”等五项要求。中共广东区委、广东省农民协会也致电电白农民,组织农民游行示威,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严惩摧残农运的土豪劣绅地主、右派官吏和不法军人,保护农民运动。
国民政府对南路乡村冲突事件的干预表现出两面性,既继续扶农又忽视对伤农事件的干预,以致土豪劣绅地主防军伤农事件连续发生。9月,海康发生了震动全省的程庚被杀案件。程庚是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海康从事农运工作,由于工作深入,甚有成效,遭到土豪劣绅怀恨。海康县县长苏民、驻海康防军营长陈公侠与劣绅邓志圣勾结,诬陷程庚 “引匪、济匪”,悍然下令将程庚枪杀[4]520。海康县农民协会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提出撤办县长苏民、驻防军营长、辑办劣绅、抚恤程庚家属等四项要求。一些国民党左派也批评国民党忽视农运的错误。在各方压力下,海康县长苏民不久去职,防军营长陈公侠亦奉命他调。南路程庚被杀案件,标志反农势力的攻击达到了疯狂的顶点,乡村权势阶层将屠刀举向第一线指挥农会的特派员,表明反农势力的增长和农会势力的下降。另有茂名茂南区莲塘县恶霸梁竹铭,既是大地主,又是团董,横霸一方,无恶不作。被扣押后释放,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国民政府对冲突事件的双面政策助长了乡村权势阶层在南路乡间变本加厉。1926 年夏秋之后,“驻防南路的陈济棠师长,他不但是收缴农会的枪支,解散农会组织,并无所顾忌地屠杀农民运动负责人。”[5]61电白民团进攻第二区农会;麻岗乡农会执行委员黄润延被民团枪杀;海康县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民团趁机联合,在驻防军的支持下,向农会发动进攻,先后发生了公平市农民自卫军被马村民团缴械,二、六、八区农会被命令解散,以及东门头、西村仔、东关等乡之农会会员被截殴、缴械、捆绑、囚禁的事件[5]61。所有这些事件,都说明了南路同广东各地一样,面对此起彼伏的冲突,国民政府未能制定出一套多方妥协的政治调解机制和有效控制,导致冲突愈发激烈,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已面临破裂。
四、国民政府干预冲突的失败
1927年 “四一二”政变至7月,国民党在南路各地的驻军与各县县长、地主土豪劣绅、民团组成的南路反农势力,掀起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屠杀农会会员和农会干部的恶浪。“四一二”事件后,就发生了 “四一六”阳江事件,县长陆嗣增、驻防军营长梁开晟、警察局局长梁鹤云派出军警包围了国民党县党部、农运特派处、工运特派处等,几天之内,被捕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达23 人。其他各区也纷纷追捕和屠杀农会会员。到阳江检查党务和农运的中央特派员梁本荣被捕,后与其余15人均于1928年被国民党杀害,阳江农运趋于停滞。高州、化县、电白、遂溪、海康、廉江、钦廉等地也连续发生事变,大批共产党员、农工运动干部和积极分子被逮捕屠杀,南路农运领导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已经无法进行对农运的领导。
由于国民政府未能确立农会在国民党政治结构中的权力定位,未能形成对应的制度安排,对革命统一战线中成分复杂的党政军权斗争缺乏足够的预判和掌控,对伤农冲突的容忍和敷衍政策,导致国民政府不能左右政局,导致乡村权势势力对扶农政策不以为然。由此可见,此时的国民政府还是一个弱势政权,对革命统一战线中成分复杂的党政军权斗争缺乏足够的预判和掌控,在国民革命和国民党党权向上发展的时候,在握有军政权强势势力的压力下最终丢弃了农民。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右派和乡村强势势力的暴力压制忍无可忍,对国民政府的处置行为彻底失望,1927年5月至9月,南路农民在“南路革命委员会”和南路特委的领导下,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斗争在南路各地爆发,先后组织发动了乐民起义和斜阳岛武装割据、东海仔暴动、吴梅农民自卫军战斗、廉江梧村垌农民暴动、茂名沙田暴动等系列武装反抗,标志着国民政府对南路乡村冲突的干预政策失败。
结 语
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国民党更多是决策层面者,有关农运的大政方针始终由国民党中央制定和掌握。据统计:国民党中央报告和讨论农民运动问题的会议和通过的决议案,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4年1月31日至1925年12月)共有48次会议72项决议案;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1926年1月至12月中央党部北迁前)共有27次会议32项决议案;中央政治委员会 (1924年7月至1926年6月)共有49次会议60项决议案;中央政治会议 (1926年7月至12月中央党部北迁前)共有35次会议86项决议案;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 (1926年12月至1927年4月广州清党反共前)共有19次会议72项决议案[4]15。有关农民政纲和政策,重大问题和事件的处置,都是由国民党中央决定,共产党更多是在基层组织的运作中发挥作用。国民党是政权、军队拥有者,但无农运人才,共产党有农运人才,但无政权和军队,两者合则两利,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农运人才,打开农运局面,巩固国民革命群众基础,促成和支持北伐,国民革命向前发展,共产党可在农运中壮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扶农政策的实施起推动和监督作用。因此,合作是对国共双方有利的事情,单方面有利的合作是难以成功的,南路农运、广东农运的崛起和发展,是国共双方合作的产物。国共双方合作最后走向低落和失败,是双方利益发生冲突后国民政府未能及时干预和正确协调的结果。
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南路农运虽然最后走向低落及失败,但历史实践为南路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传播了革命种子,革命虽然一度处于低潮,但斗争并未停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形势在南路的发展,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南路农运的实践,也为共产党人积累了维护农民政治和经济利益工作的经验和智慧,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时期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以及当前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