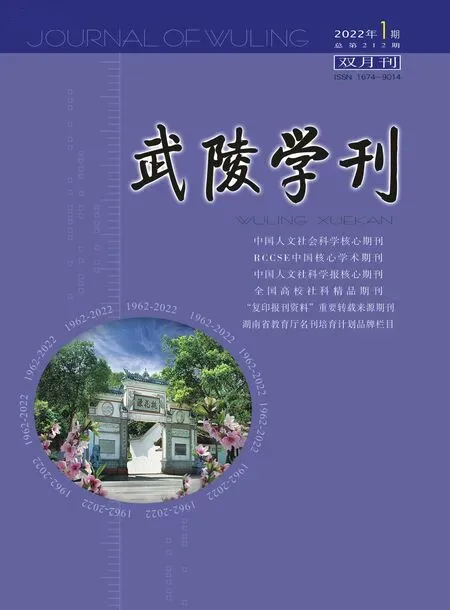语境诗学生成的历史逻辑与知识谱系
徐 杰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语境理论产生于人类学,滥觞于语言学。也可以说,语境更多的是语言学转向之中的新范式,而语境作为一种思维并非语言学转向才产生的。笔者在《语境诗学的哲学基础与学理合法性》中提出语境诗学,将语境作为文艺理论的元范畴,并以此为基点审视和反思传统文艺观念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建构一套迥异于传统的诗学论域[1];还在《空间的逻辑:文学语境空间层域的内部关系》中提出文学语境的“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维度及其内在关系[2]。梳理整个西方文艺理论史,我们发现语境意识和语境思维其实一直存在于整个文艺和美学思考之中,只是理论家侧重的内涵不同,并非以语境这个词来表述而已。无数的文学语境意识、观念和思想共同汇聚成为语境诗学的长河。我们对语境诗学生成的知识谱系进行考察,发现语境范畴的诗学维度与语言学维度有着相同的结构。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特别是语言学家胡壮麟先生对语境的划分,语境分为文本语境、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语言学从共时层面划定了语境的层域,我们则是从诗学的历史维度来寻找语境的内部、情境和外部维度的生成过程。文艺作品的“关系性”和“有机性”是语境的内部维度(文本语境)存在的思想基础。当外在于主体的自然和社会随着文论的发展试图等同于语境的内义时,文学的“自性”也借助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力量与之形成一种历史性的张力。情境哲学产生于从普遍世界情况到个体殊相(理念到实在)的过程,然而其背后的理念则使得语境陷入自反性的境地。
一、形式与关系:语境诗学内部维度的生成
语境论思维滋生于哲学家对原子论的逐渐摆脱和超越之中。“关系主义”认为美在数之间的关系(比例论),这推进了早期古希腊哲学家对世界本体的认识。早期古希腊哲学家对世界的本质探究着眼于自然事物及自身内部。不管是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还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毕达哥拉斯,艾菲斯学派的赫拉克利特,爱利亚学派的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认可世界的本质或基础原子是“不可分、不可穿透和单纯的原子”[3]。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弦乐之中发现当琴马置于弦的不同位置发出的音是不同的,优美的旋律则是其背后数的关系,就像罗素所说:“他把世界假想为原子的,把物体假想为是原子按各种不同形式排列起来而构成的分子所形成的。他希望以这种方式使算学成为物理学的以及美学的根本研究对象。”[4]数本身指称或代表的对象毫无意义,意义存在于数与数的关系之间。单个语言单位确实自带意义,但是文艺作品的意义存在于整体之中,存在于基本元素的搭配和关系之中。不是1+1=2的砌和关系,而是1+1>2的涌现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文艺的本质就在于数与数之间和谐匀称的关系。“没有一门艺术的产生不与比例有关,而比例正是存在于数之中。所以,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5]同样是“我”“等”“你”“吃”“饭”,五个字不同排列组合,其含义千差万别。字的意义是固定的,内包于语言千百年的约定俗成之中,可是字构成的句,句构成的段,段构成的章,都会以“意义溢出”的形式反叛着“语言的原子意义”。这种意义的涌现其本质就是作为整体性的语境生成的。
偏重对象内部形式和关系的语境思维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体现得更为体系化。在《诗学》之中,亚氏对悲剧的分析完全是从创制性知识的角度,而非理论性知识的角度进行研究,比如探讨“诗艺本身和诗的类型,每种类型的潜力,应如何组织情节才能写出优秀的诗作,诗的组成部分的数量和性质”[6]27等。悲剧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和规律成为他分析的核心,语境思维在亚氏看来是文本内部语境。文学自身的内在属性主要来自于诗歌反映事物的普遍性和因果性,而非像历史一样记载无必然性的具体事件。亚氏认为情节不应该出现这种意外情况,否则是对必然律或可然律的破坏。诗人对作品素材的选择,对作品形式的塑造和加工,使得诗从生活语境之中独立出来,形成自身的语境。什么是使作品成为这类艺术的关键,他认为是“媒介”“对象”和“方式”所营造的独有语境。诗人之所以是诗人,并非像柏拉图所说的作品对理念进行了模仿,而是因为他们都使用了格律文,如节奏、话语、音调的单用或混用。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作品要产生美,“不仅本体各部分的排列要适当,而且要有一定的、不是得之于偶然的体积,因为美取决于体积和顺序”[6]74。“排列”意味着诗艺之中的具体部分是遵从整个作品语境的。作品语境的整一性要求悲剧中任何事件严密绾和为整体,不能随意挪动或删减;如果可以,它就不是整体的一部分。
亚里士多德对作品内部语境的肯定直接影响到贺拉斯。古罗马时期,文艺理论家对具体的诗学技术的要求是以作品语境的协调为标准的,而不是外在的政治和道德诉求作为标准。贺拉斯认为艺术作品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精微的模仿对象,而在于作品内部的有机统合。比如他在谈及艾米留斯学校附近的拙劣的铜像工匠时,说他们对铜像细处的雕刻极为精美,但从整体语境角度审视,这些作品往往是失败的。同样在戏剧之中,“假如你把新的题材搬上舞台,假如你敢于创造新的人物,那么必须注意从头到尾要一致,不可自相矛盾”[7]97-100。人物性格和行为“一致性”其实就是在凸显作品自身作为一个有机语境。同时,文学文类构成自律性的语境,制约着遣词造句和风格选择。使用的语词一定要与文类语境相符合,其使用才是纯一的。比如悲剧的文类语境决定了诗句必然是与“轻浮”无缘的。
生命有机论和自然主义成为文艺复兴甚至启蒙运动时期文艺理论的底层代码。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理论透显着当时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尊崇,自然科技的发达将医学、自然和天文等知识话语融入了诗学话语之中。文艺复兴时代其实是在完成一种整体性的话语转型:从继承到创新,从文献到现实,从观察到实践。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研究偏重的是古代医学文献而非临床或生理学实验。医学人文主义者专注的是对阿拉伯医学的驱逐,并为希腊医学经典著作进行辩护。直到17世纪之后,此种趋势才逐渐让位于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和临床医生[8]115-116。这个时期的植物学家同样将目光聚焦于古代植物的图绘,而非“费心去观察生长在附近的草坪和森林中的花木”[8]119。如果说文艺复兴是一种从古代到现代的过渡的话,那么启蒙运动则是现代性话语的正式开启。启蒙运动时期,医学的进步成为科技革命的重要信心来源。这一时期医学并非仅仅是处理疾病的学问,而是哲学研究的基础和新哲学话语的标志。狄德罗翻译《医学辞典》时就说道:“没有当过解剖学家、博物学家、生理学家或医生的人,很难深入地思考形而上学或伦理学问题。”[9]可以说,医学话语直接影响到文艺话语。十七、十八世纪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美学家,对于艺术和美的论断都是以协调和统一作为标准的。笛卡尔认为:“美不在某一特殊部分闪烁,而在所有部分总起来看,彼此之间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协调和适中,没有一部分突出到压倒其他部分,以至失去其余部分的比例,损害全体结构的完美。”[10]生命有机论在牛顿力学的强大攻势之下,逐渐走向“生命物理主义”,物理世界的科学规律也适用于生命现象,甚至心灵内部的现象。当时的代表性著作《人是机器》正是体现了这一思想。自然主义在这种背景下被召唤出来应对机械主义的哲学,比如布封认为好的文学应该向大自然学习,是内在紧密关合的。大自然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完善,“那是因为每一个作品都是一个整体,因为大自然造物都依据一个永恒的计划,从来不离开一步;它不声不响地准备着它的产品的萌芽;它先以单一的动作草创任何一个生物的雏形;然后它以绵续不断的活动,在预定的时间内,发展这雏形,改善这雏形”[7]216。在这一点上面人类自身是无法比拟的,人类的精神永远无法和大自然相比,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来自经验和冥想,而这些经验又是在对大自然的摹仿中实现的。在自然主义之下,作品与自然的同构关系被提出来,语境与生态的隐喻关系第一次凸显。
在此背景之下,作为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文艺理论家代表,狄德罗是第一个将语境作为艺术哲学“元概念”的理论家。在狄德罗看来,关系(语境)不是简单的比较概念,而是一种“更具有哲理性,更符合一般的美的概念以及语言和事物的本质”[11]31。关于美的本质和根源,他认为如果只就个人喜欢的品质作为美的特性,便受限于空间和时间的某一点。相反如果将美归结于对关系的感觉,关于美的观念便是可以跨越时空的。狄德罗的关系将对象内部语境扩展到对象与主体之间的情境语境。他认为关系这个概念存在于两个层面:一个是客观存在的“能够唤起”的美,一个是“已经感觉到的”“关系到我的”美。前者“我的悟性不往物体里加进任何东西,也不从它那里取走任何东西”;后者相反,我们主动将判断和比较带入物与物的关系之中。“真实的美”是在一种作品内语境之中产生的美。孤立地观察一个对象,表面是切断了关系,实际上是在审视对象的内部组成之间的关系。当说花或鱼是美的时候,意味着我看到的是对象的“秩序、安排、对称、关系”。客观性的美存在于物体身上的内在关系之中,并非主体想象力对对象的虚构性赋予。“相对的美”则是外语境的扩展,从外部要素对作品进行的审美判断可谓千差万别。如果将花或鱼与其他同类联系起来并被言说为美的时候,意味着对象在主体心中唤起的关系的概念最多。外在关系的异质性,而非内在的同质性,故而对“美”效果不同,这便产生“相对的美”。随着美的对象的抽象化或具象化程度加深,其美丑判断会发生变化。
在狄德罗看来,美诞生于对关系语境的感知。美感的程度生成于作品关系语境的延展性和丰富度。首先随着作品语境扩延,作品意义逐渐充盈而具有美感。这种思维就是一种不断扩大对象参照语境的方式,进行审美判断。狄德罗以古罗马时代荷拉士悲剧为例来阐述此问题。老荷拉士的两儿子战死,被问及怎么样看待仅剩一个儿子的情况时,他说出了“让他死”。如果仅仅是“让他死”,三个字的关系没有美与丑;如果赋予其战争背景,可以引起兴趣;如果“他”指代的是被问者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这句话就成为精妙的话。“美总是随着关系而产生,而增长,而变化,而衰退,而消失。”[11]29与此同时,语境的层次越多,美感越强烈。“从单一的关系的感觉得来的美,往往小于从多种关系的感觉得来的美。一张美的面孔或一幅美的图画给人的感受比单纯一种颜色要多,星光闪闪的天空胜过蔚蓝的帷幕;风景胜过空旷的田野;建筑物胜过平平的空地;乐曲胜过单音。”[11]34文学作品的意义被多重语境赋予之后,其复杂性和丰富度带来作品美感的立体性。狄德罗“关系论”提出的思想背景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生命有机整体论和自然主义,比如他在论述人面孔的器官是否美时说道,天然歪的鼻子其周围器官的畸形弥补了鼻子的畸形,即它们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故而最完美的艺术作品都无法与大自然的创造相比。一个鼻子不单单是孤立存在的,还牵涉到周围生命组织;人工创造的作品永远不及自然生成的作品完美。文艺复兴时期对身体内部生命体内在联系的认识,对应于文学艺术作品内部的内在关联。启蒙时期艺术被认为是对真正美的扭曲和偏离,这使得文艺作品倾向于在走向自身之外的“自然状态”中寻找完美。
作为德国的天才式人物,歌德在论述文艺时依然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认为自然造物远远高于人工创制的作品,美的作品是以自然作品为判定标准。歌德的《拉奥孔》继承了前人对作品内部语境的思考,认为雕塑作品所呈现的身体也是一个绾合的整体。特别是当他谈及雕塑之中父亲被蛇咬的地方时,他认为“咬伤的那个点决定了肢体现在这样的运动,即上半身躲闪,腹部收缩,胸部隆起,肩和头下垂;我甚至觉得,面部一切表情也都是由眼前这一不期而遇的痛苦的刺激而决定的”[12]53。身体的一点刺激而牵动整个全身的动作网络,这其实是从作品内部语境来说明其各要素的内在关联。将这种语境思维扩大,如果整个作品作为一个点,这个点和与其有着隐秘关系的周遭环境之间也存在关系链。生命体的整体性投影和隐喻到整个文化语境。同时,我们的感官感觉总是在对立面之中感觉,比如痛苦消除之后的宁静,却令人有一种愉悦的感觉。身体的感知具有在“异质”他者之中产生自我的倾向,这也是语境论的感官隐喻基点。歌德创作了经典的《浮士德》,他对歌剧的理解和批评更有说服力。他认为经典的歌剧自身就是一个小语境(“小世界”),对歌剧的审美判断是按照语境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来进行的。因而,我们对于艺术作品的欣赏必然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并在此整体语境之中体验到整一有机的美感。艺术自身作为语境是区别于生活语境和自然环境的。雕刻的马不一定必须戴挽具,因为它遵循审美原则而非生活逻辑。艺术遵循美和愉悦的规则,生活强调正确和实用的规则。但是,正确的规则是大自然的外在表征,因为它是源自人们自身的感觉、经验和喜好制定的。“自然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则要求最严格的内在有机关系。”[12]161歌德清楚艺术与自然各自的界域,在各自语境之内遵循完全不同的逻辑。歌德不仅认为单个艺术作品是整一的语境,还认为由无数经典艺术作品构成的“艺术整体”也是一个语境,即复数的艺术语境。优秀的艺术作品审美性,其自身全息地包含着整个艺术作品之中的经典因素和普遍属性。“要想讨论一部杰出的艺术作品,几乎必须讨论整个艺术,因为一部杰出的艺术作品包含了艺术的整体,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一部艺术作品的特殊事例中得到普遍的结论。”[12]45文艺创作大多数并非如我们看上去的那样处处充满着天才式的灵感和卓越,更多地是在作品的不同要素的雕琢上强于其他作家而已。
二、价值与世界:语境诗学外部维度的源流
最早从价值语境维度来审视和判断事物的美学家要数赫拉克利特,他认为事物的本质并不在自身,而在于外在于事物的他者。纯粹的、独立的事物,其存在毫无意义,事物总是在对立面之中呈现自身的。“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疾病使健康成为愉快,坏事使好事成为愉快,饿使饱成为愉快,疲劳使安息成为愉快。”[13]23他还认为没有不义,何来正义。同一条路既可以是上山的路也可以是下山的路,这取决于我们选择的方向。同样是物理事实意义上的路,不同的场景和目的下的讨论,其本质是不同的。同时,美具有相对性,“海水最干净,又最脏:鱼能喝,有营养;人不能喝,有毒”“最美的猴子同人类相比也是丑的”“最智慧的人同神相比,无论在智慧、美丽或其他方面,都象一只猴子”[13]24-25。总之,相反的要素组合才能产生美,美不是纯一的构成;同时,同一对象由不同主体进行判断,其结果有着本质的不同。审美相对论,就是以神或者世界总体为出发点,语境性地判断对象的价值属性。这种早期的非本质主义式的语境论,具有明显的价值阶梯性,而非均质的语境结果。不管如何,赫拉克利特第一次将对象的研究视角投向了对象之外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在对象的本质构成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从相对论出发的语境论,必然为将来种下审美相对主义的理论基因。
苏格拉底的美学标准是适称,他认为美是对象与主体之间的适恰性,而非对象本身的客观物理属性。苏氏从相对性语境角度来审视事物的价值属性:美与好的问题。事物自身并没有固定的本质,都是在语境之中与周遭的适配度来成就自己的性质和自性。他说,如果被放在合适的环境之中实现合适的功用,粪筐是美的;相反,金盾牌也可能是丑的。当他与胸甲制造者皮斯提阿斯聊天时好奇地问:同样是胸甲,在结实度和成本上都不高的胸甲,你为何比别人卖得贵。皮斯提阿斯说他的胸甲不可能完全相同,主要考虑合用性,这为其带来价值。可是皮斯提阿斯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是合用。苏格拉底说适称并非从事物本身来看的,而是从与使用者的关系来说的。虽然胸甲是外在于身体的东西,适称的胸甲就像本来就长在身体上的“自然的附加物”一样。“一个严格精确”的胸甲面对同一个人的不同姿势、弯曲、伸直时怎么能合用呢?“合用的并不是严格精确的,而是使人用起来不感到难受的。”[14]苏格拉底的美不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本体论式的数学。毕达哥拉斯认为美是静止的、抽象的、理论逻辑式的;而苏格拉底则认为美是动态、具象的、实践情境式的。在合数学规律与合人的目的之间,苏格拉底选择了后者。这根源于苏格拉底将哲学思考从自然转向了人世。早期希腊哲学家,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都是从世界的时间起源角度寻找本原,巴门尼德从世界的逻辑前提(本体)角度思考世界。这种倾向被智者学派的普罗泰戈拉以“人是万物的尺度”拉回了尘世。苏格拉底以辩证法方式洗去其极端相对主义的倾向,将思辨置之于人世的实践语境维度。他并非像其他哲学家一定关注万物的本体和本源,更多思考的是与人类相关的事情,如虔诚、适宜、弓刀、明智、刚毅和怯懦等。可以说,苏格拉底的美学是建立在实践论,而非知识论的基础之上的。实践必然涉及到人当下的境况和语境。故而,他论美不是本质主义式的,而是语境主义式的。
近代文艺理论家对文学语境理解主要是先在的、客观的,故而对文学进行研究是从物理语境或社会历史语境来做的。文论家从实在语境角度阐释文学,如从天气、气候、地理地势等方面来研究这些因素对文学的直接作用。后来人们意识到物理语境直接进驻到文学并不能为具体文学阐释提供新鲜的血液,于是将注意力转向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文学的物理语境探讨也好,还是文学的社会历史语境探讨也好,之所以兴盛,是与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分不开的。斯达尔夫人的《论文学》真正开启了从外部语境研究文学现象的先河,其写作目的在于将宗教、民风、法律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挖掘出来。受到孟德斯鸠的天气与人的快乐感受度理论的影响,斯达尔夫人的研究重视时代、社会环境对文学艺术的直接影响,认为文学作品表现的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历史过程。在探讨希腊文学时她指出,希腊诗歌的产生并不是受之前文学影响,因为希腊诗歌早于其他文学形式,并被视为典范。真正影响希腊诗歌的是文学环境因素。希腊诗歌的发展是最初形象思维和诗情的迸发产生的无法超越之美的结果,而恰好希腊当时的时代提供了这样的语境,“英雄时代的历史事件、人物性格、迷信、习俗都特别适合于诗的形象”[15]。同时炎热的气候、活跃的想象和人们对诗人的颂扬都激发着诗人们的狂热和对诗歌语言的音乐性追求。斯达尔夫人还将西欧文学分为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她认为造成南北文学差异的原因是自然环境和社会时代环境的直接影响。北方天气阴霾暗淡,海滨、风啸、灌木、荒原等使得人们具有了一种忧郁的精神气质,北方文学因而充满着一种高尚纯洁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但是缺乏一种对文学审美的成分。像北方文学作家代表莎士比亚的剧本在哲理和认识上高于希腊悲剧,但是在艺术审美上却略逊一筹。南方空气清新、树林繁茂、溪流清澈等使得人们具有一种激情的气质。人们享受安逸的生活,爱好艺术,在艺术性上的造诣非常高,然而文学的哲学思想性完全不能同北方文学相比。以地理环境作为文学解释的主要因素,在斯达尔夫人这里可谓贯彻得非常彻底,而丹纳则自觉地寻找和建构比较完整的文学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他将孟德斯鸠的地理说、斯达尔夫人的文学与社会关系研究、黑格尔的理念演化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的实证研究等综合起来,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说。种族作为内部动力,包含着人的先天的、生理的因素;环境作为外部动力,包含着气候、地理等因素;时代作为后天的力量,包含着文化等因素。三者从不同的侧面构成了文学的社会条件,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丹纳同时将作品与植物进行比较,植物的生长除了是一颗合格的种子之外,还必须具备气候和自然形势。而作品的生成也一样需要“精神气候”对才干的“选择”,“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发展”[16]。
十七、十八世纪的自然主义在斯达尔夫人和丹纳那里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到了十九世纪,文艺的外部语境从之前的自然主义逐渐走向现实主义;语境也由自然环境置换为社会历史。典型的理论家代表是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的文艺理论走的并非是黑格尔和谢林的推演式路子,而是以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作为探讨基础。在别林斯基看来,诗人从一出生就受到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比如十二世纪诛杀异端,十九世纪反对按照自己相信的原则去杀害别人,两种环境滋生的艺术作品理念必然差别极大。艺术家在不同的时代所书写的内容必然受到时代精神影响,比如中世纪画家的作品内容主要是圣母和圣徒。因此,在美学上,别林斯基坚持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艺术是现实的再现;因此,它的任务不是矫正生活,也不是修饰生活,而是按照实际的样子把生活表现出来。”[17]73莎士比亚的作品同样有法国热狂文学那样对生活中种种不堪一面的描写,但是莎士比亚的艺术作品在审美和道德层面都是优秀的,因为他不像热狂文学单独将生活中丑恶的图画从“完整的生活”中抽引出来,而是按照实际的样子把生活描写出来。在别林斯基看来,“现实”包含着“可见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事实的世界和概念的世界……显露在自己面前的精神,是现实性”;而“幻影性”则是“一切局部的、偶然的、非理性的东西,作为现实性的反面,作为它的否定,作为若有,而不是实有”[17]103。因此,现实原则并非是说诗歌是对现实的抄袭,而是“幻影性”的反面,即精神之中普遍性的真实(典型)。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反对将美视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反对艺术美高于客观现实中的美。他认为“真正的最高的美正是人在现实世界中所遇到的美,而不是艺术所创造的美”[18]10。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主要指美并非存在于抽象思想之中,而是存在于现实的、活生生的个别事物之中。同时,他反驳了现实生活中美是稀少的观点。现实之中的自然美随处可见,生活之中的崇高情感也到处都有。现实中美很稀少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总喜欢在美的东西之中挑选出顶级最好的,“倘若有或者可能有那么个东西X比我眼前的东西A更高级,那么这个A便是低级的”,实际上美与不美并非抽象的数学比较的结果,而是生活语境的结果。“一条在某些地方只有一呎深的河之所以被认为是浅河,不是因为别的河比它深得多;不用任何比较,它本身就是一条浅河,因为它不便于航行。一条三十呎深的运河,在实际生活中不算浅,因为它完全便于航行;没有一个人会说它浅,虽则每个人都知道多维尔海峡比它深得多。”[18]44-45因此,艺术作品之中,美即便有等级,次级的作品从生活来看并非就不美。
三、对立性与情境化:语境诗学的自反性维度
西方文论史上存在一种“去语境化”的理论路径,认为文学和艺术其本质和意义都来自客观、抽象和永恒的理念。然而由于理念与诗歌相去甚远,同时理想国又驱赶了诗人,故而诗歌的可取之处只能是符合理想国价值的那部分。柏拉图的《伊安篇》谈到,伊安对荷马史诗的解说是依靠磁石一样的灵感,而非技艺知识。“如果你凭技艺的规矩去解说荷马,你也当然就能凭技艺的规矩去解说其他诗人,因为既然是诗,就有它的共同一致性。”[19]7所以,在艺术领域有个现象,只会判别画家画的“波吕格诺特”的好坏,而不能判别其他画家的好坏,原因就在于诗歌和吟诵诗人都是受到灵感的驱使。“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19]7在这种诗神灵感的支配之下,他们会做一下“神志清醒时所不能做的事”;诗人的创作并非凭借技艺而是诗神的灵感传递,故而他们的能力各随所长。不过,伊安不认为自己诵诗解说荷马时被诗神凭附着。于是苏格拉底以荷马史诗中的例子进行反驳,对驾御技艺的妥帖性只能由御车人而非医生的技艺来评判。同样地,切羊酪片只能由医生技艺评判,城堡附近的战事只能由预言家评判,将官对兵士的讲话只能由将官的技艺来评判等等。最后伊安只能承认自己解说荷马的能力来自灵感而非技艺。柏拉图最后说,诗歌中不同角色的叙事只有担当此角色的人最有阐释权。换句话说,如果文艺作品诞生于行业从业者,他的专业化知识可以让作品更为深刻。这种思维背后已然是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认为诗歌是对现实的模仿,现实是对理念的模仿。因为现实较之于诗歌更接近真实,故而现实之中的知识必然对于诗学知识具有话语权。柏拉图主张的“个人阐释权”表面是倡导语境论思维,即不同的人面对同一文本阐释的力度与其行业相关性成正比;实际上,其观念是指向具有去时空化的、永恒的理念的。真正的语境诗学是建立在承认文本基础之上的,认为诗歌之外的其他东西具有“赋义”行为。柏拉图认为诗歌本身毫无独立性和生发性,其意义通过像“镜子”四方八面地旋转,从“理念”的折射中获得。虽然苏氏和柏氏都承认诗歌之外存在着异于诗歌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可是前者认为意义是通过诗歌自身的情境效应形成的,而后者则认为是现象(包括情境)之外的理念赋予的。
诗的本质是一种模仿,正如画家的床是对木匠的床的模仿一样。它们都是模仿的产品,与真理都隔着三层。在苏格拉底看来,木匠制作的床是全然本真的存在着的,画家画的床只能通过某一个点(“观点”)去审视,所以图画只是对床的外形的模仿。因此,“摹仿和真实体隔得很远,它在表面上像能制造一切事物,是因为它只取每件事物的一小部分,而那一小部分还只是一种影像”[19]69-70。如果说一个人可以同时模仿和制造对象,相信大家都会选择制造。所以,对于整个城邦来说,诗人(如荷马)是完全不能和意大利的呼卡雍达斯和雅典的梭伦相比的。因为诗人和画家一样都是摹仿者,创作出影像,通过文字的韵律、节奏和乐调使受众信以为真。同时,摹仿又常常只能摹仿“无理性”的部分,滋养和灌溉欲念与快感,从而支配和控制人的理性。因此,柏拉图只允许“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歌进入理想国。诗歌意义和价值来源于柏拉图建立理想国的需要:教育幼小孩子,我们必须选择好的虚构故事。赫西俄德、荷马和其他诗人的虚构故事恰恰有着严重的毛病:拙劣地“说谎”,比如赫西俄德《神谱》之中克洛诺斯推翻父亲并割去其生殖器,自己做天神的故事。这不仅有损神的威严,而且相争相斗的故事会被不辨真实与虚构的儿童模仿。这无疑对理想城邦的建立是有害的。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国需要严肃的、正能量的和遵守规范的诗人与故事作者。诗人的写作和画家画画必须是正面的、积极的、美的、善的,因为罪恶、放荡、卑鄙和淫秽的丑恶事物进入艺术之中,必然会在潜移默化之中毒害纯洁的心灵。我们应该“寻找一些有本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方面描绘出来,使我们的青年们像住在风和日暖的地带一样,四围一切都对健康有益,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19]60。在柏拉图身上,我们又可以看到诗歌并非一种本质主义式的存在,没有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诗歌的价值就在于社会政治价值,即如《法礼篇》中所说“如果一个群体的目的(telos)是让公民过上有德性的生活,有德之人所创作的诗歌或戏剧更有益于(起码更不会危害)社会,即便这些作品毫无艺术价值,也优于道德品行不端者技艺高超的作品,这完全符合古老的恩培多克勒原理——同类相生、同类相吸”[20]37-38。总之,柏拉图眼中的文学和艺术并没有太多自己独立的空间,更多地是为文学艺术之外的社会和政治服务的工具,抑或是对终极客观理念美的“隔三层”式的摹仿。
黑格尔的情境论是理念对立性语境的表征。在黑格尔的美学之中,他实际探讨了两种语境:一种是作为“一般世界情况”的社会时代总体语境,一种是有个别人物及其行动展开的具体和当下的情境语境。黑格尔的美学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不过他批判了理念论中的空洞性,“美本身应该理解为理念,而且应该理解为一种确定形式的理念,即理想。一般说来,理念不是别的,就是概念,概念所代表的实在,以及这二者的统一”[21]135。黑格尔的理念相对来说较好理解,就是对象理想的美的状态,这与典型形象相通。然而概念在二者统一之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概念在实在之中实现了自己。朱光潜先生在翻译时将概念与实在的关系注解为理性与感性。“概念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统一,和实在中各种差异相对立,而是本身已包含各种差异在内的统一,因此它是一种具体的整体。”[21]137概念具有普遍性,也具有自我否定性(即特殊性中的自我实现);概念可以在自己的另一面(实在)中与本身统一。概念原本存在于完满统一之中,但当其存在于形式中时,概念转化为殊相。黑格尔作为唯心主义美学家,坚信理念才是最为真实的,具体的实在只有符合概念时才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他的哲学思想直接体现于美学观念之中,“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21]142。美的理念不同于抽象的理念,它具有让所有人在形式之中见到最理想状态的美学对象的形式。同时,作为一种感性显现,它并非以物质性刺激人产生认知和占有欲望,而是被理念心灵化了的。美一方面具有理性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具有感性形式的具体性和个别性,同时必须完成两方面的协调统一。特殊性和感性的形式对美来说是一种限制和不自由,只能在实在之中呈现出“无限的整体”,美的对象才是自由的。
黑格尔认为理念(或概念)是普遍的和统一的但不可能永远处在自身之中。特别是在艺术美之中,艺术既追求一种普遍性,又必须通过“定性”(特殊性与差异性)来实现艺术的美学。这与黑格尔秉持的辩证法一脉相承。首先,相较自然美,艺术美体现着透过心灵而达到的观念普遍性的维度。他将艺术美中的理想状态与自然美之中的自然状态进行比较,认为艺术对没有意义的、散乱的和陷入时间之流的自然事物进行了提升、凝聚和最优化固定,比如现实中的莲花由于其个体差异、环境影响以及不同时间段的呈现总是不完美的,而莫奈的《池塘·睡莲》则可以排除一切缺陷将理想状态的、具有普遍性的莲花创作出来。“诗所应提炼出来的永远是有力量的、本质的、显出特征的东西,而这种富于表现性的本质的东西正是观念性的东西而不是只是现在目前的东西,如果把每件事或每个场合中现在目前的东西按其细节一一罗列出来,这就必然是干燥乏味、令人厌倦、不可容忍的。”[21]214自然美学指涉的是可以激发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需求的个别对象,而艺术美则是将观念形式化了的,这一过程是外在的自然对象被心灵过滤和创构的过程。其次,艺术美从理想的本质和时代状况到具体的个别性,必然要通过特殊情境,在差异、对立之中实现“理想的定性”。就好比耶稣也不可能一直生活在永恒世界之中,亦被置入冲突和斗争之中。心灵的伟大只能在对立矛盾之中顽强地挣扎出来才能回到统一。艺术美之中的差异性和对立性必须是在情境之中实现,故而情境成为艺术美从普遍世界情况到个体殊相(理念到实在)的基本条件或过程。它尤其体现在“动作”或“情节”之中,“一种动作或是一个人物性格的现实存在都和许多细微的间接的情境和条件以及许多个别的事件和行动联系在一起”[21]252。
按朱光潜先生的阐释,“普遍的世界情况”是一个时代的总体情况,而情境则是具体人物或情节产生的具体的时空场景。其实也即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情境语境。差别在于,黑格尔将“普遍的世界情况”定格为处于无矛盾和冲突的理念状态(“天真状态”),如果没有在具体化的过程之中实现分裂和冲突,这种语境只能是艺术的“潜能”状态。黑格尔改变了我们对社会文化语境实体化和先在化理解的倾向。同时社会文化语境只能通过情境语境达到“有定性”的实现,“情境就是更特殊的前提,使本来普遍世界情况中还未发展的东西得到真正的自我外现和表现。……情境一方面是总的世界情况经过特殊化而具有定性,另一方面它既具有这种定性,就是一种推动力,使艺术所要表现的那种内容得到有定性的外现”[21]254。故而,黑格尔将“情境”视为一种中间状况。“情境在尚未转化为具体定性之前,还保持着普遍性的形式,也就是无定性的形式,所以在我们面前的起初只是一种像是无情境的情境。……分裂和由分裂来的定性终于形成了情境的本质,因而使情境间出一种冲突,冲突又导致反应动作,这就形成真正动作的出发点和转化过程。”[21]255总的来说,黑格尔的情境语境较之于社会时代语境来说,更偏向于作品存在得以实现的具体语境。
结 语
近代之前的西方诗学中语境思想总体上可以分为:社会—文化语境、作品语境和情境语境。这种分野在早期古希腊就初具雏形:赫拉克利特认为语境非均质,毕达哥拉斯则认为语境是均质的。前者带来语境的价值判断维度,偏向外部社会;后者形成语境的事实判断维度,偏向内部形式。文艺理论家对文艺语境的思考和建构已然形成了语境的雏形:苏格拉底式的情境语境,柏拉图式的社会政治语境和亚里士多德式的作品内部语境。但凡后来对文学的语境性思考都逃不开这三种路径,只是语境思维的内涵和基础受其他学科知识的影响发生了理论置换而已。文学的文化语境很大程度上是外决定型的,是由已然存在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等种种因素构成的;文学作品语境是作品借由文字图像和声音等媒介为自己生成氛围统一的语境。这就好像解题和研究的差别:解题是根据别人出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而研究则是自己给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寻找答案。外部文化语境先在地存在着,似乎一切艺术现象都是一面镜子,需要借助于它的光自己才会发光;作品语境自己为自己“铺路”,通过语言的腿走出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语境,好像自己就可以发光,独立成一个世界一样。但是,文学作品并非独立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系统之外。庞大的文学体系就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同时它还创造和生产着文化意义。内部、外部和自反的语境有机地关联着。“一个语境就是以特定方式联系起来的一组整体(事物或事件);这些整体都拥有一种特征使得其它一组整体以同样的特征和关联方式出现;并且它们都‘近乎统一’地出现。”[22]文学语境的静态观察召唤着文学情境语境的出场,因为文学情境语境游走在作品语境和文化语境中间,对他们进行着动态性的调整和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