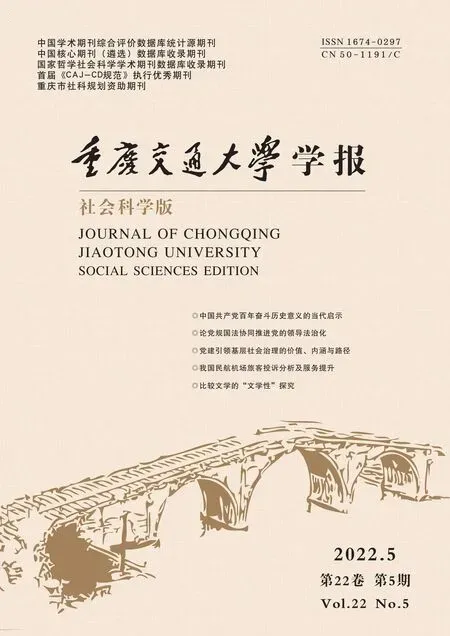《燕妮·特赖贝尔夫人》中的“对立性”寓所空间书写
傅 琪
(大连外国语大学 德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德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台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擅长通过“非门当户对”的悲剧婚姻故事展现19世纪下半叶普鲁士社会贵族与市民的差异和矛盾,即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然而他写于1895年的长篇小说《燕妮·特赖贝尔夫人》(FrauJennyTreibel)在“创业时代”背景下有了新的侧重和突破,转而揭示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小说中精妙细致的寓所空间书写,生动展示了19世纪下半叶德国市民阶层的惯习,更是将“创业时代”德国资产阶级内部有产市民阶层和有教养市民阶层的对立与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施密特宅邸
小说开篇是个“动态”的空间定位:“一辆敞篷四轮马车从斯皮特尔市场辘辘而来,它先拐进疗养街,后又拐进鹰隼路,不多一会儿就在一所住宅前面停了下来。”[1]1坐在敞篷四轮马车中的正是小说的女主人公燕妮·特赖贝尔夫人。从她的行车路线可以看出,这是从市郊进入老城的方向。她要去的地方是曾经的恋人——施密特教授的宅邸。“这宅子正面尽管只有五扇窗户,然而相当高大,只是显得古香古色。它用黄褐色油漆粉刷一新,这也许给房子增加了一点儿整洁的感觉,不过它却丝毫也没有因此而显得更漂亮,在这一点上几乎是适得其反。”[1]1
可以看出,这不是一栋讲究排场的房子,也可能是因为主人身为普通市民阶层,没有足够的财力让房子看上去尽显档次,尽管它位于柏林老城,地段相当不错。房前的木板楼梯已经磨损,房门上挂着的刻有名字的绿色铁皮招牌也已起褶,上面的字模糊难辨,虽然房子正面被油漆粉饰过,但依然难掩其老旧过时的细节。正因如此,整栋房子具有一种由历史沉淀下来的底蕴,颇有一种“良好市民气质”。“楼下光线极其暗淡,楼上则充斥着一股浑浊的空气,人们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双料空气。”[1]1这空气表面上是夏日的暑气和厨房怪味的混合,实则是有教养市民和有产市民之间的矛盾气息。
从马车上被搀扶下来的贵妇特赖贝尔夫人便是有产市民阶层的典型代表。她乘坐尽显社会地位的座驾,装束讲究,衣着时髦,随车还有佣人陪同伺候。在这栋老旧的宅邸面前,她的驾临顿时显得那样“突兀和出位”[2]。殊不知这位高贵的夫人竟是柑橘铺老板女儿出身,如今已是商务顾问夫人。其夫特赖贝尔靠生产颜料起家,成为有钱的工厂主,之后又授封为皇家“商业顾问”,从而一跃成为家财万贯的上层市民,燕妮也因“夫贵妻荣”,摇身变为阔太太。施密特宅邸的位置和外观都表现出有教养市民的传统价值观与根脉传承,与暴富的“上层市民”形成鲜明的对立关系。
再看内部,前厅通往前室的狭长过道铺着亚麻布地毯,前室“是一间漂亮的、高大的房间,百叶窗已经放下。所有窗户的窗扇朝里开着,其中有一扇窗户的前面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摆着几盆桂竹香和风信子。一张茶几上放着一个玻璃盘,内盛着柑橘”[1]3。亚麻布地毯显示宅子的主人生活简朴,虽然宅子的外观不惹眼,但里面的房间却宽敞、高大,居住性和实用性强。所有窗扇朝里,这暗喻其内敛、不张扬的特点。窗台上摆着的花也是主人品格的象征:桂竹香气浓郁,呈亮黄色,给人阳光般的感觉。桂竹的花语是困境中保持贞节、真诚,风信子寓意恒心、贞操和生命。整个内部居室虽不奢华,但颇有一种“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气质和格调。
人们从墙上挂着的照片可以看出施密特教授的出身:
教授的双亲,即纹章院(1)纹章院于1855年成立,是普鲁士司宗普并处理贵族事物的一个机构。会计官施密特及其娘家姓施威林的太太的肖像俯视着这盘柑橘——老会计官身穿大礼服,佩戴着红色老鹰勋章;娘家姓施威林的太太,高颧骨,翘鼻子。这些尽管带有市民色彩,不过眉宇间波美拉尼亚(2)波美拉尼亚是德国普鲁士北部省名。—乌刻马克(3)乌刻马克是地名,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区附近。名门望族苗裔的神采始终跃然可见。后来的,或者不妨说很久以前的波森(4)波森是波兰地名。波森有人定居远比波美拉尼亚-乌刻马克早,所以作者说“很久以前的”波森血统。血统则看不大出来了[1]3-4。
教授父亲的红鹰勋章是普鲁士授予奖励贡献卓著的平民、文官或士兵的,分量自然与普鲁士级别最高的骑士勋章——黑鹰勋章不可同日而语。老施密特的祖母为法姓,因此他的家族很可能是17世纪逃亡到柏林的法裔移民。他们在勃兰登堡区有自己的聚居区,渐渐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地道的“市民”。老施密特正是靠着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供职于封建机构,并因业绩突出获得勋章奖励。施密特的母亲具有普鲁士人的典型外貌特点,早就与古老的波森贵族血统扯不上干系。由此可见,施密特出身于一个典型的有教养市民家庭。
除了空间陈设,我们根据施密特女儿科琳娜与特赖贝尔夫人的谈话,也可以清晰辨别有教养市民阶层和有产市民阶层在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方面的不同。科琳娜这样形容特赖贝尔夫人的生活:“一辆四轮马车,一幢公馆,一座花园……复活节一到,宾客纷至沓来,门前车水马龙。”[1]6其父施密特却“低估一切身外之物:产业和金钱。一切的一切,凡是使生活舒适、美好的东西,他都低估”[1]8。而在特赖贝尔夫人眼中,这样的施密特教授算是“博雅之士”,女儿科琳娜也出身于此等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讲英语,博览群书”[1]7,通晓政治和历史。这也是她邀请科琳娜赴约参加家庭聚会的原因——为了充当陪客,招待她儿子的英国商人朋友纳尔逊。
二、德国的有产市民阶层与有教养市民阶层
19世纪的德国市民阶层主要受两种思想影响——理想自由主义和保守民族主义,实现国家统一是这两种思想的共同政治目标。然而,1848年革命失败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市民阶层的惯习。普鲁士王国宰相俾斯麦通过一系列王朝战争战胜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实现民众渴望已久的国家统一。所以,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完全不是资产阶级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结果,而更多归功于封建统治阶级铁血强权的“顶层设计”。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德国贵族对德国市民阶层的胜利。贵族阶层的传统特权被固定在帝国宪法中,他们在几乎所有的国家权力领域具有决定权。统一后,贵族把持着行政、外交和军事部门三分之二以上的重要职位。因此,相当一部分市民背离原先批判贵族的共和理想,适应新的“形势”,顺从了由宫廷和贵族主导的帝国社会制度,接受了军阀国家和军阀贵族的生活模式。
威廉帝国时期,有产市民阶层的生活呈现明显的“封建化”趋势:富裕有产市民的奋斗目标是升跃至贵族等级,或者至少获得一个尊贵头衔。企业家会送儿子去所谓的帝国军队服役,工厂厂房被置换成别墅,以效仿和复制贵族拥有的宽敞的生活空间。这是市民向获胜权力的归顺和投降,毕竟后者非但没有阻碍有产阶级的经济繁荣,反而极力提携他们,并用荣誉和头衔嘉奖他们。原先着眼于反宫廷和追求社会平等的市民法则被贵族的勇士伦理所排挤。市民中产阶级的道德和文化标准渐渐与精英式的、关切名望的封建贵族荣誉“联姻”,从而交织成一种新型的社会准则。这也导致在资产阶级内部有产市民和有教养市民阶层的缝隙愈发无法弥合。
社会学家哈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用“工业化的封建社会”[3]51来形容当时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结构。这种畸形状态建立在经济实力强大的大资产阶级与政治势力稳固的贵族之间的历史妥协上,因为他们的共同对手是已经产生并日渐强大的属于社会“第四阶层”的无产阶级。虽然贵族阶层在政治和军事上居于统治地位,但在国家经济领域往往由资产阶级中的有产市民阶层担任要职,他们掌控着国家的财政及工商业。相较于拥有世袭家产和土地的封建贵族,有产市民阶层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出建设和领导经济的巨大潜力。他们逐渐飞黄腾达,在资产和财富上很快赶超贵族阶层。统一后的德国已经是一个进步的工业国,旧有的封建社会结构日益瓦解。在这种情况下,贵族的政治统治实则明日黄花,早已不合时宜。然而,“温和”的资产阶级非但没能获得政治上的领导权,反而以一种“仰视”和“尊崇”的姿态,渴望在社会等级的金字塔中跻身贵族行列。
施密特代表了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有教养市民阶层。这一阶层从歌德时代一直延续至威廉帝国时期。他们崇尚自由和平等,不愿服从贵族统治或是接受其价值观。他们鄙视钱财,与封建化的资产阶级新贵决裂。因此,这些不顺应形势甚至略显迂腐的有教养市民阶层单方面放弃原先与有产市民阶层的联盟,他们完全脱离政治,让人不再感受到他们“在1848年之前的豪迈情怀和在保罗教堂前集合时的激情”[4]434。他们对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结盟的冷淡态度从未激化,而是以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态满足于一种与有产市民阶层的“柔性对立”[4]434。小说中施密特与恋人燕妮由于“三观不合”终未成眷属的故事,恰好是这一分裂和对立的巧妙体现,因为燕妮最终正是被一位封建化的资产阶级新贵——特赖贝尔娶进家门。
特赖贝尔是典型的有产市民的代表。他本是生产亚铁氰化钾和柏林蓝起家的工厂主,后被威廉帝国授予“商业顾问”的荣誉头衔。其实,这并不“尊贵”,只是多少给他罩上一些贵族光环。他的夫人燕妮出身于小市民家庭,骨子里贪婪成性,自认为夫贵妻荣。一跃步入有产市民阶层后,她一心只想追求更多财富和更高的地位。作家借施密特之口道出,燕妮·特赖贝尔夫人就是“布尔乔亚的样板”[5]91。冯塔纳对这一人物的塑造已经全然超出个性范畴描写,燕妮所代表的是整个有产阶层的精神特质,是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性格的生动展示。
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西方社会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划分阶级时,使用“布尔乔亚”(Bourgeois)表示社会中的富有阶级之一,指有产者、中产阶级,通常翻译为资产阶级。在小说创作的前期构思阶段,冯塔纳甚至想把题目拟作“布尔乔亚夫人”,后定为“燕妮·特赖贝尔夫人”,足见这一人物对作品主题诠释的重要性。
小说伊始,特赖贝尔家宴请宾客的主要目的便是要联络各种人脉关系,使自己在政治上再有长进。他欢迎一切“具有宫廷气息的人”大驾光临。特赖贝尔是个十足的实用主义者,深知那些贵客会给宴会带来极大的“装点价值”[3]55,也可能对他在政治或经济上的攀升大有裨益。他认为“商务顾问”还是个“残缺不全的头衔,有待在今后加以充实”[5]35。身为市民阶级工厂主,他本应跻身进步党团阵营。就连贵族代表齐根哈尔斯夫人都认为,他不该参与政治,而应该向市政方面挺进,去争取“市民王冠”[1]35。然而,特赖贝尔却秉持保守主义,期望借助王宫贵妇进一步靠拢封建势力,以捞取政治资本。
三、特赖贝尔公馆
海德堡大学的荣休教授迪特·博希迈尔(Dieter Borchmeyer)在专著《何谓德意志?》(Wasistdeutsch?)中论述了小说《燕妮·特赖贝尔夫人》与威廉时期普鲁士的关系:“19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其他文学作品能像《燕妮·特赖贝尔夫人》那样,以如此丰富的手段反映上述社会现实。作为小说情节的主要发生地之一,仅仅是柏林工厂主特赖贝尔的公馆别墅就生动地展示了威廉帝国有产阶级的惯习。”[4]4321888年4月26日,冯塔纳致信保尔·施兰特尔的时候谈道:“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那种嘴上谈着席勒,心里却想着盖尔松(一家柏林百货公司的名字)的资产阶级的空虚、伪善、傲慢和冷酷。”[6]
小说第二章详细描写了特赖贝尔公馆,使我们得以窥见威廉帝国有产阶级的“追求和品味”:
特赖贝尔公馆坐落在从克卜尼克街延伸到施普雷河边的一大块地基上,这里地势很平坦。从前沿河这一带只有工厂的厂房耸立。这些工厂每年生产大量的亚铁氰化钾,后来工厂有了发展,又生产一种叫柏林蓝的颜料,其产量仅次于亚铁氰化钾。可是,一八七○年战争后几十亿的钱财流进国内,连头脑最冷静的人也被这股盖工厂、建住宅的浪潮卷进了漩涡。这时商务顾问特赖贝尔也觉得,他那坐落在老雅各布街的住宅跟时代和他的身份不相称了,虽然这宅子据说是康塔特(5)卡尔·封·康塔特(Karl von Gontard, 1731—1791),德国古典学派建筑师。设计的,有些人甚至还说是出自克诺勃斯多夫(6)格奥尔格·文策斯劳斯·封·克诺勃斯多夫(Georg Wenzeslaus von Knobelsdorff, 1699—1753),德国建筑师、园艺师、画家,柏林歌剧院的设计者。之手。于是,他在他的厂区盖了一座带有庄前小花园和后花园的时髦别墅。这座公馆的底层离地面很高,下面是地下室,上面加盖了一层楼面。这层楼面,由于窗户低矮,给人的印象不像是二楼,倒像是中间层。特赖贝尔已经在这里住了16年。他不明白,他竟然会碍于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的一位建筑师,况且还只是一位假想中的建筑师的情面,在那俗气的、空气污浊的老雅各布街耐着性子熬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对此他的夫人燕妮起码是有同感的。工厂近在咫尺,一旦风向不利,当然就有诸多弊端;不过,尽人皆知,把烟雾吹过来的北风是极为罕见的,况且也大可不必偏偏在刮北风的时候招待客人呀。除此之外,特赖贝尔逐年都要加高工厂的烟囱,使初创时期出现的弊病不断得以消除[5]16-17。
19世纪80年代是德国统一后的“创业年代”,以兴办工厂、修建铁路为主要标志。德国资产阶级尽管在政治上还依附于贵族的统治,但经济上却迅猛发展成为最强大的阶级。冯塔纳对特赖贝尔公馆的描写具有“史料价值”[7]125,因为这栋别墅代表着一个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在创业时代,由于暴富而挤入上层社会的资产阶级“没有传统,没有历史”[8]。历史性缺失造成的不确定的社会定位导致他们不可遏制地要求讲究排场,不由自主地渴求跻身上流社会,这首先表现在他们的“居住文化”上。特赖贝尔从老雅各布街搬到具有封建庄园性质的新别墅,这一举动彰显工业发展的普遍趋势。它并非自然的社会流动,而是城市社会性驱使下的流动,创业精神要求另一种外部环境来诠释新的阶级意识。因此,原先得体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的别墅让位于一栋“能代表自己身份”的公馆。尽管克卜尼克街上的空气同样不够新鲜,尤其当北风刮起烟雾的时候。但是,新居的地址却足以给人带来精神上的优越和满足感。“他正好住在位于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区与封建贵族领地之间的工业氛围浓重的城郊。”[7]126这样,他就能更便利地掌管工厂,享受远离狭隘城市空间的相对自由。
特赖贝尔公馆所在的路易森城郊并非贵族街区,而是一个带有不均匀性社会结构的工业城郊。生活在其中的上层有产市民往往定期与西部的富人区和老城中的有教养市民阶层联系,以此获得在城郊内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联系的“多核性”一方面导致城市结构整体上的混乱无序,另一方面表明有产市民阶层的“中间状态”,他们无法把自己的社会关系限定在自己的生活空间内。他们不属于贵族,又与市民性的传统价值渐行渐远。“巴黎、伦敦以及其他大城市往往具有相似的空间特征,柏林也一样,那就是城市的西部往往是优渥的富人居住区,东部大多是厂区或工商业活动区。”[9]特赖贝尔住在东部厂区内,这属于创业时代的特有现象。
尽管别墅能够代表特赖贝尔的身份,然而特赖贝尔夫人却一直认为它还不够奢华,而且有很多欠缺之处。比如,它至少还缺两个房间和一道偏门,由此送货人、勤杂人员和那些小市民可以进到室内,而现在的情况是“随便哪个厨房小厮都可以大模大样地穿过前花园径直朝宅子走来,仿佛他是应邀来赴宴似的”[1]15。这种牢骚充分表现出特赖贝尔身为有产阶层的阶级优越感和面对无产阶级的自大与傲慢。此外,由于窗户低矮,第二层楼更像是中间层,且公馆不远处就是工厂,每当风向不利,便会将有害气体吹进屋。特赖贝尔只能采取补救措施——不断加高烟囱。可是,风向是不受约束的,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往往是资产阶级有产阶层急功近利的惯用手段。所有这些建筑设计的瑕疵和缺陷,都暗示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不健全性”[10]和与阶级属性相悖的审美趣味。
应邀去特赖贝尔公馆赴宴的宾客大多乘坐各式马车前往,有轿式马车、轻便敞篷马车、出租马车等,这是前工业时代典型的交通工具[11]。相对于火车和蒸汽机船等现代技术交通工具,马车无疑是“旧时代”的象征。此外,它也是彰显各色人物身份地位的微型可移动空间。特赖贝尔家的长子奥托携妻子海伦妮乘轿式马车首先到达。奥托同他父亲一样,是个工厂主,经营高端木料生意。克卜尼克街的几家友邻厂主坐敞篷马车来。福格尔桑少尉乘出租马车来。齐根哈尔斯夫人和博姆斯特小姐两位宫廷妇人更是尊贵,居然由特赖贝尔派自家四座双驾豪华马车接来。一切有钱、有地位的人物都视这种极具封建特色的交通工具为自己的“移动名片”,旨在向他人展示优越的身份和地位。只有科琳娜及其表兄马塞尔步行前来赴宴,这与之前那些高高在上的有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代表形成鲜明对比。
走进公馆内部,“饭厅跟位于前面的那间客厅大小一样,位置对称。从这里人们可以眺望那座公园般美丽的大后花园及其发出淙淙声的喷水池”[1]25。喷水池旁被豢养的白鹦以“一种人们熟悉的、满含沉思的眼睛时而望望带平衡球的水柱,时而又朝饭厅里面窥视”[5]26。特赖贝尔家还豢养了一只纯种意大利博洛尼亚犬。这些具有异域特色的动物和装饰设施都是特赖贝尔公馆极尽奢靡的体现。饭厅与客厅大小一致,位置对称,暗示其功能作用也有一定意义上的等同性,即用于招待客人。在威廉时代,社交是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组织宴会、晚会或邀请郊游等方式结交人脉,同时也利用这些机会不遗余力地彰显自我、炫耀财富。那个具有田园色彩的后花园通过一排高高的白杨树与厂区隔开。第四阶层的社会现实及其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就这样在有产阶层的日常生活中消弭、隐身遁形。后花园里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喷水池上方随着水柱跳上跳下的小球。住宅、花园、厂区三种不同性质的空间依次相邻,充分体现出创业时代特有的非均质性空间布局。
饭厅里的枝形吊灯灯芯被捻得很低,对于午后的阳光来说,这黯淡的灯光简直多此一举。但这是商务顾问刻意追求的效果,因为他不喜欢“点瓦斯街灯的那一套操作程序破坏他的饭局气氛”[1]25。饭厅的天花板和墙是用黄色灰泥抹就的,上面镶嵌着柏林雕塑家尤里乌斯·弗兰茨的几幅浮雕,只因会超出预算,便没有用更知名的赖因霍尔德·贝加的作品。这种不懂装懂,只将艺术看作点缀工具,仅仅用价钱衡量艺术效果的做法,正是资产阶级暴发户典型的做派。他们极力效仿并迎合封建贵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艺术品位,居住空间的装饰装潢和日常生活的繁文缛节都是封建宫廷范式的翻版。这种布尔乔亚式价值观在当时成了一种时代病,不仅风靡于有产阶层内部,还传染给一些有教养市民,施密特的女儿科琳娜便是最典型的“受害者”[3]56。
四、“家宴”对比
施密特教授家的茶话会与特赖贝尔家的豪华晚宴同时进行。但是,“会场条件”及“与会人”却有天壤之别。“如果满员的话,一张圆桌的周围,一盏配有红色灯罩、古香古色的煤油灯下,围坐着七位九年制完全中学的教师,其中大多数都有教授头衔。”[1]69从空间上看,这里没有富丽堂皇的宽敞客厅,也没有装点考究的长条形大餐桌,更没有枝形吊灯发出的和暖灯光,寓所里甚至没有专用的饭厅。他们用餐的地方就是科琳娜前一天接待来访的顾问夫人的那个房间:
餐桌放在房间正中央,桌上蜡烛和酒瓶林立,已经摆好了四副餐具;桌子上方挂着一盏吊灯。施密特背对着两扇窗户间的狭墙,在他的朋友弗里德贝格的对面落座。弗里德贝格则可以同时从其座位上照见镜子。黄铜烛台被擦得锃亮,其间摆放着几个在义卖集市上用彩票购来的瓷器花瓶。半锯齿形、半波浪式的花瓶口上插着几小束桂竹香和勿忘我。酒杯前横放着一个个长条形茴香味面包。主人认为,与一切茴香味的东西一样,茴香味面包具有特殊的强身滋补的功能[1]85。
特赖贝尔家的晚宴座次格局是主人夫妇分别坐在餐桌长端的两头,首尾呼应,客人完全根据身份地位和重要性落座。几位陪客穿插其中,与特赖贝尔夫妇形成周密的招待圈,丝毫不敢怠慢每一位对他们大有用处的贵客。而施密特的茶话会只来了三个朋友,还有一个人来得很晚,因为“只有那些没有什么别的更有意义的事好做的人,才来参加晚会。看戏、玩纸牌远远居于优先地位,这就使得聚会时人到不齐成了家常便饭”[1]72。施密特作为主人只是背对着两扇窗户间的狭墙,根本谈不上主位。与佣人众多且种类齐全、训练有素的特赖贝尔家相比,施密特家只有施默尔克太太,即一个女管家负责准备酒席。因此,她没能按时备好菜肴,还招致了施密特教授的不满和讽刺。
宴请那晚,特赖贝尔家“餐桌中央用丁香和金雀花铺了一个小小的花坛,代替通常放在那儿的大花瓶”[1]26,而施密特家摆放的是几个在集市上淘弄来的瓷器花瓶。特赖贝尔家的客人从饭厅朝窗外望去,看到的是美丽的后花园;而施密特家的客人从座位上看到的是挂镜中的自己。
从受邀者来看,特赖贝尔邀请的是工厂主、宫廷贵族或政府官员等,而有资格来施密特家“参会”的人都是有教授头衔的知识分子。施密特称这个特殊的“小圈子”为“希腊七孤儿”[1]70。这个有趣的名字源自“希腊七智叟”,即公元前六七世纪的七位希腊政治家和哲学家。Waisen(孤儿)与Weisen(智者)同音,所以这个文字游戏便成为茶话社团表面“自我解嘲”、实则“暗自彪炳”的巧妙称呼。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有产市民阶层和有教养市民阶层在社交习惯与社交目的方面迥然不同。对于有产市民来说,社交是生活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甚至可以决定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他们将宴请聚会等社交活动常态化、仪式化、功利化,以此获得能够攀附和利用的人脉关系。而对于有教养市民阶层来说,社交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聚合”过程,是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们谈天说地、高谈阔论、针砭时弊、讨论学问的休闲活动,是在自由的空气中吃着最便宜实惠的食物却能获得最宝贵精神财富的过程。他们是有教养市民阶层的典型代表,保留市民阶级最原初的本性,是独立于封建贵族和有产市民的社会群体。
五、结语
《燕妮·特赖贝尔夫人》中的寓所书写在一种“对立性”空间话语中暗示了19世纪末德国市民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分化。有教养市民阶层和有产市民阶层在政治立场、价值观念以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别与对立,通过其寓所空间特征得以鲜明体现。作家冯塔纳由此辛辣讽刺了当时德国有产市民阶层对封建势力的妥协和依附,这一阶层日渐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其革命性在一种有违常理的反比关系中导致德国的种种重大变革只能依靠容克贵族的“顶层设计”。然而有教养市民阶层虽抱有一腔气节,却再无心无力参与社会变革。19世纪下半叶德国资产阶级的畸形发展极大削弱了自身的政治力量,尽管德国在1871年统一后经济基础已跻身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行列,可上层建筑却依旧呈现浓重的封建色彩,二者的矛盾为德国此后的种种危机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