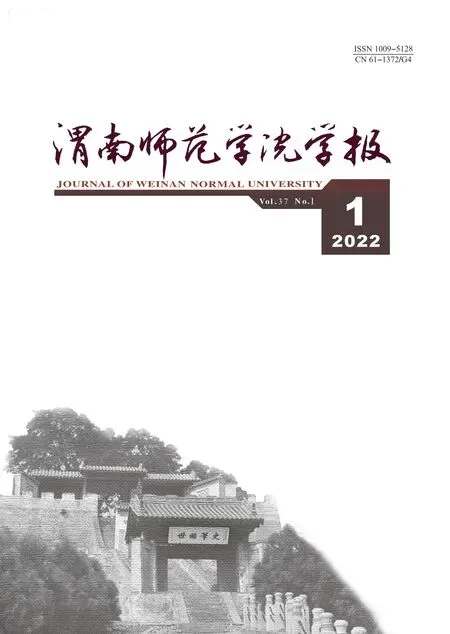作为文学典故与精神典范的“子长游”
刘 林 云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司马迁和《史记》,是历代文学作品的重要典故资源和精神养料,为无数诗文作者不断书写、解读和体认,并因层层演绎和“再创造”而获得了历久弥新的丰富内蕴。“子长游”便是诗词领域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示例。一方面,其毫无疑问指向了众所周知的史实与典故,即司马迁(子长)的游历行为本身;另一方面,“子长游”也因写作者的不断解读和阐释而获得了一种逐渐固定下来的精神内涵,成为诗词写作的惯用语,在作品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易于从读者心理层面召唤出具有共通性的文学趣味和精神价值。这既促进了司马迁和《史记》在文人精神、文学系统中的传承与发展,又使得“子长游”这一具有丰富内涵的固定词组在不断沿用中促进了诗词本身的创作与互动。
一、“子长游”之于司马迁及《史记》的意义
“子长游”在宋代以降的诗词作品中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学典故,其根基首先还是在司马迁平生多游历(尤其是弱冠之年的壮游)的史实上,而丰富的游历对于太史公自身以及《史记》的成书又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曾对自己的游历活动作有专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1]3293其游历范围之广、游历活动之丰,可见一斑。而这是司马迁对于年少壮游的重点记叙,专门探游妙水奇山、寻访大邑名都;适其真正继承父亲司马谈遗志、迁为太史令后,他扈从汉武帝不断遍览四方,同样“大大开阔了视野,增进了学识,获得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生活感受”,以及“无穷的创作灵感”[2]41。而在《史记》的具体篇章中,亦多见游历对于司马迁修史的重要影响,其往往在诸篇的“太史公曰”中表露自己的所游之行、所游之思。正因亲历山川、探闻南北,司马迁得以在《史记》的具体书写过程中多有真实可靠的细节性材料,频出新论,同时又透露他本人的思想情志,使皇皇史书的“实录”更多了一种人文关怀的生命气息。
古人认为,山川风物乃“诗人性情之根柢”[3]475,是故,《文心雕龙·物色》有此妙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4]694-695“江山之助”既是刘勰本人基于社会历史事实得出的精到总结,又因无数文人骚客的自觉体认、丰富演绎而成为一种精神指南。后人正是注意到了游历对于司马迁及《史记》的重要影响,认为他“纵游江南沅湘彭蠡之汇,故其文奇恣荡轶,得南戒江海烟云草木之气为多”[5]401,“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6]381。司马迁生性爱奇,他乐于探幽寻胜,而这种经历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他的爱奇之心,并直接给他的文思、辞章灌注了一股独特的奇气。《史记》之所以被誉为“无韵之《离骚》”[7]53,一部分原因即在于《史记》与《离骚》都具有爱奇、写奇的共性。而《史记》的“奇”元素,自然与太史公的游历密不可分。
作为后人心向往之的历史人物,司马迁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不仅表明了太史公的重要影响和价值,而且深刻地呈露了后世文人自身独特的审美趣味与精神特质。相较前代,唐人游历之风颇盛,且多追慕司马迁者,留下了不少名篇佳句,如白居易之“斯人死已久,其事甚昭彰”(《杂感》),牟融之“落落长才负不羁,中原回首益堪悲”(《司马迁墓》),都对司马迁其人其作彪炳史册、个人命运落拓可悲的事迹有较为深刻的表达,可谓是唐人体认和追慕司马迁的代表性作品。
关于司马迁的文学作品,在宋代以后泉涌般地出现,而许多诗词都认识到了游历对司马迁自身及其作品(《史记》)的重要意义,如“子长游览文章健,张掖滇池在此行”(元代宋褧《送王君实西台御史·其九》),“子长好远游,为文时出奇”(明代王绅《送郑叔贞从驾巡边三首·其三》),以及宋人马存在《赠盖邦式序》一文中的著名论断:“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而观之,岂不信矣。”[8]显然,这些表达都既准确、客观,又各有特色,别样多姿,将司马迁的文学形象刻画得丰富而立体。也正是在大量文学作品的书写中,“子长游”的表达形式渐渐脱颖而出,成为众多表达中极具典型性的文学典故和书写惯例,并迅速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精神典范意义的固定语,为元、明、清等不同时代的诗文作者不断体认。
二、“子长游”的主要精神内涵
“子长游”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审美词组,是在宋人手里(集中在诗词作品)开始得以充分书写的,并为后世不断沿用和发展。宋人极其重视个人的游历之行——青年时期进行一番壮游更是大部分读书人的必然选择。如前文刘勰所提之“江山之助”,这一观念得到了宋人的广泛呼应,如黄庭坚认为“江山为助笔纵横”(《忆邢惇夫》),宋人在诗文创作、游历实践和思想总结等诸多方面,都对“江山之助”有着丰富的表达和演绎,表明其对宋人确实有着重大价值,“一是增长学识经验,二是陶冶人格性灵,三是启迪诗思诗艺”[9]108。而“子长游”这一词组的出现和定型,也正是在这一重要语境下实现的。宋人有着大量直接使用“子长游”的诗词作品,关注的精神内涵也颇为丰富,往往多从司马迁及《史记》本身出发,结合时代或个人趣味加以发挥,进而影响到元、明、清多朝文人对于“子长游”的书写。
总而言之,宋人始确立的“子长游”这一固定用语,在多个朝代文人的不断体认下,所指向的精神内涵大概可归为四点,具体如下。
其一,“子长游”指向了如司马迁般探奇览胜的个人爱好、想法与行为。如“善弈从来数弈秋,胜游今作子长游”(宋代喻良能《次韵马叔度再用前韵见寄》),“何当共作子长游,南浮沅湘北齐鲁”(宋末元初于石《次韵赵九翁》)等,都是一种试图将自身的游历观念、行为与“子长游”相呼应的表达策略。而且,在类似的书写中,禹穴、潇湘等皆为惯用地名,一则在于子长曾游历其地,再则因为后人也多前往禹穴、潇湘等地寻幽览胜。这一层指向最具有现实性,也最贴近“子长游”的历史事件本身,但其使用也相对最为普通,缺乏作者个人内心复杂情感的表露。
其二,“子长游”指向了心怀壮志、渴望建功立业的蓬勃之气。这样的作品如“少年浩荡子长游,回首人间道路修”(宋代苏竹里《和高斯立见寄》),“向来苏武节,今日子长游”(宋代文天祥《长溪道中和张自山韵·其二》)等,都是在“子长游”的书写中寄寓了作者自身的豪情壮志,心系功成名就。因为司马迁的年少壮游本就意气风发,后来他的游历虽添了“发愤著书”的愤懑,却一生秉持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心,写出名垂青史的《史记》,为后人所称许、规模。故而,后人在“子长游”的表达中反复宣明自己的丈夫之志也是合情合理的。
其三,“子长游”指向了博学淹通、文采卓越的才华与能力。诗作如“昔年曾作子长游,万里江山一客舟。揽得瑰奇满胸臆,怪来开卷思悠悠”(元末明初王祎《题万里江山图》),作者相信进行了一番“子长游”,便可以使人胸怀瑰奇、文思泉涌;“他年会作子长游,剩赋新诗满人耳”(明代李进《丹阳道中》),诗人期待自己日后能通过展开“子长游”而赋得新诗、载誉于人;“文从子长游,书爱率更令”(清代沈远翼《和仁崖中枢韵赋谢黄鹿泉农部》),更是直接表明了自己对于“子长游”的向往,以及“子长游”对于其“文”的重要影响。毫无疑问,他们都充分意识到了游历对于司马迁学识、才气的重要意义,才会同样相信进行“子长游”确实提升了自身的文学修养。而实际上,正如无数文人对于“江山之助”的认同和实践一样,“子长游”这样一种选择,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的才识和创作提供了帮助。
其四,“子长游”指向了怀才不遇、遭逢苦难或生活寡趣境况下一种获取精神慰藉的方式。如“莫苦回瞻白云岭,是行聊学子长游”(宋代王庭圭《送頔子还庐陵》),“蓬荜已无原宪室,江山要饱子长游”(宋代邓肃《次韵二首·其一》)等,它们都是诗人在饱经一番苦难后,寻求学作“子长游”聊以自慰。这也正是其与前三点的不同之处,因为多了一层悲情底色,而这种基于诗人自身际遇的情感抒发,又正是“子长游”最具独特性的书写价值所在。由于“子长游”背后同样要求对自身的德行、人格进行提升,当人生失意之时,诗人词客们自感无法实现个人理想抱负,便有选择性地固守德行和人格的尊严,借“子长游”这样的书写来抒发“思古之幽情”。
毫无疑问,“子长游”是后世心向往之的精神图式,它是被一代代文人共同建构起来的理想典范,但理想却又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因此,后人的不少作品也多有对“子长游”思而不得的慨叹、愧怍或无奈,这又是综合了上述第三、四点精神内涵生发出来。典型如“所愧子长游,吾行未能止”(明代张宁《画舫清游》),“早慕子长游,晚滞周南躅”(明代杨慎《送陈德润还茂州·其二》)等,当代表着精神理想的“子长游”无法实现时,诗人便借此倾诉自己在世俗世界中难以消除的消极情绪。由此亦可知,后世所追慕的“子长游”是具有蓬勃年轻之气的理想状态,在史实层面上即狭义地指向司马迁弱冠之时的壮游,而不包括史公后来经受苦难、染上悲剧色彩的游历,这是值得注意和辨析的。
三、“子长游”在宋人笔下得以经典化的原因
“宋人作诗,无不学唐,亦无不期许变唐以自成一家;从诗思、安排,到经营、表述,无不尽心于创意,致力于发明。”[10]34“子长游”在诗词中使用,首见于北宋王庭圭之七言律诗《送頔子还庐陵》:“莫苦回瞻白云岭,是行聊学子长游。”如上文所述,其“指向了怀才不遇、遭逢苦难或生活寡趣境况下一种获取精神慰藉的方式”,并在其他宋代诗词(尤其是诗)中得到大量书写、体认和发扬,逐渐成为一个后世不易的惯用词组。这个经典化的过程,在根本思维方式上得益于宋人自出新意、自造新语的创造力。同时,其又与文人之间的游历行为、密切交往、总结领悟息息相关,科举制度、印刷业和文化教育的发达,司马迁、《史记》本身在宋代的广泛传播等等,也都是重要因素。
一方面,随着社会文化、哲学理念和思维方式等诸方面的发展与转变,宋人的思想、情趣已与前人大有不同,这也直接影响到宋诗的发展,以致于宋诗与唐诗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前人对此论述已然备矣,如言“唐诗以韵胜”而“宋诗以意胜”[11]31,曰唐诗擅在“丰神情韵”而宋诗胜于“筋骨思理”[12]7,不一而足。整体说来,宋人、宋诗多理趣语、精炼语、新造语和专用语。如“诗骨”“诗肩”“诗脾”和“诗胆”等大量专用语,就是在宋人手中获得充分使用,乃至程式化的问题也明显暴露了出来。“子长游”得以在宋诗中出现,并被充分地经典化,只是宋诗理趣语、精炼语、新造语、专用语中的一个代表而已,这是与宋人之新思维、新情调紧密相关的。上节所总结的“子长游”的主要内涵,是宋代诗词完全激活、发扬了作为文学典故和精神典范“子长游”。
另一方面,单从诗歌这一文体的发展进程来看,其在唐代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成为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这就给后来的宋代诗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先天性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13]13,唐诗亦多写司马迁、《史记》者,但较侧重于其史官精神、文学成就与人格魅力的书写,且往往显得单一化、粗线条,更没有出现“子长游”这样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宋人着力于唐人未发掘之处,从而充分体认和书写了“子长游”这一精炼语和专用语,在追慕司马迁个人壮游经历、精神品格的同时,注入了具有时代特色和个体情思的新活力。
与此同时,上节所言宋人格外重视的“江山之助”观念,以及宋代文人之间密切的交游互动,也都是“子长游”得以在宋代诗词中迅速成形的重要语境。与唐人相近的,宋人也关注山川湖海、风土人情,绝大部分诗人都有丰富的游历生活,寻求在山水自然的亲近中获得写作的灵感与素材。南宋杨万里所言“江山拾得风光好,杖屦皈来句子新”(《送马庄父游金陵》),“江天万景无拘管,乞与诗人塞满船”(《江雨三首·其三》),便是自觉的领悟,诗人们往往将江山锦绣当作诗思、诗料的重要资源。而清人何世璂在《然灯记闻》中所言:“为诗须要多读书,以养其气;多历名山大川,以扩其眼界。”[14]120则完全可与宋人务求读书、不废游历的理念和实践对应起来。宋代诗人之间的过从更是极为密切,诗派、群体和个体的诗文互动、观念交流和学习借鉴多见于各种史料,这无疑为“子长游”这一语组的传播和广泛使用奠定了现实基础,并促使了其精神内蕴的丰富和深化。
此外,众所周知,宋代是中国科举制度和文化教育发达的重要历史阶段,印刷术和工商业都大为成熟,《史记》成为重要的阅读经典,这促使皇帝大臣、名师硕儒和文人士子都普遍钟好《史记》,《史记》的刊印、传播和研读蔚然成风,文人们也偏爱在文学作品中征引、评述司马迁其人其事和《史记》。“子长游”作为与司马迁、《史记》紧密相关的历史文化典故,自然易于进入文人士子的视野和书写中,并反过来在无形之中促进了司马迁事迹和《史记》故事的传播,其便在诗词作品的不断表达中得以固定下来,成为大量诗家词客普遍采用一种写作惯用语。
最后,可以发现,“子长游”的使用基本上集中在宋代以降的诗词作品中且以诗歌最为典型,在文章和其他体裁中则少有出现,这大概是与诗词讲究精炼用语、词少意丰有关。因为“子长游”显然是一个省略性的复合名词,指“司马子长的壮游或类似的游历”,若要在文中表达,则径曰“子长之游”即可,不必省略“之”字,省略“之”字,正是诗词作品中的典型作法。所以,“子长游”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是有体裁侧重或限制的,集中在诗词中表达。
四、“子长游”与后世确立的其他精神典范——以杜甫为例
实际上,随着文学作品的不断书写,尤其是文人们代复一代的游历实践和体悟,“子长游”的精神内涵早已不限于司马迁和《史记》这一源头,而是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并与其他确立起来的精神典范相互结合,形成更大的文学辐射力。
在“子长游”的经典化书写中,后人往往偏爱将屈原、李白和杜甫等人与之相提并举。其原因大概有三点:一是屈、李、杜等确是游历山川、览胜探幽之典型人物,此与司马迁相类似;二是子长多受屈原影响,而李、杜又多浸有史公之气,他们在性情、德行、才学与作品等诸方面都有一脉相承之处;三是屈、李、杜皆为后世宗慕之文学大家,饱受推赞,而其中又以杜甫最为瞩目,在大力尊学老杜的语境下,宋人开创的“子长游”往往与子美有所呼应,将其并论之作尤多,特别是“杜工部似司马迁”在宋代诗话、笔记中的提出,“标识着成就卓越、登峰造极的意蕴指向”[15]107。因此,接下来将以后人杜甫形象书写的部分作品为例,探讨其与“子长游”相互呼应、深化和补充的精神内蕴。
宋代周端臣之《送翁宾旸之荆湖》,乃是将司马子长、杜甫之游历并举的名篇,诗曰:“君不见司马子长志横秋,少年足迹不肯休。胸中盘屈奇伟气,笔力直与造化侔。又不见杜陵子美夸壮游,一身几走半九州。吟怀吐纳天地秀,作为篇章光斗牛……莫如子长子美但能事文章,蚤归来献平戎策。”此首送别之作开篇即将子长、子美的壮游互相媲美,说明年少壮游的丰富经历对他们“吐纳天地”之“奇伟气”、直干造化之“笔力”“篇章”的关键价值,诗末更是劝勉友人(亦是自勉)当以子长、子美为精神典范,写就奇伟篇章,为国家献上平戎之策,成就一番功业。其他宋人类似之作,如“杜陵半九州,诗史入嘉话。马迁多经践,有文资博雅。”(宋代李流谦《峡中赋百韵》),“奇探马迁作史意,老气杜陵出峡年。何当囊笔撰杖屦,与君题遍名山川”(宋代徐瑞《元日题仲退漫游四藁后》),亦意在强调游历之行对于杜甫“诗史”和司马迁《史记》及其文采的意义,其中二人作品之“史”,是多受益于他们的游历之“史”的。
再者,子美强调读书万卷、行路万里,本就与子长相合,更添杜甫平生多流离颠沛,其“游”中大半乃漂泊之“穷游”。子长弱冠之壮游虽非“穷游”,然其父司马谈抑郁而终,尤其是当他身遭李陵之祸却不得不继续修编《史记》后,子长的“游”,便同样是沾染了浓重人生艰辛和悲剧色彩“穷游”,这种“穷游”更多地指向精神世界的穷困与苦难。从此点看,子长、子美的“游”便有了更深一层的契合,无怪乎后人云“杜陵流落诗转豪,子长历览文始古”(宋末元初尹廷高《丙午端阳抵郡》),“子长好远游,为文时出奇。子美遍涉历,穷达皆寓诗。斯文千载事,藉此清淑资。羡子有深缘,遭遇天人知”(明代王绅《送郑叔贞从驾巡边三首·其三》)。实际上,可以将他们对于子长、子美有所侧重的评价视为一种“互文”,因为这些看似区分开来的评价几乎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共同适合于褒赞司马迁和杜甫,而两人的结合也正为后人树立了一种更为丰富、深刻的精神典范。
“古人的‘躬历山川’,不仅为了游山玩水,而且是为了考察古往今来历史文化变迁的陈迹,从而获得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的浩茫的历史意识和悲壮的使命感”[16]56,子长如此,子美亦如此,而且他们的山川之游更是系于“与古人同情、与先贤同心”的人文情怀,也正因此,后人往往可在子长之游中看到孔子、屈原的身影,又在子美之游中听见子长的回音。而子美更在诗文技法、情调胸气上多法史公,即刘熙载所言:“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17]60这就使得“子长游”(和“子美游”)之“游”在现实行动层面的基础上,更深入到了精神心理层面上的共通与共鸣,是可谓“游于心”和“游于艺”,而非仅游于一人之口目,这对于后代文人的人格影响是深远的。
凡此种种,都使得“子长游”有了更丰富的包容力,将杜甫等后世推尊的大诗人包纳其中,为赵宋已还的历代诗人沿用和发扬。宋人述及“子长游”,非仅心向太史公,亦多想见唐人如太白、子美者;元、明、清诸朝人写“子长游”,又于此之上更添了宋人气调。相继共通,而根柢则直指个人心志也。正是在这般“层累性”的发扬中,“子长游”的书写既在代代相传、不断演绎的公共传播领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又不失在具体作者、作品的私人书写领域中的个体性意义。
五、结语
运用典故,是中国文学(尤其是诗词)中的一大特色,其生成与内涵也往往与具体的历史语境有关。“在辗转的使用、转述过程中,典故的意义被一代又一代使用者们分化、综合、积累、变异,在一个典故中,意义的外延内涵越来越扩展变化”,也“变得越来越复杂”[18]138-139。作为一个历史文学典故,“子长游”的成形和内蕴演变同样如此。在宋代诗人开创的使用范式下,直至清末,“子长游”的表达一方面是对于相隔近两千年的太史公往事的回望与追慕,另一方面又承载着新时代和新个体的情感演绎,展露出一个史实背后值得充分发掘、宣扬的精神内核,而这也恰恰是中国文人诗意情怀和诗词创造得以传承不衰、标奇出新的一种表现,并进而不断激发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活力。
时至今日,游历、旅行之风蔚然,不唯有年轻人因求学、访友、寻胜而选择游历,各个年龄段的不同群体皆对旅游钟爱有加。但是,今日之游历,更多地受到了消费主义和物质享受的左右,反而遗失了中国古典语境下“子长游”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内涵,也间接指向了人们内在空虚和文化贫瘠等问题,这或许正是当下需要省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