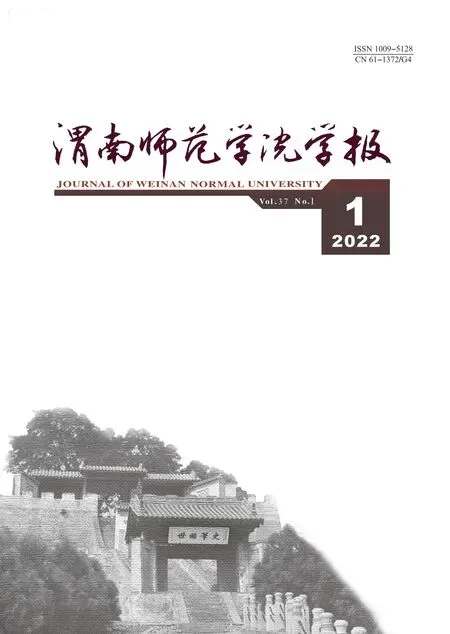柳宗元的人物传记对《史记》的师承
刘 城
(广西教育学院 文学院,南宁 530023)
柳宗元的文章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取法广博,转益多师,司马迁之文即是其中最重要的渊源之一。柳宗元对司马迁推崇备至,多次于文章中称赏司马迁,如《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云:“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而武帝尤好焉,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1]1455他还深谙司马迁之文的特色,曾于《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以“峻洁”二字概括:“《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1]2200并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坦言《史记》实乃自己为文的取法之源:“参之《谷梁传》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1]2178
柳文深得史迁之文的精髓,也得到了同辈文人的认同。在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序》中,与柳宗元并称“韩柳”的韩愈就曾评价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2]1061-1062,这个评价就连当时恃才傲物、性复偏直“于文章少所推让”的皇甫湜“亦以退之之言为然”[2]1062。在向司马迁学习的过程中,柳宗元尤其对《史记》心慕手追,其人物传记可为显例。
柳宗元的人物传记(1)本文所论柳宗元的人物传记,仅指其文集中所存以人物为表现对象并专以“传”名篇之文。《蝜蝂传》虽以“传”命名,但写的是一种动物,故不予讨论。另外,行状、墓志与碑文虽亦涉及人物描写,亦不予以讨论。师法《史记》,学界虽未有专文阐述,但一些学者在谈及司马迁对柳宗元创作的影响时,时有明察。如曾日升《论司马迁对柳宗元的影响》谈到了柳宗元对于笔下小人物的态度和司马迁一样充满着肯定与赞赏之情。[3]50韩昊然《司马迁对柳宗元的影响研究》则从给人物立传、人物典型化、借传明志和借传寄托等三方面讨论了司马迁在传记文方面对柳宗元的影响。[4]47-50顺着这些论文的启发,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探究柳宗元的人物传记与《史记》之间的师承关系。
一
在传记对象的选择上,柳宗元重视下层百姓,为他们立传并加以颂扬,此承自司马迁。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所涵纳的历史人物,不仅有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天子皇帝、王侯贵族、权臣将相,还包括身处社会底层的刺客、游侠、商贾、医生、卜者、农民、俳优等。除了把底层百姓纳入正史之外,司马迁还善于挖掘这些人物的优点及其可贵的品德节操,如他在《游侠列传》写颇受统治阶层压制的游侠阶层,虽不满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但却大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5]4054的可贵品质。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表彰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刺客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赞其扶危济困、不畏强暴,为达目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之气。在《滑稽列传》中,司马迁颂扬淳于髡、优孟、优旃等为虽为俳优却“不流世俗,不争势利”,称赏其“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非凡讽谏才能。《扁鹊仓公列传》第一次为医者作传,展现神医扁鹊的高超艺术,盛赞其“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5]3464的四处行医、救死扶伤之高尚医德。
柳宗元所写的以“传”名篇的人物传记有八篇,分别为《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梓人传》《李赤传》《曹文洽韦道安传》《刘叟传》《河间传》,除《曹文洽韦道安传》亡佚外,传世七篇的传主都是下层民众,有商人、老农、贫苦少年、建筑师、江湖浪人、普通妇女等,其中数位传主的品格节操或某类技艺颇多可称道之处。
《宋清传》中的“长安西部药市人”宋清,虽为市井细民,却有着超乎市井之道的优良品质。他待人以诚,不计较顾客的身份地位;对一时无钱付款的贫贱病人,宋清也予以善药,且从不催债,到了年终的时候,宋清估计有些顾客无法偿还药费,还常常把债券、欠条烧掉,“终不复言”。
《种树郭橐驼传》的郭橐驼虽是长安一位驼背老农,但他却善于种树。他种的树成活率高,即便是移植过来的也能存活,而且长得高大茂盛,果实结得早且多。众多同行即使学习模仿也无法比肩。更难能可贵的是,郭橐驼还能借种树之道来阐发官府治民的深刻道理。
《童区寄传》中的区寄虽是柳州的一个小放牛娃,只有十一岁,但能凭借自己的沉着冷静与机智勇敢,手刃绑架自己的两个盗贼,最后得以自救,他的英勇事迹震撼人心,以至于“乡之行劫缚者,侧目莫敢过其门”。区寄堪称是一位少年英雄。
《梓人传》写的是一个能从宏观把控全局且知人善用的建筑设计师。这位杨姓建筑师在建造房子的过程中,并不亲自做具体琐细的建筑工作,而是“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制好图纸,加以统筹规划,然后指挥其他工匠进行具体营造,建好的房屋与预期的设计无毫厘之差。
《刘叟传》的刘叟怀有驭龙之术,但却心怀国家百姓。他向鲁公进献一条龙,并提醒他未雨绸缪,最后使得鲁国在第二年的大旱渡过难关。
《史记》对下层民众的关注与颂扬,在正史之中无有出其右者。而士大夫所作人物传记,为普通百姓立传比例之高(2)关于柳宗元为下层百姓作传,可参看王青《中国平民传记的开山之作——柳宗元传记散文琐议》,《语文学刊(基础教育版)》2009年第8期,93-96页;王文远《好为“小人”谱华章——论柳宗元传记文学的“小人物”情结》,《黑河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172-174页。,所传对象范围之广,司马迁之后罕有匹及柳宗元者。
二
柳宗元在人物传记的文中或结尾处仿《史记》之“太史公曰”以发议论。《史记》多置“太史公曰”于每篇传记末尾,偶见挪于篇首和文中,借以对所叙历史人物及事件发表议论,使整篇传记在客观真实的叙述之外,还寄寓着作者的个人见解及褒贬之情,这是司马迁对史书写作方式的一大创例。“太史公曰”的书法,也为柳宗元所采纳并拓展,他亦常于文中或文末进行评述,甚至仿其而为“柳先生曰”“余曰”或“余谓”。
首先,有文末以“柳先生曰”引发感慨者,此类居多。《宋清传》文末云:
柳先生曰:“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然则清非独异于市人也。”[1]1162
此乃柳宗元就人们交往之中“炎而附,寒而弃”的现象有感而发,并以宋清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作鲜明对比。宋清虽为“市人”,却眼光远大,从不斤斤计较眼前小利,对那些“穷困废辱”者也一视同仁,不同于世俗商人为了逐利而用尽手段。与宋清相反的是,那些“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却趋炎附势,攀附权势,遗弃落难者,所作所为乃标准的“市之道”,与商人无异。柳宗元借称赞宋清“非独异于市人也”来讥讽那些以“士大夫自名”者的市侩行径。明人茅坤说该文“亦风刺之言”[1]1166,清人王文濡亦说其为“借题发挥之作”[1]1171。
《李赤传》有云:
柳先生曰:李赤之传不诬矣,是其病心而为是耶?抑固有厕鬼耶?赤之名闻江湖间,其始为士,无以异于人也。一惑于怪,而所为若是,乃反以世为溷,溷为帝居清都,其属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与向背决不为赤者,几何人耶?反修而身,无以欲利好恶迁其神而不返,则幸矣,又何暇赤之笑哉?[1]1205
柳宗元指出,李赤虽为江湖浪人,其实也是读书人,且自视甚高,将自己与李白相提并论。但他却行为怪异,把世间当成了粪坑,把粪坑当成了帝都。人们都笑话李赤,但殊不知很多人在面对是非曲与直时多数都与李赤并无二样。柳宗元提醒人们要修身养性,不要让利欲喜好迷失神志,干出荒唐之事。李朴《书柳子厚集》谓此篇“讥切当世,属意明白”[1]1210。
《河间传》亦是文末议论:
柳先生曰:天下之士为修洁者,有如河间之始为妻妇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间与其夫之密切者乎?河间一自败于强暴,诚服其利,归敌其夫犹盗贼仇雠,不忍一视其面,卒计以杀之,无须臾之戚。则凡以情爱相恋结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难恃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际,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1]3303
在这篇备受争议的作品中,柳宗元感慨道,天下不少读书人在修养节操方面,一开始如始为人妻的河间一般坚贞;朋友之间的交往也有像河间与其丈夫一样密切的。但他们最后都败给了利益。所以在柳宗元眼里,所谓的恩情是很难倚靠的,朋友之间,君臣之间,均是如此,正如宋人黄震在《黄氏日钞》所云:“《河间传》志贞妇一败于强暴,以计杀其夫,卒狂乱以死。子厚借以明恩之难恃。”[6]卷六十一
其次,有开篇以“柳先生曰”发端者。兹以《童区寄传》为例: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毁齿以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不足,则盗取他室,束缚钳梏之。至有须鬣者,力不胜,皆屈为僮。当道相贼杀以为俗。幸得壮大,则缚取么弱者,汉官因以为己利,苟得僮,恣所为,不问,以是越中户口滋耗。少得自脱,惟童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桂部从事杜周士为余言之。[1]1183
岭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居民,为了贪图钱财,不但把自己的子女养至七八岁后当货物卖掉,甚至还偷别人的小孩贩卖。有些“么弱”的成年人也没能逃脱被抓为奴的惨况。而汉族官吏只要能得到僮仆,就纵容此等恶行,这就导致越地僮仆增多,人口减少。柳宗元于篇首抨击越地的恶俗,批评官府对恶习的姑息与助纣为虐。
再次,有议论融入全文并占主导者。《梓人传》可为代表。柳宗元把自己也当作事件的亲历者,故他在文中与结尾的感叹和总结,实际也表明了他的意见与看法。他观览了梓人建造的房屋后感慨其“术之工大矣”,并从其中悟出宰相如何得众人而用之的吏治之道:
彼将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欤?吾闻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彼其劳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谋,彼其智者欤?是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为天下者本于人。其执役者,为徒隶,为乡师里胥,其上为下士,又其上为中士、为上士,又其上为大夫、为卿、为公。离而为六职,判而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连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啬夫版尹,以就役焉,犹众工之各有执伎以食力也。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其安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其远迩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于堵而绩于成也。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炫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
相道既得,万国既理,天下举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后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谈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执事之勤劳而不得纪焉,犹梓人自名其功而执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谓相而已矣。其不知体要者反此。以恪勤为公,以簿书为尊,炫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听听于府廷,而遗其大者远者焉,所谓不通是道者也。犹梓人而不知绳墨之曲直、规矩之方圆,寻引之短长,姑夺众工之斧斤刀锯以佐其艺,又不能备其工,以至败绩用而无所成也,不亦谬欤![1]1189-1190
之前介绍梓人之事,不足四百字,但柳宗元却于此处用了近650个字评议宰相之职与梓人之功。在这一大段的议论之中,柳宗元把宰相之职与梓人作了极其详细的比较。柳宗元认为,宰相辅佐天子,要如梓人“善运众工”一般,不需要事事亲自过问,而是要制定好纲领与标准,选拔好各种人才,使其各司其职,从而使天下大治。梓人的做法“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当有人提出,如果房子主人干涉梓人的规划而导致房屋坍塌,这个责任应该由主人承担而与梓人无关时,面对这样的假设,柳宗元予以反驳:
余曰:不然!夫绳墨诚陈,规矩诚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由我则固。不由我则圮。彼将乐去固而就圮也,则卷其术、默其智,悠尔而去,不屈吾道。是诚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货利,忍而不能舍也,丧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栋桡屋坏,则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1]1191
他认为,梓人如果因为贪图主人的报酬而按主人的意见改变建筑设计,导致房屋毁塌,那么这也是梓人的责任。梓人面对主人的强制干涉,应该毫不犹豫地离开。在文末,柳宗元还做了总结:余谓梓人之道类于相,故书而藏之。[1]1191认为宰相治理天下和梓人造屋极为相似。《梓人传》貌似写梓人,实乃借写梓人而实论宰相佐天子之道。柳宗元的为文之旨,清人林云铭颇能参透:“相臣贵知大体,而大体在于识时务善用人。天下之治乱安危,即相臣所以为能否,非可以才艺见长也。陈平不对决狱,丙吉不问杀人,虽未必能尽为相之道,第其言颇得不亲小劳不侵众官之意,实千古相臣龟鉴。是篇借梓人能知体要,痛发其通于相业。段段回应,井井曲尽。”[1]1199—1200
柳宗元借为市井细民立传,发表自己对政治时事及世态人情的褒贬之意。他不但常似司马迁般在文末申发观点,偶尔于文章起始处发论,甚至还将议论功能扩大,使其占据全文的中心,这也是柳宗元对司马迁“太史公曰”书法的一大推进与拓深。而诸如《梓人传》《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这类借写他人而阐明作家个人见解主张的传记,更是被后人称为“他传性托传”,其作为以传人为主的文学性散文,主要通过作家的文学虚构来完成,作家通过生动的叙事与形象塑造来写实并发表议论,而这些“议论”的重要性常常超越了“传记”的部分,从而使本以传人为目的的传记文变成了作者表达思想或情感的平台。柳宗元的这类传记“突破了传统史传体式,使得传统的‘传’由单纯记述历史的散文发展成为极富文学艺术性的散文,从而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新天地。”[7]91这可视为对《史记》的一大突破。
三
为他人立传,融自己的身世之感于其中。司马迁遭李陵之祸而惨受宫刑,故于《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等篇章流露出对君主专制的不满;经历过“家贫,贷赂不足以自赎”的惨况,则著《货殖列传》《平准书》对财富的重要性给予肯定;为李陵辩护而身陷囹圄却无人施救,故尤钦慕《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中那些“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游侠与刺客;狱中亲历过狱吏的苛刑,即在《绛侯周勃世家》《酷吏列传》中逼真地加以描述;遭遇巨耻而隐忍苟活,则于《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等悲剧英雄的传记中展现出震撼人心的悲剧精神。
柳宗元的传记文对此亦多有效仿。柳宗元在《宋清传》叙宋清生平的同时又引发出对炎凉世态的抨击,且寄寓自己贬谪之后备尝人情冷暖的无穷感慨。清人沈德潜在《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九中评该文:“以一‘市’字发出无限感慨,后段如太史公愤激于亲戚交游莫救视也。”[1]1167章学诚也说:“柳子激赏宋清,悲穷途之无与援也。”[1]1170
在《李赤传》中,柳宗元似乎也有意借李赤的遭遇感慨自己无罪遭贬的不幸身世。李赤曾比较现实世界与厕鬼所居之异:“顾视汝之世,犹溷厕也。而吾妻之居,与帝居钧天、清都无以异,若何苦余至此哉?”[1]1204柳宗元于此隐然有对当时朝政及自己所处境遇的不满。他在描述李赤因疯癫受惑于厕而死亡之后,说道:“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与向背决不为赤者,几何人耶?反修而身,无以欲利好恶迁其神而不返,则幸矣,又何暇赤之笑哉?”[1]1205对于那些故意颠倒是非黑白、善恶曲直的当权者及势利小人,柳宗元予以辛辣讽刺,这其中也饱含着自己胸怀国家朝廷、欲除弊政却反遭政敌打击流放的愤懑之情。
《河间传》叙写女子河间如何从一个“有贤操”之德的女子堕落成荡妇,最后因纵欲导致“病髓竭而死”的过程。关于这篇文章所蕴含之深意,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如胡寅、刘定之等人认为柳宗元是“托讽淫妇人有始无卒者以诋宪宗”[8]43-49,张铁夫认为柳宗元是借“河间”来影射唐顺宗,谓其与“奸夫”——宦官以及“戚里恶少”——藩镇合谋害死了王叔文并镇压了永贞革新[9]89-94,沙培铮认为该文是以“淫妇”诋卖友求荣的程异[10]9-10,而倪豪士则认为此文是柳宗元有感于被王叔文等人背叛而作[11]47。不论作何种阐释,评论者多指出这篇文章与柳宗元亲历过的永贞革新密切相关,是他身世所感之折射。作为革新派的核心成员,柳宗元回忆起曾经轰轰烈烈但旋即失败的朝政改革,必定感慨颇多,尤其是政治巨变之中朋友、君臣之间“恩之难恃”,尤为令他“可畏也”。柳宗元在《宋清传》中也流露出类似的愤慨,他对那些“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争为“市道交”且在与人交时“炎而附,寒而弃”的卑劣行径进行了讥讽。柳宗元被贬往永州、柳州十四年之中,从未放弃重返朝廷的希望,但却罕有人能施以援手。这种深深的失望,使得他在看待人际交往中的世态炎凉时常会显得异常敏感,在为人物立传的篇章中融入此类身世之感,即可作为明证。
为人物立传,应以客观载录历史事件与塑造人物形象为主。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伟大的史学巨著,堪称“史家之绝唱”。但它异于与优于其他正史之处,更在于它乃“无韵之离骚”,在客观的写实中渗透着个人的遭际,暗寓着丰富的人生体验。柳宗元的人物传记在传写他人的同时,同样也有着读者易见的个人色彩于其中。从这点来看,柳宗元可谓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四
为文尚“洁”。司马迁《史记》为文之洁,一是擅长撷取典型事件或细节以突出人物个性,二是文辞精炼简洁,三是文章结构层次明晰。柳宗元曾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以“峻洁”二字评司马迁之文,更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自己为文“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可见,“洁”字乃柳宗元为文接续司马迁的重要纽带。清人章学诚就曾在《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说过:“柳子曰:‘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未有不洁而可以言史文者。”[12]863柳宗元参悟其法而得其髓,并于人物传记中加以规摹。
首先,在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旨的人物传记中,柳宗元亦如司马迁般优选最能表现人物个性的事迹,同时又以简洁文辞绘刻细节。《童区寄传》塑造了区寄这位少年英雄的形象。为了突出区寄的胆和识,柳宗元主要以三个场景描述区寄被劫持之时以及依次杀掉两个豪贼的表现。同时,又以细节突显人物个性,如写区寄被抓之时:“寄伪儿啼恐栗,为儿恒状。贼易之,对饮酒,醉。”[1]1183极精简的十二个字显露出区寄的智谋,正是他装作小孩子般害怕发抖地哭哭啼啼,表现出十分害怕胆小的模样,才让盗贼放松警惕,也才有了他趁贼酒后熟睡之际将其手刃的机会。他杀掉第一个盗贼逃跑后被第二个盗贼抓住,将被杀之际,他的一番话又显出他的睿智与机灵:“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1]1183寥寥数语直击盗贼贪婪的本性,最终用“诚恳”的“肺腑之言”劝服盗贼保存了他的性命。柳宗元用典型的事例、简洁的语言以及令人信服的细节塑造出人物的个性。这正是他学习《史记》的高妙之处。沈德潜在《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九中就评该文“简老明快,字字飞鸣,词令亦复工妙”[1]1188;孙琮在《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中论其“在柳州集中又是一种笔墨。即语史法,得龙门之神”[1]500。《河间传》与《李赤传》,也是如此。
其次,在那些看似描写人物但却旨在说理的人物传记中,柳宗元则是在精准刻画人物的基础上,又能把道理说得透彻。《梓人传》乃柳宗元有感于“梓人之道类于相”而作。文中有“梓人之道”的描写,梓人指挥木工“饰官署”的场景即是:
委群材,会群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1]1189
“量”“视”“挥”“顾”“曰”等几个动词即把梓人的专业素养及统筹能力彰显殆尽。而工匠对梓人的依顺,也从侧面烘托出梓人的无上权威。梓人的才能,此处仅以150余字精彩叙出。但写人并非此文的真正意图,以梓人之事来论宰相如何治国才是其内核,故柳宗元接下来用近五倍的篇幅约840字加以详细阐发。他认为,宰相应如梓人一般,对天下大局能统筹规划,并能知人善用,使百官各尽其职,而不需事必躬亲。《梓人传》既叙人物,又重在申发道理,“前细写梓人,句句暗伏相道。后细写相道,句句回抱梓人”[13]300,二者详略得当,并无枝蔓之处。故而何乔新在《春秋左传撷英序》中叹其“叙事峻洁,摛词丰润”[1]1197;吕留良则在《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柳文精选》中谓其“文以理胜,又间架峻整,文势跌宕,造语精警,可谓尽善”[1]1199。《种树郭橐驼传》名为传,实则以论为主。其人物描摹较《梓人传》更为淡化,文章仅以60余字说明郭橐驼善于种树,余下400字则转述郭橐驼所论种树之术及其与官府治民相通之理,此正是王文濡在《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三七中所说的“养人之术通于养树,传其事以为官戒,乃作者之正意”[1]1183,孙琮在《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中说的“又是一篇治人大文章”[1]1181。
再次,写人与议论并重且俱佳。《宋清传》可为一例。柳宗元仅记宋清卖药一事,进而生发出世间为人处世之道。写人叙事简洁干净,议论直截精当,难怪蒋之翘也赞此文“最简洁,议论亦好”[1]1166。
柳宗元参悟并学习司马迁为文尚“洁”的旨趣,颇为后人明察,如清人黄与坚《论学三说》以“洁”字将柳宗元与司马迁之文加以勾连:
子长以“洁”许《离骚》,柳子厚又以太史致其洁。“洁”之一字,为千古文字金针。[14]
司马迁赞屈原《离骚》文辞之“洁”,而柳宗元又以“洁”称许司马迁,由屈原而至司马迁再至柳宗元,“洁”乃是千载而下穿结三人文章之金针,黄与坚于此清楚地看到自古以来优秀作家尚“洁”的追求。而邓绎则做进一步辨析:
司马迁之称《离骚》曰:“其志洁,故其称物芳。”柳宗元又曰:“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以洁言文,规摹似稍狭矣。一言以蔽之而有余,惟深于诗故深于史也。《离骚》之志与日月争光者在乎洁,史迁言为丹青而不朽于千载者亦在乎洁。孔子不得中行,必与狂狷,以其洁也;在陈思归,择斐然成章之狂狷,而裁之者,欲其洁也。史迁生周生、孔子之后,为五千年之通史,志在续获麟之《春秋》,敢为所难,而不疑者,盖自负其洁。《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宗元以洁论迁,盖亦忖度其心而得之者,非偶然也。[15]三代篇
正是因为“忖度其心而得之”,深谙史迁文的特质,柳宗元才能“以洁论迁”,柳宗元对司马迁真乃心有戚戚焉。
五
为文尚“奇”。汉代大一统的时代背景,加之特殊的生平遭际、个人的独特个性气质,使得司马迁在著《史记》时追求一种“奇”气,写奇人、叙奇事、撰奇文、抒奇趣、彰奇志,最终使《史记》成为一部奇书。《史记》的尚“奇”,为历代评家所称道(3)当今学界对《史记》之“奇”,亦多有阐论,仅硕士论文就有数篇,如栾春磊《“奇”:司马迁的艺术追求》,辽宁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张煜《论太史公的“崇儒”与“爱奇”之变》,重庆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苏娜《论司马迁爱奇》,辽宁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罗开凤《试论司马迁的“爱奇”》,西南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佟珊珊《论〈史记〉中司马迁好“奇”的审美倾向》,长春理工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这种尚“奇”的创作理念,亦为后世文家所承袭。柳宗元在构撰其人物传记时也不例外。
写奇人。《种树郭橐驼传》中的郭橐驼可为一例。郭橐驼是残疾人,“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1]1172,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畸”人、“奇”人,他有“奇”才,即擅长种树,他人无法企及,更令人称赞的是郭橐驼能借种树阐发官府治人之道。此外,《河间传》中的“奇”女子河间,《童区寄传》中的“奇”少年区寄,《李赤传》中的“奇”文人李赤,《宋清传》中的“奇”商人宋清,都是柳宗元着力塑造的奇人形象。
叙奇事。《河间传》可为代表。柳宗元在《河间传》中叙写女子“河间”如何从一个“有贤操”之德的女子堕落成荡妇的过程。她原本“独养姑,谨甚,未尝言门外事。又礼敬夫宾友之相与为肺腑者”[1]3301,且“恶群戚之乱尨,羞与为类”。但在家族恶少的多番设计引诱之下,被一“貌美阴大者”强暴,并从此变得纵欲淫乱。与奸夫设计害死丈夫,“居一岁,所淫者衰,益厌,乃出之。召长安无赖男子,晨夜交于门”,后“又为酒垆西南隅,己居楼上……凡来饮酒,大鼻者,少且壮者,美颜色者,善为酒戏者,皆上与合。且合且窥。恐失一男子也”[1]3303,如此十年之后,“河间”“病髓竭而死”。其臭名昭著,连那些“戚里为邪行者”都不愿提及。河间作为一个女子,其人性堕落的历程,让人叹息与不平,更让人称奇。《童区寄传》中的区寄,虽为少年,但却能凭借智慧,手刃绑架自己的盗贼而全身避祸,其事也足以让人叹奇。《李赤传》中的李赤,为厕鬼所惑,把世间当成了粪坑,把粪坑当成了帝都,三番五次地跳入厕所粪坑追随厕鬼,最后溺死于粪坑。李赤所为令人惋惜,但其行何尝又不是异于常规的“奇”事呢?
司马迁写奇人,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奇志与奇趣。柳宗元同样也是借写奇人,表达自己对人生、社会以及政治的观点。从这点来讲,二人是相同的。但《史记》的“尚奇”是建立在“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基础之上,而柳宗元人物传记中的奇人奇事更多是虚构幻设。由此可见,二者于同中又有不同之处。
六
柳宗元在唐代复古思潮的影响下,为文宗法先秦两汉古文,作为汉代典范的史迁之文,自然是其师法对象。宋祁在《宋景文公笔记》中说:“司马迁《史记》为纪传之祖。”[16]卷中《史记》成为柳宗元写作传记文时的摹写范本,亦在情理之中。更由于司马迁与柳宗元的人生遭际十分相似,司马迁受腐刑之后专力《史记》,柳宗元南贬十四年而以诗文抒情,皆为不平则鸣的显例,故二人的文章均有激而发,多有相似之处。宋代罗璧也曾于《经根人事作》论及:“司马迁谓古人有激而作书。……迁罹腐刑,故有此言。即是推之……柳子厚、刘禹锡、李白、杜甫,皆崎岖厄塞,发为诗章。迁之言,信而有证也。”[17]卷二
《史记》影响着柳宗元传记文的写作,但于另一方面,柳宗元对司马迁的师承与推崇,亦在很大程度上提升着《史记》的文学地位。宋人胡应麟曾论及这层关系:《史》《汉》二书,魏晋以还纷无定说,为班左袒盖十七焉。唐自韩、柳始一颂子长,孟坚少诎。[18]卷十三胡氏谓魏晋以还世人多重《汉书》,但自韩、柳“一颂子长”后,《汉书》的地位就低于《史记》了。这种观点,实际指明了《史记》在被树立为文学典范过程中,柳宗元在其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柳宗元的文章作为文学经典,取法广博,司马迁之文即是其中最重要的渊源之一。柳宗元对《史记》文法的推崇、摹写与拓深,不仅是其文章写作的精进之途,更让其人物传记成为如《史记》般的传记文学经典,同时亦是《史记》经典化历程中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