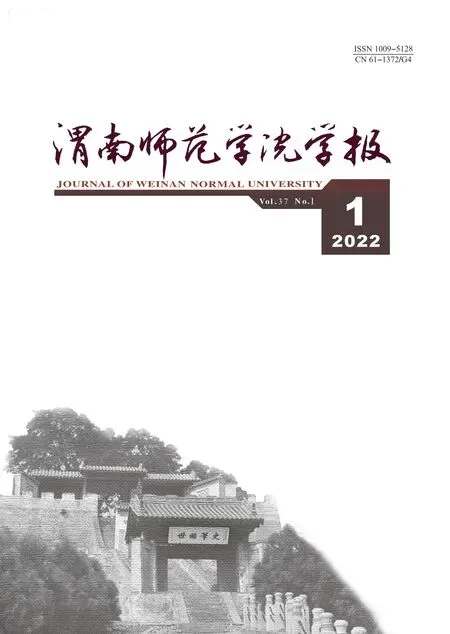《史记》单传结构论
魏 耕 原
(西安培华学院 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西安 710125)
《史记》以记叙人物为中心,本纪、世家的一部分,也带有纪传合体与世家与列传合一的性质,如《项羽本纪》《留侯世家》即是其中典型。列传则分单传、合传、类传以及附传。凡是重要人物则树立单传。而本纪或世家与列传合体者亦可视为“单传”,《史记》不少名篇都见于其中。它们的中心不同,结构亦各异,注视其中规律特征,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一、悲剧人物的对比结构
本纪中的项羽、高祖、吕太后三纪,既记当时之大事,亦叙其人之经历,而且人物刻画生动,故可视为其人传记。至于秦始皇、文、景、武四纪,虽然立名与项等三纪无异,然皆为大事年纪,纯属“纪体”。世家中的孔子、陈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虽名为世家而实属传体,因其人重要故晋升为世家。其中《绛侯周勃世家》为父子合传,《梁孝王世家》仅简略记事。
列传中单传,先秦人物有司马穰苴、伍子胥、商鞅、苏秦、张仪、穰侯、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乐毅、田单共11人;秦汉时人物单传,有吕不韦、李斯、蒙恬、英布、韩信、田叔、刘濞、韩长孺、李广、司马相如,其中秦3人,汉7人。《太史公自序》为全书总叙,属于传之别体。“纪”与“世家”可视为单传者9人,与此合为30,为数亦不算小。这些人物在当时各个领域均属一流或重要人物,故特立单传,或本纪、世家式的单传,如项羽、孔子、陈涉等。
在这30个人物中,带有悲剧性质,又采用了对比结构者,有项羽、高祖、春申君、李斯、韩信、李广、韩长孺等7人。《史记》人物大多带有悲剧色彩,若从传记结构的对比看,以此七人最为显著。其所以采用对比结构,就在于把得志与不幸对立,壁垒分明,增强悲剧气氛,从而揭示悲剧形成的原因,在各种现象中显示显形或隐形的规律与人物命运之关系。
其中《韩长孺列传》对比关系最为显明。韩长孺即韩安国,为梁孝王的中大夫,在吴楚七国之乱中,拒吴兵东进过梁,以“持重”显名。因梁孝王骄奢引起其兄景帝的猜忌,一时关系紧张。安国通过景帝之姐痛诉,先言梁孝王使吴楚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这是捍卫长安京都的功绩。至于“出称跸,入言警”,是因“梁王父兄皆帝王”,而且“车旗皆帝所赐”,故“以夸诸侯,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然朝廷“辄案责之”,搞得“梁王恐,日夜泣涕思慕,不知所为”。他又利用窦太后宠爱梁孝王,说“何梁王之为子孝,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怂恿太后出面。终于解决这场棘手的“皇室家庭纠纷”,展示其人善于揣测皇室心理、长于游说的才能,而名重朝廷。
其后梁孝王欲求为太子增加封地,“恐汉大臣不听,乃阴使人刺汉用事谋臣”。袁盎被刺后,景帝怒,汉使至梁“举国大索”。情势紧急,安国哭劝梁孝王,出谋者自杀,剑拔弩张的矛盾才缓和下来,“于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国”。梁孝王卒,安国坐法失官,以五百金送太尉田蚡,窦太后、汉武帝素闻其贤,又让他做了朝官,乃至御史大夫。汉武帝轻启边衅,欲在马邑旁包剿匈奴,当时李广、公孙贺等皆属护军将军韩安国,然匈奴闻知有伏兵而逃遁,皆无功。至此他走上了仕宦的顶峰,以后命运屯蹇。
丞相田蚡死,欲由他代理,因为给天子导引而堕车伤足。“天子议置相,欲用安国,使使视之,蹇甚”,乃更以他人为相。失去一次难得机遇。后被派前线对付匈奴,因兵少处处被动,“后稍斥疏,下迁”。接着其传说:
而新幸壮将军卫青等有功,益贵。安国既疏远,默默也;将屯又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罢归,乃益东徙屯,意忽忽不乐。数月,病欧血死。
韩安国本为法家、杂家之学,游说是其所长,而领兵才能似逊之。加上卫青以外戚为武帝倚重,他自然被疏远。派给他的兵少,故处处受制于敌。又调东边驻守,等到贬黜,幽愤吐血而死。他在梁时,能左右逢源,名声升涨,然一旦入朝,便节节走下坡路。对于匈奴则主张和亲,与武帝抗击的策略相左,故不被重用。在前线不幸的遭遇,与李广颇为相似。在梁之得志与在朝之失意就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安国两次劝说极力详写,文字亦复生色。对于前线的失意虽付诸简叙,而处处见出不得志。吴见思说:“韩安国说太后处,说梁王处,写得极其精神,是史公得意之笔。”又言:“前半兴头事写得鼓舞飞动,固妙。乃后半幅韩安国退时失运,殊觉厌厌气尽,文字亦写得厌厌气尽,其奇妙如此。”[1]7册44这是从叙事之写法上见出对比。李景星则言:“前半篇步步写其得意,后半篇步步写其不得意;前半篇以张羽、田甲诸人为趁,后半篇以王恢、卫青诸人为趁,赞语又牵入一壶遂为最后陪结。四面夹写,头头是道,其实只完得一个韩长孺也。”[2]99这是就对比之中陪衬而言。传末赞谓“观韩长孺之义”,“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太史公自序》说作传之由是因其“智足以应近世之变,宽足用得人”,故立单传以重其人,以对比凸现不为汉武帝重用的悲剧命运,寄予了深厚的同情。
比起《韩长孺列传》,《李将军列传》的对比与悲剧气氛更为鲜明而浓烈。李传叙写上郡遭遇战、雁门出击战、出定襄击匈奴三战,把李广过人之胆略,从受俘的网络中飞腾上马之奇勇,镇定自若的魄力,作了多维度的立体式刻画,而最后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一战,却受不白之冤被逼自杀。一代名将未能战死,却死于不愿上军事法庭的委屈之中,被汉武帝与卫青双管齐下的挤压逼于死地。天下尽哀,皆为流涕,见出李广之死的悲剧的震撼,是当时最大的冤案。李广身经七十余战,特选此四战构成对比,正是此传特别经营的大结构。而传中几乎处处无不用对比,文帝与公孙昆邪的评论,正是“天下无双”与“子不遇时”的对比,确定全传悲剧的调子。与匈奴射雕者、名将程不识的对比,显示不世之才;与才能不超过一般人的李蔡对比,以见对卓绝人的压抑。即使射虎也有“中石没簇”与“终不能复入石矣”的对比。传赞的“悛悛如鄙人”与“天下尽哀”,“口不能道辞”与“下自成蹊”,无不处于对比之中。这些大小对比都以才气无双而命运最不幸为中心,环绕在它的四周,整体与局部无不处于大小不同的对比中。运思之深和布局之精,即使在《史记》中亦为少见。“序杀三人处,纵马卧处,生得腾马处,大黄射裨将处,极力摹写”,而“首以文帝叹其不遇,末以武帝诫其数奇”[1]7册52,贯穿前后,其意亦在对比。真是八方出锋,四面对比,通体震动,可称绝佳之文。
《项羽本纪》为一篇大文,三年反秦与五年楚汉相争,其间千头万绪,记述显得了如指掌,而且传主的呼啸歌哭、喑噁叱咤神情毕现。写大战尤为出色。但于总体结构,前人言之却很分歧。宋人李涂说:“史迁《项籍传》最好,立义帝以后,一日气魄一日;杀义帝以后,一日衰飒一日,是一篇大纲领。”[3]72李晚芳亦言:“此篇中纪羽由微而盛,由盛而亡,中以义帝为关隘。羽未弑帝以前,由裨将,而次将,而上将,而诸侯上将军,至分封则为西楚霸王。始以八千而西,俄而两万,俄而六七万,至新丰鸿门则四十万,其兴也勃焉。及弑帝则日衰矣。以私意王诸侯,诸侯不服。由是田荣以齐反,陈余以赵反,征九江王而九江王不往,战田横而田横不下,困京索不能过荥阳,杀薛公而东阿失守,使龙且而龙且击死,委司马长史而司马长史败亡。至垓下,所谓四十万者,忽而八百余,二百余,二十八骑,至无一人还,其亡也忽焉。一牧羊儿,所系如此,可见名义在人心,不可没也。”[4]27所言前后之差异甚是,但归结到义帝,恐怕其人未必有如此大的政治影响,亦非一牧羊儿的影响所能决定。李景星说:“大旨以分封侯王为前后关键。分封以前,如召平,如陈婴,如秦嘉,如田荣,如章邯事,逐段另起一头,合到项氏,有百川归海形势。分封以后,如田荣反齐,陈余反赵,周吕侯居下邑,周苛杀魏豹,彭越下梁,淮阴侯举河北,逐段追叙前事,合到本文,有千山起伏形势。”[2]12所言不无道理,然尚未透彻。项羽之失败,分封诸侯固为重要原因,但作为全文转变之枢纽,并非由此而始。冯其庸认为“鸿门宴”与“分封诸侯”,“在全文结构上,也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是文章转折的关键”[5]273。这似乎是在李景星“分封诸侯”上又补充了一点。
关于结构的划分,是按叙事本身的形态划分,还是从政治着眼划分,有时二者结合为一,有时并不成为一个焦点。项羽失败的原因应当从“鸿门宴”开始,这也是拉开楚汉相争的序幕,即由反秦转入楚汉相争。从此他的敌人就成了刘邦,而“鸿门宴”则为大错铸成的起点。论者有怀疑“鸿门宴”的真伪,而就文章说真伪则置之度外。再则此前“基本上是以叙事为主,具体描写的地方较少,……那么,‘鸿门宴’这一段文字,作者就很自然地变换了一种写法”[5]273。此前的“巨鹿之战”每为人称美,却又是那样粗枝大叶,而此后的“垓下之围”又是一招一式地精雕细刻,如果没有“鸿门宴”的过渡,就可能尾大不掉。取其主干,则巨鹿—鸿门—垓下,就成为“三部曲”:胜利—枢纽—失败。而垓下之败的浓墨重彩,对项羽悲剧的渲染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至于前后之对比,前人言之明晰,就不消再说。
《春申君列传》也是以对比为结构。前详叙说秦昭王之辞令,中叙止秦之伐楚,约为盟国;次言与太子为质于秦数年,设计使太子归楚,返归后为相,为相二十二年为诸侯合纵伐秦失败,“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以下专叙李园进其妹于春申君而有身,再进楚王,生子为太子,恐春申君语泄而刺杀之。其间门客朱英以“毋望之祸”劝之而未纳,故及祸。叙此事及详密,与前文形成前后对比。太史公曰:“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受制于李园,旄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指出“明智”与“旄”(昏乱糊涂)的对比。前后大相径庭,分明为“两截人”(凌稚隆语)。李景星说:“通篇可分作两截读,而以‘为楚相’三字为中间枢纽。为楚相以前,极写其致身之由:如说秦昭王也,归楚太子也,轰轰烈烈,活现出一有作为人举动;为楚相后,极写其杀身之故:如邪说易入也,忠言不用也,糊糊涂涂,又活脱出一受愚弄人心肠。……论其心术人品,与吕不韦如出一辙。”[2]73春申君为了固权邀宠而死于非命,故凌稚隆说:“太史公谓平原君‘利令智昏’,余于春申君亦云。”[6]5册369
此篇在对比之后,司马迁又在文末春申君死后说:“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特意以做对照,以侥幸者无有善终,而成为历史规律。吴见思说:“初读《春申传》时,因想吕不韦盗秦,黄歇盗楚,是一时事,何不以作合传,乃史公偏不双序,却于传后一点,有意无意,眉目得顾盼之神,而笔墨在蹊径之外,岂可易测乎?”[1]5册80地隔南北,事属异国,揆其事理,则如出一辙。从行文看,嫪毐事忽然而来,又忽然而去,意在指出无独有偶,引人长思。也给结构大对比之外,添以颊上三毫之笔,使对比更加生辉。
《李斯列传》附赵高与秦二世事,《史记》不为二世立纪,不为赵高另立传,均一并纳入本传,故称一篇大传,似兼有合传性质,然处处以李斯为主,视作单传更佳。前叙上《谏逐客书》,协助秦始皇焚书,统一文字等。而“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之叹,为对比之枢纽。以下则叙受胁迫于赵高,终受其害而被腰斩,形成盛衰之大对比。“李斯凡五叹,而盛衰贵贱俱于叹中关合照应,以为文情,令人为之低回”[1]5册41。一是见厕、仓之鼠而叹不得富贵,二叹物极将衰,而不能舍弃富贵,三叹遭乱世不能舍弃权势,四叹失势被囚而富贵不能常保,五为临刑而叹,发追逐势利之忏悔,欲作布衣而不能的人生痛悔。构成对富贵权势的五部曲:企慕—极盛难止—贪权而妥协—被囚而无力回天—临终对一生的懊悔。如果从外层看,最后一叹与前四叹构成鲜明对比;若从内层看,二叹预感前景不妙,则为对比的界标。若依后者,此前为得行己志,此后则失意受制于人,亦为泾渭分明。此传自此叹之后,主要以与赵高对话组成,以对话刻画两种心理,至为缜密。李斯“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揭示了一个有绝顶智力的政治家的悲剧,悲叹的对比全从李斯口中显出,患得患失,乃至无所不至。志在富贵,而又不舍,终归取祸。从前后安排看,“《李斯传》传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变法诸事仅十之一二,传高所以乱天下而亡秦特十之七八。太史公恁地看得亡秦者高,所以酿高之乱者并由斯为之。此是太史公极用意文,极得大体处”[7]354。邵晋涵进而言之:“以秦亡结《李斯传》,见秦之亡由李斯,赵高何足责哉!”[8]631这则是史学之价值,亦可见出此传之重要。
综上可见,对比是司马迁结构文章的重要方法,有对比才有鉴别,才能凸显事物最本质的方面。从文章学看,有隐形和显形对比之别。项羽、春申君、李广、韩长孺诸纪传属后者,高祖、李斯则属于前者。如《高祖本纪》自灭楚为帝之当年起,便忙于扑灭所封诸将的反叛,直至去世之上年,因击英布受伤,却医不治。深感功臣诛尽,无人为他看守这个大摊子,老泪纵横,未久郁郁不欢病死。这与称帝之前的绝大成功,实质也构成对此。《淮阴侯列传》,前写佐汉灭楚功绩,中以求封齐王为转折点,以下则为武涉、蒯通劝其反汉而不反,接言云梦被擒,以及怏怏不欢,最后以叛名而死于吕后之手。前后亦成对比。至于合传中的对比,比单传就更为复杂,更能见各人之风采,无关本文,此处不论。
二、一分为二结构
单传容易平铺直叙写来,缺少变化。然《史记》单传中的春秋、战国及秦汉间人物,处于多事之秋,一生前后处境各异,变化极大,故多采用一分为二结构,即二分法结构,甚或一篇之中因前后事迹差异极大,一经分开,顿成“两截文”,于结构则自成一体。
《曹相国世家》于此最为典型。前半篇叙反秦、楚汉相争的战功,以“取之”“击之”“攻之”为提缀,其中“破之”所用居多。大汉建立后的平叛亦复如此。在简洁的叙事中,自成一种节奏。而自惠帝元年为齐丞相开始,则变化了另一种手法。为齐相时叙出为政趋向,本之黄老清静之术。将代萧何为相时出之对话,文法为之一变。为相专就饮酒写来,“饮醇酒”“辄饮以醇酒”“复饮之”“醉而自去”,以及“饮歌呼”“醉歌呼”“亦歌呼”反复缭绕其中,读来津津有味,娓娓动人。与前粗略的快节奏,一变而为山间小溪缓缓流淌。如此不治事的执政方式,引起惠帝诧异,又借对话中的几番对比指出萧规曹随的原因,笔法不停变换,总以舒缓为主。为将之紧凑与为相之舒徐简直判若两人。前为实写,后为虚写,亦为奇特。
所以,吴见思说:“初读曹相国战功战胜攻取,自然是坚忍豪迈一流人,其治天下也必以猛济。而后半清静黄老,写得优柔懦懦。为相者若另换一种人,作文者亦另换一种笔,岂非千古奇事,千古奇文。”又言:“此文是两半篇体,前半是战功,后半是相业,中间局法神理,照应关键,原成一片。”[1]4册52牛运震亦言:“曹相国参似是两截人,《世家》亦是两截叙法。前篇叙其战功,后篇载其相业。前篇‘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云云,为战功作结;后篇‘百姓歌之曰’云云,则结其相业也,界段极为分明。然前篇叙战功处,带载‘高祖二年,拜为假左丞相’,又曰‘以右丞相属韩信’,又曰‘以参为齐相国’,又曰‘以齐相国击陈豨、将张春军’,又曰‘以齐相国从悼惠王’云云,固已为汉相、齐相张本。篇首载参为沛狱掾,萧何为主吏,早伏萧何推荐曹参之根,篇末借百姓歌萧、曹双结作应,真是一脉贯穿文字,使人读之,不觉其为两橛也。赞语一半收战功,一半收相业,遂与《世家》表里隐映、叙断相生云。”[9]152吴氏指出“两半篇体”,牛氏进一步指出前后一脉贯穿,战功与相业界划分明,分析结构,切中肯綮。
与之相仿佛者,则是《吕太后本纪》。前半写残害戚夫人与其子赵王如意,欲鸩高祖外妇所生齐悼惠王刘肥。再叙孝惠死后封诸吕为王为侯,接叙幽杀已立为帝的孝惠太子,又幽禁饿死诸姬之子赵王刘友,且以诸吕嫁刘氏诸王,还使人杀燕王子,一直到死方休。后半篇写吕后死后,诸大臣诛杀诸吕,吕氏集团如雪山崩溃、灰飞烟灭。前后亦为两截。牛运震说:“王诸吕、诛诸吕是一篇大关键。……吕氏、刘氏,一篇眼目,故屡屡提掇,点逗生情。”[9]48无论前后两橛,前者事迹复杂却条理井然,后者一时匆迫而神气安闲,千头万绪却一丝不乱,前者百事丛集,后者聚集一点,都能从容不迫。两截文字以吕后生前死后划分,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陈涉世家》前半叙大泽乡起义,先起于垄上怅叹,起事又杂夜火狐鸣、烹鱼得书诸异事,中间交错对话,俨然传体。为王以后为后半,叙反秦各路军蜂拥而起,接近世家体,亦属“两截文体”。只是在文后补出垄上故人被杀,描写世情生动,以与文首呼应,也见出陈涉失败的原因在于为王后不能获得民心,故诸将不附。《商君列传》以商鞅变法成功与国家强盛为前半,后半终归失败而身死,前后呈现两截。前有与甘龙之辩论,后有赵良与商鞅的反复辩难,前后相映。前叙事有移木予金的情节,以之明法令之不虚;后有关舍验证的情节,揭示“为法之敝一至于此”。均属前后对比,连贯一片脉络。《伍子胥列传》前叙父兄遇难,伍员逃国至吴,后写其报仇雪恨,遭谗逼死。前半插叙申包胥哭秦廷,后半末了补叙白公复仇不遂,前为对比,后为对照,各自生色。文分两截,中心则统一于复仇之怨恨。犹如《商君传》以法为中心。牛运震说:“《伍子胥传》以赞中‘怨毒’二字为主,篇中屡屡点次报仇雪怨诸事,是一篇极阴惨文字。伍子胥仇楚平王,此正主也。他如伯州犁仇楚平王,郧公弟仇平王,吴夫差仇越勾践,白公胜仇郑人,又仇子西,皆陪客也。”[9]171
总而言之,这些“两截文体”,一来是依据人物行事,自然成文;二来是文似看山不喜平,调动各种手法打破平衡,或实虚互用,或前后穿插,都围绕一个中心,使全文脉络贯通,这就要在结构上苦心经营。《史记》之传,一篇有一篇模样,一篇有一篇作法。即是同样的一分为二的结构,也都是姿态各异,风格迥别,体现善于组织大结构以及安排局部小结构,变法多端而又有能随圆就方的艺术才能。
三、以附传陪衬为结构
在《史记》的单传里,常常带有附传。这些附传因事有涉及,不得不记者,若作成合传,事迹无多,不够标准,另立单传则更不合适,就附之于单传,这样一传就可以记载更多的人物。而一经附入单传,结构必然另起波澜。如果在重大事件上,事有先后,即顺流直下。至于事迹与传主相关,而插入空间较大者,就需在结构上有一番安排。无论何种情况,结构就有了新的变化。安排恰当,不仅使传主生色,而且能揭历史的规律,垂鉴后世。
如果事迹与传主相类,而且时有先后,就随文插入,顺带叙出,也陪衬出传主的个性更为鲜明。《吕不韦列传》中的嫪毐附传,即属这种情况。当吕不韦与秦太子之子子楚达成政治交易的协议后,设法使子楚逃归,原为邯郸歌姬与他同居而怀孕者,献给子楚而生子政,因子楚父亲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便为太子,赵国为了两国关系的亲近,即让归秦。一年后子楚即位,以吕不韦为相。子楚即位三年死,太子嬴政立为王,吕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通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就找来替身嫪毐,设法送到太后身旁,以宦官身份“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其人政治欲望亦大,欲步吕之后尘,“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然好景不长,始皇九年,事被告发,并言与太后私乱生二子。经“秦王下吏治,果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于是嫪毐及与太后所生二子被杀。秦王欲诛吕不韦,“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暂未致法。次年免其相位,使出就国河南。一年后,又因“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变,徙之于蜀。吕不韦失势恐诛,“乃饮鸩而死”。
“太史公曰”又补叙说,告发事起,“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而吕不韦由此绌矣”。
吕、毐事有先后,情势相近,故连带叙下,毐死而吕亦自杀,传主事亦为完整。毐之作为吕之替身,政治作用远不及吕,故作附传,连带叙写。吕之自杀因毐事发,也就一并叙完。这种结构顺其自然,而且反衬出吕不韦数十年经营的“奇货可居”“欲以钓奇”终归失败,不可为训。“嫪毐反攻蕲年宫事,若入文信侯传中觉无谓,而嫪毐无传,故借赞中发之”[1]6册22。而附传之作用,牛运震说:“《吕不韦传》附嫪毐,鄙夷不韦甚矣。叙嫪毐家僮与舍人,往往与不韦映照,此其用意深处。”[9]214李景星说:“吕不韦是千古第一奸商。尊莫尊于帝王,而帝王被其贩卖;荣莫荣于著作,而著作被其贩卖。幸而以鸩死结局,使人知始而贾国,继而贾名者,其终也归与贾祸。通篇以‘大贾人’三字为骨,以下曰‘贩卖’,曰‘累千金’,曰‘奇货可居’,曰‘以千金为子西游’,曰‘以五百金与子楚’,曰‘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曰‘欲以钓奇’,曰‘行金六百斤’,曰‘市门悬千金’,皆以商贾字样为行文点染。传末及赞附叙嫪毐事独详,见嫪毐亦不韦箧中奇货也。”[2]78这就把附传在结构上的作用讲得很清楚。反过来看,吕传后半以嫪毐附传结尾,一来显示事态发展的必然,二来波澜骤起,构成转折关键,三来二者事相类,吕之失势而亡,亦由嫪毐事引发,两人败亡作为终结,亦为顺理成章。商人总要算计别人,不料自己也堕入所算计之中。像吕不韦这般“钓奇”者,亦当在“贾祸”之中,只是权利富贵在握,像李斯那样“未知所税驾”罢了!
《黥布列传》以随何作为附传,同样也是随事带叙,但在传中的结构却绝然有别。英布本属楚将,在反秦中常以少胜多,立为九江王,项羽颇为依赖,坑秦二十万降兵,追杀义帝,皆使其人。项羽击齐,征兵九江,英布称病不往,由此与楚滋生嫌隙。刘邦得彭城复失,情势不利,正愁力不胜楚,希望有人策反英布,滞留项羽于齐,那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随何便毛遂自荐以游说英布。随何智士,知英布之处事皆为身谋,不会有更大的政治野心。他的说辞先从英布与项羽的矛盾晓以利害,说他不佐楚,“垂拱而观其孰胜”,“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托”,恐前景不妙;然后指出楚兵虽强,然背盟杀义帝,“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楚兵又深入敌国近千里,欲战不得,攻城力不能;楚兵至荥阳、成皋,汉坚守不动,“进则不得攻,退则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胜汉,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于是英布叛楚归汉。
这段说辞占到此传的四分之一,置于传之中间,犹如一河两岸,英布前属楚而后归汉,勾画了了。如果仅此说辞还算不得附传,在英布归汉立为淮南王,为汉击楚灭项,立下大功,又带出随何:
项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随何之功,谓何为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随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齐也,陛下发步卒五万人,骑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随何曰:“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于步卒五万人骑五千也。然而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
把刘邦问得无言以对,只好出以无赖故伎说:“吾方图子之功。”随何就任了护军中尉,英布也沾了他的光,“遂剖符为淮南王”。击项羽前“立布为淮南王”,只不过一时许诺,尚属空头支票。这样随何事便有头有尾,面目精神皆具,而可称为附传,在结构上具有“楚河汉界”之大作用。传之后来,英布被逼而反,带出滕公门客薛公,分析英布战略必出下计,因“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后来英布所为果然如此。薛公这段话固然很高明,然只听到声音,不见面目,算不得附传,在传中不过是一节插曲罢了。
李景星说:“《黥布传》纯以旁写取胜。前路处处以项羽伴说,见布之勇不在项羽下,其人之归附与否,与汉极有关系。中间详叙随何说布,见布之所以归汉也。后幅详叙薛公策布,见汉之所以制布也。一个草泽英雄,自始至终不能出人范围,是可用之才,确非用人之才。”[2]83-84所谓“旁写取胜”,是就随何、薛公而言,亦可见出附传的陪衬作用。如果把随何与郦生、陆贾写成辩士之类传,此处略加点明,英布传就不会有现在的光彩。
有些附传不过随事插入,也能使全传波澜横生,姿态多致,既陪衬传主人格性格,又使结构具有多姿多态的动能。战国四大公子传,除了平原君与虞卿合传外,其余均为单传,而且都插叙附传。这些附传如果抽掉,这些传主就不会那么熠熠生辉。
《魏公子列传》对传主简叙后,就立即推出侯嬴,这回是从头写起,说他是魏国的隐士,“年十七,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然后浓墨重彩铺写魏公子迎请侯嬴一节,接叙窃符救赵,使侯生再放光彩,以至于为了守密自杀而死,使信陵君以“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闻名于世。如果把迎侯生的渲染变成简叙,不仅附传无色,以宾陪主的作用亦顿失。前人常言此传是太史公得意文字,说质实些,附传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上赞语:“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这样深情摇曳之笔,魏公子之礼贤敬士,侯嬴之多智大义,就更余响震人了。李景星说:“通篇以客起,以客结,最有照应。中间所叙之客,如侯生,如朱亥,如毛公、薛公,固卓卓可称;余如探赵阴事者,万端说魏王者,与百乘赴秦军者,……亦皆随事见奇,相映成姿。盖魏公子一生大节在救赵却秦,成就救赵却秦之功,全赖乎客。而所以得客之力,实本于公子之好客。故以好客为主,随路用客穿插,便成一篇绝佳文字。写侯生处,笔笔如绘,乃又为好客作颊上毫毛也。”[2]72
在《孟尝君列传》里,开头为孟尝君之父田婴先立一小传,这在《史记》里很少见。又有冯驩附传,用补叙置之传末,且叙写特详,这在结构上又有什么作用?此传开头田婴小传交代了传主的来历后,立即叙写如何倾心尽力招致宾客,点明对客“无所择,皆善遇之”。接叙门客苏代以木偶人与土偶人的对话劝阻入秦。接详叙门客中鸡鸣狗盗之徒又怎样解决了出狱、出关之危迫,化险为夷。又叙舍人魏子租粟与贤者,贤者上书言孟尝君不反,杀身为盟,缓和了孟尝君与齐王的矛盾。接叙苏代设计赶走了齐相之吕礼,一直到孟尝君死后,这才把《战国策》中冯谖的故事,安排于文末,而叙述描写最为详细,大致占全传将近一半。其中收债、游说秦,叙写周备详密。因此传同样以好客为主,前面一路皆写如何好客,且得客之力,层层铺垫,意在突出冯驩,也就是突出孟之好客。置之传末而特加详叙,则有回眸一笑百媚皆生的效果。吴见思说:“《孟尝君》于中间序,而田婴、冯驩两传则附在两头,环作章法。田婴传因在前,恐其累赘,故只用简法;而冯驩传因在后,欲其衬贴,故另出精神,淋漓尽致。”[1]5册68李景星亦言:“叙孟尝君事,而以田婴、冯驩附传分寄两头,章法最为匀适。合观通篇,又打成一片,如无缝天衣。盖前叙田婴,见孟尝君之来历若彼;后叙冯驩,见孟尝君之结果如此。养士三千,仅得一士之用,其余纷纷,并鸡鸣狗盗之不若也。太史公于此有微意哉!”[2]70此传没有写成父子合传,仅以小传叙父,“盖孟尝君席父业而兴者也”[9]187,犹如《项纪》为项梁立小传一样。然又以冯驩附传收结,中间层层略述如何好客,在父传后言“使主家待宾客,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则引出正文。而冯传殿后,匠心独运,位置极有斟酌,回光返照,一片皆活。至于平原君之门客毛遂精彩焕发,因属合传,当别论之。
《史记》之附传也有出人意料者,如《田单列传》在论赞后又复缀两小传:一是燕之乐毅伐齐,齐湣王出奔于莒,被淖齿所杀。“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为人灌园。嬓女怜而善遇之。后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与通。及莒人共立法章为齐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为后,所谓‘君王后’也。”这是为了回应传末田单收复失城,“乃迎襄王于莒,入临菑而听政。襄王封田单,号曰安平君”。这个襄王即湣王子法章,为田齐第六君。这是为了补充迎襄王,襄王封田单一事,若夹在传中,不免支离,故用补叙另立小传,可称为传后附传。另一附传为《王蠋小传》,燕之初入齐,因闻王蠋贤,欲请为将,王蠋义不北面事燕,遂自杀。齐逃亡大夫很受感动,“乃相聚如莒,求诸子,立为襄王”,这最后几句又把两附传连在一起。
吴见思说:“因迎襄王一句,故追叙襄王避难之事,则在太史嬓之家也。亦因迎襄王句,故追叙齐大夫迎立襄王之故,则感王蠋之义也。拈此三段,是迎襄王注脚。然入《田单传》不得,故附于此。”[1]5册8这是从本传与附传的关系上看。李景星则言:“《田单传》暗以‘奇’字作骨。……君王后,奇女;王蠋,奇士,不入传中,而附于赞后,若相应若不相应,细绎之,却有神无迹,是乃真奇格也。”[2]76总之,这种没有章法的处理,在结构上不整不齐的附传安排,亦见出“传外传”的灵活,而不拘一格。
再如《史记》未给赵高立传,而秦之亡与赵高关系至关要紧,而又与李斯之勾结亦为要紧。所以《李斯传》就好像二人合传,而其实是为了陪衬李斯,吴见思说:“《史记》附传,皆附首末于一篇之中,独赵高一传于此纪其终,而其出处反附于《蒙恬传》内,是创法。”[1]6册41李景星说:“至赵高为李斯、蒙恬之对头,故于《李斯传》内备记其终,于《蒙恬传》内又详叙其始;而李斯、蒙恬之受祸处,写得圆足,而赵高之出身本未亦写得圆足。以一人之事附记两传之中,斯又附传中之创格也。”[2]81而且《蒙恬传》与其弟蒙毅穿插叙写,看似合传,实为单传,以蒙恬为主,亦可见附传之灵活。另外,在《乐毅列传》中带出其子乐叔,《李将军列传》顺叙其子与孙李陵,都是顺理成章的。
总之,单传中添置附传,不仅可增记载人物,传之结构亦起变化。一般以附之传末为常,然在传首亦见,如项梁、田婴;或随事制宜置于传中,则成一河两岸之布局。置于传末而非子弟者,则有回光返照之作用。或者穿插于传主的行事中,以宾陪主。这只是就单传而论,至于合传、类传中的附传,就更加丰富多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