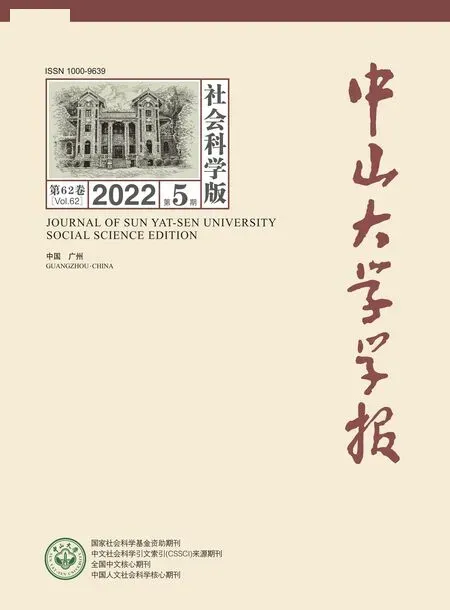接武旁流:阳湖派与桐城派关系新论*
唐 可
引 言
阳湖派与桐城派关系的定位,既关涉阳湖派自身主体性的确立,也涉及对清代中期散文史的整体性认识。乾嘉时期桐城派与阳湖派先后继起,两派成员之间多有往来,时空交织造成了二派微妙复杂的关系,究竟阳湖是桐城别派,受桐城笼罩;还是阳湖自成一格,与桐城相争胜,各家莫衷一是①曹虹:《阳湖派与桐城派关系辨析》,《江海学刊》1996 年第6 期。又收入氏著《阳湖文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30页。,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桐城派的强势姿态密不可分。研究者不论是关注时代背景、地域传统、学术师承等外部因素,还是流派风格等内部因素,最后都会不自觉地将视线聚焦于辨析两派之间的异同。
对两派关系的辨析,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主张阳湖派是桐城派支流。如郭绍虞认为:“阳湖为旧常州府治,邑人恽敬、张惠言均倡为古文,不免与桐城立异,世因称之为阳湖文派。然语其渊源所自,则亦出自桐城,只能称之为桐城派之旁支。”②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43页。二是认为阳湖派具有相对独立性。如《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说:“恽、张诸人既有接受桐城派深刻影响的一面,共同壮大了古文派的声势;又对桐城派进行了批评……与桐城派有明鲜不同。而正是主要由于后一方面的原因,阳湖派才得以脱颖而出,自成一队。”③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13页。三是指出阳湖派与桐城派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文学流派。任访秋认为:“阳湖与桐城,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尤其是恽敬,从学术思想体系,与桐城如燥湿之不相同……可知他在古文上思图别树一帜,而不屑以桐城枝派自居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后人另立所谓‘阳湖派’,以别于‘桐城派’,不是没有原因的。”①任访秋:《恽敬的古文文论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文学遗产》1984第3期。
不论是桐城派与阳湖派本是一脉,还是同中有异,或是各自独立,都是以现今的文学流派理论来考察两派之间的离合关系。在乾嘉时期,阳湖派不是以后世文学流派的面目出现,其古文理论也不是对桐城派的回应。换言之,用今天的流派眼光来看待阳湖派和桐城派的关系,事实上已经预设了两个流派之间的对话。桐城派在晚清的巨大影响力,给予其在与其他流派对话时较为强势的姿态,此种影响从道光年间既已形成②桐城派影响力与姚鼐弟子仕途发达、身居要职有关。参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家与桐城派关系考论》,《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在这样的姿态下对话,阳湖派与桐城派的地位事实上并不对等,况且桐城派的强势格局一旦形成,后世学者在论述过程中很难避免不受其影响。因此在评价阳湖派的特点和成就时,难免以桐城派作为参照系,得出的结论也就难称公允。本文试图回到历史现场,还原清人语境,重新考察处于事件中心的当事人叙述,或能为重新理解二派关系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张惠言、恽敬与桐城派的关系
作为阳湖派代表人物,张惠言、恽敬与桐城派的关系是疏离的。张惠言与桐城派的关系在于王灼引介其走上古文创作道路,而刘大櫆对张惠言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③曹虹:《阳湖文派研究》,第121页。。张惠言在《文稿自序》中论及他与王灼、刘大魁的古文渊源时说:
操其一以应于世而不穷,故其言必曰“道”。道成而所得之浅深醇杂见乎其文,无其道而有其文者,则未有也。故乃退而考之于经,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王礼乐制度于《礼》郑氏,庶窥微言奥义,以究本原……然余之知学于道,自为古文始。④张惠言:《文稿自序》,黄立新点校:《茗柯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1—122页。
张惠言在序中承认其学习古文是出于王灼的接引,但他直陈创作古文的目的是传达学术思想,并不强调古文的创作技法。张惠言的学术趣味与当时主流的汉学家更为接近,而与桐城派相去甚远。
相比张惠言来说,恽敬的学术与古文渊源,与桐城派关系更为疏远,除了毗陵恽氏家族的家学渊源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来自舅舅郑环的影响。郑环学术上的特点为调停汉宋、喜采异说,为经世之学⑤包世臣云:“先生(郑环)以经学名宇内,为宿儒。然人称先生为经师,则先生不乐,即世臣亦不以经学推先生也。先生之治经也,尚调停汉宋之间,又喜采异说……先生之志在经世,所学既成,而不得用,则常与当路讽诵民问所疾苦,于兵政、海防、屯田尤详切。然当路莫有能听之者。”包世臣:《甘泉训导郑先生碑阴述》,李星点校:《艺舟双楫》(与包世臣著,李星点校《中衢一勺》合刊),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479—480页。。恽敬说:
先生(郑环)少时喜兵家言,后出入于纵横家、法家,最喜道家“雄雌”、“黑白”之说,推阴阳进退,人事盈歉,其绪余为步引芝菌,神鬼诞欺,怪迂之术,皆好之。为文章峭简精强,必出己。读书条解支劈,凿虚蹑空,旁抉曲导,必窥意理之所至。四十后,为陆象山、王阳明二家之言,已又以为未尽,反之张子、邵子之说。⑥恽敬:《舅氏清如先生墓志铭》,万陆等标校,林振岳集评:《恽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2页。
恽敬评价郑环文章“峭简精强,必出己”,与包世臣对恽敬文章的评价“精察悍廉如其为人”⑦包世臣:《读大云山房文集》,李星点校:《艺舟双楫》,第315页。类似,可见恽敬与郑环文风有相似性。不仅如此,恽敬深受郑环“必窥意理之所至”的精神影响,他曾自述道:
测理之心可达千圣,习于文也。敬自能执笔之后,求之于马、郑而去其执,求之于程、朱而去其偏,求之于屈、宋而去其浮,求之于马、班而去其肆,求之于教乘而去其罔,求之于菌芝步引而去其诬,求之于大人先生而去其饰,求之于农圃市井而去其陋,求之于恢奇吊诡之技力而去其诈悍。①恽敬:《上举主陈笠帆先生书》(其一),万陆等标校,林振岳集评:《恽敬集》,第347页。
由上观之,恽敬与郑环所涉猎的学问范围几乎一致。恽敬自述的为学追求正是合乎万物人情的真理。
除此之外,在古文创作方面,恽敬早年对于《史记》的兴趣以及对司马迁史笔精妙的把握,也来自于郑环的点拨。恽敬说:“十五六时读《史记》,以孟子、荀卿与诸子同传不得其说,问之舅氏清如先生。”②恽敬:《孟子荀卿列传书后》,万陆等标校,林振岳集评:《恽敬集》,第114,114—115页。恽敬从郑环所教读《史记》的比较法领悟古文义法,他回忆道:
(舅氏清如先生)后见敬读《文选》,曰:“汝知从横之道乎?言相并,必有左右,意相附,必有阴阳,错综用之,即纵横也。”敬思之竟日,仍于先生之言《史记》得之。于是,读天下之书皆释然矣。③恽敬:《孟子荀卿列传书后》,万陆等标校,林振岳集评:《恽敬集》,第114,114—115页。
郑环教导恽敬作文之道必有主次、详略、高下之分:
此文(指《太子少师体仁阁大学士戴公神道碑铭》)实在前,虚在后,所以如此者,因通篇不书文端一事,故用排比法,叙次家世、科名、官位,然后提笔作数十百曲,皆盘空捣虚,左回右转,令其势稽天匝地,以极震荡之力焉。此法近日诸家无人敢为,亦无人能为也……敬才弱,不敢犯东坡,因颠倒其局用之。④恽敬:《上举主陈笠帆先生书》(其二),万陆等标校,林振岳集评:《恽敬集》,第350页。
恽敬所谓颠倒东坡之格局,乃先叙述戴衢亨之行实,“提笔作数十百曲”云云,是以对比手法突显本朝贤臣处有道之世,以此反观本朝对戴衢亨的褒扬,并与前朝不得其时之贤臣所得到的称赞做对比,显示戴衢亨实至名归,亦可知本朝君主圣明。恽敬对文章布局的处理,正是来源于对郑环所讲《史记》“纵横”笔法的琢磨。由此可知,恽敬论学论文实渊源有自,受桐城派影响不大,只是后人忽略了郑环与恽敬的这一层重要的学术背景。
从受桐城派的影响来看,张惠言与桐城派已在离合之间,恽敬学习古文也并不是从接触桐城派开始的,那么张惠言和恽敬有多少古文观念是从桐城派转手而来就值得推敲。进而言之,认为恽敬与张惠言的古文观念中与桐城派若合符节的部分来自桐城派,这一看法也值得反思。钱穆曾说:“然思想之事,固可以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相视于莫逆,相忘于无形者。”⑤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393页。其论述思想渊源的看法,对探讨二派的离合关系,很有启发。阳湖派与桐城派相合之部分,未必皆出于桐城,亦可能渊源有自,自然合辙。张惠言、恽敬对于宋儒的态度即为一例。秦瀛《拜经堂文集序》云:
在东之学,师余姚卢绍弓先生,因主张许叔重、郑康成诸儒。而其《与阮侍郎芸台书》云:“程朱与圣门躬行之学为近是”,其言于宋儒不为无见。余官京师,在东偕其乡人恽子居集余邸,其议论有合、有不合,而要以古人为归。盖子居为郑清如之甥,而在东尝学于清如,又皆与张皋文为友,殆其师友之授受、切劘,有相类者。⑥秦瀛:《拜经堂文集序》,丁喜霞:《臧庸及〈拜经堂文集〉整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9页。
在秦瀛看来,臧庸从事汉学却不废宋儒躬行之学,这与郑环、恽敬、张惠言等人的交往有关,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张惠言、恽敬论学与宋儒有相合之处。恽敬受郑环影响,对宋儒态度自不待言。漆永祥曾指出乾嘉考据学家并不否定宋儒立身致行之学⑦参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新论》,《北京大学学报》2013第3期。,张惠言虽然不采宋人《易》说,但立身行义方面则多从宋儒。
阳湖派不是一个符合当今一般文学理论定义的文学流派①严迪昌认为一个文学流派是否成立并为人们所认同,要具备四个因素:一、有号召力的领袖;二、活跃的作家群;三、共同追求的审美倾向或艺术风格;四、类似流派宣言的选本或作品集。参见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第4页。。作为阳湖派代表,恽敬与张惠言没有明确的宗派意识,也没有具体的师承关系和共同的理论主张②参见曹虹:《论阳湖派的组织形态》,《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甚至代表人物之间的古文旨趣都存在明显差异。张惠言学术上维护儒学的纯粹性,不喜释、墨;而恽敬则不拘于一家一派,追求学问的通达。虽然恽敬与张惠言有共同反对时弊的倾向,却对创作古文的最终目的和途径看法不同,很难说有一以贯之的核心观念。恽敬与张惠言的创作实绩和某些理论主张,与桐城派多相合,但阳湖派又确有特出之处,不能完全纳入桐城派麾下。这些问题,是从预设流派对话的视角很难彻底辨清的,也容易造成历史真实与后人认识的错位。如阳湖人陆继辂《七家古文钞序》认定恽敬与张惠言受法于钱伯垌,钱氏则受业于刘大櫆。任访秋已指出此说的错误,核对两人文集也可知恽敬与张惠言并非是通过钱伯垌受法于刘大櫆,而是王灼。试想陆继辂年辈稍晚于张惠言和恽敬,其所获已是不准确的信息,如再据此作出判断来分辨桐城派与阳湖派的关系,那就更加无法得知真实的状况③后来王先谦根据陆继辂的说法,判断张惠言、恽敬私淑刘大櫆。参见王先谦辑,王文濡评:《续古文辞类篡评注·原篡略例略》,台北:中华书局,1970年,第1页。。考察历史语境,会发现阳湖派一直是以颇为被动的姿态,卷入到姚鼐及其弟子对桐城派的结构中去的。从阳湖派的视角来看,对于桐城派的认识过程是伴随着姚鼐地位的逐渐稳固而发生改变的。
二、张惠言与恽敬对桐城文统的认知差异
姚鼐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为刘大櫆八十寿辰所作的《刘海峰八十寿序》中首次提出桐城文统。此时姚鼐构筑的桐城文统并不稳固,对于刘大櫆是否曾师奉方苞以及方、刘二人孰优孰劣,刘大櫆弟子吴定、王灼与姚鼐及其弟子之间并未形成共识。吴定、王灼认为刘大櫆的古文创作在认识方苞以前就已经趋于成熟。姚鼐弟子则对刘大櫆能进入桐城文统颇有不满④王达敏对方苞、刘大櫆与姚鼐之间的分歧问题,有详细的讨论。参见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当时张惠言、恽敬与桐城派弟子交游时,接触的是正在形成中的桐城文统,张惠言和恽敬对姚鼐是否能进入统序的认识存在明显差异。
乾隆五十年(1785)张惠言在歙县与刘大櫆弟子王灼相识,张氏称:“余友王悔生,见余《黄山赋》而善之,劝余为古文,语余以所受其师刘海峰者。”⑤张惠言:《文稿自序》,黄立新点校:《茗柯文编》,第121页。王灼引导张惠言学习古文,二人是同榜举人,后来又在京师、歙县多有往来,关系密切。张氏《书刘海峰文集后》云:
余学为古文,受法于执友王明甫;明甫古文受之其师刘海峰。本朝为古文者十数,然推方望溪、刘海峰。余求海峰文六年,然后得而读之……明甫之言曰:海峰治经功半于望溪,其文必胜于望溪;然则海峰为之而不至焉者,果系于世之远迩耶?明甫又言:海峰为古文既成,乃著籍为望溪弟子。呜呼!两人故相为先后哉?⑥张惠言:《书刘海峰文集后》,黄立新点校:《茗柯文编》,第183页。
此处传递出两个关键信息:其一,王灼并不同意刘大櫆与方苞的师承关系,“海峰为古文既成,乃著籍为望溪弟子”,并且认为治经不利于创作古文,言外之意仍是要强调刘大櫆古文优于方苞;其二,从张惠言的描述来看,本朝为古文者十数中没有提及姚鼐。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很可能王灼向张惠言传授师法的时候,并不接受姚鼐创建的桐城文统,只承认方苞到刘大櫆一系,故只传其师刘大櫆的古文,而无暇兼及姚鼐。
王灼并未直接表明过与姚鼐的关系,但可从姚氏弟子管同对王灼的态度略窥一二。管同在《题王悔生文集》中云:“古人著书必自称名……古人著书必无自标其字者也。顷见恽氏《大云山房文集》动于篇中署‘恽子居曰’四字,意甚以为不典。恽氏孤学无师,无足怪耳。桐城王悔生从海峰游,于此等宜素讲,今其集首《孟献子论》亦自署王悔生曰,是岂合古人之义法哉。悔生文专学海峰,其序事颇有佳者,此则不当律令,予是以辨而书之。”①管同:《题王悔生文集》,《因寄轩文二集》卷6,《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361页。管同站在桐城义法角度批评王灼和恽敬古文中自署其字不典②关于恽敬和王灼自署自字,方濬师《蕉轩随录》卷4“自署其字”条为之有辨:“不知张河间《骷髅赋》起首云‘张平子将目于九野,观化乎八方’,西汉文字已如此,不得谓之不典也。”参见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1《三代因革论二》文后案语,万陆等标校,林振岳集评:《恽敬集》第29页。。他认为恽敬孤学无师,可见其未必认同恽氏是桐城派一员。他又批评王灼不遵桐城义法,在他的认识中,王氏并不属于姚鼐一系。从桐城文统上来看,王、姚平辈,但这只能说明王、姚之间不存在师生关系,那么王灼是否只传刘大櫆之古文而不承认姚鼐呢?这还需要了解张惠言的态度。
张惠言其实很早就知道姚鼐,吴德旋自述在京时曾从张惠言学习古文,他说“予尝受古文法于执友张皋文”③吴德旋:《顾少卿文集序》,《初月楼文钞》卷4,《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6册,第40页。,此时的吴氏还未得姚鼐手教,但是已经充分表现出对姚氏的兴趣,他说:
余年二十余至京师,与武进张皋文同学为文,得桐城姚惜抱先生《古文词类纂》读之,而知为文之不可不讲于法也……尝持是说以语皋文而皋文不予非也。④吴德旋:《七家文钞后序》,《初月楼文钞》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6册,第50页。
虽然无法判断吴德旋是否是从张惠言处得见《古文辞类纂》,但是吴氏在京时已经看到以钞本形式流传的《古文辞类纂》。张惠言对于姚鼐的地位并不认可,从钱伯垌的例子可以清晰看出。钱伯垌曾师从刘大櫆,与姚鼐相识,姚鼐集中有《赠钱鲁斯》一诗。钱伯垌虽无暇亲授张惠言古文法,但在得知张氏正在学习古文之后,又专程赶到杭州勉励张氏,传授刘大櫆的古文文法,此时张氏亦未提及姚鼐。钱伯垌说:“吾见自古文,与刘先生言合。今天下为文,莫子若者。子方役役于世,未能远还乡里,吾幸多暇,念久不相见,故来与子论文。”钱伯垌专程而来令张惠言大为感动,他说:“其惓惓于余,不远千里而来,告之以道,若惟恐其终废焉者,呜呼,又可感也!”⑤张惠言:《送钱鲁斯序》,黄立新点校:《茗柯文编》,第72页。张惠言论学极看重家法与师法,他的古文创作未必与刘大櫆的古文若合符节,虽然他对刘氏是尊重的,但也清楚刘氏的古文得失。甚至在张惠言的弟子董士锡看来,张氏才是能够接续方苞、刘大櫆,得本朝文统之正的人选。董士锡在《同门祭张先生文》中说:“今之文章,孰主坛坫?方刘而降,允也可贬。先生特起,陈锋削肤;衮衮琅琅,大言以抒。”⑥董士锡:《同门祭张先生文》,《齐物论斋文集》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7册,第489页。虽然是推尊本师,但董氏的表述也从侧面证实张氏未尝以姚鼐与方苞、刘大櫆并举来教授自己的弟子。董士锡又说:“余为古文受法于舅氏张皋文先生,先生之言曰:‘本朝为古文者以十数,然推方望溪、刘海峰。’先生之文,学于海峰者也。先生之言曰:‘自宋曾子固、苏明允父子之亡,古文仅不继传,而明归熙甫继之,本朝方望溪、刘海峰又继之。’”⑦董士锡:《重赠吴山子叙》,《齐物论斋文集》卷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7册,第461页。这与张惠言的表述是一致的,对于本朝古文名家只到刘海峰为止,而不论姚鼐,可见并未接受有姚鼐的桐城文统。
与张惠言完全不同的是,恽敬接受的正是姚鼐构筑的桐城文统,这很可能跟他与吴德旋的交往有关。宜兴人吴德旋是关联桐城派与阳湖派的重要一环,吴氏最开始是通过恽敬结识阳湖派其他人的。吴氏自述早年与恽敬相识于家乡,他说:“余年十五六时识子居于家,及来都,与子居交益亲。子居之友张皋文,予师友也。予之学为古文,得子居、皋文两人为助。”乾隆五十八年(1793)吴氏26 岁,他从济南到京师,通过恽敬与张惠言、王灼等人结识①吴德旋:《送恽子居序》,《初月楼文钞》卷3,《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6册,第25页。。他曾说:“今使群天下之人知有德旋,而足下及皋文者乃反鄙夷而不屑道,则虽群天下之人知之,如未尝有知之者也。”②吴德旋:《与恽子居书》,《初月楼文钞》卷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6册,第14页。虽然吴氏对恽敬和张惠言很推重,但是在京师时其古文师法对象已转向了姚鼐,他后来回忆说:“德旋年二十余,慕古人为文而不知所以为之之法,侧闻今天下为古文者,惟桐城姚惜抱先生,学有原本而得其正。然无由一置身其侧,亲承指授以为恨。后得先生《古文辞类纂》读之,而憬然悟,谓今而后治古文者可以不迷于向往矣。阳湖恽子居好持高论,于辞赋古文必曰周秦两汉,至其论学未尝不推先生为海内一人也。”③吴德旋:《姚惜抱先生墓表》,《初月楼文续钞》卷8,《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6册,第170—171页。从这里看出吴氏曾向恽敬论及姚鼐,而且也曾将两人做过比较,可知吴氏对恽敬古文创作的熟悉。恽敬对姚鼐也并不陌生,他虽然并不完全服膺桐城派的文论,但是对桐城文统是很熟悉的,其文集中有三处论及这一文统:
与同州张皋文、吴仲伦,桐城王悔生游,始知姚姬传之学出于刘海峰,刘海峰之学出于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观之,又未足以餍其心所欲云者。④恽敬:《上曹俪笙侍郎书》,万陆等标校,林振岳集评:《恽敬集》,第134—135页。
本朝作者如林,其得正者,方灵皋为最,下笔疏朴,有力,惟叙事非所长;再传为刘海峰,变而为清宕,然识卑且边幅未化;三传而为姚姬传,变而为渊雅,其格在海峰之上焉,较之灵皋则逊矣。⑤恽敬:《上举主陈笠帆先生书》(其一),万陆等标校,林振岳集评:《恽敬集》,第348页。
承见示《海峰楼文集》(“楼”字疑衍文或“诗”字之误刻),二十余年前在京师一中舍处见之。今细检量,论事论人未得其平,论理未得其正,大抵笔锐于本师方望溪先生,而疏朴不及,才则有余于弟子姚姬传先生矣。⑥恽敬:《与章沣南》,万陆等标校,林振岳集评:《恽敬集》,第499页。
恽敬对桐城文统的认识,明显与王灼、张惠言不同。吴德旋对刘大櫆也多有批评,他曾说刘氏文章“非上乘”,并极为推崇姚鼐的古文,说:“姚惜抱享年之高,略如海峰,而好学不倦,远出海峰之上,故当代罕有伦比。拣择之功,虽上继望溪;而迂回荡漾,余味曲包,又望溪之所无也。叙事文,恽子居亦能简,然不如惜抱之韵矣。”⑦吴德旋著,范先渊校点:《初月楼古文绪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31页。吴德旋以姚鼐为古文第一,认为方、刘不如姚鼐。
王灼、张惠言一系与吴德旋、恽敬一系对桐城派文统认知的差异,究其原因,除了有师承的不同,还有桐城派在其早期的传播过程中一直存在的古文统序的认定问题,其本质是姚鼐与刘大櫆在桐城派的地位之争。刘大櫆虽然已经去世,但是他的弟子王灼还在努力发扬师说。而姚鼐的声音,则被吴德旋传播到了在京常州文人群体之中。他们的统序观分别被张惠言和恽敬所接收。王灼、吴定一系由于没有后续发展,张惠言也无心于此,以至于湮没无闻。姚鼐则成为桐城文统链条不可或缺的一环,而王灼和张惠言等关于桐城文统的另一取向被选择性的忽略了。
三、李兆洛、陆继辂对桐城派的回应
相对于阳湖派成员结构松散、开创者风格观念存在矛盾,姚鼐之后的桐城派有领袖,有师承,有明确的理论核心和作为载体的选本,具备现今文学理论对流派定义的基本要求。当再以倒放电影式的流派视角去观察历史上二派的关系,会因为桐城派的强势存在形成的“前理解”而遮蔽阳湖派的本相。
面对桐城派有意识的建构活动,阳湖派中张惠言因倾心经学,并未措意于此;恽敬虽然对桐城主要代表人物都有批评,但散点印象式的批评并未上升到具有体系的批判。阳湖派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李兆洛和陆继辂,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试图做出改变,前者着意于从文体源流角度重新定义古文概念,后者则力求重构古文文统。
李兆洛编选《骈体文钞》,认为古文与骈文源头相同,对于古文与骈文不应有所偏至,主张融合骈散,在理论上与姚鼐《古文辞类纂》摒弃六朝文不录形成鲜明对照。面对桐城派浩大的声势,李氏选择从常州的地域特色中寻找骈体文资源,这与常州一地骈俪之风有关。与恽敬和张惠言一样,李兆洛少时亦好六朝辞赋①参见曹虹:《在清代骈散并兴的接点上——再谈阳湖派的性质与风貌》,《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李氏试图从源头上破除桐城派建立的文统,力图廓清对骈文的成见。李兆洛选文只到隋朝而止,继承了张惠言的骈文观。张惠言曰:
骈偶之制,导源邹枚,东汉两晋其正声也。梁陈之流,四六始作,徐庾擅妙,古体遂衰。下至初唐,镂金刻木,虽绚藻满目,其神索然。燕许以高气振之,遂为绝特。太白之清逸,玉溪之绮丽,亦其次也。原其佳者,要须得西汉沉博绝丽之意。体格有变,精理不渝。宋以后轻率浮动,宗风坠矣。②张惠言:《题词》,陈寿祺:《左海文集》乙集骈体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49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 年,第425 页。此题词《茗柯文编》未收,参见陈开林《清代名家佚文辑考——以周亮工、陈维崧、戴名世、程廷祚、袁枚、赵翼、张惠言为中心》,《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张惠言认为东汉两晋为骈文典范,其古体变至六朝已尽,唐以后能得古意的,是“须得西汉沉博绝丽之意”的作品,至宋代则宗风堕矣。李兆洛之骈文观则与张惠言相似,他说:“文之体,至六代而其变尽矣。”③李兆洛:《骈体文钞序》,《骈体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610册,第354,348页。又在《骈体文钞》目录中说道:“至于诏令章奏,固亦无取俪词,而古人为之,未尝不沉详整静,茂美渊懿。训词深厚,实见于斯,岂得唐宋末流浇攰浮尪,兼病其本哉。”④李兆洛:《骈体文钞序》,《骈体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610册,第354,348页。李兆洛追求文质相称、骈散合一的汉晋文,茂美渊雅的骈文风格,与张惠言的主张基本一致,其理论虽然不乏呼应者,但影响仍有限。究其根源在于清代骈散之争背后是复杂的学术之争,李兆洛在文学上试图融合骈散的尝试并不能弥合背后学术论争的裂痕⑤相关讨论,可参於梅舫:《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第一章第一节《文笔考与桐城义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33—53 页;刘奕:《乾嘉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第二章第四节《文笔说的重提与发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3—162页。。
与李兆洛不同,陆继辂试图构建阳湖派自己的古文文统。陆氏本意是只选刘大櫆、姚鼐、张惠言、恽敬四家文,但由于吴德旋的建议而增为七家文。陆继辂于李兆洛刊刻《骈体文钞》的同一年编成《七家文钞》,其序云:
我朝自望溪方氏,别裁诸伪体,一传为刘海峰,再传为姚惜抱……乾隆间钱伯坰鲁思,亲受业于海峰之门,时时诵其师说于其友恽子居、张皋文。二子者始尽弃其考据骈俪之学,专志以治古文……画水因出其向所点定二子之文,又吴德旋仲伦所选梅崖、秋士文各十余篇,益以桐城三集,以命继辂,俾择其尤雅者,都为一编,目曰《七家文钞》,聊以便两家子弟诵习云尔,非谓文之止于七家,与七家之文之尽于是编也。①陆继辂:《七家文钞序》,《崇百药斋续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497册,第81—82页。
对于陆继辂编选《七家文钞》的意图,曹虹指出:“《七家文钞》的结集,主要是为了彰显张惠言、恽敬两家的古文成就……显然,恽、张两家较为晚出,当时还没有造成广泛的文学影响。扩大两家的文学影响,使世人能够‘倾心宗仰’,是陆继辂、薛玉堂的心愿。”②曹虹:《阳湖文派研究》,第128—129页。此是确评。陆继辂说“聊以便两家子弟诵习”,其实已经暗含区分桐城与阳湖的意思。然而陆继辂编选意图与选本样貌大相径庭,这与吴德旋在编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有关。
从编纂过程来看,对《七家文钞》影响最大的是吴德旋坚持不能删除方苞。当陆继辂提出要将古文选本“改为刘、姚、张、恽四家之说”,阳湖和桐城各选入两位代表人物而呈现势均力敌的态势时,吴德旋提出了明确的反对。他认为七家中彭绩、朱仕琇可删,但是方苞绝不能删。序文中提及朱、彭二人是吴德旋选入,但从现存吴氏给陆继辂的书信来看,选入彭绩不是吴氏的意思,而是陆继辂和薛玉堂的本意③吴德旋:《与陆祁孙书二》,《初月楼文钞》卷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6册,第23页。,选入朱仕琇才是吴德旋的建议。吴氏认为朱仕琇足称韩门高弟,这一看法也受到姚鼐认可④吴德旋:《与陆祁孙书三》,《初月楼文钞》卷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6册,第23,23,23—24页。。吴德旋说:“望溪必不可去,去望溪即不成书,且甚有似于续二十四家文钞后者,此尤必不可之故也。夫彼二十四家之文,主望溪为能得古人之正传。”⑤吴德旋:《与陆祁孙书三》,《初月楼文钞》卷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6册,第23,23,23—24页。“二十四家”即徐斐然选编《国朝二十四家文钞》,清朝古文大家多未入选,去取也不严谨,但选入了方苞,李慈铭曾讥讽其书编纂不精⑥李慈铭说:“本三家村学究,耳目陋狭,即予所约举之二十家,尚未能知。又专以时文挑拨之法妄论古文,务取其浅近滑易者,系以庸劣之批尾,乃井蛙自足,遽定为国朝二十四家,一何可笑耶!”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210页。。吴氏认为如果只选四家而不选方苞,就变成《国朝二十四家文钞》续作,“于刘、姚、张、恽诸君子非曰荣之,适以辱之耳。足下幸以此意达之画水先生,可不再计决也。”⑦吴德旋:《与陆祁孙书三》,《初月楼文钞》卷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6册,第23,23,23—24页。他认为唯有方苞能得国朝古文之正,以四家接续方苞,乃可得古文正传。如果方苞不入选,就无法体现出刘大櫆、姚鼐与方苞之间文统上的传承,而选入方苞,由于此时姚鼐构筑的文统早已确立,张惠言、恽敬也只能委身桐城门庭。最后《七家文钞》不但没有突出张惠言、恽敬二人古文成就,再加上彭绩、朱仕琇,反而扩大了桐城派的门庭,也完成了桐城对阳湖、闽中的嫁接。虽然吴德旋可能是出于对选本质量的考量,但是主观上却有维护桐城文统的意图,而事实上也造成了陆继辂和薛玉堂编选宗旨的模糊。
《七家文钞》编选不精也招致后人批评。方东树就曾批评编选者无识,他对方宗诚说:“往时宜兴储同人于茅选八家外,增李习之、孙可之,号为十家。可之去习之远甚,况可以侪八家之列邪?乃谓可之胜持正,尤妄说也。近时人有论次国朝文家者,以朱梅岩、彭秋士与其间,其识殆与同人无异。”⑧方宗诚:《记张皋文茗柯文后》,《柏堂集》前编卷3,《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2册,第77页。方东树认为不该选入朱仕琇和彭绩,然而彭、朱亦非桐城支流。长洲人彭绩一孤介布衣,与桐城派了无相干。对于朱仕琇,陈志扬指出:“朱梅崖年龄略小于刘大魁,略大于姚鼐,属于同一时代的人,但与刘、姚并无往来,他生前在福建从事、传授古文是独立展开的……梅崖死后,其弟子与再传弟子或转学姚鼐,或与姚鼐密切交往,这为闽派古文附属于桐城派提供了机缘。”⑨陈志扬:《朱仕琇人生价值定位与古文致思方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与阳湖派遭际类似,彭绩、朱世琇及其弟子后来也都被刘声木收入《桐城文学渊源考》里,成了桐城派。
桐城派与阳湖派后来微妙复杂、若即若离的关系,都可以从早期桐城派建构文统的过程找到原因。桐城派与阳湖派是来自于两个不同传统的地域流派。清代地域文化声气相通,并非闭塞,两派古文观总有相合之处,创作风格也有类似的地方,桐城派以程朱传人自居,阳湖派文论也无法避开儒家义理的探讨。造成后世难以辨清二派关系的根源,在于古人擅于以地域来划分流派。以现今流派的眼光看到的桐城派与阳湖派,已经是经过后来者层层叙述和桐城派“嫁接”的阳湖派了。主张同源异流,认为阳湖别枝的,看到的是根;主张阳湖与桐城派毫无关系的,看到的是果;主张异中求同,强调各自独立又有联系的,看到的就是“嫁接”的切口。指出桐城派在自我建构过程中对于阳湖派、闽中古文等“接武旁流”式的纳入,为桐城派与其他古文流派的纷争提供了一种解释,不失为观察清代中期散文发展过程的一个新视角。
余论:阳湖派的性质
张惠言与恽敬作为阳湖派的代表人物常常被相提并论。他们的古文观念有共同之处,但表象之下是深刻的差异。观念不同并不影响二人的深厚友谊,却为后世研究者造成了理论上的困扰:阳湖派何以成派?谁才是阳湖派真正的领袖?阳湖派的特点为何?研究者着眼于常州一地的文化特色,历史渊源、宗族文化,师友关系等,又或抽绎出作为阳湖文派不同于其他流派的特色或风格①如曹虹总结常州学风的特点:融通、致用、多思、文采。参曹虹:《论清代江南文化圈中的常州学风》,《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以此为基础分析他们的审美趋向及创作风格上的某些共性。从这些方面可以把握阳湖派的主要特征,但个人风格、学术趣味等却被弱化了。阳湖派成员各以性之所近,各擅胜场,共同的审美理想固然能够成为阳湖派的立派基础,但是也应注意成员之间观念上的细微差别,而成员之间的差异有时相比流派外部的差异更大。
杨万里认为理解江西诗派应该“以味不以形”,不必拘泥于籍贯地域和个体差异,“味”不是从各家特色抽象出来的某种共通的普遍性,而是龚自珍所谓“天下名士有部落”的“部落”,即家族相似性。如果以“部落”来看阳湖派的性质,能避免过于求流派之同带来的对个人之异的遮蔽,专注于分析比对阳湖派成员之间细微的差异和相似性。分析的对象越多,细节也越丰富,阳湖派的图像也就越清晰完整。“我们看到一张由相互重叠、彼此交叉的相似之处构成的复杂网络,有时是整体相似,有时细节上也相似。”②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Blackwell Publishers L,trans. by G. E. M. Anscombe,1969,p.32.不必去刻意划定阳湖派的范围以及与其他流派之间的界限,随着其自身图像的逐渐清晰,阳湖派自然能够呈现一番别样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