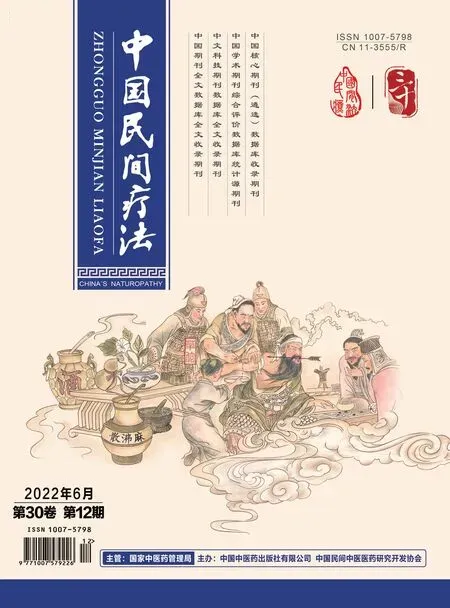《杂病源流犀烛》痹证学术思想探讨※
王胜茹,陈剑峰
(1.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9;2.南京中医药大学无锡附属医院,江苏 无锡 214000)
《杂病源流犀烛》为清·沈金鳌所作,全书重在溯本追源,汇百家之说,探究病证本质,并以证论治,务求其真,是中医史中不可多得的著作之一[1]。“杂病”一词首见于《伤寒杂病论》,其意本在概括除伤寒病以外的其他多种疾病,而本书所言杂病,涵盖脏腑、奇经八脉、六淫、内伤外感、面部、身形六大类共计92种疾病,内容丰富,涉及内、外、妇、儿等多种疾病。“犀烛”一词源于《萤窗异草》,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自序中称:“极天下能烛幽者,犀之角而已。”意指该书旨在察本源,明证治,求真知。
“痹”之病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至东汉时期又有新的发挥,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首创“湿痹”“历节”病名,为后世沿用。隋唐时期,又有医家据其病因分列“风痹候”“湿痹候”“风湿痹候”“历节痹候”“五体痹候”“白虎历节”之痹,极大地丰富了痹证的内容。金元时期,朱丹溪《格致余论》提出“痛风”病名,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从痹证的发展历史看,其称谓杂乱,缺乏梳理[2]。而在《杂病源流犀烛》中沈金鳌专列“诸痹源流”一节对痹证进行梳理,其中多有论述精妙之处,现概述如下。
1 首辨他病,次辨真假
1.1 首先辨是否为痹证 沈金鳌十分重视疾病鉴别,在《杂病源流犀烛》序中言:“知其由来,审其变迁,夫而后表里不相蒙,寒热不相混,虚实不相淆,阴阳不相蔽,皆通灵之为用也。”痹证致病因素繁杂,病程较长,临床表现多样,与多种疾病存在相似之处,临证时易于混淆,如麻木、痿证、风证之病,故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卷十三·诸痹源流》中作出鉴别。
痹证当与麻木作鉴别。《杂病源流犀烛》曰:“痹本气闭不通,或痛或痒,或顽麻。”痹证患者多兼见麻木症状,尤其属湿者,因湿者多黏腻、重着,病而不移,多表现为皮肤不仁、麻木,然两者实不相同,应注意区别。一方面,两者病因不同,痹证多为风、寒、湿等外邪入侵而发病,而麻木为风虚病兼寒湿痰血而发病,前者多为有形实邪侵袭,后者则是在风虚病的基础上复感外邪。另一方面,两者表现也不相同,痹证多表现为肢节疼痛、屈伸不利,麻木则非痒非痛,肌肉内如有万千小虫乱行,甚至掐之不觉,如木之状。
痹证易与痿证相混淆,当作鉴别。痿证与痹证是中医理论中较易混淆的两种疾病[3]。沈金鳌在书中指出痹证与痿证之间的区别:“但痿因血虚火盛,肺焦而成。痹因风、寒、湿气侵入而成也。”一方面指出两者的病因不同,痿证病因乃血虚火盛致肺叶焦燥,不能布精于五脏,失于濡养而发病;痹证则为风寒湿之邪内侵肢节、脏腑、经脉,发为“痹阻”而成;另一方面指出两者的症状表现也有不同之处,前者多表现为阳热之象,而后者则以阴寒为主。
痹证也应与风证相鉴别。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中指出:“风则阳受,痹则阴受,此二语实为风痹病之炯鉴,益可见治法不当混施。”一方面,痹证与风证虽皆为风寒湿三邪侵袭而发病,然其所犯有阴阳之别,前者犯经络之阴,后者犯经络之阳;前者多为里证,后者多为表证。另一方面,两者虽同为风寒湿三邪致病,然三邪之中又有偏重,痹证多因阴邪(寒湿),风证多因阳邪(风),前者多表现为痹阻,后者则多开泄;前者无形而痛,后者有形而不痛。现代也有研究通过结合气象学因素分析影响痹证高发的气象因子,结果表明气温、湿度对痹证影响较大,气温越低,湿度越大,则痹证发病率越高[4]。
1.2 其次辨痹之病位 沈金鳌认为临证时应当辨别痹之病位,虽同为“痹证”,确有病位之不同。如仲景所言胸痹之病,乃因上、中焦虚,阴寒之邪留于胸中,胸中气塞,幽闭不通,表现为胸闷如窒,甚则心痛彻背、背痛彻心,虽言“痹阻”,但属胸中之疾,本质为阳虚之疾,治疗时应以针引阳气。而风痹、寒痹、湿痹、热痹、痰痹、周痹之类,则多因外界有形实邪侵入四肢、关节、肌肉、经脉,表现为关节疼痛、酸楚重着、屈伸不利,治疗时当祛邪以除痹。胸痹与痹证虽然均有“痹阻”表现,但并不属于同种疾病,治疗也大相径庭,临证时不能混为一谈。现代医学书籍中也将胸痹与痹证作为两种疾病分而论之,前者属心系疾病,后者为经脉肢体疾病,亦表明两者之间确有不同之处[5]。
2 合内外因,重视传变
《素问·四时刺逆从论》云:“厥阴有余病阴痹,不足病生热痹,滑则病狐疝风,涩则病少腹积气……少阳有余病筋痹胁满,不足病肝痹,滑则病肝风疝,涩则病积时筋急目痛。”此为六气(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太阴湿土、阳明燥金、太阳寒水、少阳相火)内犯人体而发痹证。沈金鳌认为痹证不离外界六气,因人身与天地六气相应,故可有六气内淫致痹。除此之外,又因脏腑阴阳之有余、不足,有外邪入里而留存,此为气运之外又有所留,称为阴阳之痹,为痹之内因。沈金鳌强调痹证的发生不能忽略脏腑阴阳失衡在痹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机体脏腑有阴阳不足、有余之别,则外邪有内应而发为阴阳痹证。正如李梴《医学入门》所言:“痹属风寒湿三气侵入而成,然外邪非气血虚则不入。”严用和《济生方》云:“皆因体虚,腠理空疏,受风寒湿气而成痹也。”可见痹证的发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邱新萍[6]通过研究大鼠痹证模型,发现关节痹证与肺痹存在关联性,同时肾虚会导致大鼠关节痹证加重及肺损害的发生,证明五脏阴阳整体与痹证的发生发展存在相关性。
《素问·痹论》言:“诸痹不已,亦益内也。”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中对痹证发展的描述也呈现明显的传变思维,如“皆各以主时受之也,而筋骨皮肉脉又各有五脏之合,苟五者受而不去,则必内舍于合,而五脏之痹起”“由五脏而推六腑,亦以饮食居处为病本,而后邪中其腧而内应之,是以循其腧,各舍于其腑也”,基本表现为五体痹-五脏痹-六腑痹的传变过程,病情由表入里,由外向内,逐渐深重。首先,风寒湿三气入经络之阴而发为痹证,后遇五时杂合三气而为五体痹,又发病日久,复感三气内舍五脏,再合起居失常而邪中腧穴,内应成六腑痹。细细揣摩发现,“复感三气”在病情的发展演变中占据重要地位,病情绵延不止,复受外邪,终至不易治也。正如《玉机微义》所言:“三气袭入经络,久而不已,则入五脏,或入六腑。”提示注重痹证的预防调护,强调对痹证的治疗应当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在病情未发与已发两个阶段均应避免“三气”的侵袭,以防病情深重而难去。此外,沈金鳌指出经筋之痹,虽曰痹证,然不及经隧之荣气,故与脏腑无涉,乃因四季之时,防护不周,感三气而得之,指出经筋之痹的不同。苏鑫童等[7]也指出经筋痹有其独特之处,值得深入研究。
3 脉证合参,主次兼顾
脉象是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依据之一,对于痹证亦是如此。如《脉经》言“脉涩而紧为痹痛”。《玉机微义》载“脉大而涩为痹,脉来急亦为痹”。《脉诀》云:“风寒湿气合而为痹,浮涩而紧,三脉乃备。”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中首次提出:“大约风胜之脉必浮,寒胜之脉必涩,湿胜之脉必缓。”将行痹、痛痹、着痹与脉象一一对应,是其创新之处。同时,沈金鳌也指出痹证少有单一脉象,临证可见风寒、风湿、风寒湿等多种邪气杂糅致痹,脉象也较为杂乱,当仔细鉴别,不可举一废二,以致误判。
因痹证多为多种邪气杂糅而发,故沈金鳌在治痹时强调主次兼顾,首先依据主要证候选择合适的治疗大法,如兼具其他证候者,再合参以治之。如治疗着痹时,沈金鳌认为着痹为湿盛,当以除湿为大法,而其所兼之证总不离麻木,故当配合通经活络、补气养血之品,并创制了沈氏桑尖汤(嫩桑枝尖、汉防己、当归身、黄芪、茯苓、威灵仙、秦艽、川芎、升麻)治疗湿痹见指端麻木者。《类证治裁》谓“指尖麻,属经气虚,宜沈氏桑尖汤”,方中嫩桑枝尖功专祛湿除痹;茯苓健脾利水,合汉防己则利水之力愈强;黄芪益气,当归身补血,气血双补以充血脉;威灵仙、秦艽入经络,搜风祛湿;升麻升提阳气,伍黄芪升阳不伤正;川芎为血中气药,伍当归补血活血。全方合用,奏利水湿、通经络、补气血之功。痹证的治疗大法总不离祛邪与补虚,依据其证候的不同,临证时各有侧重[8]。
4 方药之外,调理饮食
痹证的治疗中饮食调理也是重要的一环[9]。《杂病源流犀烛》载:“凡味酸伤筋则缓,味咸伤骨则痿,令人发热,变为痛痹、麻木等证。慎疾者,须戒鱼腥面酱酒醋。肉属阳大能助火,亦宜量吃,痛风诸痹皆然。”可见,沈金鳌认为饮食在痹证发病中具有重要作用,调整饮食习惯是痹证治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沈金鳌强调饮食不可偏嗜,尤其是酸、咸之品,正如《金匮要略》所言,味酸筋缓发为泄,味咸骨痿发为枯,枯泄相搏,荣卫不行。历节病的发病与饮食厚味具有密切关系,因此,不过食酸咸之品可减少历节病的发生。同时应适食鱼、肉、酱、酒等肥甘厚腻之品,如过食则有碍脾之运化,水湿不行,久蕴则发热,湿热内生,蒸腾脏腑,流注于四肢关节,发为痛风。如《万病回春》所言:“一切痛风,肢节痛者,痛属火,肿属湿,不可食肉。”现代研究也表明,痛风与饮食习惯密切相关,长期高热量饮食、摄入酒精与痛风的发生存在正相关关系[10]。
5 小结
《杂病源流犀烛》作为一部医史巨著,内容十分庞大,对痹证的描述可谓是集前世大成者,虽广纳众家之说,却不流于泛泛之谈,其中多有真知灼见。沈金鳌强调治痹当首先辨痹证,既要与他证相鉴别,又要辨痹之病位;应知内外因,重视传变;须脉证合参,主次兼顾;方药之外,重视调理饮食。凡此种种,值得我们细细体会和揣摩。同时,沈金鳌严谨的治学态度、崇古而不泥古的学术思维、务真求实的治疗理念也值得我们学习。《杂病源流犀烛》作为一部“犀烛”之作,蕴藏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值得当代医家深入挖掘并运用,以助力科研与临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