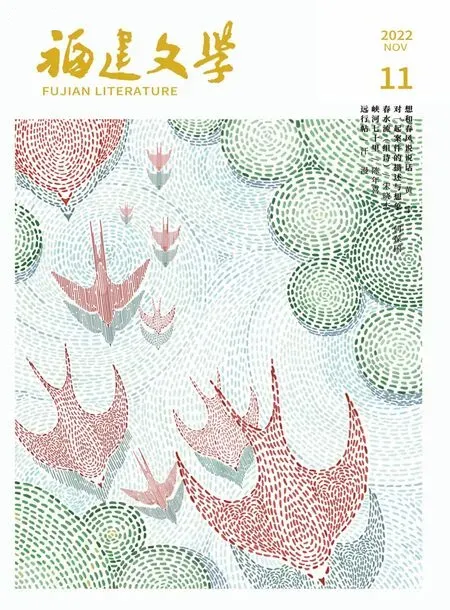福的地域色彩
朱忠甫
2002 年,我从江汉平原上的洪湖市乡村来到海滨城市厦门打工。
当时,我租住在海边的一个民房里。此地原是一个小渔村,昔日的海防前线,但厦门的高速发展,几年就将这个僻远苦寒之地变成旅游胜地。渔民们看到商机,纷纷洗脚上岸,比拼着盖房建楼出租,靠着丰厚的租金悠闲度日。
我的租处在房东家四楼,他们一家人住一楼。房东小孩有各自的工作,据说在外面都有自己的商品房,难得露面。平日里,我总见房东端坐在大厅油黑发光的茶几前,持一小巧乳白色茶杯品茶。见他面部泛光,眼里溢彩,眉头舒展,便知此时是他的幸福时光。有几次,我以为他在看我,便招手回礼,这时,房东老伴就会走出来,说有什么事可以找她。我很识趣,从此不再打扰老先生喝茶,但同时心里对喝茶更增不屑。
来厦门前,我从不认为喝茶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在我的家乡小村,只有闲极无聊时,才有人抓一把成年绿萝叶片大小的茶叶放进茶壶,但喝着那些如酱油色的茶水,也从没人表示沉醉。乡亲们认为喝茶就是解渴,和喝水一样,抓一把茶叶放进茶壶里纯属换换口味。有事没事捧个茶杯在手里,喝上了就难以放下,老先生真是在喝“工夫茶”呀!
当然,房东不会在乎我的感受。他每天照例喝茶享受慢时光,但如果家里来了客人,一堆人围坐在茶几四周品茶,他就会将心里的幸福通过笑声毫无顾忌地释放,感染得其他人也乐个不停。
在我的认知中,小口喝茶是有钱人的生活,但即便如此,我也很少听说生活在江汉平原上的有钱人,把喝茶当成吃饭,每天都不落下。可是,当我生活稳定,能静下心来打量这个村庄时,发现该村所有村民家里都摆着一张茶几,而茶几上的茶具总是闪烁着生活的光泽。
我最初以为这些村民嗜茶都是让钱给折腾的。因为这是一个富得冒油的村庄,每年的财政收入估计抵得上我家乡几个乡镇的总和。但房东老伴却告诉我,村里还有一些穷人,有的还一度为吃饭发愁。
她说,你只看我们在盖房子拿租金,有没有想到盖房子也需要钱,那些本来没钱的人拿什么去盖?也只能和你们一样去上班才能有饭吃。
我说,你们不是有土地吗?政府征用了,不就有钱了吗?
她说,你看看这个地方,前面是海,后面是山,有多少平地能用?真有多的农田,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到海里讨生活?
式(1)回归结果的残差e,即为企业的非预期投资,该值大于零表示投资过度,小于零表示投资不足。本文以正残差e衡量企业的过度投资,以负残差e的绝对值衡量投资不足,用IE表示投资效率。IE越小,表示投资效率越好;IE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差(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
如此,当地人嗜茶,只能说是一种福文化使然了。后来,我陆续去了厦门周边的一些地方,发现喝茶品茗不独属厦门人所爱,而是沿海一带居民的共同偏爱,他们完全是无茶不欢,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早晨起床后,如果不喝上两杯茶,完全不知道怎样开始一天的新生活。喝茶似乎能唤醒他们身体中的幸福基因,他们充分享受这样的时光,与贫富无关,实乃地域环境所致。
沿海居民以喝茶为赏心乐事,我想应该与当地气候有关,那里高温期长,而茶清热;应该与他们讨海的生活方式有关,大海变幻莫测,充满不确定因素,而茶降压强心;应该与那里缺乏淡水有关,泡茶是对淡水的一种珍视;应该与茶叶获取便利有关,以福建为例,茶山遍布,闽人取茶唾手可得,等等。沿海居民肯定经过了长时间探索和选择,才发现喝茶能带给他们心灵的安宁和满足,在取得广泛共识后,将它植入脚下的土地,任其野蛮生长,成为他们子孙寻找幸福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而平原四季分明,也许只有夏天才能激发人们对茶的些许渴望,要是在寒冷的冬天,喝上几口烈酒心情会更舒展,而文化往往具有连续性,一旦出现断层,就可能萎缩或消失;平原一般土地肥沃,人们生活相对安稳,无须长期喝茶压惊;平原通常淡水遍地,以至让人遗忘,当地人哪里还会去琢磨珍视它呢?至于买茶,我在家乡生活了三十年,至今也不知道在家乡哪里可以买到它。
但这并不表示生活在平原上的人们不懂喝茶的妙处,而是实在难以找到将喝茶纳入当地福文化的理由。“茶圣”陆羽的故乡天门市与我的家乡相邻,同属江汉平原,陆羽将茶文化推向全国,但我到现在也没见多少天门人像厦门本地人喝茶成瘾。让一个不喜欢喝茶的地方,诞生一个茶道大师指导全国人民喝茶,算是一种奇异。
沿海居民不仅自己偏爱喝茶,还爱以茶待客。有客上门了,一言不发,就拉他们围坐在茶几边,烧一壶开水,将一小包茶叶置于盖碗内,然后倒入开水,用盖罩住一会儿,再挪开盖将茶水经滤杯悉数倒入公道杯内,一泡茶就成了。不过,头泡茶常作洗茶叶水倒入茶桶。待第二泡茶好了,主人才将公道杯里的茶水一小杯一小杯分发至各人面前,一群人和着茶香,天南地北扯开去,待兴尽便起身离去,主人往往也不作挽留,送人至门外分别。
客人来了,几杯茶就把人给打发了,如果在我们平原上,那就由好客变成驱客了。平原人待客最真诚的方式是留人吃饭,不管你之前有没有吃过,一定要做上几个菜,让你上桌吃上几口才会开心,至今未变。
姑妈家离我家较近。小时候,我最爱去她家走亲戚,主要是因为她家孩子多,我去了有玩伴,但每次离开,她一定让我吃饱了饭再走。有时,我赌气离开,她定会叫着我的名字将我追回来,要我吃完饭再走。让我饿着肚子回家,是她无法接受的,这固然是她对我的疼爱,也是当地福文化的生动体现,仿佛我吃饱肚子,她比我更快乐。
我从家乡去厦门打工,途经武汉表哥家,正好姑妈给他带孩子。见我来了,丢下孩子,一个人在表哥家厨房给我弄了一桌饭菜,还拿出一瓶酒让我喝。我说自己没酒量,一般不喝酒,但姑妈却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男人不喝酒的,没事,喝点。看到我喝下几口酒,她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有一年,我们一帮兄弟姐妹去看她,那时她已八十高龄了。当时,她正在屋前菜园忙活,见我们过来,丢下手中菜,一路小跑过来相迎。恰逢春节,表哥表嫂们都从城里回家团聚。我们一行人很多,姑妈家也一堆儿女,我实在不想再给她添麻烦了,趁饭点还未到,就要带着大家离开。姑妈坚定地拦在前面,要我们一定吃完午饭再走,我找啥理由都给她挡回去了,她说吃饭大于天,再怎么忙,也要吃饱肚子呀!
我从小爱吃糍粑,这些年在外打工,也的确好久没有吃到了,着实想念,而姑妈家正好有。我深知她做的糍粑地道,是一般乡亲无法做到的,便说:要不给我们煎几块糍粑吧!糍粑做起来工序复杂,但做成了食用,是很简单的。只需将少许食油在铁锅里炒热,再把切成块状的糍粑放在热油上翻着煎,待糍粑软乎便可享用了。可表哥表嫂面面相觑,都说不会弄。姑妈听了,系了围裙,颤巍巍拿起锅铲给我们煎糍粑,谁也劝不住。
在厦门大街小巷穿行,和在其周边一些地方走动,发现这些地方民间庙宇盛行,可以说一个村庄就有一座庙宇。城中村的那些庙,或傍于海滩,或藏于深巷,或立于街道旁;乡村庙宇,则居于村落最集中之处,大都红砖红瓦燕尾脊,固执倔强,傲然而立,并且不时翻新。我不敢说沿海一带民间都重视庙宇建设,但这种现象肯定在沿海一带民间相当普遍。
儿子在厦门上小学时,因为住处离学校较远,我一直坚持接送。未买小车前,我主要坐公交车去接送儿子。通常,我从公交车下来,走过一段人行道,就可以到达儿子学校。虽然常走这段路,但我从未留意到它的任何不同。那天,牵一个盲人过马路,我忽然发现常走的一截人行道竟被一座庙宇的墙脚占去了四分之三。以前曾听早来厦门的朋友说,拆本地人房子给补偿可以,但如果拆他们的庙宇,那就有难度了,至此才信。
那些庙里供奉的神,据说是医神或者水神,主要为保生大帝、妈祖。但是庙宇间隔让人修葺一新,我还是看得分明的。翻新过的庙宇一般会在其一侧立上一个功德碑,告诉大家出资修庙的人有哪些。而这样的功德碑,在厦门或其周边,好像有庙宇就有它的存在。
在威力无比和深不可测的大自然面前,人类显得极端脆弱和无助,祈求神的庇护,以获得心灵的安宁和尘世的幸福,这是人类从古至今一直在做的事情,但是像沿海民间对庙宇如此热情和执着,还真的让我这个平原人感到无比惊讶。他们不仅大建庙宇,而且还大办庙会,各地具体时间虽有不同,但似乎都在上半年举行。届时,各村在外工作的游子,都会想办法回来参加,每家都在庙宇前摆上供品,道士执拂念经依次走过,继而鞭炮声齐鸣,通常逾半小时才止,比过年还热闹许多。
而在平原上找庙宇朝拜是很难的。我居住的那个镇叫峰口镇,是洪湖市第二大镇,近十万人口,据说只有一两座庙宇。每年去庙里祭拜祈福的,每个村估计就一两人。集体祭拜活动也有,峰口镇乡村历来有向土地神祈福的习俗,土地神分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均为木刻,各村根据村民意愿轮流供奉。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据说是土地公公生日),大家就敲锣打鼓把土地神送到下一家神龛上,但送来送去,我看到土地神木雕,只有在农历二月初二这一天才有人将其擦洗干净,其他时间一般是灰头土脸,没人理会。平原民间似乎更爱祭拜自家先祖,更愿向自家的“神”虔诚祈福。他们手里有了钱,只要有人挑头建本姓宗祠,拿出十万八万的毫不含糊,但修建庙宇的冲动似乎没有那么热烈。
修庙宇和建宗祠,都是民间获得心灵幸福的一种方式,两种文化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别,更不存在对错之分,它们都是盛开在艳阳下的美丽花朵,只是生长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想象,那个常年行走在惊涛骇浪上的渔人,是怎样强烈牵动着海边亲人的心!
福建的民间故事里,闽地乡亲信奉的神,大多是本地人广施大爱,或直接得道成仙,或死后让人们敬奉为神。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沿海子弟深受影响,追求的是大格局大幸福。在气节操守上,他们或许更具有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不顾生命安危将甘薯从越南和菲律宾引入我国的三位先贤都是沿海居民,林怀兰和陈益是广东湛江和东莞人,陈振龙是福建福州人。甘薯易种广收,洗净即可食用,帮助多少国人度过饥荒之年!我国也曾因种植甘薯人口大增,三位先贤实有大功!
福文化有其特定的地域色彩,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完善中形成,也必定会继续完善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