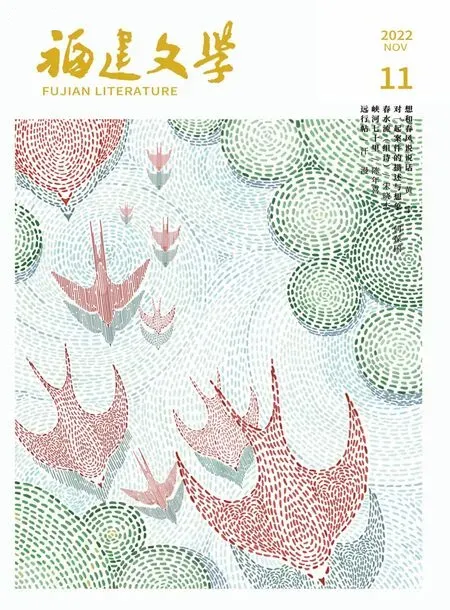公鸡的勇气
厂刀
就是那样,两只公鸡又打起来了,战况胶着。一只是红色鸡冠的白花鸡,尾部的羽毛点缀着黑色斑点。另外一只公鸡全身为暗红色,很是威武。它们打得难解难分,扑棱在一起,梗着脖子啄向对手,当它们发动攻击时,脖颈上的鸡毛都团在了一起。每一次发起冲锋,它们的翅膀张开,扑扇着,谁都不肯退让。
这是侯德柱见过最顽强的两只鸡,昨天他也在现场。红鸡经验老到,咬住对方,腿疯狂踢,又用翅膀拍对手。白花鸡输了阵,今天大有一副复仇的姿态。
侯德柱给自己点了一支烟,他看得饶有兴味,身边也来了几个人,充当临时的观众,欣赏这一场表演赛。大家都忍不住点评,好厉害的鸡。他们看了看侯德柱说,侯德柱,你又被送回来了。
侯德柱和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他把手往后伸了伸,摸到了放在口袋里的刀子,手又放回去了。过了一阵子,他从人群中退出来了,缓缓向桥上走去。太阳欲落将落,天空被映照成浅紫色。
现在,他的信心更足一点了,这次他必须去找马兵,有些问题就得解决,如果不去,那么问题就永远是问题。这两只公鸡,给了他行动力。他今天非得去找马兵报仇,不能再忍气吞声了。
侯德柱觉得自己这些年总低着头活着,在火车站要钱时是这样,抓到老婆和马兵在一起时也是这样。
在火车站,别人来赶侯德柱,侯德柱见对方气势汹汹,虽心有不快,也会默默地收拾自己的东西,然后重新换一个地方讨钱。但等他换了地方,他又会抱怨自己,为什么别人还没怎么着,自己就跑了?这样他又成了一个好欺负的人,要是跟人打一架就好了。他也在心里暗示自己,下次发生冲突,得狠狠揍对方一顿。
真的发生冲突时,侯德柱又不敢了,他和过去的自己一样,将为数不多的家当塞进麻袋,重新找一个地方。等他们不在的时候,又心中不忿,太欺负人了。
侯德柱来回换地方,很多人都认识了他。经常有人说侯德柱是骗子,跑来教育侯德柱。侯德柱说,我不是骗子,我就是没有回家的路费。
为了让周围的人走,侯德柱就端着自己的盒子,他说,我把头放在这里,要是钱够了,随便哪位把我的头拿走。
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侯德柱也端坐起来,他撸一把袖子,接着把手伸进盒子里,掏出钱,一张一张数,数了一遍,真有不少钱。
“够了。”他一把将钱塞进盒子里,然后抹了一把脸,把东西塞进麻袋,往火车站走。
几个不放心的人跟在侯德柱的身后,他们非得把侯德柱送走不可,直到侯德柱真买了票,他们才肯散去。但等他们一走,侯德柱就把票退了,又回到天桥。
侯德柱乞讨为生,他被送回去了好几回,政府送过,社会上的团体组织也送过。但送完后,侯德柱又会回来。他不想待在家里,只要他一回到家,当别人冲他打招呼,对他笑,他就觉得每一个表情的背后还掺杂着点别的意思。
老婆偷人的这件事,让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捉奸在床的时候,他还没做起现在的营生,而是在工地学木工。那一阵子下连雨,工地停工,侯德柱回到家,打算休息一阵。
他们在火笼里烤火,侯德柱用火钳戳燃烧的黑炭,火星如群星升起,又瞬息湮灭。他妈告诉他,你媳妇儿要管管了,再这样下去,不像话。也别让她老骑着摩托车到处跑,别人都说成什么样子了。
侯德柱拍了拍落在身上的灰,他说,我得锤死这娘们儿。
之前侯德柱就听到过风言风语,说他的老婆和村里的马兵有一腿。他问老婆有没有这回事,老婆说,别听人放屁,破坏夫妻感情,是不是你妈说的?如果是你妈说的,我撕烂她的嘴。
侯德柱说,我是听别人说的,你放心,我一个字都不会信。
侯德柱后来就没再过问。他在家里,老婆总催促他挣钱去。老婆对侯德柱说:“你回来干吗呢?哪个像你一样,总是往家里跑?这样的男人没出息。”
侯德柱说,再等一等吧,最近也没活儿干。
为什么别人有,就你没有?老婆问。
侯德柱不说话了,为了不被数落,他准备下午去打探一下消息。他有一个表兄也回来了。表兄在石家庄做活儿,做包工,一天五百块钱,他打算去表兄家问问,还差不差人。侯德柱出发的时候,他老婆说,赶紧去吧,晚上我骑摩托车来接你,别走路,太累人了。侯德柱心想,老婆还是心疼自己的。
以前侯德柱经常走路,后来在外面打工,全是坐车,他确实也不太喜欢走路,人一偷懒就容易变刁。
侯德柱去问了,表兄说,跟我一起去吧,虽然不怎么差人,但可以把你塞进去,但恐怕只能做小工,没有包工干。侯德柱说,没包工就算了,做小工也不错。
侯德柱没有等老婆来接他,他虽然不想走路,但也不想坐摩托车,在摩托车上,总感觉在悬崖边上,说不准就掉下去了。而且他等不及,他想立即把好消息告诉给自己老婆,知道他出去挣钱,能让老婆称心如意。
等回到家,他发现自己家的门从里面顶住了。侯德柱以为老婆不在家,但力帆摩托车还停在院子里。侯德柱听见有人说话,他好像明白了什么,用力撞门,嘴里叫骂:“赶紧给老子滚出来。”
“侯德柱?你怎么回来了?”老婆果然在里面,好像有人连续碰倒了什么东西,发出刺耳的声音。
侯德柱踹了一脚门,又在院子里团团转,找到了一把柴刀,他的力气和魄力都成倍增加。这时,门打开了。侯德柱老婆靠在门框上梳头发。侯德柱掀了他老婆一把,然后往里闯,原来刚才是烧水壶倒地的声音。侯德柱一瞥,看见了躺在床上的马兵,他正冲侯德柱乐。
侯德柱刚准备说话,但被马兵截住了:“侯德柱,你太不是兄弟了,你回来了,居然也不来找我,还等我来看你。”
“你怎么在我家里?”侯德柱问。
侯德柱老婆说:“你这说的什么话,你一走,什么都不管,家里遇到困难,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办?不都是马兵帮咱们。现在他来咱们家找你,困了来睡一觉,你急什么眼?”
“侯德柱,我们是兄弟,小时候一起长到大,读二年级的时候,你爸给你买的皮鞋大了一号,你走路老掉,去上厕所时掉进茅厕,还是我拿一根木棍,给你挑起来的。当然,我为你做的这些事都不值一提,但你回来,不来我家,这有点说不过去,是不拿我当兄弟了?”
马兵从床上起来,一把捏住了侯德柱的衣领。马兵比侯德柱高出两个头,侯德柱像放风筝一般仰着脖子,他看见马兵的眼睛都快飞溅出火星了。一瞬间,侯德柱想到了很多年前,他们还是小孩儿的时候,马兵就这样站在他的对面,掐他的脸,那时他什么都不敢说。
马兵的脸沉静如水,如刚上了云的天空。遽尔,天空又舒展开了,骤然放亮。马兵好心地用手帮侯德柱整理了衣领。
他说:“跟你开玩笑呢。”
但侯德柱老婆是真哭了,她扑过来捶侯德柱的胸。说:“你这没良心的东西,你是不是以为我偷人?”
“侯德柱,你真这么想?你要这么想,就是没把我当兄弟!我不允许有人这么侮辱我的人格。”马兵怒气冲冲的样子,感觉随时会冲上来打人。
“没有那回事,我们都是一起长到大的,怎么能不把你当兄弟?留下来吧,晚上一起喝点。”侯德柱说。
马兵没同意,他说,改天吧,我还得钓鱼去。昨天我钓了一条胖头鱼,有三十多斤,我来就是给你送鱼的。
马兵努了努下巴,侯德柱也看见了挂在墙上的鱼,看色泽是挺新鲜的。
等马兵走后,侯德柱老婆扯着侯德柱说,你以后不许说那种下流话了,败坏我的名声,也丢你的脸。
经此一事,马兵和侯德柱老婆走得越来越勤了,他约束不了老婆。他经常看见老婆骑着摩托车,身后载着马兵,他们一路嘻嘻哈哈,更像是两口子。人们都看着侯德柱笑,侯德柱觉得面上无光,他跟老婆说,以后你别跟马兵来往了。侯德柱老婆听见他的话,骂侯德柱,老娘的事你就别管了,他是我新认的干哥,他也是你的大舅子,是你的亲戚。
后来老婆跟侯德柱离婚,老婆埋怨侯德柱,别人在背后泼我脏水,你都不护着我,跟你这种男人就只会受欺负,没劲。
当侯德柱在火车站讨钱时,想到这些事,十分懊丧。怎么到最后好像错的是自己?当时该打他们一顿,出一口恶气。但侯德柱一看见马兵瞪他,他的心里就发慌。
他心想,自己要是曾祖该多好,如果这事发生在自己的曾祖身上,曾祖早就报仇了。
按照父亲的说法,曾祖真算是一个狠人,和他的弟弟比起来,简直天差地别。父亲老是把曾祖挂在嘴边,一讲起曾祖的故事,萎靡的父亲就变得生机勃勃,而曾祖的不幸也是传奇的一部分。
曾祖的弟弟为人软弱,别人牵走了他的牛,问他,这是我的牛吧?我新买的,鼻环都是新穿的。曾祖的弟弟看了一眼,然后说,对,就是你家的牛,我家的牛不这样。
曾祖则和弟弟不同,从不忍气吞声,所以打架是常事,其中有一次和人争土地的交界线,直接拿一把小铁锤砸坏了别人的腿骨。
总之,都知道曾祖不是一个好惹的人物,就是一头随时会疯狂的牛。而他偏执的性格和蛮横的作风,招致了不少仇家,积累了无数的怨气,这才有了下面的一幕。
那是盛夏的某一个晚上,有些炎热,到了后半夜才会凉爽起来。天上挂满了星辰,密密麻麻的,浩瀚之极,某一颗黯淡了下去,则有三颗会霎时亮起来。这样的好夜晚,在如今已经很难看见了。
入睡前,曾祖看着星空,便知道明日又是一个烈日,不会迎来雨天。他老早就盼着一个雨天,却不得实现。他关好了羊圈门,吐了一口唾沫,然后进屋睡觉。前半夜安安稳稳,到了后半夜,他被惊醒了。他的觉向来浅。
曾祖听到了院子里有脚步声,然后又听到了羊在咩咩叫,挂在羊身上的铜铃铛也响了起来。他暗道不好,肯定是有贼来偷羊,偷羊贼往往活跃在后半夜。他来不及细想,一手执灯,便往屋外冲。刚一脚踏出门槛,便被绊了一跤,摔得眼冒金星。
还来不及反应,就被人摁住了。这时,他才知道自己上了当,这些人是冲他来的。这一伙人假装偷羊,就是为了将他引诱出来。他一边怒吼,一边挣扎,但无济于事,恍惚间,他感到脖子很痛,然后心也一阵紧缩。
有人砍了他一刀,又将一把刀捅进了他的胸膛。他感觉血涌上了自己的头,充满了眼眶,在回光返照之际,充盈的力量灌满了四肢,踹飞了一个人。但这一脚出去过后,就变得无力了,整个人痉挛。
曾祖甚至还没有看清楚这些人,只是从一堆拥挤的声音中听出了一个熟悉的人,他还想起来当时敲碎那人的腿骨时,那人冷峻和怨恨的眼神无比深入人心,只是当时他沉浸在狂热和兴奋之中,无法预知到满心的仇恨和杀机。
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他感觉自己的眼神越来越迷茫,什么都看不清,他想微微欠身,记住这些人,可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在生命流逝的隘口,他看到一个白乎乎的影子,从他面前越过,脚步踏在了一摊积水上,溅到了他的脸上。他想骂人,怎么不看着点,但叫不出来了,力气早已衰竭。而后,他才意识到,不是积水,而是自己的血,他也就不再抱有希望了。
在这之前,曾祖从来没想过会死。他还这么年轻,总是为自己而骄傲,有用不完的力气。可如今,却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自己走向终点。
被踢飞的那个人,爬了起来,他又用力按了按曾祖身上的刀,以报被踢之仇。
这时候,他们也看到了一个光着身子的女人冲了出来。不能忽视一个人在惊吓状态下的能力,跑得太快,很难追上,他们也没有反应过来要追上去。
曾祖母跑到半路上,刚才发生的一幕让她失去了理智。她一直在床上,听见人摔倒,听见男人杂七杂八的喊叫,有人喊:“赶紧的,把刀子捅进去。”
她听见了被压抑住的怒吼,牲口快死的时候,也会这样,发出不愿意屈服的嗥叫,也有恐惧的因素,相比之下恐惧的部分更多一些。这时她惶恐到了极点,为了活命,不顾一切地跑了出去,甚至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她在小路上疾走,脚磨破了,小腿也被一些杂草划出了血痕,疼痛让她冷静下来。她突然想到了一点,年幼的孩子仍然在房间里。
她本想回去,但架不住害怕。她抱有自己的决心,到别人家去求援。她光着身子敲了别人的家门,连续敲了好几家。没有一家人有帮助她的意愿,一来邻里不和,二来他们都害怕惹上麻烦,置身事外明显是上策。
邻居们把她视为瘟神,拒绝了跟着她去家里看一看的请求,甚至怪她光着身子上门,非常不吉利。
无奈之下,她只得一个人回家。她以为,有人会拿着一把刀等着她或绑走她。她消磨了很长时间后才回去,预想到的事情没有发生,那些人全不见了。她的男人正躺在星光之下,惨白的光掩映着他惨白的脸和身躯,像一块发白的顽石。
她没有哭,进了屋,她害怕看见孩子也和他父亲一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还好,孩子瑟缩在角落,身上裹满了灰尘,但身躯完整,没有受到额外的伤害。
妈妈走后,他也醒了,又害怕得要命,一骨碌钻进了土灶。他以为那里是一个安全之所,不会发现他。但那些人来时就知道家里有一个孩子,而且是个男孩,得斩草除根。
那些人是在土灶里把孩子找出来的,其中一个人问他:“你认不认识我?”
孩子当然认得,他还知道自己的父亲和面前的男人有积怨,但他却回答这个男人:“不认识,没有见过你。”
这一拨人见孩子矢口否认,不知道因何发了慈悲心,既然不认得,就找不到他们,也不会被复仇,因此离开了,孩子也得以逃过一劫。
等天亮后,才陆陆续续有人上门,邻居们看看现场情况,的确惨不忍睹,曾祖的鲜血已凝固,和大地融为一体,他的身上还插着一把尖刀。他们什么也不说,一起动手帮忙搬运尸体。
曾祖的弟弟也远道而来,为自己的哥哥处置后事,他动手拔哥哥身上的刀,嵌得太紧,只好一只脚踩着哥哥的身体,双手用力,拔出来的一刻,身体后仰险些摔倒。他只埋葬哥哥的尸体,对于报仇只字不提。
弟弟变卖了哥哥的家产,又迎娶了孀居的嫂嫂,开始了新的生活。只有侄子对过往念念不忘,他悄悄告诉了自己的叔叔,父亲是被谁杀害的。但叔叔扇了他一巴掌,并且警告他,让他永远不要再说。后来这事儿也就不再被提及了,但这一故事却传承了下来。
侯德柱的爸爸经常把这故事挂在嘴边,家里来了客人,也经常对别人讲,有些人已经听过很多遍了。
当侯德柱听父亲讲述这一故事时,他总是为曾祖鸣不平,曾祖太不幸了,怎么有那么一个混蛋弟弟?
侯德柱问自己的父亲,后来爷爷有没有报仇?父亲往脚底板上磕烟灰,他说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时代也不一样了,没法追究。
听爸爸这么说,他只好失落地说,那好吧。
但侯德柱也不理解自己的父亲,上学的时候,侯德柱的爸爸总是告诉侯德柱,在学校,不要惹是生非,凡事都让别人一点。最初侯德柱也会和别人打架,老师让他们把大人喊来,爸爸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骂他,被老师喊来,耽误了他卖豆腐。侯德柱说,不是我先动的手。侯德柱的爸爸说,那他为什么不打别人,就打你?
侯德柱死命地瞅爸爸一眼,他深深地记住了父亲的话。别人欠了爸爸几年的账都不还,还准备赖掉。但爸爸还是坚持给人送菜,既然做赔本买卖,豆腐多卖几块少卖几块又有什么关系,怎么反而怪自己耽误了他卖菜?
侯德柱认识到,他的爸爸在自己的世界里出不来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但他有些时候,还是搞不懂,既然爸爸崇拜曾祖,为什么却总是让他学会忍着过日子,并且把这当作美德?
直到侯德柱爸爸去世的那一天,他亲手为他爸爸盖上白布,他才恍然惊觉,他上当了。他们可能并不是故事里“哥哥”的后代,而是懦弱的“弟弟”的一脉,身上有着懦弱的传统,所以才会将曾祖的哥哥树立为一座丰碑,为自己平凡的一生,增添几丝虚幻的光彩。
当侯德柱想明白了这一点,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处在深渊之中,一种沮丧无望的感受弥漫着自己的身体。他也感到恐惧,担心会一直这样下去,他成为家族精神的延续。他在火车站过着游牧式的生活,也只不过是漂泊的内心的真实写照,他找不到坐标。
这一次,那两只鸡给了他强有力的震撼,执着、凶蛮、无惧无畏,打完了第一架后,还能再打第二架,就算输了,也要一雪前耻。侯德柱的血性也被公鸡激发出来了,公鸡尚且如此,何况人乎?
他一路往前方而去。落日形如巨盾,发出刺目的光芒,看一会儿,眼睛就花了。侯德柱知道这当口马兵肯定在江边钓鱼,马兵很多时候都在江边钓鱼。侯德柱在情绪的驱使下,无比相信马兵就在那里,专心地等着自己。这股自信也让他对自己深信不疑,从此以后,他就昂首阔步地生活,让所有人重新认识他。
侯德柱走到桥上了,风呜咽,正为他擂鼓助威。侯德柱过完桥,又走了一段路,然后顺着小路到江边去。他在高处,果然看见了马兵,这次他不害怕了。在两只公鸡的启示下,他拥有了信仰。侯德柱要证明自己,他是不缺乏勇气的,他要把马兵打败,打败他的傲慢,把他的鼻子给打歪,把他打服,然后恶狠狠地告诉他:“你日了我老婆,看我弄不死你。”
锤了马兵,人们不会说他小肚鸡肠,而是说,这小子,以前真看错他了。
侯德柱打人后,可以潇洒地点一支烟,头也不回地走开。这时,马兵躺在地上,他什么都顾不上,只觉得鼻子痛,他摸着自己的鼻子,鼻涕和眼泪黏了一手,磕头如捣蒜,对自己说:“我的鼻子歪了,我的鼻子歪了,我的鼻子被他打歪了。”
“一定得狠狠揍他,不单是为自己。”侯德柱心想。这也是为了他的曾祖,此时此刻,他的身份变了,乃至于整个人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他,而成为自己的曾祖哥哥。马兵也变了,马兵变成了杀死曾祖哥哥的仇敌。
在那样一个星光月夜,哥哥倒在了血泊里,身上还插着一把弯刀。等他到来时,看着哥哥苍白的身体,忍不住大放悲声。
他一铲接着一铲地铲土,安葬完自己的哥哥后,从牲口棚里取出一口铡刀,将铡刀扛在肩上出了门。
在星光之下,他告诉自己的侄子:“叔走了,你要做个男人,什么都不要怕。”
他说完,从羊圈里的羊身上取下了一个铜铃铛,挂在裤腰带上。扛着铡刀,哼着不成曲的调子,沿着蜿蜒的小路大步流星而去,他要用铡刀手刃仇人。耳畔有虫鸣鸟叫,溪水潺潺,他背负一口铡刀,自信且慷慨激昂。遥远的山脚,偶尔还有铃铛作响,山林中狂风阵阵,正为他高奏凯歌。
没过几天,有人从外面回来,他们说,朱家坡出现了一个可怖的人,腰上挂着铃铛,背一口大铡刀,杀了人后,又从牲口棚里解下一匹马,骑上后,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
现在侯德柱感觉热血澎湃,仿佛幻想成了现实,他已经手刃了属于家族的仇敌,搬开了压在家族精神上的巨石。现在就只剩下马兵了,痼疾将被根治。
此刻,马兵在下面,他哪里都不会去。侯德柱要为曾祖正名,驱赶怯懦,成为一个浑身充盈着勇气的人。如此思虑,马兵的面容则更加可憎。他往下走,边走边注视着马兵,马兵拿着远投竿,正给鱼钩上饵,然后抛投出去,打了满竿,几个动作下去,等鱼收上来。
马兵沉浸在钓鱼的快乐之中,等侯德柱走近时,马兵才发现。马兵看见侯德柱,面露惊喜,他说:“侯德柱,你来了?也来钓鱼?你没有带渔具啊。我有多的,可以借给你使。”
“我不钓鱼。”侯德柱说。
马兵皱了皱眉:“那你来干吗?”
“我是来收拾你的,锤死你。”侯德柱想这么告诉他。但他没这么说,他什么也没有说。
“随便逛逛?”马兵没注意侯德柱,鱼竿抖了一下,刚刚有鱼上钩了,但浮漂还没有下沉,马兵的注意力集中在钓鱼上。
“好家伙,是条大鱼。”马兵兴奋地嚷嚷,他今天已经来了很久了,放了两包饵料打窝,但没怎么上鱼,鱼护里只有几条可怜的小鱼。
不过惊喜出现了,的确是条大鱼,突然浮漂直直往下坠,吃进去了大半个身子。那条鱼在拗着劲儿,鱼竿都被扯弯了。马兵把鱼竿卡在裆里,身子后仰,在岸边缓缓游走,与之对抗。水中有了很大的水花,马兵使的劲儿越来越大,脸都被憋红了。但是鱼太大了,还没有被降服。突然又有了一股大力,马兵忘了给线,一脚滑向了水里,慌忙中紧急后撤。
这时,他向侯德柱求援:“别傻站着,快来帮我啊。”
侯德柱还记得他是来干什么的,他背负着巨大的使命和责任感。他稍微愣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才上前去。他抓着鱼竿,鱼竿很滑,也许不滑,只是他的错觉,但他握得很紧,手指都泛白了,手上也起了汗。
现在他和马兵靠在一块儿,他又紧张起来,腿肚子就快要打哆嗦了,那是低血糖的前兆。现在侯德柱贴着马兵,他能感受到马兵身上的味道,还有他身上的温度,是一个活着的人,不是一个死物。
突然鱼竿上的劲儿又大了一点,侯德柱脚下差点滑倒,费了这么大的劲,他们还没有将鱼拉上来。他们还要继续僵持下去。侯德柱害怕被拖进水里。他突然摸出了别在腰上的刀,鱼线绷得紧紧的,一刀下去鱼线给割断了。那是恐慌之下做出的行为,他总觉得,再不紧急处置,他们两个人就会被拖进水里,他不会游泳,他记得马兵也不会。
水纹在他们眼前漾开,一定是条大鱼。现在他们退回来了,马兵握着空鱼竿,他有些生气,板着脸对侯德柱说:“侯德柱你干吗?你放走了我的鱼。”
侯德柱露出尴尬的笑,他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在马兵的目光下,他又没有了自信,变得唯唯诺诺。他嘴唇上下抖动,身上快瘫软下来。他又定定地朝马兵看了一眼,也不说话,扭头就往回跑。
这一番动作让马兵莫名其妙,他在后面问侯德柱:“喂,你怎么了?到哪里去?”
侯德柱脚步不停,险些摔倒,他觉得要回答马兵。有几句话不经思索,脱口而出,像早早准备好了似的。侯德柱告诉马兵:“来的时候,有两只公鸡在打架。你知道吗?它们昨天已经打过了,打得头破血流,今天它们又接着打,我要回去看看现在它们还在打没有,到底是谁打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