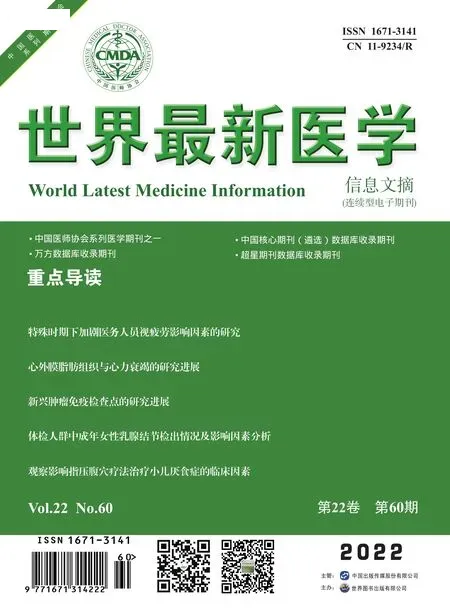叶海燕老师治疗痤疮的经验
唐瑶 ,叶海燕
(1.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 成都 610075;2.绵阳市中医医院,四川 绵阳 621000)
0 引言
痤疮又谓粉刺,是一种好发于青春期的毛囊皮脂腺部位的慢性炎症性疾病,临床表现可为粉刺、丘疹、脓疱、结节、瘢痕等多形性皮损,常有皮脂溢出,好发部位为面部及胸背部[1]。相关研究提示,痤疮发病率高达85%[2]。痤疮不仅是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而且影响容貌美观及身心健康,存在病程长、易反复、顽固难愈等难点。
叶海燕,女,成都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全国名中医李孔定主任医师学术经验继承人,四川省拔尖中医师,绵阳市名中医,绵阳市中西医结合内分泌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内分泌专委会肠胃病。叶海燕老师勤求古训,博采众长,临床经验丰富,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内分泌系统及代谢性疾病,对痤疮、黄褐斑、甲状腺结节、睡眠障碍、亚急性甲状腺炎的中医治疗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国家、省市级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获得科学技术进步奖、并开展名医工作室。
目前认为痤疮的发病与雄激素异常、痤疮丙酸杆菌过多、毛囊皮脂腺导管的角化异常、炎症、免疫失常、饮食及基因等密切相关,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中重度,目前治疗主要以药物疗法(方式为局部及口服给药)为主。药物类型主要包括维A酸类药物、抗菌药物及激素类药物[1],目前痤疮的西医治疗不仅存在容易耐药且不良反应多等问题,而且目前痤疮的治疗上面临很多难点。
痤疮在中医也被称为肺风粉刺、面疮。《圣济总录》指出皶即粉刺,其皮疹形如米粒,《外科正宗》认为其病因病机为风热外袭、感受湿热、血热郁滞、体虚感邪[3]。中医认为痤疮发病与体质导致血热壅盛,故血热外壅,气血阻滞,蕴阻肌肤;或肺胃热盛,血与热行,上蒸壅于胸面;青春期后痤疮还与肝肾密切相关[4]。根据对当代中医家治疗痤疮病案组方的相关研究,提示痤疮常与瘀、热为主[5]。据寻常痤疮的中医证候研究进展中关于近5 年的文献发现,寻常痤疮中医证型主要分为:肺经风热、肠胃湿热、痰瘀互结、冲任失调、肝肾阴虚等,病位主要涉及肺、脾、肝、肾、胃、大肠等脏腑[6]。但痤疮的病因病机仍较复杂,其临床证候分型仍缺乏一致标准。在痤疮的治疗上,中医具备很大的优势,中医不良反应少、有效性高、复发风险低且可调节免疫。叶老师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对本病进行了细致深刻的研究,且临床疗效明显,现将叶海燕老师关于痤疮诊疗经验总结如下。
1 病因病机
叶老师认为痤疮虽为皮肤类疾病,但多为内在疾病的外在表现,病性多为热、毒、湿。其因多为脾虚湿阻蕴而化热;亦可为食积蕴化为湿热;亦可为肝气郁结,气郁化火,或肝气郁结,横逆犯脾,脾失健运,水湿内停;亦可为脾肾两虚,水湿内停等。总之该病应四诊合参,从因而治。
常言“内伤法东垣”、“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痤疮病因病机可根据李东垣的《脾胃论》分析,“阴火论”即内伤杂病专家李东垣的核心学说,“阴火论”也汲取了中医经典理论著作内经中关于脏腑病特点,如脾胃的重要作用及气血生成、输布,四时升降浮沉的内容。《素间.调经论》言 “ 阴虚生内热,……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院不通,胃气热,热气薰胸中,故生内热”,指出了阴火的机理。李东垣将内伤脾胃之火统称为“阴火”,《脾胃论》云:“火与元气不两立”,“脾胃即虚,不能升浮”,即阴火病机为脾胃虚弱、清阳不升。“夫脾胃不足,皆为血病,……阴血受火邪则阴盛,阴盛则上阳分。”,即脾胃虚弱可导致阴火旺盛,而上乘头面而发病。脾胃论也指出,阴火的表现形式可为心火、肾火、气郁化火、伏留化火、凝滞生火、湿火相合、内燥化火。这与痤疮的发病是十分吻合的。痤疮可以大致分为血热壅盛,气血阻滞,血热可为素体热甚导致的热实证,或脾胃虚弱导致的阴火证。
2 治法方药
2.1 治法
痤疮多为内部调理失当引起内伤病而外现于皮肤,与外感病重视驱邪不同,内伤病重在调和阴阳,使气血通畅调和。叶老师指出在临床上使用时核心治法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健脾祛湿,且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健脾祛湿都属于中医较西医所独有的特色疗法。若为热实证,则先用清热解毒药配合活血化瘀药,以求急祛其邪,后再缓扶正祛邪,使气血调和而病愈;若为阴火偏盛,则在健脾祛湿药的基础上配合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药,以缓祛其邪扶其正,使气血调和。临床上根据其病情及兼证的情况加减化裁药物及剂量。
湿热辨证关系:叶老师指出,痤疮病人病性常为湿、热、瘀,且三者可错杂。湿热两邪治疗方法相背,《金匮要略》言“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即湿邪需用健脾、运脾类温药,然热邪需用伤脾类清热药,湿热胶着则病势缠绵难愈。湿热类若呈湿热,慎用苦寒药,尤其不可用大剂量苦寒药;可借鉴《湿热论》言“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其势必孤也”,先主祛湿热之邪的其中一邪,则能顺利祛除湿热之邪。
2.2 常用方剂
在治疗痤疮的热证上,老师主张使用五味消毒饮,而非黄连解毒汤;五味消毒饮的组成药物有金银花、野菊花、蒲公英、紫花地丁、紫背天葵子,黄连解毒汤的组成药物有黄连、黄芩、黄柏、栀子。从药物组成可以看出,黄连解毒汤四味药皆为大苦大寒之药,过于苦寒伤脾。五味消毒饮五种药物均质轻,《温病条辨》言“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该方蒲公英、紫花地丁为治疗痈疮疔毒之要药;金银花可解中上焦之热毒,野菊可清肝胆之火,紫背天葵善清三焦之火,蒲公英利水通淋擅除下焦之湿热;金银花、野菊花可清热解毒散结,擅清气分热结;蒲公英、紫花地丁清热解毒,擅清血分热结。该方治疗痤疮的热证疗效明显。
老师临床上据病人病情处方,常用处方包括五味消毒饮、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逍遥散、柴胡疏肝散、龙胆泻肝汤、当归四逆汤、温胆汤、桂枝汤、四君子汤、理中丸、六味地黄丸、越鞠丸等方的加减。
2.3 兼证用药
痤疮常可出现便秘、失眠、食积、瘢痕疙瘩、瘙痒等问题。若大便排出不畅,加入火麻仁润肠通便;大便燥结不通,采用中医所独有的急下之法,加入大黄后下通便;眠差,常配合实用茯神、首乌藤;食积常加入山楂、鸡内金、神曲、建曲等消食化积;若有面部瘢痕疙瘩,乳香、没药常配合使用活血化瘀生肌;瘙痒者,加入荆芥、炒蒺藜活血祛风止痒。
3 常用治法
3.1 清热解毒法
清热解毒法来自于《素问·至真要大论》之“热者寒之”“治热以寒”,清热解毒法即通过清热泻火、解其毒邪。本法适用于热毒之证,痤疮是一种具有热象且郁毒邪的疾病,所以也是是治疗痤疮之常用之法。根据现代研究,清热解毒法不仅能解除“外源性之毒”,如细菌、病毒和内毒素,而且能解“内源性之毒”,即氧自由基和炎性细胞因子[7],这与痤疮的现代病理学相关研究也是非常吻合的。
3.2 活血化瘀法
根据中医学理论,活血化瘀法即通过活血化瘀使血脉畅通来治疗血瘀证的治疗方法。血瘀证可为多种原因导致,如气虚、气滞、血虚、外伤、寒邪等。“瘀”最早见于《楚辞》,书中描述为“形销铄而瘀伤”。即瘀血可阻滞气血,气血阻滞,则营血不能营养周身,使机体消瘦。根据现代相关研究,血瘀证可能与能量状态、微循环障碍、血液流变学异常、炎症及免疫性炎症反应等有关。血瘀状态,可能进一步会导致各组织器官水肿、血栓形成及炎症渗出等情况[8]。久病从瘀,怪病多瘀,活血化瘀法也是治疗疑难杂症、慢性疾患的重要方法。活血化瘀法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广泛运用于临床各科,
本次研究共纳入161例2021年1月至12月至叶海燕老师门诊上就诊的痤疮病人进行总结。发现大多病人痤疮病程常较长且顽固难愈,且痤疮颜色多紫暗,肤色偏暗,舌苔偏紫暗,甚者有瘀点、瘀斑。现代人的主要死因如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呼吸疾病,均出现明显血液流变障碍,相关研究也指出现代人群普遍具有气虚血瘀倾向[9]。
痤疮慢性且顽固,为内在疾病的外在表现,且为皮肤病,也可根据久病入络的思想诊治,善用活血化瘀治疗该病;且痤疮病在《黄帝内经》提出:“劳汗当风,寒薄为皶,郁乃痤。”,也说明痤疮是气血的一种郁阻状态,在痤疮的诊疗上活血化瘀法极具价值。
3.3 健脾祛湿法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也是气机运化转输的关键,如果嗜肥甘厚味超出脾胃运化的能力,水谷精微不能转化为精血,反转化为痰湿浊邪。脾主肌肉,适当运动,可使阳气输布全身,气血通畅,脏腑功能强健[10]。激发脏腑功能平时懒怠少动,则脾之阳气不能舒展,脾运化失常,也会产生痰湿浊邪。痰湿浊邪郁久则化热。
健脾祛湿,重视脾气亏虚的体质,即通过健脾、运脾,使脾气得以发挥激发与推动作用,人体气机顺调,升降有序,脏腑功能正常;则痰湿浊邪得以消散。
叶老师认为痤疮虽为皮肤类疾病,但多为内在疾病的外在表现,其因多为脾虚湿阻蕴而化热;痤疮病人多为内伤疾病,内伤疾病易损脾胃,故其因多为脾虚湿阻蕴而化热;即痤疮病人常有脾气亏虚的体质。
4 注意事项
叶老师指出痤疮的治疗疗程约为1-2月,使用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适度运动,还要注意不用化妆品等刺激皮肤物品,饮食清淡,减少高糖、油腻及辛辣物质的摄取。
若患者痤疮红肿热痛明显,可同时配合百多邦消炎处理。
5 验案举隅
患者蒙某,女,汽车销售服务店库房工作人员,41岁,2021年07月25日初诊。主诉:面颈部红色结节囊肿2月余。现病史:患者述2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面颈部红色粉刺、丘疹,伴少许脓疱,无结节、无囊肿;患者未予重视,未行诊治,症状逐渐加重,面颈部多个暗红色结节、囊肿(较大位于颈部约3cm×3cm大小),且明显肿大,伴粉刺、丘疹、脓疱,无疼痛、发痒。至今未接受治疗。患者面部及头发油脂分泌较多,其余无特殊不适,纳眠可,大小便正常。
即往史:子宫全切术后7月。
辅助检查:免疫全套、血糖(空腹)、性激素未见异常。舌脉:舌暗红,苔薄白,脉弦细。
西医诊断:痤疮。中医诊断:痤疮。中医辨证:湿热毒证。
治则治法: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方用:五味消毒饮加减。方药如下:金银花30g 野菊花20g 蒲公英30g 紫花地丁30g 天葵子20g红花20g 淡豆豉20g 莪术10g 乳香20g 苍术15g黄精30g 芦根20g 3剂,两日1剂,水煎服,每次150mL。
二诊(2021年8月5日):患者面颈部结节、囊肿明显变小,自述无新发结节、囊肿,粉刺、丘疹、脓疱好转,舌暗红,苔薄白,脉弦细。大小便正常。予前方去金银花、淡豆豉、黄精加南沙参30g、火麻仁30g、陈皮12g、白术50g、枳实20g,服3剂。
三诊(2021年8月12日):患者面颈部结节、囊肿明显好转,自述无新发结节、囊肿,粉刺、丘疹、脓疱好转,舌暗红,苔薄白,脉弦细。大小便正常。去枳实,加大黄6g(后下)服3剂。
用药结束后患者病情基本缓解。
按:本案患者平素从事较多体力活动,属阳气素旺之体。且病人位于川渝之地,喜食辛辣刺激之物。发病之时正值立夏,就诊之时正值大暑,患者病情随气候逐渐炎热而加重。患者面部及头发油脂分泌较多,综上患者为湿热之体。患者舌暗红,痤疮呈暗红色结节囊肿,可见瘀热血停。治疗上,先急清其热,急予以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淤的五味消毒饮为基础方加减。方中蒲公英、紫花地丁为治疗痈疮疔毒之要药;金银花可解中上焦之热毒,野菊可清肝胆之火,紫背天葵善清三焦之火,蒲公英利水通淋擅除下焦之湿热;金银花、野菊花可清热解毒散结,擅清气分热结;蒲公英、紫花地丁清热解毒,擅清血分热结。红花、乳香为治疗痤疮瘀血内停的要药,红花活血散瘀,乳香活血生肌,再取莪术破血,淡豆豉解郁热,苍术燥湿健脾,黄精健脾补气益肾滋阴,芦根清热生津。此方急解其热毒,活破其瘀血,应用大量清热解毒药,故加用少许补气健脾祛湿生津等顾其正气药物;方证一致,故患者症状明显改善。治疗上紧抓清热解毒、活破其瘀血及顾其正气,随患者症状好转,根据病情逐渐减用清热解毒药物,重视使用活血化淤药物,顾其正气类药物加重;值得注意加入大黄、火麻仁通便,患者热毒症状明显,通便使其大便通畅,以使热毒从大便解。该病例是治疗痤疮值得参考得一个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