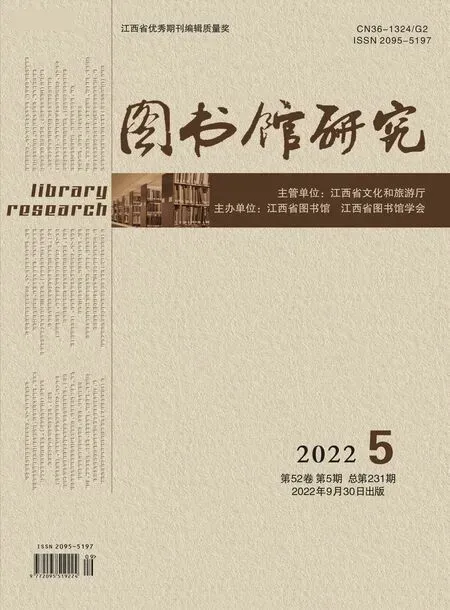《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的版本、瑕疵与价值*
王东峰
(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重庆 408100)
宋代是《杜集》整理的第一个高潮期。出于对杜甫的热爱,一大批学者和文人不遗余力地对《杜集》进行辑佚、编年、考订、校注,《杜集》由“十家注”“百家注”,再发展到后来的“千家注”。宋代雕版印刷事业的繁荣,为《杜集》整理成果的刊印和流传提供了极大便利,由此形成了宋代杜诗学的极度繁荣的局面。可惜的是,多数宋刻《杜集》早已亡佚失传,流传到今天的宋刻《杜集》仅有19 部(其中2 部尚存疑),而《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以下简称《分门集注》)则是其中唯一的宋刻《杜集》完本,其他宋刻均属残册或存在阙页补配的情况[1]。
1 编纂与刻印
杜甫的别集,《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为六十卷,但杜诗在其生前就大量散佚。杜甫去世后不久,时任润州刺史的樊晃,经多方搜集杜甫作品,仅编纂为《杜工部小集》六卷,其序文云:“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2]樊晃本在编纂时“各以事类”,显然是一个分类本《杜集》。
宋代《杜集》分类本应该是受到樊本《杜集》的影响,其始作俑者为北宋的陈浩然。陈浩然本《杜集》,宋宜写于元丰五年(1082)的序文云:“今兹退休田里,始得陈君浩然授予子美诗一编,乃取其古诗、近体,析而类之,使学者悦其易览,得以沿其波而讨其源也。”[3]所谓将杜诗“析而类之”,很显然也是一个分类本《杜集》。陈浩然本《杜集》至清代尚存世,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屡有征引,今已亡佚不传。之后,又有蜀人何南仲编纂的《分类杜诗》,同为蜀人的李石为此书所作的序文云:“吾友南仲取子美之诗句,分为十体,体以类聚,庶几得子美之变者也。南仲曷尝以是为子美诗之尽,然说诗者可以类起矣。仆不敢求其尽,试援此以从南仲。”[4]此书今亦亡佚不传。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著录:“《门类杜诗》二十五卷,称东莱徐宅居仁编次,未详何人。”[5]所谓“门类杜诗”,顾名思义,这也是一个杜诗分类本。徐居仁的生平不详,《门类杜诗》今亦亡佚不存,所以其具体编于何时难以确定。不过,《分门集注》卷首“集注杜工部姓氏”中有“东莱徐氏,字居仁,编次《门类诗》”,显然,徐氏的《门类杜诗》成书在《分门集注》之前。上述这3 种宋代分类本《杜集》,都是白文无注本。
现存的早于《分门集注》的宋代杜诗分类注释本有两部,惜皆为残卷:一为佚名编纂的《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以下简称《十家注》)二十五卷,存六卷;一为佚名编纂的《门类增广集注杜诗》(以下简称《增广集注》)二十五卷,仅存一卷。据书名推测,这两种宋本《杜集》,应与徐居仁编次的《门类杜诗》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在《分门集注》之前,现存还有一部署名王十朋集注的编年本宋刊《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三十二卷(以下简称《百家注》)。
通过比对上述几个现今存世的宋版《杜集》可以发现:《分门集注》的编次门类及每个门类下所收录的诗作,与《十家注》《增广集注》大同小异;其所选取的注家与《百家注》基本相同。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分门集注》应该是在参考《门类杜诗》《十家注》《增广集注》《百家注》等宋刻《杜集》的基础上汇编成书。
《分门集注》的编者不详。《雁影斋题跋》卷一《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集》云:“不著编辑人名字。考王琪序,称‘何君瑑、丁君修得原叔家藏及古今诸集,聚于郡斋,三日而后已’,殆即何、丁二人所编也。”[6]322“雁影斋”即指清末湖南湘乡文献学家李希圣,著有《雁影斋题跋》四卷,系据同乡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馆”藏书而撰,著录宋、元、明刻本及钞本80余种。李希圣认为此书的编者是宋代的何瑑和丁修,但学界普遍的观点是,此书是南宋书坊之人所编。潘宗周在其《宝礼堂宋本书录》首先断定此书是“坊肆无聊之作”。潘氏的观点得到后来学界的普遍认可,如《续修四库全书·分门集注》的提要也说,此书的编纂应该不是学者所为,而纯粹是坊间书贾所编。
此书没有刻印牌记,所以其刊印机构和具体时间均不可知,傅增湘在其《藏园群书经眼录》中根据此书所存的三卷残帙避宋讳的情况,断定其“当为光宗(1189)以前刊本”[7]853。但实际上,此书避宋讳玄、弦、朗、殷、匡、恒、贞、桓、构、敦、廓诸字,至宋理宗的“匀”字则全不避,据此可知,其刻印当在宋宁宗朝(1194-1224)。
2 版本与种类
《分门集注》现存宋刻三部,分别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潘宗周藏本、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翁同龢藏本、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只存三卷的傅增湘残宋本。
国图藏本为足本,潘宗周编纂的《宝礼堂宋本书录》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皆有著录,全书共二十五卷,版本为南宋建阳坊刻本,版式为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小注双行,行二十五字(个别地方二十六七字),双鱼尾,左右双栏。但此书的书口,潘氏的《宝礼堂宋本书录》著录为“白口”,国家图书馆网站的入藏题录却著录为“细黑口”。复检原书,国家图书馆的著录并无误,此书的书口位置确实有一道很细的黑线,如不细审,极易忽略,这可能就是《宝礼堂宋本书录》将其著录为“白口”的原因。
民国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初编》时,即借潘宗周藏本为底本影印。1974年台北大通书局据《四部丛刊初编》本再次影印,收入《杜诗丛刊》。197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次据潘氏藏本,改为十六开本影印,名曰《四部丛刊正编》。此后的《中华再造善本》《续修四库全书》本也皆以潘氏藏本为底本影印。
《雁影斋题跋》卷一也著录一部宋版《分门集注》,行款亦为“每版十一行,行二十字”,题名仅著录为“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集”,没有注明卷数。不过,据《雁影斋题跋》所述,“每卷前后有‘毛氏子晋’印、朱文。‘谦牧堂藏书记’,白文。又有‘孙佑宸印’白文。及‘孙佑宸生前经眼再来看’印,朱文。又有‘广圻审定’印,每卷前后皆有,朱文”[6]323,此本也是足本。通过对《雁影斋题跋》著录的该书的钤印情况,与潘宗周藏本及傅增湘藏本的钤印进行认真比对,另据《雁影斋题跋》著录的该书行款、杜诗门类名称、次序及门类总数,可知这部宋刻《分门集注》并非傅增湘收藏的残宋本,而与潘宗周藏本有前后递藏关系。也就是说,现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潘宗周藏本,是自方功惠的藏本辗转递藏而来。这就是丁延峰《存世<《杜集》〉宋刻本辑录》对海内外的公私藏书机构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后,得出现今仅有三部宋刻《杜集》存世的原因。
上海图书馆藏本亦为宋刻完帙,原为翁同龢旧藏,系翁氏后人捐藏。
近人傅增湘收藏有一部只存三卷的宋刻《分门集注》残帙,现流失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其行款为“半葉十行”[7]853,实乃笔误。今复核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实为十一行,其行款及版式与潘宗周藏本和翁同龢藏本相同。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分门集注》入藏跋语云:“是集购自江安傅氏,有其题记数则”,并转录傅增湘的手书跋语:“南宋建本,存卷十四、十五、十六凡三卷,……此本最为罕见。常熟瞿氏亦有分门杜诗,然与此本不同。”核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集部一》,仅著录有“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宋刊本)、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六卷(宋刊残本)、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二十五卷附《文集》二卷(元刊本)、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二十卷(元刊本)、杜工部草堂诗笺二十六卷(宋刊残本)、杜工部五言律诗二卷(明刊本)”总计六种《杜集》,未见著录《分门集注杜工部诗》[8]。再核《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唐五代别集》,著录的《分门集注》上一条是“《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集二十五卷》。宋刊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注双行三十字,白口,左右双阑”。藏书地点和收藏者注明“常熟瞿氏藏”[7]852-853。很显然,《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的宋刻《门类增广十注杜诗》,版式与《分门集注》明显不同,我们由此可以断定: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分门集注》入藏跋语中的“常熟瞿氏亦有分门杜诗,然与此本不同”,指的是瞿氏收藏的《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即所谓的《十家注》,而非是《分门集注》。
综上,《分门集注》现存三部,皆为宋刻。已知的几种《分门集注》的影印本,都是自潘宗周藏本而来。笔者曾用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翁同龢藏本、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残宋本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潘宗周藏本进行详细比对,发现它们不仅版式、行款完全相同,而且字体和内容也完全一样,这一结果表明,这三种本子属同一版本。
截至目前,自宋代以来,除了几种影印本外,《分门集注》尚未发现有重刻本和传抄本。究其原因,当是本书编者无名,而后世《杜集》注本新出较多,且愈加夸饰,乃至后来发展为“千家注”之故。特别是宋末元初刘辰翁的弟子高楚芳编纂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又名《集千家注杜诗》,或题《刘辰翁批杜诗》)刊印行世以后,因有“千家注”之称,再加上刘辰翁的名气,该书历元、明、清三代不断翻刻,流传较广,影响巨大,致使许多宋本《杜集》隐而不彰。周采泉就说:“高本自元迄今,嬗递至六百余年,翻刻不绝,远胜于黄鹤、徐宅、蔡梦弼各家注。”[9]101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的杜诗“千家注”就多达14种,版本有宋版、元版、明版及日本五山翻元刻本。
3 瑕疵与价值
《雁影斋题跋》称赞此书“纸墨既佳,堑印并妙,宋本中之上品也”[6]323。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称扬其版印精绝,是南宋建阳坊刻中的“佳刻”。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称赞此书写刻雅丽,是宋代建本中的精品。然此书虽然刊印精良,但讹误和瑕疵较多,因此遭到学界的普遍批评。如王国维《宋刊<分类集注杜工部诗〉跋》就批评说:“杜诗须读编年本,分类本最可恨。偶阅数篇注,支离可哂。少陵名重身后,乃造此酷,真不幸也。”[10]《续修四库全书》本提要也批评说,此书因是坊间书贾所编,粗制滥造,质量低下,而遭到许多学者的指责。这些观点实属中肯。通过细读文本,发现此书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所录诗歌有脱漏和重复。由于编者疏忽,导致有整首作品脱漏及部分作品脱句的现象。如卷四《秦州杂诗十七首》,实际只有十六首,脱漏此首:“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舡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卷九《送大理封主簿五郎亲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前阆州贤子余与主簿平章郑氏女子垂欲纳采郑氏伯父京书至女子已许他族亲事遂停》,末尾脱“珠明得闇藏。余寒折花卉,恨别满江乡”三句。卷十二《壮游》“国马竭粟豆”下,脱“官鸡输稻粱”句。卷二十《送高三十五书记》“又如参与商”下,脱“惨惨中肠悲”句。
个别诗歌前后重复录入。如卷九“外族门”的《奉送崔都水翁下峡》,复见卷二十一“送别门”;卷三“节俗门”的五言绝句《复愁十二首·其十一》,复见卷二十五“杂赋门”,题曰《绝句》。
第二,所集注释有重复。本书的编者在集注时,大都不是对原书的校注原文引用,而是有所删略和改动,但有时却又对某些注家的语意重复的注释没有甄别和筛选,全部原文录入。如卷八《幽人》:“洪涛隐语笑。”编者引王洙注:“曹植:泛舟越洪涛。晋王凝之《风赋》:驱东极之洪涛。郭璞《江赋》:鼓洪涛于赤岸。木玄虚《海赋》:洪涛澜汗。曹玭《江赋》:洪涛突兀而横持。蔡邕《(汉津)赋》:洪涛涌以沸腾。晋苏彦诗:洪涛奔逸劳。”为了注解“洪涛”一词,引用一连串诗赋作品,过于繁琐。赵次公因此批评说:“旧注(指王洙注)俱引为冗。”
又如,卷十四《兵车行》:“千村万落生荆杞。”编者首引王洙注:“《通典》:周文帝、西魏计州二百十有一。……《选》阮嗣宗诗:‘堂上生荆杞。’”后面又引王彦辅注:“阮籍诗:‘堂上生荆杞。’”按:王洙注已经引用阮籍诗句,后面就不应再引用王彦辅的相同注释。卷十五《诸将五首·其三》:“休道秦关百二重。”王洙注:“张孟阳《剑阁铭》:秦得百二,并吞山河。注言:百二,谓以二万之众,足以当百万,得形势也。”赵次公注:“祖出《前汉》:田肯贺高祖曰:陛下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山阻河,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注曰: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也。”按:所集二家注释大意相同,唯赵注所引《汉书》在前,且注解更加详细,因此,只取赵注一家即可。
第三,所集注释有错误。编者在集注时,对一些张冠李戴的错误注释没有指明或改正。如卷十五《扬旗》:“材归俯身尽。”王洙注:“鲍昭诗云:俯身散马蹄。”按:王洙注误。此非鲍照诗,乃出自曹植《白马篇》。卷十八《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临轩对玉绳。”王洙注:“星名。谢灵运诗:玉绳低建章。”按:王洙注误。此非谢灵运诗,乃出自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部分注释有脱文,编者未予补足。如卷十五《喜闻官军已临贼寇二十韵》:“谁云遗毒螫。”王洙注:“《说文》:螫,(虫)行毒也。”注释脱“虫”字。卷十六《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作》:“余亦师粲可,身犹縳禅寂。”杜修可注:“可传法偈:本来缘有地,(因地)种花生。本来无有种,花亦不能生。”注释脱“因地”二字。
此外,一些校注还存在衍文、倒误等现象。
第四,杜诗分类琐细且归属不当。此书以杜诗内容所表现的主题分类,共分“月门”“雨雪门”等七十二门。但由于编者所分的门类过于琐细,导致同一时间、同一地所作的诗歌被强行割裂,归属于不同的门类。如卷四《秦州杂诗十七首》,题解云:“同作二十首,二首见寺观门,一首见马门。”卷七《简吴郞司法》编入“居室门”,《又呈吴郎》却编入“邻里门”。再比如卷七《佐还山后寄》,题解云:“二首。同作三首,一首见宗族门。”编入卷二十四“花门”的《江头五咏》,仅录《丁香》《丽春》《栀子》三题,却将《花鸭》《鸂鶒》二题编入卷二十三的“鸟门”。王国维批评此书“支离可哂”,应该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第五,部分注释牵强附会。宋人注杜,从杜甫的心性入手,以散发着儒家人伦光辉的理想人格来诠释杜诗,过分夸大杜诗的“忠君爱民”思想和“比兴”手法的运用,认为凡杜诗皆有寄托,因此,对部分杜诗的注解纯属牵强附会之说。清代陶开虞《说杜》对此提出了批评:“尝见注杜诗者不下百余家,大约苦于牵合附会,反晦才士风流。少陵一饭不忘君,固也,然兴会所及,往往在有心无心之间,乃注者遂一切强符深揣,即梦中叹息,病里呻吟,必曰关系朝政,反觉少陵胸中多少凝滞,没却洒落襟怀矣。”[11]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凡例》中也说:“唐人中少陵固多忠爱之词,义山间作风刺之语。然必动辄牵入,即小小赋物,对镜咏怀,亦必云某诗指某事,某诗刺某人,水月镜花,多成粘皮带骨,亦何取耶?”[12]
如本书卷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题解引伪苏轼注:“古之封诸侯,分之以茅土。所谓茅屋者,制节之方州也。风,号令也,所以鼓舞万民,和四方之义也。天寳十四载,禄山起渔阳之师,诡言奉诏诛杨国忠,是谓义兵,号令天下,河北郡县。是谓茅屋破也。”卷七《江村》:“老妻画纸为碁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编者引“师曰:妻比臣,夫比君。棊局,直道也。针本全直而敲曲之,言老臣以直道成帝业、而幼君坏其法。稚子比幼君也。此天厨禁脔之说也。或说老妻以比杨妃、稚子以比禄山,盖禄山为妃养子。棊局,天下之喻也。妃欲以天下私禄山,故禄山得以邪曲包藏祸心,此说为得之。”诸如此类注释,实属穿凿附会之解。
第六,所集注家名氏有错误。本书由于是坊间书贾所编,为了显示本书所集注家众多、引用资料渊博,便于市场销售,故在书前所列诸家姓氏时,常常将一人割裂为多人。如薛梦符与薛苍舒,杜时可、杜田与杜修可,赵次公与赵彦材,李錞与李希声等等,后来的杜诗注本在征引本书的这些校注成果时,讹误相传,造成很坏的影响。另外,本书在集注时,对有的注家省称,造成校注成果指向不明,归属混乱。如所集注家有蜀人师古和师尹二人,但书中除了65 条标注为“师古曰”外,另有809条成果仅标为“师曰”①据笔者校注整理稿电子版统计。。
《分门集注》因出自坊刻,编纂质量不高,存在上述较多瑕疵,所以历来学界对其评价不高,如周采泉就认为此书,从学术价值方面来说,在宋代《集注》本中是最次的。万曼也批评此书“由于未经学者之手,讹误错乱,在所难免,……仅可供参考,不堪阅读”[13]215。不过,此本作为存世稀少的宋代《杜集》完整注本,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在杜诗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其一,是现今存世的唯一宋刻《杜集》完帙。早在清代,宋本《杜集》已不多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的提要就说:“宋以来注杜诸家,鲜有专本传世。”《分门集注》对杜诗分类过于琐细,且不科学,后来的“千家注”本问世后,此书遂隐而不彰,导致其传世数量极为稀少。所幸,在现存的十九部宋刻《杜集》中,其中仅有两部《分门集注》为完帙,而其余十七部皆系残卷或存在缺页补配的情况,而宋刻本作为最早的传世《杜集》纸质载体,在保存杜诗文献和版本校勘、旧注辑佚等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20 世纪80 年代,洪业有鉴于杜诗旧注讹误较多,《杜集》整理亟须深入,建议编纂新版《杜诗校注》一书,并建议选择以下几种《杜集》文献作为校注本:“曰校者,当以今尚孤存之王琪原刻、而裴煜补刻之《杜工部集》为底本,而以次校勘《九家注》本、伪王状元本、《分门集注本》、宋版黄鹤《补注》本、宋版及黎刻《草堂诗笺》本,……曰注者,当就宋人各注,及后来胡、钱、朱……各注,采其精当者。”[15]洪业将《分门集注》列为编纂新版《杜集》的校本之一,无疑是肯定了本书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其二,编纂体例较特殊。传世宋刻《杜集》,以编年本和分体本居多,分类本很少。其中的原因,是因为这种《杜集》编纂体例受到许多后世学者的批评,如万曼就说:“(《杜集》)注释本外,宋人还有一种分类本,……这种分类本,最为宋人陋习,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便于查考和就题摹拟”[13]213。不过,此书采用“分门”这一特别体例编纂,为研究者按照诗歌题材和诗歌内容研究杜诗提供了便利,对于考察宋代类分诗集的风气及今人以其分类为门径进行类分研究都有很大的意义。
其三,收录的伪注有一定资料价值。宋代出现的杜诗伪注(主要是托名王洙、苏轼),作伪者根据杜诗句意,从自己的主观理解出发,采取虚构史事、编造典故、虚构作品的手段随意注解杜诗,对杜诗注解危害巨大,受到杜诗学界的一致批评。此书就因大量吸收伪注而饱受学者诟病,但从文献参考的角度出发,这些伪注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如后人所驳斥之‘伪苏’注,在其他《集千家》本中,已删削殆尽,此集几乎所引独多。正可借此以分析批判‘苏注’之纰缪。为吾人提供不少反面材料”[9]654。
其四,在杜诗版本学史上有重要价值。此书上承《门类杜诗》《增广集注》《十家注》《百家注》,下启“分类千家注”,是《门类杜诗》与《集千家注分类杜诗》中间一个过渡的本子,具有重要的版本学价值。
——评王新芳、孙微《杜诗文献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