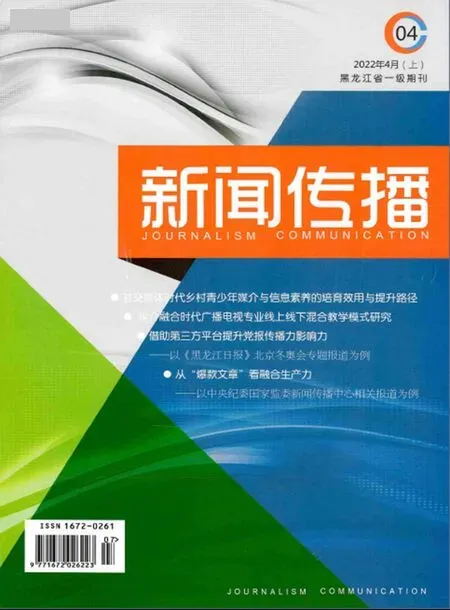如何评价传播技术决定论
张震
(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北京 100089)
自传播学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美国诞生以来,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一直被认为是传播学的两大传统学派。而20世纪四十年代兴起的媒介环境学则从技术自身的角度,探讨了媒介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以及带来的社会变迁。许多学者用传播技术决定论或媒介技术决定论来称呼他们的研究。
评价传播技术决定论,首先应当明确技术决定论的含义。《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这样定义,技术决定论通常强调技术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认为技术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能够直接主宰社会的命运,并且不会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单向地,唯一地决定了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活动的秩序以及人类生活的质量。[1]即技术决定论有两个原则:技术具有自主性;新技术导致社会变迁。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并不局限于传播学领域。马克思“手工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一著名论断体现着技术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影响。[2]
根据不同的角度,技术决定论可以被划分为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极端技术决定论与温和技术决定论。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社会危机不断加重,全球问题突出,不少学者对科技化的过程持悲观态度。技术悲观主义者对技术进行批判,认为新技术是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技术悲观论的萌芽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科技使人性堕落”的看法。[2]技术乐观主义者对技术持肯定态度,将技术看作社会发展、文化前进以及人类主体发展的促进力量。他们甚至认为科技进步能够挽救一切,技术进步一定能为人类带来美好生活。
极端技术决定论通常认为技术的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并使社会不可避免地趋向一个特定的结果,低估甚至否认其他方面的因素对于社会的制约和影响。[3]代表人物是埃吕尔。可以看出,前文所引用的技术决定论的定义属于极端技术决定论。温和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是技术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它不强调唯一性和独特性,但是认为技术是主导性的影响因素,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代表人物是温纳等。
极端的技术决定论太过狭隘,胡翼青等认为技术与人类的决定关系并非线性的因果决定关系,相反,技术与人类构成了一对互为存在的前提,但是技术总是先于社会的个人存在的,即使从表面上看人确实是技术的发明者和使用者,但人的行动却总是会受到已经存在了的技术的限制,并且其个人的时空观和社会的存在方式也由已经形成的技术定义了的社会环境决定。这种决定是一种“前提”而非是原因或者动机。[4]由此看来,在这些学者眼中,传播技术决定论是广义上的、温和的。笔者同样秉持温和传播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对媒介环境学派的技术决定论立场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般来说,技术决定论是对媒介环境学派相关理论的最直接的评价。媒介环境学派有时甚至被称为“媒介(技术)决定论”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历经三代,从第一代的英尼斯、麦克卢汉到第二代的尼尔·波兹曼,再到第三代的莱文森和梅罗维茨,每位学者对技术所持态度不同,并从极度强调技术本身慢慢发展到提出并肯定人的自主性上。
尽管哈罗德·英尼斯已经离开我们六十余年,但是其留下的《帝国与传播》《时间的偏向》两本经典至今仍被新闻传播界奉为圭臬。在20世纪40年代末,英尼斯开创了“媒介决定论”学派的先河。麦克卢汉与其同时代但稍晚,则将这个学派继承并发扬光大。
英尼斯“技术决定论”的态度,从其将媒介作为文明的分期中已经显露出来。英尼斯对于历史的分期十分细致,一共分成了9个时期。①以莎草纸和圣书文字为代表的埃及文明;②以拼音字母为代表的希腊——罗马文明;③以羊皮纸和抄本为代表的中世纪时期;④中国纸笔时期;⑤印刷术初期;⑥以报纸的诞生为标志的启蒙时期;⑦以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等为代表的机器印刷时期;⑧电影时期;⑨广播时期。[5]
英尼斯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媒介可以分为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两种。倚重时间的媒介,性质耐久且易磨损,如羊皮纸、石头以及黏土等。他们承载的文字具有永恒的性质,可以一直留存下去,但是生产、运输比较困难。相反,莎草纸和纸张质地十分轻巧、生产十分容易,能远距离传输信息,使用也比较方便。但是他们的耐久性不够,信息的传播时限比较短暂。因此属于偏向空间的媒介。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利于传承文字和文化,保证朝代的稳定延续,而偏向空间的文化则有利于帝国广泛扩张疆域。暂且不论是否符合中国历史事实,在书中英尼斯还从媒介角度,通过纸和文字的发展为研究中国的改朝换代提供了新的思路:“纸在中国的大量供应,使佛教徒能够大规模发展雕版印刷……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他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不足以满足时间的要求,因此中国总是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题。”[5]他在书中断言道:“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5]这种不折不扣的技术决定论,强调不同的媒介对于社会的不同影响,新媒介的产生,会改变社会的组织形态,带来社会的更替。
威尔伯·施拉姆对麦克卢汉这样评价:“麦克卢汉,正如他的老师哈罗德·英尼斯一样,是个技术决定论者。”[6]麦克卢汉引用凯里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媒介是巨大的社会比喻,它们不仅传递信息还告诉我们存在什么样的世界……而且通过改变我们所使用的传感设备的比例,确实在改变我们的性格。”[6]这句话透露了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真正传递的是媒介特性,不同的媒介带来的信息必然不同,即使内涵相一致的信息,在不同媒介的展现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是媒介本身而不是讯息本身定义了不同的世界。
麦克卢汉将媒介泛化,他认为人们发明技术来延伸部分肢体和感官的功能应付外界的刺激,一切延伸人体的东西都是媒介,如广播延伸人的听觉,报纸延伸人的视觉,甚至延伸人的皮肤功能抵御寒冷的衣服也可以被认为是媒介。麦克卢汉还曾经提出“媒介演变四定律”:提升、使过时、再现和逆转。电视能够放大强化和提升口语时代视听觉参与传播的感受;电视也使得印刷媒介单向的,纯视觉的传播方式过时;新的媒介可以“再现”旧媒介的内容,文字再现话语,报纸再现文字,电视再现电影;而随着电子时代技术的进步,技术可能会“逆转”,对意识进行模拟。[7]如今的AR技术“提升”感官感受,而VR技术模拟现实,似乎确实如麦克卢汉的“逆转”定律所说——又“逆转”回了口语时代的传播语境。
麦克卢汉预言的地球村也已经成为现实。从原始的部落化群体,到后来的使人们脱部落化的印刷媒介,再到使人们重新部落化的电子媒介,麦克卢汉从技术发展角度为社会予以划分。如果说广播和电视在使人们在全球范围内真正部落化上还欠了点火候,那么当今的互联网却实实在在将地球变成了地球村。这正是新的媒介技术带来的社会形态的发展。
麦克卢汉或许是一个彻底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他在书中“在电子时代我们身披人类、人类就是我们的肌肤”“计算机技术以技术给人展示了世界大识大同的圣灵降临的希望”的论断似乎都在欢呼着拥抱新的技术,拥抱新的媒介技术所带来的新的社会发展,拥抱一个似乎就快实现的电子乌托邦。[8]然而,尼尔·波兹曼却并不这么认为。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从娱乐、新闻、宗教、政治和教育五个方面论证电子媒介为美国社会带来的变化,他认为电视所带来的是简单的、非严肃性的,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一切都被变成娱乐的形式——“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还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9]在这种变化下,原本由学校出现后所形成的“童年”的概念消逝了,成人也退化为心理年龄上的儿童。他告诫美国应当警惕电子媒介。
由尼尔·波兹曼提出的“媒介即隐喻”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内涵大致相同。“如果传递的方式变了,传递的信息极有可能也不一样了”[9]信息传递的形式和语境发生变化,即使相同的信息,其内容含义可能也会发生变化,而其所包含的深层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也极有可能不一样。
“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那么你实在是太愚蠢了。”[9]尼尔·波兹曼如此看重媒介技术对社会变迁的决定性作用,单看这句论断,甚至有强技术决定论的风格。但从他的其他表述上,又能看出他认为人类可以做出一些努力来挽救这种局面。
第三代学者保罗·莱文森将自己的媒介观称为软媒介决定论。他强调在媒介演化过程中人具有自主性。媒介不断演化,但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的选择,使得技术的发展愈发人性化。也正因如此,新媒介对旧媒介正是一种补救:广播补救报纸,电视补救广播,互联网则补救了先前的一切媒介。乔舒亚·梅罗维茨则将“媒介环境”的观点和欧文·戈夫曼的“情景论”结合了起来。媒介带来社会情境的变化,媒介环境对人的行为方式和身份角色都能产生影响。他也提出受众会选择自己的媒介使用方式,肯定了受众的重要性。
可以看出随着时间发展,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所持的技术决定论立场越来越“软”,越来越“温和”,也越来越重视人类本身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这或许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传播学学科“受众中心论”的影响。当人们着眼于受众的能动性的时候,技术决定论者也无法否认人确实有进行自主选择的余地。
谈起技术决定论,许多实证主义传播学者和批判主义传播学者常常指责其过于强调技术而不是技术承载的信息内容。可是即使是实证主义者所理解的媒介也是以因果关系的方式产生社会影响,只不过所谓“因”更偏向的是媒介所携带的内容,其结论是经过数据性内容证明的,结果其实没有什么不用。更广泛来讲,这也是理解理论生成的重要的认识论视角。媒介环境的不同,使得社会学者和传播学者们观察到完全不同的社会行为,因而才产生了不同侧重点的传播学理论。[8]
人类的传播历史常常被划分为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和电子传播时代,以媒介(口耳、文字、印刷机、电子媒介)来划分的时代是否也正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视角?
因此,倘若不那么过分强调技术的绝对性、唯一性的影响,倘若抛弃极端的技术决定论调,技术决定论更像是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经验主义和批判主义的新的视角来供大家观察人类传播的发展历史。
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带来社会变革是不争的事实,在时代的分水岭上,技术往往确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印刷术破除了教会对学术的垄断和圣经的唯一解释权;传教士的报纸总是会对当地的知识分子阶层产生冲击,带来社会观念与文化的变革;自电视被发明出来之后,我们便一直生活在这种彩色生动的媒介构建的世界中——直到2012年,第三季度美国人每周看电视仍超过34小时,也就是每天接近5小时[10]。到如今,我们亦未能摆脱新媒介技术形成的社会环境——没有人能够躲避社交媒体的媒介化生存方式。
结语
极端的技术决定论必然不可取。严格来讲,也并没有哪一个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通篇展现极端技术决定论。然而“软”的、温和的技术决定论却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观察整个传播学历史和传播学理论的形成。尽管有麦克卢汉过分强调媒介技术本身或是波兹曼对电子媒介对人的控制持强烈的悲观色彩,但历代学者们都并不否定其他因素同样扮演角色,他们只是将技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已。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明示或暗示着社会的变化及变化的结果并不完全掌握在技术的手中。毕竟,技术并不是凭空产生,也是由人类发明的。因此,笔者更愿意抛弃极端技术决定论,将传播技术决定论看作是一种视角,我们不必对这种视角过分苛责,甚至应多利用这种视角理解传播以获得更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