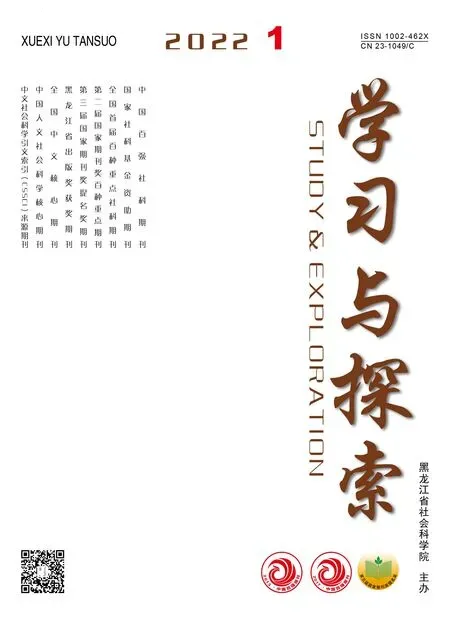关于勿吉考古文化的推定①
郭 孟 秀
(黑龙江大学 满学研究院,哈尔滨 150080)
勿吉为东北世居之肃慎族系继肃慎、挹娄之后出现的第三个族称,存史时间大致在北魏至北朝时期。由于史料的阙如与简略,虽有众多学者进行探讨,但学术界对勿吉历史源流、活动范围、文化特征等仍存在不同观点,难达一致。以考古发现为基础特别是对其考古文化的界定无疑将有助于对上述问题的深化讨论,因此也成为近年来对勿吉研究的一种新的趋势。目前对勿吉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虽然所持论据各不相同,主要观点可分为两类:其一认为凤林文化为勿吉的考古学文化,但具体解释不尽相同,张伟先生认定分布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南部的奥利加文化与凤林文化为勿吉的考古学文化,奥利加文化即为勿吉遗存,此时应是勿吉的发端时期,凤林文化的构成以奥利加文化为主体,也应为勿吉文化,代表的是勿吉繁荣、强大的时期[1]。王乐文先生认为勿吉在早期是凤林文化先民,晚期是河口四期类型、同仁一期先民[2]。魏存成先生在梳理汉魏晋及南北朝时期挹娄、勿吉的遗存时,认为分布于三江平原的以滚兔岭文化和凤林文化为代表的聚落遗址和山城的特点,与《魏书·勿吉传》所记勿吉“筑城穴居”的习俗相符合。“如果说这些都属于挹娄、勿吉遗存范畴的话,那么又说明勿吉在南迁之前就已存在不同的部落或群体。”此观点可以引申为凤林文化代表的是勿吉其中一部而非整个部族之文化[3]。第二类观点以乔梁先生为代表。乔梁先生在研究靺鞨族源的文章中否定了凤林文化与靺鞨文化的渊源关系,认为“凤林文化同靺鞨文化之间也没有更多的共同因素或反映渊源关系的内容,至少就目前的发现而言,无法推论已知的靺鞨文化是由凤林文化的发展而形成的”,提出波尔采文化或蜿蜒河类型有可能是靺鞨文化最主要来源的观点。同时,他也认识到,“波尔采文化或蜿蜒河类型就目前的认识来看,年代下限可能还到不了北朝,因此究竟是否能够被视作勿吉的遗存尚难于确定。如果从分布来看,显然从已知的波尔采文化到靺鞨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大的跨越。”[4]这里的靺鞨当指黑水靺鞨。
笔者赞同乔梁先生关于凤林文化非是靺鞨族源,波尔采文化或蜿蜒河类型还不能作为黑水靺鞨文化直接来源的判断。黑水靺鞨文化直接来源还应在晚于波尔采文化或蜿蜒河类型,而早于黑水靺鞨的遗存中去寻找。具体说来,目前被笼统划为黑水靺鞨的遗存中当存在早于黑水靺鞨的文化遗存,即勿吉文化遗存。按照这一思路,本文将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史书关于勿吉存史时间和地望记载为线索,以波尔采文化或蜿蜒河类型为上溯文化源头,对被学术界确定为黑水靺鞨的文化遗存作进一步的解析,从中剥离出属于勿吉的考古文化遗存。
一、史书所记勿吉与靺鞨
文献中关于勿吉与靺鞨的记述主要集中在《魏书》《北史》《隋书》与两《唐书》中的《勿吉传》或《靺鞨传》,其他如《北齐书》《太平寰宇记》等史料中亦有相关记载,但基本未超出前几部文献内容。在此根据本文研究主题需要,仅就两者的族源关系与所处地望关系略加陈述,主要是为廓清勿吉与靺鞨考古文化间关系提供文献史料佐证,这也是确认勿吉考古文化的基础与前提。
首先,需要确认的是勿吉与靺鞨的存史时间与承继关系。最早记录勿吉的史料为南北朝时北齐人魏收所撰《魏书》,但标明勿吉最早活动时间的则是《北史》,按照《魏书》《北齐书》《北史》等文献记载,以“勿吉”之名的朝贡大约起自北魏延兴中 (471—476 年) :“去延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魏书》卷八八《勿吉传》)《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二》则明确为延兴五年(475年)[5]。此后,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一说二年)、九年(485年)、十年(486年)、十二年(488年)、十七年(493年),北魏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年)至孝明帝正光年间,均有“贡使相寻”,规模显者达500人之多。最后记载勿吉朝贡的时间在北齐武平三年 ( 572 年):“是岁,新罗、百济、勿吉、突厥并遣使朝贡。于周为建德元年。”[6]106之后只见靺鞨不见勿吉。文献记载说明勿吉在这一阶段与中原联系较为紧密,同时也应是整个部落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由此可以确认,勿吉的存史时间在北朝的北魏至北齐阶段,其考古文化遗存的历史年代亦应锁定在这一时期。
靺鞨存史时间史料记述较为清楚,主要在隋唐时期。靺鞨称号初见于史在北齐河清二年(563年),当时将“鞨”记作“羯”:“是岁,室韦、库莫奚、靺羯、契丹并遣使朝贡。”[6]92《隋书》、两《唐书》均以《靺鞨传》或《黑水靺鞨传》记载,此不复述。
关于勿吉与靺鞨的关系,学术界基本认同两者存在同源传承关系,靺羯与勿吉只是同音对译用字不同,靺鞨是靺羯的改写[7]。但史书对此的记载仍有不确待考之处。因此有学者提出,“关于勿吉和靺鞨承转延续关系的认识即使按照传统的官方文献,也并非完全无懈可击”[4]。综合《魏书》《北史》《隋书》等史籍,由勿吉到靺鞨或许不能简单地用音转来概括,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成书较早的《魏书》更是只言勿吉而无靺鞨之名,亦无七部之说,仅是“各自有长,不相总一”的诸多邑落,是为早期勿吉的状况。其后勿吉不断发展强盛,至魏宣武帝正始年间(504—507年)西逐夫余。勿吉在扩张过程中,由原来的邑落逐渐发展到多部落,故《北史》《隋书》中始有七部之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靺鞨之名逐渐取代了勿吉之称。至于是音转而来还是相互融合的结果,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是,从族源角度而言,由勿吉发展至靺鞨当无疑义。由此确认,北魏至隋唐时期的勿吉与靺鞨存在着直接承继关系,也不排除在勿吉晚期和靺鞨早期交织共融存在的可能性。因此,勿吉考古文化与靺鞨考古文化亦当具有清晰的传承关系。
其次,要梳理的是勿吉与靺鞨在地望上的关系。《魏书·勿吉传》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去洛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月至如洛环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传中又记载了勿吉贡使乙力支自言其到和龙的经由是:“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太涂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魏书》卷八八《勿吉传》)对此,杨保隆先生综合《新唐书》《太平寰宇记》有关典籍记述及何秋涛、金毓黻等治东北史大家的考证,并验之实际地理, 提出今松花江中下游流段,乃至同江以下之黑龙江连在一起称难河的观点[8]。由此可确认,文献记录的勿吉活动中心当锁定在主流松花江流域迤北迤东的黑龙江中下游地区。
据《北史》《隋书》所记,靺鞨有七部之多,其中与勿吉活动范围重合度最高的当属黑水靺鞨。曹廷杰考证:“今爱珲城以西为古室韦地,则自今黑龙江以东俄界海兰泡,东至庙尔地方,凡混同江之南北两岸,皆古黑水部落,惟东西约径三千里,不止一千里也。”据此李德山先生考证:清人所说的“混同江”,系指今黑龙江自黑河市以东的江段;黑水靺鞨的居住地西起今黑龙江黑河、瑷珲,东至今日本海,北在今黑龙江南北两岸。因为其所居以“黑水”,即今黑龙江流域为中心,故在族名前冠地域之名,称“黑水靺鞨”[9]。以上考证可基本确认黑水靺鞨与勿吉主要活动区域相一致。
综上,勿吉的活动中心在主流松花江流域迤北迤东的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而黑水靺鞨的核心分布区也是以黑龙江流域为中心,两者的分布地望基本重合。因此,勿吉与黑水靺鞨的考古文化亦当分布在同一地域,且存在时间前后接续关系。
二、蜿蜒河类型和黑水靺鞨文化的关系
基于上述论证,在确认勿吉考古文化时必须与黑水靺鞨考古文化相比较。同时,勿吉因其存史年代早于黑水靺鞨,故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因此,有必要先对较为清晰的黑水靺鞨考古文化源流进行梳理。根据目前考古调查与发掘成果,以绥滨同仁一期为代表的考古遗存,已被界定为黑水靺鞨的文化遗存[10],与其关系较为密切的考古文化当属蜿蜒河类型或波尔采文化。乔梁先生认为,蜿蜒河类型或波尔采文化有可能是靺鞨文化最主要来源[4]。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在此拟对两者关系予以进一步分析。
蜿蜒河类型和波尔采文化的遗存大致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两岸地区,黑龙江右岸的被称之为蜿蜒河类型,俄罗斯境内黑龙江左岸地区的被称为波尔采文化。自杨虎、林秀贞先生专文论述[11]后,两者为两汉时期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两岸地区的同一考古文化的观点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12]。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之为蜿蜒河类型。蜿蜒河类型的主体特征表现为:房址均为木结构半地穴式,灶址多居室中心,有门,屋顶可复原成覆斗式。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大宗,多手制,质地粗糙,火候不高。纹饰以方格纹、水波纹、指捺纹及附加堆纹带最具特色。典型器以喇叭口球腹罐(壶)、敞口斜壁碗、敞口短颈通体方格纹的高体罐为代表。碳十四测定蜿蜒河类型的年代为公元前90—公元130年(树轮校正),大体相当于两汉时期,下限部分年代可进入魏晋时期。我国学者据波尔采文化较为发达的铁器推测其年代上限大概不会早于汉代。关于蜿蜒河类型的族属,学术界的观点并不统一,贾伟明专文论及文献记载的挹娄与挹娄系统为两个概念,并将蜿蜒河—波尔采文化划为挹娄系统[13]。笔者赞同此观点,蜿蜒河类型应是两汉时期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两岸地区的挹娄系统的文化遗存。
同仁一期文化亦主要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以往被界定为该文化的遗存包括绥滨同仁一期遗址、萝北团结墓地、绥滨四十连遗址等。同仁一期陶器均为夹砂陶,皆手制,典型器包括盘口罐、斜口器、敞口碗以及口沿下饰附加堆纹的深腹筒形罐。流行方形半地穴式板壁建筑,灶坑位于室内中部。
比较前述两支考古学文化,其文化的核心要素特别是陶器表现出谱系相同的直系亲缘关系。两者皆流行木结构半地穴式方形建筑,灶址位于房址中央。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皆手制,火候不高。蜿蜒河类型喇叭口球腹罐(壶)、敞口斜壁碗、敞口短颈通体方格纹高体罐与同仁一期的盘口鼓腹罐、敞口斜腹碗以及口沿下饰附加堆纹的高领筒形罐,无论是器物组合还是器形都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乔梁先生从陶器类型学发展的角度总结道:“波尔采文化如从类型学的角度分析,可能是目前与靺鞨基本陶器组合从器类到形制均最为接近的遗存”,并在分析靺鞨文化的渊源时提出:“在黑龙江中游地区早于早期靺鞨文化的波尔采文化中就流行着一种喇叭口、长颈的陶器,虽然这种器物的形态同靺鞨文化的盘口陶罐尚有较大区别,但就整体风格而言,两者间还是存在着许多共同点,在尚找不到当地早期靺鞨文化盘口陶罐的确切来源的前提下,目前也只能认为波尔采文化的喇叭口长颈陶罐同其的关系最为密切。”[14]
此处乔梁先生所说的靺鞨当指黑水靺鞨。笔者赞同乔梁先生从陶器类型学比对角度得出的同仁一期与波尔采文化即蜿蜒河类型陶器存在渊源关系的结论。这一重要观点对探讨勿吉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极具建设性。蜿蜒河类型所代表的挹娄系统的考古文化当是靺鞨文化最早的文化源头,但两者的年代并不是接续的,一个是两汉时期,一个在隋唐时期,所以蜿蜒河类型不可能是黑水靺鞨文化直接来源。根据肃慎族系先后出现的部族顺序,在挹娄之后、靺鞨之前的为勿吉部,因此介于两者之间的当为勿吉文化,换言之,勿吉的考古文化应在晚于蜿蜒河类型而早于黑水靺鞨的遗存中去探寻。
三、勿吉考古文化遗存的析出
基于上述分析,勿吉的考古文化遗存应锁定在蜿蜒河类型和同仁一期主要分布区的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从已经确定的晚于勿吉的黑水靺鞨遗存以及早于勿吉的蜿蜒河类型遗存中进一步析出确认。就目前发掘的考古资料,该区域晚于蜿蜒河类型,又与其文化密切相关的似乎只有以同仁一期为代表的一批黑水靺鞨遗存,我们的研究正是以这些遗存为切入点。
由于考古发掘有限及学术研究尚欠深入,以同仁一期为代表的遗存被笼统地界定为黑水靺鞨遗存。事实上,靺鞨之称最早出现于史的时间为北齐河清二年(563年),与室韦、库莫奚、契丹等“并遣使朝贡”[6]92,而被笼统划为同仁一期进而被认定为黑水靺鞨的遗存中,就有年代明显早于黑水靺鞨出现于史的遗存,且同仁一期文化自身也存在早晚的区别。所以在已确认的黑水靺鞨遗存中再做进一步的解析,从中剥离出早于黑水靺鞨的勿吉遗存,当是可行的路径。
将蜿蜒河类型与同仁一期遗址以及被划为同仁一期的遗存出土的同类器比较可以看出,以萝北团结墓葬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其特征晚于蜿蜒河类型而早于同仁一期,这些遗存我们认为就应该是勿吉的文化遗存。以萝北团结文化的标志性器物组合为坐标,相类的遗存主要包括:分布于黑龙江右岸的萝北团结墓地,以1982年发掘的3座墓葬[15],1983年发掘的10座墓葬[16]为代表;绥滨四十连1978年清理的3座房址[17];绥滨同仁遗址[10],以1973年发掘的F3和第3层(同仁文化一期早段)为代表。分布于黑龙江左岸的勃拉戈斯洛文诺耶和彼得罗夫湖遗迹[18]、奈费尔德古墓地和科奇科瓦特卡墓地[19]亦属于这一范畴。
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以萝北团结墓地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其年代早于同仁一期晚段而晚于蜿蜒河类型的时间,处于魏晋至南北朝阶段,与勿吉出现于史的时间基本相吻合。
以下与萝北团结墓地相类的文化遗存碳十四测年可为佐证。萝北团结83M9碳十四测年AD344—531年;绥滨四十连F1木炭测年AD257—526年;同仁一期早段F3碳十四测年距今1420±80年,树轮校正1380±80年(公元599—684年);黑龙江左岸的勃拉戈斯洛文诺耶测年AD370±20年;奈费尔德古墓地1962年木炭标本测年AD410—540年和AD270—600年。以上所列测年数据基本都在魏晋时期,同仁一期F3的数据较晚,但其上限尚处于南北朝时期,也在勿吉出现于史的时间范围内。
第二,从文化渊源和传承关系看,以萝北团结墓地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其主体因素当源自蜿蜒河类型,并延续传承至黑水靺鞨。
其一,典型器物存在演变关系。以蜿蜒河类型、萝北团结墓地和同仁一期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比对,萝北团结墓地的器物组合为盘口罐、深腹筒形罐、斜腹碗,这与蜿蜒河类型和同仁一期的器物组合高度一致。此外,通过对典型器物形制的演变关系研究更可清晰地看出三者的直接传承关系。
盘口(喇叭口)大罐。萝北团结墓地和绥滨四十连遗址都有出土。蜿蜒河类型出土的喇叭口大罐,口部呈喇叭状,鼓腹呈球形,底小而平,器口没有重唇特征。同仁一期的盘口大罐,口部呈盘状,直唇,宽沿,上腹鼓,下腹斜收成小平底。我们可以看出从蜿蜒河类型到同仁一期,喇叭口(盘口)大罐最突出的变化即从喇叭口转化成盘口,仅从口部的演变看,两者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显然这种变化之间是有缺环的。在萝北团结墓地中, 1983年发掘了51件陶容器,其中喇叭口大罐33件[16],特点突出地表现为喇叭口(上有小直唇)、束颈、小平底。比较萝北团结墓地与蜿蜒河类型会发现,如果将萝北团结墓地的喇叭口大罐上的直唇去掉,那么,两者的喇叭口的传承关系就清晰可见了。从蜿蜒河类型到同仁一期,喇叭口(盘口)大罐从喇叭口到盘口的演变似乎显得有些突兀,萝北团结墓地出土的器物是两者之间的过渡形态。三者的演变规律似可总结为,典型的喇叭口演变为口上接直唇的喇叭口,再到口与颈转折明显的带直唇的盘口。
深腹筒形罐。蜿蜒河和波尔采遗址出土的深腹筒形罐,体量较高,颈及器身通常装饰多条附加堆纹;萝北团结墓地及绥滨四十连遗址出土的深腹筒形罐,口沿下多装饰一周齿状附加堆纹;同仁一期的深腹筒形罐一部分保留了口沿下装饰一周附加堆纹的传统(F3出土),另一部分口部饰凸弦纹,形成双唇(F2出土)。深腹筒形罐的演变规律可以总结为:从蜿蜒河类型的通体装饰纹饰,到萝北团结及绥滨四十连的口沿下多装饰一周齿状附加堆纹,再到同仁一期的双唇。根据同仁遗址发掘报告,F3的年代要早于F2[10],是这种演变关系的支撑。
敞口碗。蜿蜒河类型出土的敞口碗形式多样,斜腹和腹略弧的碗同时出土,底部有圈足、平底之分;萝北团结墓地和绥滨四十连遗址的碗流行斜腹,均为平底,边沿略外凸;同仁一期的碗平底边沿外凸明显,且外凸的边沿压成波浪纹或在底部饰一周绳索状的花边。从蜿蜒河到萝北团结墓地再到同仁一期,敞口特征一以贯之,碗底边沿由略外凸,到外凸,再到外凸的边沿上装饰花纹,演变轨迹清晰可见。萝北团结墓地的敞口碗再次成为这种变化的中间传承者。
上述三种器物之外,绥滨四十连和同仁一期遗址同时出土斜口器,两者形状相似,只是绥滨四十连的斜口器较同仁一期的开口要高,口沿处饰附加堆纹或泥条。冯恩学先生在其文章中根据绥滨四十连遗址出土文物的特征、年代及地理位置,指出:“四十连遗址位于松花江南岸边,符合《魏书》描述的勿吉地理特征。故四十连遗址的族属应该是《魏书》记述的北魏时期的勿吉,又因为勿吉与靺鞨是一族称的不同译写,说其族属是靺鞨也是可以的。”[20]笔者赞同其将绥滨四十连遗址归入勿吉的观点,但是,勿吉与靺鞨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同一族称的不同译写,因为《魏书》最初记录勿吉仅有一部,并无七部之说,至靺鞨时期始有“著者”七部,显然是后发展分化而来,已经与勿吉有别,因此不能笼统地将勿吉与靺鞨划等号。
其二,房屋的营造技术存在递进式发展关系。蜿蜒河类型的房址呈方形半地穴式,灶址居中。绥滨四十连房址为方形半地穴式木构建筑,灶址大致位于房屋中央。室内穴壁镶有板壁,穴壁边上不见横梁,居住面上不铺木板。同仁一期房屋亦呈方形半地穴木结构建筑,室内中央有灶坑,举架升高,周边立房柱,其上架梁,居住面上铺防潮的木板。比较其房屋营造技术,三者都是半地穴式建筑,灶址大致位于房屋中央,木结构或有木板壁。不同的是营造技术日臻完善,蜿蜒河类型的房屋建造比较简单,四十连的房址木结构只是处于同仁一期木构建筑的初始阶段。
综上,从蜿蜒河类型到同仁一期文化,比较喇叭口(盘口)大罐、深腹筒形罐、敞口碗及斜口器,我们会发现:以萝北团结1982年发掘的3座墓和1983年发掘的10座墓,以及绥滨四十连的3座房址为代表的遗存出土的器物似乎都具有过渡性质。此外,就房屋建筑而言,绥滨四十连的房址在营造技术层面上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三,与文献记述的勿吉文化特征多匹配度较高。《魏书·勿吉传》记载:“其地下湿,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考古发现佐证了文献记载。同仁一期房址F3的基本结构是半地穴木构建筑,有木构基座。绥滨四十连发现的F1、F2房址内外均未发现柱洞,从房内中央塌落的炭化木头判断,当是一种“窝棚”式建筑,符合“穴居”“屋形似冢”;同仁一期F3房屋举架升高,居住面上铺防潮的木板,说明居住环境潮湿,符合“其地下湿”;同仁一期F3房屋顶盖铺木椽,上留天窗,下留出入口。这种于房顶下部开小型出入口的特点,适合爬梯出入,与“开口于上,以梯出入”相符合。此外奈费尔德古墓地经常见到马的遗骸,与文献记述使用马的习俗相符。
四、勿吉考古学文化的提出
前文依据遗存年代及对典型器物演变规律的分析,在黑水靺鞨遗存中剥离出勿吉考古文化遗存。既然我们能够把以萝北团结墓地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从以同仁一期为代表的黑水靺鞨遗存中析出,并推定其即为勿吉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那么把萝北团结墓地命名为萝北团结文化,并将萝北团结文化作为勿吉文化的命名文化,就显得很有必要了。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基于如下考虑:一是萝北团结墓地经过两次正式发掘,且两次均正式发表发掘报告,考古资料完整而信实。二是萝北团结墓地较之同仁一期文化遗存内涵单纯,时间跨度正是勿吉见于中原史籍记载的时间;同仁一期时间跨度较长,涵盖了勿吉与黑水靺鞨两个时间段,且被推定为黑水靺鞨遗存早已成为学术界共识,不宜作为勿吉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文化。三是自萝北团结墓地发掘以来,学者们对其研究比较透彻且意见趋向于一致,即将其归为同仁一期文化,属于黑水靺鞨文化遗存。我们所做的只是根据其存在时间及典型器物的过渡性特征,将其从同仁一期文化中剥离出来。
以萝北团结墓地作为勿吉文化的命名文化也有缺憾,萝北团结两次发掘均为墓地,没有居住址,遗存内涵单一。此不足可以同仁一期发掘的早期房址F3,及绥滨四十连发掘的房址作为必要补充。综合以萝北团结墓地为代表的萝北团结文化遗存,勿吉考古学文化可总结如下。
1.年代。从上文碳十四测年看,萝北团结文化的年代大致在魏晋至南北朝时期。
2.典型陶器。盘口罐、深腹筒形罐和斜腹碗是萝北团结文化比较固定的组合。尤其是盘口罐和深腹筒形罐出土数量较大,两者在萝北团结墓地的同一座墓中有伴出的现象。这表明,就萝北团结墓地而言,这两种陶器在勿吉考古文化中是并存的,也就是说是同时期的。当然,所说的陶器组合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黑龙江左岸的俄罗斯勃拉戈斯洛文诺耶和彼得罗夫湖遗址出土的陶器以盘口罐(报告称瓶形器)为主,奈费尔德古墓地和科奇科瓦特卡墓地则以深腹筒形罐为主,没有发现典型的盘口罐,但却有非典型的盘口罐出土。从年代上看,萝北团结墓地的年代明显早于黑龙江左岸的遗址。上述现象或许表明,盘口罐和深腹筒形罐在勿吉文化早期是并存的,在传播过程中并不以全部的组合传播。很可能的情况是,一部分人群偏爱使用盘口罐,另一部分人群更倾向于使用深腹筒形罐。盘口罐、深腹筒形罐和斜腹碗,或以器物组合形式,或以某种器物单独出现,代表了萝北团结文化陶器的显著特征。
3.房屋建筑。在属于萝北团结文化的遗存中,绥滨四十连、同仁一期文化遗存分别发现了房址。其基本结构为半地穴木构建筑,顶盖铺木椽,上留天窗,房顶下部开小型出入口,以爬梯出入。室内中部有圆角方形灶坑。室内窖,用于储存食物。有的房址起居之地居住面铺一层木板,木板底下垫圆形木条以隔潮湿。
4.墓葬。黑龙江右岸萝北团结墓地两次发掘墓葬特征基本一致: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一般没有葬具。葬式分仰身直肢一次葬和仰身屈肢一次葬,二次双人合葬。墓葬的一侧或角部设有生土台,其上置放陶器较有特色。个别墓葬于墓壁底部的一侧掏有小龛,内置兽头。所有墓葬均无明显的葬具痕迹,但其中的5座墓葬内含有零星木炭,这可能与当时的火葬习俗有关。黑龙江左岸的奈费尔德古墓地,墓穴呈椭圆形或长方形,均为二次葬。在20座墓穴表面上发现了带木炭的火烧遗迹,应与火葬有关。根据41座墓葬埋葬方式相同、随葬品相似的特征,发掘者推测奈费尔德古墓地属于同一个群体的居民。两岸墓葬的共同特征可以总结为:均为土坑竖穴墓,未发现明显的使用葬具现象,流行二次葬和火葬。
结 语
本文从考古本体出发确认勿吉的考古文化,实际所做的工作即是从原本认定为黑水靺鞨文化的遗存中,将萝北团结文化析出,主要基于这样一种逻辑:第一,蜿蜒河类型与以同仁一期为代表的黑水靺鞨文化两种考古文化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但是明显存在缺环,即两者之间并非直接承继关系,虽然具有诸多共同元素,但也仅能确定为族源上的间接联系。第二,以同仁一期文化为代表的考古遗存被界定为黑水靺鞨文化遗存,其时间跨度较大,从碳十四测年以及同类器物的比对结果看,其中明显存在着早于黑水靺鞨的遗存,且同仁一期自身也有早晚段之分,笼统地将所有遗存都简单地归结为黑水靺鞨的考古文化遗存显然有不合理之处。因此,从中析出勿吉考古文化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第三,以萝北团结墓地为代表的遗存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地望上都更加符合史料文献关于勿吉的记述。基于其典型器物介于蜿蜒河类型和同仁一期文化的过渡性质,以及在时间上早于黑水靺鞨而晚于蜿蜒河类型的情况,完全可以命名为勿吉考古文化。
在肃慎族系中,勿吉存史时间较短,文献记述也不多,且多与靺鞨相关联,隋唐时期粟末靺鞨创建渤海国,是为该族系首次崛起建立政权,勿吉也因靺鞨兴盛建渤海国而极易被忽略。事实上,由勿吉至靺鞨是肃慎族系发展中一个至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实现了由部落阶段到部落联盟阶段的飞跃。从宏观角度而言,靺鞨主体正是由勿吉孕育发展而形成。因此,确认勿吉考古文化对认识肃慎族系的演进过程及方式、解读古代东北民族历史均具重要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