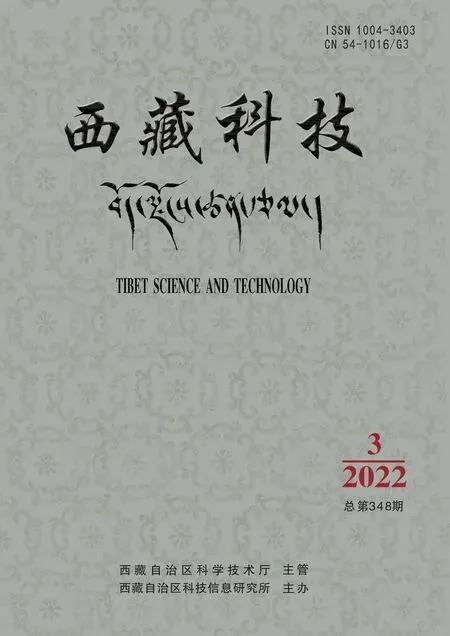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研究的五个取向*
——以西藏为讨论中心
赵国栋 刘华
(1.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2.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对生态文化的理解并没有权威定义,总体上有“宏观—广义”和“微观—狭义”两种理解视角,前者强调把生态文化看作一种文明形态,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对,后者强调更为具体的文化形式,突出日常生活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地方知识。本文将把两种视角相结合,突出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实践性,并以它为主线进行界定。
本文的界定是与日常实践直接或密切相关的,以围绕人与自然(环境)关系为中心,并主要体现于对这种关系的认知、处理的文化形态,一般呈现于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制度和物质等多个维度上。这种界定避开了传统两种理解视角造成的隔阂。关于中国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本文将基于对生态文化的这种界定,以西藏为中心,梳理和探讨生态文化研究的五种取向。
1 生态文化的整体化研究取向
此类研究取向通常围绕“生态文化”展开,把生态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并以生态文化的价值为研究中心,认为它是民族地区人们特定行为方式的深层的、重要的原因,主张它是解决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关键,并以生态文化为基础分析、评价民族地区各类问题的解决途径与方法。此类研究取向多以宗教文化、民族地区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为主。
该研究取向的形成可以追溯至“环境决定论”,特别是气候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其作用发挥的“路径中介”一般是基于人的行为文化,再至政体以及宗教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希腊的温和气候看作是适合民主政体的理想气候,寒带气候文化使当地民族缺乏本领和才智,所以难以形成完善的政体。在18 世纪,孟德斯鸠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宗教研究中,认为炎热气候导致意气消沉,所以倾向于消极的佛教兴起于印度。可见,对宏观结构而言,地理环境的作用仍在左右着一些与之相关的研究取向。
有研究认为,这种环境决定人的行为文化的分析已经被人与环境的模式所取代,该模式主张:环境起着一种“限制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作用,人与环境有着复杂的共同的相互作用。唐纳德·L·哈迪斯蒂主张,生态学的观点与方法已经逐步取代了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并且在今天已成为人类学解释最流行的方法之一[1]。虽然强调生态视角下文化的解释力,但他同时指出生态人类学也不可能提供最好的答案和解释所有问题。人类行为是如此复杂,以致不能用单一的原则去理解[1]。
廖国强等人认为自然与文化的吻合是一种必然,生存环境决定生存风格”[2],藏族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和游牧生活方式是青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特征决定的[2]。藏族三种游牧方式是一种文化构建的结果,其中主要因素有部落面积、人口多少、草场管理、牧场单位面积草产量、定居点牧户数及与之相关的牲畜数量,等等。[2]他们认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能够自我调适,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但也有某些缺陷,[2]这就意味着传统生态文化要向现代生态文化转变[2]。该研究强调自然环境的影响,并把人与环境互动形成的生态文化视作基础性的和动态变化的,生态文化的价值是其关注的中心。
该取向在专题研究西藏或藏族生态文化的研究中主要有四个体现维度。(1)苯教、佛教对生态文化的形成与维持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一点在大多数研究中被肯定。南文渊在分析苯教的影响时直言:苯教文化以崇拜自然、协调人与自然为宗旨,它融合了藏族先民创造的各种文化,为藏民族的统一奠定了文化基础。[3](2)广泛认可和使用“藏民族对高原环境的适应”观点。何峰分析了藏族对青藏高原环境的适应而形成的体质特征、器官特征以及由高原病引发的对死的体悟[4],认为看似原始甚至有违科学的禁忌习俗文化中,却蕴含着藏族极富智慧的生态文化观念[4]。(3)突出对“大自然的崇拜”及其相关后果,“万物有灵观念”则是产生崇拜的主要原因。[30]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对自然界中现象的神圣化在于人们对自然的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敬畏感。[3](4)强调生态文化内容的丰富性和体系性。譬如《藏族生态文化》从宇宙观、区域特征、相地理论、建筑、生命起源论、藏族的形成、人与动物的关系、生命理论、藏医学理论等维度进行了系统介绍。
该取向主张发现和有效保护、利用传统生态文化,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和发扬生态文化的价值,并以此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南文渊从六个方面回应了传统文化与保护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文化转化的问题。[3]认为传统生活方式是“保护和建设民族文化生态的基础”,而保护生态文化应该是全方位的,并且不能是功利性的。[3]尊重生态文化并以此为基础促进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构成了这些研究的重要观点。但是,针对这一取向,刘志扬强调:在西藏旅游观光的情境下,并不存在统一标准、客观存在的“西藏文化”,而是存在不同的理解、认知和诠释。[5]
2 生态文化的维持进取研究取向
此取向以生态文化的价值为研究中心,并把具体的生态文化视为当地生活方式的重要表现,对当地生活、经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主张保护具体形态下的生态文化,并使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呈现一种进取的态势。它并不主张以生态文化为主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相反,生态文化的变动整体上受经济社会发展制约,而它的反作用则体现于进取性地变化,这是该取向与整体化取向的一个重要差异。多以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为主。
此取向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划分为三类:(1)对具体农牧区域内生态文化的研究;(2)对某些具体文化形态的研究;(3)综合生态文化研究。当然,三者并不是截然相对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交叉,但侧重点有所差别,即前者突出区域的限定性,后者突出具体文化形态,综合研究则多针对某一民族的生态文化。
曾仁利的研究以西藏扎囊县扎西林村为田野场,从微观视角研究当地的生态文化。他通过民族志方法展现了扎西林村在能量转化守恒的载体、聚落选址、神泉文化、少耕和浅耕、播种、灌溉、拔除杂草等方面蕴含的生态文化。[6]他认为,当地生态文化体现出能量守恒和生态安全的原则,国家在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建设中应该结合这一特征,关注并利用好当地传统的生态文化。[5]
罗绒战堆分析了西藏阿里地区“神山圣湖”区域内的生态文化。他强调,要格外重视该区域的生态文化。神山地区是世界上生态最脆弱的地区之一,那里丰富的文化和生态景观也是不可替代的自然和文化宝藏。他通过类型化分析当地传统知识系统和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讨并肯定了该区域内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与生态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7、18]该研究对当地生态文化的缺陷与风险并未做过多涉及。关于这一点,赵国栋认为当地藏族群众对流浪犬的友善隐藏着以传播包虫病为主的生态风险,当地政府对流浪犬的治理路径来自于多种结构性压力,他主张要尊重当地人与犬之间的文化,并从生态产业视角把对流浪犬的“治”转化为“用”。[8]
该视角也多出现于对草原生态的研究中。麻国庆、张亮研究了阿拉善草原的生态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当地需要一种自主性的发展,并将其建立于对地方文化合理性的尊重之上;一味地突出一元化的“进步”价值判断,漠视文化的多元价值判断,一定会导致文明和文化的冲突,所以针对发展问题,要正视多元的观念和利益诉求,在现代牧区社会中形成“协调和对话的机制”。[9]包智明、石腾飞在对内蒙古清水区个案研究中强调,要重视和推进牧民的主体性地位。他们指出流动性是牧民面对生计方式与生活方式变迁作出的适应策略,它是应对牧区城镇化带来的生态困境的有效途径,这种流动性的再造主要通过牧业合作社、草原生态旅游业等牧区重建实现,使牧民在牧区与城镇之间往返流动。[10]
具体文化形态的研究涵盖了丧葬文化、水文化、能源文化、动物文化、植物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焦治平、胡冰霜考察了藏族主要的丧葬方式与地理环境、宗教文化历史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藏民族葬俗“双因素决定理论”“地理环境与宗教交互作用决定了藏民族葬俗”[11]。赵国栋从中层理论视角分析了牧区水文化的价值、风险与化解,认为本着“生态—经济—社会”的分析框架,在重视其价值基础上,要注意对水文化风险的化解与发展取向的引导。[12]先巴分析了牛羊粪作为藏族主要能源所具有的生态意义:一种和谐用能方式、体现藏族与高原环境相适应的用能技艺和智慧。[13]赵国栋以“神鱼现象”为切入点,尝试解读了这一现象的发生机制,认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应采取科学辩证的路径。[14]彭建兵、谢建辉在对布依族树神文化的研究中认为神树崇拜体现了布依族“天人合一”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同时,它也是“一种宗教教育方式……教育人们正确处理人与神、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15]
在综合研究中,尕藏才旦、格桑本研究了青藏高原游牧文化的成因、畜牧经验、牧民生活、部落社会以及口头文学等方面,认为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只能选择牧业,而牧业文化是藏民族智慧的产物。[16]王明东在分析彝族生态文化时认为,虽然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巧妙地利用自然条件从事农业生产,但这种方式却与现代生态文化的要求存在差距,他主张只有吸收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彝族的生态文化才能健康发展。[17]郭家骥指出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创造了独特的生态文化,这些文化中蕴含着古老智慧。[18]
该取向中的“进取性”主要指基于生态文化自身传统和外部环境变化而主动谋求更好的前景。杨庭硕、彭兵指出:合理的利用会促进生物物种的保护,某些人为生态系统能解决纯粹自然系统所不能解决的问题。[19]刘志扬研究乡土西藏文化传统的变化时,提出的“基于自信的文化传统的选择性重构”[5]观点对该取向的“进取性”是一个有力注释。
3 生态文化的现代化模式研究取向
该取向主张以“现代化的标准”评价生态文化,肯定生态文化在历史上发挥过的作用,但面对经济社会建设的新需求,这些文化多数需要按现代化的要求更新。该取向多采用经济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视角评价生态文化,多归入经济学、管理学范畴,关于生态文化的内容多作为整体研究的一部分。另外,一些关于生态现代化的研究亦与此取向相关,以“生态现代化”涵盖生态文化领域。对此,洪大用教授明确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20]
认为现代化中的进步取向与快速发展是解决一切生态问题的关键,朱利安·L·西蒙的《没有极限的增长》在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人口与环境的关系,该研究认为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才是解决污染的根本出路[21]。认为在市场发展的基础上,人口增长对发达国家是有利的,而且是一种最有利的投资:按照资本投资回收的标准,用折现计算的短期和长期人口增长的作用是利大于弊的,人口“投资”是比其它投资更有利的投资[21]。对不发达国家来说,总趋势是相似的[21]。
关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廖国强等人强调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要从传统转向现代,这是由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由传统的粗放型、自给型向现代的集约型、效益型的转变决定的。[2]一些研究主张,需要以科技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成升魁等人认为,要以技术现代化解决西藏的草地生态系统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强调重视技术需求与供给,包括科技创新、科技管理、科技合作等方面,这些在解决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灾害预警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22]
景晖、丁忠兵认为青藏高原先民在创造出光辉灿烂文明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23],但是,他们的现代生态环保思想滞后,到近现代后,人们不再或很少遵守宗教中关于生态保护的戒律,各种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接踵出现,加剧了育藏高原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解决的办法在于首先要加大国家对青藏高原的支持力度,通过制度化的转移支付,使高原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全国经济的发展而同步提高;其次要加强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23]。
关于生态现代化,陈学明认为,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是一种把工业文化与生态文明结合于一体的现代化。[24]他主张实现生态现代化,要使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脱钩”。他认为建设生态现代化,必须破除四个深层次难题:既要利用又应限制资本、既要发展又应驾驭科技、既要扩大又应改变生产、既要刺激又应引导消费。[24]付广华认为传统生态知识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着技术、制度和表达三个层面的困境,而生态文明建设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治理体系、现代生态理念这三种强大的现代武器将深刻影响传统生态知识。[25]
一些研究者反思了现代化取向。靳薇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各省市援助西藏的过程、成绩和不足,认为传统的以现代化为标准的援助模式造成了低效和浪费,并损害了西藏自身的发展能力,造成了“策略依赖”。[26]所以,要反思这种忽视西藏本土文化与需求的现代化援助模式。在刘志扬看来,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使西藏文化消失和灭绝,它的作用在于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将促进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使藏族传统文化更好地延续和发展。[5]
4 生态文化的附属范畴研究取向
该取向默认生态文化存在于少被发现和提及的日常生活中,是经济、社会的次生物,依赖于经济社会整体,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它对社会和生活的反作用力并不大,较少将其反作用纳入研究视野。这一取向多以管理学、经济学、人类学视角下的农牧区乡村建设研究为主。
对青藏高原草原方面的研究也体现出这一取向。胡自治认为草业是以草原资源为基础的多功能、多层次、多效益、综合开发利用的现代化产业[27],提出青藏高原需要从定居放牧、划区轮牧、多渠道消除“春乏”(春季家畜易生病和死亡现象)、季节性放牧、补饲、半舍饲以及提升人工草地建设等方面提高草地利用效率及可持续利用能力,提高农牧民生活质量。范远江强调西藏草场在牧区资源配置和生活保护中“既具有经济意义,又具有生态安全意义”[28],但草场产权的“公共性”使草场质量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提出“要加快推进和完善草场家庭承包制,明确草场所有权和使用权,加强草场家庭承包监督管理[28]。在研究中,草原文化被置于“建设取向”之下。
强调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多持该取向。罗绒战堆、樊毅斌对西藏农村社区毛驴数量的研究认为毛驴数量变化的原因在于经济环境、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变迁,生态环境退化导致毛驴没有足够的饲草,贫困与发展之间的张力是问题的根本,不仅发展会导致环境的变化,贫困更是生态环境的天敌。[29]沈宏益等人对生态安全与农牧民增收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认为经济社会发展可以增加地方财力,并进一步促进生态建设投入,所以,农牧民持续增收除了对维护生态资源安全具有积极的直接作用外,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更具有间接作用”[30]。
高原疾病研究中也存在该取向。王国强关于包虫病的调查认为包虫病是导致我国西部农牧区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原因之一[31]。该研究在西藏的林芝县、亚东县、措美县和巴青县每县随机抽取4个村。调查发现,中国包虫病流行范围广、病情重,青藏高原地区流行最为严重,所以对青藏高原地区要采取控制传染源为主的措施,实行犬犬投药,月月驱虫。[31]流浪犬是包虫病的重要传染途径,需要关注人与犬的关系与文化[8]。
实际上,农牧区的生态文化融于日常生活,看似细微,但却仍然可以直接作用于宏观结构。譬如荀丽丽强调,草原牧区的本土性知识极为重要,是牧民与“不确定性”共存的重要方式:不仅是放牧技术,而且是形成富于弹性的社会组织的方式和自觉保护自然的环境伦理。[32]赵国栋关于流浪犬的研究发现:在西藏牧区,人们对待流浪犬、接触草场、使用水源等文化现象加大了人患包虫病的风险,出现较高的患病率,这些直接引发了政府对牧区流浪犬的治理。[8]
5 生态文化的风险性研究取向
该取向认为生态文化具有积极价值,但是在经济社会进程中出现了风险,这些风险主要有两类:自身内呈现出的风险、外部带来的挑战风险,风险产生的原因、过程以及后果受到该研究取向的重视,以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为主。
一些英文研究成果持这一取向,譬如对人口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能源与乡村建设关系的研究、乡村燃料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乡村生活与生态环境演变关系的研究以及乡村聚落与地理人文环境的关系研究,等等。秋道智弥等人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认为,仅仅从生态系统角度开展的研究把人作为系统里静态化的元素,忽视了人的能动性,[33]譬如东非的游牧民进行各类牲畜组合放牧的实践以及狩猎者与猎物之间的互酬关系的建立与维持的实践[33]。该取向大多具备这种强调“人”而弱“系统”的倾向,但往往其解决的路径又会回到系统视角。
P.K.Gautam 在分析西藏气候变化与环境衰退时认为,藏族人对自然的观念以及牧民的游牧生活是西藏生态得以保存和持续的根本原因,但他指出,大量的非藏族人口涌入西藏带来了众多的生态问题,主要表现为加大了西藏人口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压力,并挑战了藏族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34]Marius Warg Næss同样强调流动的游牧生活是西藏牧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诀窍,流动性的下降导致他们的生活与自然的关系遭到破坏。[35]
饮食方面同样的研究也存在这一取向。Sindney W.Mintz 指出食物及其演变具有的符号象征性既丰富又重要,绝不是向身体提供营养可以概括的。[36]这一点在对西藏茶叶及其意义的研究中得到体现。赵国栋认为茶叶在特定的高原环境中为西藏人提供了一种生态性的保障,但这种文化面临的内外风险,譬如“茶文化与生态政策的关系模糊”“茶馆文化的生态性纠缠”,并基于此主张从多维度推进生态政策红利的实现以应对这些风险与挑战。[37]Emily Ting Yeh 关注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内地人到拉萨开展农副食品经营带来的系列后果,认为拉萨市郊出现众多的蔬菜大棚的过程是一种国家权力对西藏土地的“驯服”,并加剧了市场对西藏农民的排斥以及他们的“懒惰”。[38]
牧区流动性研究一般会涉及该取向。进入20 世纪90年代,以非洲牧区为主的研究流派把流动性范式(Mobility paradigm)推向高峰,该流派强调“对牧区的理解”。他们强调牧区流动性对牧区生态与发展的重要意义,譬如流动性是牧民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Anthony Egeru 就此指出牧民们根据不同渠道获得的关于气候的信息,并据此来适时地转移放牧区域和饮水区域,以此来应对气候带来的挑战。[39]又譬如,该流派认为流动性有助于促进牧区植被的恢复与保护。Richard Kock 等人强调,二十世纪的非洲牧区遭受了巨大破坏,[40]恢复牧区特有的流动性是进行生态恢复的重要手段。
该研究取向下的一些结论受到了质疑,质疑者认为这些研究多忽视了民族地区的整体性视角。关于Marius Warg Næss 的结论,曾仁利强调,虽然其看到了游牧与草场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但忽视了社会发展变化条件下牧民素质提高、公共资源有效利用和民生改善的诉求。[6]曾仁利强调的是一种经济社会历史中的整体观点,而在整体性中包含着某种破解“流动性困境”的出路,可能通过“城镇—牧区”之间的关联性形成更具进取性的流动性。对Emily Ting Yeh 的研究,刘志扬认为尽管该研究视角独特,但是得出的结论与事实相悖……其原因是她对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先入为主的片面理解和误读[5]。另外,也有质疑者强调运用资料的客观因果性。杨庭硕等人强调,在使用那些环境史资料时,探寻其间的客观因果关系需要格外谨慎,应确保“时间”“空间”“环境”和“文化”4 个维度的对接重合。[41]否则就存在误用资料的可能。
6 结语
以西藏生态文化研究为中心,五种生态文化研究取向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不否认生态文化的动态性。“静态生态文化”的观点已经无法与现实有效对话。这些研究也启发后续研究应更加关注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的复杂性以及其中的变动性,在经济、社会与生态进一步对话的时代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