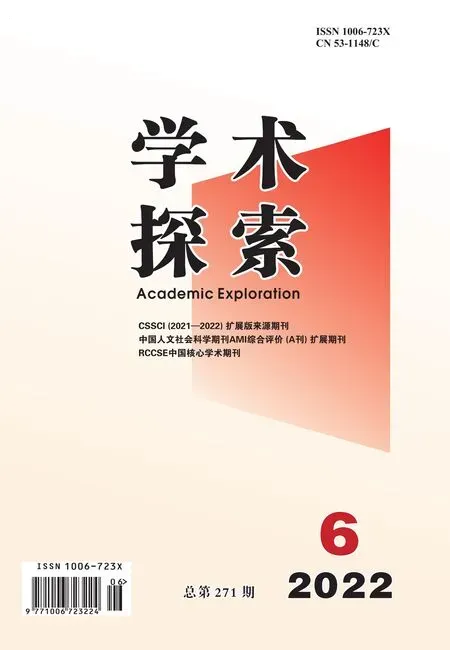孔子仁学的共同体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雷 震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核心精神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1](P164)这是对中华文化核心精神的高度凝练和总结,不仅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永恒价值,更体现出中华文化以人为本的特质。与西方传统尤其是基督教神学以“神”为中心的理念有很大的不同,从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人”是其所要探讨的核心,以人为本,在中国思想史上围绕着“天人关系”,历朝历代思想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这种对“人”的重视与关注,离不开殷周之际人文理性精神的觉醒。孔子继承了这一精神,并将其传承、深化、发展和弘扬,围绕着“仁”逐渐形成了一套关于人自身修养完善和人际关系处理的规范认识,“仁学”即“人学”。孔子仁学对于人的关注,不仅是对人自身认识的深化,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共同体思想。
一、 人文理性精神的兴起与仁学的形成
殷周之际,小邦周逐渐发展壮大,在殷、周的对抗中,不仅存在着政治立场上的斗争,还含有观念上的对立。殷人尚鬼,“好祀”“重祀”之风盛行。与殷商不同,由于周在发展历程中历经艰辛,故而更重视人。“德”作为周这一边陲小国对抗大邦殷的思想武器,逐渐成为当时周的统治阶层的共识。与商帝辛高倡天命,认为“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2](P309)不同,周的执政者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2](P329)“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2](P325)周人将天命与民心等同,将天命之转移与“德”相联系。而此时的“德”更多的是执政者之“德”。因此,这种“德”更强调施惠于民。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德”不再特指外得于人,而是指内得于己,越来越蕴含着更高的道德修养要求。而“德”观念,德的兴起与发展,表明人文理性开始觉醒,人文主义思潮已然勃发,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传统开始成形。“中国文化自西周后期兴起人文主义思潮,春秋时期已经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观念。”[3](P54)而孔子在其形成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殷周之际非自觉的观念,经过孔子将之系统化、哲理化,再经过后世儒家学者的继承与发展,使之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正是这一特征使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楼宇烈指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4](P46)
孔子的“仁学”不仅围绕着“仁”展开,更是结合了“礼”,对“人”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这种探讨是在周代礼乐精神的基础上进行整合的。孔子的“仁”是对“德”的偏重,重视人事而不迷信天命,强调自身修养,注重对社群关系的处理,这些方面都显示出孔子对“人”的重视。孔子不仅重视个体的人,也重视群体的人。尤其是孔子所提倡的在处理群体内部的关系与群体之间关系的“和而不同”思想,不仅在中国古代是处理社群关系的金科玉律,而且对于维护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亦对当下处理社会内部矛盾和国际关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孔子的仁学也蕴含着丰富的共同体思想,孔子对于人、社群、共同体的思考,不仅指导着古代中国社会的构建和价值理念的形成,更维系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正是具有这些永恒的价值理念,才构成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而且到今天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指导价值。
二、孔子仁学蕴含的人学内涵及其价值指向
孔子作为先秦儒家的开创者,继承三代文化传统和周代礼乐精神,通过对“仁”范畴的重构,以“仁”为核心,围绕人自身展开了对人生道德规范的探讨。于孔子而言,“仁”不仅是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也是施政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其基础是孝悌、核心是“爱人”,强调“以人为本”。可见“仁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即“人学”。
(一) 以人为本,树立人文理性精神
人文理性精神首要强调的是对人自身的重视。孔子提倡“仁”,强调人之“仁”,即强调人的重要性。“仁”作为四德之首,首先是与人相关,是主体人之“仁”。“仁”不能脱离了作为主体的人,“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条件,孔子通过“仁”透显出对于人自身的关注。“仁”作为人的价值的集中体现,要通过人的完善来实现。人的完善即通过道德修养来达到“仁”的境界。对于孔子来说要使得“仁”得以实现不仅需要自我修养也需要进行人际关系的调节。对于自我修养而言要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5](P177)对于人际关系的调节则需要所谓的“忠恕之道”,即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5](P178)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5](P91)达到“爱人”,通过人际关系的调节达到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目的。
孔子通过“仁”将人的道德修养树立于首位,并将之视为从事社会事务的基础,后来的《大学》对于修身的重视可以看做是这一思想的延伸。当然,“仁”不仅可以用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也可以用来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仁人,不仅要做到“仁民”也要做到“爱物”。“爱物”就是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调节,“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5](P104)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充分显示出了人对于自然万物的爱护和尊重。个人道德通过个人修养、个人完善得以完成。在整个过程中,天命的影响已显得极其微弱,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孔子哀叹周文化的衰微,却仍以传承、弘扬周文化为己任,所体现的正是人文理性精神。通过这种人文理性精神的树立,所要肯定的是个体的能动性,所欲实现不仅有个人的修养完善,更有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调节,最终要实现的是人的理想——天下“大同”。
(二) 鉴于三代,践行“仁以为己任”
三代文明是孔子仁学形成的思想来源,尤其是集三代文明大成的周代礼乐精神,更是奠定了孔子仁学的基础。殷周之际,随着人文理性精神的觉醒,“天”经历了从“宗教之天”向“道德之天”的转变。正是这种转变,促使人们对“德”予以重视。这意味着原来为鬼神所驱使的人开始试图摆脱鬼神的束缚,并逐渐自觉走上追寻自身存在意义之路。人不再只是被动地为“天命”所驱遣,无所作为;人可以通过修德,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天命”,而其实质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因此,自西周以来,无论从文化上还是政治上对人的重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并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文化传统。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各个历史阶段中这一传统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作为核心的“以人为本”这一鲜明特征却从未改变。而在这一文化传统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孔子基于“仁”所建构的仁学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孔子倡导恢复周代的礼乐之制,将“礼、乐”作为维护社会运作和稳定的规范,并向往“无为而治”,从源头上来看,孔子所构建的仁学滥觞于周礼。孔子以人为本,从人自身出发构建的“乃为一种根于身体、从身体推衍出社会人伦的伦理学理论”。[6]虽然由于受到周代礼法的影响,仁学带有宗法制的遗痕,因此在着眼于人自身的同时,强调从修身、齐家到平治天下。也就是说认识仁、实践仁的最终目的并不只局限于自身,而是要由己及人,最终达到自身道德修养完善与社会伦理价值实现的双重目的。正因如此,中国古代伦理学注重德性教育,并将之视作实现伦理价值的基础,强调以人为本,不仅着眼于人的发展,塑造人的完美人格,也强调个人在社会群体关系中的自我完善,充分体现了人本主义的价值。
(三) 天下为公,实现大同社会理想
仁学的核心是“爱人”,对于执政者则要求施“仁政”,并追求“无为而治”,因而强调公天下,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天下大同”。“大同”最早出自于《礼记·礼运》,这部著作虽然是由战国末年到秦汉之际的儒家学者所编纂,但这一思想的来源却是孔子,同时却也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在孔子的理想中,所谓的治世只有尧舜之时,并认为执政者的最高典范就是圣王舜,并称赞“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5](P236)而在“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公”是其核心。在这个社会中“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7](P769)
《礼记·礼运》所强调的“公”不仅包含权力的公有,也包括财物的公有。社会公权力的行使,以权力公有为前提。在具体实现路径上要求人才选拔时讲求“选贤与能”,而社会治理时则倡导“讲信修睦”,最终要达到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所强调的是“爱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以“和而不同”为准绳,在社会治理以反对苛政为原则,那么“大同”理想则比孔子理想中的尧舜之世更进一步。相比而言,尧舜治世,并没有完全达到“公”,而“大同”则是要彻彻底底地实现“天下为公”。这种“公”不仅有集体利益的实现,也有个体诉求的回应,最终要达到“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礼记·礼运》),[7](P769)实现人人安居乐业、天下太平。
三、 孔子仁学中的共同体内涵
周朝建立后,继承、发展了殷周的宗法制度,并大力推行分封制,构建起了以宗周为首,各封国拱卫的政治制度。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周公制礼作乐,以礼乐作为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但到了孔子的时代,原本由礼乐文明所维系的共同体已经难以支撑。“在王纲解纽的春秋时代,‘礼’与‘仪’的分化和社会的动乱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周初以来的‘敬德保民’思想,从而为仁从‘殊德’之一升华之‘全德’之名奠定了开辟了道路。”[8]“仁”作为全德之名,不仅强调自我的修养完善,而且还注重人际关系的协调,更因为源于周代充满忧患意识之“礼”,蕴含着丰富的共同体思想。
(一) 从家国到天下,共同体构建的基石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P505)人作为群体性的动物,不止有自我的升华与完善,还有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和群体关系的维护。人作为具体的、生活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的一切行为不可避免地要与周围所有的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如生产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等。因人生活于现实社会之中,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不断成长,因此必然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决定了人的本质,形成了人的社会属性。并从个人出发,发展成为家庭、家族、国家、天下,以文明为纽带,形成相互依赖、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在孔子看来,这一共同体既是实体性的命运共同体,更是文化共同体,而构成这一共同体的基础就是家庭。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群体的基础,以血缘关系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五伦”。正是由于家庭的重要性,如何处理这“五伦”之间的关系,便变得尤为重要。
孔子强调“仁”和“礼”在处理家庭关系中的重要性。在处理父母、兄弟关系时,孔子强调“孝弟”,并将之视为行仁的基础。在《论语》开篇论及何为“仁”的根本时,就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5](P4)所论及的就是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即“孝弟”原则,并认为“孝”就是“无违”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5](P17)家庭这个共同体以“礼”来维持,而最终要达到的就是父慈子孝的美好境界。以父子关系为基础进行推衍,便演变为君臣。由此,孔子将家庭伦理扩展到社会群体,并将处理家庭血缘关系的伦理规则应用来处理社会关系。而这一伦理规范作为家庭伦理的扩展,强调以天下为一家。也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仁学虽然重视血缘、宗法,但是并不刻意强调种族,“而是以天人合一的仁义道德为核心,以人性为基准,以文明为中心,以人类理想社会为引领,认识和调整民族关系”。[10]所欲构建的是“和而不同”、和谐共处的社会共同体。
(二) 从愚昧到文明,以文化构建命运共同体
西周时期,由于周文化的先进性高于周边的其他民族,周边民族都被周视为蛮夷,并严格夷夏之分。而至东周时期,随着宗周的衰落和各少数民族的崛起,各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程度却在不断加深。随着文化的互动,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出现许多不同于往时的新观点、新立场。孔子的观点就很具有代表性。孔子早年曾周游列国欲寻求可以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但郁郁不得志,始终未能找到可以一展抱负的国家,失望之余表示自己“欲居九夷”。有人问: “陋,如之何?”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5](P132)可见孔子注重的是君子的文化教化作用。
在孔子看来华夏之人和夷狄之人有着相同的人性,“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 ,[5](P236)“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5](P201)并认为华夷之辩,其标准不在于种群而在于对礼乐文明的认同和坚持,所以孔子认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5](P33)在孔子看来只要实践仁义道德,即使是蛮夷也可以被改变,而前提就是文化的交融。孟子更是对孔子的这一思想进行了发挥,孟子认为:“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11](P252)而实现的途径就是在肯定人在具有喜怒哀乐等人的共同性情的同时,不仅要尽人伦之则,也要讲信修睦之利,更要“志于道”。不仅要求道、闻道,更要行道,传道即通过王道政治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
虽然孔子通过“仁”这一范畴,围绕着人,构建了一个涵盖个人、社会与自然的人学思想体系。“孔子以‘人’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系统地论述……关于‘人’的学说”,[12](P15)尽管这种学说未能完全摆脱古代氏族血缘关系观念的影响,却让人从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奠定了中华人文理性精神的基石。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人”的关注正是在新时代对于孔子的人学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四、 孔子仁学共同体意蕴的当代价值
仁学对人的问题的系统探讨,充分显示出“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13]而其中的共同体意蕴,更是对当下我国领导人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新时代,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对于“人”自身的关注要求超出个人的范围,在更广阔的视域下对“人”的问题进行探讨。不仅需要关注人自身的发展完善,更要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不仅要着力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更要实现天下“大同”。
(一) 坚持理想信念,提升个人修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14]对于仁学中的共同体意蕴的吸收、借鉴,就是要在关注人自身道德修养提高的同时,需要从宏观的角度,倡导“和而不同”,通过文化交流促进文明之间的交往融合。
理想信念在中国古代体现于“志”,最早出自于《左传》。孔子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5](P135)说明立志的重要性,立志的前提就是要选择正确的理想信念。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5](P115)说明只有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导向,才能提升个人修养,从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提升个人修养的前提条件,其最终目的是促进人自身的发展完善。而孔子的人学思想所欲达到的不仅是人自身的完善,还有社会的完善;不但有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也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孔子人学思想的闪光点,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智慧和力量。其人学思想要求人不断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从而达到自我完善。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人是基本的单元,这就要求必须从人自身出发,通过对人类命运的关切,提高个人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从而让个人将自我的发展和完善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相联系。不再让单个人只局限于自我,而将视域扩展到全人类,不仅要为自我实现而努力,也要将眼界扩大到国家、民族、全人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完善。
(二) 传播中华文化,提供中国智慧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轴心时代开始,就形成了系统的关于文化的价值、德性的认识和理论的实践。儒学延续了中国历史早期文明与西周人文主义思潮的余绪,在昔日就显示出对于仁爱、礼乐价值的重视,形成了关于人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群关系的诸多思想,并具有普遍意义。这些思想可以概括总结为两条:一是崇仁;二是尊礼。围绕着“崇仁”和“尊礼”所形成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制度,构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仁”作为自我对他人的态度,对他人的关怀爱护,或是对他人施以恩惠,不仅是自我修养的重要体现,而且因为这种关系体现在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具有交互的特征,实则是一种个体性又兼具群体性的道德观念。孔子提倡“仁”,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将“仁”的范围扩展为基于“亲亲”,终于“爱物”的“亲亲—仁民—爱物”系统思想。“仁”的内涵已超出社会伦理的范围,迈向了自然伦理。这种对于源于血缘关系和氏族民主的“仁”的自觉转化和发展,体现着中华文化所具有的连续性特征,“礼”亦如此。“礼”虽然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实践“仁”的基本方式,但其中不仅蕴含着西周礼乐精神,而且充满了人文理性精神,体现着对礼教本性、精神和价值的充分理性肯定。“礼”不仅是共同的行为准则,也是处理群体关系的共同准则,是相互尊重的表达。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文化“敬让他人”的精神,对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而处理国与国关系时的“礼让”,更包含着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无不为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处理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中国智慧。
(三) 推崇和谐共生,共建美丽世界
《共产党宣言》曾指出,由于世界市场的开辟,“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5](P35)在理想社会里,“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16](P117)新时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历史早已步入全球化进程,闭关锁国在当今时代已无可能。世界各国在与他国的沟通、交流中相互依存,人类社会早已处在有机的联系中,并形成了一种利益纽带。各国要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自己的利益就要维系好这种纽带,就需要强调天下一家,需要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而不是以自我为优先、以自我为中心。
孔子的时代,在处理复杂的人际交往关系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时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从“我”和“人”两个层面上论述了和谐的社会关系的构建渠道。对于身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的世界各国来说亦是如此。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能仅从自身角度出发,力求实现利益最大化,而是要将本国利益注入全球利益链中去考量。“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17](P37)而不应事事以本国利益为先。
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孔子所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今世界,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全球非传统问题层出不穷,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在增强人对自然统治的同时,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和有机本性。”[18](P89)而消费主义的盛行更是加剧了生态问题的恶化。人类生存环境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这些与“人”相关的问题,如何加强有机联系,并在全球非传统问题上加大合作力度,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人类这一超越了族群、种群的维度出发,以人类整体的眼光来应对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欲重新构建的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与自然的和解”。这不仅关注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也关注人类文明的良性延续,从而注重在更高层次上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
结 语
习近平在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深刻内涵时提出:“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19]“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倡导建立一种更高程度的、走向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包含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的要求,更有对文化建设的需求。文化建设要提升至更高的一个层面,就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出发,推动以“人”为中心的人类文化共同体建构,将对“人”的关注提高到人类的层面,强调通过人类全体的共同努力和奋斗,消除文化、文明冲突,构建和谐共生的新世界,从而为新时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全新的价值观基础。这一基础的夯实,不能脱离对“人”的关注,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不仅更多地需要宏观层面的构建,还需要微观层面的拓展,即不仅需要在国际关系中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要将其贯穿于塑造人、发展人全过程中。将人自身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相结合。而孔子对于“人”的关注,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为这种精神的构建打下了中华文明的烙印,由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强调对“人”的关注,也要求从宏观层面出发,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当下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不仅是对以人为本的中国人文精神的继承、发展,更为解决当今世界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当今世界发展和合理构建和谐美丽新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