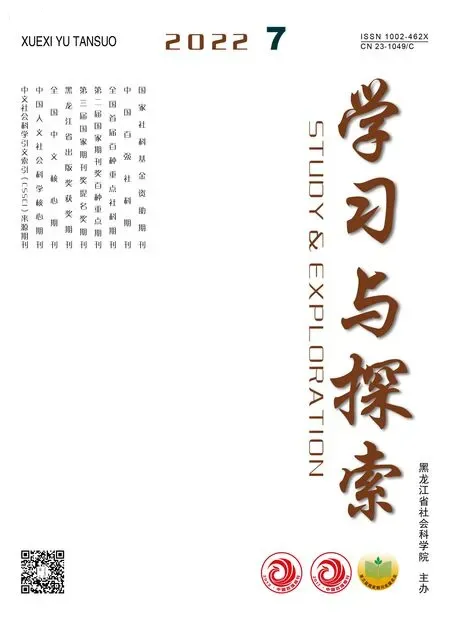朗西埃的左翼文论与以《讲话》为中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
韩 振 江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知识分子相继报道并译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尔后,毛泽东《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论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也被翻译为法文。自此,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1940—)、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1937—)等纷纷研习了这些经典文本。在西方理论视域下他们所接受的毛泽东思想被改装成了“毛主义”(Maoism),并视之为纠正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和新路径。作为阿尔都塞学生的朗西埃早年也深受毛泽东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影响,他在“五月风暴”(The May Movement)的洗礼之后,与其导师产生了思想分歧,独自从19世纪工人档案和劳工运动中凝练出了歧义政治、感性分享、审美政治等文艺理论。那么,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毛泽东政治哲学和文艺思想与朗西埃的左翼文论有何种联系和差异呢? 这个问题对于理清朗西埃左翼文艺思想的来源及其特征,同时对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阐发毛泽东文艺思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群众路线与朗西埃左翼文论
法国“五月风暴”的发生在思想上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深刻影响。早在50年代,阿尔都塞带领他的学生朗西埃、巴迪欧、巴里巴尔等研究《矛盾论》《实践论》等经典文本,他相继撰写了《保卫马克思》(ForMarx)、《论再生产》(Onreproduction)等著作,并且与学生共同撰写了《阅读〈资本论〉》(ReadingCapital)。阿尔都塞学派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发客观上促进了法国语境中“毛主义”思想及其政治运动的蓬勃发展。在这里,“毛主义”(Maoism)特指法国语境中的左翼知识分子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和阐发,这与毛泽东思想不能等同起来。或者说,法国语境中的“毛主义”是法国左翼眼中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理论的思想镜像。“作为不到三年以前获得胜利的中国革命的领袖,毛对阿尔都塞来说似乎是一个‘新列宁’:实际上自1917年以来,共产党的领袖第一次既是一位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即一位货真价实的哲学家),又是一位天才的政治战略家,他将革命力量引向胜利,并显示了自己有能力运用概念的方式对革命胜利的根据进行思考。因此,他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化身。”[1]19
朗西埃在巴黎高师求学期间就接触了毛泽东思想,“五月风暴”的革命实践和“毛主义”的影响终身性地改变了其学术思路。朗西埃说:“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加入了法国的毛泽东主义小组,这影响了我的正常哲学道路。后来斗争中遇到了挫折,陷入了苦恼,觉得革命失败了,我应该去研究一下工人的自我解放。于是,我就去研究工人的书信、日记、诗歌等。从那以后,我就不能正常地搞哲学了。”[2]朗西埃受“毛主义”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他积极参加了左翼革命运动,其二是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不同,导致了他与阿尔都塞决裂,走上独立自主的学术道路。
在“五月风暴”中起到中坚力量的左翼政治组织有“马列主义共产青年同盟”(简称“共青盟”UJCML,1966—1968)“无产阶级左派”(GP,1968—1973)等,以及有影响力的刊物《人民事业报》(LaCauseduPeuple)、《逻辑造反》等,这些“毛主义”组织基本上都是阿尔都塞的学生们建立的,而朗西埃是其中的主要成员和刊物编辑。1966年,罗贝尔·黎纳(Robert Linhart)、邦尼·莱维(Benny Levy)、朗西埃等青年知识分子建立了“共青盟”,他们吸收了毛泽东重视教育和动员民众的思想,非常推崇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3]853并明确文艺应该为千万人民大众服务,号召革命的文艺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3]861。1943年,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3]899这更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和组织办法就是党员与群众相结合。“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3]933在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群众路线的宗旨和工作原则。随着毛泽东著作的译介和阐释,以“共青盟”为主体的青年学生发起了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和车间工作的“扎根”(établissement)运动。他们广泛地对底层民众的调查研究,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
1968年,法国政府取缔了“共青盟”在内的11个左翼组织,随后莱维、朗西埃等重新组建了“无产阶级左派”。后来,“无产阶级左派”发展为法国六七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毛主义团体。1970年,他们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的主编被捕,萨特出任主编并亲自参加游行运动,支持毛主义左派的革命主张。1974年,“无产阶级左派”停止活动,但朗西埃又创办了《逻辑造反》杂志,并开始把长达十年左右的对毛主义和激进左翼运动的经验转化为学术研究。“朗西埃开始研究工人档案,编辑出版了《工人的话语:1830—1851》。在‘无产阶级左派’中的政治活动经历,给朗西埃的思想烙下了不可磨灭的毛主义的印痕。”[4]24
朗西埃回顾这段革命的经历和对工人的研究,他与阿尔都塞的“阁楼上”的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了。他在《无知的教师》《阿尔都塞的教训》中把阿尔都塞看作高高在上的指导革命的“导师”,但他认为真正的工人运动不需要教条主义的“引路人”,劳工大众可以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朗西埃说:“阿尔都塞对学生造反的态度是很僵化的。他认为他们本身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局限,搞不来阶级斗争的,必须接受理论训练。……这就使得阿尔都塞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很被动。我当时就认为,在革命中必须像毛泽东那样,相信群众的能力。而我认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对普通群众能力的不信任。……一句话概括,我与阿尔都塞的主要分歧在于:他认为科学和党在先,理论和批判在先,而我认为应该相信群众的能力在先。”[2]于是,阿尔都塞“开除了”朗西埃,并删掉了朗西埃撰写的《读〈资本论〉》章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朗西埃与阿尔都塞决裂的思想原因之一就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不同接受和阐释,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文艺理论对朗西埃的政治美学和文学政治论深有影响。
二、治安政治、无分之分者与人民概念
我们简化朗西埃的政治思想,用一个公式来表达二元对抗的政治:统治者/被统治者=有钱有权者/无钱无权者,/表示压迫的治理或治安政治体系。“政治往往被视为一组达成集体的集结或共识的程序、权力的组织、地方和角色的分配,以及正当化此一分配的体系。我建议给予这个分配和正当化的体系另一个名称,我建议称之为‘治安’(police)。”[5]46也就是说,朗西埃把政治分成了两种结构,一种是西方现成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他称之为治理、治安政治,这是西方虚假的形式民主政治。治安或治理,是源自于福柯的治理技术,指界定人们说话、行动和存在方式的身体分配秩序。或者说,治安政治逻辑是在现实中分割、界定人们行为、语言和感受方式的宏观政治秩序和微观社会秩序。另一种是政治(la politique)结构,朗西埃称之为与治安政治相对立的“后政治”或“解放政治”,是要彰显人民的平等权利和感性要求,突破或解构现行治安政治体系。“借由一个在定义上不存在的假设,也就是无分者之分,来打破界定组成部分与其份额或无分者的感知配置。此一决裂,是在重新配置用来界定组成部分、份额之有无的一系列空间活动中表现出来的。”[5]48
在二元对抗的政治结构中,处于上层的统治地位的是政治秩序中有权力的富有阶级,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是广大的无权、无名、无份的人民大众,而西方政治的实质就在于如何对人民大众进行欺骗式的份额计算。因此,“政治存在于,社会的部分(parts)与组成分子(parties)的计算被那些无分者之分(une part des sans-part)的算入打乱的地方。而当任何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平等嵌入人民的自由时,政治便已展开”[5]159。朗西埃指出,元政治最重要问题是如何把实际上无权的人民说成、表述成为治理政治中的自由公民。换句话说,西方政治原初结构是一个基于对人民的计算错误而成立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人民有权的谎言之上的实际政治统治。
亚里士多德认为,那些出生在城邦、拥有土地和生产能力的市民,是具有自由属性的人民,人民的自由与贵族的品德、寡头的财富共同构成了组成政治的份额。然而,本来就不具有自由属性的人民在政治计算中把自由贡献给了统治阶级,由此实际上是无分之分、无名之辈。“无分者没有参与之分。只有被计算为组成分子者,才有其分。”[5]29“正如人民并不真正就是人民,而是穷人;穷人本身也并不只是穷人,他们只是没有任何特性的一群人,他们由于最初区分之效果而承担了自由之空名,不属于自己的属性,一个引发争议的资格。……他们就是政治本身的结构性错误或是扭转(le tort ou la torsion constitutifs)。穷人的党派,除了作为无分之分而具体呈现自身之外,别无其他。”[5]28
在朗西埃看来,人民的别称就是无分之分者,无论是历史上的奴隶、农民、第三等级,还是现代社会的工人、无产阶级等都是无分之分。朗西埃认为,人民同时存在于治安政治“分子”份额与真正政治的阶级“分母”的二元政治结构中。个人在“分子”中被称之为公民,也即政治法律中规定地拥有平等人权的个体,其天赋权利让渡给政府,被政府所代表,由此参与政治。在阶级“分母”中的人民,则处于实际的无权状态,也就是无名无份的人民大众,因为治理体系的政治规则会规定无钱的、非白人的、非男人的等人民不能拥有或使用实际的参与政治的权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统治阶级会把自身的利益说成是代表了全社会所有阶级的利益,在西方民主政治中,人民成为一个空头的自由形式,在选举中被代表计入数目但实际政治中并无权利。
那么真正的政治如何发生呢?人民如何从无分者和无声者的非存在状态转变为存在状态?朗西埃依然从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革命思想里找到了源头。他把马克思的解放政治称之为“后政治”,即让计算错误的地方进行纠正,让非存在的工人等以无产阶级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让无分者突破治安政治秩序,让无声者发出自己的感受和声音。“透过建立一个在根本上极为异质的假定,亦即无分者之分,破坏治安秩序的感知分配。此一假定本身,最后将揭发秩序的纯粹偶然性,以及每一个言说者和其他言说者之间的平等。当两个异质的声音在某个地方遭遇彼此,政治便发生了。”[5]48-49也就是说,当治安逻辑与平等逻辑不期而遇、发生冲突的时候,该事件就具有了政治性了。例如工人罢工,当罢工的诉求是较高的薪水和好的待遇时,则不具有政治性,因为这是在治安政治秩序内部进行协调和革新的问题;当罢工要求革命性变革,特别是涉及工人政治和经济权利分配时就具有了政治性,因为政治行为就是要打破治安秩序的规则、界限和结构,以便彰显共同体之成员的感受。政治就是平等逻辑对于原初计算错误进行“纠错”的过程,这一“重新计算”关联到人民的工作、角色和场所的分配。
真正政治的发生有赖于无分之分者转化为政治主体,或者说政治是政治主体化的过程。朗西埃认为,当布朗基在法庭上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时,就意味着作为职业的工人向作为政治主体的无产阶级转化了。无产阶级既不是社会团体,也不是手工工人,也不是劳动阶级,“他们是那个只能作为不被算入者而被算入之不算数的阶级。‘人民’(Demos)是将部分与整体同一化的主体。相反,‘无产者’则是主体化那些让整体与其自身有所差异的无分者”[5]58-59。也就是说,工人与无产阶级分属于不同的“人民”概念,作为工人职业的人民只能占据治安政治秩序中的被剥削的位置,他们虽然被民主政治计算在内,但实际上无法参与政治,无法表达自我感知;而作为无产阶级的人民,则一方面揭开了在自身上隐藏的治安政治的计数错误,另一方面将自身的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等同,通过解放自身而解放全部被压迫者、无分者。
尽管朗西埃用歧义政治代替了阶级政治,用无分之分者表述人民概念,但从他抓住了政治内在的分裂,即治安政治与后政治的对抗、统治阶级与无分者的矛盾,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解放的政治观念,并与“毛主义”的人民概念存在同源的相似性。毛泽东认为,整个人类社会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并维系社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由于分工不同和对成果分配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阶级,统治阶级占有并剥夺了被压迫阶级的劳动成果,并通过社会制度加深阶级剥削程度,以此维持贫富差异,而政治就是这种阶级统治的工具和制度体系。因此,社会基本矛盾是由不同社会阶级的对抗造成的。
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有封建阶级、买办阶级、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等,即所有阶级划分为两种: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中国,统治阶级是封建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是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结合,被压迫的阶级是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等。这种二元矛盾的阶级体系下,要想达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政治愿景,就必须联合所有被压迫阶级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统治阶级的联合体。在解放政治中,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团结和联合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一阶级的大联合就成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先进的无产阶级代表要唤醒民众,走群众路线,满足人民的需求,进而使人民成为革命的主体,进行革命推翻统治阶级。一旦推翻统治阶级,则建构出阶级联合体,通过代表制度,人民直接掌握国家政权,实现人人平等的普遍选举权。这一点就是国体和政体的基础。1948年,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装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3]1272
由此可知,朗西埃与毛泽东在解放政治有一致性,也有很多差异。两者政治思想都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和对抗,致力于被压迫者的平等和解放。他们都认为在二元对抗政治体制下,无法通过把人民纳入治理政治体系中予以解决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问题,更无法解决政治平等的问题。唯一解决的途径是人民觉醒起来反抗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体系。但是朗西埃和毛泽东的不同之处也比较明显。虽然朗西埃把政治看作“治安政治”与后政治或政治的对抗体系,但他认为人民凸显自身的平等权利通过改变治安政治的规则就行,方式依然是在民主政治体系内的共识民主。但毛泽东更为清醒地指出在原有治安政治体系下人民大众的政治权利不可能得到实现,必须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全面地替代压迫性地统治工具。简言之,在探索人民大众实现平等政治权利的途径上,朗西埃还是秉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坚持了在资产阶级政治内部进行民主运动,而毛泽东则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毛泽东和朗西埃在人民的概念上的共识与差异表现在:他们都认为在对抗政治体系中,人民是被压迫的、被边缘的无权无名者。无分之分者或乌合之众可以转化为具有自觉意识的政治主体和革命主体,进而成为改变政治体制的力量。但朗西埃的人民概念是“整体与排除”的关系,也就是说,人民是被治安政治秩序实际排除在外的无名者、无分者,比如奴隶、农民、工人、第三等级、无产阶级以及现在的同性恋、有色人种等。治理政治中的“人民”既在名义上包含这些无分者,又在实际政治秩序中排除了无分者,如此一来无分者就要通过改变治理政治所固定的界限、规矩和结构来彰显自身的平等权利。
毛泽东的人民概念则是“整体与吸纳”的关系,即在排除统治阶级之外的其他各阶级的联合体,通过这个阶级联合体推翻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机器,因此人民的内涵在不断地吸纳其他阶级,外延在不断地扩大。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6]58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又把“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其他爱国主义分子”纳入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组成之中,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具有革命的软弱性,但他们受到了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压迫,具有革命要求。1948年《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明确指出了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3]1475。明确把以上四种阶级联合体明确为建构人民共和国和政府的构成部分。由此可见,毛泽东的人民概念是被压迫阶级和阶层的联合体,一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等统治阶级不属于人民范畴,是革命的对象;二是这个人民大众的联合体要组织起来,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来实现人民的民主和平等权利。无疑,毛泽东的人民观是更为宏大的被压迫者的统一战线,其目的在于通过武装革命建立国家政权,直接实现人民民主专政。
相比而言,朗西埃的无分者是指在现有政治秩序下被排除的人民大众,其概念具有一定的含混性,一是现有政治秩序中的所有者都被赋予人民的称谓,但这个“人民”在朗西埃看来是虚假的;二是被政治秩序排除在外的“剩余的大多数”,这个人民才是真实的,具有平等政治要求的。但被压迫的人民如何实现其平等政治诉求,朗西埃最终还是认为应该在民主政治框架下进行共识民主斗争或激进民主运动。从历史上来看,正如齐泽克所批评的那样,激进民主政治最后往往被资产阶级政治体系所吸收和驯服而变得“无害”。朗西埃的歧义政治和无分者可能从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和人民大众的理论中吸取了思想养分,但带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有限性,很难在现实社会中落地。
三、“文学政治论”与人民文艺
当代西方政治美学化思潮中,朗西埃的政治美学和文艺理论是独树一帜的。他认为政治与审美两个领域具有共同的基础,这就是感性共享,或感受性的分配共享。政治哲学应研究个人平等权利如何在共同体中实现,美学研究的对象应是个人的审美平等权利如何在审美体制中予以显现,个人政治权利和审美权利的实现焦点在于感性感知的权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极为重视感性问题,指出人的本质在于感性的生命活动,社会异化劳动的后果之一就是损害了人的感性感官和感受力,使得人们感受不到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的存在,而变成了异化劳动和资本的奴隶。马克思在这里就点明了人作为感性存在的生命,其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具有审美意义。在继承马克思的基础上,朗西埃指出“所谓感受性的分配共享,意味着宣示的逻辑必然也是宣示的美学。政治并不是最近才不幸地被美学化或奇观化。……因此,并没有属于现代的政治‘美学化’,因为原则上政治就是美学的。但是,在话语秩序与感受性分享之间作为新的结合点之美学自主化,则是政治的现代配置的一部分。”[5]80-81
换言之,他认为审美不是外在于政治的,而是内在于政治的,即政治体制和审美体制具有同质化的等级配合秩序。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真正的政治在于揭示和解放普通民众的感性和感知不平等,感性分配的不公直接产生政治的压抑。审美政治的“歧义”就是要唤醒民众,通过政治、思想、审美和艺术等诸多形式使得那些没有声音者发声、无分者有分、不存在者存在,在社会共同体中人人平等地分享和分有感性感觉。朗西埃的平等政治诉求也在文艺和美学上体现出来,这就是文学政治论。
(一)朗西埃的“文学政治论”
朗西埃认为,文学与政治之间有一种相互配合的同质等级秩序,也就是说审美和文艺体制总是反映了政治社会等级体制。因此,在西方的治理政治秩序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封建贵族、资产阶级、有产者,处于社会被漠视地位的是小生产者、小商业者、小知识分子、农民、工人等人民大众。而在文艺体制中,丰富多样的文艺样式在反映对象和内容上表现的也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统治阶级,而不是工人、农民等无权无份者。所以,西方文艺和审美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人民大众是漠视其存在的,也就是说,虽然人民大众在身体上实际存在,也在实际生活着,但无法发言,也无法被文艺所表达,更无法把属于人民自己的审美感受通过人民自己的审美体制表现出来。基于以上原因,朗西埃认为文艺应该革命,这一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原有的文艺—政治连结机制,即在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人在文艺机制中就天然拥有主角的光环。文艺政治应该表达那些被压迫者的诉求和感受,审美应该是人民自己的感受和审美。
因此,文学政治是“这种对空间和时间的分配和再分配,对地位和身份、言语和噪声、可见物和不可见物的再分配,形成了我所说的感性的分配(Partage du sensible)。政治活动对于感性的分割进行了重新配置。它向公共事务的舞台引荐了新的客体和主体;它让不可见变得可见,让那些曾经仅仅被当作吼叫的动物成为可听的说话生灵。因此,‘文学的政治’这种表述势必包含如下含义,即作为文学的文学介入这种空间与时间、可见与不可见、言语与噪声的分割。它将介入实践活动、可见性形式和说话方式之间的关系”[7]4-5。在朗西埃看来,文学的政治不是政治家的文学,不是文学家的政治,也不是文学作品中直接图解政治政策,而是文学文本的内容展现了与当时政治等级同质化、同构化的感性想象和感知图景。文学政治就是要打破这种政治与文学配合的等级体制。所以,朗西埃认为文艺是一种审美体制,“文学是一个识别写作艺术的新制度。一种艺术的识别制度史一个关系体系,是实践、实践的可见性形式和可理解性方式的关系体系”[7]8。
综上所述,文学政治论的含义如下:第一,政治与文艺是具有同质化、同构性的、配合性的等级体制,这一体系是政治权力所分割和界定了人的生存状态和感知体验。第二,作为审美体制的文艺是反映政治等级化社会秩序的媒介平台,在治理政治中处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不同地位的人们体验到的感知不同,而在文艺中所处的地位和角色也不同。第三,文艺的政治性在于要反对和解构审美和文艺等级体制,使得原来处于无分者、无声者、无名者地位的人民及其感受登上文艺舞台,在文艺文本中占据主角,革新文艺形式以凸显人民的新感受和新感知。
基于此,朗西埃批评了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理论,认为古典诗学所鼓吹的是帝王将相占主角、无分者毫无地位可言说的政治等级化。贵族在古希腊政治中是统治者,那么在悲剧中必然是主角,而且是善良和正义的人,而平民和奴隶在现实中没有政治权利和发言权,在悲剧和喜剧中就成为被讽刺的丑角,成为不配有好命运的人。“根据这个等级关系,虚构被划分为不同的体裁。有高贵的体裁,用于刻画高贵的行为和人物,也有低下的体裁,用于描写小人物的故事。体裁的等级也让风格服从于一种相应的原则:国王必须以国王的身份说话,普通民众以普通民众的身份说话。这一套标准将比学院式约束的定义更为严格。它将诗学虚构的合理性与人类行动的某种理喻性形式连接起来,与存在方式、做事方式和说话方式之间的某种对应类型连接起来。”[7]12-13这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诗学延续了近千年的历史。要改变这一政治社会秩序与文艺诗学秩序相互对应的等级关系,朗西埃认为有一种新型资产阶级的文学政治:一方面表现社会等级差别的文艺体系的垮台,另一方面反映新人物和主题的资产阶级诗学的出现。
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资产阶级文艺及其诗学才对古典诗学体系进行了批评和解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的《阴谋与爱情》、莱辛的市民剧、狄德罗的正剧等无不挑战着封建贵族的治安政治及其贵族文艺诗学,为新阶级的政治权利和新感知呐喊。随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化进程,摧毁了贵族等级及其审美感知体系,现代社会的个人平等、追求幸福和文艺审美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文学民主化和资产阶级文艺政治。巴尔扎克的拉斯蒂涅和吕西安、司汤达的于连、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都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人英雄,因为他们把原属于贵族的感知通过新文艺表达出来了,面粉商人、律师、诗人、娼妓、家庭主妇都拥有表达自己感知的平等权利。
(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朗西埃的文艺政治论不仅是他平等政治和解放政治思想在文艺领域的运用,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艺诗学的当代回响,并与毛泽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源于生活、文艺表现人民生活等文艺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
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朗西埃与毛泽东的文艺理论皆溯源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艺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占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里包括了社会主流文艺也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例如马克思对《巴黎的秘密》的批判就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文艺意识形态对于无产者的压抑。阿尔都塞也把文艺视为一种既是社会意识形态认同的机制,又是无产阶级打破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朗西埃或明或暗地继承了马克思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思想,实质上他把文艺也视为反对政治性压迫的工具,或者说文艺体制既体现了政治意识形态,同时又需要新的文艺革新这种文艺意识形态。
毛泽东则秉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多一些。列宁认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8]。这也被称为文艺的党性原则。毛泽东把文艺视为武装斗争之外的另一条文化战线,明确指出文艺是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文艺工作者应有阶级和政治立场。毛泽东认为文艺不能脱离阶级的政治影响而存在,统治阶级有其文艺,被统治阶级也有其文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6]69所以,毛泽东从阶级政治的解放目标出发,指出文艺为人民大众这一被压迫被剥削者服务,要达到人民大众的解放,就必须在文艺上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既然文艺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服务,革命文艺势必是为人民的政治解放服务。因此,“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6]70。在这里毛泽东强调,抗日战争时期,文艺应该反映中华民族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农民和兵士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压迫等主要内容,同时文艺也是阶级联合和统一战线的工具。最后,毛泽东强调文艺家应该有立场,即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上,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生活为表现对象进行文艺创作。
与朗西埃的文学政治论比较而言,毛泽东强调文艺为整个无产阶级解放政治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文艺具有解放政治的属性,文艺家应该具有政治立场和人民立场。换言之,这一人民文艺是政治性的文艺,也是表现政治内容的文艺,文艺家应该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其政治立场。在毛泽东看来,文艺与政治是一种直接的反映关系,文艺家与政治也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在朗西埃看来,政治与文艺是一种间接的配比关系,文艺家不直接介入政治,而是以文艺的对象、题材、内容、人物、形式等革命来“战略性”地支持解放政治的实现。但朗西埃在文艺为阶级政治解放、文艺反映政治内容等方面与毛泽东则有高度一致性。
(三)人民文艺与感性解放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从巴黎公社开始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逐渐成为政治的主体。毛泽东和朗西埃的文艺思想都在致力于:改变人民群众或无分者的历史地位,认为他们是具有主体性的,是阶级觉醒的能动主体。毛泽东认为,劳动人民最为神圣,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这就扭转了启蒙知识分子所指称的农民工人的无知麻木形象,从而让他们成为最革命的力量。毛泽东把人民大众视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文艺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应该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感受,人民大众是文艺的主角。“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6]278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思想深入人心,解放区到处在学习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
毛泽东指出:文艺大众化就是文艺家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强调文艺要表现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感受。“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感打成一片。”[7]52“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6]67革命的文艺家要求深入生活,深入到田间地头、战场和工地,与工农兵等一起工作和劳动,体会和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文艺的对象和内容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毛泽东认为文艺的形式和技巧也应该有所变革,文艺要推陈出新。不仅要改造旧文艺,还要创造新文艺,革命文艺要用革命的文艺形式来表现。丁玲、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艾青、公木的新诗歌,古元等木刻艺术,音乐《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新秧歌舞《兄妹开荒》等,无一不是体现着新的艺术形式表现着新人的新生活感受。
总的来说,朗西埃和毛泽东具有相似的政治学观点和文艺理论,两者都源自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解放政治,认为文艺与政治具有某种同构性的本质联系。更具体地说,两者都认为政治是对社会秩序的时空的分界和切割,原来受到压抑的无权无名者(人民大众)的身体感知和审美感受在新的政治空间中得到了重视和表现,新的政治空间和新的政治主体及其感性共享,使得艺术呈现了不同于以往形式的新革命。这一文学政治观不仅是朗西埃的理论核心,也是毛泽东人民文艺着重强调的关键。毛泽东指出“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个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6]81-82他认为虽然上海和延安在一个空间平面,但是政治和文艺而言,两地处于不同时空中,因而两地人民的政治权利和审美感知也是不同的,正是政治解放和人民的感受解放才会带来人民文艺的大繁荣。用朗西埃的话来说,文艺是使得无名者有表达自己的权利,使非存在者也在艺术中存在。他说:“艺术之所以是政治性的,恰恰是因为艺术相对于这些功能保持了一定间距,是因为它用某种方式架构了时间和空间的类型,以及它架构了时间及空间中的人民。”[9]2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观点,朗西埃在当代几乎用相似的语言重述了一遍,并成为他的文艺政治论的基础。
政治中的感性解放必然会带来文艺中的审美感知的解放和分享。柏拉图所认为的那些没有时间从事艺术的鞋匠和工人,他们此时有了时间用嘴说自己的话,用手写自己的故事,于是政治发生了,审美体制也发生了改变。“这种场域和身份的分配与再分配,这种空间与时间,可见与不可见,噪声与言说的划分和再划分,构成了我所谓的可感物的分配格局(le partage du sensible)。政治就在于对界定共同体之公共事务的可感物进行重新布局和分配,引入新主体和客体,让未被看到的东西变得可见,让那些被视为说废话的动物的那些人作为言说者被人们听到。这个工作涉及创造一种构成政治美学的歧见(dissensus)。”[9]25-26于是,文艺的主体从备受侮辱的阿Q变成了拿着枪反抗的小二黑和大春,在原治理政治秩序中被压抑的于连变成了法国大革命中的战士,就像《白毛女》所宣告的那样“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朗西埃和毛泽东都从政治解放中解放了作为无名者、无分者的人民大众的主体性,而文艺一旦从统治者的手中交还给人民大众,就必然焕发出新的活力。
结 语
总之,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文艺思想对法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阿尔都塞和朗西埃的文艺思想有一定的持续的影响。朗西埃的歧义政治或平等政治与毛泽东的解放政治有较大的一致性,即为了被压迫者反抗统治者的平等政治权利。同时,两者都把政治和文艺看作是对社会秩序及其时空的分割,在这种新空间中原来无名者、被压迫的人民大众要转化为政治主体,而文艺则要表现新主体的新审美感知。只不过,毛泽东是从三四十年代政治形势和文艺实践中总结了文艺与人民、与政治的关系,是从完成政治解放任务出发来透视文艺的作用。而朗西埃则是从文艺的政治性作用来促进文艺和审美体制的变革,从而揭示文艺与政治的同质同构性,以探索平等的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因此,尽管朗西埃与毛泽东在政治和审美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少差异,但就其相似点来看,朗西埃的左翼文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当代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