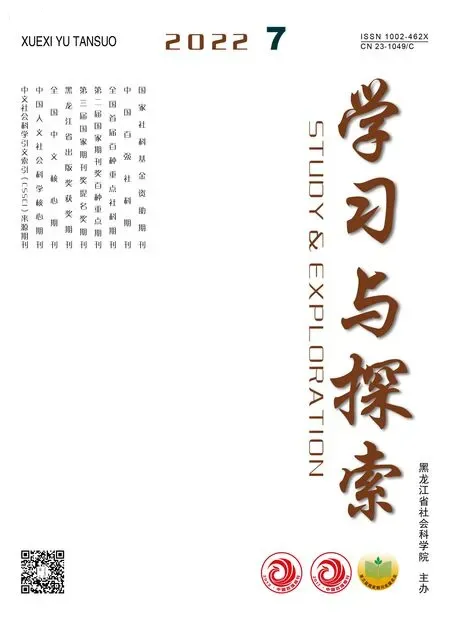陆、海疆地缘秩序与传统中国的疆域成型
李 磊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241)
关于传统中国国家形态的研究,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民族国家或帝国理论为出发点。(1)关于对“民族国家史观”的研究,参见王娟《重建“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叙事——20世纪中国民族史观的形成、演变与竞争》,《社会》2021年第1期;曹小文《全球史研究:对民族—国家话语的反思与构建》,《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关于“帝国史”的研究范式,参见刘文明《历史学“全球转向”影响下的“新帝国史”》,《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刘文明:《“新帝国史”:西方帝国史研究的新趋势》,《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9期。由于这些理论主要以欧洲的历史经验为事实基础,故而在用以解释中国时总有言不尽意乃至隔靴搔痒之感。为了消除现代学术话语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的抵牾,近年来国内学界提出的“封建—郡县”的解释模式,试图以中国既有的制度范畴来表述传统的国家形态。(2)参见张星久:《国家结构形式问题上的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表达——论中国帝制时代“封建论”的思想逻辑与发生背景》,《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5期;渠敬东:《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社会》2016年第2期;汪晖:《汉唐混合制度及其道德理想——回应苏力教授的中国宪制论》,《师大法学》2018年第2辑;周丹丹、李若晖:《寓封建于郡县:论费孝通“双轨政治”的历史真实》,《史学月刊》2021年第4期。也正是以此为起点,有学者提出了传统中国之普遍政治秩序的命题,即认为存在贯穿治内、治外的普遍原理及依此而建构出的恒定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在承认地方差序格局的基础上,以集体主义精神建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在地理上表现出空间的开放性,不拒绝治外政权及族群的加入;治外政权及族群可以随着与中央政权关系的变化而改变在五服体制中的位置,甚而被纳入郡县体制之下[1]。传统中国的这种规范性论述与近代西方的政治原理完全不同,近代西方采用的是双标与双轨,对内建构均质化的民族国家,对外推行帝国主义。传统中国的治内与治外遵循了同一原理。治内与治外的边界随着中央政权与相关政权及族群的关系变动而变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地缘战争只会改变治内与治外的边界,最严重的程度也只是更迭了王朝,而不会改变秩序模式。易言之,传统政治秩序的普遍性在于它在地理空间上能够容纳更多的政权与族群,在时间维度上能够容纳历史发展所带来的诸多变动。这些理论探索推动了有关中国国家理论的话语更新,打开了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论述空间。然而,对传统中国普遍政治秩序的探讨,还须从规范性表述延伸到事实性描述层面。政治秩序在认知领域中展现为整齐划一的形式,但实际形态却取决于各方的实际操作。本文尝试通过梳理中国的地缘政治传统,(3)姚大力先生认为:“中国边疆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民族性。基于中国边疆的极大一部分属于内陆亚洲的地理范围这一事实,中国边疆的民族属性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内亚性诸特征。”参见姚大力《中国边疆的基本特性》,《学术月刊》 2019年第2期。从现实主义层面丰富对传统中国之普遍政治秩序的理解。
一、西、北地缘关系的一分为三及其连环盛衰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初二,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文中凝练地概括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处之地缘政治的变化。
“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言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2]
在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来表述东南海疆危机之历史转折意义的同时,李鸿章则以“多在西北”概括历朝历代的备边方向,并认为西北是“中外界限”的显现场域。李鸿章所谓的西北当以嘉庆新修一统志为疆域范围[3],大致范围指蒙古高原及天山南北路[4]。尽管自汉代以来的中央政权多将这两个地区分而待之,但两者实际上同处游牧世界中,只是扮演着不同的经济角色。
蒙古高原、准噶尔盆地历来以游牧经济为主,天山山麓及塔里木盆地周缘存在着一定规模的灌溉农业。在张骞向汉武帝汇报的情报中,天山以北是乌孙人繁衍生息的场所,他们以游牧为生产、生活方式(《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分布着三十六国,后来发展为五十余国。它们为绿洲上的定居点,建设有城郭,从事农业与牧业(《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受制于资源禀赋,三十六国规模都不大,人口最多的龟兹也仅有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人(《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当匈奴强盛时,这些绿洲国家是游牧世界中农产品、手工业品、商品的重要补给基地。匈奴西边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众所周知,西域被纳入汉朝的地缘战略始于军事。在发动征伐匈奴的战争之前,汉武帝曾计划联络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返回长安,他出使十多年,打通了汉朝通往中亚的道路,获得了大量的西域资料。此行虽被司马迁称为“凿空”,但汉朝并未达到与大月氏军事联盟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西域并非汉朝唯一的地缘战略通道。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遣使自巴蜀四道并出,求取通往身毒的道路,尝试开辟经身毒到大夏。由于次年霍去病占领河西地区,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故“巴蜀—身毒—大夏”之道被放弃。
元狩年间西汉与匈奴的决战结束后,西域的通商价值立即凸显。这使西域在发挥其在游牧世界中的结构性功能的同时,也扮演着汉地农耕区与外部世界之交易中介的角色。这种角色的重叠不仅改变了西域的既存秩序,而且使之成为农耕区与游牧区之间的博弈议题。对于游牧区而言,失去西域等于失去了农产品、工商品的补给基地,也削弱了它对东西方之间贸易的影响力。正因有匈奴的军事威慑,楼兰、姑师敢于劫掠汉使、阻断道路,西域由此具有了地缘风险性,成为汉朝分配治理资源的重点地区。
汉朝第一阶段的战略是,在天山以南直接打击楼兰、姑师,故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以王恢破楼兰,赵破奴破姑师;在天山以北则通过和亲的方式使乌孙成为维护汉朝在西域、中亚统治的重要力量。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武帝派宗室女细君和亲乌孙。细君死后,解忧继任。第二阶段是借太初元年至三年(公元前104—前102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破大宛之威,在轮台、渠犁戍守数百人,设置使者校尉领护。第三阶段是汉宣帝时将南道纳入领护之下,并向北道发展。“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衆来降”(《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匈奴日逐王归汉,不仅使汉朝并护北道诸国,始置西域都护,而且迫使匈奴撤销在西域的统治机构,罢僮仆都尉。《汉书·西域传上》记述了西域治理权更迭对于匈奴与汉朝盛衰的影响:“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汉朝“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由此,汉的政治影响力深入中亚地区。
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攻杀匈奴郅支单于,斩其首,传诣京师,县蛮夷邸门。按《汉书》的记载,攻杀郅支单于的军队为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汉书》卷9《元帝纪》),也就是汉朝在西域的军事力量。郅支单于之死以象征性的方式展现了西域对于游牧世界的战略意义。《汉书·西域传上》也看到了“西域服从”与“单于称藩臣”两大事件之间的关联性,“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所谓“单于称藩臣”,是指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朝觐汉宣帝。汉宣帝在诏书中将呼韩邪单于的这一举动称作“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并命其“赞谒称臣而不名”(《汉书》卷78《萧望之传》)。尽管在两汉之际汉与匈关系仍有反复,但匈奴依附汉朝的趋势已成。(4)姚大力先生对匈奴的游牧型生计及社会文化,以及匈奴内部政治变动背后的社会势力因素作了新的阐释。参见姚大力《匈奴帝国与汉匈关系的演化——早期北亚史札记》,《中华文史论丛》2021年第2期。这是因为在丧失西域等农耕区后,匈奴只能日益依赖汉地的农产品、工商品以及各类技术,即便是与东汉相抗的北匈奴亦主动提出“合市”。在得到东汉朝廷诏许后,“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
正因自西汉开始,蒙古高原与西域在中原王朝的秩序构想中被分而治之,蒙古高原上的游牧社会形成了对汉地的路径依赖。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政权与汉地的中原王朝之间形成了正向对应关系,双方盛衰相伴。如匈奴与汉朝,柔然与北魏,突厥与魏齐周隋,吐蕃、回纥与唐朝,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鞑靼、瓦剌与明朝,均出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巴菲尔德用“Shadow”比喻这种关系,将中原王朝称为“Primary Empire”,而将游牧政权称为“Secondary Empire”[5]。获取河西地区、凿空西域,除了改变游牧世界的结构性关系并让游牧社会更加依赖汉地之外,还有一个对中国历史有着深远影响的结果,那就是青藏高原上诸族群也被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游牧世界中割离出来,与汉地农耕区直接关联。汉代羌人所处的地域以西海为中心,南抵达蜀汉以西,西北接西域。汉初之时,羌人处于匈奴的控制之下。汉武帝获取河西地区以后,隔离了羌与匈奴。羌人与匈奴相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围枹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后汉书》卷87《西羌传》)。宣帝时,羌人“度湟水,郡县不能禁”。羌人向湟水流域发展的目标是“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后汉书》卷87《西羌传》),这反映出农耕与游牧两种生活方式在湟水流域的竞争。冲突的结果是汉宣帝令赵充国与诸将将兵六万人击破平之。汉朝置金城属国统辖降附的羌人。
西汉以后,羌人开始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东汉统治危机的爆发,重要原因便是持续六七十年的羌乱[6]。西晋关中地区人口总数的一半是内徙的羌人与氐人。十六国诸政权的统治民族虽有不同,但自屠各汉国以来皆以包括氐羌在内的“六夷”为主要依靠对象。
当羌人内徙时,慕容鲜卑的一支在西晋时期自东北迁徙至青海,融合当地氐人和羌人,建立了吐谷浑政权。隋朝建立时,吐谷浑在始称可汗统治下达到极盛,占领鄯善、且末,控制西域通往中原的南部通道。如前所述,对蒙古高原、西域及青藏高原分而治之是汉代以来地缘风险的防范战略,吐谷浑向西域的发展正与之相冲突,故而引发与隋唐两代的战争。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出兵大败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南走,投降隋朝者达十余万口,“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隋书》卷83《西域·吐谷浑传》)。隋朝由此控制住通往西域的道路。
唐朝灭东突厥后,西域诸国纷纷遣使入朝,西域之路重开。为了解除吐谷浑的威胁,唐太宗于贞观九年(635年)命李靖为主将,节制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李道彦、高甑生等五部,攻击吐谷浑,吐谷浑伏允可汗战败后被部下所杀,其子慕容顺被唐朝册封为西平郡王。唐朝由此控制了吐谷浑旧境,以及青海高原及川西一带。随后,吐蕃接替吐谷浑继续向西域、河陇地区发展。松赞干布时,文成公主入藏奠定了唐朝与吐蕃间的甥舅关系。松赞干布死后,吐蕃贵族以战争、渗透等各种方式,试图将控制区域扩展至吐谷浑、西域,一度控制安西四镇二十余年。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阿史那忠节率众以讨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而还。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吐蕃又“请去安西四镇兵,仍索分十姓之地”(《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安史之乱中,吐蕃乘机夺占河湟、陇右,代宗时一度攻入长安。总体说来,唐朝对吐蕃的风险防控兼具战和,并存在着协商机制。除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的和亲外,还有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的金城公主入藏。围绕着河西九曲的控制权,双方在中宗、玄宗时期均进行过商议[7]。即便在安史之乱后,唐蕃仍在德宗建中四年(783年)以会盟的形式确定疆场[8]。穆宗长庆年间,唐蕃更是通过会盟的形式终结了唐朝联合回鹘、南诏抗衡吐蕃的格局[9]。
与蒙古高原族群的关系历来为中原王朝的首要政治议题,但自西汉将羌人纳入汉王朝体制之后,治理青藏高原也成为中原王朝的重要问题。唐朝最主要的地缘风险由蒙古高原转向了青藏高原,便是这一历史运动发展的结果。
二、东北的体制化与地缘关系中“中心—边缘”的角色倒置
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仅言历代备边多在西、北,而不言东北,这是因为清朝以东北为发祥地,李鸿章奏折不能无视本朝的政治正确。实际上,自唐朝覆灭后的千年里,影响中国历史甚巨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或起源于东北,或崛起于东北。如果说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是较为典型的游牧政权,统治区与中原的关系是游牧区依存于农耕区的关系,那么辽、金、元则建立起王朝体制,统治地区囊括游牧、渔猎与农耕区。可以说,采用中原王朝的政治体制并建立起适合游牧区与农耕区的治理架构,成为北方民族政权崛起并转化为正统王朝的关键。明朝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东北平原上的治理取得此前中原王朝不曾有过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朝继承了元朝的治理体系。同样,后金的崛起与胜利,也是明朝自身治理体系演化的结果,它是在继承了明朝的治理结构与统治形态之后才成长起来的。
与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相比,东北平原经济结构中除了游牧业,还有渔猎、农耕经济,但是受限于生产力水平,东北平原更加依赖内地。所以明朝前期在东北的统治稳固、明朝后期后金以明朝为生死敌人,这些恩恩怨怨都是两者关系密不可分的表现形式。今日的东北三省在明朝政治体系下并非一个整体。辽宁省以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被称为辽东,辽东是东北平原、蒙古高原、华北平原的交汇点,是重要的交通要地,也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当地百姓除了汉族外,还包括蒙古、女真、高丽等族群。终明之世,辽东地区都是明朝直接管辖的地区,也是明朝东北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区。明朝将辽东各族民众均纳入军户体制,编为二十五卫,军户平时劳作,战时作战[10]。
辽东以外主要是蒙古、女真诸部的居住地,北达外兴安岭、东到库页岛、东南抵图们江、鸭绿江等地。由于这一广大地区与内地社会发展水平相差太大,所以明朝因俗而治,设置羁縻卫所。“羁縻卫所,洪武、永乐间边外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明史》卷90《兵志二》)奴儿干都司由朝廷派遣流官任职,官员定期出巡以安缉部民。《永宁寺碑记》《重建永宁寺记》记述了永乐九年至宣德八年(1411—1433年)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巨船巡查之事。永乐九年的规模是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宣德七年则是官军一千、巨船五十。(5)碑文释文参见钟民岩《历史的见证——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文考释》,《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除了政治层面的治理之外,明朝还试图将地方文化纳入官方轨道中以增强国家认同。《永宁寺碑记》的碑侧便有用汉、女真、蒙古、藏等四种文字镌刻的六字真言[11]。
尽管奴儿干都司诸卫多为羁縻卫所,但明朝在东北平原的治理并非完全被动顺应部族格局,它仍有将东北体制化的宏大构想。这一体制化是接续元朝而来,除了将若干元朝治理单位转化为卫所外,还继承了元朝驿站体系,形成以辽东都司为中心的主要交通路线。除了通向京师的海、陆三路外,还有“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通往建州左卫及朝鲜)、“纳丹府东北陆路”(通往毛怜卫)、“开原西陆路”(通往义州)、“开原北陆路”(其中“海西西陆路”通往兀良哈三卫,“海西东水陆城站”通往奴儿干都司)[12]。明朝由此构建了治理东北的地缘体系。
在社会治理方面,明朝在制定朝贡、互市制度时,对东北诸部优惠最多。自明成祖永乐年间至明神宗万历年间,东北马市一直在进行。隆庆、万历年间,不仅不断增设马市,而且开市时间突破制度规定,如开原马市是天天开市。与对鞑靼马市有着诸多限制不同,女真诸部基本可以在马市上换取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13]。故而在明朝治理东北的200年间,尤其是明中叶以后,东北女真诸部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关系日趋密切。汉人、朝鲜人源源不断流入,为东北的农业开发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明神宗万历年间,东北的耕地面积显著扩大、单产数量显著提高。尽管有学者认为《建州纪程图记》中有关女真地区粮食产量记载的数据偏高,但也承认其农业取得的进步[14]。
在东北经济与内地日益密切,女真社会发展依赖马市贸易的同时,明朝在东北的治理体系却遇到重大挑战。瓦剌崛起后,蒙古高原势力向东发展,明朝的东北卫所体系遭到很大破坏[15]。明宪宗成化年间,建州右卫都督董山之乱的发生进一步动摇了明朝卫所体系的部族根基。明朝卫所体系的瓦解导致了治理供给不足。从明世宗嘉靖年间到明穆宗隆庆年间,卫所体系下的女真各部围绕着维系经济命脉的交通要道而展开激烈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海西四部、建州五部、长白山三部的格局[16]。明朝只能以经贸关系为交际资本来重塑地缘格局,其政策是扶持开原边外的海西哈达部,隔绝鞑靼与建州。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哈达部首领王台去世,哈达部发生内战,海西叶赫部、建州阿台部势力卷入。明朝为了延续以哈达制服诸部的政策,出兵干预[17]。正因明朝治理东北的模式由建构卫所体系转向扶植盟友,努尔哈赤的势力才得以崛起。尽管努尔哈赤的祖父与父亲为明军所误杀,且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将之列入对明朝的“七大恨”之中,但事实上努尔哈赤的崛起得益于明朝的扶植。努尔哈赤起兵后的忠顺姿态让明朝视之为下一个王台。明朝将王台的“龙虎将军”号除授给努尔哈赤,意图倚仗其稳定抚顺以南的地缘局势。
努尔哈赤称汗后,后金立国的关键在于经略辽东都司。辽东都司为明朝东北治理体系的核心区,明朝在此经营已达200多年,为了巩固对辽河以东地区的占领,努尔哈赤于天启五年(1625年)迁都沈阳。占领了辽河以东的土地后,后金已经由一个女真人政权转而成为包括蒙古、朝鲜、汉族在内的多民族政治体。皇太极恢复汉人的自由民身份,编为汉军八旗;又启用汉人士大夫进入官僚集团,并以中原王朝为样本,构建官僚君主制。这些措施重构了东北的政治体系,如果从长时段来看,后金的政治体系其实是明朝辽东都司及东北诸卫治理体系的继承。
后金是在明朝的地缘秩序中借助体制性因素成长出的地方势力。随着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九年(1636年)的两征朝鲜,后金与朝鲜结成君臣关系;崇祯五年(1632年)、七年(1634年)的两败察哈尔林丹汗及收复漠南蒙古十六部,后金转化为兼有蒙古高原东部游牧社会、东北平原农牧社会、辽东及朝鲜半岛农耕社会的王朝形态。尽管明朝试图以体制化的方式治理东北,但王朝的治理体制不仅孕育出边疆地方势力,而且为其提供了连结游牧与农耕两个区域的治理框架,使其成长为兼具游牧文明的战斗力与农耕文明的组织领导力的新王朝,完成了由地缘政治中的边缘向中心的转换过程。
三、东南海疆的地缘风险与危机管控
在《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将清朝所面临的东南海疆危机视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一表述是以陆权国家为基本立场的。事实上,明朝曾积极建构海疆的地缘秩序。在西欧势力海上东来的半个世纪以前,即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1405—1433年),明朝曾有过七下西洋的壮举。郑和率领明朝水军不仅与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联系,而且开拓航路并主导了海疆地缘秩序[18]。西欧殖民者的东来正是沿着郑和下西洋的航线,逆向从西洋往东洋扩张。
明武宗正德年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印度果阿后,又占领满剌加(马六甲)。满剌加是海上丝绸之路上联系西洋与东洋的交通枢纽,葡萄牙人占据该地,不仅使往来东、西洋的华商因此饱受劫掠之害,而且在战略上开始迫近中国东南海疆[19]。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舰船闯入广东珠江,虽以通使为名,但随即占据东莞屯门,杀掠居民,掠卖人口,筑室立寨。继任的明世宗在处置葡萄牙侵占满剌加、东莞屯门的问题上态度积极,在道义上谴责了葡萄牙[20],但由于明朝已经放弃了成建制地大规模航海活动,国家力量退缩到近海及大陆上,丧失了郑和下西洋所构建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治理权,缺乏切实军事、政治措施的谴责只能是流于形式,无助于改变葡萄牙占领满剌加的事实[21]。
不仅如此,对这一事件的处理还严重影响了明世宗此后的海洋政策。在他统治的45年里,明朝严格审核勘合贸易资格,资格不符者、非期而至者均不与贸易。这一政策的初衷本是强化明朝朝廷对海外贸易的管理,但结果却是进一步收紧了贸易渠道,间接造成了走私贸易的兴盛。嘉靖三年(1524年),葡萄牙人盘踞宁波甬江口外的双屿岛从事走私贸易;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葡萄牙人又以福建的浯屿港、月港为走私据点[22];而且倭寇之中,亦包括葡萄牙人。
此后葡萄牙人问题的解决,以及对西班牙、荷兰、英国人侵扰的应对,均不是基于明朝对于海疆危机的通盘战略规划,(6)关于明朝海疆秩序的变化,参见刘祥学《“四夷来朝”与明初百年对外关系的变局》,《历史研究》2020年第6期。而是地方政治运作的结果。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通过行贿的方式最终获许留居澳门。明神宗万历年间,葡萄牙派往海道副使处交纳贿金时,因有其他官员在场,海道副使宣称葡萄牙人的每年贿赂钱五百两白银是地租银,交纳国库[23]。地租的确立是对葡萄牙人在澳门租赁居住的性质认定。
对于西班牙、荷兰、英国人的侵扰,明朝则以军事防御给予回应。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西班牙人在虎跳门结屋群居,海道副使章邦翰饬兵严谕,焚其聚落,驱逐了西班牙殖民者。(7)关于西班牙在万历年间与明朝的交涉,参见Carmen Y. Hsu, “Writing on Behalf of a Christian Empire: Gifts, Dissimul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Letters of Philip II of Spain to Wanli of China”,Hispanic Review,Vol.78,No.3,2010, pp. 323-344;李庆:《明万历初年中国与西属菲律宾首次交往考述》,《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荷兰军舰占据澎湖,同时行贿明朝税监,请求互市。明朝福建巡抚徐学聚上疏力陈荷兰人之企图,福建总兵施德政派遣都司沈有容谴责荷兰人对澎湖的非法占领,并严管沿海民众不供给荷兰人补给,迫使荷兰人离开澎湖。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人再占澎湖,福建巡抚南居益率兵于天启四年(1624年)占领澎湖,迫使荷兰人拆除城堡撤离。崇祯六年(1633年),荷兰再犯南澳,焚毁明军水军战船、打死明军兵士后,福建巡抚邹维琏以郑芝龙为先锋,与荷兰激战于科罗湾。明军斩敌二十余,擒一百一十八名,焚甲板巨舰五只,夺一只,击破小舟五十余只[24]。崇祯九年(1636年),英国舰队闯入广州虎门炮台与明朝守军交战后,两广总督张镜心派遣海防同知到澳门督促葡萄牙人驱逐英国势力[25]。明朝的这些军事行动虽然都取得胜利,但是从战略上看,只是对东南海疆危机的被动防御,而非积极管控。
崇祯九年英国与明朝的战事表明,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200年,英国便遵循同一条海上路线东来,并在同一地点展开对中国的袭击。可以说,鸦片战争并不是突然爆发,而是在200年前就已经有多次预演。从长时段来看,这是明朝放弃对海疆地缘秩序主导权的恶果。面对西欧殖民者闯入中国东南地域杀人夺地的行径,明朝大都通过军事手段予以惩戒,但这是基于明朝国力的相对强盛。待到鸦片战争前后,西强中弱之势已成,西欧殖民势力不仅控制了海道,而且深入把控了海疆与陆疆之间的地缘结构。
在攻击中国之前,英国在与缅甸的战争中,就积累了与规模庞大、组织健全之亚洲国家交战的经验。在第一次英缅战争中,英国起初从陆地侵入阿拉干[26],由于在陆战中难以取胜,转而改道海上直取仰光,迫使缅甸签署《扬达波条约》[27]。英军在鸦片战争中凭借机动优势游击中国东南海疆,溯流入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切断北京朝廷的生命线之大运河,正是基于从海道威逼仰光的战争经验。《南京条约》中割地、赔款的内容也与《扬达波条约》相似。可以说,基于对亚洲国家海疆与陆疆间地缘结构的掌控,英国形成了一套侵略亚洲国家的程式。李鸿章所言“千年未有之变局”正是中国地缘环境恶化、风险失控的结果。
四、结论
传统中国的疆域成型于清嘉庆年间,这一疆域是历代建立并完善地缘秩序的结果。秦朝一统六国后,建构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结构性关系成为中国政治的首要议题。无论中原王朝,还是游牧政权均有自己的政治构想。
对于中原王朝而言,大一统须建立在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统一性之上。无论是施行律令如一的郡县制,还是兼采因俗而治的五服制与封爵制,抑或如清朝另建理藩院管辖藩部,其核心要义均是建构“一”与“多”的关系,即王朝与各地之间均是以一对一的方式建立政治联结,而非面对多个地方的政治集合体。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汉朝凿空西域的地缘意义在于将匈奴影响下的蒙古高原、西域与青藏高原诸多势力分别对待,既让匈奴失去了天山南路绿洲农耕区,从而不得不更加依赖内地农耕区,又让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在地缘秩序中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实现中央政权对两区域的分别治理。
对于游牧政权而言,他们习惯于直接占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过渡地带,即胡焕庸线两侧的宜农宜牧区,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政治途径迫使农耕政权岁贡、开榷场。在其所主导的地缘秩序中,农耕区是服务于游牧社会的。匈奴对天山南路绿洲农业地带的控制与赋税征收,契丹对燕云十六州的占据与对北宋的岁贡所取,选择地域不同、对象有异,但行事逻辑是一样的。而当其社会内部农业地区的权重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其政权将向中原的王朝体制转化,从而具备了入主中原的资质。金朝与后金的政权建构均遵循了这一发展轨迹,区别在于金朝在崛起后迅速占领华北,完成了王朝化过程,但留下了农耕、游牧、渔猎的区域整合难题,地缘矛盾、经济矛盾、社会矛盾以治内族群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后金之兴,实为渤海、辽、金、元、明历代将东北体制化的历史结果。后金既受到明朝东北治理体系之羽翼而成长,又得以借鉴其联结游牧区与农耕区的治理框架,从而在入主中原之前已经初步完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造。可见,游牧政权的政治逻辑与中原王朝并非截然对立,当其社会内部游牧、农耕权重比例发生逆转时,政权性质的王朝化几乎是必由之路。
东南海疆的地缘秩序是近500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命脉所在。无论是以中原为中心建构地缘秩序的明朝,还是身处北方民族政治脉络兼续中原王朝法统的清朝,都面临东南的地缘风险。在西欧人东来之时,晚明与清朝试图以严守官方贸易的方式来管控海疆,然而这一缺乏对海疆地缘关系进行整体构想的方案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仅东亚海域的倭患一度甚嚣尘上,而且西欧诸国纷纷将其全球殖民体系扩张至中国周边。可以说,鸦片战争之前的200年,中国便因海疆地缘秩序主导权的丧失而被迫陷入对西欧殖民者的反侵略斗争之中。而西欧殖民者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海疆与陆疆之间的地缘结构,鸦片战争的行军路线与政治策略更是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近现代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传统中国尤其是晚明与清朝海疆地缘构想的先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