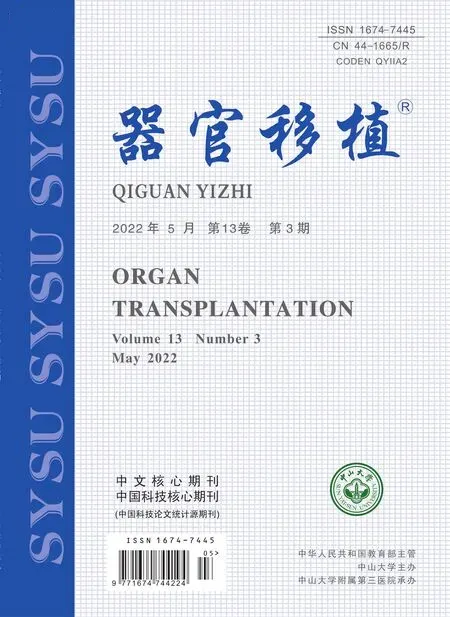儿童肺移植临床研究进展
李慧星 毛文君
肺移植作为治疗儿童终末期肺病的有效手段,可取得与成人受者相似的预后,可以有效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活质量。据国际心肺移植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eart and Lung Transplantation,ISHLT)统计,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国际上仅开展2514例儿童肺移植,数量远远不及成人肺移植[1]。近年来随着肺移植技术的成熟及经验积累,我国已有多家肺移植中心逐步开展儿童肺移植,但总例数相对较少,发展较成人肺移植相对缓慢。
1 儿童肺移植的原发病类型
一般认为受者年龄<17岁的肺移植均可定义为儿童肺移植,儿童肺移植受者多为大龄患儿,但国内外肺移植相对成熟的中心正逐渐突破受者的年龄限制,北美地区开展了数例婴儿肺移植[1]。国外儿童肺移植手术原发病类型,按发病率依次为囊性纤维化肺病、特发性肺动脉高压、间质性肺病、闭塞性细支气管炎、α-抗蛋白酶缺乏症、艾森曼格综合征等。国际上,年龄>5岁受者原发病主要以囊性纤维化肺病为主,1~5岁受者原发病多为特发性肺动脉高压,婴幼儿肺移植原发病主要为特发性肺动脉高压及肺表面活性物质缺乏[2]。而在国内,囊性纤维化肺病的发病率有所下降,儿童肺移植原发病类型与欧美人群存在差异,按发病率依次为特发性肺动脉高压、闭塞性细支气管炎、间质性肺病等[3]。
囊性肺纤维化是因编码囊性肺纤维化跨膜电导调节因子蛋白的基因突变导致气道干燥、黏液稠厚、纤毛清除能力变差,进而出现慢性呼吸衰竭,预后差。囊性肺纤维化患者会出现反复肺部感染,病情进行性加重,需尽早行肺移植评估[4]。儿童特发性肺动脉高压病情进展迅速,诊断到死亡的自然病程通常在3年内[5],儿童肺动脉高压患者出现右心压力升高或咯血时,提示有猝死风险,应尽早列入肺移植等待名单。儿童间质性肺病是以呼吸窘迫和低氧血症为主要症状的疾病,胸部影像学提示弥漫性肺间质病变,常因肺表面活性物质缺乏引起。新生儿伴有肺表面活性物质缺乏,病情往往进展更快、更凶险,是一种致死性疾病,肺移植是唯一的治疗手段[6]。需肺移植治疗的其他儿童间质性肺病包括肺泡毛细血管发育异常合并肺静脉移位、新生儿慢性肺病等[7]。闭塞性细支气管炎是指细支气管炎症导致的阻塞性肺病,儿童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病因复杂,常与严重的病毒感染或支原体感染有关[8],或继发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吸入性损伤、Stevens-Johnson综合征、骨髓移植术后等[9],儿童闭塞性细支气管炎常进展为呼吸衰竭,也需尽早肺移植治疗。
2 儿童供肺的利用及分配
自器官移植开展以来,各移植中心一直致力于提高供者器官利用率,主要从供者维护、灌注系统改进、分配策略优化等方面着手。目前国内供肺均来源于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由于儿童捐献难度大、占比低,导致儿童供肺短缺,且各年龄段儿童胸腔体积差异大,儿童受者获得匹配供肺的条件更为苛刻。利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来扩大供者池有积极意义,根据新生儿科或儿科重症监护室死亡病例,分别有8%~36%或9%~20%为潜在DCD供者,因此需要更好的社会宣传、政府引导、医院扶持等有效措施增加对供者的利用。
离体肺灌注(ex vivolung perfusion,EVLP)技术可在离体状态下精确评估肺功能状态并提供修复功能,扩大供肺利用,使部分边缘供肺经修复、评估后安全应用于临床[10-11]。但受制于高昂的运行成本,EVLP系统未在国内普及应用,国内个别移植中心已尝试应用国产化EVLP系统,以满足更多的供肺灌注需求[12]。
目前国际供肺分配都基于肺源分配评分(lung allocation score,LAS)系统进行分配,根据肺移植等待列表中受者的预期寿命和肺移植术后1年的预期生存率计算分值,以此决定器官分配优先权。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已借鉴国际LAS系统,建立了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hina Organ Transplant Response System,COTRS),并增加儿童优先原则[13]。
3 儿童肺移植外科手术技术的选择
由于匹配供肺稀缺,有专家提出了肺减容或肺叶移植的方法,儿童肺移植使用肺减容并不会增加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14]。而紧急情况下,活体肺叶移植亦是一种选择,适用于年幼或肺腔容积小的儿童,供肺一般分别来自两名亲属捐献者的左、右下肺,优势在于手术规划有序、供肺质量高,可降低术后排斥反应及感染发生率。近年来肺叶移植在日本发展迅速,1998年至2019年,日本进行了234例活体肺叶移植,其中15岁以下儿童肺移植占24%,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活体肺叶移植术后5、10年生存率(79.0%、64.6%)优于常规尸体肺移植(65.7%、60.3%)[15]。但考虑到对活体供者造成的固有风险,活体肺叶捐献仍仅是紧急状态下的慎重选择。
由于儿童肺移植受者胸腔小,器官匹配度差,支气管和血管吻合对于外科医师极具挑战。为保证良好的手术视野、术中辅助应用体外循环或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等,目前手术切口常选择横断胸骨Clam-shell切口、胸骨正中切口。肺移植具体术式选择由患儿原发病、供肺匹配率、心肺衰竭程度等因素决定,随着肺移植外科技术的成熟,吻合技术问题均可得到妥善解决,允许采用双肺移植术[16],为患儿争取更好的长期生存率及术后肺功能状态[17],如合并心肺功能不全、先天性心脏病、艾森曼格综合征等情况则需行ECMO或体外循环辅助完成心肺联合移植。ECMO能够提供术前过渡桥接、术中心肺功能支持[18-19],降低术后原发性移植物失功等并发症发生率,在肺移植中逐步替代体外循环[20]。但肺移植中应用ECMO应做好随时切换转流模式的准备,切换循环转流模式的常见原因包括出血和更高的氧合循环支持需求[21],合并先天性心脏病需同期手术的患儿,则可直接应用体外循环作为术中循环支持,对于肺动脉高压合并房间隔缺损的患儿,右心室的舒张末高压在肺移植术后仍会持续一段时间,不关闭房间隔缺损有利于术后恢复,在肺移植同期不需行房间隔缺损修补术。
4 儿童肺移植术后并发症的处理
儿童肺移植术后受者早期死亡原因常为重症感染、原发性移植物失功、手术相关并发症和多器官衰竭等。感染是儿童肺移植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发生率为69%~90%[22]。由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感染的控制尤为困难[23],儿童肺移植术后极易合并巨细胞病毒及真菌感染,因此术后1年大约有50%的死亡与感染相关[24]。感染的预防及治疗可借鉴成人肺移植术后感染管控模式,但对于儿童肺移植术后巨细胞病毒感染的管理,目前全球肺移植中心并没有统一的策略,国际指南中也没有专门针对儿童的诊疗规范[25]。
慢性移植肺功能障碍(chronic lung allograft dysfunction,CLAD)是制约肺移植术后长期生存的最主要并发症。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综合征(bronchiolitis obliterans syndrome,BOS)是CLAD最常见的形式,儿童肺移植术后5年内大约37%的存活儿童会合并BOS[26]。在传统的序贯式双肺移植术中,气道血液循环依赖肺动脉的静脉血逆行灌注,气道缺氧被认为是BOS发生的重要原因[27]。因此支气管动脉重建技术应运而生,与传统肺移植技术相比,应用支气管动脉重建技术的儿童患者,术后气道缺血的发生率明显下降,但BOS的发生率并没有明显下降[28]。迄今尚无有效的方法治疗肺移植术后CLAD,可尝试的治疗方法包括调整三联免疫抑制(环孢素或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糖皮质激素)方案、应用大环内酯类药物、全淋巴照射以及体外光分离置换法[29]。终末期移植肺衰竭最终的治疗方法是再次肺移植,然而儿童再次肺移植的资料非常有限[30]。美国圣路易斯儿童医院肺移植中心提供了再次肺移植的经验,136例儿童肺移植受者中,14例进行了再次肺移植,术后2年的生存率为58%,明显低于初次肺移植[31]。
5 儿童肺移植的预后
据ISHLT统计,儿童肺移植术后受者中位生存期为5.4年,其中术后生存时间超过1年的患儿,中位生存期延长至8.9年。肺移植术后早期的“疾病挫败感”心理状态使患儿依从性变差,增加排斥反应发生的风险,15~19岁年龄段受者相比低龄儿童受者有着更高的病死率[26],极可能与该年龄段受者心理变化导致依从性下降有关。而便捷的筛查工具可及时发现患儿免疫抑制剂血药浓度低下的情况,如发现确有依从性下降行为,医师及家属可及时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帮助患儿克服心理障碍。虽然儿童肺移植开展较少,但随着移植中心经验的积累及围手术期管理技术的提高,儿童肺移植受者的术后生存率较过去又有质的飞跃,并且儿童肺移植受者术后长期生存率与成人相比可能更具优势[32]。欧洲的肺移植中心在儿童肺移植领域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患儿术后1、3、12个月的生存率分别为96.6%、93.1%和82.8%,中位生存期59个月[30]。无锡市人民医院2007年12月至2020年8月实施12例儿童肺移植,患儿术后均康复出院,仅1例患儿因气道狭窄合并感染于术后半年死亡,其余均存活至投稿日[33]。
6 小 结
随着肺移植技术的发展成熟,儿童肺移植的开展逐渐增多。儿童肺移植的适应证主要为特发性肺动脉高压、间质性肺病、囊性肺纤维化等,EVLP、肺叶移植、体外生命支持等先进技术在儿童肺移植中逐步推广应用,借鉴成人肺移植的处理经验,儿童肺移植的手术技术、围手术期处理、术后管理日臻完善,总体生存率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我国儿童肺移植开展数量少,尚无符合我国国情的儿童肺移植指南出台,也缺乏某些关键技术如国产化ECMO、EVLP临床应用等。我国的儿童肺移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较少,需要各方努力,推动我国儿童肺移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