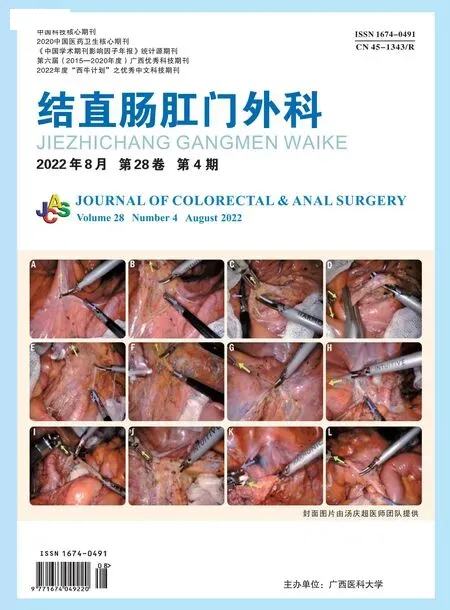痔病与梗阻性排粪障碍综合征共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李青,钱海华,苏丹,任东林
1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 江苏南京 210029
2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肛肠外科 河北邢台 054000
3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肛肠外科 广东广州 510655
痔病(hemorrhoidal disease,HD)是最常见的肛肠良性疾病[1],涉及各年龄层和不同性别的成年人群[2]。在美国,HD在成年人群的患病率为50%[3],我国成年人群HD的发病率也高达50.28%[4]。HD通常被认为与功能性胃肠病(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FGID)相关,尤其是便秘和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5-6]。罗马Ⅳ标准通过症状组合来定义功能性便秘(functional constipation,FC)和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constipation,IBS-C),然而上述二者之间存在重叠[7-8]。此外,盆底功能协同失调或排空障碍可见于IBS[9-10],亦常见于FC[11-12],包括慢传输型和正常传输型的便秘[11]。新近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HD患者普遍存在排粪不协调、排空障碍症状[13]。笔者团队开展的一项临床病例研究也验证了梗阻性排粪障碍综合征(obstructed defecation syndrome,ODS)与HD术后复发之间存在相关性[14]。ODS包括多个由于盆底功能异常(耻骨直肠肌痉挛、协同失调等),解剖改变(直肠前突、直肠脱垂、盆腔器官脱垂等)和心理因素等引起的排粪异常症状,具体表现为排粪时间过长或排粪次数增多,排粪困难,过度用力,不完全排空或便后不尽感,肛门坠胀或疼痛,需要用手指、泻药或灌肠帮助排粪等,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15]。ODS评分是临床评估和量化患者排粪障碍严重程度的重要工具[16],尤其是合并FC、IBS和精神疾病史的排粪障碍患者[17]。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关于HD的发病机制的认识多基于非遗传因素方面的研究,而有关遗传因素方面的认识尚不充分。最近发表在GUT上的关于HD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的荟萃分析首次揭示了HD是一种部分遗传性疾病,发现HD和其他疾病存在共同遗传成分及病理生理学证据,从而证明了遗传因素可能在HD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作用,并暗示了HD与排粪障碍相关疾病之间的共病可能[18]。本文旨在归纳HD和ODS的病理生理学变化及流行病学等非遗传因素方面的相关研究进展,同时基于最近的遗传因素的新发现进一步阐述二者潜在的共病机制。
1 HD与ODS共病机制的非遗传因素
1.1 HD与ODS相互影响
HD通常被认为与便秘相关[19-20],有研究结果显示便秘患者的HD患病率高于健康人群[21],而且更容易合并排粪不协调等排粪障碍的症状和球囊排出试验结果的异常[22],另一项纳入1 074名HD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排粪用力与HD患病率增加有关[23]。排粪困难和排粪用力往往出现在HD的症状之前[13],因此,改善排粪障碍已经成为HD基础治疗的一部分[24]。此外,HD患者中合并便秘的比例也较高[25]。新近的一项有关HD与FC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在HD患者中FC患病率较高,出现排粪不协调和肛门基础压力升高更为普遍[13]。
HD复发率较高的原因通常被归因于手术技术[26-27],尽管手术技术不断进步,但术后复发率仍然较高[28]。Ruan等[29]对1998至2019年间发表的关于吻合器痔固定术(stapled haemorrhoidopexy,SH)与开放痔切除术(open haemorrhoidectomy,OH)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系统评价的结果显示SH和OH的复发风险相近。随后,Naldini等[30]基于5篇关于SH和OH系统评价的高质量文献研究结果认为,两种手术方式有着相似的复发率。结合前述研究结果,笔者团队认为HD复发率较高还可能与患者术后伴随的ODS有关,于是开展了一项纳入1 162名HD术后患者的回顾性临床研究,其结果显示ODS评分是HD术后复发的独立预测因子,且ODS评分每增加1分,HD复发的风险就会增加1.38倍[14]。
1.2 HD与ODS的流行病学
1.2.1 年龄 韩国一项样本量为194 620的横断面研究显示HD的患病率为16.6%,其中老年人患病率较高[31]。另一项纳入了218 920名HD患者和725 213名健康人群的GWAS研究数据显示,年龄越大,HD发生率越高[18]。便秘患病率同样与老龄化存在显著的相关性[32],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体内胶原蛋白、结缔组织、肌肉组织的比例下降,加之直肠感觉减退[33],随着排粪冲动的意识减弱进一步引起粪便滞留和水分重吸收,最终导致ODS[34]。
1.2.2 性别HD相关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女性的患病率更高[18,31],女性的生育次数与HD分度和复发有显著的相关性[35]。ODS患者也是以女性居多,这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首先,女性更短的功能性肛管长度决定了其直肠对机械扩张的感觉阈值低于男性,对便意刺激更敏感[36];其次,女性较高排粪障碍发生率可能与性激素的周期性波动有关[37];再次,经阴道分娩是会阴下降的危险因素[38]。
1.2.3 BMI和运动习惯 以往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BMI值每增加1,HD的患病风险增加3.5%[39]。最近一项纳入403名研究对象的横断面研究结果提示超重会增加HD的患病率[25],特别是腹部型肥胖与HD相关性更为显著,这可能与肥胖引起的腹内压升高、痔静脉丛充血有关[19]。肥胖引起的盆底高张力和机械效应同样与ODS密切相关,随着BMI值的增加,直肠感觉阈值升高,对便意刺激的敏感性降低,球囊排出试验时间延长,直肠排空不完全[36]。
运动习惯与HD亦存在关联性。笔者团队的研究显示,相比几乎不运动的HD患者,术后偶尔参加体育运动的患者的复发风险为0.445,而经常运动的患者的复发风险为0.337,这表明体育运动对HD的复发具有保护作用[14]。一项关于运动与ODS的研究证明,运动明显减少或长期卧床休息可能导致便秘及排粪障碍相关问题[32]。
1.2.4 膳食纤维摄入量 有研究发现膳食纤维摄入量增加与HD患病风险降低有关[23],低膳食纤维饮食则可能导致HD发生[20]。有研究报道排粪障碍也可以通过增加膳食纤维素的摄入量改善[19],这可能与纤维素可与肠道益生菌协同作用,从而降低粪便pH值来调节粪便性状有关[40],继而降低排粪时直肠肛门所需的压力梯度,有利于粪便排空,改善ODS[41]。
1.2.5 排粪姿势 新近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HD患者由坐位改为蹲位排粪,HD的症状得到明显减轻或缓解[42],原理为从肛门直肠生物力学角度,下蹲姿势可以增加髋关节屈曲和骨盆后倾的角度,有利于增大肛门直肠角,因此下蹲姿势更有助于粪便的排空[43]。
1.2.6 心理因素 抑郁被认为是HD的危险因素之一,HD的相关症状同样会对患者的心理和情绪造成影响[44]。心理因素与ODS亦可能存在相互影响。新近一项大脑功能核磁共振成像的研究结果显示:与健康人群相比,合并FC的成年人排粪时大脑功能区出现不同的基线活动模式和信号[45]。此外,还有研究显示心理和情绪也可以通过传出通路影响结肠和直肠功能[34]。
1.3 HD与ODS的病理生理
排粪行为依赖于神经、肌肉、内分泌系统和认知系统的协调,并且从生理学角度大致可描述为基础期、排粪前期、排粪期和结束期这四个阶段[46]。基础期描述了一组非排粪状态,此期间主要为结肠运动,包括碳水化合物的细菌发酵过程,液体、电解质和短链脂肪酸的透壁交换,固体粪便的形成及向远端推进的过程。排粪前期则发生在排粪前30~60分钟,乙状结肠内容物移向直肠,超过阈值的直肠扩张启动直肠肛门抑制反射,继而导致肛门内括约肌(internal anal sphincter,IAS)的松弛和肛门外括约肌(external anal sphincter,EAS)的收缩。肛管收集的感觉信息通过盆腔内脏神经传入神经元,一方面引起脊髓反射弧介导EAS收缩,另一方面通过脊髓丘脑束传递到脑干和大脑皮层,最终引起肛门括约肌的抑制或松弛。排粪期一般从排粪前15分钟开始,通过EAS的自愿松弛、腹壁收缩、下蹲姿势、髋关节屈曲、骨盆后倾和肛门直肠角的锐度从65°~108°变为110°~155°等,引起耻骨直肠肌松弛和肛提肌收缩,以增大肛门直肠角,并通过耻骨尾骨肌的收缩以移动会阴体,形成直肠肛门压力梯度并引起肛管扩张,联合纵肌收缩使肛垫变平、外翻,最终完成排粪行为。结束期代表排粪反射和排粪行为的终止,在粪便排空后会发生一系列变化以重建基础直肠肛门压力梯度并恢复排粪节制的过程。
目前,HD公认的病因学和病理生理学理论是以Thomson提出的细胞外基质降解引起黏膜滑动的“肛垫下移”学说为主。尽管ODS的具体病理生理变化尚未被充分认识,但可以通过排粪行为的时间节点分析HD和ODS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潜在的共病机制。首先,痔组织具有感觉神经支配功能并有感知直肠内容物的“采样”功能[47],一项关于ODS患者排粪前期功能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ODS患者的“采样”功能受损[48]。其次,联合纵肌和Treitz肌的退化也被认为是形成HD的最重要的致病因素[3]。而上述解剖结构贡献了高达10%~20%的肛管静息压力[49]。在排粪期,排粪障碍状态下反复用力会导致肛垫向远端滑动,可能诱发或加重HD的症状[50]。痔组织的脱垂会引起肛管静息压发生变化,进而导致直肠肛门压力梯度改变,可能引起患者直肠坠胀或排粪不尽感相关症状,已有研究证明避免用力排粪可以减轻HD患者的脱垂症状[51-52]。另外,肛门痉挛、肛管压力升高是HD的重要病理生理特征[5],也是ODS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会进一步导致直肠肛门压力梯度变化的异常及无法协调腹部和盆底肌肉排出粪便[53]。
2 HD与ODS共病机制的遗传因素
以往关于HD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非遗传学的危险因素,而对其遗传因素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ODS与HD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潜在的共病机制尚不清楚。新近研究发现HD和其他疾病存在共同遗传成分及病理生理学改变,从而证明了遗传因素可能在HD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作用[18]。该项研究纳入218 920名HD患者和725 213名非HD患者,对HD与其他疾病之间进行了多重遗传相关性分析,根据计算出的多基因风险评分并通过RNA-seq分析评估了痔组织中的基因表达情况,从而确定已知有生物学功能的风险基因作为HD的风险基因,包括NEGR1、MRVI1、MYH11、ELN、CHRDL1、ANO1、SRPX、ACHE、SRRT、GSDMC、ELN、COL5A2、PRDM6等共102个风险基因[18]。研究者通过免疫荧光实验对上述部分基因编码的蛋白质进行验证,上述基因参与调控细胞外基质的形成、肌肉收缩、线粒体的功能和糖基化等过程。基于上述研究对HD的新认识,我们从以下几个风险基因及其生物学功能进一步探讨ODS与HD可能的共病机制。
2.1 ANO 1基因
上述研究发现,HD患者更容易罹患IBS和FGID,其中ANO1基因在痔组织、直肠组织、血管中均呈高表达(rs2186797,ANO1,PP=97.0%),并且与基因型驱动的Cajal间质细胞(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ICC)功能调节异常相关[18]。目前已知ANO1基因主要在上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和感觉神经元中表达,而在人类胃肠道ICC中高度表达[54]。ICC是控制肠道蠕动的胃肠道起搏器,参与调节肠道运动,已被证明与IBS相关[55]。研究表明,对比非IBS人群,IBS患者的ODS评分显著增加,且IBS与ODS在协同失调方面存在着重叠[9],有研究显示ICC的分布在ODS患者与非ODS人群之间存在差异[56]。林宏城等国内学者认为直肠ICC数量的减少是ODS发病的重要因素[57-58]。另外,相关研究发现,ANO1在急性疼痛、慢性疼痛和焦虑相关行为的控制方面也发挥着影响作用[59]。因此,ODS与HD可能均受到ICC/ANO1的影响。
2.2 MYH11基因
上述研究显示,MYH11基因在痔组织中促进mRNA上调(rs6498573,MYH11,PP=63.2%),这可能与Treitz肌的功能相关[18]。MYH11基因编码一种平滑肌肌球蛋白。相关研究表明,MYH11的过表达导致自噬降解增加,引起收缩信号中断,从而导致蛋白质水平降低[60],并与胃肠道运动功能障碍有关[61]。根据目前已知的生物学功能相关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的研究,MYH11基因参与细胞外基质的组织、肌肉、骨骼和表皮的发育,可能参与ODS、脱垂性疾病及盆底功能障碍的发生发展。
2.3 ELN基因
上述研究结果认为,HD是一种神经肌肉动力、平滑肌收缩和细胞外基质受损的疾病,与憩室病、Ehlers-Danlos综合征、Williams Beuren综合征等有共同的风险基因[19]。其中,ELN基因在痔组织中高表达,是M1共表达模块的关键基因。ELN基因的产物是弹性蛋白,而弹性蛋白参与构成细胞外基质。ELN基因的突变会导致皮肤松弛[62]、可能与憩室病有关[63]以及诱发Williams Beuren综合征,可伴随胃肠道不适、腹痛、便秘、直肠脱垂等症状[64]。李娟等[65]的研究认为直肠黏膜下层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表达异常可能是ODS的发病机制。因此,ELN基因不仅在痔组织中高表达,而且可能与MYH11基因一样,同时也参与细胞外基质、肌肉、骨骼和表皮的发育,还可能参与ODS、脱垂性疾病及盆底功能障碍的发生发展。
2.4 NEGR 1基因
上述研究结果还发现,HD与精神障碍性疾病(焦虑、抑郁和癔症)、疼痛相关特征(包括腹痛)有遗传关联,NEGR1(神经元生长调节剂1)基因在痔组织中高表达[18]。NEGR1的产物可以调节神经突触的生长和突触的形成。另一项有关抑郁症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已将NEGR1确定为重度抑郁症的风险基因[66]。另一项研究显示NEGR1在焦虑和抑郁患者中影响成人海马神经冲动的发生,导致情感行为异常[67]。近年来,脑—肠轴参与肠道运动、排粪障碍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其在IBS和FGID中也有重要的作用[68]。脑—肠—菌群轴在慢性便秘和FGID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可能是慢性便秘发病率高、临床疗效欠佳的因素之一[69]。有临床研究证明,手术干预无效的ODS患者大多也存在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因素[70]。
2.5 ABO基因
上述研究另一个重要发现是O型血人群患HD的风险较高,而A型和B型血人群患HD的风险较低[18]。ABO基因的A、B等位基因编码糖基转移酶,分别编码糖基转移酶A(GTA)、糖基转移酶B(GTB),催化形成A、B抗原[71]。A、B抗原不仅可以在胃肠道的上皮细胞表达,还可以在分泌腺的黏蛋白上表达。近年来,已经有关于ABO血型的基因组研究,ABO基因在许多类型细胞中表达糖基转移酶,它通过修饰细胞表面糖蛋白上的寡糖来决定个体的ABO血型,这促使血型和疾病之间的关联逐渐引发关注[72]。
除ABO基因在HD和胃肠道的共表达外,肠道微生物与ABO基因之间也存在密切关系[73]。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也可能通过脑—肠轴系统调节激素(血清素等)和代谢产物(短链氨基酸等)来影响宿主行为,并且存在双向调控机制[74-75]。最近一项发表在Nature的研究证明了宿主ABO基因对肠道中特定细菌丰度的影响[76]。此外,一项关于宿主遗传学、饮食对肠道微生物和疾病的影响的队列研究结果显示,乳酸粪球菌的水平与人类的ABO血型相关,肠道细菌对肠道黏膜分泌的A/B/AB抗原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无论高纤维饮食或低纤维摄入量,分泌A、B和AB抗原的肠道黏膜中乳杆菌丰度均显著增加;O型血人群只在高纤维饮食情况下,肠道黏膜中的乳酸杆菌丰度才升高[77]。上述研究似乎提示了O型血人群需要摄入高纤维饮食和更多的益生元来改善肠道的微生态环境,从而改善肠道功能,避免ODS的发生。
3 小结与展望
HD和ODS作为常见的肛肠良性疾病,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两者的病因、发病机制受非遗传因素和遗传因素的共同影响,且均涉及复杂的病理生理学过程。HD和ODS还有着诸多的共病机制,但仍有待进一步开展深入的研究以阐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肛门括约肌和盆底肌的神经通路与反射机制,肛门感觉受体和相关传入通路的详细表型,脑—肠轴的病理生理学机制,自愿与非自愿因素在排粪障碍中的具体影响等。本文以临床问题为导向,依据HD和ODS之间共病机制的研究进展,并结合HD遗传因素研究的新发现,探讨HD与ODS的潜在共病机制,以期为二者的发病机制研究、临床诊治及管理提供新的思路。
利益冲突声明全体作者均声明不存在与本文相关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