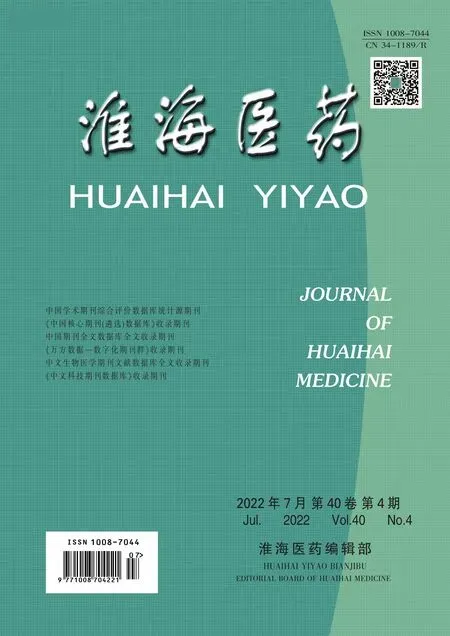肠道微生物代谢组学检测在疾病诊疗中的研究进展
吴敏,张丽霞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表明,许多基因对人类疾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影响,包括代谢性疾病、炎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除了遗传因素,环境和人为因素在疾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也逐渐被揭示,肠道不仅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同时也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体肠道为微生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成人肠道内的微生物数量高达1014,接近人体体细胞数量的10倍,其包含的基因数目约是人体自身的100倍,补充人体的代谢功能。微生态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不仅能调节肠道微环境,还可以通过物理交互或通过机体分泌的代谢物分子进入全身循环从而影响人类的正常生理和疾病。微生物群与机体平衡被破坏会引起多种疾病,常见的有炎症性肠病、乳糜泻、食物过敏、结肠癌等。因此,本文概括地总结了肠道微生物代谢组学检测在疾病诊疗中的最新进展。
1 TMO(三甲胺-N-氧化物)
氧化三甲胺(TMAO)是肠道微生物重要代谢产物之一,由富含磷脂酰胆碱(PC)和左旋肉碱的营养素在肠道微生物三甲胺(TMA)裂解酶作用下分解为TMA,进入肝脏后经黄素单氧酶(FMO)3氧化而成[2]。TMAO具有多种生物活性,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肾脏病等密切相关[3-4]。TMAO通过诱导胆固醇的变化(降低胆固醇逆向运输),影响甾醇代谢。动物实验表明2%胆碱饲料诱导啮齿动物6周,通过口服补充谷甾酮(一种法尼类X受体)而降低TMAO水平,使动脉粥样硬化疾病得到改善[5]。
口服胆碱结构类似物3,3-二甲基-1-丁醇的剂量 (DMB)或碘甲基胆碱(IMC),一种针对微生物TMA产生的天然抑制剂酶,可以降低血栓形成风险;与此同时,利用肠道微生物群靶向抑制剂碘甲基胆碱可以阻断MAO胆碱饮食诱导的升高,改善肾功能,减弱肾小管间质纤维化进程[6]。表明微生物酶可以作为靶标来研制新药。
2 短链脂肪酸(SCFAs)
SCFAs是胃肠道中浓度最高的代谢物之一。膳食纤维能够影响结肠微生物群,多糖发酵的产物,特别是SCFAs属于有益生物活性分子[7],可反作用于宿主。SCFAs对宿主的作用包括调节T细胞和巨噬细胞分化及促炎介质的下调。这些作用有助维持肠道间的精细平衡。核梭杆菌生长过程中释放的SCFAs可以通过游离脂肪酸受体2 (FFAR2)触发人中性粒细胞的趋化,参与炎症反应[8]。而且游离脂肪酸可作为2型糖尿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在预测2型糖尿病易感性方面有很大潜力[9]。
脂质代谢与代谢性疾病密切相关,一些SCFAs,特别是丁酸盐灌肠在溃疡缓解期患者中的应用较大,而对结肠炎或肠易激综合征影响作用相对较小。动物实验表明,对新生小鼠直接给予丁酸盐或谷氨酰胺可减弱疾病表型,母体摄入丁酸盐会影响新生小鼠的粪便微生物群和代谢物及实验性胆道闭锁的表型表达,谷氨酰胺可促进胆管上皮细胞的存活[10]。而丁酸作为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G蛋白耦联受体激活剂能显著改善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自闭症、亨廷顿病及精神分裂症[11-12]。
3 长链脂肪酸(LCFAs)
LCFAs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作机体膳食补充,或者作为亚麻籽,或含有亚油酸的紫苏油和含有ω-3和ω-6脂肪酸(fatty acids,FA),被认为是机体必不可少的,因它们不能由人体产生,主要通过饮食获取,并最终经代谢产生生物活性脂质介体,可以降低血压(花生四烯酸)或通过减弱炎性细胞因子来调节炎症[13]。多种共轭亚油酸、氧基FA和羟基FA为微生物代谢物,由乳酸菌、粪肠球菌等肠道中共生菌产生。可以靶向作用于巨噬细胞中的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γ受体,增强上皮屏障完整性[14]。此外,共轭亚油酸可作为维生素和纤维辅助治疗溃疡性结肠炎[15]。
4 4-乙基苯硫酸盐(4-EPS)
4-EPS是一种食物发酵产物,可能为尿毒症毒素。小鼠有低浓度的4-EPS。动物实验显示,母体免疫激活4-EPS增加(Mia)自闭症谱系障碍(ASD)小鼠模型,4-EPS水平升高与行为异常相关,脆弱芽孢杆菌治疗可改善异常影响,表明ASD具有益生菌和后生菌作用[16]。
5 吲哚
肝性脑病(HE)是临床上常见的以代谢紊乱为基础的神经精神异常综合征,其临床表现可从亚临床改变,如轻微肝性脑病(minimal hepatic encephalopathy, MHE),进展到昏迷。研究[17]证实,肠道微生物(gut microbiota, GM)及有害毒副产物如氨、吲哚、羟吲哚和内毒素参与HE的发病,尤其通过肠-肝-脑轴功能失调机制在HE的疾病进展发挥重要作用。
肠道微生物区系是生物活性代谢物的主要来源之一,色氨酸在色氨酸酶作用下生成吲哚,该过程离不开微生物基因组编码程序[18]。色氨酸衍生物,如由产孢梭菌转化的3-吲哚丙酸(IPA)和由乳酸杆菌编码并由色氨酸酶识别的吲哚-3-醛,通过芳烃受体(AhR)介导参与疾病的发病。AhR由配体激活的古老的保守蛋白,在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的不同组织中广泛表达。AhR通路失调与许多发育缺陷和慢性疾病有关[19],如吲哚-3-醛通过AhR介导淋巴细胞产生IL-22引发白念珠菌感染[20]。在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多发性硬化动物模型中,吲哚代谢物通过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炎症反应,降低了星形胶质细胞的致病活性。此外,吲哚-3-丙酸补充剂(一种5-HT前体)可用于治疗共济失调和多发性硬化症[21-22]。
6 其他蛋白质衍生代谢物
结肠菌群可分泌氨基酸、有机酸、核苷及多胺,且宿主-细菌共培养产生的代谢物与单独培养的宿主细胞或单独培养的细菌产生的代谢物不同[23]。牛磺酸水平增加可影响炎症小体信号转导,因此可用来调节炎症反应。肠道疾病研究[24]表明牛磺酸为结直肠癌和糖尿病患者的有利代谢物,可预防糖尿病血管并发症,主要通过介导氧化应激生酮还原碳水化合物途径发挥作用[25]。
丙酸咪唑是一种新近发现的组氨酸衍生代谢物,在2型糖尿病的病理生理学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激活p38γ、p62和mTORC1途径对糖尿病患者造成伤害。因此,临床研究[26]提出通过调整饮食(低蛋白质)方案来抑制咪唑丙酸盐的产生。
7 多胺
多胺参与炎症的反应调节,通过氨基酸脱羧产生精胺,可降低结肠IL-18水平并抑制NLRP6炎症小体产生,在炎症性肠病患者和慢性DSS诱导的结肠炎小鼠体内水平增加[27]。与此同时,多胺释放节律与人体生物钟功能有关,因此控制肠道多胺水平可调节炎症反应[28]。
8 维甲酸
维甲酸由肠道梭状芽孢杆菌产生,通过IgA调节免疫应答[29]。维甲酸及其受体的缺乏与结肠炎、结肠癌及IBD相关[30]。同时,全反式维甲酸(ATRA)作为一种治疗免疫失调的潜在物质被广泛应用,如血小板减少症、类风湿性关节炎、肝硬化、癌症及自身免疫性疾病[31-32]。
9 胆汁酸
肠道微生物通过调节自身群落比例和代谢产物的释放影响宿主的葡萄糖代谢和胰岛素抵抗[33]。初级胆汁酸(BA)由鹅去氧胆酸(CDCA)和胆酸(CA)通过肝细胞从胆固醇在肝脏中合成,CA转化为二基脱氧胆酸(DCA),CDCA生成单羟基石胆酸(LCA)。结肠细菌进一步代谢7a-氧代-lca为“三级”BA和熊去氧胆酸(UDCA)[34]。UDCA可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促进2型糖尿病患者糖代谢,进而减轻体质量,对抗感染也起着关键作用。因UDCA可抑制患者粪便中艰难梭菌的生长,常被用作治疗艰难梭菌相关性囊炎[35]。而DCA可阻碍前列腺素E2合成(一种抑制隐窝修复的物质),具有促进伤口修复作用[36]。动物实验表明,在小鼠肝癌模型中,通过继发性BA给药可减少自然杀伤T细胞积聚,降低CXCL16表达,从而逆转抗肿瘤作用[37]。
10 黄酮类
黄酮类化合物是多酚类次生植物代谢物,具有广泛的生物能力,包括抗氧化作用,对血管内皮细胞保护作用和抗癌活性。黄酮类化合物是主要的膳食植物多酚,对健康有积极的作用[38],如芦丁和槲皮素可以抑制大肠杆菌和粘质沙雷氏菌生长;木犀草素作为抗氧化剂抑制肥大细胞,参与炎症反应[39]。
由肠道产生或调节的代谢物微生物群虽功能多效,但高度依赖于上下游作用因子。如SCFAs作为能量燃料,通过修饰组蛋白残基调节基因表达,或通过与受体结合和触发起信号分子作用。下游信号级联高度依赖于细胞类型、浓度、组织背景及受体表达模式。另外,疾病的产生也取决于特定代谢物对疾病的分子病因学,可用干预手段调整防代谢物水平,综合给药的途径、频率及个体间药代动力学的差异,使得防代谢物有助于疾病病理生理学改变。肠道微生物代谢组学研究为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治疗方向和治疗靶点,需要进一步加深相关研究,以期使疾病的诊疗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