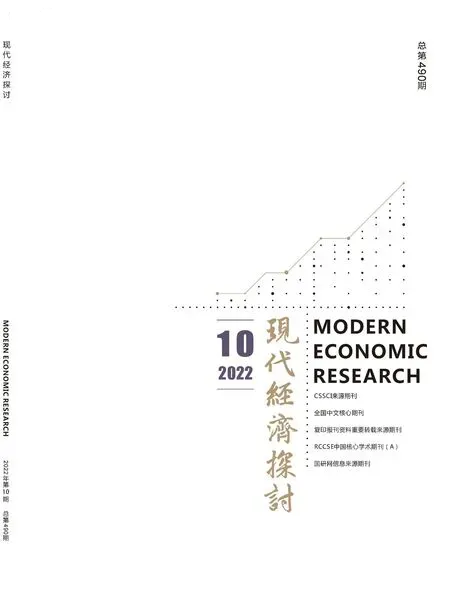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支付场景前瞻及法制障碍透视※
郎平
内容提要: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启了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的新赛道。从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进行考察,可明晰其国际环境,同时立足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可行性,廓清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中的货币构成和支付基础设施,从而前瞻其跨境支付场景。然而,境外市场主体对数字人民币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币值稳定性和支付基础设施的健全性,这需要国内法制为其提供保障。鉴此,检视国内法律制度,数字人民币的法律身份及技术规则存在罅漏,虽不构成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法律障碍,但会影响数字人民币的可接受性。故可采取以下措施来补苴罅漏:一是法定数字人民币的“身份要件”,二是创制数字人民币数字技术法,从而为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适用提供法律支撑。
一、 引 言
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CBDC),又称之为法定数字货币,是央行基于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行的、具有现代信用货币本质属性的数字货币(白津夫和葛红玲,2021)。目前,根据各国央行对CBDC的研发现状,可将其分为面向公众的零售型CBDC和用于金融机构间大额支付的批发型CBDC。2021年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第三次CBDC调查报告》调研了各国央行零售型和批发型CBDC的研发情况,相较于2019年,2020年关注零售型CBDC的央行在增多,批发型CBDC的央行在减少,但同时关注零售型和批发型CBDC的央行与2019年持平,占比在50%左右(Boar和Wehrli,2021)。目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泰国共同推出Inthanon-LionRock项目,新加坡-加拿大推出Jasper-Ubin项目,欧洲-日本推出Stella项目、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央行共同推出的Aber等项目,都以挖掘批发型CBDC在跨境支付中的潜力为目的。2021年7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组发布《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宣布:“当下的数字人民币是零售型CBDC,未来人民银行将积极响应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关于改善跨境支付的倡议,研究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领域的适用性。”2022年冬奥会开启了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场景,这为数字人民币“跨”向全球勾勒了一幅全景图,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适用已然蓄势待发。鉴此,有必要考察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厘定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基础构成要素,前瞻其支付场景,为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适用探路。然而,数字人民币“跨出”国门后,“点对点+电子支付+央行信用”的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取决于境外市场主体的可接受性。这一可接受性不再囿于人民币币值稳定性对其信用国际化的支撑,而是技术赋能后的币值稳定性与支付基础设施健全性的双重支撑,而国内法律制度则是二者最为牢靠的制度保障。故,有必要检视现有的法律制度,查缺补漏,从而为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可接受性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也为法定货币数字化变革潮流中的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助力。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要以开放和包容方式探讨制定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和原则”。这为如何完善中国现有的法律制度,提升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可接受性指明了方向。
二、 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1. 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必要性
第一,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提升跨境支付效率。根据202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显示,自2018年四季度起,人民币已经连续13个季度蝉联全球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信用的提升,将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对人民币使用的黏性,而高效支付结算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无疑是增强人民币使用黏性的关键。目前可以支持人民币跨境流通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有:一是境内的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hina National Advanced Payment System,CNAPS)+外国代理行或港澳离岸支付系统等模式,二是专用于人民币跨境业务的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CIPS)。CNAPS由大额实时支付系统(High Value Payment System,HVPS)和小额批量支付系统(Bulk Electronic Payment System,BEPS)两个应用系统组成。用于大额实时支付的HVPS和CIPS都采用实时全额支付系统(Real Time Gross Settlement,RTGS)进行结算。众所周知,RTGS的运作模式是在整个营业日内,通过支付指令连续、逐笔处理每笔资金的支付信息,存在支付成本高、耗时长的缺陷。另一方面,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跨境人民币现钞业务明显下降。银行跨境调运人民币现钞总计136.25亿元,同比下降87.0%,其中调运出境23.18亿元,调运入境113.07亿元,人民币现钞净调入89.89亿元。但目前中国零售型数字人民币试点已经辐射境内、跨境使用两个场域,批发型数字人民币正在研发之中。未来,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作为人民币“家族”的新成员,其中零售型数字人民币的境外使用不仅可以满足“无接触式”的交易方式,还可以节约人民币跨境调运的成本,规避新冠肺炎疫情等对人民币的境外现钞业务的负面影响;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落地则可以提升支付效率,降低支付成本,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助力。
第二,应对私人加密货币冲击及各国央行CBDC博弈的双重挑战。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改变了金融业格局和人们对银行固有的信任。2008年中本聪在《比特币: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提出了加密货币的理论框架,即一种无需依赖传统银行体系就可以实现货币存储和支付的替代方法(Ward和Rochemont,2019)。随后,不断有新的加密货币推出,截至目前,已经有上万种加密货币,市值已近上万亿美元。私人数字加密货币已向传统金融系统发起挑战,在此背景下,各国央行将面临的威胁是:个人不再依赖法定货币进行消费、支付等,这将削弱央行在货币政策中的货币控制权。私人加密货币可能严重削弱货币政策的传导,也限制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能力(Fung和Halaburda,2017)。各国央行开始探索研发央行数字货币。根据BIS调查结果,部分央行仅关注批发型CBDC,如加拿大、新加坡等,部分央行仅关注零售型CBDC,如巴拿马、厄瓜多尔等,但同时关注批发型和零售型的央行占比50%。可见,数字人民币不仅要应对私人数字货币的冲击,而且还要与各国央行CBDC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展开博弈。鉴此,加速推进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将有助于在博弈中获得先发优势。
第三,削弱对美元跨境交易结算支付网络的依赖性。当前的跨境支付体系是以用于“资金信息”报文传送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和用于美元跨国结算的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为核心建立起的全球支付网络。SWIFT涵盖200多个多家,接入机构超1.1万家,而CHIPS作为全球最大的资金传输系统,是美元跨境交易清结算的中枢神经。为了便于与SWIFT跨境代理支付业务的对接,中国的CIPS也采用了国际通用的ISO 20022报文,所以中国CIPS对SWIFT有较强的依赖性。支付基础设施作为资金运作的通道和枢纽的地位决定了谁掌管了支付基础设施,谁就掌握了经济命脉,就拥有话语权(梁静,2017)。例如,美国通过SWIFT对伊朗、朝鲜的金融“核”制裁。鉴此,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适用将有助于削弱人民币对以美元为核心的CHIPS和SWIFT系统的依赖性。
2. 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可行性
第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五通政策”的实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为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提供了现实条件。例如,在贸易领域,仅2021年中国同湄公河五国的贸易额就近4000亿美元。在金融领域,截至2020年末,中国已经与2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此外,由于人民币在周边国家越南、老挝、缅甸、蒙古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的可接受性程度高,所以在蒙古国、越南等还会使用人民币(现金)进行交易。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对人民币的市场需求极大,部分国家境内使用的人民币不仅限于存款货币,还包括现金。存款货币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提供了便利的支付服务,而现金则提升了人民币的泛在性,二者从不同层面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这也为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适用提供了现实条件。未来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适用,不仅能够迎合人们对无现金社会的需要,还可以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效率,降低支付成本,提升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的层级。尼尔·梅塔等(2020)基于中国与非洲的国际贸易市场,设想“中国将建立一个代币化的人民币,并在非洲进行测试。亦或,中国将创造一种以人民币背书的非洲货币‘非洲元’,类似欧洲的欧元,以在整个非洲流通”。从理论上建构了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又一场域。
第二,香港的离岸金融市场为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适用提供了“支点”。离岸金融市场具有“两头在外”的特征,通常是非居民之间以离岸货币所从事的金融交易,资金的提供者和资金的需求者都是外国的(韩龙,2021)。根据《2021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上经营的人民币业务包括存款、贷款、发行人民币债券和人民币央行票据、以及央行票据回购与逆回购业务等。在香港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人民币投融资主体包括国际金融组织、央行、主权基金、商业银行、基金、保险公司等各类海外投资者,地域分布涵盖港澳台、亚太、欧洲和非洲等多个地区。据2020年末统计,涉及人民币存款5285.49亿元、贷款1520亿元、发行人民币债券2707.38亿元、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1550亿元、央行票据回购做市总额734亿元。目前香港已经形成了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上的人民币业务模式丰富、交易额巨大、交易主体多元,这都对人民币的流动性、安全性、低成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适用恰好可以迎合这一需求。可见,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数字人民币的需求之外,香港的离岸金融市场在“呼唤”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适用。2021年3月,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对外表示:金管局正在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对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的技术测试做相应准备。数字港元与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实现,可以满足香港离岸金融市场对人民币流动性、安全性、低成本的需求。鉴此,以香港离岸金融市场为“支点”来推进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适用具有可行性。
第三,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场景呈现出跨向“全球”的趋势。一方面,随着《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将进一步深化亚太地区的经贸发展。其中,日本、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中国既是两大协定的签署国,又在积极测试CBDC,两大协定已先行勾勒出了区域性CBDC的跨境支付场景。另一方面,2021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阿联酋央行、国际清算银行、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共同搭建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m-Bridge项目)启动测试。中国的六大行(工行、农行、中国银行、建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汇丰银行、外汇交易中心,泰国的银行业协会,法国兴业银行,香港外汇结算中心共22家境内外金融机构参与,辐射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泰国、香港4个辖域,涉及数字贸易结算、跨境代币发行、跨境保险费用支付、跨境商业金融交易、低值聚合服务、供应链融资、跨境电子商务等11个跨境支付场景,法国兴业银行、高盛集团、渣打银行等这些参与测试的国际金融机构,其业务触及全球,如果m-Bridge项目落地,将有助于数字人民币“跨”向全球。
故,立足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可行性,考察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构成要素,前瞻其支付场景,可为其跨境适用探路。
三、 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构成要素及支付场景前瞻
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适用包括数字人民币和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基础设施的跨境适用,以下将分而述之。
1. 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基础货币构成
当黄金不再成为货币供应量的组成部分时,一国总的货币供应量=纸币(或现金)+存款货币,由此形成了“央行-商业银行”的二元货币信用创造系统。由于存款货币具有需求的内生性,所以商业银行位于货币信用创造系统的第一个层次上;央行发行的纸币因以内生性需求为“指标”具有外生性特点,所以央行位于货币信用创造系统的第二层次上。因此,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增发纸币,确保存款货币银行从准备存款账户中不断地提取现金,从而支持存款货币银行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表明,目前数字人民币将采取中心化管理、“央行-商业银行-公众”的双层运营模式,基于金融的普惠性,以满足国内零售支付需求为目的,所以属于零售型CBDC,主要作为现金类支付凭证(M0),不计息,并明确数字人民币将与实物人民币并行发行、长期并存。所以,随着数字人民币(M0)的落地,中国总的货币供应量=纸币(或现金)+零售型数字人民币+存款货币。2021年3月27日,中国与伊朗签署了《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在石油和贸易中将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结算,而基于零售型的数字人民币明显难以适用于跨境支付。2021年7月《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表明未来将研究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领域的适用性。
鉴此,中国未来跨境适用的数字人民币将是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目前,部分国家已经成功测试了批发型CBDC的跨境支付。例如加拿大央行2016年3月便开始展开研究的Jasper项目。该项目所使用的结算资产是一种可以反映加拿大央行账户中加元存款的数字存托凭证(Digital Depository Receipt,DDR)(白津夫和葛红玲,2021)。DDR与加元之间可相互兑换,由参与测试的银行通过分布式账本在Corda平台上完成DDR交易。在Corda平台上可以容纳多种货币结算选择,除原子结算外,还嵌入了流动性节约机制(LSM),即批量进行的净额结算,实现了金融机构间的大额资金划拨,其后在证券结算清算系统中又成功测试了券款兑付,并与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合作,通过在加拿大央行的Corda平台和新加坡金融监管局的Quorum平台应用哈希时间锁合约(Hashed TimeLock Contract,HTLC),实现了代表加元的DDR和新加坡元的DDR跨境、跨货币、跨平台的原子结算。所以,中国的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可以考量将央行的资产“代币化”,以“数字代币”的形式来实现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
简言之,随着零售型数字人民币、用于跨境支付的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落地”,中国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成员将从“纸币+存款货币”扩展为“纸币+零售型数字人民币+存款货币+批发型数字人民币”。
2. 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支付基础设施构成
基于上述未来中国人民币基础货币新增成员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要考量二者跨境适用的基础设施构成,离不开现有“现金+存款货币”构成的支付体系。现金具备“点对点”的交易优势,而基于账户的存款货币则主要用于大额支付,通过账户所在银行间账目上的借增贷减来实现交易,最终以交易双方各自账户余额的增减来判定存款货币的转移,所以支付基础设施是存款货币流通的管道。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支付基础设施需要立足于零售型数字人民币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这两种货币来考量。
第一,基于零售型数字人民币的支付基础设施主要是“钱包”,有两类:一是软钱包,仅需要提供手机号码就可以在手机上通过“数字人民币APP”使用零售型数字人民币来购物、住宿等。二是硬钱包,即基于安全芯片等技术支持的手环、卡片等硬件设备来使用的数字人民币钱包。截至2021年10月末,数字人民币钱包累计开设1.5亿个(其中,个人钱包1.4亿个、企业钱包1000万个),累计交易1.5亿笔,金额合计620亿元。2022年2月的冬奥会,为境外人士在中国境内使用零售型数字人民币提供了丰富的场景。未来,零售型数字人民币将在满足中国周边国家越南、蒙古、老挝等国境内对人民币现金交易需求的同时,还可以实现支付的“无接触”,降低跨境人民币现钞的调运成本,提升人民币使用的泛在性。
第二,基于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支付基础设施,既可以考量升级国内现有的跨境支付系统,如升级CIPS,也可以考虑搭建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平台。但无论最终选择以上哪种路径,最关键的问题是适用于批发型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基础设施的底层技术。由于分布式账本技术(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是由已知的组织合作创建的网络,用于创建共享记录并进行协作,没有矿工和挖矿,可以用来发行“代币”;并且DLT网络不是去中心化的,创建分布式账本的组织具有完全的控制权来管理网络结构、确定其用途和功能,同时账本的历史记录会在多台服务器上存储,由多个节点更新、确认网络上的新消息,节点间相互通信以确保维护最准确、最新的交易记录(提安娜·劳伦斯,2021)。所以,DLT具有点对点交易、智能交易、隐私交易、不可篡改、可追溯等特点(谢平和石午光,2019)。目前,Jasper-Ubin、Stella、Aber等批发型CBDC项目,都选用了DLT。中国在零售型数字人民币(M0)中也部分采用了DLT。鉴此,未来对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可以考量运用DLT来实现中国境内跨境支付系统的升级,也可考虑通过DLT来搭建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平台这两种方案。
3. 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支付场景前瞻
资金支付通常服务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梁静,2017)。目前,2022年冬奥会用于跨境支付的零售型数字人民币主要是用于商品市场,而参与的m-Bridge项目则侧重于另外三大市场。所以,可以立足于零售型数字人民币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前瞻其跨境支付场景:一是立足零售型数字人民币,前瞻商品市场的跨境支付场景。零售型数字人民币商品市场的跨境支付可以从后端合约运行和前端钱包支付两个视角来展现:后端合约运行中,先将支付信息预先转换为智能合约;待交易达成后,智能合约将自动执行交易,无需交易双方介入;支付完成后,智能合约将交易信息自动上传至区块链社区,供全体社区成员共同认证,并加以不可更改时间戳标记(张乐和王淑敏,2021)。而前端钱包支付,使用者可根据对数字人民币的数额需求、偏好等,选用软钱包或硬钱包进行零售支付。二是立足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前瞻其跨境支付场景,以证券市场的证券结算为例。目前,中央证券存管(Central Securities Depository,CSD)、证券结算系统(Securities Settlement System,SSS)、中央对手方(Central Counterparty,CCP)等结算模式都采取的是第三方簿记形式,由CSD、SSS、CCP等中心机构在中央服务器上对证券账户或资金账户的余额借增贷减,从而完成证券和资金的转移(姚前,2021)。这一情形下,交易环节为交易方进行证券交易→中央对手方(CCP)进行轧差清算→中央证券存管机构(CSD)和证券结算系统(SSS)通过证券账户进行证券结算→最后通过支付系统完成券款对付和资金结算。未来,在批发型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券款结算场景中,钱包地址将取代账户,客户无需在特定的机构开户,其私钥在本地生成。所以仅需对钱包、身份、账户间进行关联即可。由用户使用实名身份注册钱包,钱包与其身份信息、生物特征等身份标识以及银行账户和证券账户对应。同时,在服务业务方面,钱包除提供单纯的支付服务外,还可扩展其业务服务范围界面,比如与证券交易有关的服务、资产投资管理服务、信息服务等。
然而,由于国际社会是由“各自为政”的主权国家所构成的,具有主权身份的CBDC在境外的流通主要依赖于其国际币信,这一国际币信的直接体现是境外市场主体对CBDC的可接受性。立足于数字人民币的构成要素及其支付场景,数字人民币的可接受性包括币值的稳定性和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基础设施的健全性,而与之相匹配的法律制度可为二者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鉴此,有必要立足数字人民币的这两大领域,检视中国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可接受性的法制保障,看其是否存在罅漏,为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适用保驾护航。
四、 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可接受性的法制保障及其罅漏
1. 数字人民币币值稳定性的法制保障及其罅漏
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尚未落地前,由央行发行的现金和商业银行发行的存款货币共同组成基础货币,为保持币值的稳定性,已经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法律制度:一是商业银行需满足资本充足率的合规性要求,已具备良好的吸损能力;二是商业银行与央行之间的储备金制度,为资本供给的持续性提供了保障。三是配置的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央行提供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在重要性支付机构从国内支付能力变成国际支付能力时,面对国际支付中的“挤兑”也已具备偿付能力;四是面对银行内部信用脆弱性这一固有缺陷,商业银行已经能够通过自治来有效避免风险。五是强有力的监管。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宏观审慎+微观审慎”的双支柱监管措施,监管机构能够“自上而下”地从时间维度和截面维度审视金融系统性风险,金融机构能够“自下而上”通过自治来防范、处置微观风险。这些法律制度为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促使人民币信用从国内向国际层面延伸,国际社会自愿接受人民币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然而,理论上要维护人民币的币值稳定,还需要中国将货币总量与货币化的社会财富总量保持一致,使人民币成为社会财富的价值对应物(韩龙,2021)。故,发钞行所发行的货币数量也会影响币值的稳定性,通常由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
然而,随着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落地,法制层面和理论层面能够确保数字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性吗?一方面,零售型数字人民币采用的是“一币两库三中心”的运行体系,由人民银行通过大数据处理中心实现对零售型数字人民币投放数量的精确掌控;另一方面,未来适用于跨境支付的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由于使用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商业银行会通过在央行持有的银行账户(即准备金账户)来访问央行货币,所以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相当于将央行的准备金“代币化”,以此方式实现货币生命周期的连续性,并不会随意创造货币,而且商业银行交易中下沉至链上的“数据”会实时反映其货币的增减情况(谢星和封思贤,2020)。可见,沿袭“现金+存款货币”二元货币创造结构的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不仅具备了现金、存款货币的生命周期特征,不会冲击现有的二元货币系统的法律保障机制,而且还实现了货币数量的精准投放、跟踪,不但不会影响货币数量投放的失控,反而能够弥补现金投放数量预估失准的弊端。一言以蔽之,法制层面,现有的国内法制能够为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性提供保障,理论层面,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落地”也不会影响币值的稳定性。
“凡有国者必设关,凡有币者必循法”(宝山和文武,2018)。但数字人民币当下存在的如下罅漏不可不察。目前,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人民币管理条例》)等都未对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法律身份”加以明确,仅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法(草案)》提及“人民币包括实物形式和数字形式”。对于零售型数字人民币、未来跨境适用的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等都没有从法律上给予定性。尽管国内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的测试,在冬奥会跨境支付场景的应用,都表明数字人民币“法律身份”的缺失并不够成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法律障碍。但是,这一缺陷随着未来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落地,如不及时补苴罅漏,可能会影响央行声誉,尤其在跨境适用中,反而可能会削弱其国际竞争力。比如,未来随着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适用,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应由央行作为债务人还是由商业银行作为债务人?又如,零售型数字人民币目前是不计息的,未来批发型数字人民币是否应该设置利息?如何设置?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一而足。这些都是境外市场主体选择使用批发型数字人民币时的考量因素,也是提升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国际货币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亟需补苴罅漏。
2. 数字人民币支付基础设施域外适用的法制保障及其补苴罅漏
数字人民币支付基础设施的域外适用,即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或平台)的域外适用。众所周知,金融基础设施域外适用一般会导致与该设施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域外适用。所以,既要立足未来,建构批发型数字人民跨境适用的支付系统,又要检视当下人民币业务跨境支付系统,以批发型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域外适用为指针,以当下人民币业务跨境支付系统可触达的范围为场域,尝试廓定数字人民币支付基础设施域外适用的范围及面临的问题。
上文已述及,对于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可以考量运用DLT来实现中国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系统的升级,也可考虑通过DLT来搭建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平台这两种方案。首先,要升级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系统,需要先明晰中国现有的人民币跨境业务支付系统的构造。目前,中国人民币跨境业务的支付系统包括:一是由“外国银行行内跨境支付(代理行)+CNAPS跨行支付”,最终以境内支付的方式完成人民币的跨境结算。二是中国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清算所的债券存款和交易结算的基础设施与CNAPS连接,为境内外机构的人民币债券交易提供券款对付(Delivery Versus Payment,DVP)结算(梁静,2017)。三是通过中国建立的CIPS来实现人民币的跨境支付。四是接入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等人民币清算行,以离岸市场为支点,实现人民币的跨境支付。可见,中国现有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系统俨然已经形成了国内跨境支付系统、专用的跨境支付系统(CIPS)、离岸支付系统三大管道。如果考量运用DLT来升级中国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系统或者搭建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平台,方案如下:方案一:升级国内跨境支付系统。国内跨境支付系统的核心是CNAPS,根据央行第三季度电子支付数据显示,国内的电子支付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从成本收益考量,升级中国的CNAPS反而可能会出现负收益。方案二:升级中国的CIPS。中国的CIPS主要是报文传送,截至2020年末,CIPS已有境内外1092家机构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入。所以需要将用于报文传送的CIPS升级为可兼容批发型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的系统。然而,对于CIPS的底层技术如果选择DLT,则需要考量DLT的安全性和升级成本等,这关乎着金融机构对升级后的CIPS的可接受性,一旦技术成熟,可以考虑。方案三:以离岸市场为支点,建构在岸支付系统与离岸支付系统的双边跨境支付平台,满足离岸市场对数字人民币的需求,深化数字人民币的流通广度和深度。揆诸国内,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资本跨境流动频繁,与此同时,作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上海,其离岸金融业务模式与其他离岸中心的业务模式相类似,所以可以运用DLT来搭建上海→香港的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平台,利用在岸与离岸市场的错位发展优势,从深度上和广度上渗透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适用黏性。2021年3月,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就对外表示,金管局正在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对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的技术测试做相应准备。实际上,除搭建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在岸支付系统与离岸支付系统的双边跨境支付平台之外,未来还可以将其拓展为与他国互联的双边CBDC跨境支付平台,甚至是多边CBDC跨境支付平台。
纵而观之,目前中国对数字人民币基础设施域外适用的主推方案是,搭建以香港离岸市场为支点的双边跨境支付平台,积极参与的是用于多边CBDC跨境支付的m-Bridge项目,未来还可以考量升级CIPS或者搭建区域性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平台等。无论哪种方案,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跨境支付系统中数字技术的“互操作性”问题。“互操作性”的内容包括CBDC间的结算规则、标准等。以CIPS为例,金融机构只要接入和使用中国的CIPS,就必然需要接受与此设施相关的金融交易规则。当下中国对金融机构间的支付清算安排已制定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规则》《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操作指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服务协议》等支付业务规则,以及涉及证券交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修订)等法律法规,对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等的清结算业务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业务规则体系,为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但却有罅漏,其并未涉及有关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技术规则。比如,未来批发型数字人民币“链上”的发行主体、账户的所有权归属、以及客户间的结算最终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会触动境外市场主体使用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敏感神经。鉴此,如何从立法上来弥补跨境支付业务规则中的这一技术规则漏洞,显得极为迫切。
五、 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法律对策
面对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中法律身份和技术规则的缺失问题,既可以考虑以“打补丁”的方式来完善现有的法律规则,也可以考量“另起灶炉”创制新的法律规则,以下分而述之。
1. 法定数字人民币的“身份要件”
《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中表明:数字人民币是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具备货币的价值尺度、交易媒介、价值贮藏等基本功能,具有法偿性,主要定位于现金类支付凭证(M0),不计息,所以目前试点阶段是一种零售型CBDC。《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为数字人民币法律地位的确定廓出了框架。鉴此,可镜鉴《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来完善中国的《人民银行法》《人民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数字人民币的“法币身份”提供法律支撑。应考量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数字人民币币种的范围。一是基于M0的零售型数字人民币,其法律地位将与“实物纸币”等同。二是未来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适用场域。之所以要明晰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法币地位,目的是将其与人民币稳定币厘清边界。区块链公司树图(Conflux)2021年9月发布公告,Conflux将在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试点离岸人民币稳定币的跨境支付。人民币稳定币是由Conflux发布的一种与数字人民币挂钩的离岸人民币稳定币,只在价格上与数字人民币挂钩。目前虽然已经获得上海政府批准,但该试点项目尚未真正落地。未来,锚定数字人民币的稳定币可能会越来越多,为避免与跨境适用的批发型数字人民币混淆,厘定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主体极为必要。然而,从域外各国央行批发型CBDC项目的研发动向来看,可以将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央行作为发行主体的批发型数字人民币,主要用于央行之间的CBDC清结算,比如 2020年12月,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瑞士国家银行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运营商SIX之间推出的Helvetia项目,旨在测试两央行货币间的代币资产结算方法(BIS等,2021)。另一类是由商业银行作为发行主体的批发型CBDC,主要用于金融机构之间存款货币的清结算。如星展银行、摩根大通和淡马锡集团的Partior项目,该项目主要是利用DLT将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数字化,其中可由星展银行和淡马锡集团提供新加坡元、摩根大通提供美元,以实现各种金融交易的原子结算。故,可根据“合约”来确定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主体,由央行发行的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就由央行作为发行主体,由商业银行以存款货币发行的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就由商业银行作为发行主体,而不可机械地判定只要是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其发行主体就与存款货币发行主体一致,是商业银行。然后,根据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主体来确定“代币”归属、账户归属、以及相应的“代币”权义。
二是数字人民币的法偿性问题。各国对主权法币的法偿性规定并不一致,中国法币的法偿性属于绝对的法偿性,不存在数额、面值等使用受限的附加条件。但是由于零售型数字人民币因数字技术赋能,具有可控匿名性和离线支付等特性,所以,零售型数字人民币的绝对法偿性必然受到制约。鉴此,零售型数字人民币的法偿性应该设置边界,这一边界需要考虑可控匿名性的支付上限,以及移动支付无法实现的具体情况来廓定。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取决于境外市场主体的可接受性,如果对批发型数字人民币也施以法偿性规定,势必会引起法律冲突,触发批发型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的法律风险,反而不利。
三是数字人民币的计息问题。目前零售型数字人民币不计息,但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则应配置与存款货币相同的利息标准。因为主权国货币在境外的使用并不依赖于主权国的法律强制性,而是取决于居民或非居民因对本国货币币值稳定的信心和受益的考量(韩龙,2021)。因此,要保证批发型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中的国际货币竞争力,收益率也是主权货币间竞争的关键因素之一。例如,瑞士的e-krona项目,对基于价值的e-krona通常不支付利息,而对基于账户的e-krona就会支付利息。鉴于此,对于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是否计息需要分情况。
2. 创制数字人民币的数字技术法
目前,大部分的批发型CBDC项目所采用的底层技术都是DLT。但是不应仅囿于技术本身来创制数字人民币的技术规则,而是要以数字技术为背景,创制适用于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的技术规则。全球范围内,目前瑞士已经基于DLT的证券概念,创制了“DLT”法规。根据该法规,可基于分类账创建和发行批发型CBDC“代币”的证券,同时,批发型CBDC“代币”作为瑞士国家银行的负债,持有人可以直接向瑞士国家银行主张债权,并且该债权会附随代币的转让同时转让至接收方(BIS等,2021)。但对于该代币的所有权及其转让的最终确定性,则遵循民法中的“合约”规则,发行和赎回批发型CBDC的主体,以及DLT平台中的各参与方,将依据“合约”来确定彼此间的权义,同时,还会根据《瑞士责任法》(Swiss Code of Obligations)中的支付指令条款来确定批发型CBDC转让的最终性。从瑞士“DLT”法规的内容来看,其主要是厘定批发型CBDC的发行和赎回规则,明晰批发型CBDC的法律地位,将其确定为瑞士国家银行的负债。然而,对于批发型CBDC所有权的转移规则、交易中双方的权义问题、以及清结算的最终性问题仍然适用既有的《民法》《瑞士责任法》等法律规则。揆诸中国,尽管人民银行已经发布《金融分布式账本技术安全规范(2020)》(以下简称《DLT安全规范》),但是《DLT安全规范》是以安全作为整个立法的宗旨,侧重于对隐私的保护、潜含的技术风险、以及分布式账本技术系统的运维问题等,对于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适用而言,金融机构虽然可以此来建设分布式账簿系统,但是却无法应对批发型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中的“痛点”,比如数字化代币的所有权转移问题。鉴此,对于未来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适用,可以专门创制《数字人民币的数字技术法》,对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发行、赎回,及其法律地位是央行负债还是商业银行的负债等问题进行规定,为批发型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提供法制保障的同时,增强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国际货币竞争力。
然而,当下加速推进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落地固然重要,但防范零售型和批发发型数字人民币潜含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尤其是批发型数字人民币跨境适用中的货币替代问题。对此,为了避免过度的货币替代,可以通过对链上批发型数字人民币交易中下沉的数据采取实施的动态跟踪,在配置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的同时,嵌入流动性节约机制,以此来管控批发型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中潜含的货币替代问题。此外,还可以通过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来防控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