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八点二岁的分量有多重
□ 逄春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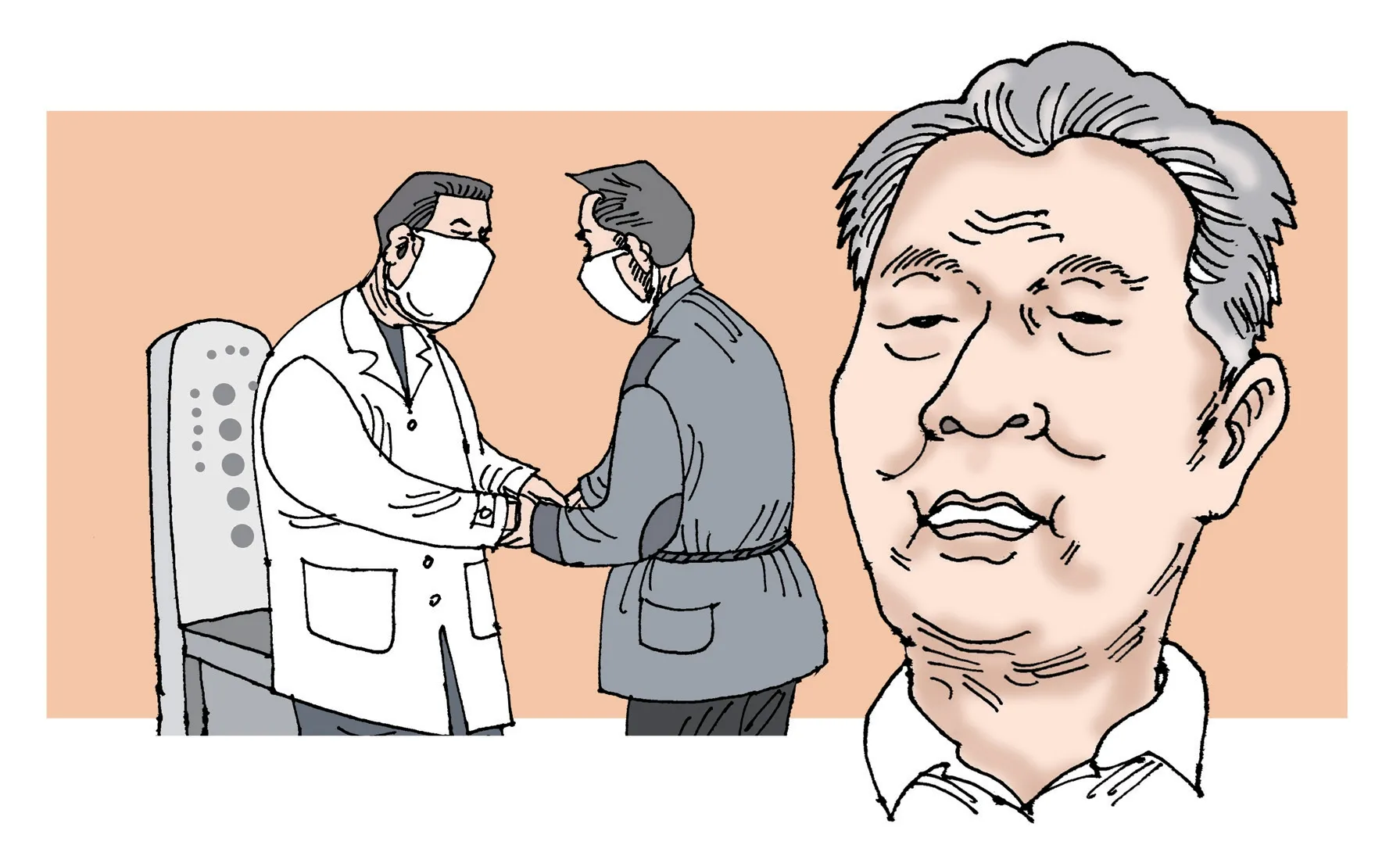
黎 青/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七十八点二岁”。
有史料记载,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预期寿命不足40 岁。2018 年12 月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 年的67.8 岁提高到2017 年的76.7 岁。
我查阅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只有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到了人均预期寿命。这是一条了不起的重大信息。七十八点二岁,是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的结果,是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的福音。近代以来,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健康长寿,是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着14 亿多人口的巨大规模,环境千差万别,有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平均预期寿命达到这个数,堪称奇迹。
曾几何时,病有所医,何其难也!1958 年6 月30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为题,报道了当地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看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一气呵成《送瘟神》:“(其一)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今天,我们再读这两首七律,仍可从中看出毛泽东忧国忧民之情在关注消灭血吸虫病这一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血吸虫病,老百姓叫它“大肚子病”。当年,这种病遍及南方12 个省市,患病的人数1000 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 亿人,危害极其严重,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病区人口减少,生产力下降,少数病区甚至田园荒芜,人烟凋敝。
1950 年冬,血吸虫病重灾区之一的上海市郊任屯村农民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尽快治好血吸虫病。信发出不久,毛泽东派出的医疗队就到了任屯村,不分昼夜查病治病,抢救了不少病人。
毛泽东非常关心血吸虫病。1955 年11 月17 日,他专门请在北京的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来杭州,报告关于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1956 年2 月1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6 年3 月3 日,毛泽东接到中科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写给他的信:鉴于土埋灭螺容易复生,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采用火焚的办法,永绝后患。毛泽东当即指示卫生部照办。
在《送瘟神》诗的后记中,毛泽东写道:“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12 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现在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者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到疫情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从这段后记中可看出,毛泽东为打赢消灭血吸虫这场大仗,他的心情是多么急切、感情是多么投入、决心是多么坚定!(材料引自2019 年第6 期《党史纵览》)
我近来看了一本书叫《国家行动——麻风防治的中国模式和世界样板》。“麻风”?过去听到这个词都心悸。如今,得这种病的人几乎消失了。怎么消失的?是国家组织几代“麻医”(治疗麻风病医生)治的。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让我震惊的“治麻”细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麻风肆虐,人们可谓谈“麻”色变。一人得病,全家遭殃。患者王某治好了,兴冲冲地回家,父母见他回来,吓哭了。全村人恐惧不已,都躲着他们全家。绝望了,最后一家人不堪忍受侮辱而服毒自尽。郑大有大夫第一次去诸城出诊,寻找麻风病人,几个病人偷偷摸摸把他领到墓地。“坟墓前的小石桌子就成了郑大有的工作台,他就这样在阴森森的坟墓前给麻风病人检查病情,采集血液样本,发放药物。”墓地没人,对歧视的恐惧压过了对死亡的恐惧。每个“麻医”都有被歧视的经历,到患者家里,患者家属不承认家里有麻风病人,住县委招待所都被赶出来。1964 年,“麻医”潘玉林到安丘行医,招待所服务人员看到介绍信上有“麻风”二字,明明有房子,也不让他住。
更让人心寒的是,“麻医”的亲人也被歧视,亲戚跟他们断绝了往来,孩子上学没有玩伴。“人传染上麻风病不可怕,也好治。传染上麻风恐惧症最可怕,最难治。一个人得了麻风,毁掉的是一个肉体,一个社会得了麻风恐惧症,毁掉的是人间亲情和温暖,带来的是信任的危机和道德底线的突破。”《国家行动——麻风防治的中国模式和世界样板》中如此表述。
忍辱负重,“麻医”们擦干眼泪再出发,把委屈藏在心里,一点点地感化病人,感化病人家属,把一个个病人收治到麻风村。经过几代人的泪水、汗水,甚至血水的巨大付出,这种可怕的疾病基本消除。我记住了他们的名字:马海德、尤家骏、孙昭水、马桂臻、张立彬、张基瑞、郑大有……随后跟上的是马天恩、张福仁等新一代。他们有的已经去世,背影渐渐模糊,但是在共和国“治麻”史上永远抹不去。
我说的背影,还包括麻风病患者,他们是无辜的,除了忍受身体被病毒侵害的折磨,还忍受着心灵上被隔离在常人之外的煎熬。作家在写医生的同时,把笔触伸向了患者的内心,其中的思考,很有价值。
盯着这些与麻风搏斗的医生的背影,我想起了一个意象——“井”。宋代学者杨简在《慈湖易传》中谈到井卦,说:“‘井’赡养润泽之功无穷,而实寂然不动。”井,风吹不走,日晒不干。它养人是无穷的,井里的水,你打了之后,还有,不见少。这些医生长期执着在“治麻”最前沿,是大地上一眼一眼最清澈的“井”。他们有“井”的品格,他们身上蕴藏的汩汩之水,让世界变得清澈透明。
功不唐捐。《国家行动——麻风防治的中国模式和世界样板》里说,到2018 年,我国新发麻风病患者只有1600 人。世界范围内,麻风病还在猖獗,其中印度的新发病人占全球新发病人的59%,每年高达10 万多人。这本书生动描述了中国为世界贡献的麻风病防治中可以借鉴的科学模式。一部国家麻风病防治史,彰显着执政党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血吸虫病、麻风病,都被我们党领导的医疗机构和“华佗”们制服了。而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蔓延,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疫情一定会控制住。
事是人做出来的,故事是人讲出来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七十八点二岁,就蕴含着很多内容,有好多故事可讲。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联系实际,联系自身,也许领会更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