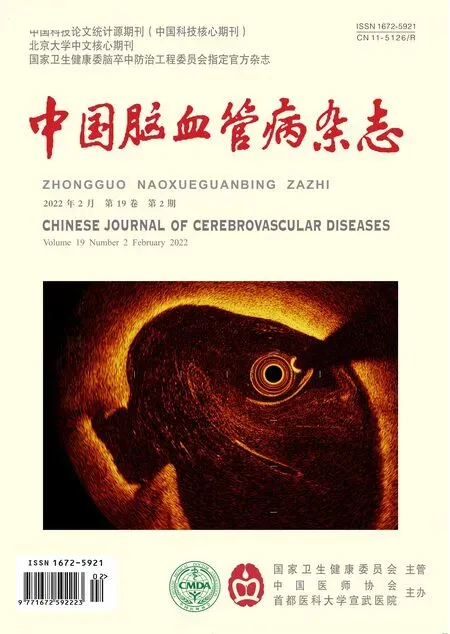颅内外血管狭窄术后支架内再狭窄的研究进展
姜英 王乃东
支架内再狭窄(in-stent restenosis,ISR)是指支架内或支架边缘3 mm范围内经血管造影证实狭窄率>50%的狭窄[1-2],也有研究判定管腔残余狭窄或复发狭窄率>70%为ISR[3]。ISR增加缺血性卒中复发风险,影响患者长期预后,是限制支架临床应用的主要原因[2]。不同部位ISR的发生率有所不同,颈动脉支架置入术(carotid artery stenting,CAS)后ISR的发生率为1.6%~24.0%[3];椎动脉支架置入术后ISR的总体发生率已从2009年的28.8%降至2014年的15.1%[4];颅内支架置入术后ISR发生率可达14.4%~30.0%[2]。以上数据提示,ISR已成为目前血管内治疗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就ISR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临床治疗进行综述。
1 ISR的形成机制
ISR是血管对损伤的病理反应,生理生化因素作用下的内膜病理性增生与血管重构失衡是ISR的形成基础[3]。综合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ISR的发生机制,可以概括为:血管内皮损伤及炎性反应是ISR形成的起始条件,血管平滑肌细胞(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VSMCs)的增殖、迁移以及细胞外基质重构是ISR形成的中心环节[5]。
1.1 血管内皮损伤及修复
血管内皮是血管壁和血流之间的保护屏障,健康的内皮层紧密连接,可严格调控脂质和炎性因子的浸润,具有良好的抗血栓形成功能。内皮细胞通过产生并释放生物活性介质调控血管壁的状态,以应对体液环境的变化。一氧化氮对维持血管稳态有重要作用,生理情况下,一氧化氮以L-精氨酸为底物由一氧化氮合酶催化生成。目前已知的一氧化氮合酶有三种亚型:神经元型一氧化氮合酶、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和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6]。内皮细胞的损伤一方面影响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活性,使其解耦联,导致一氧化氮生成减少,细胞氧化应激损伤,在应激损伤的后期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高表达,产生过量的一氧化氮,生成超氧阴离子,导致一氧化氮-环磷酸鸟苷信号通路受损;另一方面,内皮的损伤会选择性抑制神经元型一氧化氮合酶,导致环磷酸鸟苷降低,诱导增强缩血管反应,加速新内膜的病理性形成及血管重构[7]。
支架作为异物,改变了血管局部血流动力学。支架厚度、孔径、贴合血管壁后形成的凸起均可改变血管壁的剪切应力,内皮细胞通过多种感受器感应剪切应力的变化,包括离子通道、酪氨酸激酶受体、G蛋白耦联受体、细胞黏附分子、初级纤毛和糖萼,这些细胞感受器将机械信号转化为化学信号,激活磷酸腺苷激活蛋白酶、蛋白激酶B等信号通路,调控内皮细胞的增殖、炎性因子的表达,导致内皮功能障碍[8]。
支架置入术后,内皮细胞始终处于损伤与抗损伤的过程中。研究表明,生理条件下血管再内皮化是抑制新内膜病理性形成及ISR形成的重要途径,内皮细胞的修复除了来源于支架两侧成熟内皮细胞的迁移、增殖,可能还需要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EPCs)的参与[9]。内皮损伤后刺激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通过活化内皮细胞增加基质金属蛋白酶的分泌,基质金属蛋白酶9可通过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信号通路刺激一氧化氮释放,上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加速动员EPCs至外周血[10]。EPCs表面的趋化生长受体4通过与血小板诱导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结合,募集迁移至受损的血管表面,在黏附分子的作用下EPCs归巢并分化为成熟的内皮细胞[11]。另外,Wang等[9]通过SD大鼠建立颈动脉球囊扩张损伤模型,移植EPCs,观察受损动脉再内皮化及新内膜增生的过程,研究表明,在颈动脉损伤的早期,EPCs趋化聚集于血管损伤部位并通过旁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等细胞因子促进再内皮化。
1.2 炎性反应机制
血管的机械性损伤是炎性反应的首要条件,但炎性反应程度与个体的敏感性及组织再生能力有关。支架置入术后血管周围聚集大量白细胞,白细胞表面黏附分子高表达促使血小板活化,与此同时,损伤的内皮细胞分泌白细胞介素(IL)、肿瘤坏死因子(TNF)等,激活中性粒细胞,增加细胞间黏附分子的表达,促进趋化因子和整联蛋白合成,最终刺激VSMCs增殖迁移、细胞外基质沉积,导致血管重构[12]。既往研究已证实,IL-1、IL-6、TNF-α、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是脑血管支架置入术后ISR的炎性预测指标[13]。超敏C反应蛋白也被证实与颅内外血管ISR密切相关(OR=2.20,95%CI:1.29~6.66,P=0.018)[14]。然而近期的一项研究纳入141例因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行支架置入术的患者,最终纳入115例患者,术后平均随访68个月,出现ISR组38例,无ISR组77例,两组间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3.6±2.8)比(3.7±3.4),P=0.872]、平均血小板体积[(10.6±1.0) fL比(10.6±0.9) fL,P=0.929]、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153.7±105.2)比(149.5±82.5),P=0.813]、C反应蛋白[(8.1±16.3) mg/L比(17.8±42.7) mg/L,P=0.20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因此,炎性指标能否作为颅内外ISR的预测因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15]。
1.3 VSMCs的增殖及迁移
VSMCs增殖及迁移是动脉粥样硬化及ISR发生发展的共同病理过程。血管损伤导致内皮下胶原纤维和纤维连接蛋白暴露,血小板黏附聚集,在多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作用下, VSMCs由分化-收缩表型转化为去分化-合成表型,并分泌大量的血小板衍化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等,引起VSMCs增殖[5]。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BB是促使VSMCs表型转换最强的生长因子,主要与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b结合并使其磷酸化,激活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通路,促进VSMCs有丝分裂,趋化VSMCs的增殖和迁移。有研究表明,在血管修复的早期,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BB联合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可以促进内皮细胞活化增殖,同时抑制VSMCs的增殖迁移[16],这可能是由于内皮细胞与VSMCs中雷帕霉素靶蛋白的表达存在差异,他克莫司选择性抑制VSMCs雷帕霉素靶蛋白的表达,而不影响内皮细胞。
2 ISR的影响因素
2.1 血管解剖及生理特点
由于颅内外血管解剖及组织学的差异,颅内外动脉支架损伤后的重塑过程不同。颅内动脉缺乏弹性膜,中膜约占总血管壁厚度的52%,外膜较薄,只占31%,脑脊液及外膜自主神经的分布可能使颅内外血管对支架置入更敏感[17]。有研究者利用小鼠血管损伤模型,探索颅内CAS后血管重构的特征,并与股动脉比较,结果表明,颅内颈内动脉新内膜的形成延迟,中膜VSMCs增殖减少,外膜增生明显,这些病理生理差异可能不利于颅内支架置入术患者的预后[18]。椎动脉开口于锁骨下动脉,其结构类似于冠状动脉,富含弹性纤维蛋白及VSMCs。李景植等[19]研究纳入325例椎动脉起始段重度狭窄行支架置入术的患者,椎动脉走形弯曲的患者105例(32.3%),ISR组49例(42.2%,49/116),无ISR组56例(26.8%,56/209),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椎动脉走形弯曲是椎动脉起始段支架置入术后ISR的危险因素(OR=1.52,95%CI:1.02~2.28,P=0.04),可能与支架的置入使弯曲的椎动脉非自然矫直,增加血管的弹性回缩力有关。
2.2 支架的设计类型
支架设计类型与ISR的相关性目前尚未明确。就CAS而言,理论上开环支架置入术后ISR的发生风险高于闭环支架。Alparslan等[20]研究纳入155例因颈动脉狭窄行CAS患者,共139例完成6个月随访,其中71例置入开环支架,68例置入闭环支架,累计13.7%(19/139)的患者出现ISR,开环支架组16例(22.5%),闭环支架组3例(4.40%),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提示开环支架置入术后可能更易出现ISR。而另一项研究纳入双侧颈动脉狭窄患者52例,一侧置入开环支架,另一侧置入闭环支架,结果显示,开环支架(9/52,17%)与闭环支架(7/52,13%)ISR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10)[21]。Megaly等[22]通过回顾性分析单中心成功行CAS 的颈动脉狭窄患者148例,随访1年,累计25例发生ISR,其中开环支架15例(13.04%,15/115),闭环支架5例(5/1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ISR影响因素的结果显示,闭环支架与ISR显著相关(OR=12.45,95%CI:1.94~79.90,P=0.008)。
目前用于治疗椎动脉狭窄的支架主要包括金属裸支架与药物洗脱支架。一项荟萃分析表明,药物洗脱支架ISR发生率(22/142,15.49%)低于金属裸支架(47/140,33.57%;OR=0.388,P=0.001),但是该研究中置入药物洗脱支架患者的平均随访时间仅14.2个月,无法评估长期ISR情况[23]。药物洗脱支架抑制血管再内皮化,可能导致远期血栓形成[2,16,24],因此,与金属裸支架相比,药物洗脱支架是否具备长期优势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颅内支架包括球囊扩张支架及自膨支架,与术后ISR的关系存在争议。Guo等[25]研究表明,球囊扩张支架(19/57,33.3%)比自膨支架(5/40,12.5%)更易发生ISR(P=0.019),但Peng等[26]荟萃分析指出,支架类型(球囊扩张支架与自膨支架)与ISR发生无关(P=0.817)。
2.3 脑血管病危险因素
2.3.1吸烟:吸烟是ISR的危险因素之一[4,22]。可能与吸烟释放多种化学物质损伤内皮功能,导致新内膜形成及VSMCs增殖迁移有关。Huang等[27]利用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技术评估吸烟(31例)、戒烟是否超过1年(戒烟≤1年36例,戒烟>1年27例)、从不吸烟(85例)的新发病变患者置入西罗莫斯洗脱支架1年后血管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当前吸烟患者新内膜增生的平均面积大于从不吸烟者[(1.04±0.72) mm2比(0.96±0.68) mm2,P=0.04],戒烟程度(戒烟是否超过1年)与新内膜增生呈负相关(回归系数B=-0.154,95%CI:-0.187~-0.121),表明持续吸烟促进新内膜的形成,增加支架表面新内膜的面积。Wu等[28]研究表明,尼古丁进入ApoE-/-小鼠内皮细胞后诱导活性氧的产生,活化含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炎症小体,促使IL-1β和IL-18成熟,引起炎性反应,促进动脉粥样硬化。
2.3.2高血糖:一项荟萃分析纳入18项研究共17 106例颈动脉支架置入的患者,对其建立风险比随机效应模型,研究表明,糖尿病与颈动脉ISR发生风险增加有关(HR=1.68,95%CI:1.00~2.83)[29]。高血糖可延迟内皮细胞的修复,促进炎性因子的表达并刺激VSMCs增殖及迁移。潜在机制可能为高血糖促进过量活性氧形成,上调缺氧诱导因子1,导致糖酵解及谷氨酰胺分解增加,抑制内皮细胞与VSMCs胰高血糖素样肽1的N-糖基化,削弱胰高血糖素样肽1对内皮细胞的保护作用,同时促使 VSMCs迁移至内膜[30]。另外有研究表明,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可预防ISR,一方面可通过增加一氧化氮的生物利用度,恢复糖尿病患者内皮依赖性血管扩张;另一方面可抑制VSMCs收缩,减少VSMCs的增殖及迁移[31]。
2.3.3血脂异常:颈动脉血运重建内膜切除术与支架置入术的对比研究(carotid revascularization endarterectomy versus stenting trial,CREST)表明,除糖尿病(HR=2.44,95%CI:1.46~4.08)外,血脂异常也会增加颈动脉ISR的发生风险(HR=5.12,95%CI:1.25~20.96)[3]。高密度脂蛋白及其主要蛋白成分载脂蛋白A-I可以调节改善血管内支架的生物相容性,包括抑制VSMCs增殖及新内膜增生,抑制血小板活化与血栓形成,增强内皮再血管化,抑制单核细胞聚集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32]。ApoE基因多态性与颅内外动脉支架置入后ISR的发生密切相关,E4/E4基因型是ISR的独立危险因素(HR=3.305,95%CI:1.118~9.773,P=0.031)[33]。有临床试验表明,他汀类药物具有减轻炎性反应、抑制VSMCs增殖、迁移以及血栓形成的作用,是预防ISR的重要药物[1]。
2.4 抗血小板聚集药物抵抗
在预防围手术期脑血管事件中,阿司匹林及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聚集作用因人而异。Song等[34]研究抗血小板聚集药物低反应与CAS后新发脑缺血病变的关系,纳入76例CAS患者,术后出现新发脑缺血病变组患者(45例)氯吡格雷抵抗的发生率高于无缺血病变组患者[82.2 %(37/45)比41.9%(13/31),P=0.001],而阿司匹林抵抗的发生率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0.0 %(9/45) 比 9.7%(3/31),P=0.340],提示氯吡格雷抵抗更易诱发颈动脉术后脑缺血事件。氯吡格雷属于前体药物,部分通过肝脏细胞色素P450(cytochrome P450,CYP450)代谢转化为活性产物。Lin等[35]回顾性分析90例接受椎动脉支架置入术患者的病历资料,在术后3个月、6个月、1年进行随访,检测氯吡格雷代谢基因,包括CYP2C19、 CYP3A4以及P2Y12,结果表明,CYP2C19功能丧失的基因型是椎动脉支架置入术后患者发生ISR的危险因素(HR=2.959,95%CI:1.325~6.610,P=0.008)。
2.5 技术处理因素
Guo等[25]回顾分析20个中心行支架置入术治疗的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患者97例,研究ISR与血管内技术因素的关系,其中出现ISR者24例,未出现ISR者73例,随访1年,结果提示,较长的支架(校正后OR=0.816,95%CI:0.699~0.953,P=0.01)、局部麻醉(校正后OR=6.000,95%CI:1.693~21.262,P=0.006)是ISR的危险因素。另一项观察95例颅内动脉狭窄患者置入Wingspan支架后长期疗效的研究中,平均随访(34.9±23.3)个月,影像学观察单纯行球囊扩张者19例及支架置入前后行球囊扩张者61例,两组ISR的发生率分别为26.3%(5/19)、4.9%(3/6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6),提示支架置入前后进行球囊扩张可降低ISR的发生风险[36]。Zhang等[37]通过建立颅内支架置入术后ISR的预测模型发现,ISR不仅与狭窄部位(回归系数B=-1.391,优势比:0.249,95%CI:0.095~0.652,P=0.005)、血管解剖特点(回归系数B=2.195,优势比:8.982,95%CI:3.132~25.763,P<0.01)、残余狭窄程度(回归系数B=1.163,优势比:3.199,95%CI:1.284~7.973,P=0.013)相关,可能还与球囊充气压力(回归系数B=4.117,优势:61.367,95%CI:17.757~212.080,P<0.01)、脑血流灌注分级(回归系数B=1.174,优势比为:3.234,95%CI:1.291~8.101,P=0.012)有关。
3 临床治疗
目前针对颅内外血管ISR的治疗手段主要包括血管内介入及外科手术。血管内介入包括球囊扩张成形术及再次支架置入术。药物涂层球囊及药物洗脱支架的应用是目前ISR治疗的研究热点。常用的涂层药物有紫杉醇、西罗莫司、佐他莫司、雷帕霉素,均具有抗炎性反应、VSMCs增殖和免疫抑制的作用,旨在预防ISR的发生[16]。Zhang等[38]纳入115例颅内动脉狭窄的患者,其中42例行药物涂层球囊扩张术,73例行支架置入术,倾向性评分匹配分析患者76例,每组38例,平均随访(185±33) d,结果表明,药物涂层球囊扩张组总体ISR发生率(2/38,5.3%)低于非药物球囊扩张组(13/38,34.2%,P=0.003),但两组随访期间症状性ISR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6%(1/38)比10.5%(4/38),P=0.375],提示与传统的支架置入术相比,药物涂层球囊能降低颅内动脉总体ISR的发生率,但术后症状性ISR的发生风险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生物可吸收血管支架、减容技术为ISR后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但其临床疗效尚不明确[1]。颈动脉ISR外科治疗主要为颈动脉内膜切除术。一项荟萃分析比较再次行CAS与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治疗ISR的疗效,结果表明,再次支架置入术主要用于治疗出现复发性严重狭窄或症状性ISR,虽然介入治疗创伤性小,但两者治疗ISR的疗效类似,术后出现再发卒中(0.99%比0.98%,OR=1.010,95%CI:0.987~1.033)、死亡(1.00%比0.97%,OR=1.031,95%CI:0.999~1.063)及ISR(1.000%比1.000%,OR=1.000,95%CI:0.995~1.00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39]。关于外科手术是否同样适用于椎动脉及颅内血管,由于相关研究及病例报道较少,该部位ISR的处理方案尚未明确。
4 总结
颅内外ISR是当前困扰神经介入医师的难题之一,其发生可能与内膜损伤及修复、炎性反应、VSMCs的增殖及迁移相关,吸烟、高血糖、血脂异常、支架的选择、技术处理因素均是ISR的影响因素,需根据患者个体综合性分析,但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病变是基础环节。近年来腔内影像学技术如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技术已成为冠状动脉支架术后探讨ISR形成原因的理想手段,目前在颈动脉、椎动脉狭窄中也得到应用。通过可视化观察支架置入部位、贴壁情况以及支架与斑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技术将来有望成为指导手术方案、明确ISR病因的重要评估手段[40-41]。相信随着临床技术手段的提高以及材料制造学的不断发展,ISR的解决方案将会更全面、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