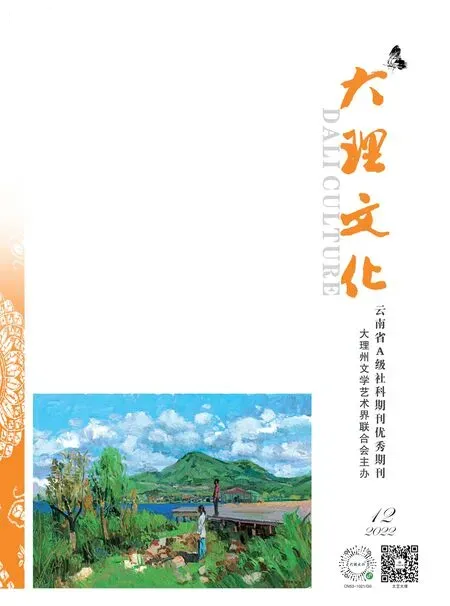古灵魂
●张锐锋
卿云烂兮
糺缦缦兮
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
明明上天
烂然星陈
日月光华
弘于一人
——卿云歌
晋景公
我近些天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每日头痛欲裂,浑身无力,不知怎么会成为这样?我每天夜晚都会做一个可怕的梦——一个鸟面人身的怪物会出现,他抓住我的胳膊,要将我拉进一个黑暗的山洞,我拼命挣扎,并在这挣扎中醒来。这个怪物是谁?他要将我拉到什么地方?那山洞究竟是什么?它在哪里?有一个夜晚,我久久不敢入睡,但还是睡着了。在一片乌云中,那个怪物又来了,他要抓住我,我就问他,你是谁?你为什么每天都会来到我的身边?又为什么要抓住我?
他说,你让我的香火断绝,我就让你的气息断绝。然后他又一次抓住了我的胳膊。他的力量很大,似乎我已经逃不脱了。我感到十分恐惧,又一次挣扎着,可是我就要被他拖入那个洞穴了,就在这洞穴的边沿,我突然醒了。我大喊一声,睁开了眼睛。四周一片黑暗,夜晚愈加深沉了,我就在这样的深夜坐起,仆人也来到了我的身边,问我,国君梦见了什么?为什么大叫?或者有什么需要吩咐我吗?
我说,快点亮灯,我要看见灯光,我要看见我的身边有什么人。灯光出现了,灯光一点点靠近我,我看见了灯光所照耀的并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我熟悉的寝宫,还是我熟悉的仆人,一切还是熟悉的。我看见了自己胳膊上有很多的红印,显然这是被那个鸟面人抓伤的,我的内心更加恐惧。我挣扎着起来,在每一个角落搜寻着那个人。他必定藏在这个屋子里,可是我却看不见他的踪影,而在灯光里,只有我自己的影子投射到白色的墙壁上。
天还没有亮,我就将大臣们召集到我的身边,我将自己的梦告诉他们,问,你们谁知道那个鸟面人是谁?他为什么要来到我的梦中作祟?我感到自己十分虚弱,醒来之后浑身都是冷汗,我感到寒冷,感到自己就要被他拖到永远的黑暗里了。我还想知道,那个山洞里面有什么?他为什么要将我拉到里面?我醒来之后借着灯光,看见我的胳膊上都是他的抓痕。你们一定要帮我祛离那个怪物,不然我就很难活下去了。
史官占卜之后,说,你所梦见的是中衍,他是伯益的玄孙,相传他就是鸟面人身,曾经为商王太戊驾车,太戊十分欣赏他,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他辅佐商王太戊屡建功勋,就是嬴姓的先祖,所以后来的嬴姓多为显贵。他的先祖是大业,娶的是少典的女儿女华,能够驯服鸟兽,被舜帝赐予嬴姓。大业的子孙一定遇到了不幸,所以要让中衍前来作祟。
我问韩厥,你一定知道他的子孙是谁,我是不是得罪了他的子孙?我梦见那个鸟面人对我说,你让我的香火断绝,我就让你的气息断绝。我从来没有让谁的香火断绝啊?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韩厥说,我想,他所说的乃是赵氏家族,因为赵氏家族就是嬴姓的后裔。大业的子孙如今在晋国已经断绝了香火,这不就说的是赵氏吗?从中衍传下来的后人都姓嬴了,中衍就是鸟面人身,他来到人世就是为了辅佐商王太戊,他的后代一直在辅佐周天子,都有着美好的德行。
我的心一颤,难道就是赵氏吗?可是他的后代已经没有了,我已经将他们都杀掉了,那么我将怎样弥补自己的过错?我将怎样摆脱这中衍的纠缠?我对韩厥说,你继续说吧,我该怎么办?韩厥说,到了周厉王和周幽王的时候,因为天子昏庸无道,叔带就离开了天子来到了晋国,一直侍奉晋国国君,先是侍奉晋文侯,一直到晋成公,每一个世代都建功立业,赵氏宗庙的香火一直旺盛。可是到了现在,你将赵氏宗族都已灭尽,晋国的百姓都为之深感悲戚,所以在占卜的时候就会得以显现,而他的先祖也会在你的梦中出现。他要将你拉入山中的洞穴,就是要为自己的子孙报仇,黑暗的洞穴乃是通往地下的深泉。
我说,那我该怎么办呢?赵氏家族已都死了,我不能让他们死而复生。唉,我当初怎么没有想这么多呢?要是赵家有一个后嗣就好了,那样我就能弥补我的过失了。韩厥说,的确人死不能复生,但即使突然遇到了春寒,满树的花儿凋零,总会有一朵花儿还留在树上,这棵树上还会结出一个果子。这样的果子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顽强,而是为了安慰树的主人。也许,赵家仍然有一个人活着,赵盾也许还有他的后裔,不然那个中衍就不会出现在你的梦中了。也许他告诉你,他的后裔已经长大了,你可以将其扶立了。不然他为什么不在从前你杀掉赵氏的时候出现,而要在这个时候出现呢?
好吧,别人都退下吧,我要和韩厥好好谈一谈。韩厥既然这么说,必定还有另外的隐情。是的,我要和韩厥谈一谈,看他还有什么好办法。等到朝臣都走了之后,韩厥才将事情的原委告知我。我才知道当初我被公孙杵臼和程婴两个人蒙骗了。原来程婴已经带着赵朔的儿子藏在了深山,而屠岸贾也被蒙骗了,我们以为已经将赵氏家族斩草除根,可是他的根仍然存留在深山。不过这样的蒙蔽却为我找到了弥补自己过错的办法,看来上天从来不会折断所有的路,总会将一条路隐蔽起来,留作无路的时候供我行走。
我说,那就太好了,你去寻找他们,将赵武带到我身边,我要重新将赵氏后人扶立,并重新封赏他,这样他的先祖就不会作祟了,我也可以安宁了。当初都是屠岸贾瞒着我将赵家宗族杀掉,我也要惩罚他。我知道我的谎言不会让韩厥相信,但我还是要这样说,不然我又怎样为自己来说明呢?现在晋国已经安定,下宫之役已经发挥了作用,现在给赵氏恢复名誉反而会让民众更加相信我的仁德,又可以解除赵氏先祖的幽魂对我的骚扰,这样的事情何乐而不为?我当初有杀掉他的理由,现在也有起用他的后嗣的理由,我的理由不仅是我的理由,也是上天的理由。
既然是上天的理由,那么我就可以用这样的理由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的理由中包含了我的理由。而且我已经看到人世间万物的低贱,不论是什么人,你用剑刺向他,他就会感到痛楚,并因着这痛楚而叫喊。这是绝望的叫喊,痛楚的叫喊。但是他会忘记这绝望和痛楚,他会忘记这绝望的叫喊。你若在他的伤口抚摸,他又会因着这抚摸的快乐而欢愉地叫喊。因为他忘掉了伤口的来历,只看见了现在的抚摸者。
我乃是晋国的国君,我看见了这人世间的低贱。我既知道剑的力量,也知道抚摸的力量。剑的力量是尖利的、让人痛苦的,而抚摸的力量是轻柔的、让人深感愉悦的。我拥有这两种力量,我可以随意使用它,所以我才会成为他们的主人。我深知怎样做是最好的,那就是我想做的总是最好的,违背我的心愿的乃是最坏的,因为我不乐意这样做。所以我所做的所有事情,既不是为了安慰别人,也不是为了安慰自己。我不需要安慰。无论是剑还是抚摸,都是一个君王的仪式,在这样的仪式中我的座位才被确立。
可是我现在浑身无力,赵氏的先祖中衍在我的灵魂里作祟,我忽然变得无能为力了。我敌不过已经死去的人,我只能战胜活着的人。所以我必须为了自己而安慰死者的灵魂。的确是我杀掉了赵氏宗族,我灭掉了他们,因为他们妨碍了我。现在我又要找到赵氏的后嗣——我觉得这乃是上天对我的照应,我竟然无意之中留下了树上的唯一的果子。这是违背我意愿的果子,而现在却合乎我的心愿。我以为这树上的果子已经摘尽了,可是我现在从树叶之间又看见了它,它仍然是为我而存在,为我而在风中摇动。现在我需要它。

韩厥
我已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国君,国君一下子变得十分高兴,脸上的阴云散开了。他知道在自己身上作祟的鸟面人会得到安慰,他就会因为这安慰而离开自己的身体。当然这也是我报答赵氏的机会。我曾经在赵朔面前答应过他,我要照顾他的孩子,要让赵氏宗庙的香火得以延续。可是多少年过去了,我的诺言一直没有实现。我不能欺骗自己,也不能欺骗死去的灵魂。
国君对我说,你要是早一点告诉我,我就会早一点将赵武召回,怎么还用等到现在?都是屠岸贾蒙蔽了我,他瞒着我策动了下宫之役,我知道之后已经无法挽回了。从赵盾的先祖开始,赵家一直是忠臣,一直辅佐晋君,晋国之所以能够强盛,赵氏的辅佐居功至伟,我们怎能这样对待他的后代呢?国君说着,似乎眼角悬挂着晶莹的东西。
国君所说的并不是假话,但其中却混杂了假话。我知道他哪一句是真的,哪一句是假的。他所说的,并不是出自他的真心,而是出自他的所需。我不相信屠岸贾所做的国君不知情,难道屠岸贾敢于背着国君攻打赵氏宗族?敢于将赵氏宗族连根拔除?但是,赵氏宗族始终对晋国忠心耿耿,辅佐几代君主功勋卓著却是事实,这一点,谁又能否认呢?
我又怎能将赵氏孤儿的实情告诉国君呢?若是让国君早一点儿知道,那么赵氏孤儿就性命难保,因为不论是屠岸贾还是国君,他们所想的就是斩草除根,就是将赵氏宗族连根拔除,怎么会让赵氏孤儿独存于世?若不是国君被梦魇所压,怎么会施行这样的仁慈?现在扶立赵氏后嗣的机会来到了,这样的机会来自国君的恶梦,这个梦缠绕着他,让他不能脱身。它就像一根绳索捆绑了他,让他感到了痛苦。从前这样的痛苦乃是他给予别人,现在轮到了他,他接受了这样的痛苦,也为了摆脱这痛苦而要还给赵氏失去的东西。
可是这失去的东西意味着他们的全部生命,这又怎能失而复得?若是我将赵武寻找回来,仅仅意味着赵氏宗族新的开始,从前的一切已经失去了,只有这根脉还得以保留。幸亏在一个夜晚,一个梦侵入了国君的睡眠,它用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天意,提醒国君所欠的债务,这债务已经要压垮国君的性命。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不得不用尽办法去弥补。这个梦是来自上天还是来自他自己?若是来自上天,说明神已经有了安排。若是来自他自己,说明他自己的灵魂里已经住满了讨债者。
我看见国君虚弱的样子,甚至开始同情他了。他的虚弱不仅是他的外表,也不仅是他的身形内外,而是他的心已经虚弱不堪,他的灵魂已经虚弱不堪。他不是经不起自己内心追忆的折磨,而是经不起来自灵魂里的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的折磨。从他杀掉赵氏宗族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带着鲜血放到了他的灵魂里,然而他并不知道。鸟面人的形象就是从这鲜血里生出来的,他穿过了他的身体,进入了他的梦。他拉着他的胳膊,要将他拉到自己的洞穴里。那里是无限的黑暗,除了黑暗还是黑暗。
这个世界不能没有黑暗,不然光明又怎样显现?但处于光明中的人对黑暗充满了恐惧,他不敢接受黑暗的馈赠。就像他的梦中所展现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挣扎,不断地挣扎。一个睡眠中的人和一个清醒者乃是同一个人,但睡觉的人却不能理解清醒者,清醒者也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梦中人。因而他原本是两个人,两个不同的人,而其中的一个遭遇折磨的时候,另一个却充满了痛苦。这样的痛苦却让睡梦者突然清醒,转回自身。可是他怎会知道自己的真身又在哪里呢?
这将使人感到困惑,这困惑将探入最深的黑暗,那是不可知的地方。他将搅扰人的记忆和生活,他将用绝望和恐惧改变原先的想法。国君尽管想掩饰自己的谎言,却不能掩饰自己的困惑。因为这困惑透露了他内心的真实。他说,你要尽快找到赵氏孤儿的藏身之处,尽快找到程婴,尽快将他们带到我的身边,让我看见他们。不然我就要死去了,你要拯救我,你要将我梦中的黑暗驱除干净,让我能在睡眠里安宁。
我答应了他,因为这也是我的想法,我终于可以让我的承诺得以实现,我可以安抚死去的赵朔了。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他的灵魂又在哪里呢?我相信,他不会离开太远,因为他要看见自己的儿子出现在朝堂上。也许他就在我的身边,我身边有着无数的事物,他就藏在其中。也许一片飘零的落叶中就有他的眼睛,也许一粒尘埃里就有他的眼睛,也许一个飞蛾里就藏着他的灵魂,他用飞蛾的翅膀不断扑着面前的灯焰,他不甘心就这样结束。他并没有远离,而是在生活里不断盘旋。
国君说,这件事情不能让屠岸贾知道,不然就会引发叛乱。我还不知道群臣是怎样想的,也不知道民众真实的想法。所以你将赵氏孤儿赵武找回来之后,要藏在我的宫中。当人们前来问候我的时候,我就让他和众臣一个个单独见面,这样我就能掌控大局。若是突然将赵武带到朝堂,可能会引发各种想不到的事情。我说,好的,我现在就去寻找,我相信一切都会照常进行。因为朝堂上的众臣都是想念赵氏的,民众也是这样,赵氏的仁德,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赵氏宗族的光一直照着,每一个人都能看见自己心里的东西。
路途真是太遥远了,我在春风里向着远处进发。我知道程婴藏在一座山的深处,也知道他奔逃时候的方向,可是我到哪里去寻找他呢?临行的时候,程婴告诉我,他会在路边留下记号,到时候就按照这记号寻找他。多少年过去了,那些记号还在吗?程婴和赵武还活着吗?我出了都城,就仔细地察看路边,他会将这记号留在哪里呢?我坐在一块石头上苦思冥想,回头的时候,豁然看见身边的一棵大树上有着深深的刀痕,那个刀痕指向了前面的方向。尽管已经很久了,那刀痕已经开裂,已经变得比原先要粗糙和更为深长,但那就是程婴的记号,因为它绝不是寻常的疤痕,它似乎是一个字,好像是一个赵字。
我找到了,找到了深藏在时间里的秘密,一个精巧的、令人震惊的秘密,一个让人感到既苦涩又愉悦的记号。这个字被时光扭曲,被雨雪折磨,也因大树的生长而生长,它已经长大了。它被注入了更多的不幸和苦难,也被注入更多的血泪,它凝聚着赵氏宗族的血,凝聚着万物的哀伤,它在刀痕中成长。我突然从这个字里看见了赵武,看见了赵氏的后嗣,也看见了程婴和赵武活着的形象。是的,他们仍然活着,必定活着。我的双眼一下子涌出了泪水,我用手不断地擦着泪水,但这泪水却越擦越多。
跟随我的御夫来到我的身边,问我,为什么这么忧伤?我说,我看见了赵氏孤儿,也看见了他死去的父亲。他又问,我怎么没有看见?我说,因为他们被刻在了大树上,因为大树活着,所以一切都活着。是的,我从一棵树上看见了他们,他们和我们一样,经历了十几个春秋,也经历了无数风雪。他们的果子悬挂在树枝上,他们的叶片飘落又重新萌发,他们活在一个让我悲伤的刀疤里。
我登上了车,沿着刀疤指示的方向前进。车轮带着我的悲伤转动,马蹄踩踏着春天的路,这仍然让人感到荒凉的路,也在一个深深的刀疤里。或者说,这乃是树上的刀疤的延伸,它一直通往深山。接着我不断看见树上的刀疤,我知道,我距离他们越来越近了。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我来到了一座山前。在一条小路的前面,我看见了最后的刀疤。这是程婴留下的最后一个记号。我似乎已经听见他们的呼吸了。
我将马车弃置在一边,沿着这条小路开始徒步攀登。山势越来越险要,两边的密林重合在了一起,除了鸟兽的痕迹,已经看不见人的踪迹。鸟儿一群群在树上欢叫,我穿越这密林的时候,它们又像乌云一样飞起,遮蔽了我头顶的天空。接着我听见了溪水的声息,它发出了细小的哗哗哗的流淌声。一道深深的沟壑挡住了去路。就在这时,我看见对面的山坡上有一座农舍,屋顶上冒着炊烟。农舍前似乎有两个人影,他们很小很小,看起来并不是真实的,他们在若隐若现中飘忽不定。
我想,我找到他们了,那两个人必定是程婴和赵武,不然什么人会在这样的地方居住?我走下了山沟,趟过了溪水,沿着一条弯曲的山路向上走去。这条小路一定是他们踩踏出来的,他们需要来溪水旁取水。我已经从这小路上看见了新的脚印,也许这是他们刚刚留下的。这十几年来,他们是怎样生活的?程婴真是一个非凡的志士啊。他将一个婴儿培育为一个成人,这将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心力?
我的身体在渐渐上升,一点点接近生活的真相。当我的头在山坡上露出的时候,我的目光看见了他们。一个老人和一个少年,他们衣衫褴褛,手中拿着木棍,敏捷地跳跃、挪动着双脚,这是程婴在教练剑法。两个人就像两只鹰在腾空盘旋,一会儿扑在了一起,一会儿又分离开来。他们的身上好像有着一对黑色的翅翼,山风将他们身上的衣缕不断掀起,手中的木棍不停地交织在一起,发出了沉闷的碰撞声。
终于他们停了下来,坐在屋前的石头上低语,交流着练习的心得和秘诀。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我从他们的样子可以推测他们所说的话。休息了一会儿,他们就站了起来,开始教习箭法。他们举起自制的弓箭,又在大树上一些细小的树叶上涂上了黑点。这些树叶萌发不久,还没有长成真正的叶片。然后他们拉开了弓。程婴先试射了一枝箭,箭将那片树叶击落了。然后他接着拉开了弓,他将自己手上的三枝箭搭在了弓上,然后“嗖嗖嗖”连发三箭,一枝箭追着另一枝箭,将树上的三片树叶击落了。
赵武也举起了弓箭,也连发三箭,树上的叶子掉落了很多。然后他们跑到了树下,寻找落叶中那些涂了斑点的。他们之间似乎没有多少语言,只见程婴会心一笑,点了点头。赵武放下了弓箭,他的胳膊是那么粗壮,肌肉绷紧,就像许多大蟒盘绕,可以看出他有着不凡的巨力。我大声喝彩,他们都回过头来。
程婴有点儿发呆地看了半天,才认出了我。他的泪水一下子奔涌而出,顺着他满脸的皱纹,弯弯曲曲地流淌。他的鼻翼翕动了几下,嘴角在抖动,可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我说,我们可以回去了。我说得很轻很轻,我却看见他浑身颤抖。我抬起头来,看见远处的山峦已经绿了,无数的树木就像无数的士卒,正在从山谷向着高处奔腾。一座座山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的奔腾之中,山顶的飞云也随着这群山在奔腾。
程婴的确已经变得十分苍老,他的脸上已经是沟壑纵横。然而这沟壑中似乎藏着充实的活力,这沟壑中收集了十几年的艰辛时光,汇聚了悲痛的溪水,奔涌着愤怒的喷泉,燃烧着岁月的火焰,留下了发黑的、却拥有内在光辉的灰烬。他将自己的孩子替换了这个孩子,将自己孩子的形象收藏到了这个孩子的形象里,又将自己的血泪注入了这个幼小的灵魂。他和这个孩子一起,随着飞云和群山在时间里奔腾,又在奔腾里煎熬和等待。
而赵朔的儿子一天天长大,他的血脉里流淌着残酷的血泪。他的生活一开始就是苦涩的,他们就在这没有人烟的地方生活,孤独、悲愤、寂寞地等待,灌注到了每一个单调的脚印,从山下走到了山上,又在山上的云雾中被遮没。太阳从自己的肩膀上升起,月亮从黑暗里升起,漫天的星斗描绘着深不可测的未来,他们一直等待着时光的尽头,却看不见时光的尽头。现在赵武已经长大了,他是那么壮实,就像年轻的野兽,从暗夜走来,又在山上的密林间游荡。
他不知道自己与先祖的联系,却知道因为这联系而有了自己,也拥有了这样独特的命运。也因为与先祖的分离才保留了自己。他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保留自己。他的身上有着先祖的血脉,也有着先祖的使命。他在这样的孤苦之中,寻找着曾经失去的东西。可是他又怎能知道未来将怎样安排?他眼里看见的只有这山林的四季变化,看见树木在春天发芽,又在秋天落尽树叶。看见山岚从山间升起,弥漫于整个世界,又在阳光中消散。他仅仅从程婴的口中得知自己的来历,也知道这来历的意义,但从前的一切,并不在他的记忆里。没有记忆不等于没有从前。从前就在他的身形里,在他的眼神里、在他的步态里、在他的骨头里,他的每一步都携带着从前。
赵武
我没有见过父亲,也没有见过母亲。我的记忆中只有一个人,就是眼前的这个人。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说,他并不陌生,他就是我能看见的唯一的亲人。除了他,我很少见过外面的人。当然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这个人从来不会笑,但经常会在夜晚哭泣,我醒来之后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做了一个恶梦,一个可怕的恶梦,一个让他伤心的恶梦。他说总会有一个人走入他的梦,可他不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我很小的时候就跟随他到山上砍柴,他教我怎样寻找适宜烧火的干柴。秋天的时候,我们背着自己编织的背篓,将落叶收集起来,整齐地堆放在屋前,用来点燃炉灶。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开辟田地,将谷种播撒到其中,等着禾苗长高的时候拔除田间的野草。到了秋天就收割,将谷子收藏到屋子里。我们还自己制作弓箭,到山林里狩猎。他教我辨认野兽的踪迹,也分辨各种野兽的叫声,教我怎样捕捉不同的野兽以及告诉我野兽不同的习性。
他还教我剑术,他的剑术是精妙的,当他刺向我的时候,我几乎看不见他的剑从哪个方向过来,不过我们的手里并没有真正的剑,只有树枝和木棍。但我仍然可以从他手中的树枝上看见闪烁的剑光。他将一根木棍拿在手里,挥舞起来的时候,就像手里什么都没有,只看见他的影子在后面腾跃,好像飞翔的猛禽。他也教我怎样射箭,怎样专注于前面的目标,怎样在一瞬间捕捉跳跃中的猎物,将弓上的箭发出去。
在我看来这个人无所不会,无所不能。我们一起去泉边听泉,并辨别各种细微的声息,即使是一只飞虫从旁边飞过,都要听得见。他还给我讲述各种争战的故事以及上古传下来的神奇兵法。他说,我们没有战车,但要学会驾驭战车,还要让每一匹战马都听从你的命令,也要让它们和你的心相通,你只要将缰绳轻轻一抖,它就能领会你的旨意。他还说,人与马匹之间,就像人与神灵之间一样,要学会倾听和领悟。
可是我学这么多事情要做什么?我在这茫然中练习,他不断给我演示。一次,我忍不住对他说,你教我的乃是人间的事情,我们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里,学这些有什么用呢?他沉默了,就像一块石头一样站立在一棵树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开口说话——他说,我该告诉你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你是谁,也要告诉你我是谁。我不是你的父亲,你的父亲已经死了。我是你父亲的仆人,也是你的仆人。我服侍你乃是服侍我的主人。我从你的身上看见了我曾经服侍的主人,也看见了我身上的光。
他说着,开始抽泣,开始流泪,就像我在夜里经常听到的哭泣。我又问,你在梦中见到的是谁?他给我描绘了这个人的样子以及他的每一个动作。我说,这不就是我吗?我不仅在白昼让你操心,还在夜晚的睡眠里不让你安宁。他说,我梦中看见的好像是你,也好像是你的父亲。你们在我的梦中是分不开的,你们原本应该是一个人。可是他已经被杀掉了,你却留下了,我将你带到这深山老林,就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
我说,我不需要知道一切,我也不想在你的梦中,因为那会让你痛苦。我不想做任何让你痛苦的事情。我在你的身边是快乐的,可是我的快乐却加重了你的痛苦。所以我不想知道从前的事情,从前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乃是生活在现在,而不是过去。可是现在我是多么满足,和你在一起,我所要的一切都有,我唯一不想要的,就是你的痛苦。
他突然愤怒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愤怒。我只是见过他的悲伤,却没有见过他的愤怒。他脸上的皱纹顿时扭曲为一条条凌乱的沟壑,他的愤怒顺着这沟壑上升、下降、飞跃和盘旋,我感到就连这愤怒都是充满了痛苦的,因为他的一切已经被痛苦所浸泡。他说,你不属于现在,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逃脱现在。我们都是被现在所囚禁,我们为什么要安于被囚禁的日子?我乃是因为曾经发生的事情,才带着你离开了从前,但是我乃是为了你的将来,我所做的都是为了你的将来。你的将来也不是属于你的,而是属于那么多死去的人,里面有你的父亲,所以我不能将你和你的父亲分开,你的形象里有你父亲的形象。你属于复仇,你属于赵家宗庙的香火,你属于你的不曾见过的先祖,你不属于你。
——神灵护佑你,先祖护佑你,你的父亲护佑你,都是为了一个长远的繁衍,长远的谋划。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他转瞬即逝,就像我们在这山间所看见的树上的叶子,但因为大树的原由,叶子会凋零也会再次滋生。你就是这树上的叶子,你乃是因为大树而来,也为了大树而去,你不属于你自己,却属于这大树,是大树的一部分。你是我的主人,但大树是你的主人。这就是我将你引领到这里的原因。
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愤怒,也第一次听到他愤怒的言语。他用这样的语言告诉我是谁,也告诉他是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独的生命就可以说明的问题。因为没有单独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追寻往事的结果,都是往事的叶子。这叶子只是在树上才是叶子,离开了大树,叶子就会沦为烧火的柴草,就会默默地腐烂,成为泥土的一部分。我以为自己只是属于自己,可是我知道了我的身世,就知道了我的从前。尽管这从前不在我的记忆中,但他仍然在我的血脉里。我的心,我的身形,都是往事的化身,除了往事我还有什么呢?因为我就是往事,就是往事的绵延,就是活着的往事。
往事乃是带着血的往事,所以我的身上、我的心上都浸满了血。我乃是用血和起来泥巴,我的身形乃是被这血的往事所捏制。所以我成为了这个样子,也必定成为这个样子,不然我又怎么认出自己是谁?我的面孔上有着我的父亲的面孔,所以我一次次进入这个人的梦中。这个人说他是我的仆人,可在我的心中,他就是我的父亲。一个父亲就是他的儿子的仆人,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儿子,可是我难道不是我死去的父亲的仆人吗?难道不是我眼前的这个人的仆人吗?若是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我,不会有我的现在,我也不会明白生活的意义。
我原以为将在这深山里度过一生,但终于知道这深山仅仅是藏身之地,仅仅是为了走出深山的踏脚石,仅仅是为了渡河而建造的渡船。我终于知道了,我不是为了在这里,而是暂时在这里停留。我原本就在别处,现在我所在的地方,乃是别处的栖息地。那一夜,我没有睡着,我辗转反侧,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我现在是多么安心,我的日子是多么富有,可是未来又在哪里呢?它就像星辰那么遥远,我的手触摸不到它。
有一天,我正在和我的养父练习箭法,突然听到一个陌生人的喝彩。他衣冠楚楚,显然是来自高贵的家族。他打破了我的宁静,将我的日子推到了另一个地方。我知道这个人叫韩厥,是晋国的卿大夫,也曾是赵氏的家臣,我的父亲在临死前曾将我托付给他,我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现在这个人出现了,他说,晋国的国君已经悔悟,已经知道我还活着,他要将我接回去。
是啊,我从来就不属于自己,我跟着别人来到了这里,又要跟着另一个人回去。我已经熟悉了这个地方,可我要跟着一个陌生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在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候来到这里,现在却要回到我不曾记得的地方。可他们告诉我,我应该回到那里,而不是留在这里。那里究竟有什么呢?他们说,那里有我的根,有我的仇恨,有我的悲伤,也有我的希望。那么我将抛弃这里,抛弃这里的山林,抛弃这里的农舍,抛弃这里自由自在的、白云般充满了生气和活力的日子。
我已经爱上这片山林了,我喜欢在冬天的雪地里打滚,喜欢将屋前的厚雪铲开,喜欢在一觉醒来发现屋外已经是大雪纷飞,已经是漫山遍野的雪白。我也喜欢在雪地上寻找野兽的踪迹,在这样的踪迹上踏上我的脚印。我也喜欢在春天的荒凉里挖取苦菜的根须,并在凛冽的泉水里洗净,这样的苦菜十分新鲜可口。夏天的时候我坐在树下,想着自己的心事,常常陷入了冥想,并在这冥想里感到迷茫。但这样的迷茫乃是快乐的迷茫。我天还没亮起来的时候就开始练习舞剑,我手里的木棍就是我的剑,它在天地之间回旋,扫落寂寥的晨星。
我是多么喜欢这个地方啊,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已经熟悉这里的每一道沟坎、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木,当然还有我亲手栽植的几棵树,它们已经长大了。它们比我长得更快,也长得更高。我很喜欢它们秋天的样子,满树都是金黄的叶子,还夹杂着一些红色的叶片,它们的色彩让人感到一种充满魅惑的忧伤。可是我就要告别这些熟悉的事物了,告别我的成长地,告别我的欢欣和梦幻般的过去。因为我要将自己和我所不知道的过去,更遥远的过去,联系在一起。
晋景公
赵武真的来到了我的身边,我看着这个人,这个充满了英气的少年,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他父亲的影子。是的,赵朔就是这样的眼神,就在这眼神一闪之间,我忽然觉得赵朔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感到了一阵惊骇。我对他说,当初都是我的过错,我不知道屠岸贾策动了下宫之役,他假传我的命令,不然怎么会有那样的结果呢?好在你活下来了,赵氏宗族将因为你而重新兴盛。现在你先藏在我的宫中,我让群臣一一和你见面。人们都以为你死了,可你仍然活着,这会让他们惊愕。
好了,一切都过去了,过去的归于过去,现在的归于现在。也许因为赵武归来的缘故,我的梦中,那个鸟面人消失了,他竟然无影无踪了。看来韩厥说得对,我只要将赵氏的后嗣重新扶立,让赵氏的宗庙有了香火,那么我就会好起来,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几天我的身体似乎也好多了,我不再因为噩梦而烦恼,我胳膊上的红印也消散了。我甚至觉得,我的目光也变得明亮,我照着镜子,看见脸上的晦暗正在散开,只是我的头发和胡须都白了,就像这些日子被蒙上了飞雪。
我觉得好冷啊,从病榻上坐起来,看着眼前的一切,好像仍然被黑暗笼罩,我渴望到外面去,渴望看见大的光亮,可是我的身上仍然缺乏力气,冷汗从头上流了下来。为什么我会这样虚弱?我曾经是那么强壮,可现在的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人都要老的,可是我老得太快了。大臣们不断前来探望和问候,我就将赵武叫出来,他们都感到惊奇。他们没有想到,赵氏的树上还留着最后的果子。
是啊,他们所惊奇的也是我所惊奇的,这乃是上天的安排,我又怎能违背这上天的意旨呢?我已经这样虚弱了,我对这样的安排只有顺应,要么我将变得更加虚弱。我感到神灵就在我的头顶上,他一直看着我。差不多所有的大臣都说着同样的话,他们说,我们知道是屠岸贾背叛了国君,他假借国君的命令发动了变乱,灭掉了赵氏宗族,这都是为了他的私仇才这样做。我们本想早一点打问赵氏孤儿的下落,将他请回来,可是国君却身患重病,我们只有将这样的计划搁置。现在国君的意愿乃是我们的意愿。
于是我命人围住了屠岸贾的家宅,让程婴和赵武领兵攻打。屠岸贾的家宅很快就被攻破了,程婴和赵武也诛杀了屠岸贾的宗族。报仇的已经报了,他们在杀戮中获得快意。这是彼此之间的杀戮,我只是这杀戮的观赏者。我已经看见了,人间的事情就是彼此杀戮,没有杀戮就没有仇恨,没有仇恨也不会有杀戮。这是残酷的循环,这是天意中的残忍。天上的神灵是嗜血的,神灵乃是通过杀戮来重新安排一切,我不过是借助了这样的天意而已。

我又将原本属于赵氏的封地赐给了赵武。说来十分神奇,我不仅不再有噩梦缠绕,身体也渐渐好起来了。虽然仍然感到虚弱,但可以走下病榻,到外面观赏风光了。我来到了郊外,现在的草地上已经开花,夏雨在昨夜飘洒,地上湿润的泥土将我的脚迹印在了路上。我不用别人来搀扶,自己拄着长杖在布满雨滴的草地上徘徊。太阳又一次升起,这是新的一天的开始。天上的云朵在高高的天上悬挂,而阳光从这云朵的旁边射下来,无论是远近的树木还是无数的野花都绽放着光芒。
我觉得浑身清爽,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我的身体已经被这清新的空气灌满,多少日子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愉快。我毕生所做的每一件事,就像树影一样从眼前掠过,它们飞翔着,有着各自不同的面目。我只看见了各种残酷的争斗,看见了各种虚无的结果。在这样的争斗中,争斗者得不到的,另一个争斗者也不会得到。上天似乎将一块肉放到了祭坛上,谁都想得到那块肉,可它最终仍然在原先的地方。而争斗者不仅没有获得什么,而且因为那诱惑使得自己也成为了祭坛上的肉。
我既是这争斗者中的一个,也是置身事外的观赏者。我争斗,是因为我需要从争斗中获得乐趣和利益;我观赏,是因为我同样喜欢从别人的争斗中看见我自己的争斗。现在我已经看够了一切,也看够了争斗。我在病榻上忘掉了别人,却感受到自己的珍贵。我害怕那个梦,那个梦从争斗者的暗穴出动,来到了我的梦中,也要将我拉入那样的暗穴。不,我感到了恐惧,于是我心中的自己觉醒了。我乃是在无端的梦中觉醒,而一个令人恐惧的噩梦却是一个人觉醒的开始。
在所有的争斗中,我始终占有优势。因为我一开始就站在高处,而更多的人都在低洼里。我看着他们在污泥中挣扎,看见他们在污泥中争斗,我只是站在高处向他们发出嘲笑。他们听不见我的嘲笑,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忙于争斗。当我的梦中出现了鸟面人之后,我就感到还有更高者也在嘲笑我。争斗和虚无,嘲笑和又一次嘲笑,这就是人间的生活?那个鸟面人的出现,难道就是赵氏先祖的幽灵前来扰乱我的生活?还是更高者深入到了我的梦中,戴着鸟面来提醒我?还是上天用这样的方式说明它的旨意?
总之我的确获得了一个清爽的日子。我拖曳着自己的黑影,从草地上穿过。在这里,我忘掉了从前,也忘掉了争斗的理由,忘掉了我的嘲笑,也忘掉了更高者的嘲笑。真正的快乐乃是真正的遗忘。没有遗忘又怎能获得快乐?遗忘既是快乐的理由,也是快乐的源泉。我遗忘了从前的噩梦,遗忘了曾经的杀戮,也遗忘了争斗者的血。我的眼前只有无数的野草和鲜花,只有树木的影子和我自己的影子。我从这影子里可以看见我的身形,也可以看见那黑暗轮廓中的每一个细节,我为发现了自己而惊喜。
现在我将赵氏的封地归还了赵武,我也将从前的血洗净了,所以我的面前才会有这么明亮的光。我从前是为了剥夺,现在却为了恩赐。剥夺和恩赐并没有界限,因为没有剥夺就没有恩赐。剥夺会引发仇恨,但恩赐却引发回报,它们都会令我愉悦。我就为了这样的愉悦而做我所做的,不然一个国君要在他的宝座上做什么呢?若是没有愉悦,我的日子岂不是枯燥乏味?我看见从前的仇恨已经从赵武的脸上消逝,代之以感恩者的欣喜。他年轻的表情里洒满了阳光,就像种子在春天萌芽和开花。
赵武
我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我的父亲和先祖们都曾为这个国家效力,我的归来是因为我的父亲和先祖而归来,我回到了我应该回到的地方。我曾以为要在深山里一直生活下去,可现在我的生活却发生了转折。我的秘密不在别处,就在我的身形里,在我的灵魂里,在我的父亲和先祖的灵魂里。我就带着这样的秘密在深山里和我的师傅程婴一起过日子,可现在我的秘密从深山挖取出来,放到了阳光里。
国君将我赵氏的封地归还了我,这原本就是属于我的。我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我掬起了一抔土,跪在地上痛哭失声。泪水将我手中的土变为了泥,这泥土里有着秘密的种子,有着我身体里原先家族包含的无限痛苦。我的父亲和先祖已经死在这泥土里,我手里的泥土里有着他们的一切。我已经为他们复仇,也将宗庙里的香火重新燃起。他们的形象就在这泥土里,就在那香烟里,就在我的每一个脚印里。我从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见他们,所以我痛哭失声。
我曾在深山里快乐地生活,从来没有这样痛苦,这乃是来自我的泥土的痛苦,是我的父亲和先祖们的痛苦,他们将这痛苦给了我。昨天我在宗庙举行了弱冠礼,我已经真正成为一个人,一个戴着冠冕的人,一个恢复了爵位的赵氏后人。那么我将背负着从前、背负着痛苦走向属于我、也属于我的父亲和先祖的地方。那是什么样的将来?我不知道,也无需知道,我只要知道自己的现在就已经足够。我举起镜子,面对着镜子里的这个陌生人,是的,我就是这个陌生人。我要和这个陌生人一起,走向陌生的地方。
我已经认不出自己,但我知道我所认不出的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我有了新的自己,与从前的自己已经诀别。可是我的师傅程婴却要离开我了。他向朝堂上的大夫们辞行,他说,我应该离开了,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为了报答赵氏对我的恩情,我答应将赵武抚养成人,并将他扶立为赵氏的继承者。现在赵氏宗族灭族的血仇已经还给了屠岸贾,他曾经给别人的又给了自己。行恶者必然要得到报应。赵武已经长大了,也恢复了赵氏的爵位,我就要到黄土之下与赵盾和公孙杵臼相会去了,我已经没有什么牵挂了。
朝堂上许多人都哭了,国君也劝他留下。说,你是真正的义士,我从你的身上看见了赵盾的魅力,赵氏家族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就是因为他们能认识有德行的人。你和公孙杵臼能够舍去自己的性命为赵氏扶立后嗣,也说明了赵氏先祖积累的功德太大了。我需要你这样的义士,晋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还是留在我的身边吧。你所做的,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你的诺言也已经兑现,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来留住人世间的光辉。
程婴说,我的光辉不在我的身上,而在地下的黑暗里。我已经不留恋光了,因为我在光亮里待得太久了。我要追随赵盾和公孙杵臼而去,他们也许等得不耐烦了。那里的黑暗不是漆黑,而是炫目的暗,它比光更亮,更值得追寻。在人世间,我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我留下来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赵武已经长大,他也不需要我了。我身上的本领也都已经教给了他,若是我还活着,我就成为别人的牵累,就成为他后面的暗影。我不希望他拖着这个暗影,我希望他拥有完全的光明。这样的光明,我已经隐约看见了,若是我到了黑暗里,我会看得更清楚。
我说,你不能走,我也不愿意看着你这样走,因为我从记事开始,你就在我的身边,我离不开你。我的父亲只给了我身形,给了我血脉,而你给了我一切。若是没有你,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或者已经被野兽吃掉了。现在我活下来了,成为一个人,成为赵家的继承者,这都是你的功劳。我怎么能让你走呢?我开始痛哭,我的泪水滂沱而下,我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我上前拉住了他的衣襟,我说,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从前你伴随我,以后你仍然伴随我,不然我不知道自己该怎样走路了。
他说,我也舍不得你,但我必须离开你了。当初公孙杵臼选择了死,我们已经有了约定,等事情成了之后,我就会随他而去。我对生者没有背弃约定,又怎能背弃与死者的约定?现在是我离开的最好机会,因为一切都按照上天的意旨施行。国君的病好了,晋国已经安定,赵氏家族的功勋也得以彰显,那么我还留恋什么呢?我舍不得你,是因为你一直在我的身边长大,但我怎能继续留在你的身边?你前面的路已经开通,你的步履也已经稳定,以后你不会摇摇晃晃了,我已经搬开了你前面的石头。我还要留恋什么呢?
韩厥说,我们都答应过赵朔,要将他的儿子保护好,让他能够留下赵氏的香火。现在他也可以在九泉之下瞑目了。这是多么好的事情,赵武已经是一个成人了,赵氏的爵位也已恢复,你却还要离去,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论是赵朔还是他的父亲赵盾,还是死去的公孙杵臼,一定不愿意你现在就和他们相会。每一个人都是要死的,都要最终到黑暗里去,你为什么要现在就走呢?你既然能够等待十几年,为什么不能多等一些日子呢?你既然有足够的耐心抚养赵武长大,为什么不能再添一些耐心等到自己的最后一天?
程婴说,不,我不等了,也不愿意再等下去了,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既然已经看见了结局,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决定这样的结局?我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选择,所以我才心安理得地活在人世。我从小练习各种本领,我知道我是有用的。赵盾厚待我,赵朔也厚待我,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我知道自己终会有用的。我既然选择了服侍赵氏家族,我就知道自己选择了怎样的路,也知道自己选择了怎样的结局。那我还有什么遗憾的呢?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我的孩子没有了,但我从赵武的身上看见了我的孩子,那么我要有的也都有了,我还有什么要留恋呢?我从抱着赵武离开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我从来不贪生怕死,因为我已经死了,一个死了的人害怕死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选择一个日子,一个好日子,现在这个日子来了,我又为什么要逃避这个日子?我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日子,那么我又为什么要逃避呢?我也知道,赵盾和公孙杵臼也在等这个日子,好了,我就要和这个日子一起奔赴黑暗了,这个日子只有到了黑暗里才有炫目的光辉。
然后他转向我说,你离开我,并不是失去,而是获得你应有的。我看见从前的你,也看见现在的你,当然我也看见了将来的你。你没有变,因为你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变化的只是外表。我的眼里所有的你都是现在的你,我能从现在的你的样貌里看见从前、现在和将来。所以,我看见的,以后就不需要再看见,一切已经铭刻在我的心上。你从来就在我的心上,从我抱起你的那一刻起,你就没有离开我的怀抱,没有离开我的心。我的手从来没有松开,我生怕把你掉在地上。
——现在我就要松开手了,但你仍然没有离开我的心。我会给你一件礼物,一个我的记号,让你看见它的时候就会看见我,它证明我一直还在你的身边。这就是我身上的剑。这柄剑是你父亲赠给我的,它有我全部生命的秘密。我的生命在铸剑者铸剑的时候就已经将我铸造在里面了,直到你的父亲赠送给我之后,我就知道我就是它,我在它的里面,我的灵魂在它的里面。我的一切在它的里面。
——这柄剑我从来没有用过,它一直被我珍藏,我决心只用一次,用于我生命的结束。然后我将这剑传给你。实际上,我早已将它的所有秘密都传授给了你。当我们在山间习剑的时候,你的手里虽然拿着一根木棍,但实际上你所拿着的就是这柄剑。只是你不知道自己手里拿着什么。木棍只是外表,它乃是这剑的幻化,所以你所持的木棍也是沉重的,它有着剑的分量。它似乎没有这剑的锋芒,没有这剑的光泽,可这也仅仅是一柄剑将自己的光芒和光泽收敛到了内部,让你看不见。
——这剑里不仅有我的秘密,也有你的秘密,还有这剑本身的秘密。你只要看见它的外形,就可以看见它的神奇。它不是铜,也不是木棍,更不是它所显示的锋利的刃。它埋藏着仇恨、邪恶、诅咒、荆棘、激情和爱,它们似乎充满了矛盾,却混合在了一起,牢牢地凝聚在了一起,成为一个完美的形象。它是畸形的珍珠、扭曲的错觉、怪诞的幻象,是拥有进击的力量,也拥有厌世的爱,它奇诡地分裂,又神奇地铸就自己。它不仅将自己铸造为这个样子,也将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铸造为它们的样子。它是物,也是人;它是形,也是灵魂,它不仅在人的手上,也在人的心中。它承担着无限的罪,也承担着无限的爱。
他说完后,甩开了我的手,从容地走出了国君的殿堂。这时所有的人都明白,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拦他。他的步伐是那么有力,他的脚步是那么响亮,一直走出了殿门,我仍然能听见他的脚步在回响,我站立的地面仍然在震颤。他的背影很快就从我的眼中消逝,但他的背影的背影却仍然在我的眼前晃动。他不是从我的跟前走出去的,而是像一个飞舞的神,衣袍飘动,边走边拔出了身上的剑,凌空一跃,一道红光闪耀,然后我就看不见他了。
晋景公
我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了。已经好多日子没有做梦了,这竟然让我有一点失落。尽管我害怕噩梦,但我的睡眠竟然完全空了,每日起来我都在回忆夜里的梦,但我一个也记不起来了,也许我再也不会做梦了?可若是没有梦,我又从哪里得到上天的启示?
自从程婴自杀之后,我在夜里总是睡得不踏实,我想着他挥舞剑的样子,他竟然就这样杀掉了自己。我真敬服这样的人,即使是死,也是那么完美。可是我对死却充满了恐惧,我不愿意死,因为我活着乃是快乐的,我不愿意失去这快乐。我也不敢想象死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一想到死者被重重的土所覆盖,他的肉渐渐腐烂,最后只剩下了一堆白骨,那是多么令人恐惧。在那里除了黑暗还是黑暗,什么都感受不到,什么也看不见,既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甚至连一个噩梦都没有,那是多么令人恐惧。
所以,我从前是因为噩梦而恐惧,现在又因为失去了梦而恐惧。我就被这恐惧所折磨,短暂的快乐也很快消失了。我竟然又病倒了。我又觉得浑身软弱,站立不稳,甚至迈不开步子了。我多么希望自己也像程婴一样,面对一切而毫不畏惧,可是我做不到。我虽然是一国之君,拥有一个庞大的国家,但若失去了自己,我的拥有也变得没有了。我乃是为了这拥有而活着,我不能让自己面对一个黑暗的无。
昨天夜里,我在朦胧中睡去,做了一个噩梦。我梦见一个人从麦田里拔了一把麦子,他转过脸来的时候,我吓坏了。这张脸太可怕了,一道刀疤倾斜着贯通整张脸,好像那个脸完全是拼接起来的,更可怕的是,他没有嘴,也没有鼻子,只有两只眼睛看着我。我扭头就跑,但我发现自己的腿脚在飞快地摆动,却怎么也跑不了,我感到背后有一只手伸了过来,抓住了我的衣襟……这时我醒了过来。
我的双眼直直地盯着深深的夜,盯着这没有光亮的黑暗,很久没有从惊恐中缓过来。我能听见自己怦怦怦的心跳,也听见自己大口大口地喘气。当仆人点亮了灯的时候,我竟然睁不开眼,亮光比黑暗还要刺眼。我让灯光移开,我的眼帘上的光亮变得微小,寝宫里的一切变得清晰了,可那张脸和他手中攥着的麦子仍在我的面前摇晃。这是怎样的噩梦啊,不,不是噩梦,不是从前的噩梦,而是恶梦,一个真正的恶梦……噩梦可以化解,但恶梦却不给你化解的机会……它从我的梦中把我推醒,不,在我的梦中抓住了我,我只有在醒来的时候才能挣脱。
我终于熬到了天亮,光线从狭窄的窗户射进来,柔和而温馨。可是夜间的恶梦仍然缠绕着我,我的身上就像盘了一条毒蛇,我既感到恐怖又感到被它的力量束缚。我召来了桑田巫,将我的梦告诉了他。他有着进入别人梦境的本领,所以他能够知道每一个梦的含义。他坐在那里,闭上了眼睛,他说,我要将你的梦重复做一遍,这样我就可以问那个梦中人的来历以及他的来意。
一会儿,他睁开了眼,对我说,梦中的人是蚩尤的大将,他被黄帝迎面砍了一刀,头被劈为两半,所以他的脸就成了这个模样。他来到你的梦中,拔掉了你的新麦,就是说,你已经吃不上新麦了。我勃然大怒,我说,我要将你囚禁起来,若是我能够吃上新麦,那么我就杀掉你。桑田巫说,我只是将梦中的含义与你说了,无论你愿意不愿意听我的话,都不能改变梦的意义。
我仍然十分愤怒,我说,我就要等着你的话不能应验,我要用剑把你所说的话刺穿。他说,我说的都是真的,因为我的确从你的梦里看见了这梦的意义。我的真话不仅可以抵御锋利的剑,也可以经得起烈火的烧炼。我让人将他捆绑起来,带到黑暗的牢房,让他在那里不断做我的梦,让他不断从惊吓中醒来。我先让我的恶梦惩罚他,然后用我的剑杀掉他——这是最后的惩罚。他要知道,他所说的话乃是要流血的。
过了几天,我的病情越来越重了,我只能躺在榻上,连起身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就派人前往秦国求助,我听说秦国的医缓有着起死回生的高超医术,也许他可以治好我的病。我盼望着医缓很快到来。我计算着,他应该在路上了。我又在朦胧中睡着了,而在这一次,两个顽童出现在了我的身旁,一个小孩说,听说医缓就要来了,那个人可十分厉害,他会不会伤害我?要么我们都逃跑吧?另一个小孩说,我在肓之上,你在膏之下,医缓即使来了也无用,我们还是放心在这里玩耍吧。
醒来之后,医缓果然来到了我的面前。这个人一看就相貌非凡,他的脸上有一股温馨之气,让我浑身感到舒适。他仔细看了我的脸色,让我伸出了舌头,又摸了摸我的脉象。他的手是温暖的,我能够感受到他手指上的热力。过了一会儿,他还是摇了摇头,说,国君的病已经进入了膏肓,我已经没有能力医治了。这时我忽然想起我所做的梦,两个顽童就是我的病,他们在我的膏肓之间作祟,我怎么能驱除这两个顽灵呢?
宦官
我听说国君不断做各种各样的恶梦,这恶梦已经住在了他的灵魂里。我从来没有恶梦,只有一个个好梦伴随着我。可是也有很多谜梦,我没有理解它的含义。但这并不重要,每一个日子都不需要梦的指引,因为我所做的事情都来自别人的命令。我乃是照着命令行事的,这些事情从来不会出现在梦中,我的梦与我的生活无关。
可是国君的梦和我的梦不一样,他的每一样事情都需要自己作出决定,所以一个梦就可能改变一个决定,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将因为这个梦而改变命运。可是他因为一个又一个梦而病倒了,他想摆脱这些可怕的梦,却在这梦中越陷越深。就像车轮陷在了泥坑里,越是想脱离泥坑,就会陷得越深。
我是服侍国君的宦官,我每日都想着国君的病况。我希望国君能够一点点好起来,这样我的心情就会更好。现在想起来,国君对我还是很好的,他从来没有用鞭子抽打过我,有时会骂我,但我知道他骂我的时候一定心情不好。一个人心情不好就想骂人,不骂我还能骂谁呢?我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不过我没有骂人的权利,只有将自己装做没什么事情的样子,谦卑地对待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一个梦既可以让人兴旺,也会让人毁灭。我曾听说过很多做梦的故事,一个人因为做了一个好梦,很快就会发生好事情,他的命运就会因此而发生转折,就像在密林里迷路的人,一下子看见了开阔的路,这让他的内心充溢了喜悦。而一些倒霉的人就不一样了,他因为做了一个不祥的梦,很快就遇到了烦恼,甚至引来了杀身之祸。我甚至怀疑,每一个人生来不是因为与人世间的事情相遇,而是与自己的梦相遇。每一次与梦相遇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那么我始终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梦?梦究竟是什么?它究竟是怎样进入我们的身体?又是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梦真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我们不知道它藏在哪里,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它究竟是被谁主宰着,它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样子?我们看见的梦中的样子总是千奇百怪,可我相信它有着一个本真的面目,我们只能看见它的变化,却看不见它的真相。它有时候会变得很美,有时候又变得十分恐怖,它的变化乃是为了我们每一次相遇都不能认识它。它不是像人一样,用嘴巴说出自己的用意,而是用不同的形象说出自己的用意。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很难猜测到它说的话。
更多的梦仅仅出现一会儿,它出现的本意就是为了让我们忘记它。那么,它即使不出现,我们还能记住它吗?不,它出现了,我们知道它出现了,但却忘记了它,这样它就可以不断在我们的身体里获得快乐,而我们忘记它的时候也会感到快乐。它出现的时候,有时候会给我们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更多的时候,它仅仅给我们一些片段,这乃是它懒惰的时候,那么它也会疲劳,它知道我们既盼望它,也畏惧它。
我有时候也会将我的梦告诉国君,国君会因为这梦的荒诞而开怀大笑,我也因此而感到得意。可是我现在的梦变得越来越没有新意,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了。我的职责就是让国君欢愉,可是国君已经卧病不起,他已经不可能快乐。他所关注的只有自己的病情,除此之外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
夏天的日子越来越炎热,太阳从早上升起之后,它的热力就传遍了整个天空和地面。我甚至感到我的脚印都在冒烟。据说,外面田地里的麦子已经快黄了,接近收割的季节,农夫已经开始计划着怎样将新麦收入粮仓。他们每天观看天上的云朵,希望在这样的时候有更猛烈的暴晒,若是遇到了连阴雨,那么,麦子就要在雨涝中遭殃。
我没有可能到外面去,人们所说的景象我看不见。我只是从早上到夜晚在忙碌,在国君的宫殿里转来转去。我听说,国君曾做了一个梦,让桑田巫来占卜,桑田巫说,国君不能吃上新麦了。他因为这样的丧气话被囚禁了,也许他为自己的占卜而后悔。国君说,他一旦吃上新麦,那么桑田巫就将被杀掉。
我估计这个桑田巫就要死去,因为这几天国君的病情已经明显好转,他又可以出来走动了。尽管他的身体仍然十分虚弱,但毕竟已能够自己走路了。国君问我,你最近又做什么好梦了?我说,自从国君生病之后,我就没有做过一个梦。我整天思虑着国君的身体,盼望国君什么时候会痊愈,每一夜都睡不好,怎么会做梦呢?
实际上,我的确做过一个梦,只是我不敢告诉国君。就在昨天夜里,我梦见我背着国君在登天。国君是那么轻,那么轻,我几乎感受不到他的重量。他紧紧贴在我的背上,两手牢牢地抓紧我,却像一片羽毛一样轻。我背着他一步一步地向上走着,我先是踏着一个梯子,那个梯子很高很高,一直通往云端。我背着国君,每一步都是那么轻松,几乎不用什么力气就走上了云朵。
云朵的上面一片灿烂,无限的开阔、无限的光明,其中隐隐约约有一条大路。我就顺着这条路,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一脚踏空掉落到地上。我可以清晰地看见地上的人间景象——地上的房舍就像一个个小盒子,而忙碌的人们就像蚂蚁一样。世间的东西变得那么渺小,我看不出他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可在我前面的路上,没有一丝阴影,我也看不见自己的影子。我背上的国君也不说一句话,他只是随着我向着高处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从我的脚底升起,就像烟缕一样上升,直到在我的全身弥漫。
这是一个怎样的梦?据说,一个好梦不能对别人说,一旦将自己的好梦说出去,这个梦也就破碎了。梦是脆弱的,只要稍不小心就会破碎。我一直守着这个梦,守着我快乐的秘密。所以这几天我尽管比往常还要忙碌,浑身都感到疲惫,但我有着快乐的秘密,所以我一直是快乐的。我不能将这件事告诉国君,也许他会因为我的快乐而愤怒。因为我的快乐不是他的快乐,我的快乐在我的背上,可是他在我的背上却是悲伤和绝望的。那么我背负着悲伤和绝望,却获得了快乐。这样的事情,我怎么能轻易说出呢?不,不,这个梦是这么令人愉快,我又怎能独享一个好梦呢?我听说,独享的好东西不是真正的好东西,它会在一个人的独享中变坏。我还是忍不住告诉了身边的人们。
国君想要破掉桑田巫的断言,他让人送来新麦。田地里的新麦还没有完全成熟,但他已经等不及了。人们从田里寻找成熟的麦子,送到了宫中。国君非常高兴,让人给囚禁中的桑田巫说,我现在就要吃到新麦了,你的头就要掉下来了,你是不是要重新占卜?看看你能不能活过明天?桑田巫说,梦中说的就是上天说的,上天所说的都是真的,我只是重复了上天所说的,为什么还要我说假话呢?
有人告诉我,我长得很像国君,可我却是国君的仆人,是一个宫中的宦官。我很像他的样貌,但我不是他。也许这就是我的悲哀,也是我的快乐所在。那些觉得我很像国君的人们,也不敢说出他们的真实看法,那样可能会引起国君的愤怒——他怎么能够像他的仆人呢?他会感到这乃是一种侮辱。即使是人们悄悄地说,我也不喜欢这样的说法,这不是由于我相貌的僭越,而是我更习惯于我乃是我自己。
我不认为这是对我的赞美,那些赞美者只是习惯于赞美国君,才因赞美他而赞美我。他们原本不屑于赞美我,乃是由于他们的习惯而赞美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赞美是赞美他们的习惯。难道我要成为别人习惯的一部分吗?我从来不愿意成为别人,甚至我不愿意成为国君——唉,我也不可能成为国君,我只是国君的一个仆人,一个宦官,我怎么能成为一个国君呢?
因为这样的缘由,我甚至厌恶自己、憎恨自己,然而我又满足于这样的厌恶和憎恨。我知道我是独一无二的,而国君也是独一无二的,我的痛苦来自我自己,我的快乐也来自我自己,而国君的痛苦却属于国君。不然我在梦中为什么要背着国君登天呢?这天上的景象太美好了,我不能独享这美好,我必须和国君一起享受这天上的美好,云朵飞过我的身旁的时候,也要飞过他的身旁。
可是另一件事情发生了,就在新麦做好的饭放到国君面前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腹中发胀,就让人扶着去了茅厕,结果没有站稳,掉入了茅坑。我急忙赶到茅厕,跳入了茅坑,一股臭气冲入我的肺腑,我差点儿晕了过去。我从屎溺中捞起了国君,背着他回去,为他清洗了浑身的屎溺,但他已经死去了。这时众多的侍卫捉住了我,他们说,让这个人去殉葬,听说他做了一个梦,背着国君登天,现在他的梦可以应验了。
编辑手记:
著名作家张锐锋是新散文的拓荒者和代表人物之一,《古灵魂》同样也是其对散文不断探索的力作,总字数逾百万字,本期选发了其中的部分章节。节选的章节,作家进入的是与赵氏孤儿案相关的那些历史人物的灵魂世界,在虚构与非虚构中,多重声音汇聚在一起,一个又一个古老的灵魂在自语,有着君臣的声音,有着孤儿的声音,有着宦官的声音。这些古老的灵魂在疾病、梦魇、仇恨、放逐、孤独与救赎中,追忆往事,揭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对自我进行了反思与重构,一些人在忏悔,一些人开始看透人性在权位面前的微妙变化,一些人生活在因复仇沉压于身的痛苦中,他们各自完成了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在《古灵魂》中,作家呈现的是自己的文学观和历史观,作家在写作中再次延续文史组构的传统,在写古人在历史的同时,作家又何不是在写当下,写当下很多人与古人在普通日常中的人生遭遇与内心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