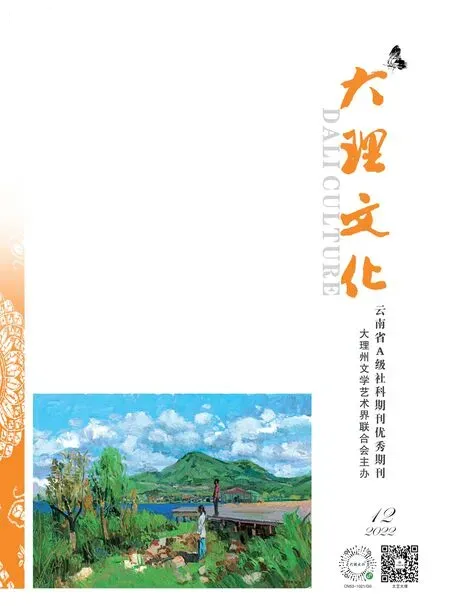与己书
●刘鹏
楔子也是倒叙
是的。我是在正月初一那天,才想起“本命年”这个词。又一个本命年,应该体验中国红泼辣的滋味。如果下一场雪,那我不仅是开在辽阔天地间的一树红梅,还是一团燃烧在白茫茫背景里的星星之火。但,问题关键是后知后觉的我与来去匆匆的光阴,不在同一个频率。
来时,狭路相逢,毫无准备。
去时,伤痕累累,意犹未尽。
你说我这是在写《本命年年终总结》也罢,或者《本命年之检讨》也行。如果说,此轮本命年就是一个人由盛而衰的分水岭,那我亦举起双手坦荡承认。尴尬在于,我是该带着劫后余生的心理来回望本命年呢,还是以幸灾乐祸的心态笑对逝去的一堆数字?
说句老实话,我真是太老实了。
这一年里,我是糊里糊涂趟过,也是惊心动魄度过。是一朵霜打过后的菜叶子,不是茄子。菜叶子黄了,但黄叶底下新添了几许沧桑的滋味。善于品味的人,能从中咂摸出快感。
我就说说这样的快感吧。这无疑是一次奇异的过山车之旅。尽管我生活的空间未变,周边的人群未变,但时间风化着一切,年轮的刻度更密集了,记忆的沟壑更宽阔了,与你的谈资也更多了一层含蓄。
怪异的耳鸣
耳朵是用来听声的。我的耳朵却有话要说。
静静听时,这声音嗡嗡嘈杂,让我烦躁难耐;故作听不见时,这声音清晰无比,仿佛在自说自话。我双手捂住两耳,两耳“吽吽”,如念佛号。
我误以为那声音在耳外,像苍蝇、蚊子,时不时挥舞手臂,做驱逐状。然而很多时候,母亲在一旁说话,我却听不清。“啊?”“什么啊?”让她再说一遍。一旦周边有杂声,即使母亲再说一遍,我也未必听得清。
时间一久,母亲觉得其中必有蹊跷。她颇为紧张,劝我去看医生。
我向来像蔡桓公,讳疾忌医。母亲说一遍,我就笑:“没事儿,可能最近工作累了,我多注意休息,估计很快会好转。”事与愿违,两个月后,耳朵里面“涛”声依旧。
有时候,我看得开,想到蒲松龄《聊斋志异》第二篇《耳中人》。秀才谭晋玄耳中有人,常于闭目养神之际窃窃私语。谭秀才不以为疾,自以为“修炼日久……莫非已得正果?”我虽不求正果,但也略有小喜,因为耳朵里的幻听现象,让我有了非非之想。在现实世界里憋闷得久了,胡思乱想也是一种解脱。
解脱,也是幻想出来的。耳中长久闹腾,我的精力逐渐无法集中,看书时,双目紧盯书籍,但心思早就离魂出窍了,手中偶尔还会翻篇,但内容一无所知。母亲见劝我不成,便让我妻子“威逼利诱”,又或者“吹枕头风”。我落入彀中,在妻子和母亲的监督下走进医院,其情状犹如胆战心惊的犯罪分子。
到了医院,交费挂号,坐等叫号,陈述病征。
陈述完毕,医生问:“有没有颈椎病?”
答曰:“有。”
“多久了?”
“两年,或者三年,也说不清,只是这两年每到夏季,总要疼几次,疼得厉害!”
医生“嗯”一声,点点头。继而又问:“有没有高血压?”
我连忙摇头。
“那经常熬夜吗?”
“天天夜不休,天天十二点后才睡觉。”母亲抢答,妻子附和。医生再次“嗯嗯”点头。
“以前做过哪些工作?有没有在噪音环境下生活过?”
我一愣,想起了十年前的工作。十年前,我在苏州一家纸厂做过两年操作工。偌大的车间内,齐整整安放着七台大型机器生产线,我负责M线的手帕纸生产。七台机器同时开工,“轰轰轰轰”,震天响地,所有噪音如雷贯耳,无一处角落安静,粉尘像皮球在轰鸣中坠落、弹起,弹起、坠落。公司每周给员工配发一副黄色软胶耳塞,但降噪功能微乎其微。但凡说话,都得高声喊叫。离开纸厂后,我慢慢发现自己的听力减弱,父亲的嗓门一向很高,但只要我们之间隔着一扇薄薄的门窗,我就听不清他说什么。我以为耵聍太多了,总想着什么时候掏掏耳朵,让耳朵也来一次清爽干净,但又怕疼,故而一直耽搁至今。
医生说这和耳屎无关,是耳鸣现象。他神情严肃,说完不再提问,全神贯注开检查项目表。母亲急了,问可有大碍,可有治疗方法。医生说:“耳鸣通常情况下有两种可能,一是内耳毛细胞缺血缺氧,二是耳神经不断受损、死亡。现在要确定哪种原因导致耳鸣,再针对性治疗。一定要及时治疗,不能再拖延了。”开完单子,吩咐我们去缴费、检查。
我心有戚戚,仿佛瞬间衰老下来,害怕悄然而至,害怕我的世界从此静悄悄。而事实上,人的衰老总是先从头部开始的。
牙齿的背叛
我的听力需要治疗,我的牙齿却无药可救。
清明节陪老婆回娘家。丈母娘知道我爱吃炒蚕豆,便好心好意买了一大袋。我见到蚕豆,如狼扑羊,张口就咬,只听得一声脆响过后,嘴就歪咧着“咝咝……咝咝”地呻吟起来,并赶忙将蚕豆渣吐出,一颗牙齿随之有气无力地落地。
这颗陨落的牙齿,毫无征兆。我急得团团转,不仅因为口腔右侧突然空洞了一片感觉不适应,还在于那颗牙齿本身——它是一颗专用来咀嚼食物的磨牙,如果没有它,蚕豆吃不起来了,肉也吃不起了,我无法撕咬,无法品味人间美味了——我是个吃货,我笔下的美食文章在各大报刊发表,难道我的吃货生涯就此打住?我不甘心,尝试着把一切咀嚼撕咬的重任都托付给左侧牙齿。不适应。我一直都使用右侧牙齿的,左侧牙齿显得力不从心,而且我也不敢过分依赖它们,生怕它们再有个三长两短,我该如何是好?
果不出我所料。几天后左侧牙齿也酝酿着罢工了。首先是在咀嚼糖醋排骨时出现塞牙缝现象,塞牙缝说明牙齿疏松,极有可能是虫蛀现象。我立即加大刷牙力度,每天刷两到三次,吃过食物立即漱口。我待它如上帝,它却待我三心二意,时好时坏。好时吃嘛嘛香,不好时就酸疼堵心。
每次牙齿疼痛时,我都渴望能够拥有一副父亲的牙齿。父亲的牙齿不甚整齐,也不大干净,常年抽烟,焦黄一片。可那确实是一口战斗力非常强的铁齿铜牙,冷热不忌,软硬兼顾。母亲常说他牙齿是“狗牙”,非但没有贬义色彩,反而还夹带着羡慕嫉妒与咬牙切齿。母亲牙齿很差,刚过六十,就不断地掉牙、拔牙、补牙,社区牙科诊所、市口腔医院、省口腔医院都光顾过了。自从我的牙齿打算告老还乡后,我常祈祷它们再坚强忍耐一些时日,好歹等我混到母亲这个年龄再退休。
想象永远美好,现实不如人意。仲夏之际,社区组织免费体检,牙科医生吩咐我张嘴,用灯照了照,说我有颗牙齿蛀空了,要拔掉。拔牙?我岂敢!我拼命护它们还来不及呢!他用木片碰了碰那颗牙齿,再次嘱咐我尽快拔掉,避免其它牙齿受影响。
没几天,那颗牙齿就落在了饭碗里。那天雷暴雨,狂风怒号,好像替我为那颗牙齿开追思会。
牙齿是人体最坚硬的部位。在我这里,它们却显得异乎寻常地脆弱,也许只是吃了一颗蚕豆,也许只是一片薄薄的木片磕碰,它们就有离开牙床、陨落草莽的悲剧。从一颗牙齿的分崩离析,我渐渐对本命年有了一种“惹不起”的慨叹。
盛大的失眠
上帝无疑是宇宙中最高明的创造者,他创造的人不仅各部位无比精确,而且十分完美。科学家发明的机器是无法与之媲美的。不过,上帝也没有能够突破时间之谜——所以无论是机器,还是人,都有着使用周期。理论上讲,在设计之初,我们身体各部位零件的使用周期都是一样的,但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以及零部件使用方式、爱护程度的不同,最终让这个周期千差万别、长短不一。
本命年,是一个带有虚构性质的词语,从身体与精力来讲,是在走下坡路。因为生命在无法阻止地滑坡,我的心绪渐渐紊乱,失眠趁虚而入。
失眠是一把专门切割时间的钝刀,它锈迹斑斑,豁口太多,更像一把锯子,它喜欢在夜晚慢条斯理地消磨时间,让人厌倦时间的漫长,痛恨失眠的残忍。然而,失眠本身与时间之间并无绝对联系。换言之,失眠不是时间惹的祸。
我曾一度与失眠失之交臂,没想到现如今它又回来了,我仿佛听到胡汉三的奸笑声,随后看到失眠丑陋的嘴脸。
也许是在二十四岁,我有过一段声势浩大的失眠。那时候,工作难觅、爱情难觅、梦想受阻,失眠席卷而至。
有趣的是,青春是可以挥霍的,我享受那种失眠。每次躺在床上,透着微弱的月光,我的脑细胞在紧张工作。我给自己设定若干个计划,在年底前要谈个女朋友,带她去海边玩,带她见父母,安慰父母紧张的心。我要写一本皇皇巨著,讲述像《哈利波特》那样神奇的故事,还要写一本诗集,要把青春的梦想完美展现。我还要有一个工作,挣足够的钱来孝敬父母,养活自己,买房买车,牵女友的手轧马路……
所有的渴望,都具有可操作性。这些都是当时造成失眠的根本原因,只要这些问题妥善解决,失眠也就无处附丽。
青春的失眠,是华丽的,正应了辛弃疾“少年未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站在三十六岁的悬崖上回头看,昔日失眠,恰恰给苍白、单调的人生增添了一抹迥异的色彩,尽管阴郁暗淡,却十分有故事。
少年情怀总是诗,中年趋于现实主义,哪敢用诗情画意来伪装?现实就是生活,生活容不得假设。中年人的失眠,往往伴随着惨痛的经历,每一夜的失眠,那才是真正的忧郁和睡不着,真实而猛烈,不再害怕爱情,全身心地忧惧晚年与健康。这个时候的失眠,关系到毕生,不容马虎。
我看得见中年的红灯。失眠如此声势浩大,生物钟无法调节它的兴衰。
我通常在妻子匀称的呼吸声中辗转反侧,摸着黑,坐起来,望着窗外,对面楼上影影绰绰有些灯光,很自然地想起过去的三十五年,从理想快速切换到现实,从孩子突然指向自己,思维有时候是跳跃性的,有时候又十分僵化,死水微澜。跳跃性的思维,让自己产生一些新的动力,不由得握拳发愿,而僵化的思绪,则作茧自缚,为情为事所困,越陷越深,爬不出陷阱,也透不过气来,一整夜都能纠结在同一个问题上,拉锯一般割裂自己。
时间就这样在思想纠缠的荒原上,燃为灰烬。我其实贪恋夜晚的甯宓与孤独。作为一个写作者,白昼喧嚣吵嚷,笔墨找不到一个切入点。夜晚能与缪斯近距离接触。他就在眼前的黑暗里徘徊,就在白色的灯火里跳跃。他是一个偷窥狂,偷窥夜晚幽灵的举止,我是他观察的对象。
失眠的夜晚写作,写出来的文字是犀利而冷峻的,字里行间有一种急迫表达的欲望。我从未抽烟,现在再也忍不住漫漫长夜的煎熬,一滴尼古丁能杀死一头牛,而一支烟的焦油含量胜过一瓶兴奋剂的威力(我固执认为),我在烟雾里脱下沉重的枷锁。
失眠,带来灵感,让我得以辨别“同情相怜”与“同病相怜”二者之间微妙的差异。
我有一位女性朋友,她常年失眠——失眠于她而言,是顽固性疾病,重于皮癣。她每年都要去心理医生那边求助、疏导。我用不着。她有几次,惶惶不安地告诉我:“我怕我迟早会死在通往睡眠的路上!这是一条狭窄、曲折、令人发疯的绝路!”我想象不到事情会如此严峻。她伸出手腕给我看,那白皙、瘦弱的皮肤上有一个伤疤,异常明显,如一把匕首扎在静脉上。她说,“我差点就走了。”“走到哪里?”“天堂。又或者,地狱。”对于天堂与地狱,我和她都持有怀疑。但,从那以后,我就隐隐担忧她。更担心那把匕首,有一天再次割破血管,引爆一个不再年轻的生命。我庆幸自己的失眠,还不至于铺平死亡的道路。
相反,伤口有了白细胞才有了弥合的可能,人生有了失眠,才有了重新解读生命与死亡的新机遇。我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我的失眠是病非病,是一道摆在我面前的门槛。我需要跨过去,冲出本命年!
怀旧没有休止符
极端。两个极端。
一方面记忆衰退,一方面过去很多没有想过的事情,又被记忆钩出来。于是我明白,记忆是具有选择性的,它比遗传基因更具理智。然而,当事人未必喜欢它们这样的特点。
我想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格格不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会选择逃离这座城市,去苏州、上海,去绍兴、舟山,去周边的省市,去乡村古镇,去亲近自然界中的山水、鸟兽、昆虫。
我与那些地方,有着渊源,不是在那里长期生活过,就是从那里路过,以一个游客身份走过那里的街巷,亲近过那里的山水草木,能够记得周庄石桥上一只挡道的灰狗,记得安昌河沿上垂挂的腊肉,记得黄浦江中起伏不定的漂流瓶,记得东极岛塔塔旅行社的胖哥与他的惆怅……
更多的时候,我通过一首老歌,瞬间陷入过往。公司常去KTV聚会。面对一群90后的小年轻,我只好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孤独地喝酒。他们拉我去飙歌。我婉拒:“我是先天性失歌症患者,实在是不会唱歌!”我真不会唱歌吗?我会唱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会唱《冬季到台北去看雨》,我会唱赵传的《小小鸟》,会唱纵贯线的歌曲,唱《倩女幽魂》,唱《东方红》,哼《沙家浜》选段。怀旧没有休止符,怀旧如跳蚤爬满了我记忆的袈裟。
城郊有寺庙,每年会开办一到两次的禅修班,我会主动报名。禅修的同时,也好躲避世俗。
过去十多年里,各种形式的同学聚会,我都是积极的参加者,我策划聚会的形式,我主动联络同学故交。今年,我出人意料地远离这些聚会,一来时间确实腾不开,二来心里渐渐对这样的聚会起毛。聚会是时间之阱,浊酒入愁肠,几家欢乐几家愁。无论是谁,都要怀旧,想起过去的事情,分毫不差,揭人伤疤,说人短处,荤段子层出不穷,记忆太公平了,竟然不曾亏欠任何一个人。
我躲避这样的局,从局内人逃出来,成为局外人。以局外人的视角观察与思考,就像具备了上帝的视角,怀旧已经被人为妖魔化。
怀旧人人有之,上了一定年龄,总会有一些心结无法解开。但我不愿意被别人的怀旧裹挟,在一片唏嘘、欢呼、揶揄之间波涛汹涌,跌宕起伏,身不由己。我的怀旧,非常私密化,只属于我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
最近,我的书房里添置了一件时髦的器物——倒流香炉。燃一炉香,看白烟袅袅,时云,时雾,时升,时落,时断,时续,历历往事随之沉浮辗转。
无须矫情。我承认我早已中了怀旧之蛊,毒侵五脏六腑,化作骨中之髓。只是跌入本命年之后,这怀旧愈发显得醇厚,如老酒、如普洱,自斟自饮,自得其乐。
倘若能化作只言片语,行于笔尖纸上,也是一件悲中喜乐之事。
契诃夫曾有一个著名的发问:“为什么恰恰到了老年,人才注意到自己的感受,批评自己的行动呢?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就不管这些?到了老年,就是没有这一套也已经够难受的了……年轻的时候,整个生活不留痕迹地滑过去,几乎没触动思想,可是到了老年,每一个极小的感受都像钉子那样钉在头脑里,引起一大堆问题。”怀旧,是一种解脱。建立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可以看出生命是具有自我修复功能的。
让“一大堆问题”来得更猛烈些吧!我在将老未老的十字路口,已经做好了巡天一看彩虹万里的准备。
试图与死亡签署一份密约
10月的某一天,早晨骑车去上班,不小心被一辆电动车撞上,左手小拇指受伤,至今还疼着。左脚脚踝部分也随着季节转换而出现疼痛。颈椎病在今年夏天又复发了一次。我想重回母体,让母亲的子宫再次孕育一个新的、健康的胚胎,我想再次劳烦母亲经历十个月的短暂而漫长的煎熬,将我分娩出来,许我呱呱落地。我拥抱世界,爱拥抱我。
然而,这样的幻想,仅出现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生命只有一次。所以面对疾病、困境的时候,每一步都值得谨慎与严肃。
我经历了疯狂成长,经历了肆意挥霍,如今走向青黄不接的中间地带,这是一个危险的境地。前有天堑,后有鸿沟。我知道,我可能是个特例,经历不同的人,在同样的年龄段里,未必会出现我这样的情况。我面临的现状,看似尴尬与不顺,但我感谢这一切的遭遇。
……
本命年是什么?我仿佛再次听到耳朵里出现了嗡嗡声,难道真有一个人在我耳朵里与我窃窃私语么?他是谁?他说些什么呢?他是给我紧迫感,让我抓紧时间再逐梦而行,还是让我顿悟人生处处不尽如意的真谛?或者一切都不是。那又会是什么?
我是在害怕。但也是在享受。
也许,每一个本命年,不仅是承上启下的一个轮回,也是老天给我们敲响新一轮警钟的时候,也许你粗粗看着,仿佛一切都不够完美,而实际上却在残缺的生命背后,暗藏着一个更为美好的开端。
那么,我很乐意和死亡签署一条密约。里面要约法三章,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一切美好,才刚刚开始。
谁也不会愚蠢到与死亡签署一份合约。我是个例外。
人老话多式的自嘲
毋庸置疑,我控制不住地向你透露了太多尴尬之事。本该在此戛然而止,或许还能使你馈赠我一点儿唏嘘、共鸣。遗憾的是,人老话多,是我们这些性情中人惯犯的错误。
念大学时,那位高数老师不一天到晚说:哎,树老根多,人老话多?我从那里没有学会一导二导,只学会了人老话多式的自嘲。按理,我还没有老,我母亲还健在,按照联合国最新的说法,就连我母亲也算不得老年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奔老一族”。母在,不言老。我时时提醒着自己。
庆幸在许多关键的时间点,我遇见了许多人、许多事。身体发肤的疾苦,精神意志的摧折,在很久以前,就有圣人以身相劝。于是,我相信了他,也相信了自己。人的一生就该如水,溅落一地,因为只有让它破碎,才足以映照更多的阳光和月色,听到更悠远的源自地脉的潮涌和穹窿之上的天籁。
朋友,我一直喜爱苏东坡的诗词,因为他确实放达豪迈,看得开,也吃得开。我们这些寻常百姓,能用文字记述自己的喜怒哀乐,应当庆幸知足。
你说是不是?人生至此,不妨浮一大白吧。没有花生米、茴香豆?那就掰一段时光,下酒。后面的路还长着呢,只有喝到尽兴处,才明白何谓柳暗花明,何谓无心插柳,何谓人生况味,又何谓“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编辑手记:
疏雨与我们分享了她与书的故事:从图书馆借书、向老师借书、旧书摊上淘书、书屋里蹭书、热衷逛书店以及因热爱戏曲而写书。正如她自己所言:“每个人都是一本有故事的书,人和书的每一次相遇都开启一段新的旅程。”疏雨与书的每一次相遇,都是一场未知但充满惊喜的旅程,在这些旅程中,她将灵魂舒适地安放于书架制造的无限延伸的空间里,或是临摹着书中绝美的画景,或是制造着一个个蹭书的小把戏,或是因爱书而得到好心人的赠书……借由书籍,她与他人、与世界产生着美妙的际遇,由书之内的美发掘和创造书之外的美;在书的浸润之下,她也成为一本有故事的书,感动着与她一样深爱书籍和阅读的人。
朱金贤的《草命》通过讲述自己艰难求学、摆脱贫困命运的故事,反映了大多数像他一样“出生草芥”的来自偏远贫困山区的农村人的奋斗史。“狗尾巴草”贯穿全文,具有多层次的象征义。第一层指“生于草野民间,一生卑微如草”的众多山里人。作者在描述这层含义时,将自己和亲人比作草,比如说自己从小“像草一样生长,视野尚未触及远方”,说爷爷的手指像“风中颤巍巍的草”,至此,狗尾巴草在作者心目中都作为一种消极的、负面的喻体出现,暗示作者小时候对狗尾巴草的厌恶。直到后来,作者上学之后,对狗尾巴草的态度发生了质的转变,作者意识到狗尾巴草的价值,并将在异乡打拼、奋斗的乡里人比作狗尾巴草。狗尾巴草的第二层含义便是象征乡里人“柔弱却坚韧,平凡而勇毅,顺势而动”,尽管“命如草贱”,但只要保持信念,奋力生长,无论身处何方,都能闯出一片天地,实现自我价值。
又一年即将过去,刘鹏在《与己书》对过去一年的自己进行总结,既完成了一场与自我的对话,也在这场对话中不断适应着变化的自己,与自己达成和解。随着年岁渐长,耳鸣、牙病、失眠、怀旧……这些词语一一在我们身上应验,在一边阅读一边对号入座的时候,感叹着“我不再年轻了”以及“年轻真好”……然而作者并未停留在原地,而是在“与死亡签署密约”的无畏和时刻自嘲的醒悟中,明白成长的奥义:“人的一生就该如水,溅落一地,因为只有让他破碎,才足以映照更多的阳光和月色,听到更悠远的源自地脉的潮涌和穹隆之上的天籁。”一年又一年,时间赋予我们的不仅有日渐衰老、病痛不断的躯体,更有豁达、乐观、自信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