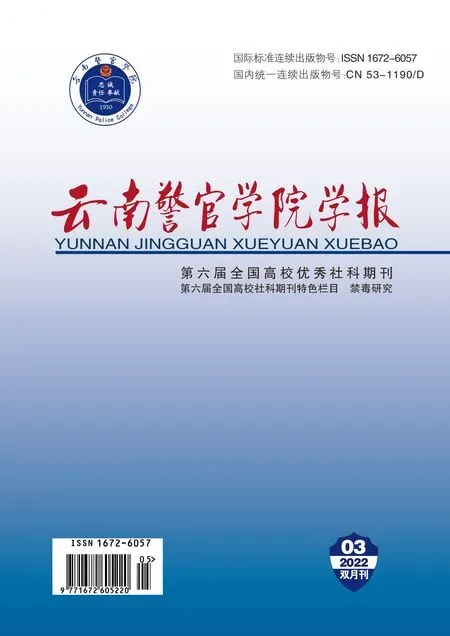网络恐怖主义言论刑法规制的难点与完善
李梦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一、引言
网络恐怖主义的发展成为了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新症结。恐怖主义的传播形式从19世纪“以行动做宣传”恐怖主义理念为代表的“以身试法单向型传播模式”,到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9·11”事件后达到高潮的利用现代媒介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暴力活动推广的“媒介导向型恐怖主义模式”,再到如今以恐怖组织与受众人群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互动为主要传播途径的“社交媒体互动传播模式”,“言论”在互联网的匿名性以及群体传播模式的影响下成为了恐怖主义活动的重要方式。网络恐怖主义言论虽看似只是互联网海量信息中的一小段文字、几张图片、一些音视频信息,却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可承受之轻”。2020年2月27日,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国际社会需要再次承诺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无论其动机如何。出于种族、族裔、政治和意识形态动机的右翼和至上主义团体诉诸恐怖主义策略,特别是针对少数群体采用这种策略,其带来的威胁日益增加,这越来越令人关切。仇外心理、反犹太主义、反穆斯林仇恨、偏见和贬抑女性的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行为蔓延,令人震惊。”(1)联合国系统在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方面开展的活动:秘书长的报告(A/74/677)第11条[EB/OL].[2021-2-23].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0/033/22/pdf/N2003322.pdf.
网络恐怖主义言论主要包括煽动或宣扬(美化、赞美)恐怖主义、鼓励助长恐怖主义罪行、鼓励参与或指示支持恐怖组织的活动、为实施恐怖主义犯罪提供指导方法或技术等内容。一般而言,恐怖分子首先在社交媒体网站、公共论坛等平台上煽动他人进行恐怖袭击,包括提供如何造成最大伤害的详细指引,在所煽动的暴行发生后,再发布进一步的宣传型言论美化以上行为并鼓励其他人效仿。网络恐怖主义言论对社会秩序的强大破坏力不在于所载信息的形式,而在于开放式的互联网环境中传播的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情感的激烈表达而导致的潜在恐怖活动的可能性。“宣传(propaganda)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说出口的东西,即由精妙、敏感和潜在的情感挑衅所引发的巨大想象。”(2)BEN S. Speaking of Terror: Criminalising Incitement to Violence[J]. UNSW Law Journal, 2005(03).恐怖分子利用言论方式扩大恐怖主义影响,刺激受众的感官神经,软化人们的心理防御,使之逐渐失去对暴力恐怖活动残忍效果的敏感度,变得麻木不仁,甚至开始同情恐怖分子或支持、参与恐怖活动。“言论”的使用是网络恐怖主义在全球造成广泛影响的主要因素,也是世界各国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主要症结。
刑法作为规制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最后手段,必须考虑到言论的性质所带来的价值取向、行为认定、入罪判断以及传播媒介等问题。当前我国相关刑法规制散见于煽动、教唆、帮助、预备等类型的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犯罪之中,相关研究也并未认识到“言论”这一特殊传播方式所导致的现有刑法规制的缺陷。本文通过梳理网络恐怖主义言论刑法规制的主要争议,借鉴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世界主要国家刑法在解决相关问题上的立法动向、价值观念、入罪认定以及犯罪控制等内容的经验,为完善我国网络恐怖主义言论刑法规制提供参考。
二、网络恐怖主义言论刑法规制的核心争议与域外经验
虽然当前世界各国刑法均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规制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相关犯罪的规制措施,但将网络恐怖主义言论作为刑法规制的对象,需解决犯罪构成上的几个主要问题,即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分类、与言论自由的关系、言论入罪的条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等。下文分析网络恐怖主义言论刑法规制所涉以上重点问题的域外经验,梳理可资借鉴或不被采用的原因,获得我国刑法规制网络恐怖主义的启示。
(一)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定义
“网络恐怖”(cyber terror)一词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首次出现,加州安全与情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里·柯林将网络恐怖定义为“控制论与恐怖主义的融合”(the convergence of cybernetics and terrorism)。(3)BABAK A, ANDREW S, FRANCESCA B. Cyber Crime and Cyber Terrorism Investigator's Handbook[M]. Boston: Syngress, 2014:11.2001年,信息安全专家多萝西·丹宁教授将网络恐怖主义定义为:“对计算机、网络及其存储信息发动非法攻击或制造攻击威胁,恐吓、胁迫政府或其人民,以促进特定政治或社会目标的实现。”(4)DOROTHY E D. Is Cyber Terror Next?[EB/OL], 2000-11-01, https://items.ssrc.org/after-september-11/is-cyber-terror-next/.2002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定义网络恐怖主义的概念为:“利用计算机网络工具关闭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如能源、交通、政府运行)或者胁迫、恐吓政府或平民的活动。”(5)LEWIS J A. Assessing the risks of cyber terrorism, cyber war and other cyber threats[M].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2004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将网络恐怖主义定义为:“以影响某一政府或人民服从特定政治、社会或意识形态议程为目的,利用计算机和电信能力实施的造成暴力、破坏和(或)中断服务,在特定人群中制造混乱或对不确定多数人造成恐惧的犯罪行为。(6)HENYCH M, HOLMES S, MESLOH C. Cyber Terrorism: An Examination of the Critical Issues[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Warfare, 2003(02).然而,以上定义虽然强调了网络恐怖主义传播特定政治、社会或意识形态的目的,却未能区别于网络激进主义(cyber activism)和网络极端主义(cyber extremism);虽然指出了非法攻击、攻击威胁或恐吓、胁迫等手段,但并不能看出此种活动与网络犯罪(cybercrime)的显著区别。“网络恐怖主义”这一概念似乎成为了恐怖分子和恐怖集团在网络空间开展活动的代名词。
由于网络恐怖主义的概念模糊,恐怖分子利用网络空间进行的指挥和控制、全球信息交流和规划、筹款以及试图增加其支持、合作、宣传、招募和信息传递从而影响公众舆论的活动(7)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Counterterrorism[EB/OL], Jihadists and the Internet (2009 update)[ 2010-05-01]. http://www.fas.org/irp/world/netherlands/ jihadists.pdf.,即网络恐怖主义言论活动,并未得到各国刑法具有针对性的回应,而是根据行为的不同被归类于仇恨言论或传统犯罪的网络化进行处理。因此,刑法规制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第一步,就是要将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表现形式进行提炼,以此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规制方案。本文认为,网络恐怖主义是指利用信息传输、信息系统和网络的完整性、保密性或可用性所进行的,以促进政治、宗教、种族、文化或意识形态为目的,实施、准备实施或威胁采取破坏社会秩序的行动、在全部或部分公众中制造恐吓或恐惧气氛或影响某一政府或某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政治决策,严重损害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和公共安全,导致国家和社会受到的严重经济损失或者严重损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行为。网络恐怖主义言论作为“网络恐怖主义”行为的“利用信息传输”侧面,强调恐怖活动组织和恐怖行动个人为了促进特定政治、宗教、种族、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实现,通过恐怖活动网站、暗网和社交媒体等网络媒介发布煽动暴恐袭击、助力恐怖活动、制造集体恐慌、加速极端化进程等言论的行为。网络恐怖主义言论具有言论与行为的双重性质,从行为上可划分为煽动(鼓励)、宣扬(赞美)、恐吓(编造传播恐怖主义虚假信息)和转化(教唆、招募等)四种主要类型。(8)李梦琦.网络恐怖主义言论治理的现状、阻碍与完善[J].公安学研究,2021(01).
(二)“安全价值优先”下的人权隐忧
刑法的价值——安全与自由体现着刑法的终极追求,两者间冲突与平衡一直是刑法研究的争论焦点,在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刑法规制中也不例外。自“9·11”事件后,世界各国恐怖犯罪相关立法侧重保护安全价值。英国《2006年反恐怖主义法》规定了鼓励恐怖主义罪和传播恐怖主义宣传品罪,并将赞美恐怖行为或预备实施恐怖行为也纳入刑法打击范围,2019年《反恐怖主义和边境安全法》中又将表达支持恐怖组织的言论行为也认定为恐怖犯罪。法国在2016 年颁布的《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及其资助、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及加强刑事诉讼保障法》中增设“恐怖主义活动煽动罪”(9)凌胜利,胡碧钰.21世纪以来的法国反恐政策研究:观念、体系、举措与效果[J].公安学研究,2020(04).等等。以上国家通过增设新罪回应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危害,体现了对安全价值的追求。然而,安全价值的优先必然带来挤压人权的隐忧,“网络恐怖主义言论”这一命题本身更是体现了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这一公民基本权利与相关言论所威胁的社会安全的冲突。那么,刑法规制网络恐怖主义言论时,究竟应该在安全与自由之间做何取舍?
以美国为例,美国法律保护言论自由,但也在近年来加强了对“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规制。2016年以前,基于言论自由的宪法价值,即使是恐怖组织或恐怖活动分子,也有法定的表达权。美国法院根据“布兰登堡规则”,要求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只有在能够证明某一明显且即刻的具体言论可能导致严重的颠覆性犯罪,甚至是“迫在眉睫”时,才存在对其进行刑法规制的可能性。同时,由于美国法律只将对其国家安全有威胁的活动组织定义为恐怖主义组织(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简称FTO),如果一个组织为美国服务——不管它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多“恐怖”,均不认为是恐怖主义。这种对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放任态度使得美国的公共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例如,某条宣传招募恐怖分子的信息,既无“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又非导致危险“迫在眉睫”,但其此类言论依然具有对公共安全的强烈威胁,根据美国法律确不能有效规制。此外,正是因为互联网发展前期美国对言论自由的过度保护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恐怖主义言论泛滥,世界主流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均为美国企业,互联网的无国界性使得这些媒体上的恐怖主义言论在全球造成严重影响。正因如此,恐怖分子在社交媒体上的出现频率激增,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了巨大挑战,仅2016年就有50余人丧生于恐怖袭击。2016年后,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社会危害性倒逼美国的刑事立法。《美国法典》第18章第2339A条将为被认定的恐怖组织提供物质帮助的行为视为犯罪,并将“专业意见”纳入“物质帮助”;2016年9月,美国国会颁布《反恐怖主义赞助者法》(the Justice Against Sponsors of Terrorism Act),规定了以援助、教唆或共谋方式使他人犯下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公民的刑事责任。此外,美国法院明确认定言论自由条款不保护煽动恐怖阴谋的言论,包括与恐怖作战计划、恐怖技术信息如制造炸弹的说明)、恐怖资金转移相关的言论以及旨在影响信仰和行动的言论,即所谓的恐怖招募演说或恐怖宣传言论。
正因为秉持自由价值的美国在网络恐怖主义言论刑法规制上付出了惨重代价,在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相关刑事立法中,强调安全价值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法治反恐模式”下的刑法规制作为网络恐怖主义言论治理的重要手段,若其背后的立法价值天平偏向自由一边,必然会导致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治理底线出现漏洞。世界各国刑法之所以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问题上秉持前置化的立法趋势,正是考虑到在治理网络恐怖主义言论中推进刑法“防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此外,扩大网络恐怖主义行为的打击范围,看似是出于社会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言论的限制,实则也是对人权的保障。言论自由所追求的是人的自我实现,与刑法的保障机能相一致,也就是说,刑法规制与言论自由的目标在“人”这一最终追求上达成了共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律不应该被看作‘和自由相对的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1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三)增设抽象危险犯的规制优势
各国在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刑法规制中对于安全价值的侧重在立法中体现为通过增设抽象危险犯打击恐怖主义的预备行为。以英国为例,《2000年反恐怖主义法》(Terrorism Act 2000)通过“前兆犯罪”(precursor crimes)规定对恐怖主义言论犯罪进行预防。《2006年反恐怖主义法》为特别规制网络恐怖主义言论,将《2000年反恐怖主义法》第58条第(1)款将信息记录扩大至电子数据,同时增设鼓励恐怖主义行为罪、恐怖主义宣传品传播罪(offence of dissemination of terrorist publications)和利用网络实施出版、发行或者传播含有鼓励恐怖主义内容的宣传品罪。其中,鼓励行为包括颂扬(glorify),即赞美、颂扬、为恐怖主义辩护的网络言论行为。2019年,英国《反恐怖主义和边境安全法》(Counter-Terrorism and Border Security Act 2019)再次更新了网络时代的恐怖主义罪行,并赋予当局更多权力来应对恐怖主义对英国构成的威胁。该法第1(1)条将“表达支持恐怖组织的观点或信仰的行为或对其支持恐怖组织的观点或信仰的表达是否会造成具体的效果不计后果的行为”纳入恐怖犯罪。除英国外,《意大利刑法典》第414条将公开颂扬一种或多种罪行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且颂扬涉及恐怖主义或危害人类罪的罪行应加重刑罚。《德国刑法典》在2009年修订时也增设了具有预备性质的反恐规定。荷兰的司法判例中也把发布对恐怖活动相关罪行表示高度道德欣赏的言论认定为煽动行为。
欧洲各国的刑事定罪以“损害原则(harm principle)”为基础,即国家只能将对他人造成或威胁伤害的行为合法地定为刑事犯罪。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具有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威胁,应考虑行为的潜在伤害或行为的社会影响的可能性和危险程度。在规制恐怖主义言论的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对恐怖言论犯罪的规制最终是为了防止恐怖暴力活动,由于恐怖主义言论导致的恐怖暴力活动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因此恐怖言论犯罪由损害原则初步认定。(11)RIK P. The preventive gaze:How prevention transform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e[M]. The Hague: 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3.另一种理解将损害归因于煽动言论行为本身,(12)SORIAL S. Can saying something make it so? The nature of seditious harm[J]. Law and Philosophy, 2010(03).即认为公开鼓励恐怖活动的表达本身有害,因为这些表达可助长或培育有利于暴力或一般恐怖主义文化的社会气氛而导致对公共秩序的间接破坏。这种基于损害原则的考虑与抽象危险犯的设置初衷不谋而合。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以具有引发实害结果可能性为基础,且这种“可能性”限于普通大众所能预见的范围。刑法增设抽象危险犯一般是为了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尤其是以社会公共安全为保护客体的抽象危险犯,其“危险”的核心特征为“不可控制性”,即一旦开启因果流程,行为人再有意地对其操纵或控制都是极端不可能的。(13)海因茨·科里亚特,张志钢.有关危险犯的争论[J].刑事法评论,2016(02).在规制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相关犯罪行为时,抽象危险犯的优势——打击危险个体以保护关乎社会整体安全的重大法益——得以体现。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危险并非集中体现为造成法益侵害的具体危险,而是通过宣传行为扩张恐怖组织、通过煽动和宣扬行为造成观念认同、通过恐怖活动造成公众恐慌、通过传递信息转化恐怖独狼等一系列利用言论方式扩大恐怖主义的影响,营造有利于恐怖主义暴力行为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恐怖主义行为具有“正义性”,即该行为不仅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通过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方式将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煽动、教唆、宣传、帮助等行为控制在准备阶段或萌芽状态,有助于保护社会安全和公共秩序,进而保障人的自我实现。
(四)言论内容及行为性质的判断
根据英国《2006年反恐怖主义法》第19节规定,以鼓励恐怖主义行为罪起诉应当经过总检察长(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批准。同时,为了防止侵犯言论自由,英国规定了鼓励恐怖主义行为罪和恐怖主义宣传品传播罪的辩护事由,即在没有证明被告有相关意图的情况下,被告可通过证明该言论或宣传品既未表达其观点,也未获得其认可作为辩护的理由。荷兰刑法虽未如英国一样规定严格的起诉审批标准和辩护理由,但却通过一系列规定严格限制了言论的入罪范围。在荷兰,动词“煽动”(荷兰语opruien)通常是指“唤起人们认为某一犯罪行为是可取的或必要的的认识,并产生导致犯罪的欲望。”(14)NOORLOOS L A. Hate speech revisited: 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hate speech law in the Netherlands and England & Wales[M]. Cambridge: Intersentia, 2011.煽动行为中包含了“确信某种形式的行为是可取或必要的”以及“劝说他人或使他人信服的”观念。《荷兰刑法》对“煽动”的判断,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辨别言论是否构成《荷兰刑法》第131条和第132条所指向的煽动行为,必须同时考虑该陈述的字面意义以及全部言论内容、言论的明显含义、发布言论的背景、发布言论时所依据的身份、预期的受众、发布方式和发布时机。二是“煽动”表现为请求(request)、鼓励(encouragement)、建议(suggestion)等形式,属于行为犯的范畴,即无论公众是否真的受到煽动,或煽动的罪行是否确实发生,都不影响煽动行为的定罪。三是与英国规定相似,荷兰刑法中也规定了间接煽动,但认定某言论是否构成间接煽动需要联系该言论的上下文语义和主旨进行仔细评估。四是在判例法中,对恐怖活动相关犯罪行为表示高度道德欣赏的声明可以构成煽动,因为这意味着行为应当被仿效,但行为人明确表示他不希望仿效的情形除外。
通过借鉴英国与荷兰关于网络恐怖主义言论入罪的判断标准,本文得出以下几点认定经验:一是要判断言论内容是否与恐怖主义有关。由于语言表达及其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性,言论的内容其实不易判断。例如,对恐怖主义暴力活动的呼吁可以被宗教信息委婉和隐喻式的表达所掩盖。在判定言论内容时,语言学家和文化专家等提供的专家意见对于理解话语含义、可能导致的后果以及它所“鼓励”的行为至关重要。因此,为达到准确而有效的言论内容判断,还需借助专家意见。二是要考虑言论行为人的影响力。如前所述,荷兰的司法实践中在对言论行为进行语境判断时,除了考虑言论表达的背景和对象外,还应强调言论行为人的身份,即其在网络中的“地位”和对受众的控制程度。判断行为人在网络中的“地位”,一般以其发布、传播言论的接受者数量和被信服程度为主要判断标志。以社交媒体上的言论为例,某一粉丝量上千万的“大v”更可能比一个粉丝量仅为个位数的“小透明”发布的言论接收者多、传播影响大。所谓行为人对受众的控制程度,即其是否在某一领域具有权威地位。由于恐怖主义一般与宗教相联系,宗教事务员或宗教领袖的言论更有可能影响言论接收者的行为。三是表达的时间和背景也可能影响到表达行为是否应被认定为犯罪。例如,如果一个言论是在恐怖袭击后不久发表的,或发表该言论的人本身就是犯有其他恐怖主义罪行或者曾公开发表支持恐怖主义言论的人,则更有利于判断言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四是要将宗教言论、政治言论和恐怖主义言论区别开来。对社会具有重要价值的言论,如有助于公共事务的言论或政治参与、宗教言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例如,在宗教集会上发表的言论、公开的信仰忏悔,或者对政府的批评和对社会不公的激烈谴责等都不能被认定为恐怖主义言论,即使行为人使用夸张、挑衅或讽刺等方式来表达观点。五是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犯罪的起诉需经高级别的司法人员进行判断并严格审核,如英国鼓励恐怖主义行为罪的起诉应经总检察长(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批准。
(五)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设置
网络恐怖主义宣传已进入“社交媒体互动传播模式”,社交媒体平台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恐怖主义对极端化进程的促进以及算法技术对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支持和影响愈加明显,“算法时代”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设置成为网络恐怖主义刑法规制的重要侧面。
当前,网络恐怖主义言论在社交媒体上较为活跃,社交媒体不仅提供了创建内容的平台和以 “标签”(tag)、群组等交流工具实现的内容定制化推送,还能与用户分享广告等财产性收益。具体而言,社交媒体平台对恐怖主义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作为传输信息的工具。《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防止在网上传播恐怖主义内容条例(提案)》强调,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对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的恐怖主义内容过滤义务,并在欧盟 “地平线2020(Horizon2020)”框架计划中开发自动防止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上传的系统。二是未移除有害信息导致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蔓延和扩散。欧洲理事会要求,如果Facebook、Google、Twitter等公司在被当局要求删除极端分子内容后的一个小时内一直未能删除,将处以高达其营业额的4%的罚款。(15)FOO Y C. EU parliament votes to fine internet firms for not removing extremist content quickly[EB/OL]. [2019-04-18].https://news.yahoo.com/eu-parliament-votes-fine-internet-firms-not-removing-190214545--finance.html.此外,英国法律也对网络平台提供者的义务做出了规定,要求“平台只有两天的时间来满足删除请求;否则,它们被视为‘认可’了恐怖分子的内容。”(16)TARLETON G. Custodians of the Internet: Platforms, Content Moderation and the Hidden Decisions that Shape Social Media[M].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8.三是通过与用户分享广告收入而间接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该行为可能因为资助恐怖活动被认定为帮助恐怖活动罪等犯罪。四是算法导致的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精准推荐。此类情况较为复杂,社交媒体通过大数据算法检测出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思想感兴趣的用户,通过精准推送此类信息提高用户对该社交媒体的依赖度,强化用户对恐怖主义的认识,甚至促使其消费恐怖分子分享的内容或直接导致其与恐怖组织成员进行联系而参加恐怖活动。
在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刑法规制中,应当特别警惕社交媒体平台利用大数据算法对恐怖活动的积极影响。一方面,算法推送网络恐怖主义言论可能符合社会危害性评价,因为此种做法缩小了信息范围,强化了用户倾向,使其更易接触到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思想。另一方面,算法还可能会促使用户消费更多具有煽动性的内容,并与具有激进信仰的个人建立联系,导致其加入恐怖组织或成为恐怖“独狼”。若不限制网络服务提供者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利用算法而导致的危险,将背离刑法在面对恐怖主义言论传播问题上对安全价值观的秉持。
三、我国网络恐怖主义言论刑法规制的完善
前文通过分析网络恐怖主义言论刑法规制的主要争议与域外经验,在网络恐怖主义言论定义、言论自由的刑法取舍、抽象危险犯的增设、言论入罪的具体认定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等方面获得启示,为完善我国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刑法规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恪守罪刑法定
如前所述,“风险社会”中的刑法对安全价值的强调成为了世界各国刑法应对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主要思路。《刑法修正案(九)》中也通过刑法的提前介入加大对相关犯罪预备行为的处罚力度、扩大制裁范围,增设与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新罪名,进一步严密了刑事法网。“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17)[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通过刑法的提前介入,圈定刑法关于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相关犯罪行为的规制范围,并非是对言论自由的过度侵占,而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言论自由的价值在于获致真理、推进民主和人的自我实现,然而,网络恐怖主义言论所宣传的恐怖主义内容将导致公众被笼罩于恐惧、政府或某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政治决策受影响、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和公共安全受损害,无辜之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损失,全然不符合言论自由的基本价值,因此被排除在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之外。刑法在合理范围内限制涉恐言论,既满足宪法的基本要求,也未侵害公民权益。通过法律划定清晰而明确的规制边界,能使言论行为的“禁区”变得更加明确,防止“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的发生。
然而,刑法的前置化与扩张不能过度。首先,强调刑法的安全价值导致的犯罪圈扩大绝不能将正常的宗教传播、私下的网络谈话以及无意为之的表示纳入打击范围,否则刑法将滑入惩罚思想犯的深渊。其次,在开放式的互联网中,并非所有通过网络渠道传递的恐怖主义信息都是具有“公开”性质的,在一对一的私人链接中传递的恐怖主义言论并不具有“公开宣扬”性质,言论内容虽可能产生教唆、帮助、招募等后果而触犯其他罪名,但仍不能以“宣扬恐怖主义罪”定罪。最后,当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行为人出于无知、好奇、刺激等心理传播网络恐怖主义言论,既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倾向,也未与恐怖分子、恐怖组织存在任何关联时,可以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相关行为中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优先适用行政处罚。
(二)完善罪名设置
我国刑法虽规定了“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但在规制通过暗语、加密技术等手段或移动硬盘等电子设备传递恐怖主义信息材料时仍存不足。此类材料不仅为“独狼”式恐怖人员提供了“自洗脑”条件,还易于通过网络传输或电子设备拷贝分散传播,导致恐怖主义思想传递的指数级增长。因此,对于利用电子设备渠道传播恐怖主义思想的行为,建议增设“走私、贩卖、运输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切断恐怖主义思想流入境内的源头,阻断恐怖主义思想的线下传播渠道,降低恐怖主义的影响。(18)皮勇,杨淼鑫.网络时代微恐怖主义及其立法治理[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2).
对于以威胁、恐吓形式发布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行为,刑法规制上也有所疏漏。当前,恐怖主义宣传活动走向了更注重恐怖主义思想侵蚀的“社交媒体互动传播模式”,恐怖分子通过发布具有威胁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言论或散布恐怖主义谣言,妨碍国家机关的公务活动,引发公共秩序混乱或大众心理恐慌。发布威胁、恐吓形式的网络恐怖主义言论主体是恐怖组织或具有影响力的恐怖组织成员以及恐怖主义狂热分子,这些人不仅具有实施恐怖活动的强烈倾向与能力,其言论也对其他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子具有指向性和号召力,此类行为的危险远大于宣扬恐怖主义罪。当前刑法无论是以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还是寻衅滋事罪进行评价,均不具有针对性。因此,建议增设“威胁、恐吓实施恐怖活动罪”来规制此类行为。
(三)优化入罪认定
在分析2017年至今关于“宣扬恐怖主义罪”或“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判决(19)相关判决为(2017)京01刑初45号、(2017)京01刑初58号、(2017)云01刑初122号、(2017)京刑终196号、(2017)粤刑终1638号、(2018)晋0502刑初445号、(2018)苏05刑初96号、2018鲁1102刑初51号、(2018)宁0105刑初49号、(2018)青刑终56号、(2019)豫1381刑初1330号、(2019)豫01刑初181号、(2019)皖刑终182号、(2020)云29刑初34号等。后发现,当前法院在网络言论内容判断和行为人主观不法的认定中存在较大问题。以上案件中,有极大一部分都是行为人在网络上接触到恐怖主义音视频、涉恐网站链接、暴力恐怖宣传品后转发至微信群、qq群、qq空间或发给特定个人,相关法院将传播文件内容等同于行为人发表的言论内容,并且在主观认定上多描述为“明知涉案视频内容为暴力、恐怖、血腥内容”,忽略了行为人自身的违法性认识。
因此,在优化入罪认定方面,一是应当对网络恐怖主义言论内容进行严格判断,将言论的字面意义以及全部言论内容、言论的明显含义、发布言论的背景、发布言论时所依据的身份、预期的受众、发布方式和发布时机等纳入考量标准。二是为避免在具体案件中因为法官认知水平不一致而导致类似行为是否入罪以及量刑幅度差异过大等问题,可以规定由检察长批准言论内容是否构成相关犯罪行为,在庭审时具体言论是否构成相应犯罪及其危害程度认定需依据专家意见。三是应当注重行为人自身违法性认识,要强调对行为人主观不法的认定,即当行为人认识到不法事实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才能构成此罪。
(四)合理配置网络社交平台服务提供者责任
网络社交平台服务提供者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中,有可能通过算法对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传播造成严重影响的一类特殊主体,应当对其配置差异化的平台责任。首先,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不法网络言论的控制力不同,将网络社交平台服务提供者分为主动推送型和纯粹中介型两类,其中平台主动推送网络恐怖主义言论不能以技术中立免责,应当以算法对网络恐怖主义言论在生成和传播中的实际控制力进行评价,确定平台构成直接的网络言论犯罪主体还是成立帮助犯;如果用户主动选择关闭算法推荐功能(20)我国拟就关闭算法推荐服务进行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21年8月公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十五条规定:“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用户提供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用户选择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相关服务。”而使平台仅作为网络言论传播中介的一般不负刑事责任,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规定的情形除外。其次,网络社交平台服务提供者对不法网络言论的控制力应当被视为与其注册人数和日活用户成正比,就其对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控制力而言,注册人数多、日活用户量大的网络社交平台服务提供者应当被视为拥有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如此既可以促进大型平台企业提升技术水平,也能使其承担与之私权力相匹配的责任。最后,应当设置网络社交平台服务提供者的合规规则保障平台发展。由于对平台设置义务很可能导致严格审查而使相关网络用户的言论自由受到侵害,因此除了对网络社交平台服务提供者配置与其控制力相对应的义务责任要求外,还应当通过负面清单和合规规则为其正常运转提供安全感,如设置网络恐怖主义言论的“负面清单”、网络社交平台服务提供者的报告义务、设置不合理删除信息的平台申诉途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