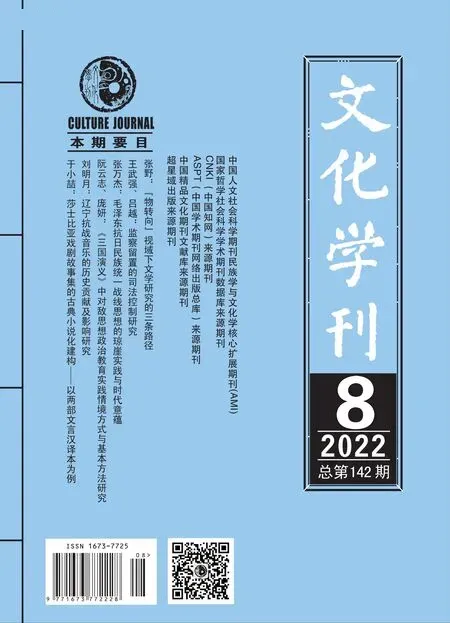利玛窦《天主实义》对“孝”的阐释与推理
王佳娣
《天主实义》是利玛窦在华期间一部重要的中文著译作品。根据谭杰的最新考证,受耶稣会亚洲传教区视察员范礼安之命,利玛窦于1594年10月至1596年10月间撰写了该书的初稿,在其后的近十年间,利玛窦根据他与中国士人和佛教人士的对话,不断丰富该书内容,雕琢文字,于1603年正式出版发行[1]。1629年,李之藻将其收入《天学初函》,1782年收入《四库全书·子部》。该书多次再版,并有日文、安南文、朝鲜文、蒙文、法文等多译本出现,1984年被译为英文。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以儒学的关键命题来阐释天主教教义,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现有成果大多从文化学、宗教学、历史学等视角关注“耶儒调和”的文本求证,而对调和的机制略而不谈。笔者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利玛窦来华传教经历,分析《天主实义》对“孝”的解读和推理,探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及辩证法的观点对利玛窦《天主实义》论证方式的影响。拟重点解决以下问题:利玛窦是如何利用逻辑推理和辩证方法对儒家关键命题“孝”进行解读的?“孝”与“忠”“仁”“礼”等其他命题有何关系?利玛窦对“孝”的解读反应了怎样的儒学观?
一、利玛窦“孝”观的逻辑基础
关于利玛窦的教育经历和背景,意大利学者米歇拉·芳塔娜(Michela Fontana)在其著作中有较详细的描述。利玛窦于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Macerate),16岁时遵从父愿离开家乡赴罗马学习法律。在罗马求学期间,他转而对神学感兴趣,退学并加入了耶稣会。1572年9月进入罗马学院(Roman College)学习,1582年随商队来到中国定居,直到1610年于北京去世。在罗马学院学习期间,利玛窦广泛涉猎各领域的知识,从诗学到修辞学,从逻辑到自然和道德哲学,从形而上学到数学均有涉猎。在哲学方面主要是学习和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观点[2]6。他深入学习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伦理学、修辞学及形而上学。为了提升自己的口才和辩论能力,他还参与了辩论小组,经常进行哲学命题的辩论练习[2]7-8。
既然利玛窦在罗马求学期间已经深入学习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就不难理解这种西学传统对其中文著译作品的影响。利玛窦在写给好友高斯塔(P. Costa)神父的信中写道“准备写本有关教义的书,用自然推理证明教义为真。[3]139”此处“有关教义的书”指的就是《天主实义》。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天主实义》)所发挥的主要论点都引自自然法则的例证,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的。[4]31”这里的“自然推理”和“自然法则”虽表述方式不同,但其内涵是一致的,即“逻辑推理”。
亚里士多德被公认为是传统逻辑学的创始人,其关于逻辑推理的相关论述至今仍有深远的影响。在其《工具论·前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提出著名的三段论,即“证明的推理”。三段论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构成,同时包括大项、中项、小项三个词项。三段论又发展出三个格、四种形式。三段论的成立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前提真实、形式正确。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只要前提真实且遵循推理规则,任何事物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借助于这一推理形式来探求,而这种推理形式本身则可用于辩证和争论[5]。
柏拉图在《高尔吉亚》中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展示了智者苏格拉底与人的对话,这种对话就是探寻真理的过程,即辩证法。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辩证法观点,同时发展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辩证法是一种有目的地在互相对立的观点中挑出好的,以得到最有可能是真的东西的过程。[6]”同时指出将广为接受的观点作为论辩的出发点,然后运用推理,得出结论。
将亚里士多德逻辑和辩证的观点投射到《天主实义》的文本中,不难发现利玛窦正是以儒家学说中的一些广为接受的观点作为出发点,运用辩证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利玛窦初入华时曾评价中国道德哲学“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也“由于他们的错误,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3]31”。因此,在《天主实义》的写作中,利玛窦强调以自然推理证明教义为真,以中士和西士之间对话的形式,借中士之口提出某一辩题,以西士的回答作为推理和论证。在推理和论证的过程中,利玛窦往往先从易被中国士人接受的儒学观点入手,对其进行阐释或意义的延伸,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一点在其对“孝”的阐释和推理中尤为突显。
二、利玛窦对“孝”的阐释和推理
在《天主实义》一书中,利玛窦论及的儒学命题包括忠、孝、仁、义、礼、信等,其中对“孝”的解读和附会最多。利玛窦通过直接引用《孝经》《论语》《孟子》《中庸》《尚书》等儒家经典中的表述或故事,对“孝”进行阐释和推理,其语义被不断扩大,已涵盖忠、仁、礼等儒学命题。
(一)孝与忠
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多次将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相提并论,进而将“孝”与“忠”建立起内在联系。在《天主实义》的首篇中就有“一家有家长、一国有国君”的提法[7]86,将父子之伦与君臣之伦并置。在第二篇中,他又写道“夫父母授我以身体发肤,我固当孝;君长赐我以田里树畜,使仰事俯育,我又当尊。[7]103”该段文字暗引自《孝经·开宗明义》,原文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显然在这里,利玛窦又将父子之纲与君臣之纲并置,并将其提升到天下有道之重要影响,孝与忠之内涵相融通。这种观点实际上与传统儒家伦理观中五伦的次序相冲突,为了调和这种矛盾,利玛窦巧妙地采用类比的方式,由家父推理出国父、天父,进而引出人有三父的概念[7]213,将其并置于孝道之范畴,指出违背三父者,皆为不孝子,再次强化了孝与忠的内在联系。利玛窦将“忠”“孝”并置,甚至混淆其内涵,主要是为了引出众生平等的思想,即“世人虽君臣父子,平为兄弟耳焉”[7]213。
(二)孝与仁
在《天主实义》的最后两篇中利玛窦又分别从正反两方面辩证地阐释孝与不孝,进而将其义引申到“仁”。在第七篇中,利玛窦借中士之口引用了舜因孝得名的故事,“故父为瞽瞍,弟为象,舜犹爱友焉。”该故事暗引自《尚书·尧典》《孟子·万章上》《孟子·尽心上》等章节。在儒家典籍中强调的都是舜对父、舜对弟的孝悌美德,虽然二者皆为恶人,但舜仍守孝悌,赢得了美名。在这里,利玛窦避开“孝”,而选用了“爱”一词,这样就用爱将孝与仁建立起联系。为了以仁证博爱,再次提出“双亲、兄弟、君长与我有恩有伦之相系,吾宜报之”[7]196,要报答父母之恩,则要爱父母,即使“虽虎之子为豹,均爱亲矣”[7]197。在第八篇中,利玛窦又从反面对此观点进行论证。在回答中士“无后是否不孝”的质疑时,利玛窦认为“孝否在内不在外”[7]212,即评判一个人是否孝敬父母,要看他的内在品质,而非外在表现。他举伯夷、叔齐、比干为例,认为他们虽无后,但“孔子以为仁”,孔子都说他们是仁义之人,谁还能说他们不孝呢?即使有的人生了很多子嗣,但“无善可称”,没有德行的人又怎么能说他孝呢?由此可以看出,在利玛窦看来孝即仁,如果一个人没有德行,也就称不上孝,行孝就是为仁,那样才能“天下有道”[7]213。
(三)孝与礼
对孝道的论述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多处可见。“中国的道德书籍充满了有关子女应尊敬父母及长辈的教诲。[4]76”利玛窦还对中国的丧葬礼仪进行了极细致的描绘,以证明中国人对长辈的孝“没有别的民族可以相比”[4]77。在《天主实义》第三篇中,利玛窦将“孝”之内涵扩大到“礼”。其引用《中庸》第十九章之言,指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礼[7]115,利玛窦认为孝子贤孙在先人去世后采用各种祭祀礼仪对逝者表达尊敬和思念之情,这是孝的表现,意义重大。又将事亡、孝道与礼统一起来,即孝道表现在事亡的礼仪,因此,“事亡之礼即孝”的观点形成。在第六篇中,利玛窦借中士之口提出“子为养亲而行盗,其意善矣,而不免于法,何如?”[7]163。这里的故事出自《论语·子路》,利玛窦以此引出“孝”与“礼”的关系问题,认为偷窃财物是非礼之恶事,而孝是仁善之事,偷盗本身就非孝亲的行为,非礼则无孝,孝与礼实为一体。
由以上论述可知,利玛窦将孝道作为德性之首,以其为逻辑论证起点,在论述不同的观点时,将其与儒家命题中的“忠”“仁”“礼”等内涵加以融通,扩大了孝道的内涵意义,形成独特的孝道观。利玛窦孝观的形成由于借用了儒学观点,同时运用了自然推理的方法,在明末清初世人间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推动了《天主实义》一书的在华接受。
三、利玛窦“孝”观与儒学观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以“孝”为中心,结合其他儒家命题,构建了其儒学观的独特体系。其孝道观是儒学观的典型代表,包含着他对儒家观点的理解、阐释与推理,以及对中学和西学的融会贯通,是其合儒、补儒策略的具体体现。
首先,利玛窦的孝观是中学和西学融合的结果。中国传统儒学中的观点是利玛窦论证的前提,西方的逻辑推理和辩证方法为其提供了理论工具,明末社会思想界的宽松氛围为其儒家思想的新解提供了社会基础。崇古尊圣是中国文化传统,这就驱使利玛窦必须要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巧妙地运用西学工具对传统儒学观点进行发挥和再造,在阐释“孝”的内涵意义的同时形成自己的儒学观。利玛窦的“以西政西,以中化中”[8]98为自己赢得了“西儒”的美名,同时也让中国士人得出“东海西海,心同理同”[8]99的结论。
其次,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的孝观体现了他对儒家思想的选择性适应。早在入华之初,利玛窦谈到中国的宗教与教派时已经认识到儒教在中国最为出名,与释、道的观点也不同。文化适应的策略自范礼安提出以来,一直被利玛窦所实践。但从《天主实义》的著译来看,利玛窦并没有完全遵照儒家经典对孝的理解,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孝”进行了改写,使其在内涵上与“忠”“仁”“礼”等命题建立起联系,形成了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阐释体系。
最后,利玛窦的孝观体现了他对古儒和新儒的不同态度。在写作《天主实义》之前,利玛窦曾应视察员范礼安神父的要求,将《四书》译成拉丁文,他认为该翻译对中国和日本的传教士非常有用。这里的“有用”指的是利玛窦在先秦儒学经典中找到了合儒、补儒的基础。根据胡雪的统计,《天主实义》中引用的中国古代典籍达33种,主要包括先秦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注疏以及程朱理学,其中先秦儒家经典占总引用数的85%[9]。《天主实义》中关于孝道的论述几乎全部出自《论语》《中庸》《孟子》等先秦典籍,体现了利玛窦崇古轻新的儒学观。
四、结语
通观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对儒学命题“孝”的解读及其与“忠”“仁”“礼”之间的关系推理,逻辑推理与辩证方法的运用使论证呈现出自然法则的严谨与周密。先秦哲学本身的内在逻辑性为利玛窦的阐释和推理提供了基础,其创新的解读方式也拓展了先秦儒学内涵意义的空间。一方面,对儒家文化的适应为利玛窦赢得了“西儒”的形象,有力地推动了其在华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儒家经典及其思想也随着《天主实义》一书远播欧洲,成为儒家思想在欧洲传播的最早记录。利玛窦以“孝”为核心的儒学观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西传提供了参考与借鉴。文化的传播首先是思想的共享,共享促进共识,共识带来共进。在当代世界文化进一步融通的背景下,利玛窦对儒家思想的会通和融合及其背后的机制,为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带来重要启示。
——儒学创新发展的趋势与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