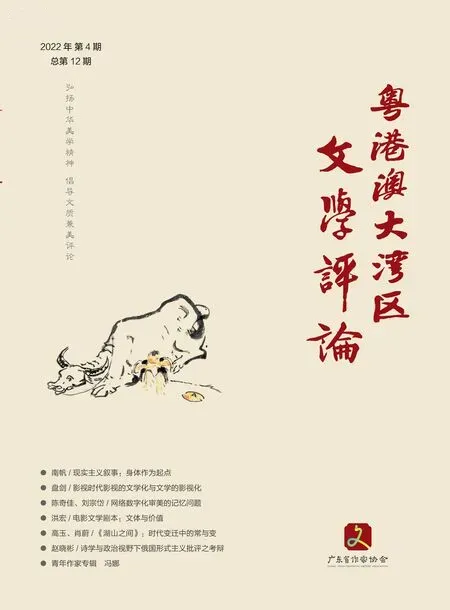“鬼气”与“诡气”:当代小说死亡叙事形态之一
徐 威
死亡是人类永远无法逃避的一个问题,也是数千年来中外文学书写中永恒的母题之一。在当代小说中,死亡亦是最为常见的情节之一。作家对死亡事件及亡者的不同叙述与刻画,生成了多种多样的死亡叙事形态。其中,“生死轮回”“通灵”“化形”“人鬼共存”“阴阳相通”“天道无常”“生死报应”“神秘预感”等死亡叙事模式,弥漫着“鬼气”与“诡气”,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是当代小说死亡叙事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一种。
一、“鬼气”与“诡气”:模仿性与本土化的统一
20世纪80年代,大量的西方哲学思潮、文学理念及现代文学作品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迅速地影响了一批中国青年作家:“80年代人们经历了太多的现实变动和思想变动……我们在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浏览了西方一个世纪的思想成就和文学成果。在理论方面,人们粗通唯意志论、弗洛伊德、现象学、存在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在创作方面也知道卡夫卡、黑塞、纪德、塞林杰、意识流、新小说、荒诞派、黑色幽默、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实验小说等等。”[1]这些思潮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可以说,时至今日它仍在发生作用。
我们且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例。1975年魔幻现实主义的身影首次在中国出现[2],1980年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评介》一文在《文艺研究》刊发。文章将魔幻现实主义定义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产物”:“它是在继承印第安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东、西方的古典神话、某些创作方法,以及西方现代派的异化、荒诞、梦魇等手法,借以反映或影射拉丁美洲的现实,达到对社会事态的揶揄、谴责、揭露、讽刺或抨击的目的。”[3]在对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帕拉莫》的分析中,陈光孚认为其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包括“打破了生与死、人与鬼的界限”“打破了时空界限”和“西方现代派手法的妙用”;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则着重体现在“鬼魂出现”“东西方神话与典故的融合”和“象征性”上。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孤独》中译本在国内出版;1983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对于当时的中国作家而言,马尔克斯的创作路数带给了他们极大的启发与鼓舞,于是,一大批向魔幻现实主义学习的小说作品相继出现。莫言、扎西达娃、阎连科、贾平凹、韩少功等人的部分作品被视作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新世纪以来,仍然有许多小说作品自我标榜或被标榜为“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譬如,陈应松长篇小说《还魂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年)的书腰上,即刊印着“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巅峰之作”“荆楚大地的现实版《聊斋》”等宣传语。
事实上,不少学者与批评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标签的使用显得过于草率与含糊。其结果是,似乎只要小说中出现了“人鬼共存”“阴阳相通”“荒诞离奇”“亦真亦幻”“动植物化灵”“神秘预感”等特点,就理所当然地可以将其视作魔幻现实主义。甚至于,对《牡丹亭》《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同样简单粗暴地以“魔幻现实”概而论之,这多少令人感觉“惊诧”。
不可否认,许多当代小说文本所讲述的故事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确实有较大差异(甚至是颠覆性的),因而能带给人一种新奇感与神秘体验。如莫言《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陈应松《还魂记》中鬼魂游荡在人世间;王十月《米岛》中死去的人居住在树上、《收脚印的人》中魂魄游荡并回望自己一生走过的路;陈忠实《白鹿原》中通灵的白鹿与田小娥鬼魂附身于鹿三;洪峰《极地之侧》中“我”在诡异的、不知情的雪地夜游中挖出两具尸体;贾平凹《废都》中思考哲学问题的奶牛、《怀念狼》中能够变成人的狼、《白夜》与《高老庄》中的死人复生;韩少功《马桥词典》中的轮回转世;阎连科《天宫图》中穿梭于阴阳两界的魂魄;苏童《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仪式的完成》中离奇的预感与死亡……这些作品之所以显得特殊,原因在于它们或多或少都带有“鬼气”与“诡气”。
然而,对于这些小说中的“鬼气”与“诡气”,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以“魔幻现实”一语概之。一方面,我们承认它们的出现与当时的文化思潮有一定的关系,中西文化的碰撞激发着创作者在叙事形式、叙事内容与审美取向上的创新。正如李裴所认为的“小说作品对死亡的表现与一个民族对于死亡进行观照时的心态、观念有关,也与文化思潮有关。这观念、心态和文化思潮,在不自觉之中制导着小说创作的审美意向”[4]。另一方面,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它们仍逃离不出中国传统死亡观念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根深蒂固的。因此,这两种死亡叙事形态是在对中国传统鬼神文化认知、接受的基础上进行的当代转化,是“模仿性与本土化的统一”[5],是独特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当代小说死亡叙事形态之一种。
二、“鬼气”:当代小说中的“亡灵/鬼魂叙事”
陈平原认为“了解一个民族,不能不了解其鬼神观念”[6],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同样是如此。莫言、迟子建等作家所秉持的“鬼神论”“泛神论”文化观念[7]是生成当代小说死亡叙事形态的一种重要文化根源。事实上,秉持这种观念、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的当代作家并不在少数。格非曾表示:“中国的民间故事最多的是鬼故事,我小时候听得最多的就是鬼故事。如果说我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文学起源的话,那就是鬼故事。”[8]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中国文学中死亡叙事的思想根基在于中国独特的鬼神文化。当我们从鬼神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代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可以发现,它继承了大量古代文学作品(如《幽冥录》《太平广记》《西游记》《聊斋志异》《子不语》等)中所蕴含的对死亡、鬼神、死后世界的认知思维与刻画方式。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地呈现在当代小说中的“亡灵/鬼魂叙事”之中。
人们在很早以前就对灵魂的存在有所感知,但这种认知起初是模糊而超验的。恩格斯对此有独到的解释:“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于是就产生了灵魂不灭的观念。”[9]在感知到肉身之外的灵魂与其“不灭性质”后,人们对灵魂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对灵魂及死后世界的猜测、想象甚至“濒临体验”中,中国传统文化中亦产生了丰富而独特的鬼神文化。
首先是确定了鬼的存在。《说文解字》云“人所归为鬼”[10],鬼乃是人死后的最终归宿。王充《论衡·论死篇》曰:“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故谓之鬼。鬼者归也。”《礼记·祭法》曰:“大凡生于天地之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其次,鬼乃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形态。古人认为,人不仅有肉身,且还有魂魄:“魂,人阳神也。魄,人阴神也”(《淮南子·说山》)。而当人死亡,或者魂魄离开肉体不再归来,便化身为鬼,成为可以脱离人的肉体而独立存在的特殊生命形态。“魂与魄相合,居肉身则为人;魂离魄,弃肉身而得灵,则为鬼。”[11]再者,鬼亦有善恶之分。《礼记·檀弓上》中认为鬼魂“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这种善鬼更多的时候被称之为神:“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原先也有善良的(有益的)与邪恶的(有害的)‘神’和‘鬼’二元论。这两者遍布于整个宇宙,变现于所有的自然现象与人的行为和境况之中”[12]。最后,鬼神具备人所不具备的能力,它们可以跨越时空、出入阴阳两界,身具法力,能够化形为人(这就使得鬼神在具备“鬼性”“神性”之外,还具备“人性”)等等。马克思·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中国人的鬼神信仰进行社会学考察时写道:“人的‘灵魂’也被认为是由来自天的神与出自地的鬼的物质所组成,在人死后即再度离散……神与鬼都是有威力的。”[13]这种威力,既表现为“保护人和驱除恶灵侵害人间底能力”[14],也时常表现为鬼神对人的骚扰、惩戒与伤害。正因如此,人们需要崇敬、信仰鬼神,以期获得它们的庇佑与祝福。
纵观当代小说中的“亡灵/鬼魂叙事”,那些“轮回”“转世”“化形”“通灵”“魂不灭”“人鬼共存”等故事,大抵都与上述鬼神文化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我们还需看到,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鬼神文化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亦显现出不同的特征:普遍存在的祖先崇拜、东北地区的萨满文化影响下的鬼神信仰、云贵川桂等西南地区的巫鬼崇拜、荆楚大地的“信巫鬼,重淫祀”等等并不完全相同。这些不一致,同样呈现在小说的“亡灵/鬼魂叙事”之中。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环境”是影响文艺形成的三大要素之一:“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15]“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6]。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等对于作品风格的生成有着重要影响。我们且以深受荆楚文化影响的几部长篇小说为例。
王十月长期被视作“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在《米岛》《收脚印的人》《如果末日无期》等近些年来的小说新作中,我们注意到他作品逐渐脱离单纯的“底层叙事”与“苦难叙事”,呈现出愈来愈浓郁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这种民族性与现代性,着重体现在他对于荆楚文化的巧妙运用上。《米岛》中的叙事人是一棵通灵的千年古树:“千年前,一只七彩山鸡将我从遥远的河对岸衔来……我是一棵树。有人叫我菩提树,而米岛人叫我觉悟树。许多年之后,我才觉出,作为一棵树,我在人类的眼中,是如此与众不同,我被赋予了神的灵性,被人膜拜……”[17]米岛中那些死去而又不肯离去的亡魂,逐渐在古树上安身立命。他们以一种旁观者和评论者的身份对小说叙事进行辅助,以鬼身说人话,从而使得小说“众声喧哗”,生成了多重复调。除此之外,开了“天目”能见到鬼魂、能与鸭子沟通的花敬钟、白婆婆、马挖苦、叫花婆婆等人,身上同样具有一种神秘气息。小说中人鬼共存、人兽相通等具有神秘气息的故事与王十月所处荆楚文化中的崇巫风俗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另一部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中,“收脚印”这一民间传说直接构成了小说叙事得以延伸的核心主线:“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说过,有些人能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在死前临近前半年,或者一两个月,就成为收脚印的人。每天晚上,别人睡着之后,他会把自己这一生所走过的脚印都收起来。”[18]因牛头马面告知王端午其生命即将终止,王端午才会在夜深人静之时跨越时空进行灵魂穿梭,在“收脚印”的过程中回望自己的一生,从而开启了他的反思与救赎之路。凡此种种,都是王十月小说中民族性、本土性的具体显现。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民族性与本土性,恰恰又构成了王十月近期小说文本的现代性:“王十月将荆楚的巫鬼文化融入到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在小说文本中营造一种鬼魅、魔幻的大背景,又在这‘虚’的大背景中进行最为尖锐的现实主义书写”[19]。
湖北作家陈应松的长篇小说《还魂记》也与楚地巫鬼文化有着密切关联,小说显得“鬼气”十足。陈应松在接受采访时坦言:“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是非常正常的。一代代,成为文化基因,影响了楚人的生命观、世界观。我从小就信鬼魂……田野上游荡飘浮的鬼火每个晚上都伴随我们,与我们同在,浓郁的巫鬼氛围,我们与别人的生活其实是不一样的……写鬼魂的东西同样是一种真实的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20]倘若说在王十月的小说中,对巫鬼的书写是作为小说叙事一种背景、一种策略而存在,那么在陈应松的《还魂记》中,对巫鬼的书写则成了小说叙事的中心。
《还魂记》在故事开始之前的“作者自述”,颇有效仿《红楼梦》开篇的意味:“本人喜好在乡野乱窜。某日,雷电交加,被狂风暴雨阻隔,在野猫湖一荒村破舍避雨,发现一墙洞内,有一卷学生用作业本,已发黄破损,渍痕斑斑,字迹杂乱,难以辨认。细看是一本手记,为一野鬼所作,文字荒谬不经,颠三倒四。带回武汉后稍加润饰,每段文字附上小标题,公之于众,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仅此而已”[21]。事实上,《还魂记》也确实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小说中的叙述者“我”名为柴燃灯,在即将出狱之时,因为不断告密而被其他犯人杀死。死后,“我”的灵魂回到我的“养生地”,从而“还魂现身”:
“我触到了岸。我的魂触到了岸……过去的记忆越来越远。一个声音暗示我说:你会慢慢明白,你的魂触到了你的养生地,于是还魂献身……养生地就是你的胞衣所埋之地。”[22]
“死去的鬼是要收脚印的——凡是我走过的地方,我都要收回脚印。我在凹凸不平的村路上摸索……我死了,才回来。”[23]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收脚印”——不过,与王十月《收脚印的人》中作为串连王端午赎罪故事的“收脚印”相比,陈应松小说中的“鬼气”更盛。一是小说中的黑鹳庙村如同《佩德罗·巴拉莫》中的科马拉村——亡灵无处不在,人与鬼的界限模糊不清。一方面,村子里到处是“死去的活人”:“许多人在世上走来走去,其实是死了”“每个人都是一座坟”。另一方面,又有众多“活着的死人”:“我”是冤魂,纵火少年五扣、潘主任都是鬼魂。于是,因为喝了村长家的假酒而导致男人集体失明的活人群体,与无数死去又在“养生地”还魂的鬼魂,同处一村。二是在《还魂记》中离奇的人与事不胜枚举,“鬼气”十足。比如说,挖坟挖出长得像红薯的会笑的土怪;七月半,过阴兵,所有的鬼到家中吃饭,不发出一点声响;一个女婴拥有两个头颅,左边的头杀死了右边的头;一个埋在地里的骷髅被刨出来,嘴里却在念《金刚经》与《大悲咒》……这些离奇之人之事,既与荆楚巫鬼文化影响下的民俗、信仰息息相关,又是作家恣意昂扬的奇崛想象力的充分体现。三是《还魂记》的语言同样富有“鬼气”。因为是“野鬼”所做的手记,导致小说结构上显得零碎。每一篇手记,长短不一,但语言风格却大抵保持一致——大量使用比喻手法,选取的意象带有森然“鬼气”,使得小说语言在富有诗意的同时又带有黑色的忧郁与绝望。“湖水被夕阳螯了,它在疼痛地弹动。浪花泛着青光。一条歪斜的渔船像一个警察潜伏在水里。暮色昏暝,野猫呼号,白茅摇荡,虻蚊飞舞。”[24]事实上,小说的开头已经定下了整部小说的语言风格与基调——这是带有森然“鬼气”的语言:“我在窒息。鬼火般的灯。巨大的空窟。我躺在灰尘扑扑的疵纱中间。我的两个鼻子已经完全堵塞。肺部被灰尘填满……我要呛死。我已经死去。肚皮在起伏。似乎里面有一只快死的青蛙在挣扎。那是最后一口气。”[25]
在《还魂记》中,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地域文化,尤其是鬼神文化,是如何影响小说叙事形态与美学风格的生成。荆楚大地盛行的巫鬼观念,几乎完全地转化为小说情节、小说意象出现在陈应松的创作中。这些鬼魂,以及那些驱鬼、安魂等一系列传说与民俗,都是陈应松自幼便熟悉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本土文化与资源对于当代小说死亡叙事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远远超越了西方外来文化思潮与叙事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正如陈应松所言:“西方文学特别是魔幻现实主义可能会给我带来了某种写作冲动,但决定我写作的肯定不是西方的小说,是我自己的土地记忆和生活感受,我只能对我自己所处的世界有发言权,写不熟悉的生活就是说谎。”[26]
采用“亡灵/鬼魂叙事”的当代小说文本还有许多。王十月、陈应松将独特的、富有个性的地域鬼神文化融入小说的死亡叙事之中,而更多的当代作家则是单纯地将叙述者设定为“亡灵/鬼魂”。这一类小说作品中,地域色彩与鬼神文化相对而言较弱。换而言之,这些作品大多只是借“亡灵/鬼魂”来讲述人间故事。苏童长篇小说《菩萨蛮》中华金斗死后灵魂不得安息,骑着天界的黑天驴飘荡在香椿树街,而这头黑驴却正是他妻子的化身。“天界”是人们最为熟悉的鬼神概念之一。小说中,华金斗如此描述他穿梭阴阳两界:
“从我这里到香椿树街要穿过两个世界,假如骑上那匹黑天驴眨眼就到了,活人们无法理解这件神奇的事情,只有死人们知道在另一个世界里交通是多么发达,茫茫天际里每天运行着多少天马、天牛、天驴、天狗,亡灵们去人间探望亲人使用的就是这些交通工具。我听说玉皇大帝出外巡游坐的是金天车,而阎王爷到人间办事坐的是一艘美丽的七色飞船。当然,什么金天车什么七色飞船的,我只是说说而已,我从来不想这种好事,对于我来说,有一匹黑天驴骑着已经很不错了。”[27]
苏童所描述的死后世界是中国民间广泛认可的“天庭—人间—地府”三重空间架构。在这一环境设定的基础上,苏童笔下的“亡灵/鬼魂”不似王十月、陈应松笔下那般“鬼气”萦绕——他们更趋向于“人”。换而言之,苏童笔下的“亡灵/鬼魂叙事”是贴近现代的,没有表现出向民间传统靠近的强烈倾向。小说中苏童将“天界”分为多个区域,并设置了“区长”这一极具现代色彩的人物:
“我所在的天界第八区聚集了一大批像我这样死不瞑目的冤魂,大多数都犯了罪,却又不是坏人,所以第八区成了一个三不管地区,玉皇大帝不管,阎王爷也不管。我们的区长是一个打猎爱好者,有一次到山上打斑鸠,斑鸠没打到,一发子弹竟然打死了对躲在树丛里的男女,人家法院并没有判他死刑,他自己判了自己的死刑,据说他本来应该在第六区的,是他自己跑到我们第八区来的,他说他原来就在一个落后的老大难区工作,现在还是不改初衷。”[28]
小说中有关“鬼”与“鬼世界”的书写,更多时候作为一种叙事背景而出现,这是许多当代小说死亡叙事所常采用的方式。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中的“我”是刚死不久的游魂;艾伟长篇小说《南方》中罗忆苦死后以鬼魂形态讲述;雪漠长篇小说《野狐岭》中,“我”在神秘仪式中将驼队的幽魂召唤而来,并对他们一一采访;孙惠芬长篇小说《后上塘书》中徐兰被杀之后以鬼魂姿态自述;陈亚珍长篇小说《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中含冤而死的仇胜慧二十年后“死而复生”,重返故乡……这些小说文本,对“鬼”与“鬼世界”的想象与书写,在体量与深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作家们更多的是借助亡者之口,诉说人间万象,从而以“亡灵/鬼魂”视角重新打量、审视我们的现实世界。
三、“诡气”:当代小说的神秘主义叙事
当代小说的死亡叙事,在“鬼气”之外,还时常带有一种“诡气”。这种“诡气”可以称之为一种神秘主义叙事。神秘主义与文学创作及文学欣赏有着密切的联系。毛峰认为,“神秘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把握世界把握生命的诗性世界观。它如其本然地看待无限的宇宙,深知有限的人类对无限的宇宙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宇宙作为无限存在,其本源、意义过程和归宿是神秘莫测的”[29]。既然认知是有限的,那么认知神秘世界的方式也显得与众不同。“在处理无限的、神圣的事务时,理性仅仅是条件而不是准则,在这些领域,诗意的、直观的、神秘的把握方式才是构筑人文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基本精神。”[30]因而,在小说创作这样一种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艺术实践中,许多小说家都直接或间接地采用神秘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构建他们的小说世界。
具体到当代死亡题材小说中的神秘主义叙事,它是命运无常的诡异,同时也是“殊形诡制,每各异观”(班固《西都赋》)的诡怪;它是迷雾缭绕的诡秘,同时也是真假难辨的诡魅。在“亡灵/鬼魂叙事”中,我们能清清楚楚地知道鬼在何处、鬼是何种形象。相比之下,当代小说死亡叙事中的“诡气”却是无形的、神秘的,也是更难以言说的。
第一,当代小说的死亡叙事中,“天道无常”与“人道无常”的诡异感得到大量的书写。
胡性能对于死亡有着浓郁的书写兴趣:《在温暖中入眠》中,被肝硬化判处死刑的席叔从未碰过女人,他用治病的五千块钱救出年轻妓女,最终死在她温暖的怀里;《下野石手记》以“梦录”的形式书写因“我”的告密导致的海清之死及现场目睹枪决所带来的心灵挣扎;《来苏》中李琪目睹母亲的自杀,最后也用刀片割腕结束自己的生命;《重生》中陈琪为保护章瑶而死,而章瑶则一次次地试图自杀;《小虎快跑》中小虎之死呈现出底层人物的悲凉……死亡在胡性能的笔下随处可见,或是悲凉、深沉,或是荒诞、可笑。在这几种面目之外,胡性能小说中的死亡叙事还时常显现出神秘、无常的“诡气”。
在短篇小说《日常生活的景象》(三题)中,胡性能对三个独立的故事进行了速描。标题为“日常生活”,但这三个与死亡紧密相关的故事却极力凸显命运的残酷、偶然与神秘。故事之一《兄弟》的前半部分是对兄弟俩儿童时期一件往事的刻画:男孩背着年幼的弟弟,用石头将树上的核桃砸下来,分而食之。在这一部分,小说语言轻盈、灵动,一幅饱含兄弟情谊的乡村画面浮现于我们眼前。之后,这一画面迅速地、毫无过度地从静谧的美好切换到残酷的凶杀中:成年之后的弟弟用斧头砍死了哥哥。“斧头砍在了头上,男人叫了一声,他把手中的扁担扔在了地上,蹲了下来。紧接着,他的后背又中了一斧……他头上的血正不停地涌出来,随之流淌出来的,还有少许脑浆,看上去像是在一块劣质巧克力上涂抹了一丝奶油。”[31]兄弟两人为“苞谷”而互相残杀——小说描绘的第二幅景,与童年时期男孩砸开核桃“吃掉了两瓣,然后将剩余的六瓣,一一喂进了他身后的小男孩的嘴里”[32]的温馨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故事就此结束,兄弟两人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包括导致两人从相依到相杀的一切都被省略了。在故事之二《民工李朝东》中,公路边准备拦车回家的李朝东,在思念着家中妻儿的时候,被“一块西瓜大的石头”恰巧砸在头上。李朝东至死仍艰难地挪动着,想再看一眼照片中的亲人——对这一场景的特写直抵命运的残酷与偶然。在故事之三《怀抱死婴的女人》中,令人难忘的画面定格于在妇幼保健医院大门外放声大哭的女人身上:“怀抱着死婴的女人把嗓子哭哑了,她把整个脸埋在裹死婴的布筒上,肩膀有节奏地耸动”[33]。这一画面引起了围观的黑衣青年对于童年时一次濒死体验的回忆:“有几次,他差一点就死掉了,他不知道害怕,更不知道伤心,他只知道自己正沿着个巨大的漏斗往下坠后来他重新浮了上来,听见了母亲无助的哭泣声”[34]。在这一故事里,与《兄弟》一样,人物仍然是无名无姓,它仍然如同一个符号,着重凸显的是生的偶然与死的偶然。在另一篇小说《扑腾的鸟》中,报案人在梦中看见自己一年前失踪的儿子“脖子流着血”出现在自己从未去过的十里铺,最后他果然在河边一棵柳树下发现了儿子当时穿着的衣服;警官陈凯莫名自杀,同事张鲁在分析、想象、模拟陈凯如何自杀的过程中,诡异地陷入了对陈凯的模仿中,同时丧失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最终也离奇死去。残酷的兄弟相残、恰巧地被石头砸死、离奇的梦境与现实交织、诡异的“不听使唤”……凡此种种,都使得胡性能小说中的死亡叙事显得“诡气”十足。
事实上,在神秘主义死亡叙事中,不仅“天道无常”,“人道”也无常。我们且以苏童及阿乙的作品为例。
苏童的许多小说都携带着“诡气”。王德威对此有精准的评述:“宿命的记忆像鬼魅般地四下流窜,死亡成为华丽的诱惑”“苏童的南方阴气弥漫,人鬼不分。他的地方故事,鬼话连篇。”[35]“人鬼不分”“鬼话连篇”之外,苏童的作品,还借助那些毫无征兆的死亡,着重呈现出人生的偶然与无常。死亡在苏童的笔下如同是日常生活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一方面,苏童小说中,杀人并不需要某种强大的理由,一个生命的结束显得极其“随性”:《游泳池》中少年达生为了能够在阀门厂的游泳池里蝶泳,将并不会游泳的管理员老朱拉下水,让其溺死;《平静如水》中弟弟因为姐姐不肯吃鱼便用刀刺死了姐姐;《城北地带》中蝴蝶帮的三个少年偶然遇见锦红,而杀死锦红的原因仅仅是因为锦红对他们说话的语气太过泼辣了:“不玩说不玩,她那么凶干什么?我要不敲死她,谁知道她还会把我什么咬掉”[36]。另一方面,许多的死亡都是因为莫名的意外:《灰呢绒鸭舌帽》中的老柯为了追回自己的帽子而从车上摔下而死;《沿铁路行走一公里》中的小珠因为来不及闪避而被火车吞噬;《肉联厂的春天》中金桥和徐克祥意外地被关在冷库里;《饲养公鸡的人》中的普山醉倒在驳船上被石头压死……苏童始终以一种冷静的笔法、仿佛若无其事般地制造着人物的死亡。在这无处不在的死亡中,苏童的死亡叙事在逻辑上常常呈现出偶然、无常等特征。生命的存在意义、死亡的价值意义等,在这些偶然与无常中,被一一消解。这一特点,在苏童、余华、马原、洪峰等先锋作家的笔下都表现得较为明显。
阿乙的小说中同样有许多人物在突然之间遭遇死亡。《巴赫》中巴礼柯终于决心逃离过了一辈子的、平庸的教师生活:“当时他穿着黑色田径裤,黑色T恤,背着一个包,包里放着饭团、茶壶、电筒、柴刀、信纸、笔和御寒用的外套”[37]。一切似乎都顺利进行,然而,死神却突兀而至:“背包忽然掉落在地,一些野山楂从里边蹿出,跳着滚下了楼梯”[38]。《意外杀人事件》里,红乌镇的超市老板赵法才、卖淫女金琴花、落魄黑道老大狼狗、想要出走闯世界的艾国柱、精神病患者于学毅、傻子小翟六个人无辜地被外乡人李锡宗杀死。他们之间充满偶然因素的相遇,带来的却是一起又一起的死亡事件。《午后》里,在扮演包青天的游戏过程中,扮演马汉的辉东不知是“入戏太深”还是“本性邪恶”,竟然真的将安安的头颅切下。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中,陷入无聊、空洞与虚无中的“我”,毫无动机地将自己的同学孔洁残忍地杀死。阿乙对于这样一种无常,在“我”买到弹簧刀的时候如此表述:“我觉得有一把弹簧刀,事情就会有一种仪式感。我将它藏在包里,走过人群,不一会儿就忍受不住诱惑,将手伸进包里,按起按钮。嗒,它弹出去,嗒,它收回来。我感到眩晕,我是死神,可以随时决定这些路人的生死,而他们只能将之归结为偶然。但我得挑选。在我心中,一个人被杀是因为他值得被杀。我觉得这些人都不太合适。”[39]事实上,“我”此刻的这种感受与认知,在阿乙其他的小说中,同样适用——命运难测,偶然即死去,死去即偶然。
第二,当代小说死亡叙事中,诡怪之人事随处可见,可谓是“每各异观”。对这些人、事的刻画,同样属于神秘主义叙事。
莫言小说《马驹穿过沼泽》中马能够口吐人言并化身为人,《狗道》中大批的家狗因为啃食了人的尸体而变成了野狗。苏童《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的孙子、孙女像种树一样将年迈的爷爷活埋了,《仪式的完成》中的民俗学家为了体验“拈人鬼”这一习俗,最后两脚朝天地在那口大缸里死去。这口“大缸”,与《妻妾成群》中的“井”、《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的“白鹤”、《黄雀记》中不断“找魂”的祖父、《城北地带》中的“蛇”以及达生的“闹钟”一样,都是带有神秘色彩的、蕴含着死亡隐喻的独特意象。韩少功《爸爸爸》中,未老先衰却永远长不大的丙崽,外貌奇怪,只会说“爸爸爸”和“X妈妈”这两句话,而鸡头寨人却将一个如此怪异之人奉作“丙相公”“丙大爷”“丙仙”。贾平凹在《老生》中塑造的唱师这一人物形象更是“诡气”十足。用上元镇人的话来说——“觉得他有些妖”[40]。这“妖”即“诡气”,具体表现在:他的长相数十年长久不变;他不时突然离去十年八年,又突然回来;他将棉花塞在鞋里,当作脚踏白云;他将黑手帕包住老鼠,老鼠随后能变成蝙蝠飞起来;他与死人活人都打交道,他不唱的时候在阳间,唱的时候在阴间,不断地在阳间阴间里往来着;他懂得一切世间风土人情,也对死后世界无比熟悉;他对飞禽走兽花草树木无一不知无一不晓……而借助唱师之口,更多的诡异之事被讲述出来:猫与幼儿灵魂互换,猫说人话;当归村的男性都患上一种奇怪的病,生下来一切正常,而到了七八岁左右,全身关节便变大,一代代都是一米四五的个头,被称为“半截子”。对这些人、事的想象与叙述,使得《老生》弥漫着带有奇崛想象又与民间文化紧密相关的“诡气”。这些奇异之人、物、事各有特色,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第三,当代小说的死亡叙事中,迷雾缭绕的诡秘同样引人注目。这一点,尤其显著地呈现在先锋小说中。
对于许多先锋作家来说,“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因而,先锋作家热衷于在叙事中建构迷宫,使得小说文本迷雾缭绕,充满诡秘之气。马原在时间、空间、人物的不断切换与拼接中创造出他复杂的“叙述圈套”;余华时常借助疯人疯语打破常规叙事的可信度,在模糊的人物刻画中呈现迷雾人生;格非则擅长从人物内心无序的、本能的潜在意识出发,“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41]。格非的《迷舟》《青黄》《褐色鸟群》《风琴》《大年》等小说,都具有这种特质。《迷舟》讲述了军阀孙传芳所部守军三十二旅旅长萧的离奇死亡故事。萧的死亡充满了种种巧合、偶然与诡秘,倘若深思萧的真正死因,小说更显得扑朔迷离:是因那乱世中的的混战还是死于对杏的莫名迷恋?是死于警卫员的枪下,还是死于道人那句含糊而神秘的谶语?此外,小说中大量的叙事空缺同样使得小说迷雾重重。在格非看来,“现实是抽象的,先验的,因而也是空洞的,而存在则包含了丰富的可能性,甚至包含了历史”[42]。这些“丰富的可能”,时常就潜伏在偶然的、不确定的“神秘”中——正如《迷舟》中的含混卦辞、不祥预感与离奇之死。在南帆看来,“诗、棋、卜卦、预感和无故死亡时常出现于格非的小说中,这暗示了格非对于神秘的敬畏”[43]。基于这种“敬畏”,我们看到,在格非的小说中,迷雾缭绕的诡秘故事总是与不可预测的偶然命运牵连在一起,令人似懂非懂,从而激发出我们更广阔,同时也更个体化的阅读体验。
青年作家路魆的小说有着极为独特的现代派风格。具体来说,他的作品都有一种真假难辨的诡魅特质——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臆想症患者,真实与臆想在他的小说文本里相互交织,时常给人以神秘、苍凉、阴郁、恐怖之感。这同样是一种现代性与先锋性的体现。路魆热衷于言说死亡,在他的笔下,死亡的阴影无时无刻不在。路魆的作品多讲述人的怪癖与异事,比如在监狱中臆想成狂的叔叔卫无(《拯救我的叔叔卫无》)、沉迷于观察蜂巢的父亲(《阴蜂》)、远离尘世解脱无道的利马(《林中的利马》)、与牛头肉纠缠一生的马伦(《凶年》)、死而复生并以孙悟空之名自称的奶奶(《柊药》)、擅长烹制乌鸦肉的荒木与阿庆(《鸦肉店》)……在叙事上,路魆显然有意地将这些人放置在一个独立、模糊但又总显得阴森恐怖的环境之中。小说中的故事没有明确的发生时间,也没有确切的发生地点,其中的人物多处在远离人世的森林、监狱、医院、工厂里,他们往往孤独地存在。与其说路魆在描绘人的生活,不如说路魆在刻画人死后的灵魂世界;与其说路魆在书写一种真实,不如说路魆在书写一种幻觉。路魆不在乎现实生活的表象与世俗,而是直抵人心深处的焦虑、困惑、挣扎与恶。他笔下的人物大多都是病态的、畸形的,所言所为都显得匪夷所思;他建构的世界中弥漫着阴郁、冰冷与死亡,时常呈现出一幅末日景象,如同艾略特笔下的荒原。他小说的来源不是理性、逻辑与经验,而恰恰是反理性、反逻辑、反经验的潜意识与臆想。比起真实,路魆显然更相信幻觉的力量。于是,在真假难辨、现实与幻想的相互交织中,路魆的小说显得诡气十足。
四、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鬼气”还是“诡气”,它们都在中国当代小说死亡叙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当代作家从古典文学、传统文化、地域风俗、民间信仰中汲取“养料”,精挑细选,化而用之。于是,“鬼气”(“亡灵/鬼魂叙事”)与“诡气”(神秘主义叙事)亦成为当代小说中常见的死亡叙事形态,并生成了“生死轮回”“通灵”“化形”“人鬼共存”“阴阳相通”“天道无常”“生死报应”“神秘预感”等死亡叙事模式。这两种死亡叙事形态,是模仿性与本土化的统一,弥漫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以上论述中我们将“鬼气”与“诡气”分而论之,但实际上,更多的时候它们共同出现在小说文本之中,相互激发,相辅相成,共同构筑出一个神秘、奇崛而又富有个性色彩的小说世界。
[注释]
[1]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0页。
[2]滕威:《从政治书写到形式先锋的移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3]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评介》,《文艺研究》,1980年第5期。
[4]李裴:《小说结构与审美》,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页。
[5]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6]陈平原:《神神鬼鬼·导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7]徐威:《当代作家的死亡观念及其文学实践——以莫言、余华、史铁生为中心》,《芒种》,2017年第12期。
[8]格非:《故事的祛魅与复魅》,《名作欣赏》,2012 年第4期。
[9][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224页。
[10][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39页。
[11]李书崇:《死亡文化》,群言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页。
[12][13][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14]许地山:《道教史》,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15][16][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5页、第42页。
[17]王十月:《米岛》,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18]王十月:《收脚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19]徐威:《自省的姿态与未竟的救赎——论王十月〈收脚印的人〉》,《当代文坛》,2017年第2期。
[20]舒晋瑜、陈应松:中国作家网:《陈应松:我总是躲在时代的某个角落里为弱者辩护》,2017年06月14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614/c405057-29337742.html,2022年6月14日。
[21][22][23][24][25]陈应松:《还魂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第20页、第21页、第254页、第3页。
[26]舒晋瑜:《陈应松:我的语言帮助我到达了那个村庄》,《中华读书报》,2016年11月30日,第11版。
[27][28]苏童:《菩萨蛮》,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29][30]毛峰:《神秘主义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6页。
[31][32][33][34]胡性能:《日常生活的景象》(三题),见胡性能:《孤证》,学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页、第158页、第169页、第169页。
[35][美]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读书》,1998年第4期。
[36]苏童:《城北地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37][38]阿乙:《巴赫》,见阿乙:《鸟,看见我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第158页。
[39]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40]贾平凹:《老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4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2页。
[42]格非:《边缘·自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43]南帆:《纸上的王国》,《读书》,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