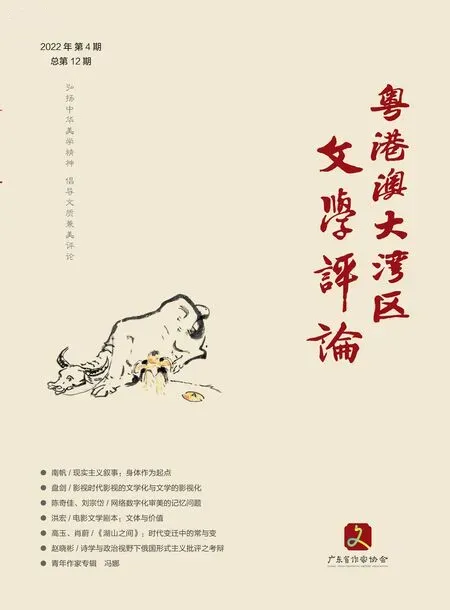电影文学剧本:文体与价值
洪 宏
被称为“一剧之本”的电影文学剧本是电影艺术创造的基础,长期受到我国电影界的重视。1930年代左翼文艺界介入电影领域,即从夏衍等人担任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开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翼电影观念的延续和苏联电影的影响,电影界对电影文学和电影剧作问题的重视前所未有。1980年代初期,围绕电影与文学的关系、电影文学与电影的文学性等问题更是引起了广泛争论。也大致从左翼电影开始,国产电影剧作逐渐从此前的故事梗概、幕表、本事等形态,向文学形态发展和转变。与此同时,电影文学剧本也常常被当作一种文学文体发表或出版。1980年代以后,随着电影产量的快速增长,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影视专业的广泛开设,尤其是最近十来年戏剧和电影领域专业硕士学位的大量设置,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数量急剧增加。毫无疑问,我国已成为电影文学剧本生产大国。
然而,另一方面的情况则是:尽管电影文学剧本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被广泛认可,创作数量也日益增长,但对于电影摄制而言优质剧本却似乎总是稀缺,甚至还会闹“剧本荒”,而且国产电影史上高质量的影片也的确是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多、出自原创剧本的少;同时,电影剧本作为独立的文学作品,虽一直多有发表和出版,也早已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将其纳入研究视野,但很显然,其文学质量和影响力总体上远不及小说和戏剧剧本;还有,电影编剧的地位和权益长期以来都显得比较脆弱,乃至时不时还要发出尖锐的维权之声。久已存在的这些实际问题除了要从现实层面寻求解决之道外,也需要从理论层面不断重新思考和探讨:电影文学剧本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体?应该如何看待它的价值?
一、“电影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电影剧作”
这三个概念很容易被认为是可以等同的,即所谓电影文学,指的就是电影文学剧本,也可以称之为电影剧作。但实际上,对这三个概念的理解,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第一种看法认为,电影文学不是专指电影文学剧本,而是等同于最后完成的影片。因此,电影文学剧本只是未完成的电影文学。张骏祥的观点最有代表性,而且直接引发了1980年代初关于“电影的文学性”讨论。他在《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在一次导演总结会议上的发言》《再谈电影文学与电影的文学价值——在第三届金鸡奖发奖大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等文章中反复强调:“真正的电影文学的完成形式是最后在银幕上放映出来的影片”[1];“影片既是艺术,又是文学”[2]。舒晓明等的看法与此相同,她说:“影片,是根据电影剧本拍摄制作而成的,我们习惯上把剧本叫做电影文学。但是,实际上电影剧本还只是没有完成的电影文学,只有通过电影丰富而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创造性地把电影剧本用文字描绘的形象体现在银幕上,电影文学才得以最后完成。”[3]邵牧君的观点也与此接近,他说:“电影文学是已经存在的影片的全部思想和艺术内容的文字记录作品,一部电影文学作品不能脱离作为它的视听对等物的那部影片而独立存在。”[4]第二种看法认为,电影文学指的是电影文学剧本,但电影剧作则不同,它包含但不等于电影文学剧本。例如,王迪认为:“依我看,作为影片思想艺术基础的不是电影文学剧本,而是电影剧作。早期电影没有文学剧本,但有各种形式的电影剧作。电影文学仅指电影文学剧本,电影剧作则指从剧本到影片的全部创作。电影剧本是由电影编剧完成的,电影剧作则不同,是由电影编剧和导演共同完成的。”[5]苏叔阳和郑雪来也持同样的观点。苏叔阳说:“所谓电影剧作,是指银幕上最后体现出来的全部:思想倾向、内容和表现形式。电影剧作又分为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但最后完成则体现在银幕上,由集体创作完成。”[6]郑雪来说:“电影剧作和电影文学涵义不完全等同。剧作不限于文学剧本,剧作的最后形式是影片完成后才确定下来的。导演剧本也属于剧作,电影文学专指文学剧本。”[7]第三种看法则认为电影文学经历了从早期的幕表、本事,到电影故事、电影文学剧本、电影小说等发展阶段,大概在1930年代电影文学发展成熟。例如,周斌认为,电影文学包括电影文学剧本、电影小说、电影故事。[8]
深入辨析上述三个概念的内涵,并不是纸上游戏,而是有着现实意义。如果承认电影文学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尊重并重视电影文学剧本在电影的思想艺术创造中所具有的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就需要准确界定这三个概念的内涵。
首先,很显然,认为电影文学剧本相对于电影艺术而言不是已经完成的作品,而只是半成品,因而属于未完成的电影文学,只有等影片创作完成后电影文学才最终完成,这种观点看似是在强调电影文学的重要性,即认为电影文学应贯穿于整个电影创作的始终,但因其把电影文学和影片混为一谈,把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和影片创作这两个前后连续却又相对独立的创作过程混为一谈,实际上就不但否认了电影艺术和电影文学的独立性,更严重削弱了电影文学剧本的基础性和完整性。电影文学不是影片;电影文学的创作主体是电影编剧,影片的创作主体是以导演为中心的创作团队;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和影片创作既前后相连又相对独立,前者为后者的二度创作提供思想艺术基础,后者则从文学作品向电影作品转换的过程中进行银幕视听艺术再创造。这些,都早已成为毫无疑义的事实。因此,真正强调电影文学的重要性,就要肯定电影文学剧本无论是作为文学作品,还是相对于未来的影片创作而言,都不是半成品,而是编剧为未来的影片进行的独立而完整的电影文学创作。其次,重视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的重要性,还要对电影文学剧本和电影剧作进行必要的区分。一方面,在电影文学剧本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文体出现之前,广义的电影剧作就已出现,如剧情梗概、幕表、电影本事等,电影文学剧本则是电影剧作和电影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另一方面,在电影文学剧本出现之后,其他形式的电影剧作也仍然存在,如电影分镜头剧本(或导演工作台本)、影片创作完成后的文字记录本等。厘清这些事实,就能更清晰地看到,电影文学剧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电影剧作,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文体,只有电影文学剧本才能为未来的影片直接提供坚实的基础,也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电影文学。电影文学剧本有赖于电影编剧的独特创造,在电影创作中发挥着其他形式的电影剧作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总之,电影文学剧本是一种独立而又特殊的文学文体,它是电影剧作和电影艺术发展到普遍成熟阶段的产物,是电影银幕创造的思想艺术基础。
二、电影文学剧本的“文学性”与“电影性”
要回答电影文学剧本为何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并且具有其他形式的电影剧作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就要进一步探讨其文体特征。电影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文体,自然有着与其他文学文体相同的“文学性”;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则主要体现为它必须具有能够被再创造为银幕艺术的“电影性”。“文学性”与“电影性”及其关系,决定了电影文学剧本的文体形态。
电影文学剧本的“文学性”,主要表现为它具有其他文学文体的共同性,并且要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于敏对电影文学剧本与一般文学创作之间的共同规律有过准确论述。他说:“文学创作是丰富的生活经验的产物,是深刻思想的产物,也是高度语言技巧的产物。在这些方面,电影文学决不例外。”[9]也有论者从“叙事性”的角度看待电影文学剧本与其他文学所具有的文学共性。例如,汪流认为,“影视剧本的叙事部分,包括主题、人物、情节、结构、语言等。”[10]这些叙事部分显然也为小说等所共有。
电影文学剧本作为文学文体的“电影性”,主要取决于它所具有的明确的指向性,即一般来说,或者说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电影剧本创作都是为了被再创造为银幕上的电影。“影片——它是电影剧作家追求的目标,而且是由导演来实现。”[11]换言之,“电影剧本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部影片的基础”,因为,“如果作家想充分、彻底地表达自己的意图,他就会写小说。他不必借助于他人或媒介,这才是纯粹的文学现象。”[12]由于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只是完整的电影创作几个连续阶段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因其目的所在,必然要受到电影艺术特性的制约。所以正如于敏所说:“一部电影剧本,不管它本身的文学因素如何,如果不适合于拍摄,通常都认为是失败的。”[13]这就要求电影文学剧本必须具有“电影性”。所谓“电影性”,主要是指电影艺术所具有的视觉形象性。张骏祥指出,电影编剧“主要运用视觉形象”,“通过可见的形体动作来表现”,“不能忘记文字只是为在导演演员以及摄影场各部分创作人员心目中唤起与自己看到听到的同样的形象的一种手段”。[14]于敏也把这种“电影性”称为“戏剧性”,即“视觉性的”“摄影机眼睛所能捕捉的”“角色的动作和语言所能表现的”,以及“布置冲突”“安排情节线索”,等等。[15]
那么,电影文学剧本的“文学性”和“电影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于敏的论述同样比较深刻。他说:“对于电影文学,单从文学上看,单从电影上看,都不对”,“这是新的文学形式,也是困难的文学形式。”他进而指出,“电影性”,要求电影文学剧本“应当吸收戏剧的一条原则:性格要由主人公自己的言行展示出来”,“漫无限制的语言泛滥,长篇大套的肖像描绘、景物描写和心理分析,会成为电影文学的灾祸”;“文学性”,则又意味着,“只要电影作者提供的是视觉形象,能唤起具体的想象,最好不必束缚他的手脚”,“电影文学不是写在银幕上的,而是写在纸上的;它总是语言的,文学的”,“不能要求文学形象成为银幕体现的等价物。”总之,电影文学剧本“用电影的方法思维,用文学的方法表达思维的结果”。[16]
从电影文学剧本的文学性与电影性及其相互依存的关系出发,电影文学剧本可区分三种具体形态:“一种比较接近分镜头本,除了人物的言行,没有更多的描写和润饰”。这种剧本显然更侧重“电影性”,其“文学性”依存于“电影性”,如苏联著名电影导演兼剧作家瓦西里耶夫兄弟的名作《夏伯阳》。“另一种形式距分镜头本远些,更多地保留了(文学)独立性的一面。不止客观的描写,也透露作者的感情和热情、他的态度和判断。必要的时候,甚至插入作者的评议”,如苏联电影大师杜甫仁科的电影文学剧本《海之歌》。第三种则是通常所见的力图在“文学性”和“电影性”之间保持平衡的电影文学剧本。[17]于敏所区分的这三种形态的电影文学剧本,都既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也符合电影艺术的特殊要求,因此都可以成为未来导演再创作的基础,而剧情梗概、电影本事、电影脚本、分镜头台本等其他形式的电影剧作,显然都不具备如此形态和特征,也就难以真正承担起“一剧之本”的重任。
三、电影文学剧本的价值
一部好的电影文学剧本不一定能拍出一部好电影,但一部不好的电影文学剧本一定拍不出好电影。这句老生常谈的话是有道理的。黑泽明也这样说:“弱苗是绝对得不到丰收的,不好的剧本绝对拍不出好的影片来”,“一部影片的命运几乎要由剧本来决定”。[18]尽管包括卓别林的一些电影在内的早期电影史上的很多杰作并没有事先创作文学剧本(现在看到的大多是根据影片整理的记录本),而大多实验性、先锋性电影导演往往还会否定电影文学剧本存在的必要性,但这仍然无法成为否定电影文学剧本价值的充分理由。电影文学剧本作为文学体裁成熟之前的确有不少电影杰作都没有留下完整的文学剧本,但从根据这些影片整理出来的记录本看,这些电影显然都内含着完善的剧作构思和剧本形态,只是没有以文字文本的形式完整呈现而已。至于那些实验性、先锋性电影导演及其创作,出于对所谓“纯电影”“绝对电影”的追求,致力于抽象的视觉形式创造,其价值固然不可轻易否定,但毕竟真正有较大影响的杰作很少,未能成为以视听叙事艺术为基本特征的电影的主流,因而也就难以对电影文学存在的正当性和重要性构成真正的挑战。
实际上,早已不需要再过多地阐述或引证电影文学剧本对于电影艺术创造的重要性了,因为电影史的事实俱在。需要思考的倒是,为何电影文学剧本如此重要,而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问题却始终存在?这就是:为何原创剧本数量众多,而高质量的却很少?同为文学文体,为何电影文学剧本的阅读价值和影响力远不及小说和戏剧剧本?为何电影文学剧本如此重要,而编剧的地位却常常被忽视甚至歧视?从上述电影文学剧本的文体特性以及电影文学剧本与电影艺术的关系出发进一步思考,也许能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启示。
电影文学为文学和电影这两种不同门类的艺术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正与戏剧文学为文学和舞台演剧艺术架起了一座桥梁相似。因此电影文学要求其文体兼具文学性和电影性,戏剧文学则要求其文体兼具文学性和舞台性(或剧场性)。这两种文学体裁都具有某种中介性质,这与小说显然不同。这种中介性质固然使其独具特色,但很显然也在相当程度上使其受限:它们既要遵循文学的规律,又要兼顾电影艺术或舞台艺术的规律,都可谓“一仆二主”。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说电影文学剧本的影响力因其文体限制而难以在文学领域和小说比肩,那么,为什么它也难以企及与它性质相似的戏剧文学剧本?而纵观世界文学史,戏剧文学剧本的成就和影响与小说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这是为什么?这需要对电影文学剧本和戏剧文学剧本进一步比较辨析。不难发现,虽然两者都是中介性质的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的“电影性”对其“文学性”有着更大的制约,而“舞台性”对于戏剧文学剧本“文学性”的制约则相对小得多。从媒介和本体的角度看,文学和电影是两种差异很大的艺术,前者是以文字为媒介的时间艺术,创造的是一种非直观的形象世界;后者是以影像和声音为媒介的时空复合艺术,创造的是可以直观的影像世界。文字符号的抽象性和文学形象的可想象性,与视听语言的具象性和银幕形象的确定性,使得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反差。因此,“电影文学剧本包含着完成影片所没有的一个极其独特的矛盾:以文学语言描写电影形象所产生的矛盾;它所掌握的手段是文字的,而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银幕的。”[19]而戏剧剧本则不同。传统的主流戏剧无论是文学剧本还是舞台演剧,都以台词(或唱词)为主体,而台词就是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文学语言,这就使得戏剧剧本的文学性不但能较少地受到舞台性的削弱,而且舞台艺术的时空限制及其剧场性等,还会反过来要求其文学语言必须突显内涵的丰富性和形式的精炼性——正因为如此,杰出的戏剧文学剧本往往能创造独具特色的杰出的语言艺术。电影文学剧本与戏剧文学剧本的这种差异,也能解释为何那种文学性强但如果未能很好兼顾电影性的剧本常常难以被搬上银幕,而戏剧剧本则相反,很难被搬上舞台的往往是文学性和文学价值不高的剧本,优秀的戏剧文学则能常演常新,并且能经受起各种观念和形态的舞台再创造,成为舞台艺术的常青树。可见,电影文学剧本文体的这种特殊矛盾性,使其很难充分发挥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全部魅力。难怪有人会说,“电影剧本的存在是为了电影界内部的人进行专业性的阅读的。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学种类”[20];“电影剧本的可读性一般都较差”[21]。
从电影文学剧本和未来影片创作的关系看,也能进一步发现电影文学剧本的边缘性质。电影文学剧本无论其电影性多强,终究还是一种文学形态,尽管它是独立、完整的作品,但对于电影创作的全过程来说,则仍然只是完成了第一道工序。虽然在随后的创作中,编剧也可以继续介入,但毕竟影片摄制是另一种性质的艺术创造,起决定作用的已不再是编剧而是导演或制片人。如果银幕二度创作不成功,自然会损害剧本的价值;即使二度创作获得成功,并且电影文学剧本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事实是那获得成功的已不是电影剧本,而是作为另一种独立艺术的影片,影片的声誉和影响会极大地掩盖剧本的价值。加之电影作为比文学更为大众化的艺术,其影片创作既要遵循电影艺术的规律,还要遵循电影工业生产和商品市场的规则,这就更加使得电影文学剧本原本具有的重要的基础作用和独特价值不断被掩盖、忽视或消解。
总之,作为沟通电影和文学两种艺术门类的重要桥梁的电影文学剧本,其文学性和电影性兼具的文体特征,一方面使其在电影艺术创作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其在文学和电影两个领域都明显处于某种边缘状态:既难以成为一流的案头文学作品,又总是落入电影艺术和电影市场光环之外的阴影之中。这是我们在思考电影文学剧本的价值和现实境遇时,应该面对的事实。
[注释]
[1]张骏祥:《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在一次导演总结会议上的发言》,《电影的文学性讨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2]张骏祥:《再谈电影文学与电影的文学价值——在第三届金鸡奖发奖大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电影的文学性讨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3]舒晓明、文伦:《谈电影的文学价值》,《电影的文学性讨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4页。
[4][21]邵牧君:《电影、文学和电影文学》,《电影的文学性讨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第232页。
[5]王迪:《电影剧作及其观念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6]苏叔阳、左元平:《电影剧作及其他》,《电影艺术》,1996年第4期。
[7]郑雪来:《漫谈电影剧作的发展过程》,《电影新作》,1982年第6期。
[8]周斌:《电影文学:现代文学史研究不能忽视的领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9][16][17]于敏:《本末——文学创作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电影艺术》,1962年第3期。
[10]汪流:《电影编剧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11][苏联]别洛娃:《论当代电影剧本的文学特性》,泽林译,《世界电影》,1990年第2期。
[12][捷克斯洛伐克]伐爱斯:《电影剧本是一种独立的文学作品吗?》,管蠡译,《世界电影》,1957年第6期。
[13]于敏:《探索》,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第24—25页。
[14]张骏祥:《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中国电影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18]转引自汪流:《电影编剧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19]李少白:《辩证地历史地看待电影和电影文学》,《电影的文学性讨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页。
[20][苏]德罗巴申科等:《八十年代苏联电影剧作的几个紧迫问题》(续),泽林编译,《世界电影》,199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