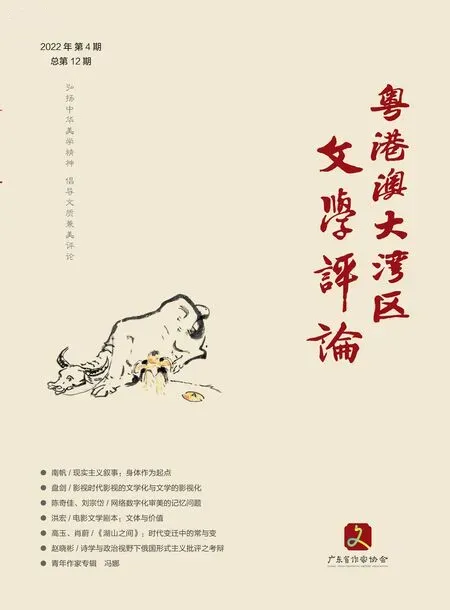影视时代影视的文学化与文学的影视化
盘 剑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文学还拥有极高的地位——那时不仅有许多文学期刊甚至一本文学期刊的征订量可以达到数百万册;那时新华书店和图书馆总是人满为患,读书、购书、藏书蔚然成风;那时一篇小说可以产生全国轰动效应,引发全民讨论,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那时作家可以一文成名、一书成“家”、一诗名扬遍天下;那时所有理科成绩不好的中学生都会做一个“作家梦”;那时,尽管社会上已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但在几乎所有综合性(包括师范类)大学里中文系仍然排在所有院系的最前面,中国语言文学理所当然为学科“老大”。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文学的身价和地位忽然一落千丈,上述一切不复存在。这时文学不再为人们所重视,作家、诗人头上不再有光环;这时再好的小说、诗歌也不再有多少读者,文学期刊生存困难,原来万众瞩目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其评奖结果也似乎只有参评和获奖者才会特别关注了……这一切显然都是因为影视——影视开始取代文学吸引人们眼球、引领社会心理、激荡大众心潮:电视剧《渴望》《北京人在纽约》播放时竟致“万人空巷”,演员凯丽、王姬、姜文因为饰演剧中主角而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这时成不了科学家的年轻人不再做“文学梦”“作家梦”,而开始做“影视梦”“明星梦”——影视粉墨登场,文学黯然离去。“这时”与“那时”其实相距不远,但却恍若隔世。
然而文学真的离去了吗?影视时代真的只是“影视的时代”?
一、作家成为编剧
许多“过来人”应该都还记得,经济大潮携带大众文化以影视为浪头冲击文学之初,包括创作者、评论者和研究者在内的整个文学界都非常愤怒而绝望,似乎文学已近末日,“人文精神”也正随之失落——当时不知开了多少相关的研讨会,而且几乎所有研讨会都开成了对文学的“追思会”和对以影视为主要形态的现代大众文化的“批判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文学整体上确实不像从前那样“神一样”地存在了,却也似乎并没有真的走向灭亡。且不说各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或文学院虽然不一定能够继续做学校院系“老大”了,但每年该招多少本科生、研究生还继续一个不少地一直在招着;中文专业毕业生找工作也不比别的专业差甚至比有的新兴专业还要好;当然所有文学教授、副教授、研究员也基本上没有失业,原来教什么课程、做什么研究、写什么论文现在也一如既往、“涛声依旧”。唯一算得上比较大的变化是作家的业内身份有了一些不同:许多人不做小说家或诗人了,而改“行”当起了编剧——影视编剧。
编剧当然还是作家,因为剧本仍然属于文学——无论戏剧剧本还是影视剧本。剧本原本也是文学的四大传统体裁之一(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尽管排名靠后。不仅剧本是文学,由此作为“一剧之本”的影视剧本使文学在影视时代仍然得以继续生存;而且,在中国,文学作品的改编一直是影视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更使得冲击文学的影视实际上与文学关系极为密切。
事实正是,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电影还处于诞生初期,就开始与当时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合作,借助文学改编建构电影叙事,形成了文学化的“鸳鸯蝴蝶派电影”;[1]三四十年代又与左翼作家合作,以“左翼电影”的创作延续了中国电影的“文学传统”。[2]这一“文学传统”虽然后来被“第五代”导演于八十年代通过强调电影的视听效果、回归电影影像本体而终结,但却又从九十年代开始被蓬勃兴起的电视剧创作所继承。据粗略统计,在所有国产电视剧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改编自文学作品——截至目前,从古至今的所有文学名著几乎都被改编了一次,有的(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庸小说等)甚至被反复改编。
由此可见,所谓的影视创作,其实不仅包含“剧本”这一文学体裁,而且还大量地把文学作品作为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没有离开文学。或许正因为如此,传统文学作家参与影视(剧本)创作就显得顺理成章,原来的小说作者甚至诗人也能够顺理成章地成为影视编剧。而随着大量作家从小说作者或诗人到影视编剧的“业内改行”,文学的创作主体被充分地保存了下来,因而所谓的“影视对文学的冲击”也就不过是文学内部各体裁主次位置的一次变换或主流体裁的重新选择——如果说以往文学的主流体裁是小说、诗歌,散文次之,剧本被边缘化;那么在影视时代,则剧本成了主流体裁,其他都相对不再那么重要了。其实这也符合文化、艺术、文学的发展规律——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主流文化、主流艺术和主流文学: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从文学艺术到影视艺术,从小说、诗歌到影视剧本——这一切都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传播媒介的选择,因为影视时代归根结底是由影像媒介取代文字媒介而成为主流媒介所带来,并由其决定其主流文化和艺术。
当然,在以影视为主流艺术和文化的时代,尽管影视中充斥着文学元素或被全面文学化,然而所有艺术、文化包括文学又都有可能受到影视的影响、面对影视的挑战和面临影视化的生存。
二、影视作为文学
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在影视时代,文学的影视化生存不仅仅表现为影视编剧拥有作家身份、剧本体裁具有文学属性和影视内容多为文学题材——这实际上是“影视文学化”的换位表达;而且,影视艺术似乎还从整体上在创造一种“另类的文学”,抑或“新的文学”。
相关史料显示,早期中国电影除了与鸳鸯蝴蝶派文学、左翼文学合作创作文学化的电影,还出版发行了众多电影期刊,“自1921到1949年,先后出版过的电影杂志共计206份(包括电影月刊、周刊、专刊)。”[3]这些期刊既刊载电影剧照,也发表一些叙述电影情节的文章,亦可看作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此外,当时电影公司还发行“电影说明书”,其原本是在电影院供观众选片、购票时作为参考的阅读材料,却又不是简单的影片介绍,而是专门请鸳鸯蝴蝶派作家撰写的文笔优雅、文学性很强的电影故事,更是可以当小说来读的文学作品,正如当时一本畅销的城市指南手册《上海门径》作者所说,“倘能把每次所看电影的说明书积面成帙,倒是绝妙的小说集哩”[4]。这些新的文学品种的出现当然并不是偶然的,也不仅仅局限于当时的电影,几十年后,每当一部原创电视剧热播,出版社都会适时推出根据其剧本改写的该剧“小说版”,而显然这些“小说版”既不能不算文学却又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毕竟它们只是电视剧的衍生作品。
当然这些期刊上的电影故事、电影院的“电影说明书”和电视剧的“小说版”作为文学新品类的“非传统性”还主要表现为题材来源于影视,实际上与影视改编文学是同样的机制、反向操作而已。还有抛开电影内容而沿用影像思维、电影手法进行创作的更另类的新文学,那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穆时英、刘呐鸥、黑婴为代表的中国新感觉派作家的创新尝试。新感觉派作家与鸳鸯蝴蝶派作家一样,都与电影关系非常密切,但二者对电影的态度、和电影的相交却完全不同,甚至是刚好相反。
鸳鸯蝴蝶派作家对电影并没有专门研究,也不想研究,他们虽然给电影公司写电影剧本却既不按照剧本的格式写也从来不用镜头语言和蒙太奇结构(他们应该不太具备电影专业知识),所以他们写的电影剧本不仅大多改编自文学作品,而且形式上也更像传统的小说(故事),也因此整个鸳鸯蝴蝶派电影都是文学化的电影,其创作的“电影说明书”一类“新文学”之“新”也仅在于内容为电影故事,语言及结构上与传统文学却无区别。
而新感觉派作家则在深入研究电影的基础上,将电影的镜头语言和蒙太奇语法用于自己的小说创作,在文学文本中强调空间与声音的呈现,由此创造出一种以文字符号建构起来的“隐性视觉形态”[5],这便在某种程度上使文学从原来的“时间艺术”变成了一种新的“时空艺术”。当然,他们这种操作对于本文论述最直接的价值和意义,是为我们提供了文学与影视更深层次的相互影响和互相成就,或文学影视化生存的一种形态。
如果说作为因影视而生的另类文学或所谓影视“新文学”,“电影说明书”及早期电影期刊上发表的电影故事还基本上用的是一种“旧瓶装新酒”模式,而新感觉派作家对“隐性视觉形态”的建构进一步对这种与影视相关的“新文学”做了触及本质属性的全新创造,那么中国电视剧的“影像元素的文字化”“体裁类型的多极化”和“叙事结构的章节化”则无疑可算是“影视作为文学”的终极表现。
相比电影,电视剧与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是因为其所依托的电视媒介与广播同源,而广播本质上属于语言媒介,强调语言的信息传播和艺术创造——电视虽然也有画面,但其画面的表现力和重要性远不如电影;电视的语言元素甚至比广播更丰富,不仅存在大量有声语言,而且还有以字幕形式呈现的文字书面语言,因此电视剧就像声画并茂的广播剧,并与文学同属语言艺术,甚至以两种语言形式兼具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双重特征。不仅如此,电视剧的体裁类型、叙事结构也与文学非常相似,不仅在短篇、中篇、长篇的体裁划分上电视剧可以直接与小说相对应,而且电视连续剧的“集”与小说的“章节”也具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结构形式、叙事特点和表达功能,事实上早期的电视连续剧如《夜幕下的哈尔滨》等就是完全按照章回小说的形式组织叙事、结构情节的,包括使用叙述者的语言,这便使得观看电视剧就如同阅读小说。同时,各种篇幅的分类、分级存在也使得电视剧创作可以原汁原味地改编短、中、长篇任何体裁的小说作品,理论上可以不用做任何删节、增补和转换叙述方式,这也是几乎所有古今文学名著都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的重要原因。也因此,电视剧究竟是影视艺术,还是影视时代的另一种文学?已不是一个答案不容置疑的问题。
三、文学从未离去却又确实离开
由上所述,我们看到,影视时代到来以后,文学表面上受到了巨大冲击,而实际上不过是原来作为主流体裁的小说、诗歌让位给了剧本,而剧本仍然属于文学;不过是许多作家从原来的小说作者、诗人“业内改行”成了影视编剧,文学的创作主体并没有分崩离析;更何况影视从一开始就离不开文学,在影视时代也同样如此,不仅围绕文学(如以既有的文学作品为题材)进行创作,而且还以自己的资源、功能推动了文学的创新发展,最后甚至把自己(如电视剧)整个地做成了“另一种文学”!由此似乎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文学从来就未离去。然而,文学真的从未离去吗?
1985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被改编成28集电视连续剧播放,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家普遍认为该剧“忠实还原了老舍原著”[6],而实际上,从小说到电视剧,《四世同堂》在表面的“忠实于原著”之下其实与原著并不完全一致。毫无疑问,二者都有两方面的内容和表达:一是反映抗战的历史;二是表现国民的劣根性,如封闭、愚昧、妥协、敷衍、无聊、自私。但小说和电视剧在表现这两方面内容时侧重明显不同:电视剧是以抗战为主,并且极力渲染、歌颂人民的抗战斗志和精神;而老舍的小说却实际上重点不在战争——战争只是特定的环境或背景,作家更关注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包括人的劣根性,并从反思和批判劣根性出发来探讨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精神与命运。二者相比,当然是老舍原著的表达更深沉、更深刻。但电视剧却只能那样改编,不仅因为该剧是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而拍摄,而且因为电视剧本身就是大众传媒创造的大众艺术,不可能像小说那样作者能够自由、独立地表达。由此不难发现,无论电视剧多么像文学,哪怕它具有文学的各种元素、形式——如同前文所述,它却绝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学。
不仅如此,在影视时代,由于受影视及其大众传媒、大众艺术、大众文化从整体环境到具体因素、各种机制的浸染、制约和影响,即使是传统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也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譬如一个时间段里集中出现的某些帝王题材、打黑题材乃至反腐题材小说,就如同那些定位非常明确的网络修仙小说一样,带有明显的市场策划性,因为它们刚好与这一阶段的电视剧热门题材惊人的一致,并且这些小说出版后很快就被拍成了电视剧。由此我们便发现,在影视时代,不仅原有的文学名著有可能在被改编的影视剧中失去作家的独立表达,如同老舍的《四世同堂》;而且一些新的文学作品也不再具有作家创作的独立性,而更倾向于以策划代替灵感、以满足市场需求代替个人自我表达。这就使得在影视时代,一方面是影视保留了文学的元素,电视剧甚至整体上都像是“另一种文学”,如同前述;而另一方面,文学也在被影视化,而且这种影视化是深层次的,直指文学核心并遮蔽了文学的本体精神,从而将文学变成绝不属于文学甚至为原来文学所唾弃的“另一种影视”,在这个意义上就相当于把文学给灭了。
[注释]
[1]盘剑:《论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创作》,《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2]盘剑:《革命文艺与商业文化的双向选择——论夏衍三十年代的电影文学创作》,《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3]杨村:《中国电影三十年》,世界出版社1954年版,第24页。转引自[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4]王定九:《上海门径》,中央书店1932年版,第22页。转引自[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5]盘剑:《论新感觉派小说的隐性视觉形态》,《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6]百度百科“四世同堂”剧集评价,https://bai ke.baidu.com/item/四世同堂/5388469?fr=aladdin#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