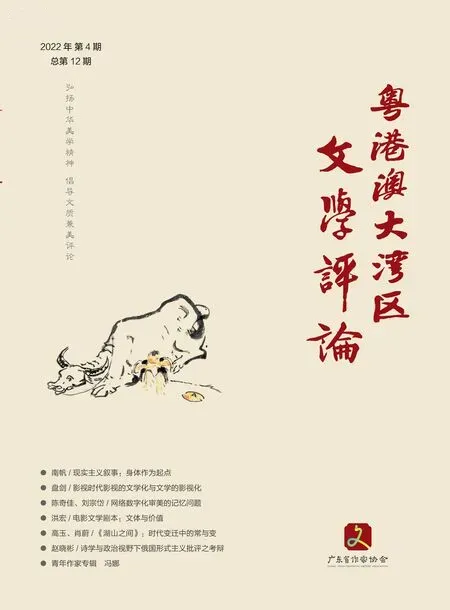地方馈赠、文化记忆与心灵镜像
——冯娜诗歌论
苏文健
冯娜是一位宁静的诗人。她的诗歌话语内敛克制,干净利落,想象力丰沛,诗风雍容自若,几乎没有语言的风暴,更多的是切身生活经验的自然流溢,透露出纯净、真切恬淡而充满蓬勃的生命力。阅读她的诗歌,我们不难感受到其独特的诗学张力,朴实与隐忍,彷徨与挣扎,犹疑与退却,希望与救赎。她的作品中有对自然的细腻感悟,对日常生活纹理的诗意发现,对现代生活、生命的伦理质询,也有对个体及集体历史文化记忆的重塑再造或发明,更有因时空流转所带来的对个体内在情感幽微的捕捉刻画等,这一切汇聚成诗人对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少数与多数、边缘与中心、地方与全球、过去与当下甚至未来、现实与心灵等多重话语空间交织的文化场域之斟酌损益。进而言之,她的诗歌作品也俨然可理解为一部日常生活史、纪游史、情感史,甚至一部心灵史,成为刻写一代人或一个时代的侧影。阅读冯娜的诗歌,可以检测发现地方性知识、性别话语、族裔政治、代际经验等理论资源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一、地方的馈赠
冯娜出生于云南丽江永胜县,白族青年,上大学后离开故地,来到异地他乡的都市广州,工作、生活并定居于此,与当代中国转型期众多出生于1980年代的青年人有着大致相似的履历[1]。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与出生地拉开时间、空间、心理的距离后,抒情主体的自我与他者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这不仅仅是一种抒情视角的变化转换,如外在凝视、内在发现与对照互看,更隐含一种情感—身份认同的微妙体认,在展现一位现代都市生活的白族青年、新时代知识女性的心灵风貌。
对作为“地方性知识”[2]的云南(出生地)之书写,的确是人们阅读冯娜诗歌时获取的重要感受。在他乡建构故乡,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成为这一代人宿命的表征。冯娜的诗歌写作是在返回出生地的再出发,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词根,这使其与纯粹的少数民族诗人的书写保持着审慎的距离。可以看到,在她书写云南(出生地)的那些诗篇,如《酥油灯》《龙山的女儿》《龙山坝的夜》《澜沧江》《金沙江》《洱海》《冬日的拉市海》等中,因为诗歌独具特色而丰富多元的意象,及其营造的边地精神文化审美空间,不由得让人心驰神往。然而,诗人并不刻意放大这种声音,并不强调这种根性经验的独特性。“他们教会我一些技艺/是为了让我终生不去使用它们/我离开他们/是为了不让他们先离开我/他们还说,人应像火焰一样去爱/是为了灰烬不必复燃。”被教会的一些技艺(我终生不去使用它们,如狩猎、采蜜、种植……)与被教给却已忘记的语言(藏语)、教给却没有唱出的高音(歌唱)形成鲜明的重复与差异,而这恰恰是通过“他们”与“我”呈现出来的:我既是他们,他们也是我,但我又截然迥异于他们。诗作通过“教给”“不过问”“为了”的重复和“教会”的差异使用,凸显出生地的根性,又经由“已经”“至今”“终生”的时间变化带来的轻重感受,更强调诗人对出生地的馈赠之爱、致敬和魂绕梦萦。
这种地方感在《云南的声响》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在云南 人人都会三种以上的语言/一种能将天上的云呼喊成你想要的模样/一种在迷路时引出松林中的菌子/一种能让大象停在芭蕉叶下 让它顺从于井水。”天上的云、松林的菌子、孔雀绿的脸、土司家放出另一种声音、云杉木、龙胆草、金沙江等,成为“云南的声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云南,那么声响,“充满了诗意、灵气、神性、巫气的土地”(冯娜语)。与前两首诗写到语言、声音等相似,《一个白族人的祝酒词》则描写边地特殊场景中的声音/歌唱——祝酒词。“山上若是还有豺狼 请它进屋/山上若是还有松茸菌 请它烤火/山上若是还有听不懂汉话的人 请他饮酒/我不知道你们在他耳普子山活了多少世/我也活成了一只没有故乡的猛禽 大地上的囚徒/请举起杯中的吗咖酒吧——/水若是还向东方淌去/命运拿走的 他留河会全部还给我们”。在此,出生地是一种命运。诗人带着语言、抒情的嗓子、淳朴的心性,一路前行,尽管“我”活成了“一只没有故乡的猛禽”、一个“大地上的囚徒”。爱德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认为:“地理的观念决定其他观念:想象上的,地貌上的,军事、经济历史上的和大体来讲文化上的观念。它也使各种知识的形成成为可能。这些知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依赖于某种地理的和人工的性质与命运。”[3]吉尔·德拉诺瓦也指出,“民族精神有时像一个神话故事一样充满神秘的色彩,但常常是虚构的,人们更有可能认为民族精神不会得到全部的表现,而是暂时凝结在事物、景物、习俗、惯例,尤其是话语、符号、文字、作品中。”[4]进而言之,冯娜这些具有地方性知识的诗歌作品,尽管带有民族的、地域的、原乡的独特元素和音符,但又不为它们所囿限,而是经过了诗人心灵深处的独特沉思和诗意发现,“化身为一个民族集体化想象的代言人”[5],构筑出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审美空间。“这个空间不是现实中的故乡,也不是当下生活的所在地点,而是一种打通故乡与生活所在地、连通起诗人身体所到之处和知识所涉之处的、内部和外部相交融的多维空间。诗人将它们通通置入自己的诗歌内部,建构起独特的诗性空间。如此,也能理解为何冯娜写地域、写风景的诗作,普遍是以自己童年成长记忆中的风景作为想象的原点,然后将她当下所看到、所想象到的风景纳入,以此建构一个以自己身份为原点、装饰着五湖四海风景的诗歌王国。”[6]换言之,诗人在“寓言化的空间”中,从回味、怀念的亲切到变得疏离与陌生的不安和忐忑,既有对出生地故乡、复数地方等反观、审视、反思和重构,同时也有对自我的反省和追问。
随地方性知识而来的,是诗人对亲情伦理、生命自然的体验、叩问与思索。这在其众多作品,如《春天的葬礼》《雪的墓园》《云上的夜晚》《母亲》《祖国》《家世》《深入地表的秘密》《一位朋友死在异乡》《群山》《私人心愿》《卓玛的爱情》《天葬台》《隐者》《苔藓》《恐惧》《迷藏》《消逝》《看不见的吹奏者》《疑惑》《金沙江的死者》《无证之罪》等中可以见出。生命、死亡、溺水、殉情、消逝、葬礼(水葬、天葬)、墓碑、墓地、墓园等成为这些诗歌经常出现的意象或词语。谢有顺认为,“生命是一种存在,对它的探问,一直是冯娜诗歌的中心议题。”[7]对于亲情伦理,《接站的母亲》《与父亲掰手腕》《陪母亲去故宫》《隔着时差的城市》等作品多有流露,语言清通凝练,情感细腻真挚,令人动容。其中,《纪念我的伯伯和道清》颇具代表性:“小湾子山上的茶花啊/请你原谅一个跛脚的人/他赶不上任何好时辰/他驮完了一生,才走到你的枝桠下面”。此诗虽短短四行,却高度浓缩人一生的历史。一个跛脚的人赶不上任何好时辰(不是时候或时代却胜似它们),而全诗著一“驮”字而意境全出。“驮”所昭示的轻与重及快与慢,既是一种生命姿态,一种精神力量,也是艰苦隐忍的存在表征。此诗用最省净的语言表达了最丰富的历史生命信息。“山上的茶花”与“跛脚的人”隐喻了一个生命的来路与归宿。同时,诗作通过“请你原谅”“才走到你”等第二人称祈使句的巧妙运用,营造一幅拟人化的在场图景,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与此相似,《春风到处流转》则这样写道:“春风吹过桃树下的墓碑/蜜蜂来回搬运着 时令里不可多得的甜蜜/再没有另一只鸟飞过头顶/掀开一个守夜人的心脏/大地嗡嗡作响/不理会石头上刻满的荣华/也不知晓哪一些将传世的悲伤。”桃树下的墓碑与来回搬运的蜜蜂、石头上刻满的荣华与传世的悲伤形成鲜明对比,一静一动,一悲一喜,短暂与传世等,诗歌在此构筑了春风与桃花(树)的相互凝情含笑,“桃花依旧笑春风”,悲慈也在其中。这几首诗都很好地透露出冯娜诗歌的举重若轻之美学质素。
其实,对生死的沉思与怀想,源自诗人对佛教文化的独特理解。读者不难发现其诗作中经常出现的语汇或意象如经卷、经幡、红尘、肉身、庙宇、莲花、酥油灯等。如《酥油灯》书写“肉身以外的黑洞 加重经书的奥义”,燃灯、花朵、涅槃等从容淡定,天地合一,衣袍、发肤、名姓、执妄等红尘皮相,两相对比,形成肉身与精神的辩证,只要心境足够纯净,敞开无蔽,“我在茫茫的水域中黯淡下来/同时获得一座庙宇”。有与无、生与死、一与多、天与地、白昼与黑夜、肉身与精神、红尘与化外等都可以同时并存。而《莲花》写由经书引发的所思所想,“一卷经书放在窗上 夜里感到寒冷/一阵又一阵”。狐鬼、桃花、黑暗、磷火等给人寒冷阴森之感。因为“我知道 无需加持/只要伸手捻住一点光焰/它们就会熄灭 并/全部回到我的体内”。与《酥油灯》相似,肉身内与肉身外、光亮与黑暗、光焰与熄灭、生与死等都在一念之间。《西藏》中“赐我最宁静的大悲大喜”,“在经书里化为莲花”,“赐我出窍的定力”,“不让尘埃 回到我的身上”。这是尘归尘土归土,是“质洁本来还洁去”的澄明。而《贝叶经》则更是将以上作品中的主题形成一个综合:“借鹰羽的白拨开酥油灯的棉芯/我总是害怕听到某种东西 破壳而出/在夜间 植物生长如电/河流平平铺开 沙石缓慢下沉/我将身体翻过来 一颗细痣迎向星斗/一切被神标记过的/都未曾走失。”
质言之,从代际角度而言,冯娜诗歌给人模糊的代际经验,或者说她是跨越代际的。从性别话语而言,冯娜的诗歌没有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也没有女性对男性的反抗与斗争,而代之以人性全面反思的书写,《苔藓》《你不是我的孩子》等或可窥其端倪。从故乡/出生地书写层面看,冯娜的诗歌,没有对故乡黑暗丑陋的书写,没有不满、揭露、批判等情感取向,破除原乡迷思,虽不乏对故土和漂泊的两相审视,也有如《速朽时代》《食客的信仰》《盲音》《岭南》《南方以南》等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批判,但更多的还是对故乡日常生活人情物理的咀嚼、抚摸和感喟,并经由个体经验来传达某种抽象思想和复杂现代情感。在族裔性层面,她的诗歌既没有对所在少数民族的历史、神话、故事、传说等的刻意渲染,更没有重新发明再造民族传统的宏大野心,而是描摹个体经验与复杂情感,借此见证时代的变迁,往往出之以理性的思辨和诗性的想象,显得更为平和持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速朽的时代,冯娜试图以世界性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和独自想象、重构故乡或复数的地方,书写别样的“恋地情结”,既显示其独特的地理、风景、文化标识的同时,又使其具有某种超越性的意义,成为一个时代的某种象征、隐喻甚或“中国寓言”。在此意义上,冯娜的诗歌虽量不算大,却充满丰富性、复杂性和内在生长性,以及在当下诗坛版图中的独异性,受到众多关注,自不待言。
二、文化的记忆
诗人冯娜是一位抒情的歌手。“一个被岁月恩宠的诗人,就不会放弃抒情。”(《杏树》)其诗歌的抒情,既有中国抒情传统的承继,也有现代性体验带来的抒情丕变,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的综合。“冯娜的诗歌,它有大地般的质朴与沉潜,也有现代诗的复杂和精微,她的写作,可视之为是传统与现代的综合。”[8]冯娜诗歌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所抒写的故事、铺设的场景以及所抒发的思想感情,都是诗人一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感受。其中,除了前述的地方性知识及其伦理思考以外,首推其独特的纪游诗和历史文化记忆的诗篇。
纪游诗,或又称之为行旅诗。一般认为,纪游诗范围比较广,属于今人的分类,不见于古籍,顾名思义,它是纪录旅游所见所感之诗,所见无非山川风物,所感无非人情世事,或赞美山水而寄情于山水,或凭吊名胜而托意于名胜。由于现代交通的便捷,朝发夕至,出行旅游更是老生常谈。作为在现代都市生活的青年诗人,几乎“登高必赋”“有史为证”,在冯娜的诗歌作品中,纪游诗,堪称大宗。譬如《庚寅年路遇大雪》《滇西公路边卖甘蔗的人》《龙山公路旁小憩》《夜过凉水河》《夜过增城》《过漓江》《漓江村畔》《夜宿幔亭山房》《沅水上》《夜滞湘西山间》《无名寺途中》《夜宿珠穆朗玛》《癸巳小满夜遇暴雨》《癸巳年正月凌晨遭逢地震》《一个人在山里住》《乘船去孤山》《乡村公路上》《夜访太平洋》《在这个房间》《在外过冬》《戒台寺独坐》《潭寺听钟》《夜行玉渊潭》《陌生海岸小驻》《山西即景》《驱车过琵琶洲》《湖畔小憩》《夜宿龙子湖》《对岸的灯火》等,涉及怀亲、友谊、纪游、宴饮、咏物、咏史、节令、品艺、时事等,记录了诗人走南闯北,游历山川、人文胜地的足迹与心迹,及探测风景的现代性之旨趣。冯娜在第29届青春诗会的感言中引述博尔赫斯的话说道:“我写作,是为了流逝的岁月使我心安。”这部分诗篇可读成诗人的一部纪游史、情感史和生活史,成为其纪录生活、描摹情感、烛照社会、思考人生和洞悉历史的重要话语空间。“从大江对岸到云端俯瞰,我开始了人生最初的行走。沿途,拾掇起文字就如同看云的喜好,是一个人隐秘的快乐、悲伤、忧愁、内心的观照和外省,或其他。”“我就这样,在诗歌里穿行,如同身背无数故乡和他乡的云朵,活着,并在诗歌里多活了一次。”[9]“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此之谓也。在冯娜看来,诗歌就像一份被记错生日的礼物,写诗既创造世界,启发人,也是一种修行、对自我的教育。
然而,与中国抒情传统大为不同的则在于冯娜诗歌的抒情语调,对现代复杂情绪的挖掘和对情感纹理温度的捕捉。譬如《对岸的灯火》中:“我看到灯火,把水引向此岸/好像我们不需要借助船只或者翅膀/就可以轻触远处的光芒”。此写水、灯火与夜的缠绵辉映,千灯互照,各得其所。《庚寅年路遇大雪》中:“大雪在暗中纷纷而落 我伸出手去/一个冬天的白也未接住”。此写大雪的磅礴。《龙山公路旁小憩》:“近处有松树 苦楝树 我不知道名字的阔叶树/它们高高低低 交错生长又微妙地相让”。这写树木的长势喜人。《龙山坝的夜》中:“黄昏过后/坝子的尽头无数星辰将要分娩”。此写神秘的星辰宇宙。《听说你住在恰克图》中:“水流到恰克图便再也不会回头/你若在恰克图死去 会遇见一个从未到过这里的女人”。此写恰克图的回旋伟力。《乘船去孤山》中:“前世的缘分,今生同船一渡就已经用尽/十年不够孤山长出一片松林/十年足够我翻山越岭 再不遇同船之人”。此写人生际会的偶然。《癸巳小满夜遇暴雨》中:“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行路/大雨先是推搡我 我身体里搭建了多年的砖瓦纷纷而落”。此写暴雨如注的力量。《癸巳年正月凌晨遭逢地震》中最后一句:“母亲的遗憾是没有年轻的男人在这个时候爱上我”。此写灾难的遗憾和大写的母爱。《夜过增城》中:“粤水怀有十二个罗汉的慈悲/荔枝因为一个人缺席而推迟成熟”;《卡若拉冰川》中:“在山上你在苔藓间按灭烟蒂/大地轻轻颤栗了一下/所有云朵都动荡不安”;《晚安》中:“大病初愈的月光 白戚戚地并膝坐在台阶上”。《一个人在山里住》中:“一个人在山里住,觉得/人活得过于坦荡也没什么意思/夜半听见敲门也不会想到有鬼/即使有鬼/也只想,请他进门喝口热水”。《戒台寺独坐》中:“太多人诉说他们的遭遇,我不必再说/太多祈求和祷告,我不必再诉/戒律一代一代,让松树长出不同的脸孔:/自在、抱塔、卧龙……/不必再数,我也在其中”。《沅水上》中:“黄昏以羽翅合拢的速度跌进沅水/岸上花期纷攘 比昨日更加浩瀚/风从其他无人的山边吹来/我感到一些不安 仿佛宁静已深入膏肓/这分明是沉落/未被我们看见的事物提早向黑暗潜进/分明是临终之美/却发出分娩时的光亮”。冯娜诗歌的抒情性,善于通过对话与潜对话或者多重反诘,表达一己的内心情感与经验感受,展示自己对存在的质询与抚慰。这种沉潜而智性的抒情语调,及自然清新的词语或意象,诗意蓬勃盎然,在冯娜的诗作中所在多有,而这都源自诗人的语言自觉和想象力。准此,冯娜以凝练的语言表达内心复杂的情感,尽量剔除芜杂的叙述性、说明性的文字,多以意象、象征等话语修辞营造接受受阻的玄思性,诗味隽永遥深。
其实,这些诗歌的抒情话语是克制的,隐忍的,与直抒胸臆式抒情相去甚远。这也使得其抒情性与中国抒情传统之抒情特质有了较大区别。张柠指认其为“执拗的抒情性”:“这种冷抒情,或者说隐性抒情,与古典诗歌的抒情方式有明显区别:从情绪上,冷静的蓝色代替了明亮的黄色,没有直接强烈的赞美或愤怒的抒发,勃发的激情是从平淡的叙述中缓缓流出;句法上则避免使用古典抒情诗那种富有气势和感染力的句式;意象代替了承载过于浓重的文化和历史内涵的传统抒情意象,回归自身与日常生活;最根本的,是经验的传达方式上,宏大事物都被消解在个体情感和经验中。”[10]林馥娜就其诗歌叙事与抒情的辩证关系,认为:“冯娜并没有因为内里的抒情本质而忘却叙述的节制,情之动人,在于隐忍。她在节制的抒情之中所融入的具体事物和场景,则使本来容易轻飘失重的抒情稳稳地驻扎于大地上,避免了神一样的‘全知’视角抒写的虚妄。”[11]良有以也。
显然地,忆旧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纪游而来的。文化记忆是所有文学形式最为倾心的主题。记忆本身就是一种写作的方式,因为记忆所激发的就是作家的想象力。“记忆者同被记忆者之间也有这样的鸿沟:回忆永远是向被回忆的东西靠近,时间在两者之间横有鸿沟,总有东西忘掉,总有东西记不完整。回忆同样永远是从属的、后起的。文学的力量就在于这样的鸿沟和面纱存在,它既让我们靠近,与此同时,又不让我们接近。”[12]文化记忆诗学试图挽回诗人通过文化记忆建构起来的审美世界,以审美来超越现代性的侵蚀。具体到冯娜的诗歌,首先是“个人记忆申述”,这主要体现在前述的纪游诗篇中,因为它们都涉及作者个人生活的内容。根据保罗·唐纳顿,所谓的“个人记忆申述”是指“那些把个人生活史作为对象的记忆类型”[13]。诗题中诸如“过”“逢”“到”“宿”“行”“驻”“憩”“访”“上”“在”“途中”等“动词”,虽不无抒情主体当下的此时此刻性,但更多的是个人借此对过往物事的追忆建构,这种追忆经过主体的沉思而有所选择,形成某种文化过滤。同时,这些“动词”的后面,多是“场所”,譬如城市、自然景观、人文遗迹、庙宇、博物馆等地点与建筑,它们成为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所谓的“记忆之场”[14]。历史记忆就是通过这些记忆存储之场所唤起的。“虽然意象具有引起回忆的力量,但是它们仍依赖词语为它们提供意义,这是因为在意象和对它的解释之间需要建立起一种联系。一旦这种联系被建立,并且被可靠地复制,‘意象就承担了路标的功能,指导着那些通过最快捷的途径记住首选意义的人’。”[15]准此,诗作所建构起来的审美空间,并非抒情主体所目遇的所有的自然图景,它们已烙上了抒情主体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旨趣。冯娜相关诗作多出现诸如:梦见、听说/听人说/说起、据说、想念、猜想、回味、记得/不记得/一定记得、曾与我说、印象中、忆旧录、记忆、目击、目睹等关键词汇,成为记忆唤起的开关,开启抒情主体进入想象虚构的艺术空间,也引导着回忆联想,领会其中的审美意蕴。“这种追忆中重要的不仅是那些已经写出的情思,而是那些不曾写出或难以写出的隐秘心思与隐约闪动的痛楚,这构成了作家完整的世界。”[16]
其次,历史文化记忆的发明。如果说“个人记忆申述”着眼个体私人性,与个人生活的内容密切相关,那么历史文化记忆的发明则凸显集体公共性,更强调其与集体、民族、传说、故事等宏大历史文化事件或著名人物的内在纠缠。可以看到,在审视历史、反思文化记忆的那些诗篇中,譬如《深夜读史》《端午祭屈子》《大地丰沛如容器》《江山或美人的侧影》《雷峰塔》《白蛇》《龟兹古国》《玲珑塔》《在博物馆拍摄一幅壁画》《石像》《回声》《猎户座》《木碗》《白雪楼》《博物馆之旅》《赝品》《赝品博物馆》《我的亚历山大》《衡水湖与荷尔德林》[17]等中,也是经由中外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文化人物、历史文化遗迹、艺术作品、文化传统等,物、人与事相互交织缠绕,营造出一个充满想象力、虚构性的诗学空间。
譬如《壁画》:
我不是着迷于那些壁画/而是着迷于那些古代的马、黛色的山/如何在人们心里复活//吞吃草叶的响动,也是此刻的空气/跑马的响鼻,拂到了人群中感到悲伤的一个/数百年无法折拢的线条/好似生活的艰辛//我不是着迷于飞天的凌空之姿/而愿意委身于一面兽皮的圆鼓/拍打它的人,不必知道我的来历/它回声嗡嗡,被汗水浸湿/我也曾猎捕、也被捕获/我跟随着人们的痛苦和享乐//人们也不是着迷于复活/而是从其他事物中感到了生命/除却繁星的赞颂/除却铭文的安慰/跟沉在心底的那口泥潭,一样深
抒情主体观看壁画,以壁画作为载体,溯游而上,展开跨时空的个人化历史想象。诗作通过“我不是着迷于……而是着迷于/委身于……”的重复修辞,让人由壁画及画中的马、山和飞天,联想到其他鲜活的生命,一幅壁画即是一幅美丽的画卷,一个美丽的王国,更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指出:“纪念地的特点是由非连续性,也就是通过一个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显著差别来标明的。在纪念地那里某段历史恰恰不是继续下去了,而是或多或少地被强力中断了。这中断的历史在废墟和残留物中获得了它的物质形式,这些废墟和残留物作为陌生的存留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18]壁画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就是这样的“废墟和残留物”,作为路标引导人们探故寻根或遐想联翩。
《甲骨文》或许更能体现这种“通过一个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显著差别”:
从一个字里看见山峦,从一个字里看见太阳/泉水自殷商的额头汩汩而出/王室的卜辞,曾向一座不会老的城池托梦//梦里,我和我的故国都已三千岁/我要向后来者,讲述山的威仪海的潮向/我要镌刻一颗星的沉落,在重复的黎明身后/用不朽的笔触,我描摹自己的鹤发童颜//每一块甲骨就是一个誓约/不尽的黄昏走过来,托付它们的年轻/时间书写着它的生命——/在黑暗的征战与埋葬当中/在重见天日的世代/在一页新的复活里,我默捻着深深的刻痕://那就是明月,那就是照耀/那就是殷墟中无数的我/还在匆忙地写就,转瞬即逝的命运
《甲骨文》对于历史文化的追忆模式更为凸显。甲骨文是抒情主体所要咏叹之物象,也是其言说的重要意象,这物象里存在着丰富的、不确定的历史文化缝隙,这恰恰成为诗人驰骋想象力、历史能力和书写能力的审美空间。不难发现,遗存之物的甲骨、梦里的甲骨、眼下的甲骨和抒情主体“我”想象中的甲骨等形成心理错综,眼前观看、托梦过去和想象未来的时空穿梭错置,回环往复,托物言志,借此填补弥合扩展历史的缝隙。诗作通过“看”“托梦”“讲述”“镌刻”“描摹”“默捻”“写就”等几个动词来完成这种效果,每一块甲骨都是一段丰富的历史,一个生动的生命,“那就是殷墟中无数的我”,让人不知甲骨是殷商,还是我,我是甲骨还是殷商,他们都是但也都不是。在历史长河里,这就是命运:甲骨的、殷墟的,你的、我的,即人类共通的命运与情感。
冯娜独特的纪游诗和历史文化记忆的诗篇,因其交织在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时空中,充满丰富的历史想象力和审美的可能性。综合前述的地方性知识或出生地及纪游诗篇来看,冯娜诗歌的地方无疑是复数多样的,从地方出发又超越地方。冯娜的诗歌空间呈现了地方空间、城市空间、异域空间、个体空间与身体空间等多种形式,揭橥社会想象、历史文化想象、存在想象和主体想象等多种审美图景,使其由一己之“恋地情结”转为寓言化的复数地方或时代的普遍性地方。“冯娜的诗中书写了不同文化与区域的地域景观,地域景观架构起诗人隐秘的精神空间,它们不仅是‘风景’,还承载浓缩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记忆、想象、认同,传达了人伦亲情以及主体的生命感、依附感与归属感。”[19]霍俊明也将冯娜的诗歌主要分为彼此区隔又相通的四个空间,出生地、南方、北方和精神生活的空间。“从空间角度来说,冯娜的诗歌是有具体指向的,但是反过来看这些空间实际上是互相穿连、交织起来的。它们一起呈现出来恰好又是彼此关联而又相互分开,呈现了现代性经验的复杂性与可变性。”[20]
三、心灵的镜像
诗歌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来表达或隐藏作者的真切想法,而读者(批评主体)则通过诗人提供的语言词汇等方式来揣摩解释这种表达出来或隐藏起来的微言大义。“一个读诗的人,误会着写作者的心意/他们在各自的黑暗中,摸索着世界的开关。”(《诗歌献给谁人》)对于冯娜而言,诗歌是一项令自我心安的事业,借此来抵抗因时间流逝而掷下生命、情感的巨大虚空。用冯娜自己的话,“诗歌就是我与这个世界的亲近和隔膜。我用语言诉说它们,也许我始终无法进入它们的心脏,哪怕融入它们的心脏,可能又会觉得无言处才最心安。”[21]从《云上的夜晚》(2009)到《寻鹤》(2013)《无数灯火选中的夜》(2016),再到《是什么让海水更蓝》(2020)《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2020),我们不难发现冯娜诗歌的抒情声音由激情青涩而笃定宁静,由芜杂繁复而清通省净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有人生阅历的持续积淀,也有诗歌书写的语言自觉,更有诗歌观念/心灵镜像的自我省思。“近年来,我将目光投向这些情感记忆在现实中的际遇、在人类命运中的共鸣、在时间中的恒定和变幻,试图获得一种更新的、富有洞察力和穿透力的眼光。”[22]这种自觉的诗歌意识主要表现在一系列所谓的“元诗”上。所谓“元诗”,是指“以诗论诗”。《诗歌献给谁人》《劳作》《词语》《寻鹤》《出生地》《猎户座》等为代表,而《雪的意志》《杏树》《地址》《给孩子们读诗》《祈祷》《歌者》《秩序》《一种声音》等都可作如是观。这至少可从以下两点说明。
其一,诗即手艺或劳作。张桃洲认为,“中国当代诗人写作和谈论中频繁出现的‘手艺’,主要沿着两个向度构建意义和汲取资源:一是回归诗歌作为‘手艺’的工匠性质和其所包含的艰辛劳作,一是突出诗歌之‘技艺’的诗性‘拯救’维度。”[23]冯娜在《劳作》中说到:“我并不比一个农夫更适合做一个诗人/他赶马走过江边,抬头看云预感江水的体温/我向他询问五百里外山林的成色/他用一个寓言为我指点迷津。”在此,诗人与农夫联系在一起,诗人以文字指点江山,农夫抬头看云预感江水的体温或用寓言指点迷津,他们共同之处在于“长年累月的劳作所得”。“诗人也如农夫,在属于自己的领土上耕作,试图说出时代的寓言。”[24]这一方面强调了诗人写诗经验的获取在于艰苦劳作的积累,另一方面突出了诗人作诗与农夫一样凭借经验,熟能生巧,自然而然。前者凸显艰苦,后者着意乐趣。“如何辨认一只斑鸠在鸽群里呢/不看羽毛也不用听它的叫声/他说,我们就是知道/——这是长年累月的劳作所得。”其实,在冯娜的相关诗作中,多次出现“手艺/技艺”,尽管不尽是对作诗的隐喻,但其都犹如农夫甚至蚂蚁或蜜蜂的劳作一样,“教会我一种关于诗歌的技艺”[25]。如《一首诗》:“我,一个冷僻技艺的研习者。”《回旋曲》:“偶尔,我们会做一些平日里想不起的事/动身去一个陌生之地或学习一门冷僻的手艺。”《诗歌献给谁人》:“冬天伐木,需要另一人拉紧绳索/精妙绝伦的手艺/将一些树木制成船只,另一些要盛满饭食、井水、骨灰。”《寄北》:“手艺人有时带来奇妙的新把戏/我尾随他,看见作坊里人们正把日子一点点用旧。”《棉花》:“壁画中的驯鹿人,赤脚走在盐碱地/只为习得那抽丝剥茧的技艺。”《杏树》:“我跟随杏树,学习扦插的技艺/慢慢在胸腔里点火。”《出生地》:“他们教会我一些技艺,/是为了让我终生不去使用它们。”《魔术》:“故事已经足够/我不再打算学习那些从来没有学会过的技艺。”《苔藓》:“需要依托梦来完成的生活,覆着一层薄冰/人们相互教导噤声的技艺。”《极光》:“如果睡眠是一种祈祷,我一定不够虔诚/如果白昼是一门手艺,人们都还是学徒。”不管是已习得的技艺,或者是不再打算学习那些从来没有学会过的技艺,又或者是噤声的技艺,它们都成为手艺人/准手艺人的命运,也隐喻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在社会交互性极强、信息传播异常发达的时代,诗人的劳作或手艺似乎变得更加艰难。在技术猛进而经验贫乏的时代,精雕细琢、经验积累式的劳作方式,显得弥足珍贵,但又似西西弗斯手中的巨石,如此悲壮,如此欢乐。“任何一种诗歌观念或写法都有可能会随着历史情境的变化而变得不再重要(丧失适应性),但技艺的积累对诗歌及其母语来说却是永远有益的,因为这是语言在表现和言说事物方面的能力的拓展。”[26]
其二,诗人的尊严和荣光。正是因为诗即手艺或劳作,在于经验、情感、记忆的积累与传承,才赋予诗人独特的使命、职责或命运。于是,何为诗人,诗人何为,成为冯娜及其诗歌的中心关怀。譬如《赝品博物馆》:“——他们能理解一个诗人、一个相信炼金术的后代/还能通过肉眼甄别瓷器上的釉彩/我们拥有相同的、模糊的、裸露的时间,和忍耐/也许,还拥有过相同的、精妙的、幽闭的心事。”面对消逝在时间长河中的器物之心事,作为炼金术士的诗人,甄别它们,抚摸它们,理解它们。《秘密生活》:“当你说起古老国度历经的苦难/我走在那属于你 却早已荒芜的矿区/——你并不知道/这里依旧盛产珍贵的石油/在你百年前的诗人,说出过你的秘密。”在此,诗人说出苦难,也铭刻苦难。《雪的意志》:“我不是藏人,我是一个诗人/我和藏人一样在雪里打滚,在雪里找到上山的路/我相信的命运,经常与我擦肩而过/我不相信的事物从未紧紧拥抱过我。”在此诗人不是神秘的,而是活生生的,她与万物的命运一样。《孩子们替我吹蜡烛》:“关于时间,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他们真的创造了新的时钟/作为他们的同行/我,一个诗人,/会继续请孩子们替我吹蜡烛。”在此,诗人是敌时间的人。《盲音》:“人们仍在建筑,在下落不明的城镇/码头仍在打捞,在匿名者的故乡/那无知者的迷途吞吐着昼夜/从不隐没也无新生/啊,千百年都是这样/作为一个诗人,我放弃了结局/作为一个女人,我理应悲伤。”《来自非洲的明信片》:“我们啊,终生被想象奴役的人/因一个地名而付出巨大热忱/因一群驼队的阴影而亮出歌声/会把遥远非洲的风视为亲信/因在沙漠上写字,把自己视为诗人。”《云计算》:“怎样运算一个人内心粗糙的颗粒/等同于多少截流的大坝、崩溃的雪线、含泪的夜莺……/一个诗人,怎样用有限的 汉语清点/——留给孩子们的遗产。”面对残酷的现实社会万象,冯娜用独特的声音对“诗人何为,诗歌何为”做出回答。冯娜言述:“诗人就是要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我与她那般短暂的相遇、我们那些无意识复制的日常生活、有意识的内心渴望。还有我与她都可能未曾觉察的人类共通的命运与情感。”“诗人的工作便是去建立连接‘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桥梁。诗人的工具——语言,则是我们在审视和甄别时代的趣味之后的心灵镜像。”[27]不管时代如何变幻,社会万象如何复杂,超越人们语言和想象力,诗人只要牢牢扎根这片土地、这颗星球,仰望浩渺宇宙,就会获得安宁和“人类存在的实证”,获得诗人的尊严和荣光。有勇气与时代、社会、心灵展开对话,就在速朽的时代诗人也大有可为,她给人温度、光亮和生命的尊严,让存在获得自我的确证。在冯娜看来,写诗就是一种修行,“与其说是我选择了诗歌这种方式,不如说是诗歌选择了我”,诗歌与诗人相互选择,相互生成。
进而言之,对冯娜而言,诗人是努力寻找词根的人,她不断地向内挖掘、反思、审视和期冀,自内及外,由小见大。里尔克有诗说到:“沉默吧。谁在内心保持沉默,/谁就触到了言说之根。”只要触到“言说之根”,其诗思才敞开。当然,冯娜也曾恐惧过,因为“我摸不到的,我摸到而感觉不到的/我感觉到,而摸不到的”(《恐惧》);也曾疑惑过,“所有许诺说要来看我的男人 都半途而废/所有默默向别处迁徙的女人 都不期而至/我动念弃绝你们的言辞 相信你们的足履/迢迢星河 一个人怀抱一个宇宙/装在瓶子里的水摇荡成一个又一个大海/在陆地上往来的人都告诉我,世界上所有水都相通”(《疑惑》);也在不断寻找,“黄昏轻易纵容了辽阔/我等待着鹤群从他的袍袖中飞起/我祈愿天空落下另一个我/她有狭窄的脸庞 瘦细的脚踝/与养鹤人相爱 厌弃 痴缠/四野茫茫 她有一百零八种躲藏的途径/养鹤人只需一种寻找的方法:/在巴音布鲁克/被他抚摸过的鹤 都必将在夜里归巢”(《寻鹤》)。此诗意象丰富,意境辽阔,语言陌生新奇,构建出一个具有层次感的审美空间。养鹤人寻鹤即驯鹤,也是鹤寻养鹤人,或者“我”寻“另一个我”。但我更愿意认为,这是诗人寻找属于自己的词根之隐喻,纵然词根“有一百零八种躲藏的途径”,但诗人“只需一种寻找的方法”,那就是被诗人“抚摸过”的词根,“都必将在夜里归巢”。所谓“抚摸”恰恰是前述的写诗即手艺或劳作。或许《词语》才更好地体现冯娜努力寻找词根的姿态,“在词中跋涉”“艰难地贴近事物的姿态”(王家新语)。此诗中这样说到:“我看不见你的藏身之所/——词语铺满砂砾的巢穴/一座巨大的记忆仓库。”“我看不见你 当你露出了词语一样的样貌/词语上微蜷的毛发/指腹的螺/——它们创造了新的词汇/精准的秒针/我拥有钟摆的相同频率和不同的年代/在童年的玻璃碎渣里我感到了——/时间/它像一个又一个词语叠加而成的迷宫。”“现在,我把词语放在耳朵上、膝盖上/它们理解衰老和冗长的命运/——多么好,当我不在这里/你依然能看到我,在词语周围。”仿佛记忆仓库的词语,它躲藏,显露,发出清响,创造,也命名,昭示语言的神力,“语言乃是家园,我们依靠不断穿越此家园而到达所是”(海德格尔语)。诗人寻找词语,而词语却在我们的记忆里,在自然的悸动中,就在我们的周围。这首诗书写了诗人寻找词语/根的迷惑困顿、心领神会和创造的喜悦。吴晓东在《王家新论》中指认王家新是寻找词根的诗人:“可以把‘在词中跋涉’的王家新喻为‘寻找词根’的诗人,这‘词根’构成的是诗歌语言与诗人生命存在的双重支撑。对‘词根’的执著寻找因而给王家新的诗歌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隐喻的深度,思想的深度,生命的深度与历史的深度。”[28]诚然,冯娜的诗歌写作有自己的质地成色,也有清晰可辨度的抒情声音,并在寻找属于自己词根的途中,辩证地调校“诗歌语言与诗人生命存在的双重支撑”,以此形塑一己诗歌美学的广度、深度和厚度。
诗人冯娜,兼事小说、散文随笔、翻译及文学评论,甚至对《诗经》《宋词》等植物有独特研究,游刃于几度空间,多元文化身份自由转换,又相互滋养,相互定义,相互发明,使其成为当代文坛年轻一代写作者中的佼佼者。冯娜的诗歌得到业界如谢冕、吴思敬、谢有顺、孙晓娅、蒋登科、霍俊明、张立群、刘波、卢桢、陈培浩、唐诗人等众多评论家的认可。同时也获得了来自各方的嘉奖与肯定,如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华文青年诗人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花地文学奖、美国The Pushucart Prize提名奖等,参加第29届青春诗会、首都师范大学第12届驻校诗人等。在实用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在纯文学接受不景气甚或式微、诗歌泛滥的情势下,冯娜的写作在传统文学的评价机制中,获得了最大善意的阐释与解读空间。质言之,冯娜的诗心宁静沉潜,诗意蓬勃盎然,诗语干净利落,诗味隽永遥深,诗风雍容自若,自成一派,不属于任何诗歌团体流派,是最可期待的。
[注释]
[1][22]冯娜、王威廉:《诗歌与生命的“驭风术”——冯娜访谈》,《山花》,2014年第9期(下半月)。
[2]在此,“地方性知识”,指吉尔兹《地方性知识》所谓的一种具有本体地位的知识,来自当地文化的自然而然的、固有的东西,也指段义孚《恋地情结》所谓的“地方”(place),它包含两个基本内容:一是感受(feeling),二是意义(meaning)。因此,“地方”含有感受和价值,它与我们行为的关系密切相关。
[3][美]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页。
[4][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7页。
[5][10]张柠:《从边地到词语中央》,载冯娜《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第6页。
[6]唐诗人:《冯娜诗歌的精神地理学考察》,《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7][8]谢有顺:《生命的探问与领会——谈谈冯娜的诗》,《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9]冯娜:《云上的夜晚》,载冯娜《云上的夜晚》后记,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11]林馥娜:《这眼中火苗的来路》,载《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冯娜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2016年,第41页。
[12][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页。
[13][美]保罗·唐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14][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皮埃尔·诺拉指出:“记忆之场”一开始便意味着两个层面的现实的交叉:一种现实是可触及、可感知的,有时是物质的,有时物质性不那么明显,它扎根于空间、时间、语言和传统里;另一种现实则是承载着一段历史的纯粹象征化的现实。见皮埃尔·诺拉《如何书写法兰西历史》,载《记忆之场》,第76页。
[15]李宏图、王加丰选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7—158页。
[16]刘毅青:《古典追忆诗学的审美超越品格》,《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17]冯娜还有大量关于植物的诗篇,此或可称之为“新咏物诗”,可将《颜如舜华——诗经植物记》《唯有梅花似故人——宋词植物记》等合而观之。限于篇幅,有待另文处理。
[18][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6页。
[19]孙晓娅:《地域景观:穿透生活的一个视角——评冯娜的诗》,《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3期。
[20]霍俊明:《黄昏中摁下世界的开关》,载冯娜《无数灯火选中的夜》,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21]冯娜:《我与世界的亲近和隔膜》,《中国诗歌》,2010年第9期。
[23]张桃洲:《诗人的“手艺”——一个当代诗学观念的谱系》,《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
[24][25][27]冯娜:《劳作》,《是什么让海水更蓝》后记,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98页、第195页、第195—197页。
[26]王凌云:《比喻的进化:中国新诗的技艺线索》,《江汉学术》,2014年第1期。
[28]吴晓东:《王家新论》,《二十世纪的诗心:中国新诗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